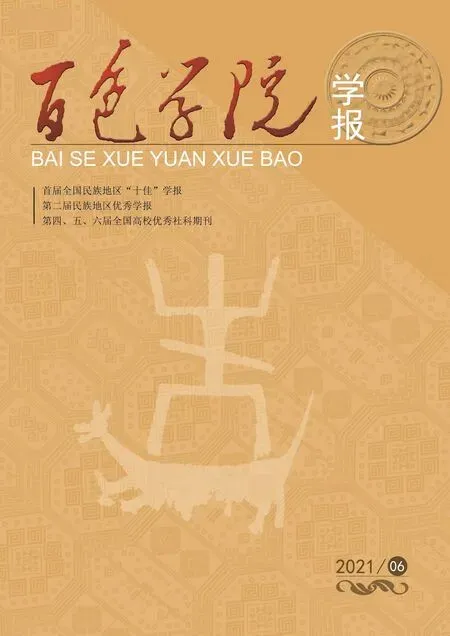文本形式翻译初探
2022-01-18周秀苗祝远德
周秀苗,祝远德
(1.百色学院,广西百色 533099;2.广西大学,广西南宁 530004)
一、形式翻译与内容翻译之历史视觉
在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对于形式翻译,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把翻译的内容与形式割裂开来,片面强调内容(或者说意义)的重要性,把形式看作次要的甚至是无关紧要的。二是认为既然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就没有必要专门研究形式翻译,而是在研究内容翻译的同时,顺便研究一下就足够了。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是有失偏颇的。
(一)形式翻译之西方视觉
语言的形式与意义相当于一个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两者之间的关系密切到有些人想当然的认为没有必要专门论述形式翻译。早在人文主义运动之始,著名诗人但丁就认为诗歌是不可以翻译的,因为诗歌一经翻译,原文的“韵味与和谐就会丧失掉”[1](P21)。西塞罗在谈到其翻译希腊演说家的演说词也把形式与意义看成必须翻译的东西,“我不是以译者的身份去翻译,而是以演说家的身份翻译的,保留与原作一样的思想和形式,或者说,保留了‘思想的比喻’……我不认为有必要逐字逐句翻译,而是保留了原作语言总体风格和气势”[2](P157)。思想往往是由有意义的词语组合来表达而不是由单个单词表达的,有意义的词语组合本身就是语言的一种形式,所以西塞罗才会如此重视形式,达到了与思想并重的地步。此外,要强调“风格和气势(style and force)”,显然会涉及翻译的单位问题,西塞罗采取了“弃树观林”的方法,放弃个体单词,从总体上把握原文的意义。可见,西塞罗虽然没有具体讨论翻译的形式处置,但显然他对形式是有相当关注的。
第一个使用民族语言翻译《圣经》的马丁·路德归纳的三点翻译观点,其中的第三点是翻译技巧的归纳,归结为7个原则:(1)可以改变原文的词序;(2)可以合理运用语气助词;(3)可以增补必要的连词;(4)可以略去没有译文对等形式的原文词语;(5)可以用词组翻译单个的词;(6)可以把比喻用法译成非比喻用法,把非比喻用法译成比喻用法;(7)注意文字上的变异形式和解释的准确性。[3](P83)
虽然马丁·路德看似大多条目讨论的都是词语,但却主要讨论虚词而不是实词,跟语法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就是说,跟语言使用的结构有更大关系。语言的结构就是一种形式,虽然很少使用“形式”二字,实质上都在讨论形式。
无独有偶,法国18世纪著名翻译理论家巴托所提出的翻译六项规则,对原著形式的关注丝毫不比马丁·路德少,其翻译规则如下:(1)尽可能保留原作语序;(2)保留所表达意思的先后次序;(3)使用同样长度的句子;(4)再现连词;(5)避免意译;(6)必要时可对原著加以修正,但首先必须强调形式的对等。[3](P124)
显然,巴托是不认可意译的,因为他明确提出要“避免意译”。此外,他提倡保留原著的语序,保留所表达意思的先后次序,就是要保留原作的结构形式。有意思的是,他提出“使用同样长度的句子”,已经是涉及翻译的视觉形式的处置问题了。要知道,巴托当时所讨论的翻译,基本上局限于欧洲国家之间语言的翻译,均属于表音类字母为基础的语言,原作与译文之间句子长度的一致性,视觉形式的相似在其中占有重要比重。
20世纪中后期,文化翻译研究派创始人霍姆斯所提出的四种翻译类型的头一种就跟形式有关,“形式相似,尽管完全一样的形式不可能,相似的形式却是可能的”[4](P56)。虽然他声称四种翻译类型同样重要,但排列在第一位,无论如何都能够说明其重要性。译文与原文形式不可能完全一样,是当代翻译理论研究的一个共识,是建立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交流日益扩大、日益频繁事实基础上的共识。既然不可能完全一致,那么对翻译形式进行适当的处置就显得顺理成章了。而且,两种语言的差距越大,形式的处置就越是重要。
(二)形式翻译之中国视觉
其实,中国古代翻译界曾经长期存在的“文、质”之争,也与形式处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谓“文”,就是在译文中对原文字面翻译过来的文字进行润色,使之显得更加有文采、读起来更顺畅;反之,“质”则强调保持原文的形式和字面上的意义,不宜轻易改动。“文、质”之争来源于翻译实践的理念分歧。佛经翻译构成了中国古代翻译最重要部分,宗教文献的翻译与信仰有关,最初的翻译者因为对宗教虔诚的缘故,对原文形式和意义的处理总是小心翼翼,译文往往亦步亦趋,不敢越雷池半步。中国古代佛经翻译如此,西方希腊七十二子翻译的圣经《旧约全书》亦如此。然而,因为汉语与梵文之间的语言差别太大,无论如何语言形式都势必要有所改变。释道安的“三不易五失本”就是对当时翻译难题的总结:
译梵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梵语尽倒而从秦,一失本也。二、梵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适合)众心,非文不可,斯二失本也。三者,梵语委悉(原原本本,十分详细),至于叹咏(指颂文),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梵有义说(梵本在长行后,另有偈颂复述长行,称为义说),正似乱辞(中国韵文最后总结的韵语),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划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5](P37)
可以看出,释道安总结的五失本几乎都与形式处置有关,头一条是语序的处置,属于语法范畴;第二条虽然主要属于词义与翻译方法问题,却与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区分有异曲同工之妙;至于第三到第五条,都与对原文的删减有关系,是因为原文在不同语境中重复出现其原先出现过的内容,所以其形式没有必要在译文中保留,都属于形式处置范畴。至于现代中国翻译理论,无论是林纾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还是瞿秋白的“对等”,其背后都可以见到翻译形式处置的影子。许渊冲的“三美”说(音美、形美、意美),更是直接把“形美”作为不可或缺的诗歌翻译原则之一。最近比较看重形式在翻译中地位的是李长栓,在其翻译毛泽东诗词的时候,是非常注重贴近原作的形式的。王东风“以逗代步”的实践,也不失为翻译形式处置的一种尝试。
二、文本结构与形式翻译
从上文可以看出,文本的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割的,很多研究都会在研究内容翻译的同时涉及形式的处置。但是,这些对形式翻译的关注或者研究,主要是将语义翻译作为主体而言的,一旦涉及两者的先后顺序,大多会把形式翻译排在内容之后,甚至有可能显示为“内容显现之际,就是形式隐身之时”[6](P106)。形式翻译研究,就是要为形式翻译正名,探索其不依赖于内容或其他主题、以其本身存在意义的研究。也就是说,把形式翻译作为研究主要对象,将之作为研究的中心和出发点,重点探索一些只有从形式入手才便于研究的课题。
(一)文本体裁与形式翻译
首先是文体的转换。里奇和索特(Geoffrey N.Leech,Michael H.Short)很明确地说,“文体是语言使用的方式”[7](P38),文体的转换就是语言使用方式的转换。一般的共识是,文体在翻译中需与原文保持一致,以诗译诗、以散文译散文,第一人称叙述的,译文中也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书信体还保持书信体的形式等。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比如诗歌与散文体裁之间的转换,叙述人称的变换。如果有例外,这种例外有没有其他条件附加到文本翻译中去?
就文本体裁本身而言,能够对视觉产生较大影响的只有两种反差较大的结构形式:以行为单位的诗歌体裁和以段落为单位的散文体裁。这与英语中的体裁划分是一致的,即分别为poetry和prose。就形式翻译而言,就是坚持“以诗译诗”原则,还是在某种条件下把诗歌形式翻译为散文形式的问题。大体而言,“以诗译诗”是普遍原则,但在一定条件下,把诗歌形式处理为散文形式也不乏成功的例子。在国外显然有把诗歌形式翻译为散文形式的例子。马修·阿诺尔德(Mathew Arnold)举了莎士比亚戏剧和歌德的《浮士德》翻译为例,声称他“宁愿读散文体的法语莎士比亚译本”[8](P253)。
其实,即使都属于“以诗译诗”的倡导者,其程度也是有区别的。在理论研究和翻译实践中,大体上有三种不同的处置方法。一种是“亦步亦趋”处置,译文与原文的形式相似度最高,卞之琳是这种方法的主要倡导人;另一种是做法是强调“神韵”的翻译,形式则可以灵活处理。在国内以郭沫若、胡适、翁显良等人为主要倡导者,在国外则有庞德(Ezra Pound)、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等人,前者曾经翻译不少中国古诗,后者为著名的《鲁拜集》的英文译者。介于二者之间的处置方法是大体上忠实于原作形式条件下有限的灵活性,这种方法以许渊冲为代表。与庞德等人相比较,许渊冲算得上相当忠实于原文形式了,很少有看到他的翻译会把一行诗歌成两行,或者把两行以上诗歌翻译为一行的情况。
莎士比亚戏剧是用五步抑扬格的无韵诗体裁写成的,就中文版的莎士比亚戏剧而言,虽然有不少译本,但到目前为止,朱生豪版莎士比亚戏剧是最受欢迎的版本,而朱生豪就是以散文体的形式翻译莎士比亚无韵诗体裁戏剧的。也就是说,就戏剧翻译而言,“以诗译诗”的原则是可以打破的。因为戏剧虽然是语言艺术的一种,但与一般的叙事诗和抒情诗不同,戏剧还是一种表演艺术,在语言使用之外增加了现场表演的因素,其中的语言实际上是以对话为主。
戏剧表演虽然舞台化,但欣赏者却往往会将戏剧与现实联系起来,追求一种真实感。如此一来,如果开口闭口都是诗歌形式,反而会让观众觉得“不真实”,而以散文体裁为主的对白更容易让人接受。比如说,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为了表示他报复安东尼奥的决心,对巴萨尼奥双倍偿还债务的提议不屑一顾:
If every ducat in six thousand ducats
Were in six parts and every part a ducat,
I would not draw them.I would have my bond
如果一定要把上文翻译为五步抑扬格无韵诗体裁,听起来肯定有些不舒服。朱生豪的译文就没有拘泥于原文的形式:
即使这六千块钱中间的每一块钱都可以分做六份,每一份都可以变成一块钱,我也不要它们;我只要照约处罚。[10](P146)
(二)叙事人称与形式翻译
叙事人称的改变也是有先例的,曾经轰动一时的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就是把原文的第一人称叙事改为第三人称叙事。当然,在封建社会末期刚刚引进西方文学的历史背景下,这种翻译手法能够成功是可以理解的。但时至今日,如果还有人以同样的方式处置原文的形式,恐怕就不会有出版社愿意为其出版了。所以,此类例子不足为训。
以散文体翻译韵文体或者诗歌体,一般属于单行道,鲜少有看到把散文体裁的文本翻译为诗歌体裁文本的。唯一看到的例外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给基辛格的赠言,由散文体被翻译为四言体裁:
To Henry Kissinger,
For whose wise counsel and dedicated services far beyond the call of duty I shall always remain grateful.
From his friend Richard Nixon
上述赠言可以被翻译成四言体的中文条幅:
赠言亨利·基辛格:
善进良策,献身尔职;逾于所司,永志不渝。
你的朋友理查德·尼克松①引自道客巴巴平台用户ustt075于2015年1月4日上传的“第6讲 词语的翻译(3)”,网址为https://www.doc88.com/p-9572604025626.html。
可以看出,就诗歌和散文体裁形式而言,以诗译诗、以散文翻译散文是比较公认的翻译原则,但以散文体翻译诗歌体裁还是不乏成功例子的。同时还可以发现,改变体裁形式的翻译方法是有条件的,即有文本以外的因素从中起作用。尼克松总统给基辛格博士的赠言,本来是以书信形式书写的,但是翻译为中文之后是作为条幅形式出现的。拉丁语系的文字以字母组合而成,文字本身的书法形式并没有形成一种广泛的艺术,文字作为艺术更多见于平面设计,比如logo设计、编辑设计等。作为logo,在翻译中通常会照搬原型而很少会翻译其中的文字。而编辑设计,也不像中国书法条幅那样被挂起来欣赏。汉语是象形文字,自古以来就是书画一体,把书法与国画同时作为供人欣赏的艺术,视觉美被提到艺术高度,尼克松给基辛格的赠言翻译,自然会受到中国书法习惯的影响。这只是极个别的个案,不足以作为把散文体裁诗歌化翻译的例证。
不过,还真有一种情况中英互译时需要改变人称的,那就是邀请函。中国传统请帖比较繁琐,如今基本上都已经简化了。简化后的中文邀请函有点像书信格式,举例如下:
约翰班德尔教授:
兹定于2021年7月12日下午6点整在龙泉饭店第一宴会大厅举行中国比较文学2021国际论坛招待晚宴,敬请光临。
着装:正式 敬请回示
中国比较文学2021国际论坛组委会
中文的请柬有点像信函的格式,抬头的是被邀请人姓名及称谓,然后是内容,最后落款是邀请人,而与汉语请柬相对应的英文文本却应该是如下的格式: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of Chinese Comparative Literature 2021 International Forum requests the pleasure of Prof.John Bandle to be present at the reception banquet at 6 p.m,July 12,2021,in the No.1 Banquet Hall of Longquan Restaurant.
Dress:formal RSVP
可以看到,英文正式请柬的格式是以邀请人作为主语,却以第三人称邀请的。格式中没有抬头,也没有落款。当然,着装要求和回帖要求还是有的。RSVP是法语Repondez s’il vous plait的首字母缩写,直译是“如果你高兴,请回复”,但前半部分显然只是客套,“请回复”才是真正的要求。正式的回帖与请帖的格式需一致,英语中也是以第三人称作主语写成的。
(三)文本视觉形象与形式翻译
其次是文本式样处置。有些文本,特别是诗歌文本,除了作为诗歌特点的样式外,可能会显示出特殊的视觉形象样式,此类诗歌在翻译过程中应该怎样处置呢?
有的诗人会运用视觉效果,把诗歌写成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形式,比如逐行增加字数的金字塔形式,或者逐步减少字数的倒金字塔形式等。其中最有特点的要算美国的先锋派诗人E.E.Cummings。他的一首“l(a leaf falls)one l iness”(图1)吸引不少人眼球,其排列为下拉形式:
整个诗歌就是a leaf falls,loneliness(一片叶子飘落,寂寞)。诗中的loneliness中间用括号括住了a leaf falls,而且leaf分开写成le和af,falls则分成了fa、ll、和s,加上曲线形排列,创造出一种树叶不急不缓飘然掉落的视觉效果。loneliness则被分成了括号外的l,和括号另一边的one+l+iness。one可以表示任意一个人,l既是英语字母L的小写形式,也是阿拉伯数字“1”,可以看作是”one”的异体形式,就是说,也可以理解为“one”这个人的影子,以此创造出一种形单影只的视觉效果。英语ness是一种后缀,加上后可以让一个形容词名词化,即形容词的实体性实现。可是在诗歌中其前只有一个i,却不能构成任何有意义的词语,即i不能实现。把l抽出,建构出一幅形单影只的人,看着一片树叶不急不慢地飘然而下,虽是实景,诗人却偏偏将之放在了括号中。这样处理的目的是要把实景虚化、抽象化,以便让读者能够代入非限定性人称one的位置,在艺术形象中体会loneliness的感受。在英语中,i即自我,自我不能实现,却孑然一身看着树叶无可奈何的飘零,应该是寂寞的极致了。
其实,这首诗的排列方式是一位外教当年讲课的时候写在黑板上的,如今印刷出来的排列方式,是把“one l iness”排在“s)”的下方,排成一个竖行,且没有错落的排法,一个竖行直排到底,完全丧失了应有的视觉冲击力。这样排列的原因不得而知,也许是因为编辑毕竟不是诗人或者文学研究人员,缺乏对诗歌意象的了解,加上直接排列一个竖行比较方便,就传了下来。
这首诗,网上的一个译本将之翻译为图2①引自豆瓣平台用户谁是派大星于2015年9月8日上传的“翻译e.e.cummings的一首小诗”,网址为https://www.douban.com/note/516058852/。。这一版本的翻译,已经注意到形式翻译层面,且把翻译的几个词也排列为树叶飘落的形状,但这只能够说是初步的尝试而已。首先,形式的数量不对等。原文把文字拆分,一共分成了9个单位外加括号,译文只有5个单位,且没有括号。其次,原文中的字母l加上括号外的组合,组成一个单词loneliness,译文中的“宀”加上后面任何一个字都不构成一个完整的汉字。原文中抽出了字母l,营造出“寂寞”的形象概念,而此概念正是加上字母l所构成的loneliness的词义所指,译文却无法构成词义上的概念,因而无法营造出相同或者相似的形象和意境。再次,原文中树叶(leaf)和落下(falls)都把文字拆分为字母组合,给人一种树叶飘零的恍惚感觉,译文没有文字的拆分,同样无法营造出相同的艺术体验。所以,我们尝试将这首诗翻译如图3。

图2

图3
和原诗一样,我们的译本同样分成了9个单位,其中最后的两个字与iness一样只算一个单位,因为二者都没有因为其组合起来构成人们广泛认可词义的词语,而分开解释反而别有妙处:原诗中属于自我无法实现的孤寂感,译文中的“叔”可以代表亲人和社会关系,而后面加上的“莫”却有“无”的意义,合起来解释就是亲人朋友、社会关系都虚无化,把抽出来的“宀”加到“叔莫”上,就诠释出诗歌的“寂寞”意境。与原诗一样,译文把“叶”字拆分为“口”和“十”;把“飘”字拆分为“票”和“风”,通过曲线排列,营造出一片叶子从树上缓缓飘落的视觉形象。译文同样以括号加在“一叶飘落”的两边,把实景形象虚化,以便将之抽象化,变为人人都可能遇到的境遇。“孑”字与“子”字有着天然的联系,与one一样可以代表任何个人。最终下来,撇开视觉形象之外,译文可以读作“一叶飘落,孑然寂寞”,或者再扩展一点,成为“一叶飘零落,孑然空寂寞”也未尝不可。
汉语是象形文字,文字本身就可以成为很好的视觉形象。当然,经过无数岁月的发展,不懂中文的人理解汉语文字的视觉形象还是比较困难的。汉语诗歌其实也可以通过文字的组合排列营造出视觉形象。比如,宋朝文豪苏东坡收到词人秦观的十四字诗“赏花归去马如飞酒力微醒时已暮”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首流水循环诗,一波波循环,每个字使用两次,就变成了一首七绝诗: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酒力微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有好事者把这首诗做成一个圆形的视觉形象(图4)。我们没有查到这首诗的英译文本,我们只好提供自己的翻译版本:

图4
I return from flower-enjoying the horse goes flying from wine I feel suffering recovers towards the evening
我们也尝试做了一个视图式形象如图5:

图5
就视觉形象而言,译文的形象有点左轻右重,因为右边和上下大多是两个单词组成的词组,而左边则全部是单个单词,这是为了照顾I return和I feel的上下对称。好在这两个词组的对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左轻右重的不足,使得整个视觉形象独具韵味。
译文的字数比原文稍多了一点:原文是14个汉语单词,译文如果把连字符号联结的词算作一个单词,一共有17个,但其中有2个冠词the,还有2个介词from,扣除这几个虚词,真正算起来还是差不多的。以流水循环方式处理,从顶头往右读,经底部再往左回归,同样可以成为一首四行诗:
I return from flower-enjoying the horse goes flying,
The horse goes flying from wine I feel suffering,
I feel suffering recover towards the evening,
Towards the evening I return from flower-enjoying.
当然,就形式而言,译文还不是尽善尽美的。除了字数多少有些出入外,英语译文中的短语from wine和单词recover均只使用了一次,而不是像原文一样每个单词都重复了一次。而且,每一行的字数或音节数也不完全一致,字数从7个到9个不等,音节数从12个到15个不等。虽然有这些不完美,但总的来说是能够反映原文形式的,因为流水循环是原诗最有特色的形式,只要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说是成功的。其次,原诗是一种动态叙事,词人秦观叙述其赏花归来路上的动态,马的跑动、马上骑手的醉态,由醉到清醒的动态和天气由白天到傍晚的时间动态变化,重点都落在“动态”上,译文则以-ing为韵脚,用现在分词形式恰如其分地反映这种动态变化的叙事。当然,最后一行的意义与原文也有些出入。原诗中还可以理解为,词人酒醒后在回归的路上还在赏花,而译文则不包含这层意思。
其实,“流水循环式”是我们自己起的名字,因为整首诗就像流水,一波波往前推进,最后,诗歌的尾部又与开头衔接,构成一首七绝诗。
如果说“流水循环式”诗歌还可以按照其本来形式翻译,“流水回文式”诗歌(有人称为“连理回文诗”)则基本上无法再照顾到其原来的形式,除了将之按照四行诗歌处理,恐怕很难有其他办法,清朝女诗人吴绛雪的四季诗就是一个例子:
莺啼岸柳弄春晴夜月明;香莲碧水动风凉夏日长
秋江楚雁宿沙洲浅水流;红炉透碳炙寒风御隆冬
这四行十个字的诗歌,可以读出四首七绝诗,以第一行为例,可以读成:
莺啼岸柳弄春晴,柳弄春晴夜月明;
明月夜晴春弄柳,晴春弄柳岸啼莺。
可以看出,诗歌的读法是先读前七个字为第一句,然后读后七个字为第二句;第三句是反过来,把后七个字倒过来读,最后一句是把前七个字倒过来作为第四句。其读法与上面所说的“流水循环式”相似,只不过流水循环式最后是首尾衔接,而流水回文式则分为正读和反过来读两个部分而不是首尾衔接。四季诗的其他三行,也可以按照同样的方法,读出三首七绝诗,在此不再展开论述。
回文结构的修辞方式,中英文都有使用。由于汉语和英语的语系不同,二者的相似度太小,回文文本的翻译是非常困难的。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回文翻译令人眼睛一亮的,要数马红军对英语回文“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的中文版本:落败孤岛孤败落。[11](P66)原文的回文不是词语的回文,而是每一个字母相对应的回文,以字母R为中心,左右两边相同位置的字母都相同。Elba岛是拿破仑战败后被流放的孤岛,虽然他后来逃离出去,并且成功组织起一支军队,但很快就在滑铁卢遭到了灭顶之灾。可以说,Elba岛就是拿破仑的不祥之地。据说这一句回文表达了拿破仑的感慨:没见到Elba岛之前他是强大无敌的。
其实,由于汉语和英语的结构及言说方式之间的巨大差异,要把回文以本来的形式翻译出来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更倾向于认为马红军令人叫绝的翻译只是一个特例。译文的形式与原文高度相似,都是7个字,以“岛”为中心,左右两边相同位置的汉字都相同。差异只有一点,英文原文相对应的是字母,即构成英语单词的最小单位,而译文对应的是整个单词而不是偏旁部首,比如“败”字对应的仍然是“败”而不是反文加上“贝”,这纯粹是中英文构词方式不同使然,是没办法弥补的。译文反映了译者的水平和机敏,因为原文恰好是拿破仑的口气,法国皇帝当然可以称孤道寡,要是换了一个普通人,译文就不能用同样的词语达到目的了。
鉴于回文翻译保持形式的难度,吴绛雪的四季诗很难保持其本来的形式。我们将之分为四行翻译如下:
On willows oriels chirp a spring fine,
A spring fine the moonlight does shine;
On moonlit night the willows look bright,
Willows bright oriels chirp a spring night.
译文的成功之处是每行保持了7个单词,与原文的字数一致;韵脚也算严谨,虽然押韵的方式是每两行押韵,而不是像原文那样第一、二、四行押韵。由于回文翻译的难度大,头两行的“流水”形式保持了下来,但第三、四行就没能够继续保持。
此外还有语法结构和修辞形式的转换。通常的做法是,在翻译中,语言结构形式需服从意义翻译的需要,在无法同时保留形式和意义的情况下,被牺牲的大多是形式,或者把原本比较隐晦的意义直白地翻译出来,或者通过注释手段来传达原文的意义和修辞手段等。同样的,有没有一些需要不惜牺牲意义而保留原文形式的情况呢?赵彦春曾经就意义与形式究竟哪个更应该保留有过论述:“在翻译过程中,原文形式肯定会丢失,而原文形式所体现的内容一定可以被保留下来。这一点是翻译的最低要求。当形式不仅能够反映内容,本身还有特定含义时,这个形式无论如何都要在译文中体现出来。而当两种语言之间的障碍过大无以表现原文的形式时,那么内容可以被否决。”[12](P70)限于论文的篇幅,关于语法结构与修辞形式方面的形式翻译,不在本文探讨。
从上述研究可知,形式翻译在中外古今的翻译实践和研究中缺席,只有意义翻译驱动的形式翻译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形式翻译本身作为研究主题应该得到重视。在本文中,我们着重研究了文本形式翻译有关问题。研究发现,文本体裁在翻译中不能转换并不是没有例外的,在有语言本身以外的因素介入时,诗歌形式可以被翻译为散文形式,甚至散文形式也可以翻译为诗歌形式。邀请函由于传统格式的原因,其中的人称和格式都要根据文化传统做相应的改变。具有视觉冲击力的文本形式,应在尽可能的程度上保留其原文形式,虽然很难做到尽善尽美,但尽量做到最好还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