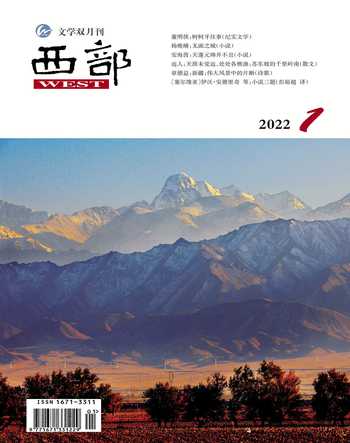一个人的城市
2022-01-13杜永利
杜永利
开始这段讲述之前,我要隐去他的真实姓名。为了叙述的方便,就叫他盖涂陈吧,该名号来自盖茨比、涂自强、陈金芳。
这三位文学人物都曾试图甩掉自己的底层属性,却在跃迁过程中撞得头破血流。人潮汹涌的城市,你很容易找到与之经历相近的人,甚至他们的表情都可以无限趋同,无不包含着疲倦、沮丧与迷茫。他们来自广阔的乡村,借着大学扩招或城镇扩张而步入城市,与故乡日渐疏远却又无法在坚硬的城市扎根,因而成了两头不靠的漂泊者。他们喜欢以蝙蝠自居,这个昼伏夜出的物种,拥有鸟类的翅膀却又归属于哺乳类,它分类上的尴尬,正好类比了无法界定城乡身份的他们。
珠玉在前,按说已无书写的必要,但是这个故事如此锐利,如同一根鱼刺卡在我的喉头,叫人不吐不快。我想我有必要写出来,因为个体经验无可替代,共性之中又包含着无法复制的个性。也因为,盖涂陈其实是我的化名,我必须讲出自己的故事。为了避免落入自伤自怜的窠臼,保证叙述的客观性,文章采取了第三人称叙述。
一
镜头拉到盖涂陈的单位。这是一家公职单位,门庭豪气,外表光鲜。落日的余光在楼盘间磕磕绊绊,经历了九死一生才抵达他的窗前。
窗台上的植物被残阳血染,多肉透明而脆弱;仙人球举着拳头、带着刺,咋咋呼呼却仍旧逃不脱透明与脆弱。他常常以这两种植物自比:刚入职的时候懵懂无知,对暗处的伤害毫无招架之力;经历了一年的揉搓以后,脾气变得暴躁,总在忍无可忍时发火,非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落人口实,搞臭了名声。别人就不同了,别人是文竹,支棱着触角到处闯荡,起初是试探,后来发现对方无力反抗,便明目张胆地开疆拓土了。他讨厌这些植物,这分明是自然界在对人类的行径进行暗讽。
他拉上窗帘,办公室暗了,往事在脑海里蹦跶。
公家单位很多工作都是虚的,没有明确分工,很多人都在钻营人际,对工作不上心。盖涂陈发现自己处于天然的劣势,与他同一批考进来的,都是在城市长大的,从小学的东西就不一样。他学种地,父母总是说:“人骗地皮,地皮骗你肚皮。”因了这句话,他从小到大没有说过一句谎,没耍过一次滑。同事却不一样,有的是富商之子,从小看的是做生意的套路,双眼骨碌一转,算盘在心里噼里啪啦已经拨了几百回;有的出身公务员世家,耳濡目染的全是为人处世的潜规则,一出手就是制胜的绝招。
新人们想着法子讨好领导,人前装勤快,给领导接接热水、擦擦桌子,私底下自己科室的垃圾从来没倒过。他们嘴巴很甜,领导爱写打油诗,他们马上在朋友圈转发,并附上“比肩莫言”几个字。盖涂陈学不会这些,很快成了异类。
那天一大早,领导给同事打电话,问昨晚交代他的材料有没有从市政大楼取回来。同事说:“办公室现在没人,需要有人守电话,我暂时走不开。”领导问:“那个谁,叫什么来着?不爱说话那个,对,小盖是吧,他在哪儿?”
同事看了看正在扫地的盖涂陈,答了一句,他还没来呢,估计在路上。领导便说,和小盖联系,让他直接去市政大楼。同事不失时机地把最后一句外放,盖涂陈只听到这一句,心想领导终于想到他盖涂陈了,竟屁颠屁颠地去了。
类似的套路,同事屡试不爽。日子久了,盖涂陈终于发现加班的总是他一个人。于是,他长出了一身刺,打算给进犯的同事一些颜色。
那天领导安排盖涂陈写一份紧急材料,要求一小时之内务必完成。他在网上找模板,同事不知情,以为他在看新闻,便假传圣旨:“领导让你去财政局送个材料。”盖涂陈正焦头烂额,理不出头绪,一听这话就恼了:“有病吧,一会儿让写材料,一会儿又让跑腿,想把我撕开吗?”说着就要给领导打电话。同事吓傻了,没想到平时不声不响的盖涂陈竟敢质问领导,便赶紧阻拦:“别急啊,你没空的话,我帮你去一趟,都是一个科室的,我帮你跑腿没啥。”盖涂陈气不过,还是打了电话,领导一头雾水。
同事露馅儿了,怀恨在心,在单位发起舆论攻势:盖涂陈真懒,啥活都推,同事之间互相帮忙,还要分得那么清。结果,一次大会上一把手说:“有些新同志太独了,工作不要分你的我的,这是咱们大家的。”
盖涂陈给同学打电话。同学说:“你知道吗?你在竞争中落了下风,领导很可能对假传圣旨的行为大加赞赏,你同事明显有手腕,有当领导的潜质。只要把工作做好,领导才懒得管手段如何。”盖涂陈直呼荒谬,生气地挂了电话。
不久季度考核开始了,盖涂陈被画了很多“差”,同事却是满纸优秀,这恰恰印证了同学的推断。他想不明白,从小就被教育不能说谎话,为什么如今却行不通了?种地和当公差真的不同吗?同学告诉他:“诚实是没用的,相反,不动声色地操控他人,才是技高一筹的表现,这是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道德从来都是骗人的,遮挡不住狂野的欲望。”盖涂陈实在听不惯这种论调,他的三观快要被摧毁了。
他怀念儿时在乡村的生活,一心劳动,多劳多得。城市的职场却并非如此,他始终无法适应这个环境,或者准确地说,他对此天然排斥,并不打算融入其中。
二
办公室完全黑了下来,打工人盖涂陈关了电脑,走到楼下,扫开一辆共享单车。有凉风吹过耳畔,他紧绷的神经终于有了一丝松弛。头上有苍天,星河灿烂晃眼,却与他无关。已经有很长时间没看过星空了,生活的雾霾遮蔽双眼,日子久了,他竟然忘记对光明的追寻,就像麦克劳德笔下的矿井之马,视觉退化了。
呼啸的公交像逃离犯罪现场一般,载着倦归的人群回家。他扫了一眼透亮的车窗,人挤着人,窒息之感触手可摸。每个人都埋头于手机,也许那是他们的窗户,能吹进旷野之风;也许那是他们的兴奋剂,能给乏味的生活带来快感。
街灯辉煌,把身后的影子拖得细瘦如剑,狠狠刺向他的脊背。反射弧过于漫长,他始终没有痛感。当然也可能是麻木了,对飞来的刀刃无动于衷,就像此刻认了命的影子,在颠簸的路途选择躺平,怎么拖拽都不肯起来。
他终于骑到了城中村。这是充满烟火气息的另一番天地,拥挤、脏乱、喧嚣,又热气腾腾。沿街的店铺不停地叫卖,声浪起伏,如同蜂巢失火。一溜招牌发出绚烂的光芒,给苍白的生活涂抹虚幻之光。小食摊主和城管玩着捉迷藏的游戏,却总能见缝插针地把生意做成幾单。空气中涌动着食物的气息,撩起打工人的口腹之欲,逗引他们走向夜市摊。重口味的臭豆腐和麻辣烫最受欢迎,迟钝的味蕾需要重油重辣来起死回生。几杯啤酒下肚,内心仍旧郁结,始知张爱玲所言不虚——喝再多也无法浇灭胸中的块垒,胃和心脏到底隔着一层皮。于是,有人醉眼迷离,有人鬼哭狼嚎,在狼狈之中眼睁睁看着曾经的自己渐行渐远。
他还了车子,胡乱买些烧饼,回到住处前已经吞完。村子里的房屋原来都是根基不深的平房,有传言说拆迁在即,于是整个村子闻风而动,开启疯狂加盖模式。盖涂陈每次外出都小心翼翼,生怕哪座楼房会轰然倒塌。他租的这栋还好些,只加盖了两层。另一个吸引他来此租住的原因,是房东有庄稼地,农忙时节能看到院子里摊开的粮食,这叫他心生亲切。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单位,他唯一的朋友是来自乡村的清洁工阿姨,她和盖涂陈一样卑微得叫人心疼。她曾对盖涂陈说:“你是唯一不指挥我干活的人,其他人只会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流汗。”
盖涂陈穿过冗长的走廊,需要不停地跺脚,以便提醒十五秒记忆的声控灯:这里有人,这里有人!他不想被忽视,他需要一种存在感,所以跺脚的时候是带着恨的,邻居们都狠狠地摔上了门。他要存钱买房,因此租住的房间是最差的,空间逼仄,仅有一张床和一桌一椅;没有空调,热天蒸桑拿,冷天坠冰窟;公用的洗手间,总是有人忽略墙上“来也匆匆,去也冲冲”的提示。朋友阿强曾来宿舍做过客,走的时候楼上晾晒的衣服正好滴下水珠,打在他的面颊上。阿强抬头看了看,觉得挂满衣服的天井很有美感。盖涂陈这才发现,原来他一直住在井里,他记得自己说了一句“潜龙在渊”。
他看了一会儿书,隔壁的浪叫准时响起。他想搞恶作剧,临开口时却捂住了嘴巴,他听见自己无声地喊:“大点声,听不见!”他无法看书了,孤独和欲望像虫子,肆无忌惮地啃噬着他的心,并没多疼,却叫人躁动不安。他想起沿街的成人用品店,永远看不见顾客,却在不断地更新货物。他想到很多故事在暗夜里悄然上演,无依无靠的打工人在陋室里互相攀缘,在风声轰隆的夜晚,他们抱紧对方,缠绕成两条互相取暖的蛇,吐出信子,交换体液。无边的孤独里他们互为稻草,在溺亡之前拯救彼此于深渊。
三
盖涂陈在这座城市已经十一年了,前几年是读书,接下来的几年在工厂做设计,一年多前考进现在这家单位。很多故交都相继离开,如今只剩下他一个人。内心柔软的部分已经对外封闭,很少有人能够长驱直入,更别说落地生根了。成人的世界,很多人都把自己砌入铜墙铁壁之中,保护自己的同时也隔绝了人类之间的信任。当发觉很多人都是表里不一的演员时,他很难再将自己柔软的斧足伸出来,只能做一只紧紧闭合的河蚌。至此,吞了多少沙子只有他自己清楚。每当夜深人静之时,他都试图将孤独与痛苦打包,以珠子的形式为柔软的内心画出保护圈。
他不喜欢去热闹的地方,尤其是人潮涌动的街头和商场,在那里,他内心的孤独会被无限放大。整座城市几百万人,人海茫茫,却没有一个人可以听他倾吐悲喜。他感觉自己漂泊在远离大陆的深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想:“我被整座大海环绕,却没有一滴水可以解我口渴。”
他刻意让自己忙碌起来,手洗衣服或者一遍遍拖地,以此来抵挡倾泻而下的孤独。自己就是一个世界,不需要分身制造另有他人的假象。因此,屋子里要放得很满,避免生出回声;镜子要遮起来,杜绝与自己的狭路相逢。他以为自己足够强大,可以轻松地疗救孤独,可惜总是在不经意间溃不成军。
有年过生日多买了一只鸡腿,因为天热而无法保存,想了一圈却想不到可以一同分享的朋友,最后只能眼睁睁看着鸡腿坏掉。有天晚上,急需手持身份证拍一张照片,他咬着身份证对镜自拍,却照得弯弯扭扭,最后只得去大街上喊了一个陌生人。有好几次出门忘带钥匙,只能喊开锁公司解决,隔壁的情侣却没有这种烦恼,因为他们总是守望对方归来……凡此种种,无不在诉说着一个事实,那便是“无人与他立黄昏,无人问他粥可温”。
先前隔壁住着一位考友,他们一起参加公职考试,成功通过面试。考友在体检时查出了肝功能受损,因此失去了入职的机会。搬走时他劝盖涂陈也快些搬走,這肝病来得很蹊跷,他怀疑墙纸和桌椅有甲醛。
盖涂陈因贪恋这里房租便宜,一直没有行动,终于在入职半年后被查出痛风。那晚他左脚的大拇指被亿万只蚂蚁啃噬,辗转反侧摊了一夜的饼子。天亮时他想起考友,想让其陪着去医院检查。电话打通后却听出声音的异样,原来考友已困囿于琐碎的婚姻生活,无法抽身。考友也来自乡村,住在岳父母家,岳父母想让孩子随女方的姓氏。考友没能考上公务员,也没有自己的房子,所以在争夺冠名权的暗战中毫无底气可言。
盖涂陈劝慰了几句,挂了电话,只能自己去医院。在公交车上他想,原来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苦水里泅渡,即便是呛水了窒息了,也不会轻易找他人诉说。
他从公交车上艰难地移下去,慢慢挪动着脚步,几百米的距离走了半小时。这时候他内心的疼痛汹涌浩大,他想哭一哭,并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所有无依无靠的进城青年。
四
盖涂陈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他先前因为工作不如意,一直没能找到对象。考进体制以后,村里的亲朋好友想着他总算安稳了,便不停地给他介绍对象。前前后后已见了几十个,大部分都是一面之后再无下文。
《水浒传》里的“潘驴邓小闲”总结得实在到位,他对照自己,发现五条没有一条过关的——没有潘安的相貌;没有勇气与女生肢体接触;没有邓通那般有钱;没有如簧巧舌,不知道该聊些什么;时常加班,没有多少工夫相陪。他不知道该如何破局,已经使完了所有心劲,却仍旧寻求不到答案。
媒人鼓励他:“这都得去碰,有的人姻缘晚,姻缘来的时候挡都挡不住。”为了早日碰到自己的姻缘,他仍旧屡败屡战。较之以往,他变得稳重多了,在遭到拒绝以后不会再难过。只是有一次,他失态了。
那位姑娘是舅妈闺蜜的女儿,学的中文,与从事文字工作的盖涂陈相谈甚欢。她从盖涂陈的言谈之中觉察出他很有才情,便迫不及待地要与他见面。他们相约在万达广场,姑娘说那里有很多饮品店,可以随便选一家聊上一下午。盖涂陈的舅妈说这位姑娘很漂亮,他心里有所准备,见面时还是被惊艳到了。那么多红男绿女进进出出,却没有一个人能盖住她的光鲜。盖涂陈本能地后退一步,心里的气已经泄了一半。
那个姑娘走了过来。她身材高挑,穿着讲究,画了柳叶眉,涂了鲜红的唇彩,很明显是个精致的女子。舅妈说她刚从上海辞职归来,空降到这座三线城市的相亲市场,可谓是降维打击。姑娘打量了一下盖涂陈,挑了挑眉,她没有去饮品店,而是临时决定去逛商场。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姑娘自顾自逛着,盖涂陈像跟屁虫一样,竭力去寻找话题,却总得不到回应。他大概猜出来了,真人和她的心理预期相去甚远,因此她恼羞成怒,懒得理他。
这时候已经到了饭点,正好逛到了一家牛排店,盖涂陈想着应该请人家吃一顿饭,说不定会有转机,毕竟在微信上聊得那么开心。姑娘同意吃牛排,但提出AA制。根据以往的经验,盖涂陈知道这是姑娘不想占他的便宜,以便日后干脆利落地消失。
坐定以后,盖涂陈重复姑娘感兴趣的话题,她总是不搭腔,最后锐利地来了一句:“你能不能说普通话?”很多人都看过来,他有些招架不住。他们老家是同一个地方的,她明明能听懂,为何要急于和老家划清界限?
服务员忙了好一会儿才过来,递上菜单问盖涂陈他们要几分熟。姑娘说七分熟,盖涂陈想到母亲说过的“喝酒三分醉,吃饭八分饱”,便说:“七分会不会夹生,来八分的吧。”服务员扑哧一声笑了,相亲的姑娘花容失色,像看外星人一样看着他。他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知道牛排的熟度有一、三、五、七分,但是没有八分熟的。
吃完这顿沉闷的饭,他们各自回去了。盖涂陈怏怏不乐,想,好不容易找到了聊得来的人,不能轻易放弃呀。他哪里知道,之所以聊得来,是因为姑娘情商高,并不是两人倾盖如故、相见恨晚。他不死心,在抖音上看见别人都在买“秋天的第一枚柚子”,于是买了一枚进口黄柚,用小刀镂刻出心形图案。姑娘收到的时候,说了一句“好幼稚”,盖涂陈快绷不住了,赶忙给自己找台阶:“是啊,是好柚子,我专门买了进口的。”
回去以后,姑娘再也没有回过消息,过了两天他发现自己被拉黑了。他很生气,打电话给舅妈,问这姑娘啥意思,居然不声不响地把他拉黑了。舅妈说:“你先别气,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吧。第一印象很重要,你想想头回见面,你穿的什么东西?”去万达那次,他穿着专门买的新衣服,花了好几百块呢。而且借了一块名表,精心打理了发型。舅妈不信,把姑娘的原话撂过来:“人家说你太土气,太邋遢。”
盖涂陈失控了,要找姑娘兴师问罪,问她为什么出口伤人。他已经竭尽所能,把最好的自己呈现了出来,却被说成邋遢,这分明就是歧视,太伤人自尊了。他想起在乡村劳作的父母,他们踮起脚尖,高举胳膊,做出认命投降的谦卑状,方才把他举到城市。没想到,在城市里他竟然连人家的脚底板都够不到!
他在电话里失声痛哭,舅妈说没事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
五
下班路过桥头的时候,盖涂陈习惯性地望一望沿河的楼盘,全市最贵的楼盘都在那里。楼顶的“碧桂园”“恒大”“建业”等字样被灯光打亮,像是发财心切的巨兽怒睁双目,俯视着地面上蠕动的蝼蚁。他奋力蹬了几下,却怎么也蹬不动,车子吱吱呀呀地喊着疼。
小时候母亲给他讲,晚上骑车要小心后座招来厉鬼。他感觉房产商就是一群厉鬼,他们套紧了笼头,意欲让他当牛做马,榨干他青春的血。
他在总结相亲失败的经验时,说自己没有邓通那般有钱,说得再具体一些,实际上就是没钱买房子。有一多半相亲对象在得知他没有栖身之所时,头也不回地走了。
不久之前,他剛碰见了以房子为相亲门槛的姑娘。那是五一假期,媒人张罗了很久才促成此次见面。据媒人说,姑娘眼光很高,百分之八十的概率看不上他。那天他超常发挥,多次把她逗笑,最终她答应第二天一起去逛街。第二天却又生了变数,她的姐姐跳出来,让推迟一天再出去。原来,空下的这一天是留给媒人提条件的。媒人开门见山地说:“先准备十五万彩礼,在市区买个房子,拿着房本过来验明真假。如果答应了就去逛街,不答应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盖涂陈想,最起码应该先接触一下,看看是否合适,直接提出这些,未免吃相太难看吧?
可是姑娘不肯松口,她早就摸清了男方的家底,对媒人说:“越是有钱的人家,我越不提条件;像他家这样的……”
盖涂陈的父母摁着他让他答应人家,说砸锅卖铁也要凑够钱。他却逃回了城市,很长时间不敢回家。
他不愿给女方扣上“物质女”的帽子,那样固然解恨,却偏离了真相,遮蔽了自己的软肋,类似于讳疾忌医,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他明白房子是绕不开的坎,没有房子,他将无法在城市扎根,稍有风吹草动,就会被吹到犄角旮旯。那种身不由己的漂泊,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品尝。
他毕业已经七年了。这七年来他节衣缩食,手机卡得要命,接近于砖块了,仍旧不舍得更换。同事说钱不是省出来的。说得很对,可是不省又有什么法子?他的父母年老体弱,决不能再去攫取他们的血汗。他做了一些文字方面的兼职,都是零敲碎打的小活。如果不是加班太多,他真想晚上去送外卖。
他每天都要看公积金的数目,浏览安居客和58同城,以便及时跟进房市的动态。他的收入很固定,一切都能被计算出来。他只能在时光流转中熬磨年岁,用蚂蚁啃骨头的劲头去慢慢攻克。
他幻想着自己已经拥有了一套房子,其中一间要作为书房,摆满喜欢的书籍。再在阳台种上蔬菜,给生活以绿意,欣赏完了还能丰富家庭食谱。他幻想着自己和妻子站在阳台上,阳光打亮他们的周身,城市在脚下铺展开。登高望远让他生出“一览众山小”的豪迈之情,那时候他一定会觉得自己就是城市的主人。
他一直等着那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