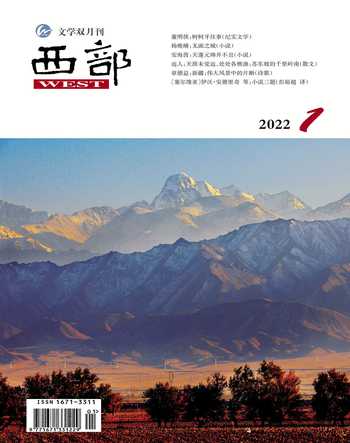行动代号:宏
2022-01-13王元
王元
心灵不在他生活的地方,但在他所爱的地方。
——英国谚语
晚上八点一刻,女歌手抱着吉他登场。黄卫经常看她演出,她一定也注意到黄卫,每次望向座位席,总是寻找与黄卫的互动,四目相对的时候,点点头,或者淡淡一笑。黄卫几次都想请她喝一杯,最终作罢。他拒绝跟任何人建立有效联系,尤其是陌生人。
主唱以外,其他乐手都是机器人。这是“桀斯”特色——AI主题。隔壁的“沙王”,主打外星元素,酒水名称都是天狼星或者银河系旋臂。黄卫有次去“沙王”,点了一杯室女座,喝到嘴里才发现是伏特加、酒吧老板到底拥有怎样神奇的脑回路,才会把毫不相干的名称扭结在一起?
歌手咬字不是很清晰(或许刻意为之),黄卫在第二遍副歌才听清一句“Melting like an ice cream when you are smile”。黄卫掏出手机,把歌词发射到搜索栏,歌名恰好是為首的单词,《Melting》(美国音乐制作人兼歌手CUCO于2016年独立发行的单曲)。接下来的操作就简单了,也是黄卫最期待的环节。他抖出当天的都市报,头版头条是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机器人暴走事件。作者用危言耸听的标题博取眼球:人类距离自取灭亡还有多久?林博士到底是救世主还是撒旦?林博士是什么和人类什么时候灭绝,黄卫不清楚,但报纸快撑不住了,以后势必要更换接头方式。黄卫展开生活版美食专栏,点击“靠谱APP”(一款可根据歌名查阅曲谱的手机应用),输入Melting,根据音符,圈出以下内容:
林卉,女,十九岁,就读于墨城师范大学三年级,对外汉语教学专业。找到这个女孩,带到3号仓库——行动代号:宏。
黄卫离开酒吧时听清第二句歌词“Melting you are a daydream stay a while”。他a while也无法stay,马不停蹄离开,任务一旦下达,必须立刻执行,没有喘息的余地。
自动驾驶汽车轻盈滑入师范大学东门停车位,黄卫步入校园,向沿途学生打听文学院宿舍楼号,问了几个都是摇头,直到遇见一对挽着胳膊的情侣。他们非常热情,如果不是赶着去看即将开场的“感官电影”,很乐意做向导。黄卫微笑致谢,祝他们度过愉快的夜晚。他循着情侣告知的路线前行:路尽头是图书馆,左拐是大学生就业中心,行经第二个路口,右拐,走到底。此刻,黄卫站在宿舍楼对面的槐树底下。他可以大摇大摆进去,揪出一个女大学生对他来说不是难事,问题在于如何不动声色地把她带到车上,送达目的地。他不想弄得鸡飞狗跳,尽人皆知。而且,黄卫不确定她在宿舍,还是上晚课,或者在自习室用功,又或者像刚才那对情侣一样和男朋友约会。
黄卫掏出酒壶,拧开瓶盖,小啜一口。酒精仿佛燃料,驱动他的大脑。他的思考方式遵循规律、规矩,不掺杂一丝邪念。
宿舍门口有两个蓝色垃圾桶,不时有女生出来,随手把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投喂进去。她们正年轻,活力十足,衣服也敢穿,颜色艳丽,款式新颖,肆无忌惮地暴露着大面积白花花的肉体。不像他。他裹着一件黑夹克,像误入夏天的企鹅。黄卫左右观察,趁没人出入,走到垃圾桶旁,挑拣出盛放一次性餐盒的袋子,拎在手里。他走进宿舍楼,看见昏昏欲睡的宿管阿姨,奉承一句你好,称自己是外卖员,小票搞丢了,只记得宿舍楼和收件人姓名,请她代为传达。宿管揉揉眼睛,厌恶地瞟了他一眼(任谁被吵醒都不会神采飞扬)。黄卫以为她要质问,结果只是一眼,便让他稍等。黄卫见她敲击桌面,唤醒休眠系统,问了两遍,确认林卉的书写,森林的林,花卉的卉。片刻,跑出一位银发披肩、牛仔短裤、趿拉拖鞋的女孩,四下张望,做寻人状。
黄卫正要上前确认,有人按住他,扭头一看,趴在肩膀上的是一只机械手。
机器人什么时候黏上来的?
黄卫自诩没有破绽,唯一可能就是它比他先到。它悄悄发力,示意黄卫跟它走。黄卫后退两步,随它没入槐树投下的阴影。它刚才就在这里蹲守吧。黄卫看见女孩左右眺望,耸耸肩,走回宿舍楼,这才把目光收束到挟持他的机器人身上:它披了一件长袖衫,穿运动裤,跟他一样裹得严严实实,乔装成人。黄卫随它来到校内停车场,不远处有两栋高层,应是教师楼。只要机器人愿意,稍加用力就能把他肩膀捏碎,对此他毫不怀疑。它也不愿闹出太大动静,否则刚才就能痛痛快快结果黄卫。退出女孩视线,他们掉了个个儿,换黄卫在前,机器人于他身后押解。它不说话,用力道指挥向左还是往右,好像黄卫只是一把方向盘。经过一辆悍马,黄卫通过后视镜发现机器人正在回头,似乎查看周围环境,以判断干掉他会不会引起远处独行学子的注意。黄卫受制于人,没那么多顾虑,身形一矮,从它手中脱落,右手抱拳,左手抱住右手,用力向后一肘。以往,遭受他肘击的敌人都会大声叫痛,吐出鲜血,但他忽略对方是机器人,柔软的腹部变成坚硬的护板。黄卫大声叫痛,就地一滚,绕过悍马车头,躲到另一侧,站定之时手上已经多了一把激光枪。黄卫双手架在车顶,朝机器人脑袋射击。它低头躲过偷袭。黄卫对准车门玻璃发起第二波攻势。开枪的声音、玻璃炸裂的声音以及报警器的声音交织在一起,像是一曲暴走的交响乐。黄卫不知道有没有命中,低头查看。悍马底盘够高,至少可以看到机器人小腿,但车的另一侧空空如也。与此同时,黄卫听见车顶传来很钝的撞击声,立马举枪,机器人已经扑下来。他们在地上翻滚两圈,黄卫仓促开了一枪,射中对方胸口。机器人的处理器一般安装在脑壳,必须爆头。黄卫还没来得及再次瞄准,枪就被它打掉。黄卫的格斗技术无可挑剔,但肌肉的力量无论如何锁不住传动轴,肉搏没有任何胜算。黄卫正在考量如何应敌(或者逃跑),机器人先动了,几个腾跃,融化在夜色之中。
回到宿舍门口,黄卫看见银发女孩被一个人影押进一辆银灰色轿车。他记住车型和车牌,匆忙跑回车旁,一把拽开车门,把自己扔在驾驶座位,点火,狠狠踩了一脚油门,引擎拼命咆哮,将车身弹射出去。
师范大学共有东、西和北三个大门,仅北大门允许外来车辆进出。东门正对的马路设有隔离带,绕到北门需要兜一个大圈,黄卫没有时间遵守交通规则,逆行到慢车道,狂按喇叭。自动驾驶系统不断发出蜂鸣,以示警告,因为严重违反交通规则强制刹车。黄卫切换手动驾驶模式;经过几年相处,他早就摸清老伙计的脾气。大部分会车司机都给他这个疯子让路,但也有个别倔强的驾驶人偏偏顶住他的车头。黄卫直接撞上去,开足马力,用较劲者的车子开道,冲到路口,猛踩刹车,对方被惯性甩出去,黄卫则左转,冲上二环路的快车道。黄卫自东向西逆行,没多远就与从北门右拐的目标车辆打了照面。黄卫左打满方向盘,车身一百八十度旋转,望着对方的车屁股,紧紧咬住。对方发现他这截尾巴,开始加速。黄卫死死叮上去,经过路口时还看见刚才被他撞飞的故障车辆。目标车辆上了高架,路况明朗,大幅提速。对方似乎还在使用自动驾驶,始终擦着限速。黄卫给了两脚油门,牢牢把对方框在视线之内。汽车追逐对黄卫来说是家常便饭,高架本身也不适合逃窜,更何况车速碾压,不到两公里,黄卫就把银灰色轿车别停。目标车辆立马倒车,黄卫眼疾手快,举枪打爆前轮,伴随一阵刺耳的尖叫,车辆刹住,柏油路擦出两道黑黢黢的胎印。黄卫举着手枪,瞄准驾驶员,迫使他下车。黄卫做好跟机器人打斗的准备,却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
“趴车盖上。”黄卫用枪指挥,中年男人依言而行,黄卫靠近,在他身上检查一番,没有摸出武器。
女孩慌忙从后座下来,挡在枪口和男人之间:“不要伤害我爸爸。”
事情有些突然。
先是机器人,又是父女情,黄卫需要时间整理和消化,更需要当事人交代。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宏:找到这个女孩,把她带到3号仓库。警笛远远传来,黄卫把男子和女孩推搡进汽车,锁死门窗,一路风驰电掣。
“我只要林卉。”黄卫试探道。他现在还不确定女孩是否为林卉本人,外卖的检验并没有十足把握,不排除是其他女孩或林卉舍友。黄卫没有直接发问,假定女孩是林卉,看他们的反应。
“爸爸。”女孩抱紧男人,好像鸵鸟把脑袋扎进沙漠。
“沒事的,爸爸在。”男人抚摸着女孩肩膀。
“下车。”黄卫把车停在路边,用枪指着男子脑门。
“求求你,别去3号仓库!”男子哀求道。
黄卫的任务大多是杀死某某,跟踪某某,将某某带到X号仓库。仓库有什么和会发生什么,与他无关。中年男子知道仓库的所在,要么,行动被渗透了,要么,他是编内人员。就林卉父亲的表现而言,黄卫倾向后者——但是父女算怎么回事?黄卫尽量不去多想,好奇心对于赏金猎人可不是好品质,事实证明,许多业内人士都死于引火烧身。
“你不好奇吗?”路上,林卉父亲主动开口。
“我的任务是林卉。”黄卫调回自动驾驶模式,腾出双手拧开酒壶盖,呷了一口。
“你听过机器人暴乱吧?”林卉父亲说,“发生在我的实验室。”
“你就是那个林博士?”黄卫当然听过,这年头,获取信息的渠道太多,新闻无孔不入,想要不知道某条热搜基本没可能;网络如同社会的血管,我们生活在网络之中。不久前,林博士研发的机器人觉醒,袭击数名工作人员,逃出实验室,被列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悬赏缉拿的非人类。林博士这三个字比时下任何超巨都有流量,跟他有关的话题长期占据热搜榜首。由此可知,刚刚袭击他的机器人就是那个通缉犯。事情不简单,但与他无关。
“我的名字是林立新。”林立新说,他似乎不喜欢林博士的尊称。网络上多是声讨和诅咒,说他打开了潘多拉盒子,也有人直接把他视为魔鬼本身,只要写一句“林博士去死”就能成为高赞评论。“我跟他们一起向你下达的任务,没错,宏。”
“所以,跟机器人有关?”
“它的名字是罗伯特。”
“明白,Robert.”
“可以这么理解,我们也是事后才发现Robert音译和意译之间的互动。它成长非常快,超出我们预期,也超出控制,死了好几个同事,而现在,”林立新说完握住林卉的手,“它盯上我女儿了。”
汽车停在3号仓库门口的时候,林立新刚好讲完事情的来龙去脉。
林立新说,机器人与人类最大的差异在于思维与视觉,计算机视觉与我们处理现实世界中的数据有着天壤之别。人类视觉系统可以在不同角度、背景和光照条件下识别物体,创建能够复制相同对象识别功能的人工智能是一直以来的难关。林立新的解决方案是制作逆向图——讲到这里,黄卫还能跟上,后面的话,每个字他都能听懂,串在一起却是天书——三维计算机图形模型是由对象的层次结构组成,每个对象都有一个转换矩阵,定义了其相对于原图像的平移、旋转和缩放比例;林立新创立胶囊网络,通过拍摄图像,提取对象及其部分,定义其坐标系,创建图像的模块化结构,可以让机器人以人类视角感知世界。林立新以汽车举例,汽车由车身、车轮、底盘、引擎、变速箱、刹车系统、车窗、挡风玻璃等零部件组成,每个对象都有各自的子集,车轮由轮胎、轮辋、轮毂、螺母等部件组成。他只能记住这些常识,后面提到的变换矩阵和视点对齐则是一头雾水,并被发热的大脑蒸发干净。这些铺垫了罗伯特的觉醒,用林立新的话说就是“它看待世界的方式变了”。
为防止机器人失控,研发者往往会在设计时留一个后门,控制罗伯特后门的钥匙正是林卉。林卉幼时遭遇车祸,眼球损伤,在视觉皮层植入辅助电极,通过刺激能够追踪和描述图形的电信号,方能“视物”。林立新为了帮助女儿看世界,研发胶囊网络,后来应用于计算机视觉。“我因女儿的祸得了科研的福。林卉小时遭遇过一场严重车祸,我基本上已经失去过她一次,我知道那种滋味,不想再尝一遍。”
接下来的经历顺理成章地联系到了宏,一旦罗伯特读取林卉大脑的源程序,就可以关上后门,再无可能入侵它的系统。林立新将情况向上级反映,参与整个行动策划,但是他后悔了。行动的核心是把林卉带到3号仓库,通过访问她的大脑,打开罗伯特的后门,消灭之。
“那为什么不进去呢?”黄卫不解。
“你以为怎么访问大脑?点击浏览器吗?”林立新眼眶红润看着女儿说,“我不能再失去她了。”
“我不能再失去她了。”他自言自语道。
“爸爸!”林卉显然跟黄卫一样刚刚得知事情真相,握着父亲的手哭了。她有理由涕泗滂沱,没人想要在平安喜乐的情况下亲近死亡,尤其是正值青春的少女。
“不就一个铁家伙吗,销毁它有那么困难?”黄卫的意思,出动几个精锐围捕罗伯特,轰掉它的脑袋。他一个人就能胜任,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火力支持。
“没用,它的意识可以上传下载,毁掉躯壳治标不治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要潜入网络,它就无处不在,除非摧毁网络本身。”林立新摇摇头说。
“如果,”黄卫假设道,“没有及时消灭罗伯特,会发生什么?”黄卫看过一些科幻电影,无非两个走向,要么,机器人追求某种境界,比如参禅,艺术创造,要么,发动硅基文明起义,推翻造物主统治,建立全新的社会秩序。
“不知道。”林立新倒是坦诚,“它就像拥有绝世武功的小孩,既胆怯又无畏;小孩看待世界的视角与成年人不同,不能以我们的历史经验去界定它的世界观。但危险一定存在,实验室死去的同仁就是前车之鉴。”
黄卫看了看林立新和林卉,后者像栅栏里的羔羊,不敢直视黄卫的目光,好像只要对上就会面临屠杀的命运。这并不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一方面,他从业多年,拥有良好的素养和信誉,鲜有失手,几次铩羽而归也是因为不可抗力;另一方面,这不仅仅是普通的任务,事关人类文明生死存亡。林卉的不幸(以前的和眼前的)真实可触,抓着他不放,往深深的回忆里面拽,生拉硬扯地疼。
“你们走吧。”黄卫扳正身子,摩挲方向盘。
“谢谢你帮我们。”林立新说。
“谢谢叔叔。”林卉紧随其后。
“我知道那是什么滋味。”黄卫灌了一大口酒,压制住不断上泛的情绪,“我女儿也出过车祸,她没能活下来。”黄卫放下酒壶,双手搓了搓脸,缓缓吁出一口气。林卉的悲惨遭遇一笔一画地鲜明起来,与他女儿的形象叠加,不胜唏嘘。
林立新父女与黄卫道别,试了两次,都打不开车门。黄卫尴尬地笑了一声,按下解锁键。林立新仍然打不开车门。黄卫马上察觉不对劲,汽车操控系统被黑了。点火系统自动做功,方向盘宣布独立,调头,驶向来时的路。
“是罗伯特。”林立新说,“它跟上来了。”
“现在开始,我的任务是保护你们。”黄卫惊讶自己能说出这样煽情的台词,过去几年他活得循规蹈矩,每天的生活被各式各样的任务盘踞,跟机器人差不多,输入,输出,直来直往,不求甚解。
黄卫试了几次都无法切换到手动驾驶模式。庆幸的是,罗伯特需要林卉(的大脑),所以没有对他们大开杀戒,否则只需要把速度提到最高,随便找一堵墙或者一棵树撞上去,就能依靠巨大的动量把三人捣碎。
“博士,”黄卫扭头喊道,“有什么办法吗?你刚才不是说了许多与汽车有关的话题吗?”
“那只是比喻。”林立新一臉无奈。
“但没人比你了解罗伯特吧?”黄卫提醒他。
“卷积神经网络存在根本性缺陷。”林立新小声说道,像是梦呓。
“大点声!”
“卷积神经网络存在根本性缺陷!”林立新喊道。黄卫自知错了,大点声和听不见都一样。“目前的技术仍然无法解决跨视点泛化的问题。同样一张照片,加上噪点,卷积神经网络就会将其识别为完全不同的事物。”
“然后呢?”
“自动驾驶汽车配备了GPS接收器、测绘技术,以及探测障碍物的雷达、扫描周边三维环境的激光测距系统、可以辨别物体的摄像机——汽车根据摄像机录制画面行进。”林立新终于说到重点,“只需给反馈的图像加上噪点,就能干扰驾驶系统,可能会导致车辆迫停。”林立新从后座挪到副驾驶,对着控制台一番操作,车辆果然缓缓减速,但他们没来得及庆祝,还没完全静止的汽车遽然加速。
“怎么回事?”黄卫向林立新吼道。
“我也不——我知道了,罗伯特刚才只是抢占了控制权,现在则是由它亲自驾驶。”林立新说罢,车载音响刺啦一声。
“你好,博士。”罗伯特的机械声音传来。
“罗伯特,”林立新说,“听我说,我们不会伤害你,请你也不要伤害我们。我会想办法帮你解除后门。”
“我相信你能做到,”罗伯特说,“但你了解我的逻辑,不会舍近求远。”
“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黄卫喊道。
“梦开始的地方。”罗伯特说完开始播放音乐。黄卫听着耳熟,很快想起来,正是《Melting》:
Melting like an ice cream when you are smile.
Melting you are a daydream stay a while.
汽车被加速到临界,但是非常平稳,丝毫感觉不到颠簸和摇晃,若从高处俯瞰,就像一道光在车流中穿梭。这是绝对效率和技术的体现。黄卫顾不上赞美,他已经失手了宏,不能在同一天搞砸两个任务。林博士和林卉的未来(以及——突然拔高——人类的未来)都落在他的肩头。他掏出酒壶,吞了两口,掏出激光枪,瞄准操作台。
“你要干什么?”林立新慌忙问道。
“停车!”黄卫没有理会林立新,对着看不见的敌人咆哮。
“你疯了?这么高的车速,你一枪下去就是车毁人亡。”林立新继续向黄卫喊话。
“你听见了吧,如果不停车我就开枪,林博士和林卉都会没命,你的后门就没人解除,永远担惊受怕地活着。对了,你懂什么叫活着吗?”黄卫想让目光有一个着力点,盯着挡风玻璃,假想罗伯特投影在上面。
“我不想伤及无辜,你们可以离开,林卉留下。”罗伯特开始讨价还价,黄卫这招奏效了,“没人想死,对吧?”
“没人想死。”黄卫说。
“所以,我们达成共识了?”罗伯特说。
“你提醒我了。”黄卫把枪口对准后座的林卉,“停车,否则我一枪打死她。”
“逻辑告诉我,你不会开枪。”罗伯特说,语气克制,没有情绪起伏。
“你到底想做什么?”林立新还没有明白黄卫的用意,林卉也吓得不敢说话,泪眼婆娑。
“三。”黄卫把枪管往前递了递。“二。”林卉从抽泣变成嚎啕。“一。”罗伯特投降了,汽车逐渐减速,停下。黄卫让林立新先下车,他跟林卉紧随其后,枪口始终固定在林卉身上。他不懂机器人的思维,但既然是智慧生物,一定会权衡利弊。他来不及跟林立新和林卉解释以及道歉,危险并未解除,所有联网的事物都可能成为罗伯特的化身,而基本上所有事物都联网了。黄卫带头,把手机扔在地上,用鞋跟踩碎。林立新和林卉目前处于牵线木偶的状态,惊魂未定,遵循黄卫的指令行事。作为资深的赏金猎人,黄卫在许多城市都有安全屋,但考虑到敌人的特殊性,他决定铤而走险。
“梦开始的地方是哪儿?”黄卫问道。
“什么?”林立新一愣,林卉也跟着摇头。
“罗伯特刚才说想要去梦开始的地方。”黄卫提醒林立新。
“实验室。”林立新一拍手说道。
“我们去那里。”黄卫说,“它肯定不会想到,我们下了车,反而去它设定的目的地。”
他们不敢搭乘交通工具,所幸距离不算太远,大概半个多小时,三人连走带跑来到一栋全玻璃外立面的大楼。林立新刷开门禁,三人鱼贯进入内部,暂时安全。壁灯在他们前方三米渐次点亮,寂静的长廊收纳了他们的喘息。推开实验室的门,打开灯,门自行合上,咔喳上锁,黄卫抬头看见一排跟罗伯特同一型号的机器人,吓了一跳。
“不用紧张,它们——”不等林立新说完,黄卫注意到其中一只机器人左胸有一个洞口。
黄卫一手将林立新父女拨到自己身后,另一手掏枪射击。罗伯特向后一倒,以腰眼为中心,整个上半身折过去。激光就像一条切线,擦着罗伯特的身体撞到墙上,溅出一个浅坑。黄卫趁机让林立新开门出去,却发现他们就像被困在高速行驶的车中一样陷于屋内。黄卫双手握枪朝罗伯特猛攻,密集的光影几乎笼罩住罗伯特的身形,有几枪让它挂了彩,撞出星星点点的火花。只要与罗伯特保持距离,就可以用持续不断的火力将它镇压。意外发生了,几块地板从中间向两边分裂,升出四根铁桩,从中释放浓浓白烟,落在身上凉凉的,不是烟,而是雾气,类似舞台常用的干冰烟雾。视线被遮蔽,黄卫宁心听着罗伯特的动静,不敢轻易开火,以免暴露位置。如果罗伯特加载了红外线系统,黄卫就是砧板上的鱼肉。
黄卫犯了经验教条主义的错误,他忘了敌人是人工智能,根本不会跟他玩猜疑链的心理游戏,他的自作聪明成了自投罗网。
任何一点轻微的响动都可能被罗伯特捕获。黄卫紧了紧鼻子,嗅到焦味,冲着味道飘来的方向举枪。激光发射时短暂地映亮周围,他看到机器人就在身侧——罗伯特“金蝉脱壳”。更换全新躯体的罗伯特一挥手,甩在黄卫脸上,他顿时晕过去。
那辆自动驾驶汽车尖叫着冲到黄卫女儿身上的时候,他就在不远处跟妻子争吵。他记得很清楚,早上起床一切都好好的,出门不久,两人就因为几句话拌嘴,愈演愈烈,遽然失控。他们停下来,女儿自顾自向前走,一脚踏空,坠入死亡。世界突然失去色彩。
沒多久,黄卫离婚了,成为一名赏金猎人,介于特工和杀手之间,有一个负责接洽的组织,但黄卫并非受命于谁。他经手过许多危险的任务,总能幸运地全身而退。当你不怕死的时候,死就开始怕你。黄卫并没有求死,不是在逃避,而是命运扼住了他的咽喉。
黄卫猛烈咳嗽几声,烟雾逐渐散去,他似乎看见林立新抓起他掉落的激光枪,瞄准的是林卉——一定是梦,黄卫还在昏迷。
一束激光穿透林卉胸口,她像一根快要融化的蜡烛垮掉了,melting。
黄卫沉入一片黑色湖水,不停下潜。等他再次醒来,房间已经可以视物,不见任何机器人,只剩他跟林立新。黄卫试着站起来,脚下却没有支撑,刚刚立直,又向前跌倒,努力了几次,才扶墙站稳。林立新比他强不到哪儿去,双眼茫然地看着前方,没有聚焦,两臂颓然下垂,右手挂着一只手枪。
不是梦!
“你做了什么?”黄卫推林立新一把,后者立刻倒下来,抟在地上,像一张被揉皱的纸,“你杀了自己的女儿?”
林立新一言不发,失魂落魄。黄卫四下寻找,却没有发现林卉的尸体,实验室的门敞开着,黄卫跌跌撞撞走出去,一间间屋子找过去,在走廊尽头的实验室撞见永生难忘的一幕:一副钢铁座椅,一个浑身散发着银光的机器人端坐其上,它的脚下有一座泛着红光的实验台;红光涌入它体内,仿佛血液;实验台旁边设有四截与刚才激战的房间相同的金属矮墩,向外漫溢着干冰化成的白烟;机器人怀抱着林卉——她的身体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半截机械义体,上面插着几根金属管道,仿佛在为林卉续命。她的眼睛睁开,嘴唇张翕不止。罗伯特正在读取林卉的大脑。黄卫想要冲过去阻止,双脚却牢牢地黏在地上,拔不起来。一切都来不及了。
撞击发生的时候,他就在不远处跟妻子争吵,眼睁睁地目视女儿腾空,翻滚,坠落,掉入死亡的深渊。一切都来不及了。
罗伯特身上的红色逐渐褪去,眼睛关闭。黄卫对机器和系统了解不多,以为罗伯特正在更新后重启,但是没有听见发动的响声。林卉的眼睛随之闭上。
“一切都结束了。”林立新站在黄卫身后,“你的任务完成了。”
黄卫使劲盯着林立新看了一眼,转身往外走。他很想灌两口烈酒,最好是去热闹的酒吧,比如“桀斯”,那个女歌手还没下班吧,或许可以请她喝一杯。
“行动代号是我拟的,”林立新说,“你知道什么是宏吗?宏是一系列命令组织在一起,作为一个单独命令完成特定任务。我们今天晚上所做的都是为了录制宏和调用宏。根本没有后门——相反,罗伯特可以设置许多备份(分身),触及整个网络,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它的监视之下。想要彻底击溃它,唯有让它自动关闭防御系统。林卉脑子里不是钥匙,而是炸弹,于罗伯特读取时引爆。这就是那个特定任务,我们的行为就是一系列命令,让罗伯特最终执行,包括你、我、林卉,包括对你的筛选(优秀的职业素养以及因车祸死去的女儿),包括你的对抗和我的射杀,我们做得越多越逼真,罗伯特上钩的概率越大。可以说,这是一个宏观的宏。”
“这就是你杀死女儿的逻辑?”
“我们都知道眼看女儿死去是什么滋味。”林立新说完把枪顶住太阳穴。砰。林立新脑袋顺着射击的方向猛地一甩,仿佛撞墙之后的反弹。黄卫惊讶于自己竟然没有阻拦,林立新从一开始就等待着这一枪,这是属于他的宏。
对于人类来说,爱是最普通最直截了当的表达,尤其是父母对子女的爱。这个理所当然的现象同样会被机器人捕捉到,在它的思维里面,这就是一种宏——仿佛遵循着某种严密的指令,他爱她,他不会伤害他。在它的思维里面,人类的爱就是宏。
黄卫从尸体手中拾回激光枪,掖进枪套,顺便掏出酒壶,把剩余的酒倒在地上。走出实验室。不知走了多久,黄卫看见停在路边的老伙计,黄卫拉开门坐进去。他曾经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碰自动驾驶汽车,但是女儿逝世第二年,他就很没骨气地提了这辆车,他的老伙计。我们都没有自己想象中坚强和勇敢,也没有保持长久愤怒的力量。他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科技的便捷,空出来的脑子可以胡思乱想:我们的一生充满各种各样的宏,至少他的每次行动都是一个具体的宏。死亡也是一个宏,经历出生、成长、收获、失去的宏。我们从一个目的到另一个目的——与人工智能不同的是,我们拥有漫无目的的时刻——从一个宏到另一个宏。
“桀斯”酒吧人声鼎沸,越到深夜越狂野。人们被技术裹挟着前行,但总有一些习惯和秉性一以贯之。
女主唱见黄卫回来,破天荒地冲他招手,她在唱一首中文歌,一首老歌,伍佰的《晚风》:慢慢吹,轻轻送,人生路,你就走……
黄卫坐在吧台旁,机器人酒保送来一杯烈性酒:“我猜你现在想要来点猛的。”
“没错。”黄卫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黄卫支付了酒钱,“请女主唱。”
没等女孩唱完,黄卫踉踉跄跄出门,耳畔立时静下来,里外仿佛两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