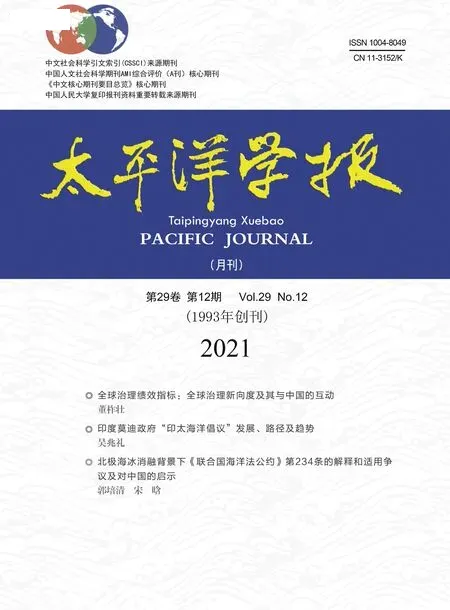东南亚共同体建设中的社会化路径:历史演进与理论思考
2022-01-13孙志伟
孙志伟
(1.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200083)
一、问题提出与既有文献评述
作为与中国山水相连的地区,东南亚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地区之一,而东南亚共同体建设则是该领域的重点方向。 伴随东南亚共同体建设进程,东盟区域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迅速提升,但要真正实现域内政治安全同盟构建、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社会文化资源整合的发展目标,仍存在相当距离。 不容否认,东南亚共同体建设经历了数十年发展,其“东盟方式”日益成熟且呈现出具有地区特色的区域共同体模式,然而针对共同体建设的成果、经验与前景一直众说纷纭、分歧不断。 厘清东南亚共同体发展的历史逻辑,思考其未来的可行性路径,是值得密切关注的重要议题。
在共同体的研究领域中,文化一直是解释性较高的分析因素。 马修·马尔科(Matthew Melko)指出,各种文明是否真实存在并不是关键,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在文明的概念中发现价值”①[美]马修·梅尔科著,陈静译:《文明的本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版,第 4 页。,即文明概念能否被拿来解释国际社会发展与文明实体间的互动关系。 东南亚区域内文化复杂而多元,是本土和外来的各方势力长期交织、多股融合的结果。②张蕴岭:“如何认识和理解东盟:包容性原则与东盟成功的经验”,《当代亚太》,2015 年第 1 期,第 4-20 页。东南亚地区的文化多元与历史发展密切相关,西方文化、中华文化、印度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这里发展共存,共同促进了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 从文化与国际关系视角分析东南亚共同体的建设路径,对于充实共同体理论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东南亚共同体建设的发展恰是文化与国际关系研究的主要议题。 “东盟方式”是一种东盟在不断发展过程中提出的、适合东盟各国的合作方式。 这一模式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合作路径,有着亚洲国家所特有的交往和互动方式。③郑先武:“东南亚早期区域合作:历史演进与规范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17 年第 6 期,第 187-204 页。有学者认为,“东盟方式”的基础是印度尼西亚传统的乡村文化,在乡村议事中奉行协商一致为基调的决策模式。 前印尼官员阿里·莫厄多婆(Ali Mocrtopo)在1974 年提出由于“大多数代表成员国的东盟领导人是老朋友”,促使东盟方式形成了“以协商体制为标志”的议事体制。④[加]阿米塔·阿查亚著,王正毅、冯怀信译:《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年版,第88 页。同样,藤田泰昌(Hiro Katsumata)指出东盟方式基于不干涉他国内政等原则形成,同时根据东南亚地区特性予以修正,形成了具有东盟特色的处事方式。⑤Hiro Katsumata, ASEAN′s Cooperative Security Enterprise:Norms and Interests in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p.65-70.同时,“东盟方式”也招致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如东南亚问题专家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认为,东盟的决策过程呈现非正式性与松散型的特点,这使得东盟内部较难形成合力,致使其在亚洲经济危机中应对乏力。⑥Amitav Acharya,“Realism,Institutionalism,and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1, No.1, 1999,pp.1-29.
东南亚区域共同体的发展有其独特的社会化路径,以“东盟方式”为代表的组织和决策方式彰显了区域合作中的思想、观念、计划及其实践进程。 自“东盟方式”提出以来,东南亚地区学者也多从本区域实际发展出发来分析这一方式的效用与利弊,如提出东盟在实现经济共同体领域仍面临巨大挑战。 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往往需要了解各国的国内问题和优先事项,从而更有效地进行多边合作。⑦Kanwara Somjai and Mahmoud Moussa,“A Literature Survey of Educ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in the Asean Countries: A Critical Analysis,” ABAC Journal, Vol. 36, No. 1,2016, pp. 13-33.新加坡一些学者更多关注的是阻碍东盟建立稳定政治环境的因素,如东盟成员国间关系和相互作用的复杂性、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利益的复杂性、东盟国家之间仍存在一定的领土边界争端等。⑧Bama Andika Putra and Darwis and Burhanuddin, “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 Challenges of Establishing Regional Se⁃curity in the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12, No.1, 2019, pp.33-49.同时,区域内学者也在积极寻求“东盟方式”的改进途径。 有学者认为,作为一个地区性机构,东盟应注重区域内各国的积极合作,进而谋求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主张东盟应该用一个声音说话,用一个可见的身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⑨Ioan Voicu, “ Asean between Aspirations and Realities,”ABAC Journal, Vol.29, No. 3, 2009, pp.1-28.此外,不少区域内学者指出,东盟合作和制度安排的灵活性,即所谓的“东盟方式”给予成员国不遵守制度的借口,也存在执行方面的问题。⑩Mely Caballero-Anthony, “Bridging Development Gaps in Southeast Asia: Towards an Asean Community,” Unisci Discussion Pa⁃pers, No. 11, 2006, pp.37-48.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设难度相对较低,各成员国推动的力度最大,但仍应确保另外两个支柱(即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进展,将三大支柱的协同效应最大化也同样重要。⑪Jayant Menon and Anna Cassandra Melendez, “Realizing an 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Progress and Remaining Challenges,”ADB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No.432, 2015, pp.1-19.
2021 年是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30 周年,对东南亚共同体的研究是一个值得深入的议题。 纵观东盟发展,其区域合作与共同体建设的动力为何? “东盟方式”在东南亚地区治理中的适用性如何? 东南亚一体化路径与世界其他地区存在明显不同,应建立具有东南亚特色的研究体系。 文章认为,东南亚共同体经历了一个由经济、安全向社会文化发展的过程,考察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化路径与“东盟方式”的互动作用是揭开东南亚区域治理的一把钥匙,更是激励我们由文化与国际关系议题出发,理解东南亚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
二、本文解释框架与主要变量分析
以文化与国际关系的视角透视东南亚共同体建设,是将东南亚区域研究与国际关系和世界政治的主流研究进行对接的积极尝试。①魏玲:“东南亚研究的文化路径:地方知识、多元普遍性与世界秩序”,《东南亚研究》,2019 年第 6 期,第 15-25 页。本文从东南亚地区特性出发,使用结构—过程和存异—求同两个维度构建一个解释框架,用以梳理具有区域文化特质的东盟共同体建设。 这一框架将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历史路径划分为四个类型:结构存异型、过程存异型、结构求同型、过程求同型。 上述类型以历史分期、阶段特征为要素审视了东南亚地区一体化建设的发展进程,以期对共同体建设中的社会化路径进行深入考察。
2.1 东南亚共同体建设的解释框架
第一个维度是结构和过程。 本文将“区域”界定为一种根植于政治实践的社会认知进程,其包含结构与过程两个维度。 从结构层面来看,其地域空间与成员数量不断扩展、功能外延不断拓宽、区域组织的功能作用日渐突出;从过程来看,区域合作是域内国家共同实践的结果,可以被视作一种社会建构的、动态的、历史的发展过程。②郑先武:“区域间主义治理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第 39 页。一般而言,区域间合作主要经历了由结构性合作向功能性合作的转变,即早期合作更加趋向于为国家间因利益相近而采取的功能性合作,较少关注国家间身份认同的趋同,凸显结构性特点;在各方普遍认可合作方式、接纳合作对象后,区域间合作则更加强调国家在合作的过程中注重彼此间身份认同的相近,既关注合作的广度、重视合作的深度,又充分考虑各国在合作中的观念意图,展现出过程性合作的主要特征。
第二个维度是存异和求同。 在国际关系研究的既有议程中,冲突与合作是一个重要范式并频繁出现在不同的研究论题中。 本文借用这一传统模式,并依托东南亚区域特性尝试提出具有“东盟方式”的思考问题路径——“求同存异”。 在本文的叙述逻辑中,一方面,求同存异包含两个层次:其一为文化层面;其二为历史层面。 从文化层面来看,求同存异与东亚、东南亚的文化影响息息相关,是本地区民众人际交往、国家间交往的重要方式。 在国际合作层面,求同即寻找不同政治实体间合作的可能,求同与合作有着较大相似性,但更加强调合作中的文化相近与身份相似。 另一方面,存异与冲突相对应,却也存在明显不同,国家间交往不以矛盾与分歧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聚焦点,更体现了国际关系处理方式中的东方哲学。③曾亦:“传统儒学视野下的现代国际关系”,载徐以骅、邹磊主编:《宗教与中国对外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218-230 页。从历史层面而言,以冷战为分界线,呈现由“存异”向“求同”转变的轨迹。 在东南亚区域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国家间互动较少、地区间分歧频繁,其区域化特征多以存异为主,在1967 年“东南亚国际联盟”成立后,东盟虽发挥了重要影响,但更多仍以“政治论坛”、“外交沟通”场所的形式出现,各成员国均可在这一信息沟通场所中表达意见、分享观点,更提倡保留国家间的分歧,并尝试寻求解决方式,“存异”的状态为主要趋势。 在冷战结束后,东盟适时根据国际形势发展变化,推动东盟成员国扩展,通过利益趋同、文化趋同等方式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并从地区一体化的角度重视东盟各国间的“求同”。依托以上两个分析维度,本文将东南亚共同体的建构路径划分为四种模型(参见表1)。

表1 东南亚共同体的建构路径划分模型
2.2 东南亚共同体建设社会化路径的变量因素
本文同时采用了共有记忆、相互依存、域外影响、自我约束四个变量来对每一类型时期的东南亚一体化建设进行具体分析。 笔者认为,这四个变量的互动关联体现了共同体建设过程中社会化路径的演进轨迹,且由于历史阶段不同,其社会化发展特质也不尽相同。 厘清不同变量对东南亚历史的影响,有利于研究者就“东盟方式”厘清研究脉络、细化研究阶段、观察发展取向,更有助于发现新的区域研究增长点。
其一,共有记忆构成了东南亚共同体发展的历史基础。 共有记忆与共有观念①共有观念是指行为体在一个特定社会环境中共同具有的理解和期望。 由于利益和观念有构成性关系。 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内,共有观念就建构了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 [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7 页。存在一定的差异。 本研究所梳理的共有记忆更加强调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因素。 除泰国外,②泰国是东南亚历史上唯一一个没有沦为殖民地的国家,但在其发展历程中仍深受英法等国的影响。 如1896 年,英法签订了《关于暹罗等地的宣言》,将暹罗列为缓冲国,并划定了双方的势力范围。 英法两国在泰国势力均衡、相互妥协,泰国在地缘位置上成为各方势力的中间包围地带。东南亚各国在历史上均深受殖民势力影响,在其后的反殖民过程及冷战时期又广泛受制于域外大国,使其在处理国家对外行为时极易从本国、本地区的发展中找寻历史经验、解决办法与可行性方案。
其二,域外压力加深了东南亚共同体发展的建设难度。 一般来说,域外压力的主要衡量指标包括:本区域内国家与域外大国联系是否紧密,地缘政治层面邻近地区经济、军事实力是否强大,周边大国在本区域的影响是否强势等。③潘一宁:“冷战后美国与东南亚的集体安全”,载陈乔之主编:《面向21 世纪的东南亚:改革与发展》,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 513 页。域外压力在东盟共同体建设的不同阶段呈现截然不同的特征与趋势。 东南亚地区在传统上即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之地,早在16、17世纪就成为西方殖民者经营,甚至殖民的主要场所之一。 经历漫长的殖民与反殖民,冷战对立与经济复苏发展后,东南亚诸国在发展中更易受到域外国家的影响甚至压力。
其三,相互依存丰富了东南亚共同体发展的合作方式。 相互依存是对全球化时代各国之间经济发展、人员流动、社会联系紧密的一种高度概括与描述。④[美]小约瑟夫·奈、[加拿大]戴维·韦尔奇著,张小明译:《理解全球冲突与合作 理论与历史》(第10 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 323-325 页。相互依存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有其生成的必要条件,如相互依存的各方之间实力相差不大,而且在地理位置、历史发展上联系紧密。 随着东南亚各国自身经济实力和政权稳定性的不断增强,区域内各国间的联系愈加紧密,社会性相互依存的链条也越来越长。①[美]彼得·卡赞斯坦、秦亚青、魏玲、王振玲、刘伟华著:《世界政治中的文明:多元多维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 25-26 页。以东南亚各国为例,在经济实力、军事力量、政治影响力上多被界定为中小国家,彼此间的国际社会影响力较为对等,更易促成东南亚区域内相互依存的客观现实。
其四,自我约束规范了东南亚共同体发展的实践行为。 自我约束是建构主义关于身份认同、集体身份形成的诸多变量中最为关键的一项。 在传统国际关系的理论假说中,无政府社会是国际关系的常态,国家处于无政府的社会下更多地基于不安全感来提升军事实力、经济实力,以获取在区域内的主导权与国际社会的影响力。②John H.Herz,“The Nation-State and the Crisis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 McKay,1976, pp.6-8.建构主义学者认为无政府社会的状态也是被建构出的关系状态。③[英]赫德利·布尔著,张小明译:《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第17 页。在建构主义的逻辑演绎中,相关国家可以依靠互相之间的联系、互动来构建一个较为安全、稳定的区域环境形态,而自我约束则是构建这一形态的重要因素。
东南亚地区一体化的研究必须要建立具有东南亚特色的研究体系。 作为东盟国家长期以来发展形成的独特外交模式,“东盟方式”注重通过磋商和对话来进行合作,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与传统意义上的决策原则有明显不同。 具有东南亚地区特色的“东盟方式”更具有社会性、过程性的决策属性,这是在地区建设过程中深受共有记忆、相互依存、域外压力和自我约束等因素影响的结果,相关因素对东南亚共同体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结构存异型:共有记忆与战后东南亚“区域自主意识”的萌芽(1943—1966 年)
东南亚区域的形成是一个政治、经济、历史和地理相结合的过程。④王正毅著:《边缘地带发展论:世界体系与东南亚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版,第 2 页。“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概念,最早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自1943 年召开魁北克会议,西方盟国决定建立“东南亚战区”(South-East Asian Command)以来,“东南亚”一词开始被广泛使用。 在早期的发展实践中,东南亚区域发展表现为较为虚弱的区域凝聚力,是“区域自主意识”的萌芽期。 区域内的地理、文化特征各异,虽有国家间合作形式的出现,但由于深受历史因素的影响,相关合作并未持续且区域互动较弱,呈现本文所解释的“结构存异”型区域模式。
东南亚的民族问题与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区域内各地区发展深受地理构造、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展现出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特性与发展脉络。 “东南亚”区域的变化过程正是世界历史进程的重要反映,在这一阶段,东南亚地区的共有记忆初步形成,且具有典型的区域特色与东方文明的色彩。⑤贺圣达著:《东南亚历史重大问题研究·东南亚历史和文化:从原始社会到19 世纪初》(上册),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 年版,第 20 页。
首先,早期东南亚地区的共有记忆有其形成的地理与文化条件。 “东南亚”这一名称最早见于1838 年马尔科姆(Howard Malcom)所著的《东南亚旅行记》一书。⑥朱蓉编:《陈序经东南亚古史研究合集(上)》,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2 年版,第8 页。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历史与文化地域,东南亚在古代历史、近现代历史时期即已形成了一定的区域特色。 在地理上,东南亚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单元,其与东亚、南亚及澳大利亚等大陆之间相对疏离。而在区域内部,东南亚各国的地理位置也相对分散。⑦[新西兰]尼古拉斯·塔林主编,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第一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第2 页。东南亚地形地貌的复杂性使得东南亚呈现国家实力不一、发展进程差距较大的地区特点,也导致了文化上的日益多元。 在本地区固有文化的基础上,东南亚有选择、有针对性地吸收了来自印度、中国、阿拉伯及西方的文化,形成了具有东南亚国家特色的多元复合文化。①张帆、杨潇:“尼加拉体系:理解东南亚国际关系的新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11 期,第 92-94 页。
其次,殖民时代的地区发展也促成了东南亚各国共有记忆的形成。 除泰国之外,东南亚国家均经历了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是众多大国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利益汇聚的地区。 大国之间政策相互作用的频率和强度,以及它们在这一地区对一些国家的支配影响,必然对政治现实有直接的影响”②Amitav Acharya,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Routledge,2001, p.52.。 而英法等国对泰国虽未有殖民之名,却也借助诸多不平等条约在泰国划分势力范围。 由于殖民者对东南亚不同民族往往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导致在区域发展的早期阶段,东南亚各地区之间联系较少。 虽与宗主国之间保有较为紧密的联系,但地区内部却呈现较为割裂、分散的状态。 殖民时代的历史、文化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东南亚地区共有记忆的形成。 相关“记忆”促使区域内国家在后续发展中更为关注自身所面临的安全困境、经济颓势,对自身主权问题更为敏感,甚至将自身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不断放大,进而影响到本国的外交判断,做出要么“选边站队”、要么唯域外大国“马首是瞻”的行为。③吴心伯等著:《亚太大棋局:急剧变化的亚太与我国的亚太方略》,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82-83 页。
最后,共有记忆的形成催生了东南亚区域内各国在战后初期“区域自主意识”的萌芽。 20世纪50 年代末,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和印尼等国开始尝试探索符合东南亚实际的区域合作模式。 1961 年7 月,时任马来西亚总理的东姑·拉赫曼(Tunku Addul Rahman)倡议,由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三国为主体的“东南亚联盟”宣告成立。④ASA, Report of the Special Session of Foreign Ministers of ASA, Kuala Lumpur/Cameron Highlands, Federation of Malaya,1962, pp.13-25.然而,该组织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就因1962 年菲律宾对沙巴的主权要求而几近瘫痪,之后也因东南亚国家联盟的出现而退出历史舞台。 东南亚联盟虽存在时间较短,但其创建是东南亚国家开始就区域事务进行协商互动的尝试。⑤Amitav Acharya, The Quest for Ident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utheast As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p.82.在东南亚联盟陷入瘫痪之际,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尼三国领导人于1963 年宣布成立“马菲印联盟”,三国认为该联盟作为一个国家集团,应坚持在不放弃各自拥有的任何主权的基础上,通过最紧密的协调联合起来。⑥Arnfinn Jorgensen-Dahl,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Order in Southeast Asia, The Macmillan Press, 1982, pp.26-28.在“马菲印联盟”的实践中,相关国家开始践行不受外部干涉、民族自决以及和平解决争端等基本原则,并且将协商与共识的议事方式融入国家间互动中,并以此作为解决分歧、分享观点的主要方式。 作为东南亚本地最早的区域政府组织,“东南亚联盟”显示出东南亚主要国家已开始了筹办区域协作机制雏形的尝试,“马菲印联盟”的实践也为其后东盟的创设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战后初期,依托各地区间共有记忆的相通性,东南亚“区域自主意识”的萌芽已开始酝酿有关国家认同与民族建构的本土情怀。 地理、文化对该地区的传统影响使当地民众在处事方式上颇具东方传统文化因素,而殖民时代的历史记忆又促使域内各国在获得独立后更为珍惜对主权的拥有,在国家间合作时也更为关注主权的维护。 但是,由于殖民者在扩张过程中人为划分势力范围,导致后殖民时代的东南亚国家间产生了严重的领土纠纷。 相关国家间的合作多因领土纠纷而趋向瓦解,但一些合作原则与议事方式为其后东盟的创设提供了一定依据。
四、过程存异型:域外压力催生战后东南亚区域内互动的形成(1967—1991 年)
过程是社会科学的重要概念。 过程研究并非刻意否定结构,而是强调在结构形态之外,存在一个变化动态的认同过程。①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8, No.2,1994, p.384.注重过程研究的国际关系成果更多关注不同时段内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联系,强调在互动联系的过程中产生更多行为意识、社会规范。②吕虹、孙西辉:“国际经济秩序变迁的理论与现实——基于结构化概念的分析”,《太平洋学报》,2019 年第9 期,第82-84页。以美苏为代表的域外压力的影响促使东南亚各国在区域内的互动更注重政治、安全议题。 处于冷战的影响之下,东盟所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仅作为一种“外交沟通”和“政治论坛”的场所,其社会化程度有待加强。 整体来看,此时的东南亚区域呈现“过程存异”的区域合作状态。
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立是该时段内东南亚地区社会化路径的重要事件。 1967 年8 月8日,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外交部长共同签署了《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 东盟的建立是东南亚区域合作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历史事件。③“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Declaration on For⁃m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 Vol.6, No.6, 1967, pp.1233-1236.自东盟成立后,东盟规范以政治、安全议题为切入点,构建区域内互动,并以“非正式的、松散性的”模式奠定了东盟合作基础。 经历20 余年的发展,东盟的相关区域实践培育了一定的地区合作意识,积累了宝贵的区域合作经验,而东盟一体化的初衷正来源于其共有记忆的基础作用、区域内部的合作基础。 这一阶段,东南亚共同体建设在社会化层面呈现域外因素更加显著的特点:
其一,冷战的外在压力促使东盟国家以政治、安全议题为切入点,构建区域内互动。 东南亚区域多为中小国家,在地缘政治上深受域外压力的影响。 在20 世纪60 年代中后期,美国陷入越南战争难以自拔,同时苏联在该地区的势力也不断扩张。 区域形势的变化促使东南亚诸国开始意识到必须摆脱超级大国的控制,降低域外压力影响,在国际冲突中确保自身安全,使“东南亚永远不成为大国争夺的场所”④[日]丸山静雄著:《东南亚与日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版,第 141 页。。 东盟国家呼吁区域内国家“确保它们的稳定和安全不受任何形式和表现的外部干预”,这一条款既适用于禁止东南亚国家干预区域内别国事务,同时也适用于阻止美国、苏联等域外大国对本区域事务进行干预。 在经历了殖民时代的被压迫、反殖反侵略时期的有限互动之后,这一时期的东南亚诸国已然在域外压力的影响下更加明确了彼此之间的利益诉求,更加主张本区域内国家应竭力避免域外大国干预区域内部事务。可以说,域外压力,特别是美苏冷战的外在压力,强化了东南亚国家的合作意识。 在主权因素的影响下,东南亚各国在区域合作中更加看重自身主权利益的维护,将捍卫自身主权的完整作为区域合作的首要因素。
其二,域外大国的影响也使得东盟在成立之初即采取了集体外交的合作方式。 有学者提出,东盟成立的直接动因首先与一种共同愿望有关,即发挥集体外交的影响力以应对域外国家的压力。⑤周玉渊:“政治安全共同体蓝图与东盟的外交协调”,《东南亚研究》,2009 年第 3 期,第 43-49 页。集体外交的实践能够对接国际社会惯用的规范制度,凸显东南亚国家参与国际社会的积极意愿。 1967 年至1991 年间,东盟区域合作的一项重要成果即为1971 年颁布的《东南亚和平、自由和中立区宣言》(即《吉隆坡宣言》)。 该文件积极倡导“防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和平解决争端”等国际规范,也敦促东盟成员国“对联合国有价值的目标和目的承担义务”⑥Sheldon W. Simon, “ASEAN’ s Strategic Situation in the 1980s,” Pacific Affairs, Vol.60, No.1, 1987, pp.73-93.。 同时,集体外交的实践也促使东盟成员国内部进一步践行“区域问题区域解决”的制度方式,以集体外交应对域外压力。 东盟呼吁“东南亚国家对于加强本区域的经济和社会稳定,保障本国的和平与发展共同负有重大责任”,主张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与中立区”,区域内主要国家通过一系列条款的确立,开始以沟通对话的形式自主决定域内事务,既避免大国势力对本区域内国家的影响,又尝试填补大国退出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以合作与集体努力的形式增强域内国家的影响力。
其三,该时段内东盟国家以“非正式的、松散性的”模式奠定了东盟合作的基础。 在东盟成立之前,东南亚一些国家就曾参加过域外力量主导建立的、具有区域合作性质的地区组织,如由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主导签订的“反共军事联盟”,或有联合国有关机构建立的东南亚开发部长会议和亚洲开发银行等。 以上区域组织多侧重于地区安全与经济发展,既与意识形态存在诸多联系,也体现了战后初期东南亚诸国渴望发展民族经济、逐步改善本国民众生活的诉求。 在东盟成立后的10 余年间,东盟国家的合作方式经历了明显转变,更多注重区域内部各国间的互动,并形成了富有东盟特色的议事方式。 东盟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大多都是相互熟识的老朋友,更倾向于领导人的直接对话或特殊的代理人在正式会议前进行“非官方”的初步交流;在商讨议题时,更加倾向于采取非制度化、松散的谈判方式,避免为解决争端设立司法和仲裁机构,更加愿意接受区域内友好第三方的调停。 在安全角度,东盟国家提倡不使用武力、拒绝军事条约,以“丰富的生产网络与温和的双边关系”塑造东南亚的区域稳定。
冷战时期的东南亚国家对域外压力有了更加清晰地认识,但也正因为域外压力的影响,早期东盟的组织架构缺少制度层面的顶层设计,仅作为一种“外交沟通”“政治论坛”的场所,区域内各国在交流平台中充分表达彼此观点,不以矛盾与分歧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聚焦点,是一种典型的“过程存异”状态。①凌彦:“民族主义与东盟的形成”,《东南亚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29-34 页。“存异”的背后也暗含了“求同”的可能,东盟在1976 年决定设立秘书处,处理东盟的日常事务并协调成员国之间的信息,进一步促进了区域内部的沟通与对话。 总体来看,冷战期间的东盟承担了避免内部冲突和争端的功能,虽然经济合作等方面差强人意,但也为东盟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五、结构求同型:相互依存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功能性拓展(1992—2002 年)
结构求同型的模型重点在于结构。 从结构层面来看,该时期区域内地域空间与成员数量不断扩展、功能外延不断拓宽、区域组织的功能作用日渐突出。 伴随冷战的结束,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新变化,东盟进一步扩展了成员国的数量,同时加强了政治、安全、经济和环境等综合性议题的国家间合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该时期内东南亚区域内的相互依存状态由理念层面转变为实践层面,国家间因利益相近而采取的功能性合作,开始寻求以集体身份参与国际社会互动,呈现出“结构求同型”区域合作模式。
相互依存首先体现在冷战结束后东盟成员国数量的扩充。 相互依存因素在一体化的发展中由理念构想逐渐付诸于制度实践。 由20 世纪90 年代开始,东盟的成员国数量不断增多。1993 年7 月,越南和老挝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1995 年 1 月和 7 月,柬埔寨和缅甸最终同意接受《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 相互依存的现实也促使区域内各国逐渐意识到相互依存的状态可以提升本地区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从而更加积极参与东南亚区域内的国家间合作。 1995 年7 月,越南被正式吸收为东盟成员,1997 年5 月,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也被吸收为成员国,其中柬埔寨因国内事务,于1999 年4 月正式加入东盟。 成员国的扩展进一步促进了本地区的相互依存态势的形成。 伴随成员国的扩充,东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种被推崇的东盟工作方式,表现为既坚持了成员国之间共同一致的原则和实践,又凸显了东南亚地区的处事风格,②Michael Leifer,ASEAN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Routledge, 1989, p.24.这是东盟各国在相互依存的影响下,在考量多种政策方案的可行性与结果后,最终选择的最优方案。
同时,相互依存也体现为东盟成员国内部多方位功能性合作的开展。 1992 年1 月召开的东盟第四届首脑会议提出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并将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不断推向深入。 东盟秘书处的功能不断扩大,涵盖经济合作、功能性合作与沟通对话等领域。 这标志着东盟由一个“沟通场所”,正式转变为在东盟首脑会议主导下、涵盖外交、经济、安全和环境等多个领域的区域组织。①Kusuma Snitwongse, “Meeting the Challenges of Changing Southeast Asia,” Robert Scalapine, et al. eds., Regional Dynamics:Securit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0, p.40.同时,相互依存的现状也促使东盟成员国努力“以东盟为中心”,应对世界地缘政治和经济变革对本地区产生的影响:在地区安全领域,建立了“东盟地区论坛”,邀请域外国家作为对话伙伴国;在经济合作领域,东盟支持建立“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推动亚太地区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在环境领域,1997 年9 月,东盟成员国发布《关于环境和发展的雅加达宣言》,主张东盟国家必须采取更具体的联合行动。②Kazu Kato and Wakana Takahashi,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Regional / Subregional Environ⁃mental Cooperation in Asia, Institute for Global Environmental Strate⁃gies, 2001, pp. 31-50.
就内部发展而言,彼时东南亚各国都面临加快经济发展、改善民众生活的艰巨任务。 而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发展更成为东盟加快区域经济合作的动力。 东南亚国家的金融、投资、贸易自由化既极大促进了各国对外贸易发展和国际资本的流入,也促使东盟各国的对外、对内经济依存度明显增加。 经济合作的实现促进了东盟各成员国家在安全领域的合作。③Dewi Fortuna Anwar, “National Versus Regional Resilience?An Indonesian Perspectives, ” in Derekda Cunha ed., Southeast Asia Perspectives on Security,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0,pp.82-88.东盟通过主导东盟地区论坛,强化了其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并将“东盟方式”作为决策机制的基本程序。基于成员国扩充与功能性合作的拓展,东盟进一步寻求集体身份的凝练。 1995 年8 月,第二届东盟区域论坛通过由东盟制定的《东盟区域论坛:概念文件》,明确指出“东盟在东盟区域论坛中承担核心角色”,并规定东盟区域论坛的参与者包括东盟成员国和东盟观察国、磋商与对话伙伴国;新的加入申请需提交东盟区域论坛主席国,由其与东盟区域论坛其他成员协商;论坛的主席国必须为东盟轮值国主席。 此类制度保障了东盟国家在区域间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也进一步凝聚了东盟各国的身份认同。 此外,东盟也开始尝试参与国际地区事务,在与东北亚国家、欧洲、美国等国家与地区的合作中,东盟选择以集体身份参与对话谈判,极大地提升了东盟的世界影响力。 伴随由经济到政治安全合作的拓展,东盟稳步推进区域内部的多方位合作,其发展理念与一体化思想也逐渐被域内外国家广泛接受。
东盟各国的相互依存有其历史与文化传统,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发展促使相关东南亚国家积极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并在政治、安全、经济和环境等领域谋求更深层次的合作与发展。④王子昌:“文化认同与东盟合作”,《东南亚研究》,2004 年第 5 期,第 27-31 页。冷战后,东南亚诸国在互动交往过程中主张了解彼此间的国家相似性与利益交叉性,通过扩大国家间双边合作的辐射面带动区域内多边共同体的建设,进一步体现了东盟方式的“求同”宗旨。 在该时段内,东盟成员国数量不断扩展、区域组织的功能作用日渐突出,内部的相互依存相较之前有了明显进步,并开始尝试参与国际地区事务,进一步提升了东盟的国际影响力。
六、过程求同型:自我约束影响下东南亚共同体的制度化建设(2003 年至今)
过程求同的核心内容是社会性关系,体现在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的构建过程中,国家与国家之间逐渐形成了较为统一的区域集体认同,并开始谋求为构建地区共同体而努力。①Amfinn Jorgensen-Dahl,Regional Organization and Order in South East Asia, The Macmillan Pree.Lad.,1982, p.73.进入21 世纪以来,东盟各国开始呈现由经济、安全领域向社会文化领域的拓展与延伸。 2003 年举办的东盟第九届首脑会议加速了一体化的整合进程,决定建成经济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及社会文化共同体,②尤安山等著:《“一带一路”建设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新格局》,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 年版,第128-130 页。更凸显了这一时期东南亚共同体在社会化路径中“过程求同型”的本质特征。
从区域整合历程来看,东南亚共同体的构建是区域内国家在共有记忆、相互依存及域外压力驱使下进行社会学习与形成认同的过程,在此期间,自我约束的作用越发明显,并直接影响了“东盟方式”的形成与发展。
共有记忆催生了“东盟方式”的灵活性特征。 灵活性即东盟在议事中反复强调的“非正式性”与“松散性”,东盟各国通过灵活性特征避免成员国之间的冲突,从而和平与稳定地解决区域内问题。 东南亚各国在东盟框架下的合作可以理解为一个社会过程,各国在其中重新界定本国在区域内的定位、区域内部局势发展,以及区域合作参与者的利益大小。 在东南亚区域合作的发展历程中,东盟各国避免分歧,力促“东盟方式”的习惯来源于对共有记忆的深刻影响与相互依存方式的正面引导。③季玲:“关系性安全与东盟的实践”,《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 年第 9 期,第 108 页。东盟各方希望以政治上的中立及经济上的合作,同时提倡以谅解的形式解决区域内部争端,这也是“东盟方式”由初级向更高级发展的主要路径。 基于共有记忆的影响,东南亚各国意识到区域内部的地缘政治危机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是制约区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引入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平等和领土完整等原则,确保了区域内国家对独立主权的维护,并在东盟区域合作中找寻共通点,推动经济、安全领域向社会文化领域的拓展与延伸,积极搭建对话平台。 同时东盟成员国意识到只有作为一个整体,通过与区域外国家或组织进行合作,才能使这一区域富有活力。 依托共有记忆,东盟的成员国不断扩展,合作方式也日趋多样,也进一步促进了东盟集体认同的形成。
相互依存落实了“东盟方式”的协商一致原则。 东盟决策者们所倡导的协商一致原则反对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在东盟的议事方式中,反对联合国大会等国际机构诉诸投票的方式,在处理问题时并不追求完全一致,也不意味着一致同意。 在东南亚地区的发展历程上,以相互依存为基础,形成东盟意识与身份认同是东盟共同体建设的终极目标。 然而,在一个具有多元宗教、文化的地区,形成一种共有认同并非易事。 东盟各国从“求同存异、循序渐进”的东盟方式出发,选择了一条多元一体化道路,即不强求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的统一,而是选择在充分尊重多元宗教、文化和政治制度的基础上,通过交流和对话塑造地区认同。④Koro Ramcharan, “ ASEAN and Non - Interference: A Principle Maintained,”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Vol.22, No.1,2000, pp.60-88.东盟各国相互依存的现实促使国家间在合作的过程中更加注重集体身份的塑造。 2004 年11 月,第10届东盟首脑会议通过了《东盟安全共同体行动纲领》和《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行动纲领》,东盟以社会文化共同体为目标进一步推动地区一体化,“东盟方式”得到了充分落实。 当前东南亚区域共同体的建设虽未如预期具有一整套内部高度认同的价值理念,但区域内不同国家相互依存的现实给予东盟共同体发展的建构路径,国家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层面的差异性更刺激区域内国家意识到相互依存的重要性,从而加深了对共同体建设的理解与认知。⑤Seok-Young Choi, “Regionalism and Open Regionalism in the APEC Region(Southeast Asia Series),” ISAS, Vol.12, 2004, pp.157-175.
域外压力促使“东盟方式”呈现政府间合作的特征。 坚持以政府间合作落实东盟的区域发展,是东南亚各国在域外压力的影响下做出的政治决定,这一特征决定东盟在制度组成上不会形成类似欧共体式的超国家机构,更偏重亚洲、东南亚特色。 东南亚区域共同体的集体意识与域外压力联系密切,作为中小国家的东南亚诸国,无论是在殖民时代还是冷战时期都更加容易受到域外压力的影响。①王琛:“小国的自我认知与外交行为:冷战后新加坡外交的演变与新挑战”,《太平学报报》,2021 年第 2 期,第 43-57 页。在东盟成立之初,域外压力的影响使得东盟领导人更为关注政治、安全议题。 各国领导人多通过彼此间的私人关系获得合作的信任,并强调既禁止东南亚国家干预邻国的国内事务,同时也禁止域外大国对东南亚国家事务进行干预。 在后冷战时期,伴随东盟集体合作行为的逐渐成形,其与域外压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呈现出由被动承担域外压力到合理应对域外压力,更尝试将域外大国因素向着对本地区有利的方向引导。 2007 年11 月20 日,东盟十国领导人参加了在新加坡举行的第13 届首脑会议,签署了《东盟宪章》。 宪章明确了东盟建设的目标和宗旨,强调要把东盟建成一个繁荣、稳定、有竞争力及以人为本的共同体。②张虹鸥、黄耿志等著:《新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南亚发展与区域合作》,商务印书馆,2018 年版,第328-329 页。相关条款明确提出,东盟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更依靠政府间合作,通过首脑会议明确东盟的发展方向,善用域外压力拓展区域内诸国影响力,展现其在处理地区争端时的“东方智慧”。③李锋著:《“金砖+”合作模式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19 年版,第 323 页。
然而,在东南亚共同体发展的当下,进一步提升影响力、拓展在国际社会的活动空间仍面临一定挑战。 一般而言,建立高度互信的基础扎根于一方以自我行为的约束来提升邻近国家的安全感与信任感,从而提高本区域内的互信程度。 在东南亚共同体发展路径中,初期自我约束主要表现在东盟通过《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规范,从而形成集团效应,带动区域内其他国家效仿,④[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年版,第 548 页。其后通过以“东盟为中心”(东盟+X)的方式处理与域外国家的关系,试图构建一个以“东盟为中心的”地缘政治经济新秩序。⑤陈宇:“地区秩序转型与东盟中心地位的消解与再塑”,《太平洋学报》,2021 年第 5 期,第 15-27 页。东南亚共同体经历数十年发展,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展现出共通融合的阶段性特征,但由于“东盟方式”主张以温和的方式处理国家间关系,试图通过频繁的沟通来达成共识,虽力促友好协商的实现,也为区域发展增添了不确定因素。 当前东盟的社会化路径更加需要自我约束,以规范东盟成员国自身行为,从而进一步加强区域内部的团结整合。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缅甸国内局势持续变化,东盟成员国高度关注缅甸局势发展。 在国家政权不稳导致自我约束乏力的前提下,东盟各国更应积极利用“东盟方式”展开沟通对话,拒绝西方国家的干预和干扰,更拒绝用特定意识形态的方式看待缅甸局势,以地区共识为基础妥善处理区域内重大问题。
21 世纪以来,东盟各国提出“东盟共同体”概念并进行了制度化建设,以社会文化共同体为目标,进一步推动地区一体化。 《东盟宪章》明确规定了东盟的法律地位与国际地位,既体现了东盟各成员国对“东盟方式”的重视与坚持,更促使东盟各国在东盟的框架下愈发约束本国与他国,坚持依照国际惯例和东盟条约解决纷争,棘手问题交由东盟首脑会议协商解决,这种议事方式集中体现了东盟方式的“求同”宗旨。
结 语
本文提出了东南亚共同体建设的四种演进类型,并以共有记忆、相互依存、域外影响及自我约束四个变量对每一时期的东南亚一体化建设进行具体分析。 在实际发展过程中,经济、安全领域的合作与地区身份认同的凝练,共同形成了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化路径。 从历史演进来看,每一阶段的东南亚地区发展均有不足,但螺旋式上升的整体趋势更加明显,且呈现由结构型互动向过程型互动、由存异式合作向求同式合作的转变。
总体而言,社会化路径的形成发展促使“东盟方式”日趋成熟。 东盟共同体内部共有记忆影响深入、相互依存日益显著、应对域外压力的行为日趋成熟、区域内各国自我约束方式的贯彻执行,既促进地区共同体的不断发展,也给予“东盟方式”最佳的实践场域。 在欧洲一体化面临一定困境,欧美政坛“黑天鹅事件”频发的当下,“东盟方式”展现出符合本地区政治—文化传统的独特优势。 有别于传统上以超国家和法律化为主轴的欧洲一体化理论,东南亚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化路径更加强调以磋商和对话等非正式和具体方式进行合作,为构建与丰富具有广大发展中国家特色的区域合作理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