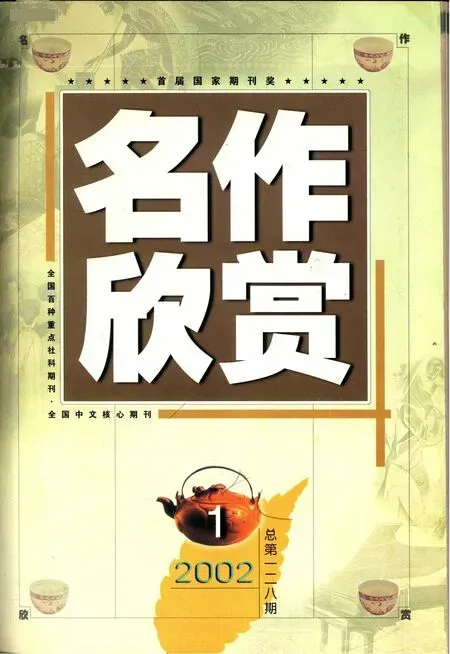韩愈《石鼓歌》:元和中兴的先鸣之声
2022-01-12雷恩海
关键词:石鼓歌 韩愈 周宣王 元和中兴 时代精神
唐初,发生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歧州雍县三畸原(今陕西凤翔县南原)出土了十只石鼓,上有文字,书法古奥拙朴,结体谨严,引起学者的关注:“盖纪周宣王畋猎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也。贞观中,吏部侍郎苏勗纪其事云: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共称古妙,虽岁久讹缺,遗迹尚有可观,而历代纪地理志者不存记录,尤可叹惜。”(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件石鼓各刻四言诗一篇,原文七百字以上,现仅存二七二字。据前人考证,一般认为石鼓乃东周时的秦国刻石,记载秦国国君游猎情况,故又称猎碣文。石鼓出土,诗人歌咏其事,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仅仅提及一句“陈仓石鼓又已讹”,而韦应物《石鼓歌》专咏其事,曰:“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忽闻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也仅仅是歌咏其文字,而别无寄托,诗意比较单薄。
贞元年间,郑余庆将石鼓移至凤翔夫子庙保存,引起了好古敏求、关心时事的韩愈极大之兴趣。身为国子博士的韩愈以为,石鼓文记载了周宣王中兴事业,文字古雅,意义重大,呼吁将石鼓迁移至京师国子监保存,既方便学子研习,又可以彰显周宣王中兴的伟业,事实上也为经历安史之乱后数十年动荡局势的大唐王朝提振精神,激励朝野奋发有为,使大唐之基业中兴。事实上,《石鼓歌》不是一篇考古学术文章,乃是一首具有高超艺术成就的长诗,诗人寄寓了别样的襟抱,有其时代文化的思潮内涵。孟子言,尽信书不如无书,胶柱鼓瑟,难得真解,论其人而知其世,方可探知此诗之旨趣所在。
韩愈志大才高,刚强果敢,勇于任事,笃信儒道,践行之而不遗余力,“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捜而远绍;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进学解》)。韩愈之才,“自视司马迁、扬雄至班固以下,不论也”。“以六经之文为诸儒倡,障堤末流,反刓以朴,刬伪以真……当其所得,粹然一出于正,刋落陈言,横骛别驱,汪洋大肆,要之无抵牾圣人者。”自晋迄隋,佛老大行于世,儒学虽不绝如缕,实则危殆已极,韩愈“引圣争四海之惑,虽蒙讪笑,跲而复奋,始若未之信,卒大显于时。昔孟轲拒杨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余岁,拨衰反正,功与齐而力倍之,所以过况、雄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新唐书·韩愈传》)。因志于古道,韩愈遂有好古之嗜,且往往因事、因物而见道,不为虚文。作于元和六年(811)秋由国子博士升任河南令时之《石鼓歌》,一方面体现出其诗“驱驾气势,若掀雷抉电,奔腾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司空图:《题柳柳州集后序》)的本色,另一方面,诗人借歌咏石鼓而率先鸣唱元和中兴之声,以为时代精神之鼓舞,凝聚心力,以图振兴,再造唐室,其思想意义更为突出。
《石鼓歌》乃韩愈七古名篇,明人黄周星说:“诗之珠翠斑驳,正如石鼓。石鼓得此诗而不磨,诗亦并石鼓而不朽矣。”(《唐诗快》)如此长诗,不明章法,殊难领会。此诗长达六十六句,可分为四大段。
第一段,叙写创作《石鼓歌》的缘由以及石鼓的来历。“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开篇直陈其事,交代写作《石鼓歌》的缘由。友人张彻手持石鼓文拓本,劝勉鼓励诗人,尝试创作石鼓歌。受劝勉,“试作”,说得何其郑重严肃。大诗人李白、杜甫是写作石鼓歌的当然人选,可惜他们已经死了很久,而诗人说自己才能浅薄,又能拿石鼓怎么办呢——即难当创作石鼓歌的重任。虽是自谦,实则将自己与李白、杜甫并列,暗含李白、杜甫之后,自己是创作石鼓歌的当然人选。而以自谦的口吻说出,见出创作石鼓歌乃重大事件,必须郑重对待,勉力为之。张彻,贞元十二年(796)与韩愈结交,从韩愈学习。元和四年(809)登进士第,为泽潞节度使从事,改幽州节度判官,幽州军乱,被杀害。韩愈有《故幽州节度判官赠给事中清河张君墓》记述其生平事迹。
“周纲凌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周朝衰落,天下动荡,民怨沸腾,周宣王奋发图强,北征猃狁,南讨淮夷,使得周朝中兴。周纲,周朝之纲纪。周宣王,厉王之子,名靜,公元前827至公元前782年在位,平定四境,史称宣王中兴。周厉王暴虐,被流放于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史记·周本纪》:“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于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挥天戈,指宣王南征北讨之事,《诗经》之《六月》《采芑》记其事。韩愈以为,石鼓文乃记载周宣王中兴之事。
宣王中兴,诸侯皆朝周,天下大定,故而曰:“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蒐于岐阳骋雄俊,万里禽兽皆遮罗。”宣王大开明堂,接受万邦来朝贺,诸侯相率而来,腰悬宝剑、佩玉,叮咚鸣和,威仪盛大;宣王在岐山之南春猎,校练士卒,诸侯之师竞相驰骋,以争雄俊,万里山林,飞禽走兽,皆被拦截捕捉。这是石鼓文描写打猎校练军队的主要内容。明堂,古代帝王宣明政教之所,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教学等大典,均在此举行。宣王中兴,大开明堂,接受诸侯朝贺。蒐,春猎。周天子阅兵都通过畋猎进行。打猎,春天叫蒐,夏天叫苗,秋天称狝,冬天曰狩。岐阳,岐山之南。岐山为周之发源地,在今陕西。山之南、水之北为阳;山之北、水之南为阴。《左传·昭公四年》记载周成王校猎于岐山之阳,韩愈论断宣王事,当据《诗经·车攻》首句“我车既攻,我马既同”,与石鼓文首句相同,而《车攻》实为宣王校猎而作。然而,《车攻》序称宣王朝会诸侯、校猎在洛阳,而不在岐山。此四句叙写宣王中兴,大开明堂,朝会诸侯,校猎而征选士卒,威仪赫赫,正是石鼓文所记载的内容。
宣王中兴、朝会万邦、校猎征士,如此盛大的事件,当然应该有如椽巨笔记载,以传永久,万世不朽,因而曰:“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从那高峻的山岭开凿石材,制成石鼓,将宣王中兴伟业、岐阳校猎之盛举,镌刻于石鼓之上,以便垂告后世,千秋万代,永不磨灭。宣王侍从臣子才艺皆推第一流,遂拣选其中最为杰出者,撰写韵语,刻在石鼓之上,长留山坳,即使沧海桑田也永存世间。长久以来,虽历经雨淋日烤、野火焚烧,却始终长存世间,似乎有鬼神呵护,不许来侵袭。镌、勒,皆是刻石为文。墮嵯峨,从高峻的山岭上开采石料,制作石鼓。撝呵,挥斥,引申为卫护。诗人以如椽巨笔,极其庄重地摹写宣王中兴、朝会万邦、校猎征士,从臣颂扬刻石而期望流传千古,而“雨淋日炙野火燎,鬼物守护烦撝呵”,乃承上承启之句,石鼓为鬼神所护佑,千百年而不毁,永存世间。
第二段,摹写石鼓文,赞誉其文辞古奥和书法之拙朴精美。“公从何处得纸本?毫发尽备无差讹。”总括写来,赞美石鼓文:张彻从何处得到这样的拓本,与石鼓之真迹竟然毫发无爽,令人为之倾倒。“辞严义密读难晓,字体不类隶与蝌”,文辞严正,文义细密,然而古奥难懂,一句概括,轻轻带过,主要赞美石鼓文字体之拙朴精美:石鼓文极早,字体不像隶书,也不像蝌蚪文。隶书,汉字字体名,也叫佐书、史书,由篆书简化演变而成。把篆书圆转的笔画变成方折,改象形为笔画化,以便书写。始于秦代,普遍使用于汉魏。秦人程邈将这种书写体加以搜集整理,后世遂有程邈创隶书之说。《魏书·术艺传·江式》:“隶书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于小篆所作也,以邈徒隶,即谓之隶书。”蝌蚪文,古代书体,以头粗尾细,状如蝌蚪而得名。《水经注》:“古文出于黄帝之世,仓颉本鸟迹为字。秦用篆书,焚烧先典,古文绝矣。鲁共王得孔子宅书,不知有古文,谓之蝌蚪书。”
于是,诗人遂将重点放在对字体的描摹与形容上:“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石鼓文年代久远,难免有缺笔少画之处,恰似用锋利宝剑砍断生蛟龙,拙朴奇古,生猛刚健。字体布局结构,活泼生动,如同鸾飞翔,仙灵降临,又如珊瑚碧树,枝干相交,奇秀灵动,此处形容石鼓文笔势飞动而纵横交错。石鼓文气势遒劲飞动,如潜龙欲挣脱金锁,飞腾而去,又如古鼎跃水、织梭化龙,气势腾跃。鼍,鼍龙,又名猪婆龙,即扬子鳄,古人以为乃龙形而尤丑恶者,此处突出石鼓文字体之奇古。珊瑚碧树,班固《西都赋》:“珊瑚碧树,周阿而生。”锁钮壮,捆绑纽结的绳索非常粗壮。古鼎跃水,《水经注·泗水》:“周显王四十二年,九鼎沦没泗渊。秦始皇时而鼎见于斯水,始皇自以德合三代,大喜,使数千人没水求之。”龙咬断牵鼎的系绳,鼎遂不得出。龙腾梭,《晋书·陶侃传》:“侃少时渔于雷泽,网得一织梭,以挂于壁,有顷雷雨,自化为龙而去。”刘敬叔《异苑》:“陶侃尝捕鱼,得一铁梭,还挂著壁。有顷雷雨,梭变成赤龙,从屋而跃。”韩愈化用此二典,造句奇崛。此处诗人着力渲染石鼓文字之笔力劲挺,笔势生动,形象纷呈,令人惊心骇目。
这样拙朴刚健精美的石鼓文,可惜,“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遗羲娥”。鄙陋的儒者编选《诗经》之时,未能将叙写宣王中兴伟业的石鼓文收录,致使《诗经》之《大雅》《小雅》,因为缺少了石鼓文而显得褊狭局促,而无从容自得之气象。孔子离开鲁国而周游列国,可惜未曾到过秦国,错过了收录石鼓文的机遇,编定《诗经》真是选录了熤熤小星星而遗漏了太阳和月亮啊。《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仪者三百五篇。”无委蛇,无从容自得之气象。《诗经·鄘风·君子偕老》:“委委佗佗,如山如河。”朱熹注:“雍容自得之貌。”《诗经·召南·羔羊》:“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郑玄笺:“委蛇,委曲自得之貌。”那些陋儒,不认识石鼓文的价值,没有收录;而孔子最后编定《诗经》,周游列国,却未曾游秦国,也错过了石鼓文。羲娥,羲和与嫦娥,指太阳与月亮。对石鼓文没有及时收录,致使埋没、漶漫,诗人表达了深深的遗憾与惋惜。
第三段,叙写石鼓文非凡的价值以及诗人呼吁保护的经历。紧承上文“遗羲娥”之巨大遗憾,诗人说:“嗟予好古生苦晚,对此涕泪双滂沱。”——自己虽然好古,然而苦于生得太晚,不能将石鼓文及早收录,因而今日面对石鼓文之残损,也只能涕泪横流了。此一句总括提顿,表述石鼓文未能收入《诗经》、成为经典的痛心与怅恨,下文遂提出了具体的补救措施。
“忆昔初蒙博士征,其年始改称元和。故人从军在右辅,为我度量掘臼科。”当初,被征召为国子博士,正是元和元年,故友从军凤翔,主掌军务,为我想方设法,筹划发掘石鼓。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由江陵法曹参军,征召为国子博士。《新唐书·百官志》:“国子学,博士五人,正五品上。”右辅,即凤翔府。汉时京畿之地分为京兆、左冯翊、右扶风,称三辅。右扶风,即唐之凤翔府。度量,测度计量,即谋划、筹划之意。臼科,即坑。古鼓埋于地下,要发掘而出。
诗人深知石鼓的巨大价值:“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宝存岂多!毡包席裹可立致,十鼓只载数骆驼。荐诸太庙比郜鼎,光价岂止百倍过!”诗人沐浴斋戒,郑重地禀告国子祭酒:石鼓这样的至宝世间存留不多啊,用毡席包裹,很快可以送到京城;运送十只石鼓,也仅仅需要数匹骆驼,将石鼓进献于太庙,可堪与鲁桓公取得郜鼎相媲美,其光辉声价超过百倍啊。祭酒,国子监之长官。《新唐书·百官志》:“国子监,祭酒一人,从三品;司业二人,从四品下。掌儒学训导之政。”据《旧唐书·宪宗纪》及同书《郑余庆传》:“元和元年五月,左丞相郑余庆罢相,为太子宾客,九月,改为国子祭酒。”太庙,天子宗庙。郜鼎,春秋郜国造的宗庙祭器,以为国宝。后来被宋国取去。宋又将此鼎贿赂鲁桓公,桓公献于太庙。《左传·桓公二年》:“(宋)以郜大鼎赂公……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大庙,非礼也。”《左传·桓公二年》:“郜鼎在庙,章孰甚焉?”
石鼓文的价值还体现在诸多方面:“圣恩若许留太学,诸生讲解得切磋。观经鸿都尚填咽,坐见举国来奔波。”皇帝圣恩如果许可将石鼓留在太学,让太学诸生讲解学习,切磋琢磨。漢灵帝时刻石经,至京师观赏之人,络绎不绝;可以想见,石鼓安置于太学,我大唐之人前来观赏学习,如波涛奔涌。太学,古代设于京城的最高学府。西周已有太学之名。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立五经博士。弟子五十人,为西汉置太学之始。东汉太学大为发展,顺帝时有二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质帝时,太学生达三万人。魏晋到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学(国子监),或两者同时设立,名称不一,制度亦有变化,但均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唐国子监下设国子学、太学等七学,此处太学兼指国子学。鸿都,东汉都城洛阳门名。灵帝光和元年二月,置鸿都门学士上。汉代立五经于学官,置十四博士,各家经文皆凭所见,并无供传习的官定经本,常因文字异同引起争端。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石,用隶书写《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七经,请名手刊刻,镌刻四十六碑,光和六年(183)完成,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前。碑高一丈许,广四尺。这对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和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后汉书·蔡邕传》:“熹平四年……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
正因为石鼓如此重要,因而要格外谨慎:“剜苔剔藓露节角,安置妥帖平不颇。大厦深檐与盖覆,经历久远期无佗。”石鼓年代久远,又有残损,因此要格外小心:小心翼翼地剔除石鼓上的苔藓,露出文字方正笔划之棱角与屈折;安放石鼓也要平正妥当。太学大厦高大深广,将石鼓严密覆盖,遮风挡雨,期望石鼓永久保存而无意外。节角,指石鼓文字笔划之棱角与屈折。无佗,即无他,犹无恙,无害。《后汉书·隗嚣传》:“若束手自诣,父子相见,保无佗也。”
第四段,紧承上文,石鼓文有巨大的价值,诗人虽然提出很好的建议,然而世人并不重视,遂予以严厉的批评。“中朝大官老于事,讵肯感激徒媕婀。牧童敲火牛砺角,谁复著手为摩挲?日销月铄就埋没,六年西顾空吟哦。”朝中的大官僚老于世故,圆滑处世,哪肯感奋激发,仅仅咿咿啊啊、敷衍塞责罢了。石鼓被弃置荒野,牧童在石鼓上敲击取火,牛儿用之磨砺尖角,还有谁来观赏石鼓宝物,抚摸爱护呢?石鼓天天遭磨损,月月受消耗,长久埋没,诗人提出迁移石鼓于太学的建议已经六年了,也只能西望石鼓,空自念叨、惋惜。老于事,熟练于处理事务之道。此处乃贬义,指圆滑世故,敷衍塞责,不负责任。媕婀,依违阿曲,无主见。敲火,敲击石头以取火。六年西顾,韩愈元和元年(806)自江陵召为国子博士,至写此诗时已经六年。时韩愈在东都洛阳,石鼓出土地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畤原,故曰“西顾”。
诗人于此,以漫画式的笔法,勾勒了“中朝大官”老于世故、圆滑依违的丑态,惜官保位,敷衍塞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对国之重宝石鼓毫无感情,绝不重视,任凭其弃置荒野,遭受风雨侵袭、牧童敲火、黄牛砺角的消损。诗人迁移太学、妥善保护的建议落空,也只能“六年西顾空吟哦”了。
于是,诗人进一步揭示石鼓的巨大价值和意义:“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继周八代争战罢,无人收拾理则那。”号称书圣的王羲之书法,与石鼓文相比较,只不过是为世俗所喜欢的“趁姿媚”之“俗书”罢了,王羲之几页《道德经》的俗书尚且能够换来一群白鹅。自从周以来八代争战,文物损毁,而石鼓得以流传后世,却无人重视,天理何在啊!
王羲之有书圣之称,《晋书·王羲之传》曰:“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唐太宗李世民喜爱王羲之书法,遂为世所重,流行极广。王羲之“性爱鹅,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善鸣,求市未得,遂携亲友命驾就观。姥闻羲之将至,烹以待之,羲之叹惜弥日。又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甚以为乐”。
韩愈好古,诗歌追求“冥观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荐士》)的拙朴劲健之美,与石鼓文相比较,王羲之的书法就不免显得媚俗了。贬抑王羲之书法,旨在标举石鼓文书法之拙朴刚健、古色斑斓,正是上文所说:“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继周八代,指自周以下之秦、汉、魏、晋、元魏、齐、周、隋。理则那,其理则为何。那,“奈何”的合音。《左传·宣公二年》:“牛则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则那?”杜预注:“那,犹何也。”杨伯峻注:“那,奈何之合音。顾炎武《日知録》三十二云:‘直言之曰“那”,长言之曰“奈何”,一也。’”李白《长干行》之二:“那作商人妇,愁水复愁风。”
自周以后,八代战乱,至大唐则天下太平,崇重儒学,尊仰孔子孟之道,以儒学选择人才,治国理政,理应重视这记载宣王中兴的石鼓啊:“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柄任儒术,重用儒学之士,委之以权柄。崇丘轲,尊崇孔丘孟轲。因而,诗人呼吁:“安能以此上论列,愿借辩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于此,呜呼吾意其蹉跎!”怎样才能把自己的这些意见,提到朝堂之上来讨论,愿意借着张生善辩如悬河之口,广为流布。石鼓歌也就要结束了,可叹我的一番深切用意,恐怕也要流于空言了。辩口如悬河,《晋书·郭象传》:“太尉王衍每云:听(郭)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蹉跎,失意,虚度光阴。谢朓《和王长史卧病》:“日与岁眇邈,归恨积蹉跎。”李颀《放歌行答从弟墨卿》:“由是蹉跎一老夫,养鸡牧豕东城隅。”
韩愈于诗的末尾,再三申述,在这个崇重儒学的时代,要重视记载宣王中兴、朝会校猎事件的石鼓文,希望自己的宣传、呼吁不要落空了,拳拳心意,谆谆告诫,意犹未已。
韩愈写作此诗,既是记述描摹作为文物的石鼓文,又是叙写记载宣王中兴、朝会校猎事迹的石鼓文,极尽渲染之能事,而别有寄托。
唐宪宗乃中唐比较能干的一位皇帝,即位以来,励精图治,向慕贞观开元盛世,信任宰相,讲论政事,对强藩叛镇执行比较强硬的政策,以恢复全国统一的局面,“军国枢机,尽归之于宰相。由是中外咸理,纪律再张,果能剪削乱阶,诛除羣盗,睿谋英断,近古罕俦”(《旧唐书·宪宗纪》)。从元和元年至五年,先后平定蜀中刘辟之乱、夏绥杨惠琳之乱、淅西李锜之乱,擒获图谋不轨的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韩愈作此诗的元和六年,朝廷正在酝酿着更大规模的平叛统一战争,最终讨平叛乱不臣的淮西吴元济,因而史臣称颂宪宗为“唐室中兴之主”,所谓:“贞元失驭,群盗箕踞。章武(宪宗)赫斯,削平啸聚。我有宰衡,耀德观兵。元和之政,闻于颂声。”(《旧唐书·宪宗纪》)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韩愈创作《石鼓歌》,歌颂记载周宣王中兴的石鼓,感慨于“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大开明堂受朝贺,诸侯剑佩鸣相磨”,渲染周宣王中兴、大开明堂、校猎征士,而石鼓文刻石记功,陈述国家之盛,乃一代史诗。韩愈在此,有意无意之间,都传达了对唐宪宗励精图治、中兴大唐的颂扬,渗透着诗人对现实政治的巨大热情,以及对太平盛世的强烈期盼。
因而,诗人在摹写石鼓文时,融入了巨大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情感,感奋激动人心。对石鼓文拙朴刚健书法之赞美:“年深岂免有缺画,快剑斫断生蛟鼍。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钮壮,古鼎跃水龙腾梭。”表面上是颂美书法,突出石鼓文的文物价值,实际上主要是彰显石鼓文的政治意义,因而才有“陋儒编诗不收入,二雅褊迫无委蛇”,未能收入《诗经》,致使《大雅》《小雅》无雍容不迫之致;孔子删《诗》,也无从辑录整理,造成了巨大的缺憾。显然,是从思想内容上突出作为载体的石鼓文价值——记录了宣王中兴的伟业。
于是,诗人向当局建议,希望能够将石鼓安置于太学,供天下人学习、摹写,其价值超过郜鼎,也会超过汉代熹平石经,产生巨大的轰动效应。而其核心则在于石鼓文是中兴王室的象征,具有极大的示范意义。
可惜,诗人的建议,未被庸陋圆滑的“中朝大官”所采纳,石鼓仍然被弃置荒野,遭受种种的损毁。为其不平遭遇,诗人极为愤激,“六年西顾空吟哦”。自周以降,秦、汉、魏、晋、元魏、齐、周、隋八代,战乱不已,至大唐而至天下太平,颂赞石鼓文的落脚点乃在大唐中兴:“方今太平日无事,柄任儒术崇丘轲。”大唐中兴,崇重儒术,任用人才,而作为中兴象征的石鼓文,正适应了营造社会氛围的现实需要,正应上文“坐见举国来奔波”。诗人以石鼓为载体,一方面欣赏石鼓文之拙朴刚健的艺术审美,一方面特别重视其周宣王中兴、大开明堂、校猎征士的丰厚内容,而且融入了诗人对现实的深切感受,将唐室中兴的现实需要与周宣王中兴暗中相联系,若断若续,若即若离,对石鼓的歌颂,遂融入了现实的内容与强烈的个性情感,因而感人至深。诗的末尾,愿借张生之辩若悬河的利口,向当朝游说:既充满期盼,又深怀忧虑,表现出矛盾的心理,感慨于石鼓之“日销月铄就埋没”的不幸,又融入了自身不遇的遭际。创作《石鼓歌》之后的《进学解》,以学生的口吻,陈述韩愈一生遭际,有曰:“公不见信于人,私不见助于友,跋前疐后,动辄得咎。暂为御史,遂窜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见治。命与仇谋,取败几时?冬暖而儿号寒,年登而妻啼饥。头童齿豁,竟死何禆?”有助于对《石鼓歌》的深入理解。
韩愈此诗,断定石鼓乃周宣王中兴伟业之产物,又赋予大唐元和时期之社会世情与思想精神,前代文物而兼后世光彩,石鼓遂成一载体。将周宣王中兴与大唐中兴绾结为一体,既有古物斑斓之美,也有古今精神相通之奇幻,才情纵横,内容丰富,而逻辑结构颇为明晰,彰显其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本色,句奇语重,古奥富赡,体势宏敞,典重瑰丽,且一韵到底,而文气浑灏流转,给人以精神的强烈震撼和独特的艺术审美享受。
作者:雷恩海,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研究中心主任。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史、文化史研究,出版有《中国古代文论的融通与开拓》《大历诗略笺释辑评》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