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 冬
2022-01-09巫昂
凛冬将至,独自居住的她明显感到冷,新入住的房子还没有彻底收拾停当,客厅里还堆放着没安装好的书桌、书架。洗衣机先是买了普通的,后来才想起来买个烘干机,海边的湿气比较重,十二月份的青岛特有的湿气。她站在阳台上,感受到海风的刺骨与冰冷,这个阳台因为装修仓促且预算有限,没有改成封闭式的。她向着洋面望去,初夏的时候第一次来看房子,她确实就是看中了这里可以看到大海,蓝色的、一动不动的大海,现在由蓝转成蓝灰,随着天气的变化,还会越来越灰。她忍住没往坏里想,回到客厅打开冰箱,里面空空如也,昨天才送到的冰箱还处于氟静置的24小时之内,她打算等周末彻彻底底地擦拭一遍后再往里放吃的。
每天快要七点了才从公司回到新家,开着自己的单厢小车,她总是走车道最靠右侧的那道,导航的声音开到最大。先买车后买房就为了能够买套便宜且略大的房子,所以车的预算在五万以内,她选择了纯白色的,纯白色的车开在碧海蓝天里多美啊,当时她想,虽然这是车外的人才看得到的。而她往往像一只疲惫不堪的鸟儿一样在回程之中,用鸟形容她不够精确,她更像一只飞不起来的笨拙的家禽。
晚饭吃什么?她在想,还没来得及去找附近的菜市场,也没有好好看看美团,她恍惚想起前两天有个本地群分享了一个“青岛一人食”的小程序,主打一个人也可以点的价格合理的外卖,说是不需要配送费,她当时随手就收藏了。虽然阳台上很冷,她从过去的家搬来的一只藤编的老旧躺椅放在这里正好。她找了件大衣披在身上,安安静静地斜躺在躺椅上点餐。
目前,这个小程序上的“一人食”的选择并不多,图文并茂,她看上了首图主推的热乎乎的多种食材俱全的寿喜锅,有牛肉片,有菌菇,有豆腐,还有蛤蜊肉和几尾虾仁。寿喜锅一直是她去日料店時比较喜欢点的套餐,通常店里会配一碗白米饭,外加一份小菜——芥末章鱼或者隔夜腌渍的棋子黄瓜。其实她极少自己下馆子,她在青岛最好的闺蜜移居烟台之后,她半年多没人可以结伴去餐馆吃饭了,只能自己去。这个小程序上的寿喜锅是装在一只看起来是一次性的硬锡箔纸小锅内的,带着盖子,店家承诺会保温送货上门,青岛市区范围内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送达。
她住在靠海的东南边,这里周边的地形地貌仅够修建一个沿着海岸线排列的体量很小的小区。她下了单,用微信付款,填上了自己的住址,想了想,没用真名,用了个网名“一只溺水的鱼”,那是她在最黑暗的时期,上一段婚姻行将结束时那场漫长的拉锯战中给自己起的名字,一只鱼如果没有鳃,只有类似于人的肺叶,在大洋深处该有多窒息。她直到现在还常常在半夜突然醒来,胸口压着一只肥硕的大象一般,想喊,喊不出来,不喊,又极度莫名地恐惧。她的嘴在半空中形成漏斗型,黏稠得像用过无数次的油一样的液体从这个口子向下滑行,形成了她胃液、体液的一部分。
离婚之后,她很长时间无法吃油腻的东西,可能是因为此前大月份流产了一次,所以只要外出吃饭,去的基本上都是日料店。青岛的韩餐馆比日料店多,但是日料的选择也不少。她经常在清水东路尽头把车停下,那里有一家店面很小的日料店,夜里还可以喝酒,但她不喝酒,往往在那里一直坐到店里喝酒的青年男女越来越多,她才昏昏沉沉地回到车里,点燃发动机,听它在前盖内闷闷地响动。她会那样又在车里坐半个小时,只为了避免回到冷冷清清的家。
新搬的家离市区远,路上有一段路又没有路灯,黑漆漆的,她买房和装修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一点。海浪在不远处涌动,击打着跟路面一样黑漆漆的礁石,那些礁石上密布着贝类,她还想找个时间去看看能不能捡点什么回家蒸着吃,香螺,或者更为常见的脉红螺。
在外卖送来之前,还有些时间,她开始下单买一些必需的家具。床头柜现在是一只快递纸箱,铺上一条雪纺围巾还能凑合着用,暂且不用买了,所有的书和杂物还都堆在纸箱里,无论如何至少得买一个六层的书架,兼作置物架,然后是餐桌,一个人买个四方形的比较合适,外加两把塑料制一体成型的白餐椅,足够了,平时最多来一个朋友,还可以坐一坐。厨房的橱柜也还没有做,她想着在之前的出租房多待一个月,就要多付一个月的房租,这边还有房贷,两头亏损,区区一点工资压根不够花,等不及放上几个月通风透气散甲醛,她便雇了一辆小货车搬家入住了。
终于把购物车内放了好长时间、反复比较的书架和餐桌椅选定了,付款的时候,她想起件事,于是又打开刚才订餐的页面,拨了上面留的送餐手机号。
“我是海岸丽景三号楼的,对,六层,没有电梯哦,得爬楼,不好意思,我还没到家,能不能把餐放在门口,给我发个短信就可以了。”
电话那头的男人低低地“嗯嗯”了两声,就挂了电话,几乎与此同时,楼道外就传来轻微的脚步声。她住在顶层,对面单元还没有入住,也还没开工装修,成天都是静悄悄的。她看了眼下单时间和现在的间隔,只有二十五分钟,照理不会这么快送达,但她没有开门,反正已经告诉送货的人只需要放在门口了。她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将耳朵紧紧地贴在防盗门上,没有听到更多的声响,确认无疑后,将门开了一个细缝,外面地上静静地放着一只黑色的保温袋,做成复古提手的款式。楼梯上并没有人下楼的声音,那人一定下楼下得又快又轻盈,应该不是个胖子,而是瘦小又动作敏捷的人。
她探出头去,迅速地提起餐袋,随即将身体缩回来,门开的量仅够她的体宽,多一毫厘都没有。没有餐桌,她在一只大纸箱上凑合着吃,在阳台附近,正好抬头就可以看看海面的风景,又不至于吹冷风。她在纸箱上铺上了两层报纸,打开保温袋,果然还是热乎乎的,这份寿喜锅的品相不错,食材的量也很足,还认认真真地配了双乌木筷子,以及一把像模像样的硬塑大勺子,象牙白的。她洗了一下筷子和勺子。
她半弯腰在纸箱跟前吃了起来。她先夹起一片肥牛片,吃进去还是滚烫的,简直烫嘴,像是刚从厨房直接端出来的那么烫。牛肉的口感不错,没有腥味,看来是拿姜片和料酒汆烫过的。寿喜锅需要用到寿喜汁,她感觉还是挺地道的,虾和蛤蜊也新鲜。她不是青岛本地人,而是来自盛产蔬菜的寿光,在青岛接近十年,对海鲜的新鲜与否也很挑剔。此刻她觉得满意,虾是挑过虾线的,这个做饭的店家做事认真。她一点点将所有的东西都吃完,最后还喝光了汤,一点渣渣都不留,觉得这个容器还可以再利用,拿到卫生间的水龙头底下仔仔细细地洗干净,放在一旁晾干。
饭后,她没有下楼散步,小区人烟稀少,外边黑漆漆的马路上,虽则冷清,冷不丁还是会有呼啸而过的车子,像是一条突然出现在隧道里的光溜溜的蛇,蛇身上的鳞片又凉又滑。饭后,她绕着空荡荡的客厅,揉着肚子转了二十圈,或者更多,一边盘算着将来客厅里还需要些什么,沙发前需要一张不那么大的地毯吗?最好是带点小碎花、棉质衍缝的毯子,她不嫌弃花色陈旧,那样比较耐用,坐在上面舒适,又易清洁。她想起昔日的猫,离婚前夕得急病突然死了,要不然它最喜欢睡在珊瑚绒质地的毯子上,也要为它专门买只珊瑚绒的小窝。过去的家尽数毁了,她几乎什么也没带,任何用过的东西,可能都会带来一些坚硬而又刺痛人心的回忆。
“你说什么?”她自言自语,用特别小的声音对自己说:“我没说什么呀,那你呢,你在说什么?”
这是她打小的习惯,自己跟自己聊天,无限延续,什么也没说,但是就像说了许多遍一样。入夜的海面,风格外的冷,远远的,不经意的,似乎有轮船的汽笛声,又像是假的,是幻听,那虚假的声音,默默地飘散在海面上、半空中。她极目远眺,在猎猎的风里,想在洋面上看到些什么,这个海湾的拐角处,正好无法看清市区的灯火,只有灰色调的、冷清的海景而已。
接下来该做些什么呢?她想了想,进了卧室,斜靠在两只叠起来的枕头上,翻出毯子盖住腿和肚子,拿起枕头边那个用了很久的iPad,打开爱奇艺,开始刷剧,二刷《知否知否》。屋里还没有钟表,所以听不到滴答滴答的声响。她想了想,起来拉上了窗帘,关上卧室门,打开放在纸箱上的一盏特别简陋的床头灯,又蜷缩回了毯子里。她有一双苍白、修长、骨节突出的手,当这双手放在毯子外时,从第三者的视角看起来有些可怖,镜头静静俯视,靠近,整个画面只剩下她的那双手。
第二天,她依然得去上班,一整天都在跟客户打电话。她是个电话卡销售员,卖联通包月卡,到了下午,感觉自己整个脑袋都要肿起来了,话也不想说了,发出声音只是利用了声带下意识的共振,并没有过脑子,就这样,一天也成不了几单。作为一名老员工,日常还得帮着培训新人,新人一个个笨得跟玻璃瓶热水袋似的,刚教的东西像热乎气儿立马散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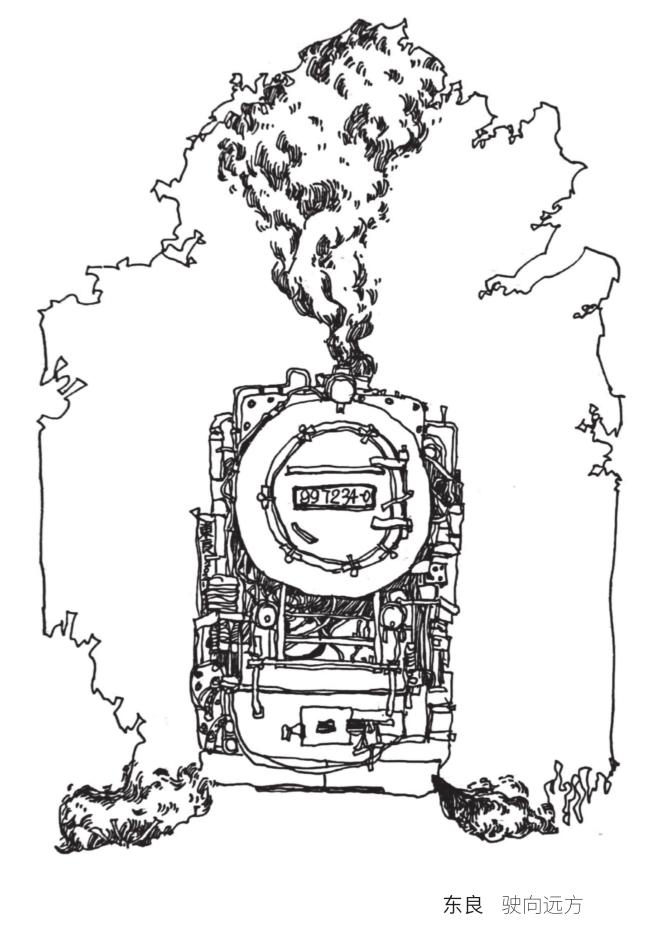
回家路上,她拐入了之前住处附近的菜市场,买了些菜。她有一只小米的全能电磁炉,能煮能炒能蒸,特别适合这个过渡期使用。她买的菜多数是用来做荤素搭配的杂菜,还买了一斤小鱿鱼,小鱿鱼蒸一下就可以蘸着酱油吃,这几乎是她最喜欢吃的海鲜,小小的鱿鱼肥嘟嘟的,八只爪子没有同类那么张牙舞爪,吸盘迷你而小巧,日常都是缩起来的。这也像她自己,這么多年她从未像那些贝类攀附在礁石上,仅像鱿鱼一样深深地隐藏在海底,或者像那些长着浓密硬刺的海胆,静态的,固执的。
回到家,她在卫生间的小洗漱台洗那些鱿鱼。她打算蒸个鱿鱼,炒个西兰花,然后做一点点米饭。米饭就放在一只碗里蒸,先蒸米饭,再蒸鱿鱼,最后炒菜,如此,两菜一饭,外加一杯白开水,就着外面渐渐昏黑的海面,慢慢吃。鱿鱼内有肥厚的籽儿,正当季,她吃不了那么多,冻了一半起来。餐后她一边啃一只烟台的梨,一边在客厅转圈儿散步。卧室的窗帘早起后就没有拉开,她过去拉开了窗帘和窗户,让风进来,主卧和客厅阳台一个朝向,实际上是朝东,但不是正东,因为海岸线不是正南正北走向的,而是微微地向西北倾斜。在这海的岬角,任何风吹过来都加剧了,这也是她入住后才感受到的。海风进入了这喇叭状的狭长地带,像是受到了挤压,但是她不怕风,甚至喜欢风,夜里听到外面风声呼啸也不觉得害怕。
真正可怕的,对于她来说,似乎是突然出现的人,陌生人。
这个小区她一个人也不认识,小区太新了,连配套的小菜店都还没有,只有一家杂货店,是一楼的一家人开在靠近人行道边的房间的。要买包烟或者一瓶啤酒的人,得踏上两级木头台阶,才能够得着主人递出来的东西。她去买过一包盐、一瓶醋,包装极其简陋,而且像假货,她打算不再去了,以后类似的物品需要靠网购。
那个周末她开车回了一趟老家,从父母家拉回来一些现成的床上用品和其他家什。母亲一定要她带上一只她不知道从哪个庙里求来的红布做的护身符,折成好几折,里面写着几句吉祥话,她随手就把它套在脖子上。
“你这样下去可怎么好?”当妈的忧心忡忡地看着她。
“怎么下去?”
“一个人孤零零的,我和你爸还得帮你哥看孩子,也不能去帮帮你。”
“我每天上班下班,日子好打发得很,那个地方很偏的,生活还不方便,你们去了也不习惯。”
“你这么说我更担心了,那个谁还来找你麻烦不?”
“找什么麻烦,人家过得好着呢。”
“哪儿过得去?那个家伙过去要不是靠着你,能有口饭吃?你看看你为了离婚,房子什么的都留给他了。”
“房子要紧,命要紧?”她小声说,也许她根本就没有接母亲的这句下茬,作为一只深海的鱿鱼,她只能在深不见底的黑漆漆的地方,自己跟自己说话。她看着母亲,年迈之后的母亲越来越像她的女儿,梳起来的头发上夹着一只塑料发夹,玳瑁色的,她帮她把那只发夹取下,整理好头发后别上,然后打算返程。
车子先往西边,再折往东南,大海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她开了会儿车窗,让海风吹进来。风砸在右边脸上,疼到麻木,但她不想关窗,也不想开暖气,方向盘上的两只骨节突兀的手,从冻得通红,到冻得发紫,像尸斑,她看了一眼手背,甩了甩手,这个念头闪了过去。与此同时,一辆巨大的卡车从身侧呼啸而过,司机不停地鸣喇叭,她不小心换了车道,但是没有打转向灯,正好是这辆卡车要超车的时候。
她的方向盘猛地左右打了几次,车子在高速上扭动蛇行,差一点就撞上了护栏。她惊出了一身冷汗,那辆大卡车早就呼啸而去,还冲她鸣了几次喇叭,并连续闪了两次车前大灯。她在一侧停下车来,惊魂甫定。这里看到的海非常开阔,海鸥正成群结队地鸣叫,它们远远看起来就像一条条脏兮兮的抹布。她下了车,站在路上,看了一圈车子,似乎没有大碍,油箱没有在滴油,她又用脚依次狠狠地踢了一遍车轮子,轮子没有瘪下去。实际上车内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汽油味,她反倒没有觉察。
拿出手机,她发现自己错过了一个电话,打过去,是送家具的货车司机,此刻正在小区门口等她。她急忙回到车里,想着天色已晚,回去肯定来不及做饭了,便打开之前用过的小程序,急急慌慌地点了一份泰式虾仁菠萝饭,有饭有菜。
海面上的雾气越发浓重,那些破抹布还在奋力飞行,她启动了车子,淡淡的汽油味似乎加重了,但她依然没有察觉,只想着赶紧回去。车子在行进的过程中微微晃动,她以为是自己受了惊导致的,也不敢开快,又花了约莫25分鐘才到家。小区门口果然蹲着个货车司机,正拿着大葱卷饼吃,车上没有其他人。她等他吃完东西,一起开进小区,司机下车,打开厢式货车的后门,找到了她的东西,往地上一滑。
“师傅,帮我一起搬上去吧?”她说。
“有电梯没有?”
“没有。”
“几楼?”
“六楼。”
“那不行,我还有好几家要去送呢,等你都耽误了一个小时,商家没人送货入户,我们只是负责物流的。”
好说歹说,司机就是不肯帮这个忙,他让她喊保安,或者随便找个邻居,无奈这栋楼离大门还有段距离,保安也好,过往的邻居也罢,此刻都看不见。司机二话不说,上车疾驰而去,将她和那堆货物扔在楼下。于是她开始一个人扛起那些板子,上了一趟楼后,放在家门口,再飞速地下楼,担心被人顺手拿走了,走到三楼楼道拐角,跟前冷不丁出现了一个男人,手里提着黑色的保温袋。
“是我的餐吧?我是602的。”
“是‘一只溺水的鱼’吗?”
“是的,你帮我放在家门口,我得赶紧下去搬东西。”
“好的。”
他上楼,她下楼,两人分头往不同方向移动。从楼梯的横切面来看,向上移动的送餐的男人脚步不着痕迹,轻盈得跟练过轻功一般,他走路像是自动悬浮的,脚底板离楼梯踏步有半个厘米的距离,一步跨两级甚至三级台阶,迅捷又有力量,只是他的力量是向内收的,外人觉察不出异样。她呢?这几年生活与工作都像过山车一样高高低低地往复,在一圈又一圈的闭环当中循环,她甩不出自己的轨道也不知道怎么甩,最后所有的东西都以脂肪的形态积压在体内,是的,除了手脚瘦小之外,她是个略显臃肿的人,肥厚的背和腰腹被灌注了大量的、多余的固态油脂。又沉重又松泡泡的她下楼的时候,上身前倾,两条腿像是承受不了腰以上的体重。
当她踉踉跄跄冲到单元门前,他已经到了六楼又折返到四楼了。两人移动的速度不同,故而所在的位置很快有了交集,当她正低头吃力地抬起下一件包装好的板子时,突然感到另外一头一轻。抬头,是送餐的那位穿黑灰棉夹克、牛仔裤和高帮皮靴的男人。
“谢谢啊,太重了实在是。”她说。
他没说什么,两人走了几步,他干脆说:“我一个人来吧,你拿点轻的。”
她放下板子,拿起了边上的沙发垫,沙发垫放在蛇鳞包装袋里,虽然鼓鼓囊囊的,但是没多重。两人一前一后地走进楼道。这个时间点,该到家的邻居也到家了,她感觉这个单元几乎还没有什么人入住,像她这样急不可耐地搬进来的人还在少数吧。他即便身负重物依然身轻如燕,很快她就追不上了,当她走到五楼时,他已经在下楼的途中了。
“还有一趟,你别下来了。”他说。
她开了门,吃力地把放在门口的东西搬进屋子,同时将门大开着,离开家的时候匆忙,通往阳台的门没关紧,此刻已经被大风刮开,风嗖嗖地吹,屋里凉极了。等她去关上那扇门一转身,看到那个男人站在客厅中央,肩上扛着件放着大长条板的包装箱,他进来得悄无声息的。
她赶紧招呼他放下东西,并帮他一起,他很自然地说:“你赶紧吃饭吧,我今天也没别的单子,可以帮你把这些东西安装起来。”
他帮她把那只保温袋拿到屋里,准确无误地放在她临时用来吃饭的纸箱子上。她想了想,书架安装肯定很费功夫,有个人帮忙也不错,于是道了谢去卫生间洗手。她洗完手,在镜子里就看到他站在身后,来不及张开吃惊的嘴,他已经把擦手的小毛巾递给了她,自己走进干湿分离的卫生间内间,上厕所去了。
他在厕所里待了不短的时间,她出来发现房门已经关上,防盗门反锁,卧室的窗帘也拉上了。她坐在小圆塑料凳上,拿出饭菜,饭菜确实是热乎乎的,锡箔纸盒内放着虾仁菠萝饭,菠萝与糯米的比例放得恰恰好,糯米的米粒不软不硬,还有椰浆的奶香味,虾仁是鲜虾剥了壳子,跟上次一样,处理得干干净净。她也特别爱吃虾,跟小鱿鱼一样百吃不厌。热气深藏、甜滋滋的菠萝饭,她用店家,也就是此刻正在帮她安装家具的男人配送的勺子吃,这样一会儿也省得洗一只勺子。这两天奔波下来,她累得浑身疼,只想吃甜糯米饭缓解一下疲劳的感觉。她吃得很慢,那个男人安装的速度却很快,显然是她的三倍速,看起来就像是视频快进。他不爱说话,一声不吭地照着图纸埋头干活,她吃完那盒菠萝饭时,他已经差不多把书架都安装好了。
然后他们俩合力安好了沙发,沙发比书架简单多了,不到十分钟就搞定了。即便如此,她帮的忙也屈指可数,主要都是他在弄。沙发是三人座,她最终决定买三人座的缘由是万一父母来做客,她可以睡在这上面,作为一张床。当她把靠垫的套子都套好,并整整齐齐地放在上面之后,他突然说:“你躺上去试试。”
“什么?”她一时间没反应过来。
“你躺上去试试。”
“我?”
“对,你。”
他突然上前一步,紧贴着她,盯着她的脸看,她还没来得及反应,他已经一把将她推倒在沙发上。这一切发生得特别突兀,她刚想张嘴惊叫,他已经用半边身体紧紧地压住她,一只手捂住她的嘴,另一只手伸出去,往地上够,从沙发底下拿出来一卷胶带,这是她搬家打包时用剩下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他找到且放在了沙发底下。他用嘴咬住胶带的一头,撕拉开一段,将她的嘴先粘上一段,用牙咬断,而后开始将她的身体和沙发一圈圈地缠绕在一起。她不停地挣扎,想要用脚踢他,然而他很快将她的两只脚用胶带缠绕在了一起,再绕大圈,很快一卷胶带差不多用完了,这下,她既发不出声音也无法动弹了,她用两只惊恐的眼睛死死地瞪着他。
他好像当她不存在一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去卧室拿来了那条线毯,盖在她身上。她进屋后换了拖鞋,脚上穿着袜子,他当然没有换鞋,此刻轮到他换拖鞋,她多买了一双男式拖鞋,给父亲准备的,他穿上刚刚好。接着,他自己烧水,从不知道什么地方找出来一包安吉白茶,给自己泡了一杯。这时候已经是夜里九点左右了吧,她挣扎累了,也觉得无济于事,闭上眼睛休息了一会儿,眼泪不知不觉淌出眼角,他一边喝茶一边瞥见了,抽了一张纸巾过来,半弯下腰,帮她擦去了眼泪。他擦拭的方式既不粗暴也不简单,相反,还细致入微,像是在擦拭上好的钢做的一把刀的刀刃。她紧闭着双眼,一动不动,任由他将自己的眼泪擦干净。
当晚,他洗漱完,就躺在她的床上睡觉,临睡前,写了一张纸条问她:“上厕所吗?”她使劲地点点头,他将她身上的胶带一层层撕开,不知道邻居,如果有的话,听到这个声响做何感想。他将她的两只手依然捆住,嘴上的胶带也没撕开,就这么押她到了卫生间,为她脱下裤子,按住她的肩让她坐下。他就站在跟前,她无法顺畅地解决,于是他走开一点,将门掩上,留一条细缝观察她,她顺利地小便了。而后,他将她捆回了沙发,这次用了一捆尼龙绳,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下过楼(下楼的时候拿了她家的钥匙)拿了放在车里的绳子。
他开着房门睡去,好像睡得挺晚的,临睡前看了很长时间短视频,有时候还发出低低的笑声,短视频的声音盖住了窗外海浪的声音。她本以为自己无法入睡,因为太冷,结果他又拿了一床被子来给她盖上,再后来,屋里的灯都熄灭了,她也就在昏昏沉沉中睡去了。半夜,她醒来两三次,屋子里弥漫着一个陌生男人的呼噜声,比她前夫的要轻,要慢,他似乎睡得很香。她在空气中闻到了一股梨花的香气,之所以分辨得出是梨花,是因为老家院子里就有一棵大大的梨树,每年春天,雪白的梨花携带着自己特有的清淡的香气,在太阳底下灼灼生辉。她觉得诡异、恐惧,然后开始担忧明天上班的事,明天是周一,公司有例会。
他起床很早,自己打开冰箱,拿出食材,在电磁炉上开始做早饭。做完之后,他将她吃饭用的纸箱放在她跟前,解开绳子,让她坐起来,在撕开她嘴上的胶带之前,在她跟前放了一张纸条,纸条上歪歪斜斜地写着:“给我安安静静地吃完,敢叫一声我就弄死你。”
他盯着她,她点点头,确实,他掌握了菜刀,随时都可能捅死她。早餐吃的是她从父母家带回来的一条石斑鱼,干煎,上面撒了一些胡椒粉和姜丝,清清爽爽又富有风味,主食是一碗米粉,放了瘦肉与贵妃贝的肉,热腾腾的海鲜瘦肉米粉,最后撒了一些撕碎的香菜。不得不说,他的厨艺甚佳,刀工娴熟且精细,她怀疑他过去做过厨师。
“好吃。”她长出了一口气说。
“嗯。”他话不多,也不爱说话,“要上厕所吗?”
“我饭后得喝茶,喝完茶得上个大号。”她毫不迟疑地说。
他将她的两只手捆上,绕过身体两圈,固定在沙发一侧,然后拿走碗碟筷子和勺,将鱼刺等物倒入垃圾桶,到卫生间仔仔细细地洗干净了那些餐具,将两只碗扣在碟子上,筷子和勺子也是如此,方便晾干水分。他做这些事情都是自自然然、理所当然的样子,排除被捆在沙发上的这个被他绑架的女人,这里就像是他居住多年的家,他像是这里天生的男主人。不远处不断传入耳畔的海浪声,像是这种充满惯性的生活的催眠曲。
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做家务事,他拿起电热水壶烧开水,用的是水龙头里的水,她呜呜地发出声音,用眼睛和下巴示意,客厅一侧放了两大提塑料桶装的农夫山泉,海边的自来水水质不佳,她早就准备了烧水专用的纯净水,他理解了她的意思,将水壶内的自来水倒掉,提过来一桶矿泉水。茶是他昨天自己找到的安吉白茶,水烧开后,他让水温降低了一会儿,才倒到玻璃杯里,给她端到跟前,茶还有点烫,他低头吹了吹,吹去了浮在热水表面的茶叶,将刚才那张纸条再举起来,在她跟前晃了晃,她又点了点头,这才得以被撕掉胶带,在他的喂给下喝了一口茶,温度合宜,因为此前他也尝了一口。她忍不住想,这样在杯沿上就会留下他的唾液,唾液里会有DNA,遵循着这个思路,那么经过一夜,他躺的枕头和床单上应该遗留了他的毛发和皮肤碎屑,事后警察认真查找就会发现他的遗留物。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她能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来告诉警察这些事情。她不知道他为何劫持她,她不知道他打算拿她怎么办,他并没有性侵或者猥褻自己,倒像是一个温文尔雅的绅士。她上大号的时候,他帮她脱了裤子坐在马桶上,依然牢牢地捆住她的双手,卫生间的门留了一条缝,他就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她想着一会儿他还得帮她擦拭屁股,还有冲马桶,感觉又尴尬又窘迫,然而他全然不觉得这有什么尴尬或者窘迫的,做得跟伺候一位重症或者高龄病人的资深护工一样自然而然。
将她捆回沙发上,他认认真真地检查了打结的部位,在她嘴上又缠绕了一层胶带,然后就出门去了。她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先是睁着眼睛,仔仔细细地听着这楼里到底有没有邻居发出的什么动静。隔壁单元有人开始装修了,正在砸墙,沉溺于砸墙中的师傅,无法想象这个单元的顶层楼梯右手边户的屋里,会有一个女人被捆在自己家沙发上动弹不得。过了约摸两三个小时,他回来了,往屋里搬东西,塑料筐里装了满满的东西,像是从菜市场回来。他还带来了各种做饭用的家伙什儿,包括一只深灰色的液化气炉,和一个不大不小的液化气罐。
他这架势,像是要在这里长久地居住。她躺在沙发上,浑身酸疼又紧绷,就那么看着他进进出出忙碌。先前他应该已经上来过两三趟,将东西放在门口,因为脚步太轻,无法听到。他如同水母当中体形较为纤细的盒水母,透明的体内有一道发散着微蓝荧光的内脏,他上楼,像是回到海底洞穴,那么轻柔、无声无息。
将所有东西搬进来后,他先打开冰箱,将食材放到冰箱内,然后在手机上摆弄了一会儿,不多久,手机上响起了女性的电子声:“您已接到新的订单,地址:青岛市四方区和睦家园三号楼五单元303室,客户:小罗,手机:13405321351。请确认接单,并尽快安排送货。”
于是他从冰箱里拿出几样菜,开始在她临时拼搭起来的那张桌子上忙活起来,摘菜,洗菜,切菜,备料,他的筐子里有调料盒,每一样东西都安置得妥妥帖帖。他支好了液化气炉和罐子,将一只锅子放在上面,备好菜后,往锅里倒了一点油,加入姜丝爆香,而后是干辣椒。她开始担心屋里充斥了油烟,回头无法消除,他已经将阳台和厨房的窗户尽数打开,冷风猎猎地穿堂而过,一道光柱从不知名的地方投射而来,在墙面上形成了菱形的光影。
他想了想,又关上了卫生间的窗户。那是铝塑边框的双层窗,她为了不装窗帘在上面又加贴了一层磨砂的贴纸。他关上窗户后,又打开,但这回仅留了一条缝隙。这个人或许有强迫症,总觉得关也不是,开也不是,过了一会儿,又将那条缝合上,关严了。
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手机上又接到了两个订单,他不得不抓紧时间做饭。她挪动嘴发出呜呜的声音,想跟他说,如果把她解开了,她可以搭把手,反正也上不了班了,当然,不能排除她想借着搭把手的机会,想办法逃离。他没有搭理她,就跟没听到一样,从冰箱又取出几样东西,继续专心致志地洗菜,切菜。他也带来了先前给她送餐用的保温袋,以及一模一样的铝餐盒。
他做的三份都是海鲜寿喜锅,或许他今天在小程序上仅仅放了海鲜寿喜锅这一道,以避免需要准备太多的食材,她无法看手机,无法确证。他的肥牛片确实是他亲手切的,他自己带来的厨师刀刀刃格外的锐气逼人,削肉如泥。他片肉的时候,神情那么专注,从背影都能看出来,本来在墙面的光柱逐渐移动到他的侧腰上,让他的身体一边带着光。
放在一只不锈钢碗里的鲜海虾,应该是海捕大白虾,开始的时候还在跳,从她的视角可以看到那些虾的虾须抖动的模样,还有突然高高翘起的尾巴。他汆烫了这些虾,分成三份,放到寿喜锅的铝盒内,底下已经铺上了煮好的金针菇、老豆腐和肥牛片,还有比较细小的鸡腿菇。她回想起自己当时第一次吃他做的寿喜锅的滋味,别说,既鲜美又感觉得到做饭的人是专心致志的。不会有比他更好的外卖餐厅老板了,这么为点餐的人负责,居然会用海捕大虾作为原材料,这是不可想象的,海捕大白虾即便在本地的海鲜市场上也要45元一斤,如果用养殖的基围虾,只需20元甚至15元一斤,成本降低了一大半。
他去送餐之前,给她看了一张纸条,好像是从兜里的众多纸条中又翻找出来的,这些纸条都略微有些皱巴巴了,像是用了相当一段时间了,她认真辨认纸条上的字之外,没有发现陈旧的血迹,略微松了一口气。
那张纸条上写着:“我出门了,你要上厕所就点点头,午饭等我回来再吃。”
她点了点头,已经哭不动也喊不动了,又困又累又乏。
他带上保温袋出门了,将防盗门关上的时候,手格外的轻,好像怕吵醒正在熟睡中的她一般。他真是一个温柔的人,即便给她展示纸条,也全无凶悍之色,表情跟平日相比,没有任何变化。他走后,她放松了下来,跟他同处一室毕竟有压力,怕他冷不丁做点出格的事情。她想着,父母尚不知道她具体的居住地址,也从未来看过她这处房子,母亲对她贸然离婚的事耿耿于怀,目前还不到让她来看自己独自居住的地方的时机,得等她慢慢舒缓过来。她原本打算等春节前彻底安置好,把他们接来一起过年,顺道暖暖房。
整个装修过程都是她一个人扛的,没有其他人介入。现在她好像独自一人在荒无人烟的孤岛上躺着,只能等着绑架她的男人送餐回来,或许他在物色下家,下一个独居的女人,然后可以将所有的东西搬到对方家里继续做饭、接受订餐。他离开之前,对上家作何处置呢?也许什么也不必做,但是把她捆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上几天,那个女人自然而然就死去了。
想到这里,她感到了恐惧。更何况,他走前开着自己卧室的窗户,没有合上,今天大幅降温,海面上已經连雾气都没有了,像一块即将解冻的冰,灰溜溜的,僵硬的。她张了张嘴,在胶带下面,用尽整个肺的力气,发出了一声悠长的“呜——”。
作者简介 巫昂,诗人,小说作者,先后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和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曾供职《三联生活周刊》,现居北京,2003年起职业写作。出版有长篇小说《星期一是礼拜几》《瓶中人》等,小说散见于各文学杂志。
责任编辑 菡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