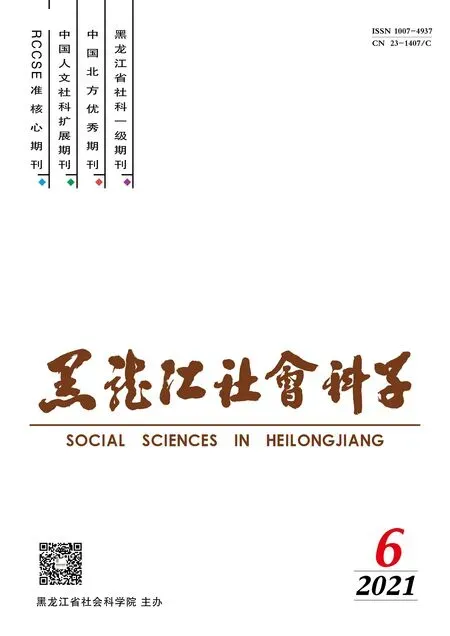辽金女真墓葬出土的萨满教神偶述略
2022-01-05梁娜,谢浩
梁 娜,谢 浩
(大庆博物馆 文物保管部,黑龙江 大庆 163316)
萨满教是一种被中国古代北方诸民族广泛信奉的、具有世界性群众基础的原始宗教,多以“萨满式的文明为特征”[1]。 辽金时期的女真民族也信仰萨满教,它以“万物有灵”思想为基础,奉行多神崇拜,深刻影响着女真民族的社会生活。
我国历代文献中,不乏对萨满教信仰的零散记载,其中关于神偶崇拜的记载颇为生动。如《史记·殷本纪》载:
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于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2]。
这里讲的是商朝的君主武乙暴虐无道,曾经制作了一个木偶人,称它为天神,并与这个叫天神的偶像赌输赢,而让旁人替代它。结果天神输了,于是武乙便侮辱它。又制作了一个皮革的囊袋,里面盛满血,仰天射它,说这是“射天”。最后武乙被暴雷击死。又《汉书·公孙贺传》有“上甘泉当驰道埋偶人”的字样[3],这里的“偶人”即木偶人,“埋偶人”便是用神偶行祭祀、诅咒之事。学者指出:神偶,即是原始宗教崇拜中被神格化了的某种灵物或偶像,认为有某种超人的神力依托其上,能作用于人类或能庇佑人类,因此人们对其供养和崇拜[4]。我国东北乃至国外许多民族,都有着神偶崇拜的宗教习俗。辽金女真墓葬中出土的神偶,大致有人形偶、动物形偶、嘎拉哈及菩萨像四种类型。
一、人形偶
在萨满教千奇百态的神偶中,人形偶最为常见:以人形为具体形态,有用金、银、铜、铁、木制作的,也有用骨、牙类材质雕刻而成的;体型小巧,方便携带。萨满教认为,人形偶是人死后魂灵和精神的依托,可以给现世的人们以心灵的慰藉;又是天神降世的代表,供奉祭拜之后随身佩戴,可以拥有无边的智慧和神威。
(一)骑士像
位于今俄罗斯的杜巴沃瓦墓地M18出土了三件骑士像,这三件骑士像均由人和动物两种形象组成,动物可能是马。其中两件动物的尾巴短小,一件没有尾巴;骑士做了简化处理,只雕刻出了一只胳膊和身体的躯干部分。尽管如此,这三件骑士像的造型依然很生动,让人联想起骑士策马奔腾的景象[5]。而俄罗斯沙伊金城址也曾出土过此类骑士像(下页图1)。
此外,属于唐代靺鞨遗迹的杨屯墓地也出土有骑士像,与前述杜巴沃瓦墓地M18出土的骑士像造型非常相似。马的形象夸张,四肢短小、颈部和尾部纤长,额头处隐约有犄角伸出,整体造型酷似腾空而起的飞龙;马背上部有镂空装饰,马尾部和人像的头顶部有用于挂坠的环钮(图2)。

图 1—10 1.骑士像 2.骑士像 3.头顶小鸟人像 4.顶部立鸟的神杆 5.佛托妈妈神偶 6.童子像 7.抱球童子像 8.武士像 9.骑鸟童子像 10.带翅童子像
王培新教授认为,这类艺术品造型中的骑士应为萨满,而马则是萨满通神的助手,寓意萨满骑马上天请神作法。富育光先生认为,萨满有时会通过梦境获得神谕,并自觉领悟或受到启发,而为了追索梦谕,萨满会骑马或骑驯鹿外出,并有雄鹰和黑狗作伴,有时要经历千难万险,甚至会经历一世或几世的努力找寻才能如愿。因此,俄罗斯杜巴沃瓦和杨屯墓地等地出土的骑士像,很可能塑造的是萨满率领众人追寻神谕的形象,体现了坚忍不拔的意志和顽强无畏的精神。
(二)头顶小鸟人像
1970年,在苏联阿穆尔河下游西河沟同博朗湖连接处附近发现一处女真遗址,主要分布在那乃人居住的博朗村对面一个不大的岛上。考古人员发现,一件头顶小鸟人像与一件轮制的瓜棱陶罐置搁在被水风吹掀的沙地上,大概是出土于岛上被毁坏的墓中。这件头顶小鸟人像呈直立状,头部为椭圆形,五官清晰可辨,身形纤瘦,双臂自然垂于身体两侧,但下半身及四肢却被简化处理了(图3)[6]。这件头顶小鸟人像没有腰带及佩戴武器,显然不是一个武士像,表达的也不是崇尚武力的精神;从头顶小鸟这个形象来看,又与现实中人的形态有所差别。不过,头顶上的小鸟虽然刻画得稚拙粗简,但依稀可见其傲然挺立的姿态,让人不禁联想到小鸟振翅高飞的景象。
现代满族萨满神帽上仍有神鸟的造型存在,且多呈展翅腾飞状。这代表着萨满可以借助神鸟的法力,在作法进入昏迷状态时,成为神灵的替身,与神灵沟通;神鸟也可以成为萨满出入冥界、与邪魔恶鬼斗争时的保护神。神帽上小鸟数量的多寡,反映了萨满主持神事活动的频率,体现出萨满本人的资历与法力,标志着萨满的等级。因此,这件头顶小鸟人像应该是萨满教通神思想的物化形式。
生活在黑龙江下游的奥洛奇人,其萨满在祭祀时所使用的神杆顶部也有立鸟的雕像(图4)[7],其侧影与上述头顶小鸟人像顶部的飞鸟非常神似,都是只有大概形态,而没有具体刻画出翅膀等细节。神杆是萨满教宇宙观中通天树的象征,而鸟是飞翔的精灵,被认为是萨满通神的助手。萨满教认为神灵来无影去无踪,或许正是为了凸显飞鸟这种神秘的特性,头顶小鸟人像及神杆中的飞鸟雕像才没有刻画其身体细节。而将其置于顶部则寓意其能飞到更高的天界,更加接近神灵,是神圣吉祥的象征,且其能代替萨满去请求法力更加强大的神,以帮助萨满驱逐恶魔。
(三)童子像
辽金时期的女真遗址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童子像,大多数为可爱的裸体童子形象。
北京房山金陵出土过一件童子像:铜制,通高5厘米,呈立姿,头上有鼻系,上身穿钱纹坎肩、下身赤裸,双手抱球(图7。相关考古报告认为童子手抱元宝)。房山金陵位于北京市西南房山区云峰山下,距离广安门约41.7公里,是历经几代、近60年营建而成的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寝。童子像出土于一座竖穴岩坑墓的地宫,其形制为长方形,四壁为麻岩石,而这件童子像就放置在其东大殿的夯土中[8],应该有特殊的寓意。
位于哈尔滨阿城的金上京城遗址附近则出土有数量较多的童子像:铜制,通高4.2~7.5厘米,多呈站立状,头顶部均有小环钮;可谓娇小玲珑、衣饰真切,有的童子像还袒胸露肚,并带有生殖器(图6)[9]。阿城白城三队的耕地中还出土了一件红铜材质的武士像:通高4.8厘米,呈坐姿,头顶部有用于悬挂的环钮;整个挂饰有被修整过的痕迹,表面微凸、背面微凹;武士的衣着清晰可辨,头包幞头,身穿铠甲。学者认为,这件武士像是女真人尚武精神的体现(图8)[10]。
1960年,在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城遗址内发现了一件金代骑鸟童子像:铜制,通高3.5厘米,头部宽0.8厘米,底部宽2.2厘米;头部虽完整,但眉毛以下部分由于磨损已无法辨识;头顶有用于悬挂的吊钮,但也已破损。童子以屈膝的姿态骑乘于形似天鹅的飞鸟之上,一只手紧紧抓住鸟的颈部,另一只手则自然垂下;整个铜像做工细致,甚至连飞鸟翅膀上的羽毛都被精细地刻画出来了(图9)[11]。
北京延庆时尚纺织品有限公司辽金时期壁画墓中出土过一件裸身童子像:通高4.9厘米,双手抱球,右脚在前、左脚交叠于后,头顶环钮已残缺[12]。这件童子像与前述北京房山金陵出土的童子像非常相似。从墓葬形制分析,延庆此处辽金雕砖壁画墓系采用火葬形式,因此应是汉人墓葬。这说明此时期北京地区的汉人已经受到了女真习俗的影响,佩戴使用童子像这类神偶。
辽金时期女真遗址中出土的这些童子像,大多为铜质,造型细腻生动;在童子像的头顶部均有用于悬系的小环钮,因此推测其应是挂坠在身上,或是穿缀于项链之上,作为护身的坠饰。金朝所在的北方地区,铜矿资源稀少,而铜不仅是铸币的重要原料,在制造器物上消耗量也很大,为此金朝实施了严格的铜禁政策。在铜源如此紧张的情况下,还制作了如此众多工艺上乘的童子像,想必这些童子像的作用绝非是仅供佩戴、装饰这么简单。这些反映出金代铸造技术有较大进步的童子像不是平民百姓所能把玩的,其拥有者必定是皇亲贵戚或者官宦阶级,这也映射出由女真社会上层所引领的时代风尚的变化。
此外,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乌苏里诺沃尼利科,曾发现一件带有翅膀的童子像(图10)[13]。该童子像昂首屈膝,双臂向前伸展,腋下有双翅,作向前腾飞之态——其形象与萨满上天请神的观念相吻合,也是萨满教中天鹅崇拜和生殖崇拜的体现。该童子像与上述我国境内发现的童子像大小相仿、材质相同,也有便于挂坠的孔洞。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小小的童子像,体现了女真人祈求多子多孙的愿望;笔者认为,童子像虽小,但是蕴含着重大的宗教意义,是萨满教原始崇拜和万物有灵观念的产物。
在现代北方少数民族中,仍广泛地制作并供奉神偶,如满族的萨满祭礼中就供奉着各种萨满神偶。“佛托妈妈”为其中之一,它是由柳木雕刻而成,是物化了的柳神形象(图5)。在萨满教的“魂化”观念中,魂魄是依附于神偶之上的(神偶系用特定的物质,如石、木、草、兽骨及铜、铁等材料制作),神偶具有生命力和无边的法力,能守护与庇佑家人[14]。童子像也是如此,《辽史·礼志六》中有这样的记载:
禁门北除地置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舆。在再生室东南,倒置三岐木。其日,以童子及产医妪置室中。……童子过岐木七,皇帝卧木侧,叟击箙曰:“生男矣。”[15]
这段史料描述了辽代再生仪的详细过程,是契丹人的求育祭祀仪式。这里皇帝参与模拟母亲生育,重新体验来到人世间的过程。仪式当中使用的“童子”便是萨满教神偶的一种,所体现的应是萨满教的生殖崇拜观念。
二、动物神偶
萨满教所供奉的动物神偶种类繁多,只是墓葬中出土的实物还太少,目前仅在俄罗斯科尔萨科沃墓地M157发现一件。这件动物偶像是在墓主人的腿部位置发现的,整体造型似一只哀号的狼,背部还有挂环[16]135。狼形偶像被认为是驱邪的护身符,而当时的人还以狼牙作为铜铃的铃舌,铃舌在晃动时发出声响,能让人联想到狼神在驱咬恶鬼。
早期氏族社会的渔猎经济使人类对动物特别依赖,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凶猛的野兽,人们只能互相协作、共同捕猎以获取生产生活资料;而由于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的低下,依靠简单的狩猎工具捕猎,人类常常面临生死威胁。在这种对动物既恐惧又依赖,又想要掌控的复杂心理作用下,最终产生了萨满教的动物崇拜观念。人们祭拜山神,认为所有的猎物都是山神的赏赐;每次狩猎行动之前,都会举行祭拜仪式,祈求山神庇佑狩猎满载而归。而虎神、熊神、鹿神、犬神、鱼神等等都是北方少数民族动物崇拜的突出代表。萨满还会模仿被视为神灵的各种动物的凶猛英姿,认为通过这种模仿行为,可以使动物具有的勇猛和力量传递到人的身上,从而使人获得超越人类的力量和独特的技能。
现代北方少数民族中如满族依然有制作各式动物神偶的习俗,在其先人东海女真中流传的著名萨满史诗《乌布西奔妈妈》中,有对于鱼祭场景的描述。祭祀时,他们会用新鲜翠绿的柳枝制作成大小不同的鱼形神偶、各式各样的鱼形帽子扔进水中,还会唱鱼歌、跳鱼舞,吃鱼虾、饮江水,以此来企盼风调雨顺、渔业丰收[17]。
三、嘎拉哈
萨满教的灵魂观念认为,死去的人和动物的灵魂依然存在,一般驻居在骨头里,并可以从中获得再生,因此骨头被认为是具有神性并能趋吉避凶的,这便是“灵骨”崇拜。《契丹国志·初兴本末》中记载了一个名叫迺呵的人,他可以操纵骷髅,在穹庐之中幻变为人形,并参与国家大事[18];这可视为萨满教灵骨崇拜的具体体现。
女真墓葬中出土的嘎拉哈,除骨制外,还发现有水晶、玉、铜等材质。如黑龙江绥滨中兴三号金代墓群M3曾出土有一枚晶莹剔透的水晶距骨(即嘎拉哈);位于松花江下游奥里米古城附近的金代墓群M24出土有一枚长2.2厘米的玉质距骨,形状酷似羊或狍子的距骨;哈尔滨阿城双城村金墓三队墓区出土了40余枚羊距骨,除一枚为铜质外,其余均为骨制,长度在2.6~3.2厘米之间[19]。又大庆市大同区老山头宝山二村墓地M1出土了一大一小两枚羊距骨:每枚羊距骨各钻圆孔一个,且都在其某一端的同一位置,均轻度腐蚀;两枚羊距骨的出土位置均在墓主人头骨附近。而根据牙齿和骨骼判断,墓主人是一名3岁左右的儿童。嘎拉哈作为随葬品出现在墓葬中并非偶然,在内蒙古土默特美岱村的北魏墓葬中就出土过一枚铜铸嘎拉哈;这说明,早在距今1500年前就已有使用模拟嘎拉哈随葬的先例了。而上述这些金代墓葬出土的嘎拉哈也说明,很早以前动物的骨头就被人们赋予了吉祥的宗教意义。
至今,满族人中还有用动物骨头做成嘎拉哈作为游戏物件的习俗。而蒙古、鄂伦春、达斡尔、鄂温克等民族也常在婴儿睡的摇车上悬挂嘎拉哈,有的还钻孔穿线、刷红漆,以达到“辟邪”和催眠的目的。可见,嘎拉哈绝非仅仅是玩具,其出现的思想根源是萨满教的动物崇拜观念;只不过经过漫长的岁月洗涤,逐渐褪去了宗教的外壳,演变成为一种游戏物件。
四、菩萨像
俄罗斯科尔萨科沃墓地M112曾出土有一件青铜菩萨像:通高6.9厘米,神态安详,头顶部有肉髻,左手握有执瓶,衣褶纹路清晰流畅;底部有座,座下有一个突起的小钮,应该是用来插在其他物体上的[16]126。这尊菩萨像的发现说明,此时的女真人已经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墓主人应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随葬的菩萨像是被奉为具有神性的萨满教神祇,作为一种护身符,在墓主人生前随身携带,死后则一同入葬,继续守护墓主人的灵魂。
早在女真人建国以前,佛教就已经在女真人中有所传播了。而大力提倡信仰佛教,则是在金太宗灭辽以后。据《松漠纪闻》记载:
有银珠哥大王者……以战多贵显,而不熟民事。尝留守燕京,有民数十家负富僧金六七万缗,不肯偿,僧诵言欲申诉。逋者大恐,相率赂通事,祈缓之[20]。
可见,金代初期佛教的势力发展就已相当可观了[21]。
宗教的发展演变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关系密切。金代以女真族为主体,但其辖境内也有汉族、契丹、渤海等其他民族生活。为了实现对多民族统治的需要,金代的宗教政策呈现出一种兼容并蓄的姿态。因此,长期以来在汉族中广泛信奉的佛教、道教,在女真族观念中根深蒂固的原始宗教萨满教,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金代统治者为了利用宗教为其政治服务,曾大力扶植佛教,保护佛教寺院并新建寺塔,使佛教得以恢复并在辽代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与此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女真贵族转而信奉佛教。不过,在广大女真族民众中,萨满教的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动摇,依旧是其精神依托。
结 语
历史及自然地理条件制约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也影响着原始宗教的表现。马克思《资本论》指出:“不同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各不相同。”白山黑水是女真族的发源地,他们世代生活在东北的崇山峻岭和河湖水滨之间,史载其“善骑射、喜耕种、好渔猎”[22]。在长期的渔猎生活中,女真人赖以生存的生产生活资料,几乎全部都需要从大自然中获取。人们对自然界中风、雨、雷、电等各种难以抗拒的力量无法理解,便产生了敬畏和崇拜的心理;山川、河流、动植物乃至整个自然界,都成了他们崇拜的对象。面对自然环境的险恶与无常,为了能够生存下去,人们便企图通过萨满教与超自然的力量进行沟通,进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萨满教表现出明显的与当时生产生活状况相符合的特征,而大量存在的萨满教神偶也被赋予了带有鲜明社会自然特点的、独特的精神情感。
萨满教神偶的制作,材料上比较多样,且略显随意:或使用木料精心雕刻,或使用草绳编制,或绣于皮子或绢布之上,或用纸笔随手画就。但不论制作方法如何,这些神偶造型体现的都是原始宗教观念中萌芽时期的神祇形象,具有很强的主观意味;同时,这些数量众多、形态各异的神偶造型还具有明确的象征意义,象征着萨满教所信奉的众多神灵,且因使用者的不同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及象征意义。倘若神偶作为法器而附着在萨满神服上,那么便象征着萨满请来的助手,可以增强萨满的法力;神偶的数量越多,代表着辅助萨满的神灵越多、萨满与神灵沟通的能力越强。若为普通族众佩戴,那么他所佩戴的这个神偶很可能是某个特定神灵的化身,体现着佩戴者的某种具体诉求。
因此,萨满教神偶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其表象所展示的东西,而是那些隐藏于偶像制作和结构中的东西[23]。万物有灵观念是萨满教的思想基础,对神的信仰、寻求人与神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是萨满教的重要观念,这些神偶的制作正是这种沟通意向的表达,象征了与神界的连接。普列汉诺夫说:“相信精灵的存在是一回事,崇拜他们又是一回事;神话是一回事,宗教仪式又是一回事。”相信有超自然实体的存在和信仰它是两回事,对于在萨满教万物有灵观念影响下产生的自然崇拜以及被物化了的神灵形象,我们也应这样看待。
萨满教作为一种超自然的社会意识形态,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它是女真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古代北方文化的重要载体;它不仅是女真社会经济和物质文化的体现,更标志着女真社会的发展水平。它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元素,给当时的人们带来了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