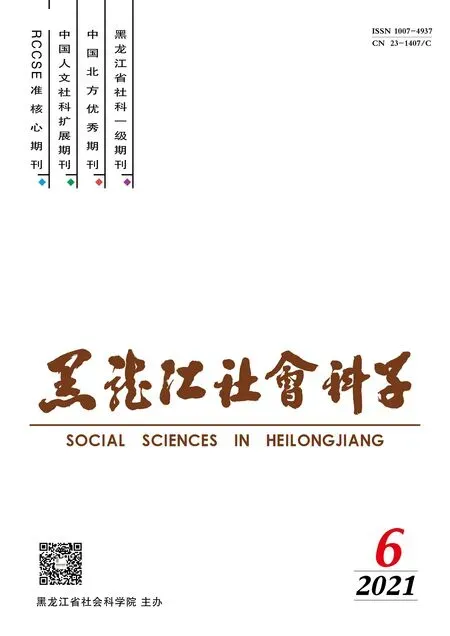略论王古鲁日本访书
2021-01-12李春光
李 春 光
(辽宁大学 历史学院,沈阳 110136)
王古鲁(1901—1958),名钟麟,字咏仁、仲廉,古鲁为号,江苏常熟人,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曾任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教授,后在北京大学任职,又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1939年曾赴日本任教。对中国小说、戏曲素有研究,曾编著《曲学书目提要》。他在滞留日本期间,对于佚书访求极为专注,主要走访了内阁文库、蓬左文库、尊经阁文库和日光慈眼堂法库。每发现珍本,他即不遗余力地进行拍摄,每天在暗室工作常常是从上午9时起到下午2时半止,甚至连带去的午饭都是在黑暗中摸索着吃的,其勤奋可知。其中,对于小说、戏曲类书籍的访求,成果很大。他自称:“在内阁文库阅览之际,曾竭我全力,摄取古典小说书影二千余页及稀见而值得供我们作研究参考的容与堂百回本水浒等小说全书七种。”[1]引言,1仅1941年,他在东京就拍摄小说100余种、胶片8000余张;其中,摄得全书者11种、旧刻小说书影109种,还有手抄和校录书稿5种。
1 王古鲁所携归的亡佚小说中,最早引起轰动的是明刊《古今小说》和《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其中,《古今小说》于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可谓一时纸贵。《古今小说》为明代短篇小说集“三言”之一,三言指《喻世明言》《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其中《喻世明言》又称《古今小说》,皆系明代文学家冯梦龙所编辑。三言中的短篇小说从不同角度揭露了社会矛盾,抨击了社会黑暗和人心败坏,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民愿望,尤其对于两宋以至明代城市发展以后市民阶级的生活面貌和思想感情有着比较广泛深刻的描写;小说情节曲折完整、人物形象鲜明、描绘细腻生动、语汇丰富,许多故事脍炙人口,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冯氏白话小说的创作成就。虽然书中有大量的封建说教、宣扬因果轮回的迷信观念以及庸俗的色情描写,但其作为明代白话短篇小说的重要选集,在明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史也具有重要价值。不过,小说在封建社会不能登大雅之堂,何况其中又有“淫词”,自然不能为统治阶级所容。因而清代将三言列为禁书,书焚板毁,有些版本在国内无传,有的虽有流传,但也不是原本和足本了。
然而,三言问世后,很快传到日本,并大为流行。据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长崎《商舶载来书目》可知,《喻世明言》即《古今小说》很早便传入日本。原书为明天许斋刊本,日本尊经阁和内阁文库各有收藏,少数文字间有异同。最早发现此书的是日本学者盐谷温,他在1924年编写《中国小说史》时,在内阁文库、宫内省图书室和上野图书馆查阅各种资料,意外地看到了“一种非常珍奇的材料”,即三言。这是之前著有《宋元戏曲史》的王国维与著有《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所未曾见过的书籍。因此他“惊喜非常”,作了《关于明代小说“三言”》的演讲,将此事广为传播。他称发现的这些书,“也许不能说是世界上有一无二”,但其为“到今日为止,虽中国人也还没见过的非常贵重的材料”,从此三言才渐为文化学术界所知。较早发现《古今小说》的中国学者是董康,据其所著《书舶庸谭》所记,他在1927年即在东京内阁文库看到了该书,称在其所见小说中为最佳刻本;此外,他还看到与该书同书异名的《喻世明言》24卷。继而1931年孙楷第赴日,亦见到了此书。其《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载有内阁文库和尊经阁藏《古今小说》40卷40篇,书中称:“内阁文库藏明刊原本,图四十叶,极精,第三十七叶记刊工姓名……尊经阁所藏为白纸本,插图形式正文行款亦同,恐系初印本。据长泽先生言,曾以内阁本校之,其序中数字间有异同。‘古今小说’中国已佚。此二本至可宝贵。”[2]卷2,23几乎同时,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等人也在《佚存书目》中著录了此书。不过董、孙二人为当时条件所限,都未能印行此书并使其在国内流传。直至1947年,商务印书馆据王古鲁摄归的日本内阁文库藏天许斋本照片排印,缺磨页处据日本尊经阁藏本校订补足,该书才得以重新在国内流布。
《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凌濛初编著。凌濛初,浙江乌程(今湖州市)人,明末文学家。所著白话小说甚多,二拍为其代表作。之所以编著二拍,据其自述,是因宋元旧小说已被冯梦龙“搜括殆尽”,“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3]“序”,1故事取材,有出自《太平广记》《夷坚志》《剪灯新话》《剪灯余话》等前人小说的,但综观全书,大部分是凌氏的创作。“故事中的主要人物,不是以往文学中常表现的帝王将相和英雄美人,而多是平民百姓,市民商人、贩夫走卒、娼妓小偷等向来不登文学大雅之堂的人物成了主角。……书中冲破了以商为末流的正统意识,肯定了商人们冒险逐利的活动。……书中不少篇章也描写了各类奸骗盗杀等丑恶故事,展示了金钱情欲漩涡中被扭曲了的人性。许多故事描写了婚姻恋爱和男女关系,批判了封建门第和嫌贫爱富的婚姻观念,肯定了青年男女对爱情婚姻自由的大胆追求,反映了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的思想对立(受李贽影响)。”“事类多近人情日用,不甚及鬼怪虚诞。……要是切近可信,与一味驾空说谎,必无是事者不同。”[3]“凡例”,3书中故事主要用通俗简练的语言叙述,人物形象较为生动、情节曲折,是三言之后明代白话小说的又一重要著作。出于与三言同样的原因,二拍全本在国内罕有流传。
《初刻拍案惊奇》的明崇祯元年(1628)尚友堂原刊全本40卷,日本日光山轮王寺慈眼堂法库有收藏,而国内已佚。孙楷第在《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中表示知有此书的尚友堂原刊40卷本,但云“未见”;而国内流传有多种36卷刻本:覆尚友堂本、消闲居本、松鹤斋本、万元楼刊本、敬业堂刊本。直到1941年,日本学者丰田穰和王古鲁才在慈眼堂法库发现该书原刊全本。原刊本不仅卷帙完整,而且所存序文亦可补国内清刊本之缺。序文称:“独龙子犹氏所辑《喻世》等诸言,颇存雅道,时著良规,一破今时陋习;而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因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若干卷。其事之真与饰,名之实与赝,各参半。文不足征,意殊有属。凡耳目前怪怪奇奇,当亦无所不有,总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3]“序”,1由此可知此书之宗旨及其所由来。原本又有清刊本所无之凡例,从此凡例不仅可以看到作者编撰此书的立意与体例,而且还可以准确知道此书刊行的年代。过去学者依据内阁文库所藏《二刻拍案惊奇》的小引断定《初刻拍案惊奇》刊行于天启七年(1627),今据此凡例可知此书虽辑成于天启七年之秋,但刊行于崇祯元年初冬。再者,依据《二刻拍案惊奇》小引可知《初刻拍案惊奇》应为40卷,而以前所见该书各本则仅有36卷,此已久成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待解之谜。而该书原本的出现足以证明《二刻拍案惊奇》小引之不误,又可证孙楷第《三言二拍源流考》中的观点——《删定二奇合传》中之二篇(《曾孝廉解开兄弟劫》《毛尚书小妹换大姊》)应出于足本《初刻拍案惊奇》——是错误的。民国以来,该书铅印本有1936年上海杂志公司“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及中央书店、新文化书社翻印本等。建国后的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古鲁校注的以覆尚友堂本为底本、参考其他版本的《初刻拍案惊奇》。1967年,香港友联出版社出版了李田意辑校的《拍案惊奇》;此本以日本所藏的尚友堂原刊40卷本为底本,又以在日本广岛大学图书馆所发现的尚友堂原刊本之后印行的39卷本补出40卷本所缺的2叶;此本在国外流行较广,影响较大。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章培恒先生整理的王古鲁注释本,此本以广岛大学图书馆所藏39卷本为底本,校以清刊本中较好的覆尚友堂本及消闲居本;保留了王古鲁所作的注释及其所撰的本书介绍和《明刊四十卷本的拍案惊奇》《稗海一勺录》三文,成为大陆所出版的最早最完整之本。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日本藏本影印出版该书,系以39卷本为底本,再以40卷本补其所缺。199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古本小说丛刊”本中的该书,是据日本所藏40卷本影印。1992年,海南出版社也出版了该书,系据日本藏尚友堂本排印。
《二刻拍案惊奇》的体例、内容与《初刻拍案惊奇》相似。其中涉及诉讼的故事所占比重较大,展示了人情世态的丑恶,并揭露了封建官吏的贪赃枉法和断案之昏庸。此书最早的版本为崇祯五年尚友堂刊本,40卷,现仅有一部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为天下孤本。1927年,董康在内阁文库见到此书,著录于《书舶庸谭》中,详载回目,并称:“为明人度曲家所取材,中国绝无传本。”[4]1931年,孙楷第赴日访书,亦见此本,著录于《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中,并称:“年来经邻邦及国内各学者介绍,世所习知,无庸称赞,唯其书此土无流传本,苦不能详其文字。”[2]长泽规矩也在《佚存书目》中亦载此书。国内北京图书馆虽亦藏有尚友堂本,但缺卷13~30,几缺一半。1957年,古典文学出版社据王古鲁1941年从日本拍回的原本印行出版,才使其在国内广为流行起来。
以上三书于国内的重新流布,在亡佚典籍回流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大大地丰富了我国的文学宝库。三言二拍集中了我国明代短篇小说的精华,是具有总结性的文集,在我国小说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些书的重新流布也使我国不少文学家和研究者为之兴奋、为之欣喜、为之惊奇,鲁迅先生即称三言等小说的发现“在小说史上实为大事”。不少学者为此撰写了专门的论著,从思想内容到艺术特色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推动了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另外,这些作品对以后的白话小说创作也起到了一定的借鉴作用。
2 王古鲁在日本访书另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他在日光轮王寺的发现。日光轮王寺是之前曾到日本的董康和孙楷第所未曾去过的地方,而在那里的慈眼堂,王古鲁在日本学者丰田穰的引导和协助下,除了看到了中日两国研究中国文学的人都没有看见过的崇祯刊尚友堂足本《初刻拍案惊奇》外,还看到了明万历刊双峰堂本增补校正《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全书,以及明刊本《鼎锲全相唐三藏西游释厄传》10卷、明刊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20卷100回、崇祯刊金阊万卷楼本《新镌扫魅敦伦东游记》100回、明刊本《禅真逸史》40回、明峥霄馆本《禅真后史》60回、明书林刘大华刊本《鼎锲国朝名公神断详刑公案》8卷、明书林刘龙田刊本《新锲全像大字通俗演义三国志传》等,这使得王古鲁惊异万分。遗憾的是,限于时间和经济条件,他只摄得了《唐三藏西游释厄传》《忠义水浒志传评林》二书,其他只摄得了书影。
而《王古鲁日本访书记》一书,则主要记录了他在日本对有关描写三国时期以前的通俗历史小说的访求,所提及的历史小说有20余种:《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开辟衍绎通俗志传》《武王伐纣书》《列国志》(旧本,有关武王伐纣部分)《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二种)《列国志传》《新镌全像孙庞斗志演义》《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秦始皇传》《前汉书续集》《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全汉志传》《东西汉通俗演义》《新全相三国志评话》等。所记虽没有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的多,但叙录比孙氏之书为详:所见各书均标注作者、版本、版式、行款、卷数、回目及序跋和题识等内容。有些书孙氏虽已叙及,但因为王氏涉猎较广、考究较细,故有新的发现,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如对于将《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秦并六国》《前汉书续集》《三国志平话》统称为“元至治刊本全相平话五种”,王氏颇有异义。指出五种书中仅《三国志平话》标注有“元至治刊”字样,其它四种并未标注;除《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缺扉页,另三种均注明为“建安虞氏新刊”,而通过在名古屋蓬左文库新发现的《京板全像按鉴音释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则可知福建虞氏刊刻了整套的平话集。他说:“这样大规模的印刷事业,似不能在短短的三年岁月之中完成。再就内容的先后次序而言,《三国志》的雕版,似较在后,而且特别标明‘至治新刊’,似乎有标新立异之意,因此,也许可以推定其他各种决非刊于至治年间,而系刊于至治以前。”[5]20他因而认为统称之为“至治刊本”,似不甚妥,不如笼统称为“元刊平话五种”较为合理。又如关于“列国志”一类的书,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只著录了一种明刊12卷本《春秋列国志传》,王古鲁则又在孙楷第未曾去过的蓬左文库发现了一部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刊印的8卷本《列国评林》。此本与通行之《东周列国志》不同,“故事起自武王伐纣,下迄秦并六国,多取宋元以来传说,如说话人的话本以及剧本所谱,取为资料。”此书的发现证明了一种说法,即:“武王克纣,伐罪吊民,则《列国志》是也。”[5]16而《东周列国志》,则没有述及武王伐纣的故事,这是因为冯梦龙据旧本之《列国志》“重加辑演”,才“始乎东迁,迄于秦帝”[5]16。这对于研究小说故事情节的演变过程很有意义。此外,书中所述蓬左文库所藏明万历刊本《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全汉志传》为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所未及,弥补了孙书之不足。
王古鲁在日本发现的古本小说还有《熊龙峰四种小说》,此书的发现及其回流亦是其一大贡献。此书最早在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京本通俗小说与清平山堂》一文中曾有过介绍,亦引起了郑振铎的注意。郑氏说:“我们见到日本内阁文库的汉籍目录中,有别册单行的小说四种:冯伯玉风月相思小说、孔淑芳双鱼扇坠传、苏长公章台柳传、张生彩鸾灯传。这四种,我很有幸的都曾见到过。但愿长泽规矩也的报告已够说明之。”[6]原书分成四个单行的小册子,每种书篇幅都不长,《苏长公章台柳传》10叶、《孔淑芳双鱼扇坠传》17叶、《张生彩鸾灯传》24叶,最长的《冯伯玉风月相思》也只有28叶。这四册书因为都是写刻,所以简体字很多,可以从中看出明中后叶所习用的简体字写法。长泽氏认为,此四种书“大概系万历时期的俗书”,又说:“这四册或为一种丛书的分册,也许在同一时间内,同一个书肆中,为了出版同一种类的书籍起见,所以它们具有这样类似的形式。”[7]3所论极是。这四种小说其实是王古鲁在日本访书时的意外收获。本来这四种书并未在他的拍照之列,只是因为其篇幅不大,故在无意之中顺手全部拍摄了,后发现其底片保存完好,喜出望外。因为这四种小说对于研究明刊话本小说具有重要的价值,于是1958年古典文学出版社将其出版,遂在国内广为流行。
《熊龙峰四种小说》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王古鲁曾将其与国内传本进行了比较,从而校出《清平山堂话本》中的错简和缺叶:如《冯伯玉风月相思》第4、5叶倒置,第10、11叶之间缺了1叶。错简问题,如果细心,可以检查出来,可是缺叶则不同——谁能想得出云琼寄给冯生的诗共有十首(尽管有“自生别后,有诗十余首,并录寄赠”的字样),而且冯生遣家僮往迎云琼的时候,也寄赠了一首“梦魂几度到河阳……”的诗呢?而《张生彩鸾灯传》和《古今小说》尽管都收录有《张舜美元宵得丽女》这一故事,但两书刊刻年代有距离;虽说在文字上没有多大变动,但大体也可以看出《古今小说》有过删削和修饰加工。其他两种则都为久已失传的小说,写得虽然不好,“不过这一类烟粉灵怪传奇,当时在民间确是很受欢迎的。……这对于了解明代盛行的小说方面,还是很重要的。”[7]4
3 除了小说之外,王古鲁还对亡佚在日本的中国明代戏曲进行了搜求、拍摄,回国后辑成《明代徽调戏曲散出辑佚》一书,1956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共收集明代安徽弋阳腔系统变调的青阳调、滚调等戏曲散出12出(均原藏日本内阁文库):万历三十九年刻本《新刊徽板合像滚调乐府官腔摘锦奇音》中的6种,即《金锏记》中的《六使私离三关》、《招关记》中的《伍子胥过昭关》、《同窗记》中的《山伯千里期约》、《和戎记》中的《昭君亲自和戎》、《长城记》中的《姜女亲送寒衣》、《升仙记》中的《文公马死金尽》;万历刊本《新刻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中的3种,即《调弓记》中的《李巡打扇》、《题红记》中的《四喜四爱》、《琵琶记》中的《临妆感叹》;万历三十八年刊《鼎刻时兴滚调歌令玉谷调》中的2种,即《题红记》中的《四喜四爱》、《米糷记》中的《鞠问老奴》《书馆逢夫》;万历新岁刊本《鼎雕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中《木梳记》的《宋公明智激李逵》。
上述作品中除《琵琶记》外,都是不易见到或久已佚亡的。明代戏曲中多演民间故事,故为民众所喜爱,像上述作品所描写的孟姜女送寒衣、伍子胥过昭关、昭君和番、梁山伯会祝英台、敬德钓鱼(辽王访友)、胡敬德诈妆疯冤、杨六郎下三关,以及梁山泊故事李逵扮货郎下山救李幼奴、玩弄权阉的李巡打扇故事等。这些戏曲有滚调、青阳调、池州调,都是明代中叶源于今安徽的新腔调,是徽调的雏形,对后来的戏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书中,王古鲁对于每出戏都撰有一篇简介:一方面介绍故事来源和有关的小说,另一方面择要举出与本出戏相关的其他剧种曲调;另外,在卷首附有书影23幅,在卷尾则有附录。这些戏曲的发现,对于研究曲调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价值,对于解决戏曲史上一些疑而未决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如以前日本和中国的戏曲研究者对于梆子腔是否出自弋阳腔颇有争议,但论辩双方均缺少充分的资料。而对于本书所收的《昭君亲自和戎》一出,王古鲁认为其“可以说是很好的‘传奇家曲,弋阳子弟可以改调歌之’的一个实例。……我们据此还可以看出《缀白裘》所收《青冢记送昭(君)》、《出塞》,以及《纳书楹曲谱》所收《昭君》及《小王昭君》的关系。《缀白裘》全书是在清乾隆庚寅(三十五年,即公元一七七○年)刊成的。《青冢记》收在第六卷里,目录中明白标明为‘梆子腔’。《纳书楹曲谱》较后二十二年,刊于清乾隆五十七年(公元一七九二年),其中补遗所收的《昭君》,称为‘时剧’,《小王昭君》则称为‘散曲’”[1]45-46。王古鲁拿《缀白裘》所收的《青冢记》和《纳书楹曲谱》所收的“时剧”来比较,又与本书所收之《和戎记》本对照,认为“可以明了《纳书楹曲谱》和《缀白裘》所收之曲,其源实出于本出”。又说:“由此可见,在明万历时期称为‘时调歌令’的滚调《和戎记·昭君亲自和戎》出,到了清乾隆时代,《纳书楹曲谱》还称它为‘时剧’,一百多年间它在人民群众中是始终受着欢迎的了。《缀白裘》中称之为梆子腔(一本作昆弋腔),有了上述的比较,使我们了解清乾隆时代《缀白裘》中所称的梆子腔确与明代流行安徽的弋阳调别流的滚调有关,并且这种具体的实例,也解答了青木正儿氏《中国近世戏曲史》中‘梆子腔果出于弋阳腔一派否耶’的疑问,证明了焦循《剧说》卷一所记‘安庆有梆子腔剧’,确系事实。”[1]47-48
又如,戏曲家欧阳予倩认为“梆子调,又称吹腔”,青木正儿则持否定看法。王古鲁对本书所收的《升仙记·文公马死金尽》出与《缀白裘》中“雪拥”“点化”两出进行了比较,从而得知这一种弋阳变调中的“雁儿落”“寄生草”“一枝花”等阕在《缀白裘》中概括地称为吹调;至少可以说,后来的吹腔是从梆子腔中分化出来的,从而可证欧阳氏之说成立。
此外,王古鲁还通过《词林一枝》带有滚调形式的各出,说明滚调早已在万历初年从青阳调中酝酿成长起来,纠正了傅芸子的“滚调之产生当在万历三十八年左右”的看法,并对弋阳腔能把传奇家曲改调歌唱及“错用乡语”的特点作了论述[1]引言,1,说明了弋阳腔和它的变调在戏曲史上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