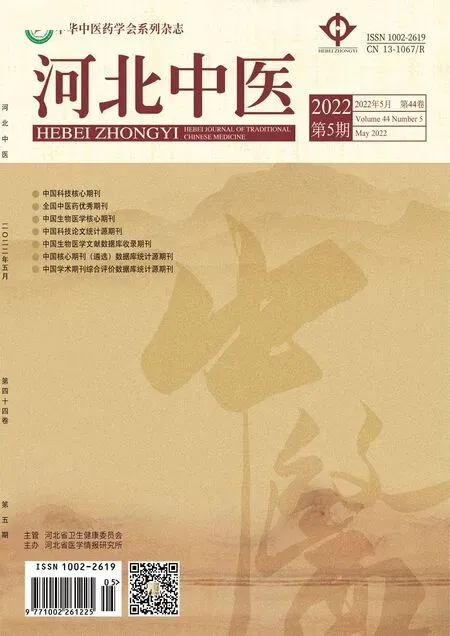巫君玉教授由“性味归经”辨证用药经验※
2022-01-01巫熙南巫浣宜郭仁真
巫熙南 刘 平 巫浣宜 郭仁真
(1.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传统疗法门诊,北京 100010;2.中华中医药学会办公室,北京 100029;3.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全国中医老年病医疗中心,北京 100091)
巫君玉,教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1990年被列为第一批全国500名老中医之一。巫教授擅治急性热病、肝胆病、脾胃病及内科杂病。
巫教授临证以中医理论为基础,根据脏腑、虚实、寒热、表里等辨证,确定相应的治法,依托中药的性味归经等理论等将中药组成包含君、臣、佐、使药的有机的方药组合即方剂,与患者病证相符,从而药到病除。现将巫教授用药经验总结如下。
1 性味归经及用药经验
对于中药的四气、五味和归经,巫教授临证应用体会颇多。比如:脾胃病中用药,《素问·脏气法时论》有“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用苦泻之,甘补之”“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补之,酸泻之”等,此苦、辛、酸味药中,用于泻下者多峻而重,用于补者多缓而轻。而胃主和降,属阳土燥金,具有热多而恶寒、恶燥等生理特性,亦为指导用药原则,故宜中病即止,太过则寒亦可以化热,甘亦可以中满。
巫教授临床根据患者病性寒热、病位脏腑经络、病势缓急等予以辨证,再根据中药四气、五味、归经等选药组方,从而达到药证相符,解除疾苦。①脘痛:热证予延胡索、川楝子;寒证予甘草、党参、白术、干姜;虚证予党参、黄芪、白芍、甘草;气滞予香附、木香、枳壳、砂仁;血瘀予丹参、三七。②呕吐:热证予黄连、枳实、黄芩、竹茹;寒证予干姜、半夏、丁香。③呃逆予丁香、柿蒂、刀豆、降香。④伤食予神曲、山楂、麦芽、莱菔子。⑤便秘:燥证予火麻仁、瓜蒌、郁李仁;实证予番泻叶、玄明粉、大黄;虚证予肉苁蓉、柏子仁、生何首乌。⑥溏泻:寒证予煨姜、肉豆蔻、补骨脂;热证予黄连、白头翁、秦皮。⑦吐酸:肝旺予黄连、吴茱萸、瓦楞子、旋覆花;虚证予海螺蛸、白术、茯苓。⑧虚胖:益脾予党参、白术、生黄芪;利水予冬瓜皮、茯苓皮、泽泻、车前草、生姜皮、大腹皮。⑨出血:热证予十灰散、仙鹤草、茅根;血瘀予三七粉、云南白药、藕节、失笑散;虚证予黄芪、阿胶、炮姜炭、血余炭[1-2]。
1.1 地域差别,南北用药异同[1]巫教授执业以来,自南而北,北而南复北者三,往复于吴燕间,深感于外感病之治未可以一概同药,盖南北之气候不同,物产、食嗜不同,居处之习异而人之腠理亦有疏密。北地气寒,人之腠理密于南人,外邪袭后,恶寒无汗之势重而期长,于冬令尤然,若以南人之治以辛凉从事,效不桴鼓,必也参用辛温始可,此为巫教授1954至1956年间所得成败之训也。巫教授于温病流行之地,温病学发皇之区,治热病悉宗温病法刻期取效,1954年北来之初,沿此法治外感,往往三、四剂不得汗解,予以溯寒温之辨,下逮河间辛温合苦寒之法而应手矣,于是以知《素问·异法方宜论》区五方分治之训不可忽而良用也,河间原系北产,为一代宗匠,创温病学先河于“主火”之间,盖亦发原乎《伤寒论》者,私揣测其“防风通圣”“表里双解”等法,犹“大青龙”“葛根”“葛根芩连”等方义推而扩之,巫教授曾仿之以麻黄入“银翘”,治表寒不解、内热已盛而血压高之患者,竟得一服而解“银翘”大剂三服不解之症;浮想所及,则张介宾二百里外客气即异之说,可知其所指矣。
1.2 药品之效因产地异[1]药求道地,盖水土之不同而药效异故也。记北京市药材公司于1960年引地黄种三十亩于昌平山坡,一年长甚茂,二年挖视大几如卵,计三年后当可用矣,时京畿方缺此药,得此讯甚欣慰,讵知三年后挖而切之,晒干仅如薄纸片,无以为熟地矣;旧《密云县志》载,淮庆地黄苗自冀东移去,有予人以利之感,然数千年来竟不闻一密云人业地黄者,得此事可以明其所以然矣,药既若是,其效用亦可想见。又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各地兴引植,以解中药不敷之求,胜于无固为其可取之理,然药效一端,尚宜有以克服,1978年虞山种黄芪,量甚丰,然计效不及口芪(产于张家口以北的黄芪)十之二三,是均因水土之不同故也。
《本经》各药下均有产地,自均为汉时地名计,知《本经》断非汉以前书,然亦非必此地有此药,余处亦有产者也,第异在效用耳。如巫教授家乡苏南,即有紫苏、藿香、薄荷、桔梗、沙参、泽兰、川芎、黄芪、麦冬等200余种,其中木本类者似尚可通用,草本类则惟紫苏、薄荷、藿香可销于全国而为名药,余则鲜者尚可用,干则效减矣,故当地中药均鲜用或晒干即用为宜,效亦可计也;当今药物不敷,药物之引种为势之所必然,难于强求道地,第种者宜于水土间求其所宜,如土壤成分之类之配合等,其在医者,则惟量情配药,或指示患者自采,或医者自采,求投剂之得效者庶几!
1.3 临床用药与四时气候[3]巫教授用药非常注意气候变化、体质强弱及禀赋等,例如:春多风温,投金银花、连翘;夏多湿暑,藿香、佩兰常用;秋多燥伤,麦冬、生地黄可使;冬中于寒,麻黄、桂枝酌加,按四时受邪之轻重而量药量。中医临证,是否一定要遵照四时气候变化,如歌诀有“夏咳减桂加麦味,冬咳不减味干姜”,再如瘦人火多,肥人痰多,老人阳衰,小儿阳稚,此类患者临床即使无火、痰等表现,用药可否兼顾,以防患于未然?曰按四时气候发病而异药,只是辨证中的一个方面。临证之时,尚需辨清体质及非时之邪的夹杂与否;如冬寒而见化热,并非必用麻黄、桂枝,秋燥而连日阴雨,便可见到伤湿,此为时邪变化之所需考虑者;患者体质亦需注意,若素体阴虚血燥,麻黄、桂枝岂能必用?若素体肥湿,干姜、半夏岂可不投?总之要大气候、小气候、体质三者互参,方法是用四诊互参统率其要,不能无的放矢。至如肥人瘦人之兼顾,亦只能在正面用药时注意不使伤及而矣。
1.4 道地药材[3]道地中药少,有碍疗效,有何法解决?道地药因产地、土质关系,药性与土质所含成分密切相关。巫教授曾亲见北京昌平山区所种生地黄,3年后大如拳,但切片晾干则如薄纸,远非比怀庆者。江南所种黄芪,形态甚丰而效用较之口芪十不抵一,故只能加大用量。20世纪五十年代后,中药用量十数倍于前,供销矛盾无法解决,只能寄望于就原产地加大种植范围,以求土质相同。若求之野生自然所产,不独量少,采挖亦难,已属势所不能适应。
1.5 单方秘方[3]单方秘方之运用不离辨证,以辨证为前提方能取效。对单方秘方持全盘否定态度是不正确的,因单方秘方传自民间,对某一病或某一证有一定疗效,与中医药起源形式相类,但传者非医,用者据证不据理,据证中亦有误讹,不分新旧、轻重,故有效有不效。巫教授在《瓣杏医谈》[1]中收有此类方药数十个,皆经亲历有效,故知要在辨证运用。
1.6 药性有新效[1]药籍之记药性、药效,间有不尽、不然者,条述于后。葶苈子素以泻肺利水为用,禁用于虚人,然近时化验,竟有强心作用,孙砚孚记之于《诊余集》,用量可至5钱(15 g)、8钱(24 g),见其效未见其碍也,不独孙氏如是,巫教授亦常以治喘而不禁用虚者也。
如水菖蒲之不特行气止痛,竟于肠炎、痢疾有好效,金钱草之可治湿热黄疸等。
1960年巫教授会诊1例糖尿病患者,尿糖检查极不稳定,或竟二日连检为阴转,而第三日则又见尿糖(+++)。患者为十数年之久病者,且体力不佳,故于中医会诊之同时,并会诊于某医院,患者尚可行动自如,故去医院时均自行就诊于门诊,而医院之尿检均无尿糖,此后第二日检尿亦无糖,怪之甚,因询其就诊前有所服食否,曰:为求能午前返病房,去协和时均晨起空腹乘车,下车后腹饥,然不敢多进米、面等制品,于院旁小店中进豆浆一碗,余则仅食滴杏仁一盘约60 g,每次均然。于是疑杏仁或有关,嘱患者量食杏仁二次以核之,竟然当日近午之尿检均能无糖,是则杏仁非竟化痰、润肺、止咳之用矣,于尿糖亦有其用也。
1.7 煎药宜讲求[1]药之用,约言之惟气、味两者,气清而味重,煎煮之时,气随汽腾而味留于液;举凡发汗、清热、化湿、止痛等之求效于气之用者,无二不需留气不使蒸发而后可,设气随汽散,则效半或竟无效矣。按之近时药物中可挥发物质作用之理,古今之说固大有可通之处,证之临床效果亦灼然可见。例如:
1964年收治肝炎1例。患者湿热黄疸,时临床总结知可于12 d内消黄疸症状,而此患者服药12 d无寸进,检方核证相符,不得其解,诊毕返门诊,于院中树根旁见药渣中有干燥茵陈,检之就询于煎药室,盖煎时不加锅盖,茵陈浮于上,煎犹不煎也,因严嘱加盖煎煮,并日日查视,5 d而黄疸退矣。
1967年秋收时,邻村一妇人胃痛,处方平肝理气药3剂,2 d后,巫教授适应友人邀至其村,遇诸村西桥头,妇方打场扬谷,询其服药有效否,曰:已服2剂无效,痛仍如前,详问煎药情景,则不盖而煮者,因嘱煎最后1剂时,需盖严,煮15 min,不得泄气,当晚、次日晨分服,若无效,可复诊,翌日询之,曰痛已蠲,因嘱再服原方3剂。
1982年于某医院,病房医师治泌尿系统感染发热1例,3剂热不退,时病房有规定:非抢救患者,必先用中药,5 d不效始可加用西药,邀巫教授会诊,2剂亦不效,巫教授查证与药符,忆及中药煎煮之弊,嘱医师亲为如法煎药2剂,方仍其旧,连夜服3煎,翌晨未热,午后亦未再作。
上述仅就煎药必须加盖而言,京地风气,自煎者每煎均达45 min~1 h左右,以为煮久则效著,而先下之味,仅先煎10 min,固不独不加盖也,此种煎法,亦为求效之谬,盖轻清之味,久煎则挥发迨尽,先下之药,多金石、贝骨难溶之属,不煎达30 min以上,溶者少而效自减矣。至有以一煎分代头、二煎,得液不足则加开水以足之,得液有余则倾弃,及夫连屉蒸而不煎,不同之病而药气互串等,均属弊端,其有损于治效则一也。故医者为治,不独需求之于理法方药之切符于病证,药之煎煮调剂,尤需讲求而不容有忽,盖调剂煎煮,犹药厂之制剂,岂可以草根树皮而轻心哉,否则医则徒劳心,病者徒耗费,甚或贻误病机,医患两不达利矣,古之医者有亲视药之举,良有以也,忆初业时邻有短工慵,患外感发热甚,巫教授诊后亲为煎之如法,1剂得解。今之医者既不能为之亲视,诿之旁人,或知有不足,或竟然渎职,其能不谆谆于此哉。
1.8 中药过敏 古籍无中药过敏之说[1],1960年以来,因大量研究中药及中医进入医院,审视密切而渐有所闻,且或有极严重之症状出现者。1962年春夏之交,北京市某医院内科收治十数名“日光性紫癜”,此症于人体暴露之可经日照部分,均紫红作肿而痒,其为衣遮蔽处则肤如常人,界划截然,即如额间帽沿所庇之区,亦紫白攸别,症之轻者则惟变色作肿,痒木不适,重则溃破而水液浸淫,且全身发热。询病起之前,悉有采食灰菜史,或早食而暮病,或昨日而今发,是则灰菜之过敏明矣,因或清热、或化湿,总参解毒之品为治而愈。灰菜即药籍所记之“蒴藿”,藜藿之属,人之素所采食者,《本草纲目》载其有解毒之功,而竟致疾,病者或告曰:叶背脉紫、茎亦紫者多致此病,茎脉青白如叶面者则食之安然;是则品种小有异也,且《本草纲目》载食用之法,须经灰水(碱水)淘煮、滤清后始可再加佐料煮食,则服法亦有讲求也。
又1972年治一周姓职员,溃疡病且兼不寐,就诊时曰:“余忌用当归,药中涉此则风疹立起,然可自愈,不为害。”巫教授初不信,曰小试亦可,以实其信,因处方外另予当归3钱(9 g),入第1剂第2煎同煎服,药后来示,果疹隐隐起矣。医患间即应诚信于诊治始终。
又北京市第六医院中西结合病房会诊一衄血患者,血小板计数(20~40)×109/L已4年,自诉服阿胶则衄甚,曾于他院等处服药时见此象,巫教授会诊时衄初止,嗣后于1986年春节前试服阿胶,诚然衄复作。
于以见中药之有过敏信然也,第襄昔未倡此识耳;夫物之于人、人之于物,固未必尽然一例,人之个体有差异,物之品类有不齐、制食有规则,医者安可不审乎其间哉,然而以养血之当归而起瘾疹,以止衄之阿胶而致衄,则非医患二者之所亲历不得知矣。
2 药证相符
2.1 辨虚实 巫教授强调,临证之时需辨清体质,若素体阴虚血燥,麻黄、桂枝岂能必用?若素体肥湿,干姜、半夏岂可不投?
又如产后有热之用当归、川芎[3],适宜用于血虚发热之症。当归、川芎为四物汤之半,属养血行血之用,补而不滞。换一角度看,不应认定产后必虚。临床上体质实者常可见到,并非产后每方必用当归、川芎。产后发热之由外邪或食滞者,归芎非主药。产后亦需辨证投药,要从祛邪而不滞邪角度着想,体实者不必用,血热者不宜用,时邪外感高热者亦不宜用,食滞者亦不必用。
2.2 辨寒热 辨证组方用药中应用辛温之品体会[1]:在脾不统血情况下,用归脾汤、四君子汤、补中益气汤等方出入,一般可以收效,但在重型的虚寒患者身上是不够的,需要参用辛温药物来振奋脾肾阳气,如黄土汤中之附子,理中汤中之炮姜等,巫教授在临证中遇到了这个问题,第1次未用炮姜而血不止,第2次加入炮姜后就收到了效果。然而血是逢热则行、逢寒则止的,在运用此类药物时,一定要明确是虚寒之体,如炮姜虽有其止血的一面,但对热证总属不宜,除非是夹在大量凉血清热药中使用,使其有制而后可。
2.3 辨表里 卫气营血[3]。卫气之分用药有别,深感用药之精在于辨证,病未过卫分不宜多加气分之药,观当今之于治外感热病,动辄石膏、知母、黄芩、黄连,清热解毒常杂其中。定位用药与截断分析法,此种用药法亦有一定之理,近几年来有称之为“截断法”者。治病以疗效为求,临床决不能弃病位于不顾,必须在病位方药基础上而后谈“截断”、谈“防患于未然”,而后在本病位方药中略增超前药味,如若倒置,便是“关门打死狗”,此意于《瓣杏医谈》[1]中已有论述。所云“有一定之理”,是指配伍得当,如卫分证恶寒或恶风时,解表方中夹用少量黄芩、栀子清气,兼有高热时亦可夹用石膏如大青龙法是可取的;若表卫未罢、且无阴伤而即用滋阴药便不妥。要求用药“精纯”之说,指辨证用药得当,如表证高热兼用清气、阴虚兼用生地黄、玄参,古人有成法,当然需要,若指卫分药气分药截然分开,则与临床症情难符,亦失辨证论治之意,有胶柱鼓瑟之嫌。至若不分表里虚实缓急,一律用清热解毒药,便与西医滥用抗生素而借防止感染为说之情相同,此情之是乎否乎,迄今尚无成论。
2.4 用药禁忌与否须辨证 再举例麻黄用药[4-5]:大青龙汤禁忌证中有汗出恶风。麻黄汤的主症有恶风、恶寒、无汗,在我们通常意识中也有无汗用麻黄、汗用桂枝的看法,似乎有汗是麻黄的禁证,对此也应深入分析,在仲景著作中实际并非如此,如麻杏石甘汤的汗出而喘是有汗而用麻黄,越婢汤的续自汗出亦是有汗而用麻黄,并且均是与石膏同用,明示麻黄并非有汗的绝对禁用药。这点也是与桂枝二越婢一汤的相同之处,均用麻黄透邪,石膏清热。用量在《医宗金鉴》桂枝二越婢一汤方后注中说麻黄、桂枝只是荣卫之药,可知方剂变化中的药味药量组合及服药方法的重要性,也可由此学到用药变化的灵活性。
2.5 药证相符宜守方[1]巫教授业医之2年,7月间治一暑热证,患者为30岁,壮热汗出,口渴引饮,微有恶风,脉洪,苔薄白润,予白虎汤加藿香、佩兰、黄芩,1剂热退;翌日午后复燃,证相同,仍用白虎出入,热又退;三诊时患者诉汗甚,日数易衣,虑体力不支,予谓脉大未杀,白虎证在,未可止汗,邪撤汗当自止,毋虑为,患者信之,自辍药辄热,遂不敢停药,计服白虎汤6剂而热退不复作,汗亦止,饮食调养而愈。此明是证是药之不可易也,赖当时易辙停药而复热之情,得坚患者意,否则难计效矣;然而,是则是矣,效亦是矣,后而思之,设仿白虎加参法,即得一太子参或北沙参参之,稍益气阴而邪撤或更捷也。
2.6 同药不同效其因诸多[1]治病辨证,须细微入理,且需详嘱煎药法及调护问题,否则药效多受影响,竟或不效者有诸。师执某,学实有素,治同村一热病,予白虎汤不效,当时乡间穷困,1剂不效即更医求速愈,非若今之可叠进三五剂者,翌日能请业师出诊,审证确系白虎证,为求全计,告病家谓此方诚是,并就原方不加味、不更量,抄一过予之,1剂而热退,师执由此而终身不复言医。此事就而析之,因由殊多:药力不速,前剂得后剂而始克奏功为其一,煎不如法为其二,药后未避直接着体之风为其三,其就病机计之:或先日恶风之况尚甚,虽有白虎证之大热、大汗、大渴及脉大等证,而邪尚未离乎卫,此时当于白虎中加达表之品如桂枝白虎意,翌日病随日进,热邪全入阳明经而白虎可得效矣,是则就效之缓捷计功之析,设一方两剂连服,固无不效之可言也。巫教授自习医迄今而不忘此事者,盖为策已之精进退,于以亦可见当日求于医者严、而业医之艰难也。
小结巫教授具有多年医疗临床工作经验,在中药应用领域体会颇多,犹如散落的珍珠记录在带教录、医谈、医案等中,今载幸会将“珍珠”串联成项链呈现到广大同仁面前,供同道共勉。巫教授认为,临床医生临证辨证要有根,即中医脏腑、寒热、虚实、表里等理论;用药辨证有据,即中药的性味归经、道地药材、煎煮等。药证相符宜守方,药到病除[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