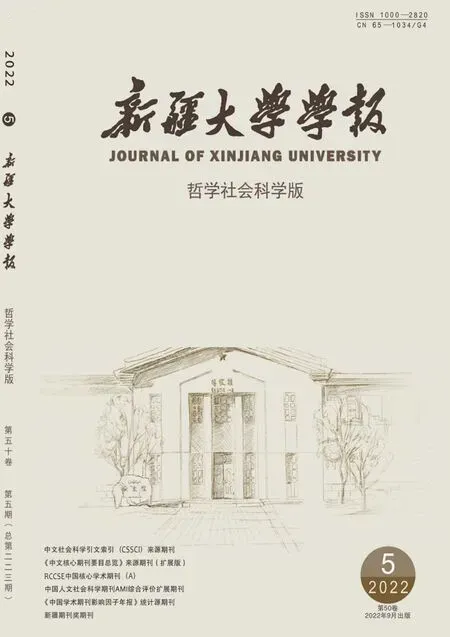先秦时期新疆历史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肇源*
2022-01-01李中耀贾国栋
李中耀,贾国栋
(1.新疆大学 历史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2.新疆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一、先秦时期新疆的人种、部族与交流
新疆古称西域,自古就是一个多人种、多族属繁衍生息的地方。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史前的西域人既有来自欧洲、西亚的欧罗巴人种,又有来自漠北、黄河中上游地区的蒙古人种。 “哈密地区是欧罗巴人种向东扩展的最东界线,而蒙古利亚人种则向西发展到了伊犁河流域。”[1]欧罗巴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在这里交汇、交流、融合,形成了欧罗巴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的混合型人种。这已经被史前墓葬的考古发现所证实。无论是闻名中外的小河墓地,还是 “楼兰美女” 出土地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以及吐鲁番洋海墓地,就目前发现的史前墓葬来看,基本上没有单纯的某一人种族属的单独文化遗址,多数都是交互混合型的。这种多种人种混合的情况,也被现代人类基因图谱分析所证实。通过对新疆当代少数民族基因成分数据分析,都具备族源多样性的特点,都属于欧亚和东西方民族融合而形成的民族。譬如维吾尔族,据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人口健康领域)计算生物学研究所协同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一项研究证明: “维吾尔族人群的遗传成分主要起源于欧亚大陆上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已分化的人群,大致可以由现代东亚人(约28.8%—46.5%)、南亚人(约12.0%—19.9%)、西欧人(约24.9%—36.6%)和西伯利亚人(约15.2%—16.8%)来代表。”[2]
多数学者认为,在秦汉之前,居于西域的主要有塞人、羌人、汉人、车师人、月氏人、乌孙人、匈奴人等多个古老部族。其中的羌人、汉人、匈奴人属于蒙古人种。塞人和月氏人属于印欧人种或主要有印欧人种的特征, “不过是后来的地中海型的印欧人种和先期到来的高加索型的印欧人种发生了融合”[3]绪论9。车师人、乌孙人属于混合型人种。《汉书·西域传》记载, “蒲犁、依耐、无雷国皆西夜类也。西夜与胡异,其类羌氐行国”[4],若羌的地名一直使用到现在。20世纪60年代于沙雅县发现的 “汉归义羌长” 铜印说明,直到汉代,还有不少羌人生活在南疆地区,后逐渐融入到塔里木盆地的各部族中。
中原人也是最早踏上西域这块神奇土地的古老部族之一。他们对西域早有认识,在新石器时代,华夏部族就开始了对西域山川地貌、风土人情的探索,并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和传说。汉文典籍《山海经》《淮南子》《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史记》等生动地记载了这些记忆和传说。他们在生产劳动的实践中发现了玉石的坚韧与美好,于是把无限的遐想和美好的愿望附着于这晶莹温润的 “天地精英” 之上,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寻找 “昆山之玉” 的艰难历程。他们不仅与西域各族人民共同开辟了举世闻名的 “玉石之路” ,而且也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灿烂的玉石文化。
中原华夏部族与西域的联系始终是紧密的。在哈密七角井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中,发现并采集了千余件石器,其中细石器中的 “船底型石核是我国细石器传统中较早期的代表物,更具有中石器时代的特征”[5]。1934年,在孔雀河下游小河五号墓地中,发现了500多粒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海菊类贝壳制成的白色小珠,这说明早在4 000多年前,我国东西部的联系就已经比较紧密了。在阿尔泰山巴泽雷克古墓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公元前五世纪的文物,其中有中原地区的织锦、刺绣和铜镜。在天山阿拉沟战国晚期墓葬中,发现了2 600多年前来自中原的菱纹罗、凤鸟纹刺绣和漆器(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这些充分说明,先秦时期,中原与西域的交往交流已经非常频繁,西域文明与中原文明交流互鉴,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及至西汉,随着西域都护府的设立,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大规模屯田的开始,中原汉人大量进入西域,逐渐成为新疆的主要民族之一。千百年来,来自中原的汉族人民和新疆各族人民一起,筚路蓝缕,胼手胝足,患难与共,守望相助,共同开发建设了新疆,共同创造了灿烂的西域文化。
在共同创造西域地方文明的过程中,兄弟民族曾经慷慨地帮助过汉族人民,汉族人民也为其他兄弟民族的繁荣发展作出过贡献。在迁徙西域的过程中,汉族人民不仅带来了中原的典章制度、礼仪文化、先进农耕技术,而且不少人还融入到了兄弟民族之中,形成了 “血浓于水” 的亲情关系,现代人类基因图谱的分析数据就是明证。这些历史资源正是我们坚持 “三个离不开” ,进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珍贵历史遗产和深厚人文基础。
二、玉文化与 “玉石之路”
中国的玉文化源远流长,人们把玉视作天地精气的结晶,使其具有了不同寻常的象征意义。人们爱玉、崇玉,以致于忘却了最初发现玉作为 “石器——生产工具” 的原始功能,赋予了它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极高的社会价值。玉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玉既是饰品又是祭祀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 “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6]玉还是权力、等级、财富的标志。《周礼》《仪礼》《礼记》等文献记载了西周有关体现权力、等级功能玉器的名称、规制与用途。明确规定权力、等级不同,所执玉器也不同。玉器也是财富的标志,被用来交换、赏赐和赠送。正因玉器有如此价值,战国时的名玉和氏璧,秦昭王竟愿拿十五城来交换,各国为了得到它甚至不惜兵戎相见。玉又是吉祥之物。原始先民对自然界的风云变幻、人世间的生老病死等现象无法认识和抵御,便祈求于神灵的庇护和保佑。于是, “天地精英” 的玉器便成了沟通神灵、消灾避难、除凶驱邪、祈求平安的祥物瑞器。玉更是君子德行的象征。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者把仁、义、礼、智、信等观念比附于玉的各种物理化学特性,《礼记·聘义》: “君子比德于玉”[7],提出了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各种学说。自儒家学者 “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8]后,玉器便被高度人格化,与政治、宗教、伦理、道德等融于一体,构成了中国玉文化的核心内涵。
连接西域与中原的 “玉石之路” ,伴随着玉文化的兴起而开辟。有人认为, “自殷商时代,吐火罗人就开辟了一条自和田昆仑山至黄河中游地区的玉石之路”[9],和田玉向中原输出的时间大约有5 000—6 000年之久。著名的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发掘出755件玉器,经鉴定,玉材大多为和田玉。妇好是商王武丁的配偶,她的墓葬中大量和田玉的出土,说明当时的 “玉石之路” 已经相当畅通和繁盛。据考古发现,随着 “玉石之路” 的开辟,周穆王时,新疆已有不少采玉、琢玉点。①参见程遂营《丝绸之路上的古城》,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63-265页;韩英《略谈和田玉的使用及其重要影响》,载四川博物院编《博物馆学刊》第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91-395页。西域先民开辟的 “玉石之路” 为中国玉文化的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
“玉石之路” 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一条玉石贸易之路,更是一条文化交流之路。它的开辟不仅加强了西域与中原的贸易联系,而且通过 “玉” 这个媒介进一步拉近了西域与中原的文化距离,通过交往交流促进了二者间由物质到精神层面的结合。西域的玉石输入中原,中原的丝帛运至西域,交往交流的观念形态也随之产生而传播。周穆王祭祀黄河,用的祭品之一是 “束帛加璧”[10]卷一,19,即丝绸与美玉。这两种美好物品的结合,不仅体现了中原与西域的紧密联系,也体现了中华民族 “化干戈为玉帛” 的价值追求。
“玉石之路” 的开辟,强化了中华民族先民的远古地理观。中国远古的地理观中,有两个最核心的观念:即 “河出昆仑” 和 “玉出昆岗” 。①参见叶舒宪《揭秘 “丝绸之路” 的前身》,《人民周刊》,2017年第1期,第75页。在远古先民的观念形态中,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源自昆仑山, “天地精英” ——玉石产自昆仑山,昆仑山就是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山,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对 “昆仑” 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他们认为,昆仑山不仅是 “天下” 的一部分,而且是拱卫天下、顶天立地的 “天柱” 。《淮南子·天文训》就反映了这种观念: “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尘埃归焉。”[11]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载,不周山就是昆仑山。②国内学界关于不周山的地理位置尚存争议。相关讨论可参见马博主编《山海经诠解》第6册,北京:线装书局,2016年,第2640-2647页。“玉石之路” 的开辟,使更多的人得以了解昆仑,朝拜昆仑,进一步开阔了人们的疆域视野,强化了大一统的 “天下” 意识。这种意识的强化为中华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和四海一家、华夷一体民族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强大的思想基础。
“玉石之路” 的开辟,也使西域在中华文明中获得了重要的地位。中国产玉的地方很多,但自和田玉输入中原之后,便以其品质之优良和产地之神圣而独树一帜,成为制作国家重要礼器的原料。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附加了深厚的政治文化意义,和田玉更成为中原王朝最重要的战略物资之一,对构建中原王权意识形态,进而宾服四夷、一统天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和田玉产地的西域地区,也因此获得了中原王朝不同寻常的关注和重视。这种关注和重视不仅为西汉王朝正式把西域纳入中国版图提供了思想文化前提,而且也是几千年来中国东西部两大板块凝聚一体、不可分离的深层文化因素之一。
“玉石之路” 和玉文化是中华文明特有的文化资源,它本身就是各民族共同开辟、创造的产物。其深厚的历史文化蕴含,正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疆肇源的基础之一。
三、彩陶文化与 “彩陶之路”
新石器时期,先民将土、水、火结合生产出了陶器。陶器的出现,是史前时期人类的重大发明,是史前人类活动的重要见证。
中国原始彩陶的大批出现,其时间可追溯至约6 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到约3 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从考古发现看,中国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大体上可以分为中原地区、西北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三大区域。 “远古新石器时代流行于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既是中国物质文明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又是精神文明的一个源头,它从哲学、艺术、史学、宗教、文字等方面启导了中华文明的形成。”[12]23陶器是用具,但先民在制作它时,也把它当做一种精神文化的载体, “是远古先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综合性表现形式和结果,也是远古社会流传至今的最直接、最可信的第一手史料”[12]23。
考古发现证明,中国彩陶从一出现起就带着中华文明的鲜明特征。它的主要文化特征是:第一,以意写形。即对自然物的描写以意取形,以意设形,充分发挥想象力,使图案的构成不受自然形体的束缚而灵动多变。第二,彩陶图案富有动态感。尤其是黄河流域中、上游的彩陶图案常常具有跃动奔放的气势。第三,高度概括凝练的标志性图案。用最简单的点、线、面组成的几何形纹样来标志出某种图腾或被描述的对象。如马家窑类型彩陶的米字或十字纹、蛙形纹,半山、马厂类型彩陶的神人纹等,都是具有徽号性质的纹样。第四,彩绘纹样与器型完美的结合。注重图案与器形、视角的统一,力求图案的造型和构成与器形相协调。③参见张明川《中国彩陶图谱》,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07-211页。以上这些文化特征,构成了新石器时期彩陶文化浓烈的中国风格,有力地驳斥了西方学者 “彩陶文化西来说” 或 “仰韶文化西来说” 的荒谬。
“最早兴起于黄河流域的彩陶文化从公元前5 000年前后就开始了它的西渐历程。”[3]33-34它自中原进入河西走廊,又由河西走廊传入西域,沿天山山脉向西流布,形成了著名的史前 “彩陶之路” 。
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原彩陶文化的向西域传播有两次波峰。第一次开始于约公元前3 000年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形成以后,彩陶文化沿着河西走廊继续西进,进入新疆东部地区。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遗存发掘发现, “作为主体的单耳罐、双耳罐类陶器,流行垂带纹、网格纹、菱格纹、手形纹等图案的黑彩,特征与甘肃山丹四坝文化陶器接近,其族源明显在河西走廊”[13]34。彩陶文化的第二次西传波峰,始于公元前1 300年焉不拉克文化形成之后,沿天山山脉长距离西传。焉不拉克文化分布在新疆东部哈密盆地和巴里坤草原,以哈密焉不拉克遗存为代表。焉不拉克 “文化是在哈密天山北路文化的基础上接受其他文化的影响发展而来。焉不拉克文化出现以后,对当时天山南北‘高颈壶文化系统’的形成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其高颈壶、弧腹罐、弧腹钵、豆、直腹杯、直腹筒形罐等彩陶因素渐次西传,导致新疆中部自东而西形成苏贝希文化、察吾乎沟口文化、伊犁河流域文化等一系列彩陶文化,察吾乎沟口文化晚期向南已经扩展到塔里木盆地南缘”[13]35。吐鲁番洋海墓地出土的双耳罐、单耳罐及其器物上的纹饰,也明显受到哈密彩陶文化的影响。 “如苏贝希文化和焉不拉克文化一样流行红衣黑彩彩陶,察吾乎沟口文化彩陶多为白地红彩,而伊犁河流域文化黑彩和红彩平分秋色。”[13]35从哈密彩陶文化到吐鲁番洋海墓地彩陶,再到察吾乎沟口彩陶、伊犁河流域彩陶文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彩陶之路” 、彩陶文化的西向延伸、传播轨迹。
不可否认,由于处于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处,新疆史前彩陶文化也受到了西来文化因素的影响。但从考古发现看,新疆彩陶文化始终呈现着黄河上游区域彩陶文化的明显特征,中原彩陶文化的影响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也被新疆彩陶文化遗存东多西少、东早西晚的事实所证实。强大的中原彩陶文化影响力,使得西来或北来的以筒形无耳器为主、以刻划压印纹饰为特征的陶器系统 “没有发展起来,或者昙花一现短暂存在后很快就消失了”[3]52。而中原彩陶文化的影响力则沿着 “彩陶之路” ,不仅延伸到天山南北,甚至影响到中亚地区的七河流域。中原文明在彩陶文化时期,就给西域大地抹上了一层厚重的底色。
“彩陶之路” 在把中原彩陶文化西传的过程中,也把中原黄河流域古代居民培育的粟、黍类农作物、农耕技术传入新疆,给新疆古代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变化,又一次拉近了新疆与中原的文明距离,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内聚向心力。
中原仰韶文化是早期中国文化的核心所在, “中国西部甘肃、青海、四川、新疆甚至西藏此后绵长延续的彩陶文化,都以仰韶文化作为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彩陶的西传实际就是早期中国文化的西传”[13]35。 “彩陶之路” 为古代新疆注入了强大的中原文化元素,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历史贡献。
四、青铜文化与 “青铜之路”
青铜是红铜和锡或铅的合金,因颜色青灰,故名青铜。考古学上把掌握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使用青铜器的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称作青铜时代。据考古学家的研究,中国青铜时代的开始,不晚于公元前2 000年,结束于公元前5世纪,持续了约1500年,大体上与文献记载的夏、商、周至春秋时期的时间相当。青铜器的发明是人类生产技术创新的一次飞跃。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国家之一,其青铜器种类繁多,形制瑰丽,花纹繁缛,制作精湛,充分体现了中国青铜器特有的艺术魅力和鲜明的民族风格,更构成了我国无可替代的青铜文化。”[14]
中国青铜文化的起源可以上溯到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阶段。考古出土的最早铜制品,是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一个由黄铜片卷成的管状物,年代约为公元前4 700年,属仰韶文化遗存。1975年甘肃东乡的林家村出土了一件属于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这是迄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时代在公元前3 000年。之后的龙山文化遗址中,也有零星铜器出土。多数学者认为,夏代开始,我国正式进入青铜时代,商周时期达到鼎盛时期。
青铜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生产工具的进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兵器质量的提高,增强了开疆拓土的军事实力。尤其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以青铜、玉等国家重器构成的礼制文化, “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15]。反映出王权的高度集中和华夏一统的强烈观念,显示出中原王权作为天下共主的担当意识,正如《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所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6]特别是禹铸九鼎之后, “九州” 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定鼎” 成为国家政权建立的象征。古老的华夏大地进入了一个青铜文明的新时代,灿烂的青铜文化之光也以中原为中心向四周辐射。
青铜文化的东西向交流形成了 “青铜之路” 。 “青铜之路” 活跃于夏商周时期,由于较少文字记载,我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主要基于考古发现。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关于 “青铜之路” 的研究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青铜之路” “主要是由西向东传播青铜与游牧文化” ,因为 “西亚早在五千年前已进入青铜时代……东亚大约四千年前才进入青铜时代,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遗址中有零星铜器出土,但不足以表明东亚进入了铜石并用时代”[17]6。另一种观点认为,青铜文化是多源发生的,中原是青铜文化的起源地之一。仰韶文化、龙山文化遗址就有铜器出土,古代文献记载的黄帝铸鼎、蚩尤铜兵就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走向青铜时代的经典概括。商代早期,具有鲜明中华文化特征的青铜文化已全面繁荣,青铜铸造工艺已相当成熟, “并随着商王朝势力的向外扩张而出现于王朝周边及更远地区,从而与周边青铜文化交互影响,不断发展”[18]。因此,作为青铜时代世界体系的四大中心(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代中国)之一, “青铜之路” 的传播自然是由东向西的。两种观点也有一致处:第一,都承认商周时期中华青铜文化创造的辉煌;第二,都认为新疆是连接东西方 “青铜之路” 的重要场域。笔者认为, “青铜之路” 的存在是历史事实,青铜文化的交流应该是双向的,这是人类文明互鉴的基本规律。即使最初的 “青铜之路” 是东向的,当它流布到中华大地,与中华大地的古老文明相结合并发扬光大之后,便焕发出更加灿烂夺目的光芒,从而形成强大的回溯力量。这种回溯力,甚至超过了原流力。因此, “青铜之路” 是一条真正意义的文明互鉴之路。关于此,新疆的考古发现就是证明。
孔雀河古墓沟文化遗址的发掘和研究表明,大约公元前2 000年前,新疆部分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 “且与中亚、西亚、中原均有联系”[19]。察吾乎遗址中出土一面动物纹圆镜,镜背绕钮铸出 “线描” 的狼形象,身体卷曲,张嘴呲牙,而在三门峡虢国墓地中也发现有一件与此风格相似的铜镜。2015年,若羌米兰遗址发现一件青铜器,与古代斧钺极为相似,初步命名为 “钺” ,制造年代为汉代以前。钺是古代中原的一种兵器,后逐渐演变为一种仪仗礼器,是君主威仪与权力的象征。①参见中国新闻网《新疆若羌米兰遗址出土罕见青铜器初步确定为 “钺” 》,网址:https://www.chinanews.com/cul/2015/03-24/7153820.shtml.访问日期2021年8月5日。2018年8月,据中央电视台报道,北京大学联合考古队在天山深处的博尔塔拉州温泉县呼斯塔古墓地出土一件青铜啄戈,初步断定年代约在4 000年前。戈是源于中原的一种兵器。另外,新疆发现有20余件铜鍑,是当时草原游牧民族代表性的青铜容器,用于烹饪、盛食,并用作宗教仪式中的礼器。连主张青铜文化西来说的学者也认为, “广泛分布于欧亚大草原的青铜鍑亦可能源于中原”[17]8。有学者认为,公元前2 000年前后,受中原文化影响,东天山和甘青的一些地区青铜文化异军突起。新疆的小河文化、林雅文化和甘青地区的四坝文化、齐家考古文化中出土的成百上千件铜器,青铜器类型和冶炼技术在当时遥遥领先,构成了中国西北青铜文化圈。西北青铜文化圈的文化传统随着东西文化的交流向西传播,至少在商代向西传入吐鲁番,而在商周之际进入天山南麓。这一文化同时沿天山北麓西传,于公元前1 000年后进入伊犁河谷。②参见吴福环《中国地域文化通览·新疆卷》,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53页。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东西方青铜文化通过 “青铜之路” 双向交流,新疆不仅是个重要的场域,而且形成了以哈密林雅文化青铜器为代表的地方青铜文化类型。在东西方青铜文化的交流互鉴中,西方的印记可能时间稍早,但东方的印记清晰、广泛和深刻。西域青铜文化作为中国地方青铜文化的一个类型③参见李文瑛主讲报告《近年新疆文物考古新发现》,载《新疆首堂文物公开课成功开讲最新考古发现震惊全场》,亚心网2011年12月12日报道,网址:http://news.iyaxin.com/content/2011-12/12/content_3203467.htm.访问日期2020年10月16日。,与中原青铜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外在联系。
“青铜之路” 传播的不仅是青铜文化,同时也是各种生产技术与精神观念的交流互鉴。来自草原文化的牛、马、羊和来自西亚的小麦等农作物借助 “青铜之路” 传入中原,分别和中原起源的猪狗鸡、稻粟黍豆组成 “六畜” 和 “五谷” ,丰富了中原人们的生活和文化;中原的稻粟黍等农作物以及舟船、夯筑等技术也随之传入西域,给西域人民带来了生活便利。①参见陆航《全球史视角中的中华文明探源——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易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7月14日第6版。尤其是中原青铜文化所展现的精神品质:如海纳百川的恢宏气度、四海为一的天下意识、和谐万邦的观念境界以及礼制文明,不可能不对西域人民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当然在这方面,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考古新发现问世。
五、远古的记忆与传说
昆仑神话是我国四大神话(昆仑神话、蓬莱神话、南方楚神话、中原神话)的主体。昆仑神话的主角有盘古、黄帝、西王母、女娲、伏羲、后羿、嫦娥等,记载昆仑神话的历史典籍有《山海经》《淮南子》《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左传》《列子》《楚辞》《史记》《汉武故事》《汉武内传》《神异经》《独异志》等。虽然这些典籍大多并非信史,但它们记载的内容同样是远古先民生活的反映和情感意志的表达,同样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茅盾先生说: “神话是各民族在上古时代(或原始时代)的生活和思想的产物” ,是 “中华民族的原始信仰与生活状况的反映”[20]4-5。昆仑神话记载了中华民族诞生初期的历史记忆与传说,其产生、流传过程与中华民族的形成、生存与发展相同步,是我们探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远古肇源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之一。
横贯我国西部的昆仑山脉,是名副其实的万山之祖。昆仑山的雪山冰峰、险境魔幻,峥嵘崔嵬、波诡云谲。于是,出于敬畏和神秘的神话故事便伴随着人们探索的脚步而产生。在先民的意识中,昆仑山是万山之祖,是连接天地的天柱;又是母亲河黄河的发源地和 “天地精英” 玉石的出产地,古人出于崇拜心理,将昆仑山完全神格化了,尊之为 “仙山” “圣山” “龙脉之祖” “万神之乡” 。
昆仑神话体系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源头之一。《山海经·海内西经》《山海经·西山经》说,昆仑山是天帝在地上的都城。据说,这个天帝就是黄帝②关于昆仑神话的相关论述,参见白剑《文明的母地华夏文明的起源及其裂变的考古报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80-285页。。《穆天子传》记载,周穆王西巡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拜谒黄帝在昆仑山上的行宫: “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宫。”[10]卷二50昆仑山有九重天,西王母、九天玄女都是九重天的主神。西王母是昆仑神话中最原始的女神,也是中国神话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位主神,民间对其信仰在战国时期已经开始。2003年5月,在毛乌素沙漠南端的古墓,出土了一幅罕见的汉代壁画。壁画中的昆仑山由五座山峰组成,高耸云天。西王母高居云端之上,羽人、三足神鸟、太一神侍奉左右。驭鱼驾兔骑龙的神仙们则呈现向西王母飞奔之状,由众多仙禽异兽表演的乐舞更是对着西王母载歌载舞,给人以西王母高高在上的至崇印象。③参见冯国《残留在沙漠古墓中的西王母神话》,《记者观察》,2003年第9期,第48-49页。这幅壁画至少传递出两个信息:第一,三足乌是中原神话中的太阳神;太一是南楚神话中的太阳神东皇太一,又称东君,配婚西王母之后,又被称作东王公。不同区域、不同体系的神出现在同一画面,正印证了茅盾先生的论断: “我以为现在的中国神话至少是由北方、中部、南部,三支混合而成。”[20]168说明中华神话从它的起源起,就具有多元交融的品质,这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的显著特征。第二,西王母在这幅画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西王母不是自然之力化成的神,不少学者认为她是当时生活在昆仑山下的母系氏族部落首领的神格化,她能成为华夏昆仑神话中至高无上的主神,并能与东皇太一成婚,说明四海为一、华夏一体的观念意识早在中华文化形成的滥觞期就已经深入人心。至于《竹书纪年》《穆天子传》记载的周穆王西巡与西王母会见于昆仑瑶池之上的故事,更是有文字记载以来我国东西部部族首领交流相亲的一段流传千古的佳话。④相关论述参见《穆天子传》卷二、卷三,高永旺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46-111页;《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范祥雍订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30-33页。周穆王西巡的目的除了拜谒黄帝昆仑之宫和获取昆仑之玉外,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宣示天子之威,和协西域诸部。
女娲补天也是昆仑神话中的一段精彩故事。女娲就是九天玄女,也是昆仑神话的主神之一。面对天塌地陷的巨大灾难,女娲勇敢地挑起了在昆仑山下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重任。女娲炼的五色石就是昆仑之玉,因为只有玉的纯洁晶莹,才能补出明亮清彻的天空;只有玉的五彩缤纷,才能织就满天的云霞。《红楼梦》描写的人物贾宝玉的真身,就是一块女娲补天遗落在昆仑脚下的 “通灵宝玉” 。女娲补天的故事隐喻了中华民族诞生初期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艰难历程,体现了中华民族坚韧不屈、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无疑,女娲不仅是一位率众战天斗地的部族首领,也是一位中华民族的伟大母亲。关于女娲造人的传说有多种,且在我国多个民族中流传,其中一种是伏羲、女娲造人的传说。唐人李冗《独异志》卷下记: “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妇,又自羞耻。兄即与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遗我兄妹二人为夫妇,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二人即结为夫妇。”[21]文中的兄长即是伏羲,亦即三皇中的青帝。这个传说流传很广。上世纪七十年代,长沙马王堆古墓出土的一幅帛画上就画着伏羲女娲婚配的图像。图像中伏羲女娲皆人首蛇身,尾部作交合状。①参见何介钧《马王堆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202-203页。类似图像新疆吐鲁番火焰山南阿斯塔纳古墓葬中也多有发现,伏羲女娲的面部,既有中原形象的,也有富于西域人长须高鼻特征的。②参见陈丽萍《关于新疆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地区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及一些问题的探讨》,《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第63-77页。创作时代自汉晋至隋唐时期。亦可证昆仑神话流传之广泛,影响之深远,不仅在中原流传,而且也在西域少数民族地区流布。
“神是原始人类的集体表象……包含着民族历史的内涵。”[22]昆仑神话是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文化,是中华民族童年时期生存与发展、观念和愿望的深刻记忆和优美表达。在这里,地理、神话和文化人格意义上的昆仑,互为渗透,形成了中国上古神话的恢弘意象,体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雄浑博大、朴厚精深。昆仑神话不仅从地理意义上把广袤的西域与辽阔的中原大地连为一体,而且从精神文化层面上把西域与中原融为一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重要远古肇源。值得重视的是,西域先民同样为昆仑神话的创造作出了贡献,其部族首领甚至成为神话的主角之一。昆仑神话为多元一体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根源性的诠释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新疆学者所说: “昆仑神话作为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大量的古籍记载,还是考古中发现佐证的诸多具有神秘色彩的字符或印迹,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发展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23]
六、结 语
综上所述,史前的新疆历史和文化是丰富多彩的。无论是各民族的共同开发,还是古 “玉石之路” “彩陶之路” “青铜之路” 的开辟以及昆仑神话的创造,都生动地反映出,是古代的各族先民用勤劳和智慧共同创造了灿烂的西域文化。西域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互鉴,息息相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休戚与共,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早期文明。虽然我们还不能说此时的各民族已经从多元走向一体,但我们从中可以清晰感受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新疆肇源的历史文化基础,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意识开始以一种自在的状态生成于各民族的历史活动之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24]千百年来,尽管历经风风雨雨,甚至曲折动荡,但始终没有任何力量能把新疆从祖国的肌体上分离出去,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初民阶段即已孕育、萌生的 “国家一统,中华一家” 的文化的力量,在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发展、巩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凝聚各民族的精神纽带,是我们必须奉守的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守住文化根脉,就是守住民族之魂。在建党百年华诞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5]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一起,去开创中华民族更加灿烂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