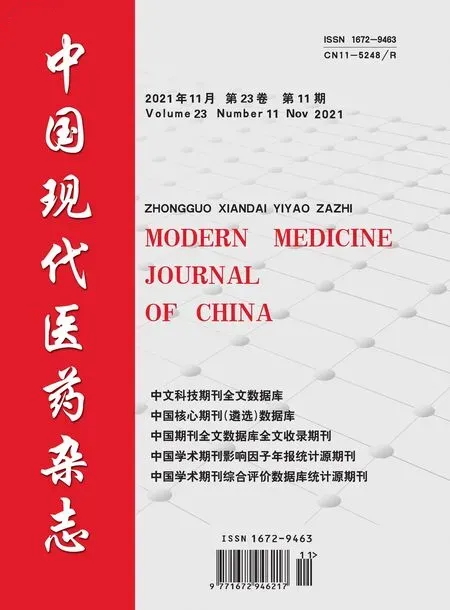癌症患者心理痛苦变化轨迹的研究进展
2022-01-01段应龙谢建飞李丽君丁四清钟竹青
段应龙 谢建飞 李丽君 丁四清 钟竹青
作者单位:1 中南大学湘雅三医院急诊科;2 护理部,湖南 长沙 410013
3 中南大学湘雅护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3
在21世纪癌症将成为全球因疾病而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阻碍生活期望提升的主要原因之一[1]。同时由于诊断与医疗技术的进步,癌症患者的生存率逐渐提高[2]。生存率的提高使癌症患者长期面临着生理、心理、社会、躯体等各种挑战[3,4]。心理痛苦在癌症幸存者中普遍存在,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包括心理、社会和/或精神上的体验,这些体验可能会影响患者的治疗。国内外研究表明癌症患者心理痛苦发生率为34.4%~65.9%,受年龄、性别、文化、疾病类型等多种因素影响,且呈动态变化[4]。心理痛苦随着癌症患者健康轨迹的变化而变化,从初始症状的出现、疾病的诊断与治疗、存活到生命的终结,心理痛苦的表现会有很大不同。心理痛苦变化的过程和原因使我们能够预测对轨迹影响较大的因素,增强对影响因素的理解,不仅能为干预措施的设计指引方向,也可以确定干预措施在哪段轨迹的作用最为有效。然而目前大部分研究关注于心理痛苦的横断面研究,心理痛苦的纵向研究极其匮乏。为此,现从癌症患者心理痛苦变化轨迹的内涵、评估工具、现状水平、影响因素和干预措施等方面进行综述。
1 心理痛苦变化轨迹的概念
健康轨迹是指健康随时间变化的过程,它描述健康和疾病的动态变化,受遗传、生物、行为、社会、文化、环境、政治和经济等多种因素影响[5]。心理痛苦为健康心理准度的一部分,心理痛苦变化轨迹则是指心理痛苦随时间或疾病进展变化的动态过程,是以时间为横轴,以心理痛苦为纵轴的函数模型。心理痛苦变化轨迹研究是指对个人、家庭、群体心理痛苦的纵向调查,它包括在自然情境中的观察研究,以轨迹为结果的实验研究或临床过程研究。横断面研究强调人们在某个时间点心理痛苦的差异,而心理痛苦变化轨迹研究的重点则是心理痛苦在一段时间内的动态变化过程,这个动态过程的变化趋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着多种类型的变化。
2 心理痛苦变化轨迹的研究现状
2.1 心理痛苦变化轨迹的模型Bonanno 开发的轨迹模型目前使用较广,并在多项实证研究中得到了验证[6~8]。它描述了人们适应逆境的4 个独特的轨迹类型,若将其运用于心理痛苦变化轨迹的研究,可将心理痛苦变化轨迹分为慢性心理痛苦型(Chronic distress)、延迟心理痛苦型(Delayed distress)、恢复型(Recovery)和弹性型(Resilience)4 种类型[9,10]。慢性心理痛苦型的患者心理痛苦处于持续高水平状态;延迟心理痛苦型的患者从创伤事件中恢复得很快,但是随事件的发展心理痛苦不断增强;恢复型的患者在事件初期会出现显著的心理痛苦,但随着治疗的深入,心理痛苦会逐渐降低,达到适应状态;弹性型患者心理痛苦处于稳定的低水平状态[11]。尽管Bonanno 开发的轨迹模型应用广泛,但其仅阐述了各轨迹类型的变化趋势,对各轨迹模型的特征及其变化机制并未作详细的归纳,同时也有研究发现患者的心理变化轨迹并非只有这4 种类型,还包括持续上升型、持续下降型等[9]。心理痛苦变化轨迹的内涵还需进一步深入和扩展。
2.2 心理痛苦的评价工具心理问题严重影响癌症患者治疗的依从性、治疗效果,也是导致癌症患者生活质量低下的原因,有效识别与评估是减轻癌症患者心理痛苦的关键。而发现患者的心理问题仅靠临床工作人员的经验判断会存在较大的偏差,利用科学的心理痛苦评价工具则更为有效。心理痛苦不仅包括沮丧、担心等正常心理感受,也包括抑郁、焦虑、恐惧等心理障碍[12]。目前心理痛苦筛查最为常见的是美国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NCCN)推荐的心理痛苦管理筛查工具,包括心理痛苦温度计和心理痛苦相关因素调查表两个部分,其中心理痛苦温度计以0~10 分表示心理痛苦程度,0 分为无痛苦,1~3分为轻度痛苦,4~6 分为中度痛苦,7~9 分为重度痛苦,10 分为极度痛苦。心理痛苦相关因素调查表共包括36 项心理痛苦相关因素,归属于实际问题、家庭问题、情绪问题、躯体方面问题及精神宗教信仰问题等5 个方面[13]。其他工具应用较多的有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14]、18 项简明症状量表(Brief symptom inventory-18,BSI-18)[15]、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re 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CES-D)[16]、广泛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GAD-7)[17]、患者健康状况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PHQ-9)[18]、贝克焦虑量表(Beck anxiety inventory,BAI)[19]、贝克抑郁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Ⅱ,BDI-Ⅱ)[20]、Zung 抑郁自评量表(Zung self 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21]等。同时客观指标包括唾液皮质醇[22]、脑电波[23]等,相比量表工具更加客观,不易受患者或测量者的主观影响。
2.3 心理痛苦变化轨迹的模式虽然Ziegler 等[24]结合国家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指南将心理痛苦变化轨迹分为4 期,分别为诊断-治疗前期、积极治疗期、治疗后、复发期/姑息治疗期,但大部分研究在心理痛苦纵向调查的时间选取上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Andreu 等[25]对102 例乳腺癌患者在乳腺癌初步诊断、术后2~7d、最终诊断及化疗期间4 个时期采用BSI-18 进行了心理痛苦的调查,发现心理痛苦在初步诊断时期程度最高,发生率为24.5%,其他3 个时期的心理痛苦程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Brinkman 等[26]采用BSI-18 对4 569 例儿童时期患癌症的成人进行调查发现,尽管少数癌症幸存者的心理痛苦程度随时间变化而有所加重,但大部分癌症幸存者心理痛苦并未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也发现心理痛苦症状的加重是疾病恶化的重要预测因素。Chen 等[27]通过对109 例青年癌症患者确诊癌症后2年内进行纵向调查发现,心理痛苦随着时间变化分为4 种变化模型,分别为弹性型、弹性增长型、心理痛苦持续型和心理痛苦增高型,并采用混合效应模型发现心理痛苦持续型和心理痛苦增高型与生活质量低下息息相关。Hellstadius 等[28]采用HADS 对108 例食管癌患者于术前、术后6 个月和术后12 个月调查发现,焦虑发生率随时间变化的波动不大,而抑郁发生率随时间变化呈增长趋势。Lotfi-Jam 等[11]采用BSI-18 对125 例癌症幸存者于治疗后2 周、3 个月和6 个月进行调查发现,65.8%的患者心理痛苦轨迹处于持续低水平状态,7.9%的患者处于持续高水平状态。Liu 等[29]采用心理痛苦温度计对新患癌症患者近1年的心理痛苦状况进行调查发现,69%的癌症患者心理痛苦变化轨迹处于稳定的低水平状态,31%处于稳定的高水平状态。李璐璐等[30]探讨乳腺癌患者从诊断期到过渡期心理痛苦的变化轨迹,使用增长混合模型识别出3 条不同特点的心理痛苦变化轨迹,分别为持续高心理痛苦组(5.3%)、心理痛苦下降组(57.2%)和无心理痛苦组(37.5%)。由此可见,不管是心理痛苦评价工具的选择,还是评价时间节点的选取,目前都没有统一规范的标准,且大部分纵向研究仅选取3~5 个时间点,研究时间较短,不能完全反映癌症患者心理痛苦变化轨迹的全过程。
3 心理痛苦变化轨迹的影响因素和干预措施
3.1 心里痛苦变化轨迹的影响因素心理痛苦的影响因素并不是唯一的,不同患者心理痛苦的影响因素并不一致,但可以归纳为疾病相关因素、照护因素、经济因素、个人因素、社会因素和精神健康因素,但这些横断面调查所得到的心理痛苦影响因素并不能反映其对心理痛苦变化轨迹的影响。目前心理痛苦变化轨迹的影响因素鲜有研究,仅少部分研究对心理痛苦变化轨迹的预测因素作了探讨。3.1.1 社会人口学 研究表明年龄较小者和教育水平较高者心理痛苦更容易沿着高水平心理痛苦变化轨迹发展[28,29]。年轻癌症患者需承担更多的经济负担和社会责任且面临个人发展问题,导致其心理痛苦水平居高不下。有研究发现年轻癌症患者可能面临经济上依赖家庭,事业发展中断以及自我形象减弱等问题,相比于其他年龄段人群,前列腺癌对年轻男性的心理伤害可能更大[31]。高教育水平患者更清楚癌症诊断和治疗的影响,对癌症治疗的期望值更高,可能会导致更多的心理社会问题。Dunn 等[32]也发现与家人一起居住的乳腺癌患者,在术后会表现出更高的焦虑状态、更低的疾病应对能力,这可能与家庭成员的影响有关。
3.1.2 性格特征 李璐璐等[30]分析了气质类型对乳腺癌患者心理痛苦变化轨迹类别的预测作用,发现抑郁质患者属于“心理痛苦组”的概率是胆汁质患者的15.63 倍,多血质患者属于“无心理痛苦组”的概率是抑郁质患者的142.86 倍,而胆汁质和黏液质患者在不同心理痛苦轨迹类别间差异没有抑郁质和多血质明显。乐观人格预示着患者在面对癌症时有更多的积极情感、更低的焦虑抑郁水平和心理痛苦[33,34]。虽然悲观人格与较高的心理痛苦水平有关,但在长期面对癌症时,同时出现乐观和悲观的应对轨迹可能表明患者防御性较强,避免了盲目的乐观或悲观,强调了系统地加强乐观主义以及承认积极和消极应对未来预期的重要性。
3.1.3 应对策略 Lotfi-Jam 等[11]发现慢性心理痛苦型和延迟心理痛苦型的患者具有较高的未满足需求、消极的应对方式及较低的社会支持状态,这提示我们解决患者未满足的需求,协助其积极应对并提供社会支持能预防肿瘤患者心理痛苦轨迹呈持续高水平状态。同时也发现情感抑制、特殊的应对方式(如无助、绝望)、认知回避及宿命论等与心理痛苦程度呈正相关[25]。在一项为期7年的对乳腺癌患者心理痛苦轨迹研究发现,在乳腺癌创伤过后,经常应用无助-绝望应对方式的患者较应用建设性应对方式的患者更有可能呈现一种虚幻感[35]。这说明在癌症患者后续生存期间,也要持续关注患者的心理康复问题。
3.1.4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包括整体社会支持和亲近关系社会支持。一项针对结直肠癌患者为期5年的6 个时间点的纵向研究表明,匮乏的社会支持与较高的心理痛苦轨迹有关[36]。长期的孤独感也预示着更高水平的焦虑[37]。医师的支持与患者更高的生活质量有关[38]。Shrout 等[39]在治疗结束后为期18 个月的调查中发现,满意的伴侣关系可能会促进乳腺癌幸存者的长期健康。
3.1.5 其他 除了上述相关因素,研究者也发现癌症所处阶段[40]、躯体功能[41]、自我认知与知觉[42]等也会影响癌症患者心理痛苦轨迹变化。
3.2 心理痛苦变化轨迹的干预措施目前心理痛苦的干预措施类型较多,包括社会心理干预、运动干预、补充替代治疗和药物干预。社会心理干预包括针对性格特征[43]、应对策略[44]、社会支持[45]、认知或知觉因素[42]等的干预设计,主要类型包括认知行为疗法[46]、心理教育、支持性治疗和家庭干预等。运动干预包括各类有氧运动、抗阻力运动以及混合方式运动等,规律的运动有助于减轻患者的心理痛苦[47]。这些干预措施一般在特定时间段实施,并不能随患者心理痛苦的存在动态实施。当前关于心理痛苦轨迹变化的干预在国内外均较少。
4 小结
癌症患者生存期的延长可能使患者面临着更长时期的心理痛苦。癌症患者的长期治疗以及复发、回归学习与工作均会影响患者的心理痛苦水平。了解癌症患者心理痛苦的变化轨迹,可以帮助临床工作者根据患者心理痛苦的变化轨迹向其提供合适且及时的心理支持或干预,以减轻癌症患者在各个阶段的心理痛苦,改善整体心理状态。根据目前研究发现,心理痛苦变化轨迹在个体及时间上呈现复杂性,虽然有一定的轨迹遵循,但每个个体的轨迹变化在时间上存在差异。同时当前纵向研究发现,诸多相关因素均会影响患者的心理痛苦轨迹。而当前针对癌症患者心理痛苦轨迹变化的干预较少。未来需要国内相关研究人员探索癌症患者心理痛苦轨迹变化标准化模式,制定动态的干预措施,使癌症患者在长期动态的心理痛苦中得到支持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