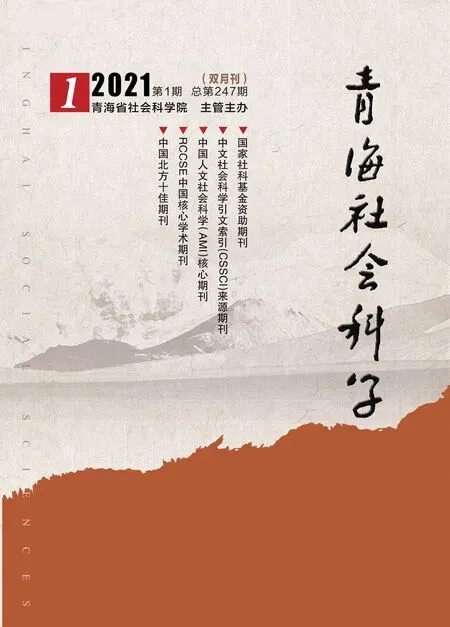意深词浅:袁枚“性灵”的特征与呈现方式
2022-01-01唐芸芸
◇唐芸芸
清代诗学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诗学的延续性和深刻性:一方面基于对明代诗学的反思,一方面建立在对前贤的或继承或批判的基础上,一方面于诗歌生命深处寻找普遍的或最美好的表达。人们提倡“性情”,自然可以针对明七子进行有效的“破”的工作。如果放弃对风格的纠缠,只提倡作为诗学基本表述的“性情”,确实是可以避免偏至的缺陷,体现出容纳百川的宽容性,即时代、风格都不足以作为价值高下判断的依据,只有抒发真性情的才是好诗。但是,这也同时消解了诗学批评的价值判断。所以,清代主流的诗学家,都会在提倡或默认“性情”的基础上,拈出新的诗学核心概念,来圆满其对文学的思考和体认,用以规范整个诗史并指导诗歌创作,这是诗学发展深入细化的表现。那么为何“性情”不能兼顾“立”的功能呢?因为“性情”只是诗学基础概念,在文学史的建构、文学理论的概括、文学批评的实践中有很多问题无法解决,如对性情的强调,是否满足人们对诗歌创作的所有需求?如果都强调抒发创作主体的真性情,那性情究竟该如何体现?诗人以创作呈现性情如何与常人的性情表达相区别?有没有一种具有普适性的、行之有效的呈现方式?抒写真性情的诗,会不会呈现出较统一的特征?即怎样呈现性情才更具有审美价值?性情还与哪些因素有关?性情及性情的表现是否有高低之分?如何评价性情诗的价值?……“性情”不具备诗学核心概念的全部功能。明代公安派正是忽视了这一点,所以纠偏失败,清代诗学家纷纷另立诗学核心概念以解决这些问题。
而到了乾隆时期的袁枚诗学,竟独提“性灵”,认为“诗者,持也,持其性情使不暴去也。人无性情之可持,于是以剿袭为诗,以摹仿为诗,以填写典故为诗,而诗之道日亡”①袁枚:《双佩斋诗集序》,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九册《零散集外文》,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26页。。为何在抒发性情已经成为普遍共识的时候,袁枚将诗学的全部都赋予一个基本的诗学概念“性灵”,诗学仍然能产生很大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性灵”,实则已经不再仅仅是作为基础的诗学概念,其本身具备了核心概念的一切品质与功能,故以“性灵”名之以示分别。
一、从诗学基础概念到诗学核心概念
自从《诗大序》对经典进行各方面的定义并被作为经典的组成部分被流传下来,其核心观念之一的“诗言志”便成为中国诗学的论述基础②《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应该是诗用,而不是诗的本质理论。。漫长的诗歌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如“诗缘情”“童心说”等等看似与“言志”异途的诗学观念,实则不过是“言志”中“情”与“性”关系的升降显隐而已③即使如明七子等被视为“无性情”的流派,我们仔细追寻这些流派的诗学表述,发现其也并没有对“吟咏性情”作为诗歌创作的本质特征有过任何质疑。他们的理论都是自然而然地建立在“吟咏性情”的基础之上对诗歌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阐释的。。这说明,“性情”是作为诗学基础概念而存在的。
对“性情”的回归,虽然是清代诗学的一大特色,但是到清中期为止,并没有一个诗学家对“吟咏性情”进行全面的反思、规范及实践。主流的诗学仍然是传统的思路:以“吟咏性情”为本质特征,着力于表述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各种诗学观念,如王士禛的“神韵”、翁方纲的“肌理”,但这二人的学说由于没有很好地阐释清楚性情的内涵,且诗学实践都缺乏包容性,偏至一隅,均招致袁枚“无性情”的批评。这种主张与表达分离的情况,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吟咏性情”的庄严性及其本质地位。袁枚为申甫诗集作序,认为当下诗坛,“有以数典为工者,有以貌袭自矜者,有泥于古者,有蔽于今者,有乘人而斗其捷者”等,这些人都“见貌自臧,律以‘性情’二字”④袁枚:《笏山诗集序》,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九册《零散集外文》,第45页。。“性情”变成一个人人可言的,仅仅作为基础却无法具体张扬的理论,至于对诗坛风貌的指导作用更是值得商榷。那么,“吟咏性情”的表述,重复得越多,便越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出现为了与传统衔接而取巧的嫌疑。“性情”作为诗学基础概念的效能实在有限。
诗学基础概念,是一切诗学观念的出发点,但不是最终的落脚点。也就是说,在性情作为诗学基础概念的时代,由此出发讨论诗歌,是一个共识,但不是终点。甚至在被无数次重复用于批评明七子后,已然不是诗学阐述的重点,诗学家的精力在于阐述其诗学核心概念。而在袁枚诗学中,不再有任何一个声明以“性情”为基础的处于核心地位的诗学概念。“性灵”就是袁枚诗学的核心。诗学核心概念,必须包含文学史的建构、文学理论的概括,以及文学批评的实践功能。袁枚的“性灵”,并不仅仅表述为诗人要写并且只能写自己的真性情,他对性情的深度、广度,以及呈现方式都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并且非常有效地进入诗歌批评和创作环节。这说明,袁枚的“性灵”诗学,承担了诗学核心概念的所有功能,从而呈现出的包容性,溶解了一切以时代、格调论诗并分高下的可能性。
那么,将“性情”从诗学基础概念转变为诗学核心概念,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可以从康雍时期的王士禛诗学中得到提示。王士禛强调伫兴,其实也是建立在“真性情”基础上的表述,我们不能轻易否认,渔洋奉命出使南海出京时感叹的“此去珠江水,相思寄断猿”,是出自真性情⑤参见蒋寅:《王渔洋与赵秋谷》,《王渔洋与康熙诗坛》,第198-204页。。但是王士禛的诗歌创作出现了格调上的趋同,所以招致批评。而这个趋同,正出于其对对象的把握方式⑥蒋寅:《王渔洋“神韵”的审美内涵及艺术精神》,《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第129-148页。。但王士禛试图用一种建立在把握方式和表现方式上的艺术风格统一整个诗歌的思路,给世人昭示了跳出唐宋诗之争的有效路径。这也是渔洋诗学成为乾隆诗学出发点的重要方面。而袁枚在“性灵”诗学的建构中,也是从把握和表现两方面入手的,这是“性情”从诗学基础概念转变为诗学核心概念的关捩。
二、独特、深刻、通达并归于“正”的人生体验
对于把握世界的方式,袁枚并没有具体的主张,他对把握的对象是什么更有兴趣。毫无疑问,自然是性情。但这个性情又具备什么特征呢?即在人与世界的关联中,怎样的体验值得书写呢?袁枚对性情的整理,出于对前代性情讨论的反思。“吟咏性情”已经融入中国诗学的血液中,流淌千百年。那么,同样是血脉相连的诗学,如明七子,又是如何走向“吟咏性情”的对立面呢?之后拯救明七子的公安派、竟陵派,对性情的召唤是那么明显和急迫,却为何无法成功整饬诗坛呢?
明七子,“以古之格调写今之性情”,性情被格调所制约,在选择和表达上都有严格的限制。正是因为格调相似,性情究竟是古人的还是今人,真假难辨。明七子对性情的表述中,在最基本的“真”的问题上受到质疑,性情变成了一种普遍性而千篇一律,招致了“无性情”的断语。
我们一般认为,明七子提倡以古人格调限制今人情感,是在体制上对诗歌“正”体的归依。但如果突出性情的部分,就可以看出,明人对性情入诗的筛选,是依照已经成为典范的诗歌“正体”的标准。以此论性情,便可以保证性情之“正”,这也是“雅”的一个方面。
强调“真”,是公安派诗学批判明七子的核心。但公安派的兴盛如昙花一现,正是因为其斩断了文学创作与传统的联系,只求“真”与“变”。公安派对性情的宽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不仅仅是缺乏“雅”,而且缺乏深刻性。他们对“真”与“变”的浅率理解,搅动了整个诗坛,但是对人生体验的深刻性并没有认知的自觉,所以招致“浅率俚俗”的批评。
竟陵派自然是看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要学习的是古人之精神,归结起来就是“孤”“独”。这本是非常深刻的人生体验。但是竟陵派却并未以这种深刻的人生体验对整个诗史进行观照,而是将“孤”“独”直接置换为风格方面的范畴,仅仅将眼光局限于“深幽孤峭”的晚唐诗歌。这是明代诗学对七子纠偏的再一次失败。
归结起来,明代诗学在性情问题上,公安派通达却不深刻,且不归于“正”,竟陵派深刻却不通达。而明七子似乎在性情问题上最没有发言权。其诗学实践中出现的性情雷同,成为后人纠偏的重点;其对“正”的追求,以及公安派纠偏的失败,却也昭示了诗歌性情的基本特征之一。自从清初钱谦益解决了性情与格调孰先孰后的问题,人们已经不再将二者一一关联。而对性情之“正”的讨论,成为主要问题,如黄宗羲等讨论忠孝。性情之“正”究竟如何限定?深刻、通达与“正”之间的关联如何?这些都在袁枚对性情的全面反思中得以解决。
袁枚认为,创作主体需要把握的是对象化客体,需要呈现的不是物本身,而是在人与物的关联中体认出来的独特、深刻、通达并归于正的人生体验。这些特征,鲜明地体现了袁枚与明代公安派、竟陵派谈性情的区别,也真正对“性情”的内涵做了最大程度的消纳和清理。
首先,性情之“真”,来源于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景是众人同,情乃一人领”①袁枚:《人老莫作诗》,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二册《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五,第553页。,面对类似的对象,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体验,这是由个人之“性”决定的。“人之才性,各有所近”②袁枚:《答蕺园论诗书》,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三册《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第594-596页。。“性”来源于天,“其人之天有诗,自能妙万物而为言;其人之天无诗,虽勤之而无益”③袁枚:《存素堂诗初集序》,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九册《零散集外文》,第33-34页。。诗人之性就是“萃天地之清气,以月露、风云、花鸟为其性情。月露、风云、花鸟之在天地间,俄顷灭没,惟诗人能结之于不散”④袁枚:《随园诗话》卷三,一九条引黄宗羲语,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81页。,就是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所以“诗写性情,惟吾所适”⑤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六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4页。,且“我欲为则为之,我不欲为则不为”①袁枚:《随园诗话》卷三,十四条引周亮工语,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79页。。
深刻性是袁枚“性灵”的重要特征。蒋寅先生已经明确指出:性灵,不仅仅是灵动,有趣。更在于注重人生体验的深度。那种深度既可以体现于儿童、老妪都能领略的浅俗歌诗,也能体现于人所共知、人所同感的格言警句②蒋寅:《袁枚诗学的核心观念与批评实践》,《文学遗产》2013年第4期,第118-126页。。我们翻阅袁枚诗集,发现其诗歌被大量的花事占据,如《落花》组诗③袁枚:《落花》,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小仓山房诗集》卷三,第38-40页。、《伤桐》④袁枚:《伤桐》,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一,第234页。《悼柳》⑤袁枚:《悼柳》,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五,第305页。《买梅》 《种梅》 《看梅》 《折梅》系列⑥袁枚:《买梅》《种梅》《看梅》《折梅》,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小仓山房诗集》卷十,第193-194页。等,他自称“最识花情性”⑦袁枚:《有恨》,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小仓山房诗集》卷二三,第515页。“一生不肯离花住”⑧袁枚:《记得》,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第428页。“坐拥牡丹与芍药,是老人极得意时也”⑨袁枚:《与陶怡云(四)》,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九册《零散集外尺牍》,第61页。“我宁负人不负花,花开时节常归家”⑩袁枚:《供芍药数十枝中日对花独坐》,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二册《小仓山房诗集》卷二七,第633页。,《又病》中“消受名花都有分,年年只是负芙蓉”⑪袁枚:《又病》,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五,第321页。惹人动容。而他“处处种幽兰,朝朝对牡丹。主人心未足,自画一花看”⑫袁枚:《画》,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第439页。。花事陪伴至老,花诗中也承载着诗人对时间的敏感,更集中体现了他对天地万物的热忱,这种热忱,是以自己为万物之一的平等相待,是一种最真诚的热爱。
与深刻性紧密相关的是“通达”,若无通达,便无法顾及各种人生体验,容易以一种或一类体验概括整个人生及群体体验,甚至很容易如竟陵派一样将体验置换成风格。最著名的材料是袁枚在《再与沈大宗伯书》中对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不选王彦泓(次回)艳体诗的讨论:
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孔子不删郑、卫之诗,而先生独删次回之诗,不已过乎⑬袁枚:《再与沈大宗伯书》,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三册《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第323页。较早关注袁枚的日本学者铃木虎雄,认为袁枚对王彦泓艳体诗之见“太过”。铃木虎雄著,孙俍工译《中国古代文艺论史》,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33页。?
袁枚关于男女之情的看法,还可见于《答蕺园论诗书》:“有必不可解之情,而后有必不朽之诗。情所最先,莫如男女。”⑭袁枚:《答蕺园论诗书》,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三册《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第594-596页。所谓“不可解”,与叶燮的“不可解”不同:叶燮的“不可解”,为不可与客观事实相比附的解释;而袁枚的“不可解”,是解不开、无法化解之意。男女之情,确实是自古以来均无法化解之情愫。从这个角度来说,对男女之情的深刻体验,便是产生不朽之诗的重要来源之一,自然应在体现“不拘一格”⑮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原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的《清诗别裁集》中。
除了倡导男女之情入诗,袁枚还批评唐顺之说诗文带富贵气则不佳⑯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七四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532页。,认为“笔性灵,则写忠孝节义,俱有生气;笔性笨,随咏闺房儿女,亦少风情”⑰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二,七二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五册,第673页。。所以,在袁枚这里,“志”有多种:
诗言志,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⑱袁枚:《再答李少鹤》,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八册《小仓山房尺牍》卷十,第232-235页。。
袁枚对人生体验的接纳,是非常通达的。只要具有独特性和深刻性,无论忠孝节义、富贵雍容,还是儿女之思,都值得入诗。不过,这些性情都应归于“正”:
舍性情无以言诗,而非正亦不足以见性情。……夫论不归于卓犖,事不切于伦常,则岁妍辞丽句,嚼徵含商,不逾时而散为飘风燐火者,不少矣①袁枚:《仙霞阁诗草序》,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九册《零散集外文》,第18页。。
其天高,其学广,故其蕴深而旨趣远;其涉历久,故其识充而指陈实;其性情和以庄,故渢渢乎韵之流、风之永,而莫不轨于正②袁枚:《小画山房诗钞序》,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九册《零散集外文》,第27页。。
袁枚对性情有一个导向性的制约,只不过这个制约并不是理学意义上的,不是“义理之性”,而是用“论归于卓犖,事切于伦常”简单概括,指的应该是对事理、伦常的遵循。性情的独特、深刻与通达,都归之于“正”。袁枚认为“言为心声,诗又言之至精者也。试观汉魏三唐以迄两宋,凡以诗鸣者,大率君子多,佥人少”,“心善则虚,虚则受”③袁枚:《存素堂诗初集序》,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九册《零散集外文》,第33-34页。,他承认道德与诗歌创作及流传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这里的“心虚”,指的是“作诗如鼓琴然,心虚则声和,心窒则声滞”④袁枚:《龚旭开诗序》,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三册《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一,第219页。。袁枚特别强调人格之“清”,专作《清说》一文以明之⑤袁枚:《清说》,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三册《小仓山房文集》卷二二,第423-425页。。相应地,作为源头的“性情”必须“清”:“性情者,源也,词藻者,流也。源之不清,流将焉附?”⑥袁枚:《陶怡云诗序》,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三册《小仓山房文集》卷三一,第632-633页。他对性情并非放任入诗,这一点很明显。“先有寸心,后有千古”⑦袁枚:《答蕺园论诗书》,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三册《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三十,第594-596页。,袁枚强调的性情之“正”,与明七子的“正”自然有别,但思路是一致的,或者说正是解决了七子留下的问题。
三、意深而词浅:性情的呈现方式
性情在袁枚这里获得了广度和深度上的限定,指向的是诗歌创作主体体验的过程。那么,具体到诗歌的呈现,袁枚也有其倾向,那就是“意深而词浅”。词之浅深,与性情之厚薄有这样的辩证关系:
朱竹君学士曰:“诗以道性情。性情有厚薄,诗境有浅深。性情厚者,词浅而意深;性情薄者,词深而意浅。”⑧袁枚:《随园诗话》卷八,九九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309页。
因为诗以“性情”为主,所以诗的薄厚以性情而论,而不是以词的深浅论。性情之“厚”,即上文分析的独特、深刻、通达、归于“正”等。浅白的表达,能更好地承载深刻的人生体验,若希冀用艰深的语汇营造出一种深刻的表象,那样反而会将性情稀释,会导致转换:“性情薄者,词深而转浅;性情厚者,词浅而转深。”⑨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一〇一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545-546页:近见作诗者,好作拗语以为古,好填浮词以为富,孟子所谓“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朱竹君学士督学皖江,来山中论诗,与余意合。因自述其序池州太守张芝亭之诗,曰:“《三百篇》专主性情。性情有厚薄之分,则诗亦有浅深之别。性情薄者,词深而转浅;性情厚者,词浅而转深。”余道:“学士腹笥最富,而何以论诗之清妙若此?”竹君曰:“某所论,即诗家唐、宋之所由分也。”因诵芝亭《过望华亭》云:“昨夜望华亭,未睹九峰面。肩舆复匆匆,流光如掣电。当境不及探,过后心逾恋。”“九叠芙蓉万壑深,登临不到几沉吟。何当直上东峰宿?海月天风夜鼓琴。”又,《江行》云:“犬吠人归处,灯移岸转时。”《端阳》云:“看人悬艾虎,到处戏龙舟。”《太白楼》云:“何时江上无明月?千古人间一谪仙。”《同人自齐山泛舟》云:“聊以公余偕旧友,须知兴到即新吾。”皆极浅语,而读之有余味。昔人称陆逊意思深长,信然。芝亭字仲谟,名士范,陕西人,今观察芜湖。其长君汝骧亦能继声继志。《题署中小园》云:“风吹花气香归砚,月过松心凉到书。”《将往邳州》云:“此去正过桃叶渡,归来不负菊花期。”又,《华盖寺》云:“曲径松遮洞,岩深寺隐山。”皆清雅可传。
袁枚引赞《漫斋语录》“诗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淡”一语,并对“精深”和“平淡”进行分析:
(余)每作一诗,往往改至三五日,或过时而又改。何也?求其精深,是一半工夫;求其平淡,又是一半工夫。非精深不能超超独先,非平淡不能人人领解。朱子曰:“梅圣俞诗,不是平淡,是枯槁。”何也?欠精深故也。郭功甫曰:“黄山谷诗,费许多气力,为是甚底?”何也?欠平淡故也。有汪孝廉以诗投余。余不解其佳。汪曰:“某诗须传五百年后,方有人知。”余笑曰:“人人不解,五日难传,何由传到五百年耶?”①袁枚:《随园诗话》卷八,六六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294页。
这里的“精深”,需要“气局见解,自然阔大”②袁枚:《随园诗话》卷四,二九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121页。,不仅仅指的是人生体验的深刻,还指的是在诗歌中将这种深刻表达出来。袁枚批评黄庭坚诗,虽然力大,但艰涩拗口,气象反而变得局促。
在“意深词浅”这一点上,袁枚与沈德潜“其言浅,其情深也”有一致之处,但沈德潜的“言浅”,是去“质直铺陈”,崇尚比兴③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二条,潘务正等编《沈德潜诗文集》第四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1908页。,袁枚则着重在用典上进行批驳。他对用典一直保持着警惕,认为“笔豪健,好征典者,短于言情”④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五七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525-526页。,并援引叶燮的比喻:“用典如水中著盐,但知盐味,不见盐质。”⑤袁枚:《随园诗话》卷七,六七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255页。他自己的写作经验是这样的:写咏物、咏史诗,把材料翻遍,但却有典不用⑥袁枚:《随园诗话》卷一,四三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21页。。不提倡大量用典,并不是不知道这类典故,而是将这些典故的精髓融入精深之意中,但不具体出之。这样的写作,自然需要“改至三五日,或过时而又改”的。“精深”需要用“平淡”之语,方能有助于气局见解的表达,亦便于“人人得解”,以求得深意的广泛流传。
袁枚要求的“浅”,并不是“浅俗”的“浅”,正如《随园诗话》中强调的“诗贵淡雅,但不可有乡野气”,“乡野气”,便是一种粗率浅俗的表达,并无深意⑦袁枚:《随园诗话》卷四,二九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121页。。他还以梅尧臣为例辨析了平淡与枯槁的区别⑧袁枚:《随园诗话》卷二,四一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53页。。袁枚特别强调,“词浅而不失之俚,意深而不失之晦”⑨袁枚:《蓬岛樵歌题辞》,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九册《零散集外文》,第53页。。这种“浅”,不是指向直接的、毫无修饰的陈述,而是承载着深刻的人生体验,并对这种深刻进行反思、消化,最后竟出之以自然,不借助于艰涩的典故,深奥的表述。袁枚说的“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⑩袁枚:《随园诗话》卷五,四三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162页。正是此意。“朴”不是简单的朴实无华,而是出之于大巧之朴,洗净铅华后的“朴”。袁枚的“浅”,是一种在经历过深刻体验后对自然状态的回归,有类于在“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之后进入到的“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状态。正如他批点赵翼诗时说的:“诗到真处,白描胜于着色。”⑪袁枚:《瓯北诗抄》附袁枚批语《赴滇从军作》后批语,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三册《小仓山房文集》辑补,第741页。翻阅《随园诗话》中表扬的“天籁”之作,无不具备“意深词浅”的特征,如:
诗有极平浅,而意味深长者。桐城张徵士若驹《五月九日舟中偶成》云:“水窗晴掩日光高,河上风寒正长潮。忽忽梦回忆家事,女儿生日是今朝。”此诗真是天籁。然把“女”字换一“男”字,便不成诗。此中消息,口不能言⑫袁枚:《随园诗话》卷八,八六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304页。。
青阳两诗弟子:一陈蔚,一沈正侯也。二人有五绝句,皆天籁而不自知其佳。余为表而出之。陈《春闺》云:“春来花满枝,春去花散飞。几度花开落,栽花人未归。”沈《村晚即事》云:“身安万事闲,日落一村静。携儿向月明,壁上看人影。”皆绝妙天籁,非粗心者所知⑬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四,六七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五册,第733页。。
这里还可以关联到学问的问题。我们常常以为袁枚诗学是排斥学问的。其实袁枚说过,诗歌“妙境”,“全在书卷富足,方寸灵明”⑭袁枚《再答李少鹤》,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八册《小仓山房尺牍》卷十,第233页。,所以学问是其“意深”的根基之一,还是避免浅俗的法宝:“诗难其雅也。有学问而后雅,否则俗鄙率意矣。”并将诗之“雅”与“真”并立⑮袁枚:《随园诗话》卷七,六六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255页。。但这并非主张在诗歌中直陈学问,因为这违背了“词浅”的原则。学问之厚重,是融入到“意深”中的,与袁枚对典故的态度一致。
具体到袁枚的诗歌创作上,学界一般认为“袁枚主张雅,但其作品仍被视为俚俗”,有研究者分析原因:第一,正统诗学的雅,包括内容与审美表现形式两方面。而袁枚所谓雅并不指性情方面的含义,并不指性情之正。第二,题材方面,正统诗学认为并非一切事物都可以入诗,入诗与不入诗的分别,就是雅俗。第三,即使是审美表现形式方面,具体内涵也与传统诗学不同。正统诗学在审美表现上要求的雅,是典雅,或是清雅,或是古雅等,是与通俗对立的。而袁枚的雅却是与通俗相通的,以俗为雅①张健:《清代诗学研究》第十六章《古典与近代之间:袁枚的性灵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26-781页。。
学界对袁枚诗歌“俚俗”的判断,显然大有可商榷之处。袁枚确实在理论上主张“雅”,《续诗品》中专有“安雅”一品。虽然其不主张唐宋之争,但若非要以某一个标准分唐界宋,那只能拈出一“雅”字②袁枚认为诗分唐宋在于唐全都雅,而宋以后有欠雅驯。而不应该以含蓄、刻露分唐宋。袁枚:《随园诗话》卷七,四六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247页。。袁枚对“性情”有“正”的规范,即最基本伦常,只不过这个“正”,比义理之性范围要大得多,但也不是“一切事物都可以入诗”,必须是体现独特、深刻、通达并归于“正”的性情才能入诗。而所谓“清雅”,更是袁枚直接使用过的术语,如《随园诗话》中对张士范诗的评价便是“清雅可传”③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一〇一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545-546页。。至于其诗歌创作,也如其诗歌理论,“意深词浅”,与一般的俚俗并不能相提并论。
袁枚的“雅”确实比明七子的复古风潮对传统的依随呈现出来的“雅”要宽泛,但其诗歌也没有与“通俗”相通,并没有流入俚俗。学界之所以有这样的误解,原因有三:
原因之一是出于袁枚对“诗人”身份的划定:“诗境最宽。诗之所以为大。读书穷尽未必得,村妇也可以偶得”④袁枚:《随园诗话》卷三,五〇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95页。,看起来似乎是在诗歌“雅”事中纳入了“俗人”之作。袁枚认为,有独特、深刻、通达并归于“正”的人生体验之人,并不是以知识占有、财富占有、权力占有来划分的,而是以天性决定的。只要是值得回味、共享、传播的人生体验,都可以入诗。诗人身份的“俗”,并不会导致诗歌之“俗”。无论袁枚是与“赀郎蠢夫互相酬和”,抑或“燕钗蝉鬓,傍柳随花,问业于前”⑤铃木虎雄著,孙俍工译《中国古代文艺论史》,第109页。,并不影响袁枚作为“诗人”的表现权力。
原因之二是袁枚提倡“词浅”,并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践行。但上文说过,袁枚的“浅”,并不是浅俗,而是对人生体验的最佳表达。他写母亲之情:“手制羹汤强我餐,略听风响怪衣单。分明儿鬓白如许,阿母还当襁褓看。”⑥袁枚: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小仓山房诗集》卷二二,第494页。诗中并没有深奥的典故,或精心的布局,但我们能感受到真实的生命气息,让人感动。词之浅,并不足以推导出诗“俗”。
原因之三是袁枚诗歌中有大量入诗的题材,不见于传统诗歌,如写癣、疮、染须等俗物俗事。但是,袁枚非常强调咏物诗的寄托⑦袁枚:《随园诗话》卷二,六三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64页:咏物诗无寄托,便是儿童猜谜。,诗歌要体现的,不是“物”本身,而是人生体验。这些俗物俗事,只是人生体验的载体。如著名的咏苔诗:“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⑧袁枚:《苔》,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小仓山房诗集》卷十八,第394页。还有另一首《苔》:“各有心情在,随渠爱暖凉。青苔问红叶,何物是夕阳。”⑨袁枚:《苔》,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小仓山房诗集》卷二一,第469页。《诗集》卷十三连咏镜、簾、床、灯、扇、尺、杖、帐、香等,都是寄物咏怀之作⑩袁枚:《镜》《簾》《床》《灯》《扇》《尺》《杖》《帐》《香》,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三,第271-273页。,更不用说《随园二十四咏》⑪袁枚:《随园二十四咏》,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五,第324页。,甚至还咏钱:“百物皆可爱,惟钱最寡趣。生时招不来,死时带不去。”⑫袁枚:《钱》,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二册《小仓山房诗集》卷三五,第917页。俗事如写齿痛⑬袁枚:《齿痛》,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三,第261-262页。必与《噬嗑》联系;治瘧的过程也是写得起伏跌宕,读来如同身受⑭袁枚:《瘧》,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小仓山房诗集》卷十二,第247页。;《镊须》写尽了对十六年时间流逝的感叹⑮袁枚:《镊须》,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小仓山房诗集》卷十四,第293页。;《苦疮》⑯袁枚:《苦疮》,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小仓山房诗集》卷三,第45-46页。末句“秋月照瘢痂,点点亦孤映”是对“满目尚疮痍,我身胡独争”感叹的诗意呈现。题材之“俗”,词之“浅”,但前提都是“意深”,便不至于将这些诗划入“俗”。
袁枚用诗歌记录其生命的每一次体验和感动,草木鸟兽、器皿珍藏等或寻常或异常之物,早起、午倦、晚眺、不寐、生病、客来,乃至斗蟋蟀、推窗、染须(或不染须)等平常事物,及建成随园的过程等生活细节,更不用说春秋四季或读史看书的感悟了。至如“一卷书开引睡迟,洞房屡问夜何其。高堂怜惜小妻恼,垂老还如上学时”①袁枚:《一卷》,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小仓山房诗集》卷十六,第339页。,不正是生活之情调吗?但凡诗人生命中有感触有体验的时刻,都被写入诗。当然其中不乏如《拔齿》《补齿》②袁枚:《拔齿》《补齿》,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一册《小仓山房诗集》卷二一,第463-464页。等稍嫌过分呻吟的篇章,但总的来说袁枚的诗歌生命无疑是完整的,丰富的,诗中充满着起伏的情愫,无不体现出他对生命的极大热忱和对时间的敏感。耳顺之后,“老”是常见的题目,他临终作诗除留别诸人外,还再作诗留别随园③袁枚:《病剧作绝命词留别诸故人》《再作诗留别随园》,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二册《小仓山房诗集》卷三七,第1008页。,词中流露出的哀戚被坦荡消解,体现了生命厚重的圆满、自得与不舍,与其遗嘱一样,像一个远行者的交代。这是一个至死写诗并将诗独独视为性情写照的诗人,如蚕吐丝般,“一使千秋知”④“一笑老如此,作何消遣之?思量无别法,惟有多吟诗。譬如将眠蚕,尚有未尽丝。何不快倾吐,一使千秋知。”袁枚:《遣怀杂诗》,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二册《小仓山房诗集》卷三一,第790页。。袁枚的诗作践行“意深词浅”,虽然转益多师,不名一家,但呈现出“乃无心而自合唐音”⑤袁枚:《随园诗话》卷七,六七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255-256页。的情况,自然也是“雅”的。
结 语
人们都很清楚,明七子的偏执表现在对传统典范的执着上,以至于牺牲个性而希求与传统相合。公安派、竟陵派都试图进行矫正,但都以失败告终。公安、竟陵的诗学观念自然都存在问题,上文已有讨论。但究其核心,是公安、竟陵并没有找到明七子诗学失误的根本原因。我们知道,严羽的《沧浪诗话》对七子的影响很大,清人批评七子时也常常捎带对严羽进行批驳。严羽诗学的核心是推崇盛唐,核心表述是“兴趣”。“兴趣”即“感兴的趣味”,在于对审美对象的感兴,并于诗歌中的趣味呈现,这才是盛唐人的妙悟,与宋诗的理趣相对,以李白、杜甫为代表。若明七子遵循严羽推崇盛唐的思路,自然是应该推崇“兴趣”,往前追溯,与陈子昂提倡的“兴寄”也有相通之处。但明七子对盛唐人的妙悟,只在于接受了“格”与“调”,即看重的是文本形成的过程,而忽视了感兴的产生和呈现,特别是忽视了对现实人生的体验。公安派、竟陵派都没有直接指出并解决这个问题,所以纠偏失误。清代诗学发展到中期,对明七子的问题不再止于情感上的立场表达,而必须深入到诗学核心,所以,开始对诗歌创作主体与对象的关系、诗歌产生过程更加重视,如叶燮对“理事情”的分析,如王士禛对伫兴的坚持,如翁方纲试图以“事境”进行重新表述等等。袁枚在这一点上走得更远,他强调性情是对现实人生的体验,这种体验独特、深刻、通达,并归于“正”,实则接续了陈子昂的“兴寄”传统,而“兴寄”又是陈子昂对汉魏传统的归纳。如此,中国文学情感表达的传统得以在诗学上完成接轨并深化,尽管袁枚并没有明言这一点⑥袁枚对严羽的理解仍同于常人的误解,认为严羽所说的“羚羊挂角”“香象渡河”,只是诗中一格,必须知道,但不是全部。王士禛奉为至论,不妥。袁枚:《随园诗话》卷八,七一条,王英志编《袁枚全集新编》第四册,第296页。。袁枚只谈“性灵”,便可以包含对文学史的梳理、文学理论的概括,以及文学批评的实践,说明“性灵”并不仅仅如“性情”一样只是诗学基本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性、自足性,以及价值判断适用性的诗学核心概念,体现了袁枚对传统诗学的深刻反思。特别袁枚对“意深词浅”的强调,并在具体的诗歌批评和创作中践行,使得中国古代诗歌情感表达的传统拥有了详尽清晰的内涵及具体可行的呈现方式,用于整饬诗坛风气,无疑是良药一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