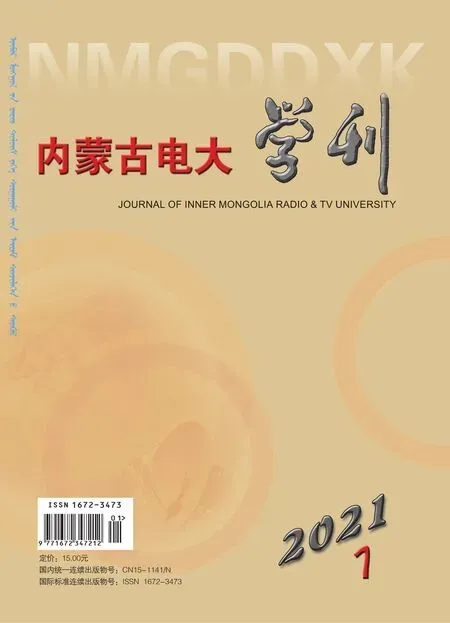入华粟特人墓葬浮雕中葡萄元素初探
2022-01-01赵沛尧
赵沛尧
(新疆师范大学 历史学与社会学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7)
我国学界对粟特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在经历近百年的发展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总览粟特研究的成果,大体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粟特本土历史研究、粟特文文献研究和入华粟特人研究。前两个方面多以考古文物为依据,因粟特文为一门死文字,在学习等方面存在较大困难,研究成果不容易取得,所以入华粟特人这一方向被大多数学者所关注。自21世纪以来,随着一批入华粟特人墓葬的发现,学界对入华粟特人的研究有了更深层次的进展。针对入华粟特人墓葬的浮雕问题,国内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对浮雕内容解读和浮雕顺序整理等领域,多以饮食、服饰、生活方式为研究视角,对墓葬上浮雕单一元素的关注较少。鉴于葡萄元素作为入华粟特人墓葬浮雕上多次出现的重要元素,笔者将出现葡萄元素的粟特人墓葬进行统计分析,从三个方面来阐释入华粟特人与葡萄元素的关系。
一、浮雕上的葡萄藤蔓
在入华粟特人的墓葬中,很多浮雕中都绘有大量的葡萄藤蔓。在安伽墓的石椁浮雕中就有萨保在葡萄园与突厥人一起饮宴和观赏舞蹈的场景;虞弘墓五号浮雕的夫妻饮宴场景,浮雕上部也绘有大量的葡萄藤蔓;史君墓和安阳出土的浮雕中,也出现了入华粟特人在葡萄架下饮酒庆祝节日的场景。这可能是根据当时入华粟特人的生活环境描绘的。
荣新江在《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一书中这样写道:“粟特聚落中建有葡萄园,在新年节庆日子里,人们带着礼物和祭品,聚集到首领或其他贵人的葡萄园里,饮酒作乐,而且不分男女都可以参加这种户外活动,与汉地的习俗不同,粟特聚落中有生长旺盛的葡萄,形成葡萄园,这必然是粟特移民种植的结果。”[1]不仅如此,他们的节日也与葡萄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类节日里多数活动又在葡萄园中进行。根据阿里·比鲁尼的研究:“每年的五月十八日是里巴巴花拉节,又作巴米花拉节,意即饮纯美葡萄浆。二十六日是卡林花拉节,意为品尝葡萄。这个节期在下半年持续很久,自七月十六日始,至八月九日终”[2]
其实,葡萄园的功能不止于单纯的饮宴庆祝活动,还带有一定的宗教意味,这与粟特人信奉祆教密不可分。藏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的安阳北齐石棺床的一幅浮雕中,生动描绘了当时祆教徒在葡萄园举行赛祆活动。“赛祆”是对祆教祭祀活动的总称,包括“燃灯仪式”“供奉神食及酒”“幻术表演”“雩祭”等四项内容。 虽然自索罗亚斯德之后祆教已经有了祆祠,但是这种野外赛祆的传统依然被保留了下来。入华粟特人初入中原后,作为虔诚的祆教徒,由于没有专门用于祭祀的祆祠,他们便恢复了野外赛祆的传统。在赛祆仪式中,以酒(葡萄酒)祭祆作为一个重要环节,被入华粟特人格外重视。据《敦煌文书》中的《官酒户马三娘龙粉堆支酒本和算会碟附判词》:“四月十四日,夏季赛袄用酒肆瓮。”[3]P2629《酒破用历》:“城东袄赛神酒两瓮。”[3]P3929《敦煌廿咏·安城袄咏》:“更有雩祭处,朝夕酒如绳。”[3]可见入华粟特人在进行赛祆仪式时,葡萄酒作为仪式的重中之重,是必不可少的物品。由此推断,为了赛祆活动的便捷,野外最好的赛祆场所,就是粟特人自行建造的葡萄园。
可见,入华粟特人墓葬浮雕中出现的葡萄藤蔓,一方面是入华粟特人在聚居地种植葡萄的结果,另一方面则跟祆教在粟特人心中的重要地位有关。
二、酿造葡萄酒
葡萄酒最早由西域传来,最早酿造葡萄酒的方法也来自西域。关于酿造葡萄酒的方法,在入华粟特人的墓葬中已有所展现。在甘肃天水出土的粟特人墓葬中,该墓葬石棺床的9号浮雕,展示的是一幅酿造美酒的场景。该浮雕中部有一高台,三人坐在台上,似在进行酿酒作业。高台底部有两个兽头,口中流淌着美酒。兽头下面两个大瓮正在盛接。
虞弘墓的左侧的第二块浮雕同样描绘的是一幅酿造葡萄酒的场景。根据《太原隋代虞弘墓清理简报》(以下均称《简报》)的描述,该浮雕画面左上方为一座精雕细刻的六角台座,上有勾栏,栏内从左至右并列三人,手臂相接,蹲腿屈膝,做舞蹈状。三人均为男性,体态肥腴。 但是,关于这三名男子的动作,学界有着不同的解释:《简报》称之为做舞蹈状(胡旋舞) ;姜伯勤认为该浮雕是一幅描绘祆教仪式的图像;[4]还有部分学者认为这是酿造葡萄酒的场景 。针对以上三种不同的解释,笔者更倾向于第三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根据安伽墓、史君墓的石椁中的与胡旋舞有关的浮雕来看,表演胡旋舞的舞者,几乎都是一人独舞,或是几人分开单独跳舞。日本学者森安孝夫在对胡旋舞考证之后,得出以下结论:“胡旋舞的特征就是在于高速旋转,可是必须在被称为舞筵的小块圆形绒毯上面跳舞,不能够离开绒毯一步。”[5]综合其他出现胡旋舞的墓葬浮雕及森安孝夫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大部分胡旋舞场景基本上都包含以下几个元素:(1)有乐师的伴奏;(2)有酒器;(3)圆形绒毯。而虞弘墓的这幅浮雕中仅仅出现了一只胡瓶,胡旋舞必备的圆形绒毯也未有出现。而虞弘墓的第5号浮雕中出现的胡旋舞场景,则是一名男子在圆形绒毯上完成的。就笔者看来,这三名男子跳胡旋舞的结论应不成立。
姜伯勤以浮雕中一些人物存在头部光环从而判定这幅画面反映的内容是祆教的某种场景,但马尔沙克认为并非如此。他指出:“画面中有的人头周围有光环,有的没有,这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含义,因为头光只是装饰性的,与人物的身份和宗教地位无关。”[6]为了印证马尔沙克的这一说法,笔者对虞弘墓石椁浮雕上的人物形象做出了详细的统计,结果如下:
发现其中共绘有人物34人,其中有头光的人数为23人,无头光的人数为11人。在虞弘墓正中心的夫妻饮宴图中,四个侍从都绘有头光,反而男女主人没有头光。在第三、第四幅浮雕之中,描绘的是同样的场景,但第三幅中的人物绘有头光,而第四幅却没有。经过笔者细微比较发现,两幅图像存在着细微的差别。如第四幅浮雕的骆驼绘有驼峰,而第三幅没有;第三幅射手的飘带,在第四幅浮雕中也没有展现。所以笔者认为雕刻虞弘墓浮雕的工匠在雕刻过程中可能存在疏忽或是其他原因,从而导致了一些细节出现了偏差。虽然说头光确实是神祇身份的一种象征,但在研究虞弘墓的浮雕时,我们并不能把有无头光作为区分凡人和神祇的唯一标准。所以,笔者认为姜伯勤的这一观点还是存有疑问的。
一部分学者认为是酿造葡萄酒的场景,也就是所谓的“踏浆”,这是一种古老而传统的葡萄酒酿造方式。马尔沙克认为,这是一个罗马题材——普提神(putti)榨葡萄汁的场景。在古埃及纳卡法老陵墓的一幅壁画上,很明显地看到几个工人站在一个装满葡萄的浅池中,正在赤足踩踏。这种方法后来也出现在古罗马的壁画之中,如罗马圣贡斯坦扎教堂回廊顶的马赛克镶嵌画。在澳门葡萄酒博物馆,还专门展出过一幅图片,在一个硕大的容器上,有许多男女踩着葡萄在跳舞。其原因一是为了庆祝丰收,二是把这项艰苦的劳动与娱乐结合起来。 荣新江在其书《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一书中提到,太原发现的虞弘墓石椁的图像上,都有胡人酿酒的图像,从踩踏葡萄到把酿好的酒装在酒瓮之中,以及搬运酒坛的情景都有所反映。
所以该浮雕上所谓的“胡旋舞”的场景,应该是酿造葡萄酒。笔者认为在踏浆的过程需要不停地添加葡萄,所以在六角台上两侧的男子才会手持葡萄藤蔓。
个别学者在对这幅画面进行解释时,以三名男子体态丰腴,不适合跳胡旋舞为由,将此幅画面来作为否认跳舞的证据,但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无说服力。因为唐代的安禄山就以擅长跳胡旋舞著称,据《安禄山事迹》记载:“(安禄山)晚年益肥,腹垂过膝,自秤得三百五十斤。以肩膊左右抬挽其身,方能移步。玄宗每令作胡旋舞,其疾如风。”[7]在这段材料中,安禄山三百五十斤,笔者认为其中虽有夸大的成分,但足以说明其晚年体型肥胖。但安禄山跳起胡旋舞时,其疾如风。所以说,体态丰腴并不是不适合跳胡旋舞的有力证据。
综上来看,笔者认为这幅浮雕展示的是酿造葡萄酒的场景,而并非所谓的胡旋舞或是祆教仪式。
三、饮用葡萄酒的器具
在山东青州出土的粟特人墓葬中,石椁左侧第二幅的商谈图,主人坐在束腰足墩上,手举高足杯,商人双腿弯曲,手中也捧高足杯,似乎与主人对饮。日本信乐美秀博物馆所藏的北齐入华粟特人石椁浮雕有两幅反映饮酒器具的图像,马尔沙克的夫人瓦伦蒂娜·腊丝波波娃分别将其称之为美秀夫妇饮酒图、美秀葬礼饮宴图。[8]荣新江在整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对美秀博物馆所藏石椁浮雕进行了重新组合,这两幅图像被编号为E和G。[9]E是主人和夫人对坐在一粟特式的凉亭里饮酒,二人左手手握有波纹的玻璃酒杯,凉亭前有一名舞者,舞者下方有一胡瓶。G则描绘的是粟特老萨保与突厥人订立盟约,萨保的儿子成为新首领的继承仪式。在继承仪式完成后,老萨保与突厥人举起高足酒杯。
在公元五至七世纪,西亚、中亚以及欧洲拜占庭等地普遍使用高足杯,质地包括金、银、玻璃、陶等诸多种类。[10]而E号中的男女主人正是使用的玻璃制品,而这种玻璃制品很可能源自罗马玻璃。如黑海北岸五世纪的罗马遗址出土过许多波纹、网纹玻璃残片,俄国南部还出土过一件完整的波纹高足杯。笔者在经过仔细观察后,发现美秀博物馆所藏的E号浮雕中的玻璃制品,也为高足杯。因此北齐时期的粟特萨保所使用的玻璃制品可能为罗马玻璃。
康业墓的石椁浮雕中的第四、第五幅展示了粟特人饮酒的器具。第四幅左侧一人右手握细颈圆腹胡瓶,左手持酒杯,卑躬屈膝。 笔者认为这并不是自己饮酒,而是将美酒献给面前的主人。第五幅图为饮宴图,图中主人左手端一叵罗,旁边一胡人侍从手持细颈瓶。浮雕下半部分共四人,最左侧一人手持胡瓶,中间二人均手持叵罗或浅底盘,最左侧一人手持来通或酒囊。
叵罗,是一种类似于碗的敞口浅底饮酒器具。在汉文史书中,很早就有关于叵罗的介绍。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这样载道:“叵罗,杯盏之属。”[11]P5592《北齐书》记载:“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僚属,于坐失金叵罗。窦泰令饮酒者皆脱帽,于珽髻上得之,神武不能罪也。”[12]《旧唐书·高宗纪》中这样写道:“(上元二年)庚午,龟兹王白素稽献银颇罗。”[13]P3491《新唐书》中则是:“显庆三年,献金盎、金颇罗等,复请昏。”[14]P7457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叵罗无论是作为一种酒器还是贡品,在南北朝之后已经出现在当时的宴饮活动之中。
汉文史料中,胡瓶最早记载则是西晋时期。《太平御览》卷七五八引《前梁录》:“张轨时,西胡致金胡瓶,皆拂疎作,奇状,并人高,二枚。”[15]张轨于永宁元年(301年)出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开始了对河西走廊的统治。而当时的胡人之所以送金胡瓶给张轨,很可能是有所求。金胡瓶作为一种珍贵的物品,一般用于朝贡或赏赐,汉文史书中还有所体现。如《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三中:“(武德二年)癸卯,上谓侍臣曰:李大亮可谓忠直。手诏褒美,赐以胡瓶及荀悦汉纪。”[11]P5691《旧唐书·吐蕃列传》曰:“(金城公主)及是上引入内宴,与语,甚礼之,赐紫袍金带及鱼袋,并时服、缯彩、银盘、胡瓶,仍于别馆供拟甚厚。”[13]P4524《旧唐书·吐蕃列传》云:“如蒙圣恩,千年万岁,(吐蕃)外甥终不敢先违盟誓。谨奉金胡瓶一、金盘一、金碗一、马脑杯一、零羊衫段一,谨充微国之礼。”[13]P2345无论是李渊、李显还是吐蕃外甥,都把金胡瓶作为一种珍贵的礼物,这在上层社会中是一种普遍现象。而在民间,普通汉人关于胡瓶的使用却少之又少,仅仅出现在一些边塞地区。如王昌龄的《从军行七首·六》中:“胡瓶落膊紫薄汗,碎叶城西秋月团。”
在虞弘墓中,酒器也在多幅浮雕中出现,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第三幅浮雕的下半部分。一名男子坐在一个镶有花边的圆垫上,右手握一角型器酒杯,似乎正在开怀畅饮。这种角形器的酒杯就是来通。来通(Rhyton),源于西方,克里特岛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已出现,后来传至希腊并于下部加装兽首。希腊式来通最迟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传入中亚、西亚,陕西博物馆的唐兽首玛瑙杯就是典型的“来通”。来通这种酒器的特点就在于其小口处均用兽首作为装饰,并加上防止酒洒出的塞子,在饮用时一般拔出塞子,小口朝下,大口朝上。
综上来看,在入华粟特人的墓葬浮雕中,胡瓶和叵罗是使用率最高的酒器,作为倒酒器和饮酒器中最简单的工具自然受到了入华粟特人的喜爱。同时,这两种酒器的高频次出现,似乎也反映出入华粟特人喜爱饮酒这一事实。而对于高足杯和来通,因其大多饰有花纹和兽首,更多的被认为是一种地位的象征,从而多次出现在墓主人和妻子的手中。
本文从三个方面来阐释入华粟特人墓葬浮雕上的葡萄元素,得出如下结论。
1.葡萄无论是作为商品还是食用,都与粟特人的日常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墓葬浮雕上出现大量酒器的描绘,则说明粟特人的生活中经常以酒为伴,由此可以推断出葡萄在粟特人心中占有重要地位。
2.粟特本身是个商业民族,经商是他们最为擅长的本领,当这些粟特人背井离乡之后,免不了会出现对故乡的思念。
3.葡萄藤蔓所构造的葡萄园,被作为祆教仪式中的一个暂时性的场所而赋予了宗教含义,仪式中也需要大量的葡萄酒。基于以上两点,葡萄也与祆教产生了密不可分的关系,从而被入华粟特人视作一种精神象征。本文通过对入华粟特人墓葬浮雕葡萄元素的研究,为进一步了解我国南北朝时期入华粟特人生活状况提供了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