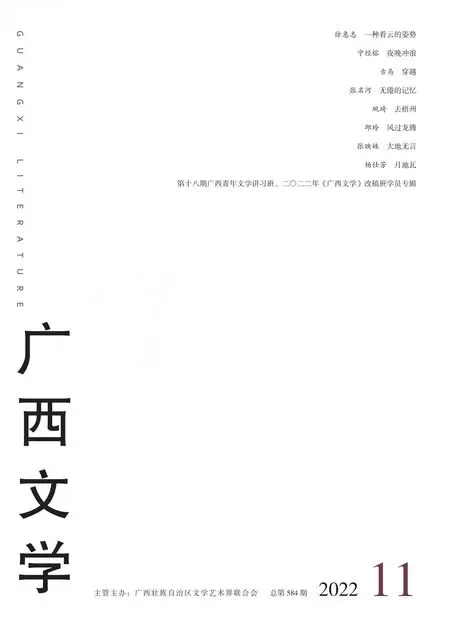守夜人
2022-01-01黄霞
黄 霞
一
家门口挂起白色的挑丧纸。
灵堂还没搭好,屋里安安静静,没有哭声。推开爸妈的房门,妹妹趴在母亲床上。妹妹比我先到家,家里每一个人的头上都缠了白布,眼前白茫茫的一片,再也无法止住她的眼泪。我不敢说话,脑子里大段大段的空白。
棺材早已封上红纸,红得那么突兀。早在几年前,家里就备好了两口棺材,爷爷一口,奶奶一口,架在房梁下,就在落日的方向,高高地注视着堂屋里的一切,似乎在提醒每一个人,日子都是越过越短的,像浅浅的残阳,一点点陷入平地,拉不住,扯不回。也如同奶奶手上的那只原本明媚如骄阳的铜镯,在岁月中被幽深暗绿点染,最终横亘在这一方小小的棺材里,只在方寸之间,被黑暗慢慢吞噬。奶奶把她的日子过完了,先于家里的每一个人。
棺材左边铺着破旧的席子,我盘腿坐在上面,背靠着墙壁,面对着奶奶。这是我第一次面对亲人的离去,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靠近棺材。薄薄的棺材板就这样隔开了两个世界。奶奶应该不孤单吧,我们都守在她身边。
幽暗的夜色中,煤油灯闪烁着微弱的光,玻璃灯罩在摇摇晃晃的火焰舔舐下,显示出疲惫。黄纸、元宝一张张一个个被丢到火盆里。摇曳的火光把姑姑的脸映得明明暗暗,我看到她脸上斑驳的泪痕。“姑姑,你过去歇歇吧,我来烧会儿。”在那张黄纸快要燃尽的时候,我抓起一个元宝丢入火盆,火舌吞噬元宝,纸灰在盆口飞旋,又跌落盆底。姑姑低下头,没有应答,她长久跪在火盆边,火焰舔得她脸颊滚烫发红。钹声鼓声层层叠叠,她两眼凄茫,又止不住放声哭了。
一个最亲的生命在她面前逝去,而另一个最亲的生命正在她腹中孕育。
二
姑姑是奶奶四个孩子中年龄最小、个子最高、见过世面最多的一个:高中毕业,在衣架厂加工过衣架,也代表厂里去外地参加过展销会,后来又在烧烤摊烤过烧烤,在家门口的食品加工厂也加工过酸嘢……可这样的见世面,其实在村里人看来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在她们看来,玩得多,没有稳定的工作,又迟迟不出嫁,就是不行。用姑姑后来的话说,当年她没少被村里的人过问。村里像姑姑这个年纪还没出嫁的女子,没有几个。被问多了,自然就真的放在心上,也觉得是个问题了。虽然这是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但还是会放在心上。久而久之,这些话,就像芒刺一样,隐隐刺痛。
那日,阳光斜斜地落山了,放学回家路上,我跟着几个高年级的姐姐排着队把脚浸在水沟里踩水玩,说笑间,有个姐姐突然问我:“哎,你姑姑怎么那么久还没出嫁啊?”我只随着潺潺的流水回驳了一句:“关你什么事?”她们就没再说什么了。可这话,到底烙在我心上了,在情绪控制不住的时候便会脱口而出。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又是个阴雨绵绵的午后,这样斩不断、划不掉的蛛丝网般绵密黏稠的雨已经连续下了好几天了,桌子椅子腿脚都长了毛,把我也沤得毛毛躁躁的。姑姑和平常一样,督促我做作业。可那一天炒鸭腿的香味使我无法专心,匆忙盛来了鸭腿,正要啃,姑姑偏又说到了我的作业,叽叽喳喳。我一气之下把鸭腿往她脚边砸,蹭掉了桌脚的一大块霉菌,香喷喷黄亮亮的炒鸭腿顿时凄哀地躺在潮湿的地板砖上。
“这脾气,长大了还得了。”姑姑说,“前两天刚说邻家那个嫂子,一气之下把一车西瓜全砸到路上了,没想到我们自家也有这么一个暴脾气的,来日还不知道砸什么呢。”
我犹豫片刻,那句话终于脱口而出:“要嫁还不早点嫁出去!”并且是直呼姑姑名字的。
“啪!”热辣辣一个巴掌瞬间落到我脸上,“是谁教你说这话的?你这是要把你姑姑赶出去的意思?这个家,还是我的,我都没赶她,你就少多嘴。”说着,奶奶拉着姑姑,母女俩哭了起来,我也哇哇地哭了起来。那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样的话,是多么伤人。我的的确确伤了家里两个女人的心了。
“要不,你就去看看吧。”终于有一天,奶奶开口了。
“但是,那么远,我放心不下你啊。”姑姑说。也是在一个月前,姑姑跟奶奶提起有人给她介绍对象这回事,只说是靠海的城市,大地方,有吃不完的海鲜,男人也长得英俊。奶奶听了姑姑的话,沉默了好久。
“年纪也不小了,想去看看,就去吧,要是不满意再回来。”奶奶说。“老是待在家里也不是办法,你不知道村里人说话多难听。”
终于在我十岁生日那一天,姑姑怀着忐忑的希望,奔向让她后来万般无奈的日子。广西到浙江,地图上好多缠绕的线条,咫尺即千里。从此,奶奶每天都盼《新闻联播》早点结束,早点播报《天气预报》,她不识字,但会竖着耳朵听浙江,听台州。奶奶总让我帮她拨电话,电话那一头“咔尼呀咔尼呀”的声音让我慌忙挂掉。后来摸清门路,开口第一声一定要交代“找小黄”,那边“小黄”的呼唤也远远地传开了,迫切的脚步声向我们逼近。“喂,喂”,奶奶把脸贴到听筒上,双手紧紧握着听筒,红色的听筒,干瘦黄皱的双手,矮小的背影就站满了整个黄昏。
那个我应该称之为“姑丈”的男人,识字不多,跟亲戚出去见过点世面,会说普通话,人并不精明,会点剪头发的手艺,自己开个发廊,生意不好。和姑姑一样到了该成家的年纪了,还没讨到老婆。那个春天,姑姑在媒人的带领下,坐了一天一夜的大巴,从广西到浙江,一切都是陌生的。那时的姑姑可真年轻,高挑的身材,时尚的穿搭,那家人一眼就相中了她。
我也终于没等来让我饱餐一顿的喜宴。没有迎亲的队伍,也没有送亲的队伍,一句“太远”,就完全把双方必要的礼节都省了。这一次,她又牵着奶奶的心,一个人启程。
奶奶总算把姑姑嫁出去了,留给她的是秋夜里依旧热闹的蛙声蝉鸣。只有奶奶知道,这些声音是在夜里的哪时哪刻消散的。奶奶眼睛不好,枕头里塞满了决明子,据说能使人眼目清凉。她欠起头松了松头发,略一转侧,决明子沙沙作响。翻了个身,吱吱嘎嘎牵动了全身的骨节。又把手臂枕在头下,腕上的手镯,恍恍惚惚,映着月色泛出清冷暗淡的光。她听到姑姑在叫唤她,若有似无。姑姑脸上堆满笑容,姑姑戴着墨镜,双手斜搭在姑丈的肩上,姑丈比姑姑高出一个头,面色红润,两手垂直贴在裤腿中缝上……他们在家门前迎着阳光笑,他们映在昏黄的电灯泡下笑,他们笑得那么开心。奶奶枯干瘦削的手颤巍巍地举着不久前姑姑寄回的照片,看了一遍又一遍,所有的思念都落在了指尖。
三
午后的阳光浅浅地落在门前,映着奶奶瘦小的躯干。她接过我为她拔下的白头发,在指头上绕了几圈之后丢到手边的垃圾桶里。对着路口方向走来的人喊:“今天回来挺早啊,上来坐坐啊。”她总是这么热情。我们家在路边,路面到大门口之间垒起高高的台子,房子就好像从石台上长出来的。“快,拿椅子。”她看着那人正爬上台阶,就吩咐我进家里拿椅子。两张矮矮的椅子,托起两具瘦弱单薄的骨架,顺着西斜的日光,长长地勾出她们共同的心事。她有太多的话想要倾诉,可到最后,还是扯到了生死别离的纠葛。一提到死,她就想到姑姑,一提到姑姑,她就更不甘心这副躯体上的种种隐痛。尽管每次的叙旧,都让她陷入这样的困境,但她依然执着架起小椅子,靠在那扇陈年的绿漆木门边上,右手搭在左手腕上,转动着手腕上那只黄铜手镯。两眼木木地看着门前的人来人往,望着路口的方向。路口连接着二级公路。她就这么一天天地盼着,守着。
奶奶说她那条有骨质增生的腿越来越不听使唤了,小腿上的止痛贴撕下又贴上。手腕上的铜手镯越来越宽松,颜色越来越暗淡。她坚信身体健康的人,身体里阳气盛,铜镯子金灿灿地发亮;身体不好的人,身体里阴气盛,铜镯子就黯淡无光。
她再一次卧床,是在一次阴雨天,一瘸一拐拖着小锄头回来之后。我要扶她,她不让,叫我走开。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敷药、吃药、打针、吃药,反反复复。致命的藤蔓终于从腿脚渐渐爬到了腰上,唤醒了几年前的那场大病,最终蔓延到全身。
病中的奶奶变得越来越小气,越来越多疑。母亲叫我扫地,奶奶觉得我母亲在嫌弃她,是嫌她打针产生的废弃棉签把家里弄脏。她自己清扫棉签,装到垃圾袋里拿到门前的垃圾堆丢掉。之后的几天不肯上桌吃饭,说怕脏了我们的饭桌。等我们煮好饭菜之后,她才颤悠悠地从房间里钻出来,提着她翻出来的小锅,一根手指粗的长铁棍穿过那口小锅的两只耳朵,架在木糠灶上。水煮沸了,倒入半碗大米,不停地用长勺在锅里搅啊搅,升腾的雾气隐隐约约把她隔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她有意让我们看到她,以显示她的寒酸,把小锅里的米粥舀出半碗,小勺子打了小半角猪油,撒点盐,端着碗,提着那口锅回了房间。房间因为光线暗淡而显得幽深。我们的目光在灯下相遇,她白了我一眼,绷着脸,半句话不说,闷着头,默默咽下那粥。
“别碰,脏。等会儿你妈又该看不下去了。”我正要接过她的碗,这句话就把我拦住了。
“我妈只是叫我扫地而已,也没有说是嫌弃你啊。”我说。“我妈是讲究些,就算去外婆家,看到家里脏了,也会直说,也会跟表弟表妹说,家里脏了要及时打扫的啊,外婆也在场的。”
她脸一沉,“要是你姑这样说我,我也不会生气的。”我无言以对。
是啊,就是这么亲疏有别,每一位母亲都能最大限度地包容自己的孩子。可她是否也想过,姑姑远在他乡,是否也这样受到她婆婆的不待见?或许她也在怕吧。每次我母亲委屈地哭诉,“你们就是欺负我兄弟姐妹不在身边!”我想,奶奶也不可能不受触动。
幽深、阴郁的空气一天天在屋内盘绕。奶奶在房间里反反复复叠着那几件衣服的样子一直压在我心里。她总是趁我在房间的时候,从衣柜里拿出一个裹得严严实实的塑料袋,把里面的衣服取出来,展开,抖一抖,跟我说,等她咽气了,记得给她穿上这几套衣服。我不知道她相不相信前世,也不知道她会不会期盼来生,她只盼着这一世早点过完,这一世太苦。“白色的这件,记得给我穿在最里面,蓝色的这件穿中间,黑色的这一件,穿最外面。”她伸出左手,下巴压着衣领,右手压在左肩上,左手包住掌心朝里勾了勾左边的衣袖,袖子刚好盖住她腕上的手镯;又伸出右手,重复比画着那样的动作。三件衣服,里里外外,她欢喜地把一件件举到胸前比画了个遍,她享受着这样的试衣时光。或许她真的希望那一天的到来,当她真正穿上这几件衣服的那一天,姑姑一定会回来,所有的儿女都会回来守着她的。
几件衣服都是她喜欢的款式。每逢赶集的日子,奶奶总是换上这样的衣服去上街。左衽斜襟土布上衣,蓝色的居多,厚重的布料没有什么点缀,唯一讲究的就是领口的盘扣。“记住了吗?这几件衣服,我就收在这个柜子里,你可记住了!”她的声音顺着落日的方向,穿透屋檐,绕过架在房梁上的那两口棺材,落到我床前的这个衣柜里。
这个暗橘色的衣柜立在门后很多年了。四只矮矮的脚撑起了“三合一”的柜子,最下层是衣柜,衣柜上荡开一个平面可以当书桌用,再往上就是书架。最下层的衣柜很矮,每次要打开柜门必得蹲下还需稍稍低头。对称的柜门中间嵌着暗锁,锁眼周边是同奶奶一般沧桑的沟壑。姑姑离家后不久,衣柜的钥匙拧不开了,奶奶着急,闷声跑到厨房拿来钝钝的斧子沿着锁眼边凿。父亲闻声赶来,才帮她挖出了锁头,这才算把柜子打开。从此以后,再不敢把这两扇门关紧了。
四
姑姑在大家都盼着她的时候回来了,一起回来的还有素未谋面的姑丈。奶奶怎么也没想到,她是在病床上以脆弱、无助、破败的身躯迎回了自己的女儿女婿。
医生已经停止用药。一米见方的病床上,奶奶像两根缠绕在一起的柴火,右边小腿压在左腿上,松松垮垮,右脚指抵在左脚背上不停地抓挠。右前臂搭在额头上,肘关节顺着手腕刚好遮住了眼睛,手掌自然弯曲落在床单上。姑姑两肘支在床沿上,两根食指并拢把眉头往上挤,眼睛直直地盯着床单。奶奶左手腕上暗淡的铜镯坚硬地随着奶奶的手在床单上摩挲,床单被砸出深深浅浅的印痕。
父亲从主治医生那里回来后一语不发。他的目光在床沿上与奶奶相遇,又迅速收回。“今天怎么还不打针?”奶奶望着立在床边的那根光秃秃的杆子突然开口。“医生说这两天先停一停,那药连续打不得的。”其实大家都明白,不管换什么药,都打不进了。她的血管已经萎缩。
她眼睛里现出格外凄凉的神情,紧紧地抓着姑姑的手,终于挤出了几句话——“是不是没钱啊?你们再想想办法,就是借钱,像几年前那样,跟亲戚们借一借,我们先借钱,等以后好了,再慢慢还,行吗?”那一刻,奶奶像被父母遗弃的孩子那样无助。这个曾在家门口跟她孙女说自己命不久矣,早就给自己准备好了寿衣的人,在医生真的下了判决书的时候,也会这样苦苦地哀求。姑姑眼里早已噙满了泪水,也抓住奶奶的手,两个人都无法平静。
无论如何,真的要出院了,生的希望再也无法在她的血脉里激起波澜。所有的人望着医院的白床单白枕头白棉被,满眼疲惫。
出院回家那天,山头的乌鸦啊啊地叫着,一声声牵扯着每个人的心。后院四棵鸡屎果树还像往年一样,边开花边结果。奶奶的日子不多了,或许是一天,或许是两天、一个周、一个月,谁也说不定。在最后的日子里,姑姑和奶奶须臾不离。守着奶奶,守一天少一天。原来的瘦肉粥换成了米汤,像从前喂我那样,姑姑沿着碗沿,半圈半圈刮起一勺一勺的米汤,放在自己嘴边轻轻地吹,抿一小口,不再烫嘴了才送到奶奶嘴边。奶奶下巴贴着胸口,吃力地伸着脖子张开嘴,让姑姑把米汤送到嘴里,再紧紧地用她光秃秃的上齿龈把勺子里的米汤刮下,含在嘴里,喉咙微微颤抖,温润的米汤顺着无力的唇舌缓缓渗进了她的身体。我突然想到鸟窝里那些张大嘴巴嗷嗷待哺的雏鸟,充满期待,拼尽全力,要争夺母鸟口中那口食物,是那么无助、那么弱小,一场狂风骤雨,就足以把它们掀翻,足以断送它们的生命。病床上的奶奶,就是这样脆弱。终于,她不再张嘴,姑姑给她擦了擦嘴角,又躺下了。
奶奶看着不可知的方向,又把目光转回姑姑身上,时间在姑姑身上凝固,柔软,凄哀,直到被自己手腕上的黄铜手镯硌醒。奶奶动了动手腕。“帮我把这镯子取下吧,硌得慌。”然后,就慢慢睡去。话已经很少了,她正在慢慢接受自己即将死去的事实。
五
家里变得热闹起来。奶奶意识还清醒的时候,每个来探病的人都会在床前坐一坐,三五成群;后来,奶奶意识越来越模糊了,来探望的人就只是到床边叫上一声,打个招呼,奶奶微微睁开眼睛看了那人一眼,又缓缓闭上,舒出一口长长的气。大家因为奶奶重病而聚在一起,他们来探望奶奶,守在我家门外,陪着家属一起守着。万一有事,他们可以第一时间帮上忙。等待总是那么漫长,他们也漫无边际地聊着。乌鸦早就练就了一身敏锐的嗅觉,乌漆漆一团潜伏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啊啊啊地叫着。门前的人越聚越多,谈话的声音,一阵高过一阵,起起伏伏,仿佛冲淡了盘旋在我家周边的阴霾。那是人气,是生的活力。夜深了,屋里并没有什么异常,才各自散了。所有的人,都在等着奶奶慢慢死去。
奶奶是在四月初十上午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噼里啪啦,短短的一阵鞭炮声在家门口响起,夜间散掉的那些人也就明白了,放下手头的工作,又三五成群聚到我家来。
六
这是奶奶在家的最后一夜。
麽公披着炫彩的长衫在灵前踏着诡异的舞步,嘴里吐出悲音袅袅、哀韵绵绵的唱腔。我闭上眼睛,试图把绵密的低语一丝丝捋开,却又在“咚咚锵……咚咚锵……”的碰撞声中湮没。麽公嘴里念着,手上的木槌“嘟哒,嘟哒,嘟哒”不停敲打桌上的木鱼,我试着去数木鱼敲了多少下,“嘟哒嘟哒”的声音时缓时急,捉也捉不住。
夜深了,麽公点着了一大捧土香分给我们。我们人手一支,在麽公的带领下围着棺材,转了一圈又一圈。灰黑的床单把棺材和大门隔开,就成了帷幔。帷幔上贴着一个用白纸剪成的大大的“奠”字,提醒我奶奶去世已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转到“奠”字前,分批,站着拜,跪着拜,磕头,叩首。香火浓浊的烟气弥漫,我使劲睁开迷离的双眼,仿佛香案旁两只长喙、红首白羽的呆滞仙鹤真的能驮着奶奶前往遥远的天堂。
大家没有过分地悲伤,只有长久地静默。亲戚们围坐在桌边叠元宝。妹妹会叠三种元宝,每一样都能叠得很漂亮。亲戚们都夸她,她一听到大人们夸她,叠得更卖力了,好像已经忘记了所有的悲伤,又或许,把对奶奶的全部思念,都寄托在手中的这一个个元宝里,让奶奶带着这些元宝,了了这一世不能达成的心愿。
天还未全亮,家门口已经聚满了人。香案上香火还盘旋着几丝轻烟,烛火摇摇晃晃。旗伞倚在大门口,伞摆上密密匝匝的纸条在晨风的吹动下刷刷作响。告别的时候到了,盛放祭品的桌子被撤下,帷幔也被撤下,麽公在棺材上绑了一只鸡,活的,一开始还扑扇着翅膀,后来就卧在棺材上不动了。四五个壮汉拿着麻绳在棺材上捆扎缠绕,手臂粗的木头穿过麻绳,棺材就被抬起了。
我又听到了姑姑的哭声,虚弱,震颤。
送行的人依次接过麽公递来的香火,星星点点排到奶奶身后。麽公的钹又响起了,父亲在队伍前撑着旗伞,叔叔把奶奶的照片举在胸前。照片是很多年前奶奶在她娘家门前拍的,她坐在门前,穿着青灰色的左衽斜襟布衣,背景是涂着黄漆的大门,明晃晃,分外夺目,奶奶也笑得格外灿烂。奶奶去世的那天早上,姑姑在一大沓照片中选出了这张,拿到照相馆放大几倍。纷飞的黄纸伴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一直飞旋到与墓地隔河对望的津口。眼前还是灰蒙蒙的,彻耳的钹声,神秘的咒语,离我越来越远。
墓地在河对岸,没有桥,只有浅浅的石搭,抬棺者艰难地蹚水渡河。茫茫的河水,不息地流动,我似乎产生了一种幻觉,我盯着越久,河水就流得越快。红彤彤的棺材直直地往河对岸挪动,河水被抽断,但很快又续上,奶奶却离我们越来越远。我才意识到,这是真正的离别。
望着渐行渐远的棺材,我跟着姑姑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