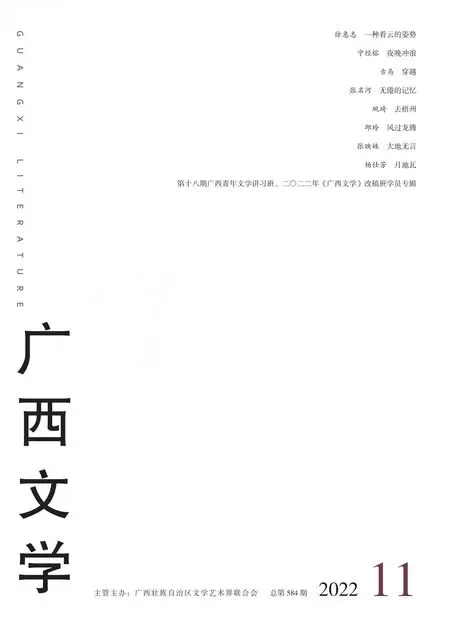留 宿
2022-01-01彭世民
彭世民
唦、唦、唦——
母亲生着气,手里的锅铲在锅里使劲翻炒青菜。晨曦从窗外照进厨房,落在母亲不高兴的脸上。我站在厨房门口,望着坐在灶弯里添柴烧火的父亲。灶膛里的柴火哔哔剥剥响,火光照着父亲的脸。父亲脸色凝重。
“叫你别把不三不四的人往家里领,这下好了,两双解放鞋被人家顺走啦。今天你就赤脚去捡茶籽吧。”母亲噘着嘴,在埋怨父亲。
我立马明白了母亲生气的原委:昨晚借宿的两个乞丐偷走了我家两双解放鞋。两个借宿的乞丐贼眉鼠眼,进屋以后东张西望,一举一动,令人生疑。我走到窗台一看,那两双半新不旧的解放鞋果然不见了;再跑进房间,发现昨晚借宿的两个乞丐也人去房空。我重新回到厨房。
父亲将脸埋在手掌里,让母亲继续数落着,一言不发。
我知道,父亲一定有什么苦衷。吃完早餐,父亲默默走出厨房。他说:“我上山捡茶籽去啦。”说完,他悻悻地望母亲一眼。
在汨罗江沿岸的湘北一带,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多数农村家庭生活条件不好,交通也很落后。一些挑担的小货郎、耍把戏的、算命的、要饭的,他们走村串户,基本上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借宿。小的时候,我们住在大屋堂里,几十户连在一起,很是热闹。也是那些小货郎、耍把戏的、算命的、要饭的向往的地方。只要拨浪鼓一响,我们就从屋里弹出来,看那货郎担里又带来了什么新鲜东西。箩筐里面有针和线、顶针、针锥,更多的是女人用品,耳环、项链、手镯,漂亮的花卡子、黑卡子,扎头的,还有孩子们喜欢的花生、糖果等各种小吃,琳琅满目,是个名副其实的百货担。我们就拿出平时积攒下来的牙膏瓶子,捡来的破套靴跟他换辣椒糖、红老姜吃。大人们用稻谷、米或者红薯丝、鸡蛋之类的物品与他们交换,这大概是最原始的贸易方式——物物交换吧。
有时候,“嘭嘭嘭——”锣声一响,我们就知道耍把戏的来了,总喜欢在他们屁股后面跑,它带给我们快乐和憧憬,是我们平淡生活的调味剂。
耍把戏的嗓门又大又亮,吆喝起来一串一串的:“各位乡亲父老,大爷大叔,大嫂婶子们,初到贵宝地,讨口饭吃。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农村人爱看热闹,片刻工夫就将耍把戏的围在中间。
只见那人拿出一张纸,在众人面前,一边转着圈走,一边用食指和拇指将那张纸弹得啪啪响,手一抖,那纸立刻变成白花花的票子。我十分希望学到他的本事,有了钱,再不用为换辣椒糖找不到牙膏瓶子苦恼了。
天黑了,父亲将那耍把戏的领到家住,我想你吃了我家的饭,总应该教我将纸变钱吧。吃完饭,我缠着他,他见我这样执拗,掏出一块红布,盖在一个空箱里,手伸向半空中,招了招,朝红布处一指就能掏出鸽子来。他拿出一个玻璃杯,盖上一块红布,变了一杯酒给父亲喝。
“不要酒,我要学纸变钱。”我嚷着,吵着要学那本事,耍把戏的正色说,“不行,小孩子不能学,你长大以后,我教你。”我从那以后天天盼着耍把戏的来,希望自己快快长大。
当然,伴随着我成长的外地人——还有耍猴子的:他们牵来的猴子穿衣戴帽,左摇右晃地出场,翻筋斗、爬杆子、骑车子、做鬼脸,高兴的时候给围观者敬礼、握手;还有放刀人,他们吆喝着:“放刀啰、放刀啰”,并且声称:“今年放的刀子,明年再来收钱。”可是有的几年也不见来收钱;还是补锅的、腌鸡的……这些人都来来回回在村里跑,走到哪里,天暗了,就借宿在哪里。我家三间房子,父母一间,姐住一间,我和哥哥睡一间,一张床。家里来了客人,我和哥哥就得到木楼上临时开铺。木楼很矮,伸手能摸到瓦片,而且没有窗户,夏天像个蒸笼,热死人;冬天像一把谷筛,寒风从瓦缝、墙隙里吹进来,冷得人发抖。
那个时候,家里三天两头有人借宿,这些客人不是我们家的亲戚朋友,都是跑江湖的人。母亲要种菜,下地干活,一家人的缝补浆洗,养家畜家禽,操劳油盐柴米,已经够忙的,父亲还要将那些人领回家。尽管母亲心里不高兴,但来者为客,还是会尽力招待。这些人嘴里总是说: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吃啥我们就吃啥。大方一点的小货郎,有时候也会给母亲拿些针线,给我们抓几颗糖果;耍把戏的,偶尔也会给我们讲一下魔术技巧和障眼法,有时候也会付可怜的一点生活费。
我最不喜欢算命先生,他们依靠嘴巴子忽悠人骗饭吃。眼睛看不到,就靠着一根拐棍走路,有时候还要人牵着。他们根据不同的人排出不同的生辰八字。他们多是讲一些吉利话。在农村,大多数人喜欢听那些算命先生廉价的奉承话,尤其是一些家境困难的人,说过两年,生活会有好转或会逢什么喜事,他们听了都是乐呵呵的。
有一天晚上,父亲留着两个算命先生在家里住。年长的叫李先生,雪白的头发,灰暗的面孔,深陷的眼眶,加上满脸皱褶,看起来年龄跟我爷爷差不多。另一人十四五岁,眼瞎,还是秃头,李先生叫他刚子,刚子个头和我差不了多少。
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应该是第三次来我家借宿。他们来了,我和哥就得爬上小木楼去睡。我心里很不乐意,但迫于父亲的威严,我又不得不爬木楼去睡。
那晚上我突然闹肚子,夜里要上茅房,家里住的地方到茅房要穿过三百多米的巷子,手电没有电了,只好一手端着煤油灯,一手扶着楼梯。闹肚子,身子软,我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头上、手上都蹭破了皮,还好摔得不重。
第二天清晨,客人们还没起床,母亲在灶房里给他们做早餐,父亲在灶房里帮忙烧火,母亲又开始和父亲吵嘴。
母亲说:就算我求你了,以后别把这帮人招在家里了,你看孩子都从楼上摔下来,要摔个三长两短,你就后悔去吧……
父亲半天没有回应母亲,他见母亲气消了不少后才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时难,你也不同意借宿,他也不同意借宿,这大冬天的,外面还下着雨,你叫他们在哪里过夜……
母亲本来是背着他们与父亲争吵的,正好碰上李先生摸着去灶房倒茶时听到了。吃完早饭,李先生带着刚子给父母道谢,说是要去我们相邻的大屋里去送童关。
那时天还下着雨,冬天的风从脖子里灌入,冷得人直打哆嗦。怎么,去送童关也不急着这一时半会的,要去等雨停了再走。父亲在不停地挽留着。
不了,我们去送了童关,还得回家一趟,有个酒要喝。李先生说。父亲只好派哥哥打着伞去送他们一下。哥哥去了一会儿就回来了。母亲问他怎么一回事。哥说:李先生说他记错送童关的时间了,那家孩子出生的日期是下个月的今天,李先生说,正好他们要回家去一趟。
母亲突然想到是不是她跟父亲吵嘴的事被听到了。母亲对父亲说,还愣着干吗,快去把人追回来呀!雨这么大,小河堤上全是烂泥,别摔出个什么事来。
父亲追了去,见到小刚子摔得满身是泥。母亲心疼,赶紧烧了一大锅热水给刚子洗澡。
经过那件事后,借宿再来我家,母亲不让我睡楼上去了,她说挤就挤一点,挤也是有次数的。借宿的来了,我与他们挤一个床铺,有时两人,有时三人。睡在床上,有的打呼噜,有的磨牙。最让人受不了的是有些借宿的可能因为长时间不洗澡,身上散发出一股股臭味。但相比我住在楼上,晚上去小便都要爬梯子下楼,我情愿闻这股臭味。
在我们大屋堂里,谁家生了孩子,算命先生就会准时走到。在我们农村,有算命先生送童关的说法,小孩子一出生他们就来送童关,算出小孩十二岁前的关煞,什么几岁到几岁,有深水关或汤火关之类的,算出有什么关煞,孩子的父母都会请算命先生把关煞给寄掉。
算命先生来了大屋堂,都喜欢住在我家,说我父亲是好人,我母亲随和。背地里却有人说我父亲耳根子软,人家说他几句好话,他就不知道怎么拒绝人家了。其实父亲并非是耳根子软,在我们家里,他是一言九鼎,绝对权威的。他只是心善,同情弱者,怕这些人冻着、饿着。
母亲也是尖刀嘴豆腐心,小商贩、耍把戏的、要饭的,这些人好对付,有饭给他们吃,有张床给他们睡,他们也不挑剔,总是说尽好话。算命先生就不一样了,他们眼睛看不到,母亲要把饭菜端到他们手上,偶尔还背着我们在他们饭碗里埋上一个鸡蛋或一块腊肉。晚上还得把洗脚水或洗澡水给他们打好,试好水温,怕他们冻着或烫着。
尤其是到了大冬天,天寒,多雨。有一天,算命的许先生来了,正好碰到下雪,出不了门,一住就是几天。一天到晚坐在火塘屋里喝热茶、扯淡,烧水铜壶挂在火塘上面的铁钩上,里面沸腾的水,一直从铜壶盖周围和铜壶嘴冒着热气,他们喝完一杯水,又加一杯。到了夜里,我把桌子搬到火塘边上,就着煤油灯,一边做作业,一边听大人们扯淡。
父亲问许先生,我这三个孩子,大的初中毕业,死活不去读书了,没办法,我打算送他去学木匠去。女儿吧,读书成绩也不好,估计也没有什么书分。至于我那小家伙(指的是我),人是聪明,就是过于调皮捣蛋了,在学校三天两头闹事,不让人省心。你走的地方多,见识广,帮我算算,这几个孩子今后的前程看。
许先生掐指算了起来,他说我哥学木匠,将来会是个好木匠。姐姐也没什么书分,可以送去学个裁缝。至于说到我,他说我像是一块豆腐,需要压,压实了,这孩子能出门,将来会有个一官半职,压不好,就是块无法无天的料……
听了许先生的话,我心里把他祖宗十八辈都骂了个遍。当着父亲的面,尽管我恨他恨得牙痒痒的,但我也不敢说半句反驳的话。
晚上,和许先生睡在一张床,我把被子裹我一个人的身上。许先生上床摸不到被子,他也不生气,反而跟我聊起天来。
他说:怎么,嫌我这个瞎子在你父亲面前多嘴了?
就是,你不说我哥,不说我姐,就挑我的事,你安的是什么心?我不愿读书,关你卵事,你管得了吗?对他,我压根没有好的语气。
他说:小子,我小的时候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主,我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从小被父母惯着、哥姐照顾着,在学校读书,我是个打架王,我打不过人家就喊哥哥姐姐帮忙。那些喜欢打架闹事的同学估计是被我打怕了,平时都躲着我。有一次,我落单了,几个平时被我欺负过的同学把我堵住了,有一个被我打倒的同学书包里装了石灰粉,他当时抓了一把石灰撒在我的眼里……
我的眼睛就这样被毁了,十四岁就开始学算命,这就是我的命。你现在年纪小,等到你长大了,再后悔就迟了哦。
听到许先生的话后,我由恨变为同情,同时觉得他说的也是完全为了我好,我对他也没那么讨厌了,那晚上我还主动给他捂脚。
后来,算命的只要到大堂屋来了,见到他们,我都会主动去牵扶他们,或为他们带路。晚上住在家里,我也会帮他们盛饭或打洗脚水。
当然,借宿的人也是五花八门,形形色色。
母亲背地里跟父亲吵,但吵归吵,只要父亲把他们领到家里来了,母亲就会把他们当客人对待……
父亲对我说:“你母亲其实是尖刀嘴豆腐心。”
我说:“我知道。”
父亲又告诉我,更早的那个早晨,母亲认为被乞丐偷走的两双解放鞋,是他拿给他们的。
其实,这事母亲后来也猜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