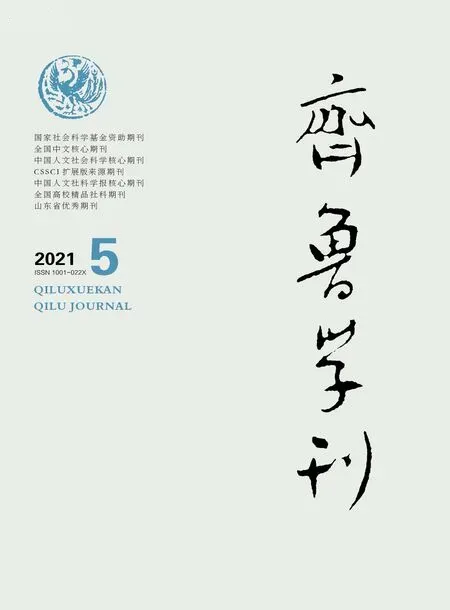关于《乐经》文献问题
2021-12-31王齐洲
王齐洲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暨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9)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经典无疑是其核心内容。然而,由孔子及其后学所确立的儒家“六经”,在汉以后实际上只有“五经”发挥作用,作为“六经”之一的《乐经》几乎没有参与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建设中来,仅有一段出人意外的小插曲在西汉末年上演过,不久就烟消云散,实在让人诧异。汉武帝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独《乐经》未立,故《乐经》传承不明。王莽虽在汉平帝时奏立《乐经》博士,五年后代汉自立,但新朝十多年便灭亡,辅佐新朝的国师刘歆自杀,新朝经学也随之被废弃,博士被遣散。《乐经》和《周礼》等古文经典因其是新朝经学而被后人指为伪造,两千年来,聚讼不断。宋代疑古思潮勃兴,不少经典受到质疑,《乐经》之有无遂成为话题,一直延续到现代。《乐经》与整个儒家经典相联系,牵涉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需要也应该进行科学探讨并做出合理解释,从中或可开辟出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天地。有关《乐经》的问题很多,而最重要最基础的问题是《乐经》的文献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则无从谈起。因此,本文就《乐经》文献问题提出意见,以期引起大家的重视,促进有关研究的深入。
一、“六经”之一的《乐经》不是曲调曲谱
先秦有儒家“六经”之称,《乐经》即其中之一。最早提到儒家“六经”的是庄子。《庄子·天运》载:“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1](P95)《庄子》之书多寓言,说老子与孔子共论“六经”,显然与史实不合,故后人多不信。然而,新近出土战国楚竹书已提到儒家“六经”,如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六德》称:“故夫夫,妇妇,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六者各行其职,而谗谄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1)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第四组简文《六位》(原题《六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31页。李校本“诗”“书”“礼”“乐”“易”“春秋”均未加书名号。《语丛一》则对“六经”的价值做了概括:“《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书》……)者也;《诗》,所以会古今之诗也者;《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2)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第五组简文《物由望生》,第160页。李校本“礼”“乐”“书”“诗”“易”“春秋”均未加书名号,括号内为断简。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原题《语丛一》,原文为:“《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今之恃也者。《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者也。”其“易”“诗”“春秋”均有书名号,“礼”“乐”未加书名号。郭店楚简葬于战国中期偏后,与庄子同时,这说明《庄子》中的“六经”之说有现实依据,只是借老子、孔子发表议论而已,并不全是妄说。因为有出土的战国楚竹书为证,今人大多不敢再否定先秦有儒家“六经”这一历史事实了。
不过,对于“六经”的文献问题,人们的看法并不相同。《诗》《书》《礼》《易》《春秋》都有文字文本存世,且汉武帝时就立有与它们相关的经学博士,尽管在具体文献的认知上(如《礼经》)学界仍存在不同意见,但大多认可《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有独立的文字典籍。而《乐经》在武帝时未立学官,故传承线索不明,汉平帝元始四年(4年)王莽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学者筑舎万区……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2](P741)。但后人多以为王莽托古改制,造作伪籍,且此《乐经》在新朝灭亡后湮没,故相信者不多。
正因为《乐经》文献疑莫能明,所以不少学者以为《乐经》并非独立经典,没有文字文本。持这一意见的学者并非个例,历代都有。例如,唐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时说:“言其道精微,节在音律,不可具于书。”[2](P528)宋王应麟说:“乐者人心之和,不以书传也。”[3](《置五经博士》)元吴澄说:“《礼经》之仅存者,犹有今《仪礼》十七篇。《乐经》则亡矣。其书疑多是声音乐舞之节,少有辞句可诵读记识,故秦火之后无传,诸儒不过能言乐之义而已。”[4](卷三十六)明周琦说:“《乐经》既亡,独《乐记》不亡,可见《乐经》是记声音乐舞之节,非文辞可读之书,秦火后汉儒不收矣。”[5](卷十)清张廷玉说:“《乐记》者,记乐之义也。古有《乐经》,疑多是声音乐舞之节,少有辞句可读诵记识,是以秦火之后无传焉。”[6](卷四十一)所有这些意见,都是否认《乐经》是独立经典,不承认其有文字文本。清四库馆臣甚至说:“沈约称《乐经》亡于秦。考诸古籍,惟《礼记·经解》有乐教之文。伏生《尚书大传》引‘辟雝舟张’四语,亦谓之《乐》,然他书均不云有《乐经》。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手定也。”[7](P320)即是说,“乐”散在执礼、歌诗、舞蹈等活动中,并无独立文本;如要寻找独立文本,那也只有先秦遗留的古乐曲谱,但那却不是文字文本。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今人在标点古籍时,常常不敢将“乐”加上书名号,以暗示虽有“乐经”之称,其实并无《乐经》文字文本。而那些主张《乐经》有文字文本存世的学者,说法又各不相同。如柯尚迁、朱载堉、张凤翔、朱彝尊、阎若璩、李光地等以为《周礼·大司乐》章即《乐经》文本,程颐、章如愚、熊朋来、丘濬、何乔新、徐师曾等以为《礼记·乐记》即《乐经》文本,林岊、胡寅、叶时、刘濂等以为《诗经》即是《乐经》,还有一批学者如黄佐、方观承等以为《乐经》存于众经之中。不过,尽管他们意见不同,但认可《乐经》有文字文本却还是一致的。
近代以来,今文经学复兴,古文经典受到质疑。康有为以为一切古文经典都是伪经,“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8](P2)。他解释儒家“六经”:“六经皆孔子所作。《诗》三百五篇,《书》二十八篇,《礼》十七篇,《易》上下二篇,《春秋》十一篇;《乐》在于声,其制存于《礼》,其章存于《诗》,无文辞:是为六经。”[8](P75)这一解释实际上也是否定《乐经》为独立经典,强调其“无文辞”即无文字文本。钱穆撰《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批评“康说前后横决,无一而可。彼固徒肆臆测,全无实证。然即就其臆测者论之,亦未能条贯,更不需再责实证也”[9](P124),所论切中肯綮,但对《乐经》却未予深究。康有为的“伪经说”现在很少有人相信,但他认为《乐经》“无文辞”,与四库馆臣所说古乐“遗谱”疑即《乐经》残存一样,在当下学界仍然深有影响。如杨伯峻便说:“儒家经书,最初只有‘六经’,也叫‘六艺’。到后来,《乐》亡佚了,只剩下‘五经’。《乐经》可能只是曲调曲谱,或者依附‘礼’,由古人‘礼乐’连言推想而知之;或者依附‘诗’,因为古人唱诗,一定有音乐配合。”[10](P3-4)陈桐生教授甚至认为:“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乐经’,是一个亦虚亦实、亦真亦幻的概念……《乐经》绝不是文字写成的古籍,凡是认为《乐经》是文字典籍的观点,都基本上可以判定为偏离了准星……既然《乐经》不应该用文字写成,那么,那些先秦儒道学者头脑中存在而无法写出的《乐经》,其内容应该是什么呢?答案是:上古三代音乐的曲谱。”[11]
上面那些认为儒家《乐经》是曲调曲谱而否定是文字文本的理解和判断,是否可以成立呢?答案是否定的。
其实,《乐经》不是曲调曲谱,是可以通过传世文献的正反两方面证据得到证明的。
《汉书·艺文志》云:“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二者相与并行。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鼔舞,而不能言其义。”[2](P528)这里引用的应该是刘歆《七略》中《辑略》的意见,班固自然是赞成这种意见的。刘、班等人认为,孔子所阐发的“礼乐”是为社会政教服务的,并且“相与并行”,相须为用。而乐官为畴官,乐师也世守其职。曲调曲谱为乐师所习,世代相传。而周代“礼坏乐崩”之后,“乐”已“无遗法”。所谓“无遗法”,并非没有古乐的曲调曲谱,而是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些古乐配合“礼”来“安上治民”“移风易俗”。其实,古乐的曲调曲谱直到汉代也未完全失传,汉初“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官,颇能纪其铿锵鼔舞”,就能证明这一点。世代相传曲调曲谱的乐师是盲人,其后继者中有明目者也往往使其致盲来强化其听力,以确保其能够世守其职,故有“师旷薰目而聪耳”(3)朱熹:《阴符经解》下篇“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解引“筌曰”,《四库全书》本。陶宗仪《说郛》卷七下录张良《阴符经》同。之说,献给汉文帝《大司乐》的窦公也是“两目皆盲”[12](P35),他们不需要用符号记录这些曲调曲谱来传习古乐,即使有记录古乐的曲谱符号,他们也不可能看见。乐工演奏乐曲靠乐师教诲,同样靠演习记忆,不靠曲谱。因此,在畴官和世职未被破坏的西汉之前,无人发明记录曲调曲谱的符号是很自然的事。不是时人没有这种智慧,而是社会没有这种需要。陈桐生教授认为“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中国一直没有发明记载音乐曲谱的技术”,是无人将三代乐曲编为一书从而形成《乐经》文本的主要原因[11]。这样理解,并不符合秦汉之前礼乐文化发展的实情。
事实上,三代乐舞在秦汉仍有传习,并未完全失传:“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庙乐惟《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高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13](P3592-3593)其中《武德》《昭德》《盛德》为汉人所作,而《文始》为舜乐《韶》,《五行》为周乐《武》,西汉宗庙乐舞一直沿用不废。先秦雅乐在汉代也有保存:“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驹》、《驺虞》;八篇废,不可歌;七篇《商》、《齐》,可歌也;三篇间歌。”[14](P244)东汉末年,曹操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常为汉雅乐郎,尤悉乐事,于是使制定雅乐。时又有散骑郎邓静、尹商,善调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能晓知先代诸舞,夔悉领之。远考经籍,近采故事,考会古乐,始设轩悬钟磬,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13](P3596)。这些历史事实,与主张《乐经》是上古曲调曲谱的学者们所说的《乐经》已经亡于秦火的意见不相符合,也证明三代曲调曲谱并非《乐经》。
既然两汉仍有上古三代乐舞和古乐雅曲存世,汉人并未将这些三代乐舞和古乐雅曲作为《乐经》看待,后人也未发现汉人记录三代乐舞和古乐雅曲的任何曲谱,我们有何理由说古乐曲谱就是《乐经》呢?四库馆臣正是因为将古乐曲谱视为《乐经》遗存,给自己带来许多困扰,以致无法处理后来大量出现的《词谱》《曲谱》等音乐文献,只得将所谓“讴歌末技,弦管繁声,均退列杂艺、词曲两类中”[7](P320),自己否定了曲调曲谱可能是《乐经》的推测。
曲调曲谱不可能成为《乐经》,还可以从先秦两汉的乐学文献中得到反证。在《荀子·乐论》《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等乐学著作中,我们看到的都是对乐义和礼乐关系的讨论,却不见有对曲调曲谱的阐释。即使其中提到三代乐舞,也同样是释其义而非释其谱。因为曲调曲谱只是“器”和“艺”,而非儒家提倡的“道”。离开了孔子所提倡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的所有曲调曲谱,在孔子及其弟子们看来,就根本不是“乐”。例如,《礼记·乐记》载,魏文侯问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的回答是:“今君之所问者乐也,所好者音也。夫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当文侯继续追问什么是“乐”时,子夏说:“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民有德而五谷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此之谓大当。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以为纪纲。纪纲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15](P1540)子夏所谓“德音之谓乐”,虽然包含了音声歌舞,但主要指称社会的稳定和谐和人民的富裕安康,他称之为“大当”,如果离开了“大当”,声律歌颂就不是“德音”,也就没有“乐”。“乐者与音相近而不同”,郑卫之声是“音”(或曰“淫声”)而不是“乐”,这是儒家学者的基本认知。
以曲调曲谱为《乐经》,将“乐”仅仅视为音乐,或者加上歌舞等艺术,以为声音之道,诉诸听觉,不诉诸文字,而舞蹈也只是场上表演,故无文字典籍,其文本形态只能是曲调曲谱。这样理解儒家“六经”之一的《乐经》,并不符合孔子选择并阐释的西周礼乐文化及其所开创的儒家“乐教”的基本精神。孔子“乐教”虽与音乐教育有关,但主要指向人格修养和精神境界[16]。《乐经》文献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与这种将孔子“乐教”理解为音乐教育的认识局限是颇有关联的。
二、《乐经》是孔子对西周“乐教”文献的选择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儒家“六经”非孔子创作,而是历史文化遗产,有丰富的文献积累。在西周,“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王大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国之俊选,皆造焉”[15](P1342)。这说明,在孔子之前,本来就已经有《诗》《书》《礼》《乐》之教,并且应该都有相应的教材。西周的贵族的礼乐文化教育,到春秋时期仍然延续着。例如,春秋中期的鲁僖公二十七年(前633年),晋国“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郄縠可。臣亟闻其言矣,说(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夏书》曰:‘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君其试之。”[17](P1822)这里将《诗》《书》《礼》《乐》并称,并认为懂得它们就是有德、义,可见学习《诗》《书》《礼》《乐》对于人格培养之重要,这已经成为贵族们的教育传统和文化传统。稍后,楚大夫申叔时在回答楚庄王如何教育太子时也说:“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道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18](P485-486)《故志》《训典》等可归入《书》类文献。这说明,在春秋时期的楚国贵族教育中,《诗》《书》《礼》《乐》也是其教育内容,而且都有相对固定的教材。赵衰的时代早孔子一个世纪,申叔时的时代早孔子半个多世纪,这证明《诗》《书》《礼》《乐》教育是周代的传统教育,连“南蛮”之地的楚国也同样受其熏陶,而有关文献的积累十分丰富。我们说儒家“六经”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也有可靠的文献基础,是一点也不夸张的。
在孔子时代,虽然“礼坏乐崩”,贵族教育已经式微,平民教育悄然兴起,但积累了几百年的礼乐文化遗产是深厚的,其文献遗存也是丰富的。孔子非常重视礼乐文献,他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19](P2466)他还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19](P2463)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19](P2481),他并没有创作《诗》《书》《礼》《乐》,只是挑选、整理和阐释西周流传的文献典籍作为教育弟子们的教材。在他的时代,这些文献典籍在不同地区以不同形式存在着,这可从近年出土的战国楚竹书中得到证明。
近年出土的多批战国楚竹书的下葬年代虽是战国中期偏晚,但这些文献的产生年代应该比下藏年代更早,有的是战国早期,有的是春秋时期,甚至有的可能是西周早期。例如,湖北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有一批文献为学界公认为是孔子孙子子思的著述,如《缁衣》《五行》《六德》《成之闻之》《鲁穆公问子思》等,它们应该是战国早期的文献。至于《孔子诗论》《民之父母》《子羔》《仲弓》《弟子问》《颜渊问于孔子》《季康子问于孔子》《孔子见季桓子》等,均与孔子相关,可能是产生于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文献。在已公布的清华大学所藏战国楚简中,有一批未见传世的《书》类文献,如《尹诰》《说命》等,可能是西周史官整理的商代文献(4)参见杜勇:《清华简与古史探赜》上编辨伪篇第一章、第二章,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至于其他篇目,“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厚父》在流传过程中也发生个别文字上加工润色的可能性,但基本可以断定其初始文本当出自周武王时史官的手笔,故可以作为周初的真实史料来使用”[20](中编,P103);“《皇门》是一篇以西周原始档案为蓝本,在春秋时期略有加工润色的历史文献”[20](中编,P156);“《祭公》篇不是后世托古之作,而是西周中晚期史官整理成篇的古文献,其真实性毋庸怀疑”[20](中编,P161);“《金縢》的制作年代当在周室东迁之后,而不晚于孔子之前的春秋之中世”[20](下编,P294-295)。而《成人》篇与《尚书·吕刑》相关,“应定性为《尚书》类文献”[21]。总之,这些出土文献无可辩驳地证明,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末期,传世文献的丰富程度远远超过今人的想象。孔子所谓“文献不足征”,是指符合其所需要的礼乐文献不足征,而并非缺乏一般性的历史文献资料。孔子在当时流传的历史文献资料基础上,选择和整理作为其弟子们学习用的《诗》《书》《礼》《乐》等教材,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与孔子同时而略晚的墨子出身卑贱,却仍然对《诗》《书》十分熟悉,常常在其著述中引用先王著作,并曾反复解释:“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盘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5)孙诒让:《墨子间诂》卷《兼爱下》,《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墨子在《尚贤》《天志》《明鬼》《非命》《贵义》《鲁问》等篇都重复了同样意思的话。这充分说明,儒家“六经”的形成有坚实的文献基础,毋庸置疑。
具体到与《乐经》相关的乐学文献,出土文献虽然不多,但也没有缺席。例如,清华简有《周公之琴舞》一篇,李学勤指出:“《周公之琴舞》的性质是一种乐章,堪与备受学者重视的《大武》乐章相比……《周公之琴舞》乃是与之结构相仿的乐诗,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其内容,这不仅是佚诗的发现,也是佚乐的发现。”[22](P224)饶宗颐在《从郭店楚简谈古代乐教》一文中也指出:“楚简里有《缁衣》全文,现在所知,香港中文大学和上海博物馆亦有《缁衣》零简,证明《礼记》里面有不少应该是先秦的书,并非汉人所作。”[23](P152)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上篇的中心就是论乐,也是重要的乐学文献。如说:“凡古乐龙心,嗌乐龙指,皆教人也。《赉》、《武》乐取,《韶》、《夏》乐情”;“凡道,心术为主。道四术,唯人道为可道也。其三术者,道之而已。《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义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24](P282-283)。这些思想,对于理解儒家《乐经》和“乐教”也是有帮助的。
如果我们认可《礼记》等传世文献中有不少是先秦文献,那么《礼记》中的《乐记》和其他各篇中的乐学资料就为我们探讨《乐经》文本提供了重要文献依据和有价值的线索。例如,《乐记》中的宾牟贾与孔子讨论《大武》,子夏与魏文侯讨论古乐和今乐,子贡和师乙讨论各人所宜歌,等等,都是可以直接或间接反映孔门“乐教”的生动材料。《礼记》中的《曲礼》《檀弓》《王制》《文王世子》《礼运》《礼器》《郊特牲》《内则》《玉藻》《明堂位》《少仪》《学记》等篇都有与乐教相关的内容。因此,对所有先秦乐学文献进行综合分析,应该是可以探寻到《乐经》的踪迹的。
众所周知,秦汉时期的论、说、记、传,都是释“经”文献。既然有《荀子·乐论》和《礼记·乐记》传世,怎么会没有《乐经》文本传世呢?不然,它们的解释对象是什么呢?《荀子·劝学篇》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群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25](P7)此所谓学“经”,就是学习儒家经典,包括《诗》《书》《礼》《乐》《春秋》五种。如果没有文字文本,如何“读”?如何“诵”呢?
其实,“经”并非神秘之物:“经,径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26](P91)所谓“经典”,就是大家经常使用的重要文字典籍。因此,先秦各家都有自己的“经”,道家有《道德经》,墨家有《墨经》,法家有《法经》。先秦儒家“六经”,是经过孔子选择、整理并阐释的重要典籍,当然是文字典籍,或者说是孔门教材,这应该没有疑问。然而,由于受疑经思潮影响,仍有人怀疑某些儒家经典,加之《乐经》是否存世并无定论,自然就更容易被质疑其有文字文本了。其实,《乐经》与《礼经》一样,在先秦是应该有文本传世的。《汉书·艺文志》云:“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2](P528)魏文侯师事孔子弟子子夏,撰有解说《孝经》的《孝经传》,其以儒家思想立国是大家都承认的,其乐师窦公所传的《大司乐》也应该是儒家乐学典籍,这是符合逻辑的结论(6)参见拙文《子夏“乐教”与〈大司乐〉的由来》,《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即发。。事实上,这一章后来也的确被整合进传世的《周礼》之中,证明了《大司乐》是儒家乐学典籍这种推理是可以成立的。魏文侯乐师的后人将其家传的《大司乐》献于汉文帝,足可证明孔子时代有乐类文字典籍传世。
皮锡瑞曾说:“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犹之李耳既出,始著五千之言;释迦未生,不传七佛之论也。”[27](P19)这当然不是说孔子之前没有《诗》《书》《礼》《乐》等文献,而是说孔子之前的《诗》《书》《礼》《乐》只是文献类目名而非文化经典名,是孔子选择西周以来留存的文献资料加以系统整理和创造性阐释,成为孔门弟子学习的教材,这些儒学教材才成为中华文化经典,而孔子之前的《诗》《书》《礼》《乐》却不可视之为经典。《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这里以《诗》为例,说明孔子之前虽有许多《诗》,但不是“六经”中的《诗》(即《诗经》),“六经”之《诗》是经过孔子整理、合乐并阐释后的儒家教材。这当然不是说,《诗经》之前的《诗》不是《诗》,或不能成为文字文献,新出土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及许多《逸诗》便是“古者《诗》三千余篇”的证据,而是说那些《诗》不是后人特指的儒家经典《诗经》。《乐经》当也可以依此类推。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并不表示《诗》《书》《礼》《乐》在孔门都有固定教材,只是说孔子在传统的《诗》《书》《礼》《乐》文献中挑选出了适合他进行儒学教育的材料以作教材之用,有的当时已经固定下来,有的仍在不断地建设之中,从而出现较为复杂的文本面貌。从相关信息来看,孔子之时,作为孔门教材的《诗》《书》已经定型,而《礼》《乐》则处在逐步完善的过程中。孔子自己说过:“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19](P2491)证明孔子直到晚年才修正完善其“乐教”教材。正因为如此,儒家后学对《礼》《乐》的引用就不如《诗》《书》之明确,加之《礼》《乐》知识必付诸实践才能发挥作用,孔子重视“执礼”就是明证,而战国时期“礼坏乐崩”更甚于春秋,缺少了社会实践的支持,也是儒家后学极少引用《礼》《乐》的原因,这便造成了后人探讨《乐经》文献的困难。《礼经》好在有《汉书·艺文志》著录的《礼古经》《礼经》《周官经》可供选择,但唐人撰《五经正义》却不选它们,反而挑选了《礼记》作为《礼经》文本,说明其中的问题也不少。《乐经》的遭遇就更狼狈了,直到今天,其真实面目也仍然被笼罩在五里云雾之中。然而,只要我们承认《乐经》作为儒家经典独立存在,并进行认真细致的文献清理,这一问题是可望获得解决的。
探讨《乐经》文献,必须跳出某些思维误区,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前进。将《乐经》与曲调曲谱挂钩是思维误区之一,前文已经辨明,不再赘述。另一思维误区是,认为《乐经》应该是“乐学”作品合集。因为在一些人看来,儒家经典如《易》《诗》《书》《礼》《春秋》都是作品合集,《乐经》自然不能例外。这种看法似是而非,容易形成误导。其实,作为儒学教材的“六经”,各有所取,也各有所职,所谓“《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1](P216),在文献形式上并无统一规划与要求。例如,《诗经》为春秋中叶以前传世诗歌作品合集,这些诗歌作品经过孔子的挑选和阐释(7)关于《诗经》的成书过程,有二次编订说、三次编订说和多次编订说。,然而,孔子对这些诗歌的阐释不一定要附着于这些诗歌文本,它可以单独成书,所以才有了“三家”或“四家”对《诗》的不同解读,有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而《易》本为卜筮之书,传为孔子所作的《十翼》则改造和规范了它的思想指向,使其成为宣扬儒家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一部哲学著作,因此,添加《十翼》的《易》才是儒家经典《易经》,没有《十翼》的《易》则只是卜筮之书。就《礼经》而言,汉代学者均认为是《仪礼》,而《礼经》的意义和价值则是通过《礼记》来阐释的,没有《礼记》阐释的《仪礼》只是仪注、仪节,不是儒家经典。因此,唐代孔颖达奉命编撰《五经正义》,于《礼经》不选《仪礼》而选《礼记》。就孔子所选择的原始文献而言,《仪礼》和《易》一样,它们都不是作品合集,只是一些社会行为规范和宗教信仰记录。它们之所以成为儒学经典,是孔子改造和阐释后并以之作为儒学教材的结果。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二者在文献形式上也不一致,《礼经》“经”与“传”分行,《易经》“经”与“传”合行,然而,这并不妨碍它们都是儒学经典,因为大家都是通过“传”来理解“经”,“经”与“传”相辅相成,已经成为习惯。正因为如此,以《乐记》《乐论》为线索去理解《乐经》,思考《乐经》,搜寻《乐经》,是符合儒家“六经”形成的文献基础和思维逻辑的,我们应该对此持积极开放的态度。而《乐经》的文本形态和历史遭遇,也同样能够启发我们进行《乐经》文献的深入探讨。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立《乐经》,这是探讨《乐经》文献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西汉末年儒家经典文献尤其是古文经学仍处在整理和完善的过程之中,能够为解决《乐经》文献提供许多有价值的线索。由于此问题牵涉面广,笔者拟另文讨论(8)参见拙文《王莽奏立〈乐经〉管窥》,《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即发。,这里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