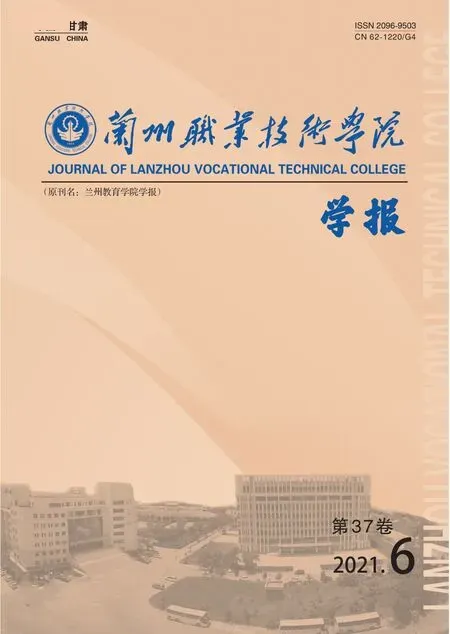语性理论视阈下的中华典籍翻译
——以《庄子》英译为例
2021-12-31柴奕洋
柴奕洋
(山东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中华文化典籍浩如烟海,与中国文化思想一脉相承,是中华文明的宝贵遗产。在西学东渐、中学西传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文化典籍是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博大精深的中华古典文化能否更好地呈现在世界各国面前,取决于典籍翻译的质量。然而文化典籍多以文言形式表达,词藻晦涩难懂,与现代汉语差别较大,本就存在误读或理解不当之可能;加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汉英两种语言的不同特质,跨越千年时空准确传承中华典籍中的文化信息和文化内涵实属难题。目前,我国典籍外译的效果不够理想,一方面,是缺乏特定的翻译理论指导典籍英译,译文质量有待提升;另一方面,是部分译文过分倾向异化或归化的翻译策略,外国读者阅读后会有理解上的偏差,不利于传递中华典籍的文化精髓。
一﹑文化差异决定了跨文化翻译的难度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本和词语的含义都是相应文化的映射。自巴斯奈特提出文化翻译理论后,译学界的“文化转向”论成为焦点。“文化学派”的学者认为在翻译中应该更多地着眼于文化语境和文化视野,实现从文本到文化的迁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中华文化典籍好似一座深邃宝藏,凝聚了历史、政治、文化、诗学、哲理、观念、意识形态等诸多语言文字之外的因素。应用“文化翻译”理念,译者应在翻译中将文本置于一个整体的文化语境进行考量,尽最大可能实现文化功能的重构。然而,文化特质的转写存在困难,这是由于中西方文化在文化背景、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
(一)文化背景不同
在文化背景层面,中华文化强调“以德修身”的思想观念。儒家思想以礼乐教化为本,建构伦理秩序。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并不完全依赖于法治,更多是辅以德治,以德化民,让人们自觉培养起对政治规矩的认同。而西方文化则更多地注重人性观,认为人的德性只可能产生于法律环境的后天规范。政体必须以法律为基础,法治优于人治。中国和西方在“德治”和“法治”理念上的分歧,决定了两种文化的不同走向。中国文化更偏近于“仁义礼智信”式的含蓄包容,而西方文化相对而言,更加“冷血”、更具“狼性”,有着独特的理性反省和理智批判。
(二)宗教信仰不同
在宗教信仰层面,中国尊崇道教,而西方重视基督教。中国的宗教文化虽有“儒道释”三教之说,但道教并非从他国引进,而是土生土长的本国宗教,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的道家和道教(有差别)主张道法自然,天有天道、地有地理、人有人伦、物有物性,在这种无为而治的思想指导下,社会趋于稳定和平,人们的心灵也趋于和谐安宁。西方在古罗马神话和希腊神话等影响下,本就斗志昂扬,崇尚好强好斗的勇武精神,基督教中的耶稣受难则更是赞颂了其以极大的毅力受苦受难最终英勇牺牲的“受难型”品格。这种颇为悲壮的英雄主义与东方的“天人合一”观念形成了巨大反差。
(三)意识形态不同
在意识形态层面,中国诸子百家的学说中均包含了“中”的思想。佛家有“中道观”的思维方式;儒家讲求“执中”“中道”“中庸”“中和”;道家也涉及“中”“正”“和”等思想。这份对“中”的坚守让中国人自古就崇尚集体主义,抨击个人主义,出现了诸如“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等警示言论。而西方思想却恰恰相反,更提倡人性和自由意志,个人权利至上,不会强求少数服从多数。这种对个人利益的满足逐渐演化为哲学上的人本主义,政治上的民主主义,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以及文化上的自我意识觉醒等。
由此可见,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差异,使得文化翻译的实现变得十分困难。中华文化典籍多受特定历史时期文化和意识形态之影响,文学色彩浓厚,在跨文化翻译和传播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文化误读。为了保证源语读者和译入语读者在信息接受层面的对等,典籍翻译的整个过程都要受到文化的驱动和制约。目前而言,译界尚无专门用于指导典籍翻译的翻译理论。笔者认为,高健先生的语性理论可以作为一种很好的翻译指导理论,对中华典籍翻译大有裨益。
二、高健与语性理论
(一)语言个性理论
高健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翻译大师。他提出的语言个性理论,简称语性理论。他认为,语言个性决定了不同语言的特色,翻译时如果对语言个性认识不足,就无法译出佳作[1]。高健将诸家学说归纳为传达论、临摹论、改写论、反映论、模仿论、原物论、释义论等。他认为这些理论都不够全面,原因是忽视了语言个性的存在。正是因为每种语言都有各自不同的个性,才表现为纷繁不一的语言特征。
(二)汉语和英语的语性差异
关于汉语的语性,高健在《语言个性与翻译》一文中列举过其主要特点,诸如意合成分、求雅意识、对称性和简练性、词语间的连缀粘合性、虚词妙用等[1]。而英语的语性则包括质朴性、用词变化性、构词灵活性、转义丰富性等,更加富于变化。
古汉语典籍英译实质上是一个先从文言文转换成白话文,再从白话文向英文转换的过程,即为原文言文内容在另一种语言上的重写。该过程应充分关照两种语言的语言个性,加以协调,在翻译中保留译入语和译出语的语性特征,以达到抽象的直译和具体的意译,句法上的尽量严谨和词法上的高度灵活[2]。
目前,语性理论的相关翻译实践主要集中于英译汉,汉译英的翻译较少。笔者认为语性理论非常适合作为文化典籍翻译的指导,可以让译文达成与原文言文相媲美的效果。笔者拟以文化典籍《庄子》的英译为例,探讨语性理论对典籍翻译的指导意义。
三、协调论在《庄子》英译中的应用
(一)协调论
语性理论视阈下的协调论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个协调的过程[3]。由于汉语和英语两种语言的语性不同,协调论主张从内容与形式、意义与语言、体式与风格、语序与强调、修辞技巧、文化因素、表现手法、繁简程度等多个层面进行协调,在两种语言间做出让步妥协[2]。协调的幅度由大到小均可,但在协调无法全面兼顾时,应衡量源语和译语的得失,从整体出发进行考量。
在高健先生看来,句式里任何成分的忠实性和价值性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译界的“绝对派”过分强调某个词义的绝对确切性,或是词汇中英译文的绝对对应性,忽视了词义本身的相对性、伸缩性和灵活性。无论是词汇还是短语,语句还是语篇,都会因上下文、临近词、语境和文体风格的变化而变化[4]。高健的协调论更趋自由,认为翻译中任何一种元素的合理性和适用性都是有条件的,同样意义的语句置于不同文化的语境下,其措辞和表达都会出现微妙的改变。因此,语性理论视阈下的协调论,可以帮助译者更好地理解何为形式、何为表面、何为真正的忠实、何为“愚忠”[4]。
(二)协调论对典籍翻译的指导意义
目前,协调论更多地应用于文学作品的英译汉翻译。笔者认为,协调论同样可以作为中文作品英译、尤其是中华典籍外译的指导理论。
典籍翻译更注重文化意境的还原和修辞上的调整,以准确传达古典文化为重。然而文化典籍中的文字为古汉语,与当今的现代汉语相差较大,不易理解。因此,在翻译时要不断在源语和译语之间进行协调。可先将原文言文转换成贴切的白话文,之后再将准确达意的现代汉语译成英文。翻译时注重原文整体的文化语境和思想要领,不要太过狭隘地拘泥于单个词的含义。
(三)协调论指导下的《庄子》英译
笔者现以《庄子》译文为例,探讨语性理论视阈下的协调论是如何指导典籍翻译的。
例1.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5]。
译文1.Long ago there was a great rose of Sharon that counted eight thousand years as one spring and eight thousand years as one autumn. They are the long-lived[6].
译文2.And for the huge Chun tree of ancient times, spring lasts eight thousand years and autumn lasts another eight thousand years. This is what great age means[7].
两个译本在细微方面有所出入。例如“以...为”,译文1中译成“count...as”,大致意思可传达清楚。但译文2中直接用了“last”,这样的表述带有歧义,会让读者认为是春季的时间持续了八千年,与原文表述不符。再如“大年”的翻译,两个译本的译法“long-lived”和“great age”都凸显了存活时间长的表面含义,但后者主要用于形容人的寿命很长、年事很高,用来描述树木不够妥当。相比之下“long-lived”在动植物身上使用的更多,相对更贴切。
关于原文中的“春”和“秋”,笔者认为,这两个词并不是为了强调季节,而是为了突出大椿的寿命之长。正如“春秋”这个词至今仍在沿用,形容高寿或时序更迭。因此在翻译时不应将其分开译为“spring”和“autumn”,而应使用“春秋”一词的延伸义,凸显大椿的长寿。
例2.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5]。
译文1.The morning mushroom knows nothing of twilight and dawn, the summer cicada knows nothing of spring and autumn[6].
译文2.Dawn mushrooms never know the young and old moon. Summer cicadas never know spring and autumn[7].
两个版本关于“晦朔”有不同的翻译。笔者认为两个翻译都不太恰当。晦朔一词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晦指的是中国阴历历法的每个月最后一天,而朔指的是阴历每个月的第一天。朝菌又叫大芝,在清晨的时候生长出来,见到太阳立刻就会逝去,因此它“不知晦朔”,因为寿命太短完全不晓得一个月的时间变化。译文1中的“twilight”和“dawn”指的是黎明和黄昏,这样代指的是一天的时间,而非原文中的一个月的时间。译文2的“young moon”和“old moon”指的是上弦月和下弦月,上弦月和下弦月中间相隔只有大约半个月的时间,也没有到一个月。
此外,将“不知”译为“knows nothing of”或“never knows”也太过表面化。这里的“不知晦朔”“不知春秋”指代的还是朝菌和蟪蛄的寿命短,并不是表达它们对这些知识一无所知。因此,笔者以协调论为指导思想,认为该句可译为Morning fungi have never lived more than one month, summer cicadas have never lived more than a year.虽然从字面上没有直译,但体现出原文言文的实意和内涵。
例3.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5]。
译文1. When he rises up and flies off, his wings are like clouds all over the sky. When the sea begins to move, this bird sets off for the southern darkness, which is the Lake of Heaven[6].
译文2.When it thunders up into flight its wings are like clouds hung clear across the sky. It churns up the sea and sets out on its migration to Southern Darkness, which is the Lake of Heaven[7].
“怒而飞”意为振翅奋飞,怒表示奋发,这里指鼓起翅膀一飞冲天。译文1中的“rises up and flies off”有些气势过弱,不如译文2中的“thunders up into flight”,更能展现大鹏鸟一鼓作气飞而震天的气势。而“垂天之云”是在形容鹏鸟的翅膀很大,像是垂漫天空的云彩,因此译文2中的“hung”未免太过直译,只注重了“悬挂”而没有体现出羽翼硕大的感觉。至于“海运”这个词则又涉及到了传统文化,海运表示海动,古有“六月海动”之说,海动必有大风,而鹏鸟正好可以借助风力南徙。但两个译文对于“海运”的翻译都不够贴切。译文1中的“Sea begins to move”太过字面直白,像是在说大海开始移动,与原文意思不符;而译文2中的“churn up”有翻腾,搅动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是鹏鸟飞起来之后产生的气流使得大海翻动,但原文却是海动在先、鹏鸟乘气流南徙在后,并非鹏鸟拍打翅膀致使海动发生,译文2混淆了原文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根据协调论,笔者以“stormy sea and surging waves”的意译指代海动,将天池(天然形成的大水池而非某个地名)译为“a great lake naturally formed”。
综上所述,语性理论视阈下的协调论,注重还原传统文化背景,从文化语境的宏观角度看待词句语篇的翻译,在文化概念词的翻译及解决典籍翻译中的文化歧义等方面颇有助益。
四、结语
中华文化典籍是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的精髓。在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引领下,典籍外译是中国文化对外输出与传播的媒介,有利于促进对外交流和文化多样性,凸显我们的文化自信,其重要地位不容忽视。然而在当今译学界,仍然缺乏专门的译介理论指导典籍翻译,典籍翻译领域的研究有待深入探索和完善。
高健先生的语性理论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通过完美再现和谐译文,赋予典籍翻译新的生命形式。语性理论视阈下的协调论注重还原传统文化背景,从文化语境的宏观角度看待词句语篇的翻译,在文化概念词的翻译及解决典籍翻译的文化歧义等方面具有重要指导作用。语性理论指导下的典籍翻译具备与原作相媲美的竞胜意识,保证译文的艺术性和独立性无愧于原文,有助于弘扬典籍文献中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语性理论的指导下,中国典籍翻译必将翻开新的一页,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