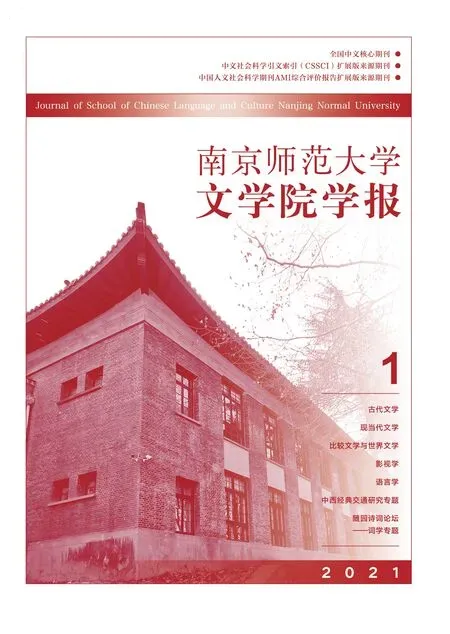认同资源、重造依托与创作审美张力的生成
—— 沈从文与“五四”
2021-12-31石沙西龙永干
石沙西 龙永干
(华东师范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作为从偏于一隅的湘西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以“乡下人”自称,成了沈从文自我认同的一种基本言说。但令人吊诡的是,这样一个“乡下人”却对“五四”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与少有的执著。从1920年代到1980年代,从文坛青年到著名作家,“五四”是他文章中的高频话语,在“乡下人”沈从文的眼中,“五四”形象如何?他对“五四”的认识有着怎样的变化?他为何要反复言及“五四”?“五四”对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认识,是推进对沈从文认识的需要,也涉及到深入把握“五四”在现代作家代际嬗变中的演进路向和具体持存。
一、“五四”余波的影响与自我认同的寻求
沈从文的童年和少年时期,都是在荒僻的湘西度过,他最早接触以“五四”为中心的新思想新文化是1922年他在保靖充任湘西王陈渠珍的司书时。经由印刷工人赵奎五的介绍,他开始接触《新潮》《创造》等新式刊物和《超人》等新文学作品,从而开始了与“五四”的结缘[1](P360-362),并进而决心离开湘西前往北京,去寻求别样的人生。就此,他自述道:“一九二二年‘五四’运动余波到达湘西,我受到新书报影响,苦苦思索了四天,决心要自己掌握命运,毅然离开家乡,只身来到完全陌生的北京。”[1](P397)就沈从文的人生发展和思想变化来看,“五四”是一极富召唤性存在的精神灯塔。但就他对“五四”的认识与评价来看,则是他到北京且开始文学创作之后的事了。
综观沈从文的“五四”言说,1927年12月的《艺术杂谈》应该是他较早对“五四”进行评议的文章之一。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并非对其充满敬意和礼赞,而是颇多批评和微词,“这运动,算是俨然运动过一次,有人呐喊过,擂过鼓,且挺奋而前,竟说新旧肉搏过,革命了。这是奇事。”成功了么?“说成功,真还差得远!”非但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未曾取得成功,而且对新文学(文化)运动中的发起者、倡导者那种“功成名就”后倚老卖老、不思进取的情形颇有不满和批评[2](P18-20)。作为初登文坛的青年,且为基本生存而孜孜矻矻的沈从文来说,面对文坛权威形成的无形压力,生发出愤懑和不满也是自然之事。同时,沈从文前来北京,怀着人生的憧憬和青春的激情,但先前所向往的“五四”运动已然进入低潮,理想和现实,期待与失落,让其对“五四”及都市多有愤懑和不满。这种情形也在他初到北京时期的《蜜柑》《乾生的爱》《看爱人去》等作品中有所体现,虽然这些小说并非直接针对“五四”而发,但对青年学生、小知识分子灰色生活的揶揄讥讽同样可以视为对“五四”憧憬失望后情绪的自然流露。
随着认识的深入和创作的发展,到了1930、1940、1980年代,沈从文的“五四”认识发生了诸多的变化,不仅对其予以认同,而且对其思想和精神予以高度赋值。这里有一般意义上的“五四”认识,但对于以文学为志业且深受蔡元培“以审美代宗教”观念影响的他来说,最为关注的还是“文学革命”。他的“五四”观,更多更直接地体现在他对“五四”文学的批评中,如《论汪静之的<蕙的风>》《论徐志摩的诗》《论闻一多的<死水>》《论刘半农<扬鞭集>》《论落花生》《论冯文炳》《论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论中国创作小说》《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等等。在这些文论中,他认同废名、周作人、徐志摩等人的清新冲淡、自然温厚,认为鲁迅“疏忽了读者”[3](P87),对郭沫若部分诗歌“保留的是中国旧诗空泛的夸张与豪放”[3](P135)有所微词,但他在考量和评价新文学时,无不是将“五四”视为源头,认为中国新文学的业绩首先是来自“五四”思想精神上的革新和解放。“五四运动的勃兴,问题核心在‘思想解放’一点上。因这运动提出的各样枝节部分,如政治习惯的否认,一切制度的疑惑,男女关系的变革,文学的改造,其努力的地方,是从这些问题上重新估价,重新建设一新的人生观。”[3](P84)正因集中关注“文学”,“工具的重造”和“工具重用”的认识也成为了他对“文学革命”的基本认识。“文学革命的意义,实包含‘工具重造’‘工具重用’两个目标……两目标同源异流,各自发展,各有成就:或丰饶了新文学各部门在文体设计文学风格上的纪录,或扩大加强了文学社会性价值意识。”[3](P286)工具的“重造”“重用”的直接结果就是“语体文”的出现,“‘创作’这个名词,受人尊敬与注意”。[3](P197)正是“五四”,才有了“新文学”,才有了1920年代文学的多样姿态和斑斓景观。与之相应,对“五四”意义的认识也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到了对“文学革命”意义的彰显。“把明白易懂的语体文来代替旧有的文坛,广泛应用到各方面去……且成为社会变迁的主要动力。”[2](P133)“将‘语体文’认定当成一个社会改造民族解放的工具。”[4](P53)思想自由,促生了理性精神的萌生,“文学革命把这种精神与愿望加以充分表现,由于真诚,引起了普遍影响,方有五卅,方有三一八,方有北伐,方有统一,方有抗战。”[2](P297)
从上述论述可以见到沈从文“五四”认识的基本情形:“五四”思想解放推动了“文学革命”的“工具的重造”和“工具的重用”,而“文学革命”进而影响到了中国国民思想的改造和中国社会的进程。这种“五四”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文学主义”的倾向,更有着对“五四”进行“精神原乡”的赋值意味,他是在给新文学以思想精神源头和发展滋荣的沃土,更是在对先前心目中的“五四”进行“乌托邦”[5]的强化。
就在沈从文以“五四”为参照对新文学进行批评的同时,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他还在不断地言说着自我与“五四”的关联。“我是受‘五四’运动的余波影响,来到北京追求‘知识’实证‘个人理想’的”[4](P377),“刚到北京,我连标点符号都还不知道。我当时追求的理想,就是五四运动提出来的文学革命的理想。”[4](P384)沈从文并非“五四”的倡导者,更非“五四”的亲历者,他反复言说自我与“五四”的关联,除开强化“五四”对自我思想和人生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外,应还有着文化身份确认,自我认同的意图。如查尔斯·泰勒所言“我最重要的规定关系得以出现的道德和精神方向感来定义我是谁。”[6](P49)在这种反复的言说中,沈从文所要强调的不仅是自我是“五四”的向往者受惠者,而且还有着表明“五四”是我的归属所向和认同资源的需求。
从湘西到北京,从乡村到都市,沈从文经历的不仅是生存空间的转换,更是生存场域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只要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存在着冲突和不对称,文化身份的问题就会出现……身份要成为问题,需要有个动荡和危机的时期,即有的方式受到威胁。”[7](P194-195)物质的困窘,爱的缺失,“我是谁”“我要做什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一系列问题都直接严峻地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让他陷入了极度的苦痛之中。“我发现在城市中活下来的我,生命俨然只剩下一个空壳”[4](P30)。无论都市给沈从文带来怎样的压力和困窘,怎样的迷惘与困惑,他一直在各个城市中辗转并不断成长。而就其赖以支撑的精神资源来看,最为基本的应是“湘西”所给予他的种种,除此外就是“五四”和“五四人”给他的启迪、引导和帮助。如果说“湘西”赋予他以韧性的品质和意志,那么引导和激活这种品质和意志的,则是“五四”思潮中积极探寻生命意义的激情和日益觉醒的生命意识。“五四”让沈从文获得了“人的觉醒”而走出了湘西,让他辗转彷徨中的思想和精神有了归属和依托,更让他在纷乱时代中获得了坚定的信念和不竭的源头活水。这种影响不仅是其人生的抉择,更是融入到他的精神血脉中从而成为他人生的原则和信条。发扬和继承“五四”,是沈从文的“庄严的义务”。他不再仅仅是“五四”的向往者和受惠者,而是以自觉地肩起了“五四”继承者、发扬者的责任和义务。“我有机会由学习而参见,又由参见而将这份经验,这点工作精神,于二十年后再来鼓励及许多工作者。……所谓‘五四人’,还始终守住本来信念,本来岗位,屹立不动,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对内战与强权,且还有个根本否定态度,永不妥协。”[2](P302)“五四人”是称人,也是自称,沈从文由“五四”的边缘人、局外人变成了局内人、继承者。在与“五四”关联中,他实现了自我“五四人”的身份蜕变,更完成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形塑。
可以说,沈从文的“五四”情结,不仅让其获得了归属所系和认同资源,更是让他实现了自我角色和文化身份塑造的完成。从这一层面可以说,“五四”成为了沈从文自我形塑的重要资源。“自我形塑着一条从过去到可预期的未来的成长轨迹。个体依据未来的预期而对过往历史进行筛选,并经由此种筛选过程对过往历史进行再利用。”[8](P71)“五四”是其筛选的存留,更是他的有意选择。也正因如此,在《文坛的重建》《论中国创作小说》《新的文学运动运新的文学观》《二十年代的中国新文学》《文学运动的重造》《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等文章中,他对“五四”的言说不仅仅是向往和憧憬、认同和崇拜,而且有了更多的“过来人”的自信和骄傲,而这也恰好表明沈从文在“五四”的言说和践行中完成了“五四人”的自我认同和确证。
二、“五四”认识的拓展与“重造”思想的依托
在沈从文的认识中,“五四”运动中影响最大,也最为重要的当属“文学革命”,他有时甚至就将“五四”运动的内涵和外延都框范于“文学革命”。这种认识的形成,与其将文学作为自我志业相关,也与其认识的向度和视域有关。但随着实践的丰富和识见的深入,沈从文对“五四”的认识有了新的拓展和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一处,则是他不仅从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层面来阐发“五四”的价值和意义,而且开始对“五四”运动进行理论的总结和萃取。
沈从文在观察和思考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进程时,常高度肯定“五四”的价值和意义,但因志业所在和视域所限,又往往将“五四”的社会价值归因为“文学革命”。如在《白话文问题》中就认为:“从‘五四’起始,由于几个前进者谈文学革命,充满信心和幻想,将‘语体文’认定当成一个社会改造民族解放的工具,从各方面来运用这个工具,产生了作用,在国民多数中培养了‘信心’和‘幻想’,因此推动革命,北伐方能成功的。”[4](P53)但到了《“五四”二十一年》《五四》《纪念五四》《五四和五四人》《文运的重建》《文学运动的重造》等文章中,他虽然依然强调“文学革命”在思想改造和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和意义,但他对“五四”的认识逐渐扩大,“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领导的‘思想解放’与‘社会改造’运动。”[2](P133)“五四运动二十八年了,每年必有纪念会。”之所以要纪念,是“因为‘五四’二字实象征一种年青人求国家重造的热烈愿望。”[2](P268)“近三十年中国变化太大了。向这半个世纪短短历史追究变化的原因,我们必承认民八五四实在是中国大转变一个标志。有学术自由,知识分子中的理性方能抬头。理性抬了头,方有对社会一切不良现象怀疑否认重新检讨的精神,以及改进或修正愿望。”[2](P297)“‘五四’运动在中国读书人思想观念上,解放了一些束缚,这是人人知道的一件事情。当初争取这种新的人生观时……‘重新做人的意识极强,‘人的文学’于是成为一个动人的名词。’”[4](P6)由此来看,沈从文的“五四”认识虽然注重“文学革命”的内容,但其关注点不再停留在文学或审美等范围,而是扩展到了思想解放、时代发展、社会变革等等方面。不仅将“思想解放”“理性抬头”的启蒙值域置于首要地位,而且注重将“破坏”(“怀疑否认重新检讨”)和“重建”(“改进和修正”)相结合。虽然这种认识与陈独秀、鲁迅等人对“五四”在伦理、政治、道德、家庭、教育、社会、经济、婚姻、劳工等等问题上进行的广泛关注相比显得较为狭窄,但与1920年代沈从文作为“文学青年”对“五四”的憧憬和崇拜相比,视域已然有了极大的扩展和丰富。
非但观照“五四”时的视域有了极大的拓展,沈从文还以自我认识和体验为基础对“五四”精神进行了应有的总结和萃取。“五四精神的特点是‘天真’和‘勇敢’”[2](P298)。他所谓“天真”和“勇敢”就是“能从市侩的商品与政客的政策推挽中脱出,各抱宏愿和坚信。”[2](P135),就是“大家真有信心,鼓励他们信心的是求真,毫无个人功利思想夹杂其间。要出路,要的是信心中的真理抬头”,是不顾“功利计较和世故运用”与商业和政治两种势利予以抵抗。[2](P298-299)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将五四的旗号高举为“德先生”和“赛先生”[9],民主和科学遂成为了“五四”的根本所在。将“五四”精神概括为“天真”和“勇敢”,虽说是在上述精神谱系下的自我体验式的提炼和萃取,但它与一般的“五四”精神不同,不是价值理念范畴,而更多的是人生态度和人格品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与沈从文认识“五四”的视点有关,也与其此时提倡文坛和文运的“重建”有着直接的关联。
其实,沈从文早在1930年代初就已开始强调文学创作者应有“天真”和“勇敢”的气质和精神,《现代中国文学的小感想》《窄而霉斋闲话》《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新文人与新文学》《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等文章中都或多或少地论及。他认为文学上要取得成功,“在‘创作态度’上,我们似乎也需要一点儿严肃才行。这一点,于无名作家,尤其是一个不可疏忽的信仰。”[10](P36)面对功利主义创作趋势的盛行,“白相文学态度”的泛滥,他渴望“带着一点儿稚气或痴处的作家出来”[10](P41)承担起文学的责任和使命。在《文学者的态度》中,他尖锐地批判了上海文人的轻浮孟浪、投机取巧。与对上海作家的“玩票白相”的态度相比,沈从文对北方作家的“诚朴态度”[10](P55)极为认同。这些“稚气”“痴气”“带点儿顽固而且也带点儿呆气的性格”可说是“天真”和“勇敢”的近义词,都是对作者文学态度和人格性情的强调。及至1940年代,沈从文为了进一步强化新文学的影响,让“五四”精神“历史化”,以铸就新的传统,他以“天真”和“勇敢”对“五四”精神进行概括。这是他上述认识的延续和深化,也是面对文学受金钱操纵、政治推挽挑战的应对。也正因如此,他积极呼唤“文运的重建”“文学运动的重造”。重造需要资源和依托,于是作为现代思想和文化发端且给其文学创作以莫大影响的“五四”也就自然成为他“重造”赖以建立的基础。“五四”在困境中的重造和创新,给其“重造”的路向,“五四人”的“天真”和“勇敢”,更是其师法的对象。
“五四”运动,让新文学得以滋荣发展,更让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新文学遭遇到了种种困境:“第一是民国十五年后,这个运动同上海商业结了缘,作品成为大老板商品之一种。第二是民国十八年后,这个运动又与国内政治不可分……”[4](P17)要让文学发挥其审美效用、让读者“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理解”[3](P493),就得进行“文运重造”“经典的重造”,就得摆脱“商业竞卖”和“政治依附”形成的桎梏,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这种伟大的作品一面记录了这时代广泛苦闷的姿态,一面也将显示出民族复兴的健康与快乐生机。”[10](P50)在沈从文看来,“文坛的重造”“经典的重造”,可克服“工具的滥用”和“工具的误用”,但其最为根本的指向是实现“民族的重造”和“国家的重造”。“社会必须重造,这工作得由文学重造起始。”[1](P375)“‘国民道德的重铸’实需要文学作品处理。”[10](P172-173)“若当真理解五四精神,必承认对于强权所抱有怀疑否认的精神,修正改进的愿望,在文坛上还得好好保留它,使用它。五四已有了三十年的历史。我们还需要重来三十年继续努力。”[2](P301)“五四”那种狂飙突进的批判意识和创新精神,“五四人”积极追求的“天真”和“勇敢”,让作为“五四”哺育起来的沈从文不仅获得了理念的支撑,更让其获得了具体实践的范型。
可以说,因痛心于文学受商业利益和政治势力的束缚和桎梏,忧患于社会和国民道德精神的堕落和颓败,沈从文大声疾呼“经典的重造”“国家的重造”和“民族的重造”。于是,“五四”运动中“天真”和“勇敢”的更生和复苏成为了他最为切近而真实的渴念,“五四”的价值和意义也就不再拘囿于自我认同的精神资源,而是成为了“重造思想”得以萌蘖的精神母体和根本依托。
三、“五四”观念与“乡下人”意识的相生互发
众所周知,沈从文一贯以“乡下人”自称,从散文《扪虱》到自传体小说《中年》,从《记胡也频》《从文自传》等传记到与张兆和、王际真等人的书信,从《萧乾小说集题记》《习作选集代序》等文论到《对作家和文运的一点感想》《从现实学习》等随笔,“乡下人”成了沈从文的自我定位,也成了他在现代文坛上最为显著的身份徽记。“教育同习惯使我永远近于一个乡下人。”[1](P6)“我原是个不折不扣的乡巴老”[1](P373)……但从前面论述可以见到,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却对“五四”有着超乎常人的关注。“五四”是现代思想和精神的发端,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元话语。既然是“乡下人”,为何对“五四”如此关注,两者之间是否会产生格扞和矛盾?既然是“乡下人”,那么“五四”对于沈从文究竟意味着什么?贴近沈从文的具体境遇与思想脉络,可以直觉到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和对“五四”的认同之间非但没有格扞,而且同为沈从文自我认同的资源,彼此间呈现出互发相生的态势。
任何个体的自我认知,并非生而知之,而是在各自人生轨迹与具体境遇中逐渐生发并趋于成熟的。沈从文之所以自称“乡下人”,与地域文化的涵养、乡土意识的强化有着密切关联[11](P204),但它得以发明的最为直接和具体的刺激是“城市”这一生存环境和“知识分子群体”这一交际圈子。从沈从文自陈“乡下人”的高频时段来看,较为集中在上海时期和昆明时期。有论者将其概括为“上海都市文化空间中的‘乡下人’”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中的‘乡下人’”是有一定道理的。[12](P26-33)而从其“乡下人”的具体指陈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首先,是经济社会层面的。因生于湘西长于行伍,转而在都市中生活时,经济的贫困、见识的浅陋让沈从文深感卑微。其次,是思想文化层面的。沈从文未曾接受高等教育,更未曾有过远渡欧美或扶箧东瀛的求学阅历,这让他在知识学历层面存在一定的紧张。最后,是品德心性层面。虽然沈从文在经济和文化上有着极为明显的“劣势”和不足,但湘西人“情感的素朴,观念的单纯,以及环境的牧歌性”[13](P163),让他在自卑或缺失中获得了补偿性的优越。这种“乡下人”的性情气质,能与自然生发交感,萌生泛神情感,能为美和爱而倾心,会摒弃理性和文明对人的桎梏而沉迷于“生命”的信仰之中[4](P128)。相较前两者,这才是沈从文“乡下人”的精髓。也正因如此,这个“乡下人,走向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权量不合。”[4](P94)他超越一般道德规范,不计较利害得失,摆脱政治束缚,而葆有超乎寻常的审美气质和诗性精神。也正因如此,他能捕捉到山水自然的声光影色,会恣意书写男女的身体悦乐,会为“神之再现”意醉神迷,会为久远传说而神魂颠倒,会为生命庄严而向虚空凝眸……正是这种“乡下人”性情,能让他对都市中人泛滥的欲望、精明的理性和仕宦人格进行尖锐批判。
“乡下人”情结,是“五四”之外沈从文自我认同的另一重要资源,更是他个体创造的重要源泉,“作为个体的创造性力量,它使人按照自己憧憬或假想的目标有选择性地看待生活中的经验,选择一定的方式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生活风格。”[14](P8)也正因如此,他笔下出现了种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5](P5)。正因受“乡下人”意识的影响,“五四”在他的意识中有着一般普遍性的同时更有着属我的独特性。因对现代文明的憧憬,他对“五四”充满了渴念,甚至将其“乌托邦”化;因对蔡元培、周作人、胡适等人的感恩和敬佩,对陈炜漠、陈翔鹤、董秋斯等人的友谊和情义,让他对“五四”认同亲近,热情礼赞。“幼稚,无妨,受攻袭,也无妨,失败,更不在乎。大家真有信心,鼓励他们信心的是求真,毫无个人功利思想夹杂其间……一切出于自主自发的,不依赖任何势力……仁而无私勇而自信”[2](P298),“所谓‘五四人’,还始终守住本来信念,本来岗位,屹立不动,威武不屈,贫贱不移”,他们“忠诚”“还带一点天真的稚气”[2](P303-304)。在沈从文的意识中,“五四”精神的“天真”“勇敢”与“乡下人”的“朴素”“呆气”“真诚”品质是息息相通;两者不计功利得失,不畏强权压制的精神,也是彼此呼应。从这一层面上说,沈从文的“乡下人”意识和“五四”情结的会通,不是思想认识上的趋同,更像一种审美经验的融会。当然,在这种融会相通的同时,也有着彼此间的交流、对话和激荡。就这样,“湘西”和“五四”在沈从文的生命经验中奇妙地结合了起来,不仅同为他自我认同和形塑的重要源泉,也在一定程度上让其思想和创作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张力。
“五四”经验和“乡下人”情结在沈从文那里有着共存的一面,更有着对话交流的一面。“五四”精神让沈从文突破了“乡下人”情结的自闭和自足,走向了更为开阔高远的生命境界,也让其创作具有了独特的审美张力。在一般人意识中,人们多对沈从文的“乡下人”情结予以认同和肯定,或认为这是“带有明确的少数民族含义”的表达[16](P394),或认为这是“现代性思想批判的宣言”[17](P61)。其实,沈从文认同和肯定自我“乡下人”身份时,“五四”现代理性和反思精神又会让他对“乡下人”的不足和局限以一定的间离。首先,他在言说“乡下人”特点时,就对其弱点时有审思。“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15](P3)“所谓‘乡下人’,特点或弱点也正在此。见事少,反应强。孩心与稚气与沉默自然对面时,如从自然领受许多无言的教训,调整到生命,不知不觉化成自然一部分。”[4](P87)其次,他在创作中也常通过人物或叙述者对“乡下人”的种种“疯狂”予以反省。在《主妇》中,叙述者对此就反思到:“生命最脆弱一部分,即乡下人不见世面处,极容易为一切造形中完美艺术品而感到倾心。”[18](P316-317)作为“湘西之子”,他总与这个理性功利精于计算的世界格格不入,总是“过于爱有生一切”,为“爱”和“美”而“如中毒,如受电”[4](P23-24),陷入“为抽象发疯”,嗒然“吾丧我”的境地,而深深喟叹“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4](P39)沈从文上述种种自我审思,固然表现出他对自我道德品行的认同甚至优越,对自然、生命、爱和美的诗性沉湎,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局限的自省:一、过分认同“乡下人”会让自我认识和视域形成局限和偏狭;二、过于“向虚空凝眸”,“为抽象发疯”,也可能让人陷入虚无和抽象的纠缠而于世于事无补。为美疯狂,为爱痴迷,为自然倾心,为生命沉醉……是生命的理想状态,但生命不可能于纯粹诗意和审美中存在,必定要面对现实和生活,在抽象和具体,理性和情感,现实和诗意的两相乘除中,总是优劣共存、高下相倾的。
为避免“乡下人”认同可能生发的偏执,为让恣肆泛滥的情感得以节制,为让人生拥有“情感的发炎”又能致力于时代和社会的进步,沈从文有着自我的调节机制,那就是意识深处的“五四”精神的依凭。“五四”的热情和执著,单纯和勇敢,天真和努力,“五四”的理性意识,批判精神,社会使命和时代责任,让他从“乡下人”与自然的单纯相处,生活环境的牧歌情调,对爱和美、情感和生命的天性中得到了另一种教育,获得了另一种热情和悦乐。让他在认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的同时,又让他不忘却自己现代知识分子的意识和身份;让他为生活和命运沉湎时,而不至于忘却了应有的间离和超越。于是,在认同和赞美乡下人的朴素单纯、勇敢和热情的时候,在表现他们如同蓖麻一般滋荣萎落的“自然”人生时,他会出乎其外,给其以现代理性的观照;在见到他们“不悖乎人性的生命形式”的同时,也会为他们因理性缺失造成的悲剧而深深忧患;在为美和爱而让自我成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浪漫派”[4](P127)的同时,又能时时属意“民族的重造”和“社会的重造”。于是,他在《萧萧》中,会为萧萧在童养媳制度中无意识将自我命运的悲剧轮回至下一代身上而悲恸;《丈夫》中,会为丈夫尊严丧失妻子身心受损而悲怆;《柏子》中,他会为柏子那种“不曾预备要人怜悯,也不知道可怜自己”的自然人生而哀戚;《会明》中,他会为会明对战争本质思考缺席的蒙昧而愀然;在《长庚》中,他在为实际和抽象,现实和想象,生活和生命的思考而陷入“疯狂”时,会回到“五四”的理性精神和改造取向。“从‘五四’到今年正好二十周年。一个人刚刚成熟的年龄。修正这个运动的弱点,发展这个运动的长处,再来个二十年努力,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权利。”[4](P40-41)《边城·题记》中,他会真诚地提醒读者,“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19](P59)“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20](P512)的“五四”文学精神,时时给他文学创作以主导和牵引。
可以说,沈从文的“乡下人”情结,让其“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20](P57),“五四”精神又会让其对底层人生的蒙昧和理性缺失以应有的警觉和反思;当他为“美”“自然”“艺术”甚至于“爱欲”而近于疯狂时,“五四”赋予他的理性精神和责任使命,又会给他以应有的调整纠偏,指向现实的批判和改造。就是这样一种相应相对、相生相发,给他的思想精神以某种动的态势,也给他创作以独特的审美张力。
结 语
总之,“五四”在沈从文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创作中是一个重要且特殊的存在。它引导着沈从文从湘西走向城市,进行新的人生抉择;它是沈从文自我认同的重要资源,也是沈从文“重造”思想得以形成和展开的重要依托。与此同时,“五四”情结还与他的“乡下人”意识互发相生,丰富了他自我认同的资源和形塑的可能维度,也让“乡下人”在致思创作时获得了应有的审美张力。它让沈从文偏爱“乡下人”,沉迷于“爱”“美”“生命”时,又不至于陷入偏执狭隘,流于唯美抽象;在凸显自我审美个性和独特体验之时,又不至于过分疯狂而脱离现实生活和时代真实。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对“五四”也并非完全认同,他曾将“五四”后社会和文坛等问题认为是“工具的滥用”和“误用”的结果,在《蜜柑》《知识》《大小阮》《新与旧》《道德与智慧》《八骏图》《长河》《乡城》等小说中对“学生”“知识分子”“城市文明”的讽刺和批判,又从另一层面表明他与“五四”为代表的现代文化关联的复杂性。而他在《习作选集代序》《水云》《烛虚》《传奇不奇》《摘星录——绿的梦》等作品中对生命的思考,向虚空的凝眸,身体悦乐的迷狂等,则不是简单的“乡下人”观念、“五四”情结甚或两者简单相加就可以涵括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