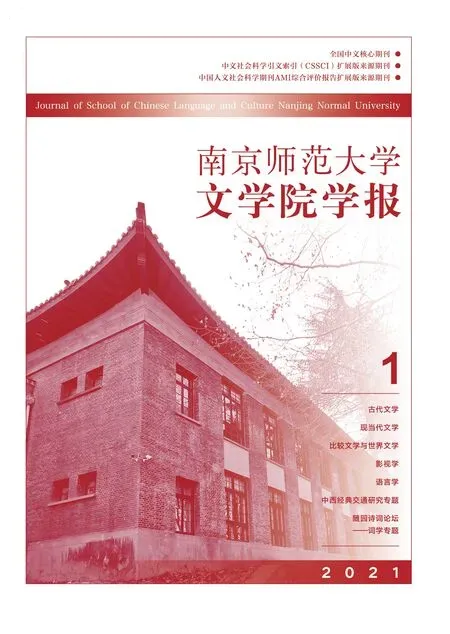现代文艺专刊与民国旧体词的创作
——以四种民国刊物为例
2021-12-31张文昌朱惠国
张文昌 朱惠国
(华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241)
词是一种古老的文学样式。它诞生于歌筵舞席之间,最初依靠口头方式传播。后音谱失传,仅供读品,彻底成为了案头文学。晚近以来,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和机器印刷技术的成熟,现代传播媒介逐渐形成。考虑到旧体诗词在当时文士中的巨大影响力,以《申报》及“三琐”(1)“三琐”即《瀛寰琐记》《四溟琐记》《寰宇琐记》,由申报馆发行,它们是我国最早的文学期刊。为代表的早期报刊媒介为了吸引读者以提高销量,也为了增加一些填充的“佐料”,纷纷开辟诗词版面。由此,原本主要依靠传统方式抄写及刊刻,仅在小范围内传播的词进入了大众传媒阶段,获得了新的发展契机。根据上海图书馆编《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三卷和《上海图书馆藏近现代中文期刊总目》粗略统计,民国期间刊载旧体词作品的报刊不下百种。文艺类报刊自不必说,甚至一些军事、医药、商务类的报刊也不乏词作点缀。这些刊物与当时的政治格局、思想文化等因素扭结在一起,共同塑造了新的词坛生态。
从传播学的视角来看,报刊是报纸和期刊的合称,但二者在文学传播的效能上存在差异。报纸以发布新闻为主,主要面向普通读者,很多不知名的业余作者也能在上面发表文字,难以保证质量,相对来说比较次要。期刊杂志则以揭载评论为主,遵循一定的办刊宗旨,具有解释诱导的功能,文化气息和学术气质更浓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文艺性专门期刊,一般辟有固定栏目发表词作,由于其主持与编纂者多是接受过良好传统教育的旧式文人,具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可以凭借其人脉和选取作品的专业眼光,获得同等层次的作者和受众群体,因而构筑出了高品位的传播平台。遗憾的是,由于资料琐碎收集不易,也由于现代文学史的长期“遮蔽”,这些刊物上的旧体词作品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仅有的一些讨论也主要集中在“词学”,即研究的层面,而对其“创作”层面的关注还明显不够。基于此,本文以民国时期刊载词体作品数量较多、影响力较大的综合性刊物《小说月报》与《青鹤》以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两大专业词学刊物《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为例,探讨现代文艺专刊在民国旧体词创作与传播方面的作用与地位。
一、旗帜与纽带:词坛“同人”的跨域集聚
我国的现代报刊是在来华传教士创办的宗教刊物影响下产生的。作为一种西方舶来品,其最初并不受士大夫阶层的欢迎,早期报刊上所刊的诗词作品也不过以娱乐消遣性质居多。甲午战争以后,受诗界革命、国粹运动、南社活动等历次文化运动的影响,作家们进行了大量创作实践,诗词的活力得到增强。再加上报刊业本身的发展,在类别的划分上趋向细化,以严肃的诗词作品和研究性文章为重要刊载对象的文艺专刊逐渐出现。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前期《小说月报》和《青鹤》。
《小说月报》是一份以刊登原创文学为主的杂志,1910年7月创刊于上海,1932年停刊。刊物以1921为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期由王蕴章、恽铁樵主编(2)具体而言,从1910创刊起至1912年第三期之间由王蕴章担任主编,此后王赴南洋,恽铁樵接任主编,持续至1917年第十二期。1918年起复由王蕴章主编,持续至1920年底。,是旧体文学的重要阵地;后期全面革新,成为新文学的主流刊物。王蕴章是典型的旧式文人,为“广说部之范围,助报余之采撷”[1],他在创刊之时即广设门类,将自己擅长的诗词纳入其中。恽铁樵亦曾声明:“文苑中之诗词,虽非小说……丁此文蔽之世,广为传布,俾青年知国文之高者如此,虽弊报不足言兴废继觉,抑亦保存国粹之一道也。”[2]在他们的主持下,前期《小说月报》的栏目尽管不断调整变更,但“文苑”专栏长期保持,专门刊登旧体诗文和词作。此外,恽铁樵主持时期所辟“最录”专栏,也收录了部分旧体词作品。《小说月报》并非每期都刊载词作,也没有“词录”“今词林”这样一直固定的独立专栏(词作一般列于诗作之后,1915年在“文苑”专栏下设有“词”这一子栏目,不久取消,直到1918年恢复并在以后成为常设栏目),但由于办刊时间长,积累的作品不在少数。作品署名不统一,少数为真实姓名,多数为字号或笔名。根据我们的统计,如果从民国元年(1912)的第二卷第十一期算起,除五芝、语侬、眉盦、贞卿、秋白、怀荃、署仙、芸巢、槁蟫、天徒等尚待考证的10人之外,可确定真实姓名的民国词家达59人(3)《小说月报》中收录有张之洞和谭献的作品,以其未入民国,没有计算在内。,发表词作近400首。其中刊载数量在10首以上的有7人,分别是:況周颐(夔笙)44首,王蕴章(莼农、西神)41首,徐珂(仲可)37首,邵瑞彭(次公)35首,程颂万(子大)30首,吴承煊(东园)23首,冒广生(疚斋)11首;5至10首的有12人,分别是:吴绛珠10首,潘飞声(兰史、老兰)9首,五芝9首,朱祖谋(彊村、沤尹)8首,汪诗圃(诗圃)8首,赵尊岳(高梧、叔雍)7首,刘炳照(语石)7首,张庆霖7首,陈匪石(倦鹤)6首,成舍我6首,樊增祥(樊山)5首,夏敬观(剑丞、吷庵)5首。这些人可视为前期《小说月报》的骨干词人。
《青鹤》为半月刊,1932年11月由陈灨一创刊于上海,1937年8月停刊。历时近五年,共114期。刊物创办的目的是“为国学谋硕果之存”[3],事实上内容以研究古典文学为主。主编“颇从事于网罗作家,部署旧闻”[4],刊载了许多当时已故或在世名人的未刊稿,词学方面包括俞樾的《曲园词》、陈锐的《袌碧斋诗词话》、陈启泰的《癯庵未刊词》等,此外还有不少況周颐、文廷式、夏敬观、黄孝纾等著名词学家的著述。《青鹤》设有“词林”专栏,其下最初分设“前人诗录”“近人诗选”“近人词钞”三个子栏目,前者自一卷二十一期之后不再刊载,后二者则持续始终,其中“近人词钞”栏目专载旧体词作。该栏目的刊载方式没有定格,有时一期分载各家词作,有时每期独载一家,或多期连载单个词人的词作。作品署名皆为字号,除敏生、葆初、莼心、守一、蔚云、醇庵、章甫、谨叔、逋翁等暂时不能确考的9人外,可确定真实姓名的词家共50人,发表作品350余首。其中作品数量排名前十的分别是:张伯驹(丛碧)45首,夏敬观(吷庵、剑丞)44首,冒广生(疚斋、鹤亭)41首,林葆恒(忉庵、子有)35首,黄濬(秋岳)32首,陈方恪(彦通)26首,黄孝纾(匑厂、匑庵、公渚、霜腴)25首,李宣倜(释戡)10首,袁毓麟(文薮)5首,吴庠(眉孙)、溥儒(心畬)、龙沐勋(忍寒)、胡汉民(展堂)、费保彦(四桥)、敏生并列4首。这些人可视为《青鹤》的骨干词人。
《小说月报》和《青鹤》都是综合性刊物。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方面,随着报刊对社会生活的深度介入,词人和词学家们与报刊发生了各种联系,对报刊媒介的认识和使用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新文学渐成主流文学,在公共空间对旧体文学形成了强势挤压,为了接续传统、振兴词学,客观上需要一种能够将词学界团结起来的媒介。在这个背景下,专业的词学刊物诞生了。
《词学季刊》专以研究词学为主,是民国时期最早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份专业词学刊物。1933年4月由龙榆生在夏敬观、叶恭绰、吴梅等人的帮助下创办于上海,至1937年因战争爆发而终刊。共十二期,实际出版的只有十一期,最后一期已付排印,因日军炮轰上海而被毁,仅剩残稿。在专栏设置方面,《词学季刊》大致参照了当时的国学刊物,其创刊号《编辑凡例》上规定的内容分“论述”“专著”“遗著”“辑佚”“词录”“图画”“佥载”“通讯”“杂缀”等九项,出刊时略有调整。其中涉及民国词人词作的有三项:遗著、辑佚和词录。前两项只是少量刊登已故词人的佚作或未刊词稿,起到保存文献的作用,真正能反映当时词坛状况的是“词录”栏目。
与许多刊物将诗词当做“补白”,只是偶尔刊载词作不同,《词学季刊》对词学创作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其已出版的十一期每期皆载有“词录”专栏。具体来看,第一卷第一号上设置了“近人词录”“现代女子词录”两个专栏,从第一卷第二号开始,合并为“词录”专栏,其中又细分为“近人词录”和“近代女子词录”两个子栏目。中间除第一卷第四号、第二卷第四号、第三卷第三号共三期“近代女子词录”栏目失载以外,这种格局保持始终。当然,根据第三卷第二号卷末刊载的《本社启事二》,刊物后期有改革栏目的计划:“兹为酬答阅者诸君雅意,并恢张声学起见,从下期起,特添辟少年词录及读者通讯二栏,专载各方来稿。”但并未克成,第三卷第三号《编辑后记》又称下期再图实现,由于残存的最后一期“词录”栏目稿件已经佚失,也就不知其情形到底如何了。刊物中的词作均署作者真实姓名,并有简短的作者小传。根据我们的统计,在《词学季刊》“词录”栏目上发表词作的作者共计113名,词作总数698首。其中发表词作数量20首以上的有7人,分别是:张尔田29首;龙沐勋29首;丁宁28首;邵瑞彭26首;邵章25首;陈家庆24首;徐小淑21首。10至19首的有17人,分别是:胡汉民19首;黄濬18首;黄孝纾16首;蔡桢15首;吕碧城15首;汪曾武14首;郭则沄14首;向迪琮14首;夏敬观13首;夏承焘12首;吴梅11首;叶恭绰11首;寿鑈11首;罗庄11首;易孺10首;路朝銮10首;陈方恪10首。这些人可以视为《词学季刊》的骨干词人。
《词学季刊》之后,与其风格和性质最接近的是《同声月刊》。它于1940年12月底创刊于南京,1945年7月终刊,共三十九期。同样由龙榆生担任主编,并承担了征稿、编辑、校对、发行等一应事宜。《同声月刊》创刊号上列出的栏目包括:图画、歌谱、论著、译述、诗词(今诗苑、今词林)、遗著、杂俎、附载。与《词学季刊》相比,增加了“今诗苑”“译述”“歌剧”等内容,后期更扩大刊载范围,设置了“文录”“散文”“剧本”等栏目。(4)在1943年4月《同声月刊》第三卷第二号上,同声月刊社发表的预告说:“本刊拟自下期起扩大范围,兼载有关文史艺术之论著,并已约定周作人、瞿兑之、沈启无、姜叔明诸先生担任纂述,特此预告。”看起来似乎较杂,但这种情况与战争期间诗词稿源不足也有一定关系,从文章的数量和质量来判断,词学仍是其主要的研究内容,因此也可视为专业的词学刊物。
《同声月刊》继承了《词学季刊》的精神,对发表词作倾注了极大热情。创刊即设“今词林”栏目,专门刊载词作,除三卷八号和十一号失载以外,持续到终刊。与《词学季刊》稍有不同的是,《同声月刊》从第二卷第六号开始,不再署作者的真实姓名,只署阶青、榆生、仲联、伯沆等字号或者笔名,这给今人查找资料造成了一些麻烦。在尽量辨别的基础上,根据我们的统计,除固叟、梦雨、骏丞、若水、沛霖、伯亚等暂时不能确考的6人外,可以确定姓名的在《同声月刊》“今词林”栏目上发表词作的作者有75人,词作总数达602首。其中发表词作数量20首以上的有7人,分别是:俞陛云(阶青)77首;龙沐勋(榆生)33首;夏孙桐31首;陈方恪(彦通)31首;廖恩焘(忏庵)30首;张尔田(孟劬)21首;丁宁(庆余)20首。10至19首的有13人,分别是:陈曾寿19首;何嘉19首;溥儒(心畬)17首;高燮(吹万)16首;汪兆铭(精卫)15首;陈洵15首;向迪琮14首;吕传元(茄庵、贞白)14首;郭则沄(蛰云)10首;黄孝纾(匑厂、匑庵)10首;夏敬观(吷庵)10首;杨秀先10首;黄孝绰(毣厂、公孟)10首。这些人可以视为《同声月刊》的骨干词人。此外,作为“今词林”栏目的补充,《同声月刊》第二卷第一号和第二号的“冶城吟课”栏目中还存邹森运词2首、俞天楫词15首,两人都是龙榆生在伪中央大学任教时的弟子;第二卷第十号和第十一号的“桥西重九诗录”中也散录着龙榆生、廖恩焘、袁荣法、林葆恒四人的唱和词各1首。
以上四种刊物在时间跨度上覆盖了大半个民国,因而极具代表性。以刊物为纽带,词人们纷纷聚集,其中有些在多个刊物都发表词作,由此形成了一个个貌似独立却又声气相通的词学群落。与传统的雅集结社都不同,他们的聚集是跨地域的,主要以邮寄的方式进行,形式自由,规模也较大。在这里,文艺专刊既充当了一种联结词人的工具,也塑造了一种开放的文化空间。综观这些刊物的产生和发展历程,还可以得出两点认识:
其一,主编个人因素对刊物中旧体词的刊载影响巨大。《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之所以能团结词学界,与主编龙榆生个人的交际能力、性格魅力和深厚学养都大有关系。《青鹤》主编陈灨一于新文学席卷文坛之际独标异帜,“颇思于吾国故有之声名文物稍稍发挥”[4],其刊载诗词显然是出于保存国粹的目的。《小说月报》作为一份以“小说”为名的文学刊物而刊登旧体词作品,与主编王蕴章和恽铁樵的文化倾向和审美趣味密切相关。不过,即使二人同为传统文人,对于旧体词的态度也仍有差别。恽铁樵具有重诗轻词的倾向,其主持阶段发表的词作不仅数量少,有时甚至长期不予刊载。王蕴章是南社和舂音词社成员,对词学创作情有独钟,其1918年重新主持《小说月报》后,发表的词作明显增多,且有较为固定的专栏。因此,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主编是刊物的旗帜和灵魂。
其二,刊物往往具有“同人”性质。《词学季刊》的宗旨是“约集同好研究词学”,所谓“同好”显然是指词体文学的专业研究者或爱好者。刊物实行“社员”和“指导员”制,撰稿人大多与主编龙榆生有过词学交游,或与其存在师友关系。为了加强联系,他们还在“遇必要时约定时地举行大会,平时以通信交换意见”[5],这一点从《词学季刊》的“通讯”栏目和“词坛消息”栏目都可以得到印证。《同声月刊》刊名即取“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命意,成员与前者颇多重合。《青鹤》则体现得更为明显,其创刊号卷首开列了一份“特约撰述”名单,成员多达105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大部分都是民国时期的诗词名家。这些人与主编陈灨一之间,“大多有或‘师’、或‘友’、或‘亲’的关系,有些还是谊兼师友或亦亲亦友”[6],他们积极在“词林”专栏上发表作品,直接造就了稿源无须外求的盛况。与此类似的情行在民国时期的国学类刊物中颇为普遍,这种“同人”属性尽管不免导致了刊物内容的狭窄和“圈子文化”,但同时也决定了刊物的专业性和纯粹性,使得稿件质量保持在较高的水准。
二、主流与潜流:核心词人的散点透视
通过前面的梳理,以上述四种刊物为窗口,我们发现一个庞大的词人阵容已经现出轮廓。去除重复和待考的词人,总共有210名民国词人。待考的词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包括在上述210人中的某一人,用了一个冷僻的笔名;另一种则不包括在其中。综合来看,当时在这几种刊物中发表作品的词人应为230余人。考察这个群体的成员构成情况,有助于我们直观把握现代文艺专刊对民国词坛的意义。
民国是中国历史由近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一方面,政治与文化思潮剧烈变动,传统与反传统势力激烈角逐,深刻影响着时人的价值观念和人生选择。另一方面,随着科举制度的瓦解与社会形态的变化,大量旧式文人不能再依靠仕途经济,而必须与外界进行频繁的互动,寻找新的出路。因而,词作者的身份也随之分化,呈现出多元的特点。总的来说,这230余人基本囊括了民国时期的各个阶层:从政治倾向来看,他们中既有较为保守的遗民词人,也有鼓吹民族革命的南社词人;从职业上看,以大学教授、报人编辑、书画艺人、政府官员为主,附以身份各异的其他词人;从性别上看,仍以男性为主,但女性词人的比例相对来说十分突出。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们再将前举刊物中词人的名单与已故钱仲联先生所撰的民国词坛点将录作一对比。
“点将录”之体初用于人物品藻,后来被引入文学领域。以诗而论,最早为清代舒铁云的《乾嘉诗坛点将录》;以词而论,则首推朱祖谋的《清词坛点将录》(5)该录署名“觉谛山人”,载于《同声月刊》一卷九号。文后附龙榆生识语云:“《清词坛点将录》,为予数年前校刻《彊村遗书》时,友人闻在(宥)先生录以见寄者。据在宥言,此为彊村先生晚年游戏之作。”。钱仲联先生颇嗜此体,曾做过多个点将录,其中涉及词学的为《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和《光宣词坛点将录》。二者将光宣以来的词坛名家按照《水浒传》中梁山好汉排座次的方式进行点将排序,虽是游戏之作,但也并非无的放矢。钱先生与录中所列词人生活年代接近,甚至与不少人有过直接的交往,他本身也是民国词坛重要作手,诗词造诣深厚,凭借其阅历和经验,能够对这些词人的词坛地位和影响进行审慎的判断,因而录中所评大体是符合实际的。从时间上看,前者与民国词坛的创作实践比较一致,适宜于作比较。《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中共列出词人109名,每人下面系以评语,其中三名姓名不全,即地贼星鼓上蚤时迁黄□;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赵□□;地耗星白日鼠白胜梁□□。比照钱先生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的做法,这里其实是有意为之,三人应当分别指的是黄濬、赵尊岳和梁鸿志,因其抗战期间的“汉奸”行径而以春秋笔法讳之。[7](P128)这109人中,曾在前面四个刊物上发表过词作的词人有44人,他们是:朱祖谋、況周颐、叶恭绰、张尔田、陈洵、夏敬观、陈曾寿、夏孙桐、陈锐、廖恩焘、俞陛云、王允皙、林鹍翔、庞树柏、邵瑞彭、吴庠、叶玉森、沈曾植、潘飞声、吴梅、曹元忠、黄侃、郭则沄、王易、谢觐虞、易孺、樊增祥、冒广生、周庆云、吕碧城、程颂万、杨钟羲、王蕴章、黄濬、赵尊岳、汪兆镛、陈方恪、黄孝绰、黄孝纾、汪东、王国维、徐珂、林葆恒、龙沐勋。44人相对于109人,数量已经不少。何况在这109人中,民国建立时已经有16人过世,另有1人卒年不可考,实际可以确定存世的只有92人。这样算来,光这44人就占到《点将录》存世词人的百分之四十八,将近一半的比例。如果仅以《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两种专业刊物作比较,这一比例甚至能够达到百分之七十五。因而,我们有理由认为,现代文艺专刊集中了民国时期最优秀的词人,足以代表当时的主流词坛。
在此,我们不妨仿照施议对先生“二十世纪五代词学传人”[8](P464)的提法,将这44人划分为三代,通过对核心作家的具体观照,揭示其词学创作与现代报刊之间的关系。
第一代词人多出生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包括樊增祥、沈曾植、朱祖谋、潘飞声、况周颐、陈锐、陈曾寿、曹元忠、程颂万、徐珂等人,以朱祖谋和况周颐为代表。朱祖谋入民国后寓居沪苏一带,致力于词籍校勘,兼事吟咏,是公认的晚清民初词坛领袖。词集之外,朱氏还有不少作品散见于报刊,如《国粹学报》《国风报》《庸言》《小说月报》《学衡》等。以《小说月报》为例,共发表了8首词作,分别是载于六卷九号的《金缕曲》(手种前朝树)、《水龙吟·麦孺博挽词》《还京乐·赠庞檗子》,七卷八号的《金缕曲》(一澹从天放),七卷十一号的《金缕曲》(未是师种放),九卷四号的《新雁过妆楼·酒边闻歌》,十卷二号的《鹧鸪天·君直斋中饮海淀莲花白》,十一卷七号的《清平乐·题香南雅集图》,其中有半数后来被收入《彊村语业》。虽多为应酬之作,有些也颇能见出词人心迹,如六卷九号所载之《金缕曲》(手种前朝树)一词,反映了朱氏鲜明的遗民情绪,是其政治词中的代表性作品,张晖先生已有专文讨论[9],此不赘言。与彊村相比,同为“清季四大词人”之一的況周颐在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上更为活跃,其《蕙风词话》《香海堂馆词话》《餐樱庑词话》《纗兰堂室词话》等多部词学论著都发表在报刊上。至于词作,则零散发表于《小说月报》《星期》《东方杂志》《申报》《野语》《时报》《学衡》《申报》等刊物。同样以《小说月报》为例,況氏在其上刊布了44首词作(6)《小说月报》六卷七号载有况周颐与程颂万的《临江仙》联句词8首,未计算在内。,分别载于四卷十一号、五卷五号、五卷十至十二号、六卷九号、十一卷七至十号。其中《绛都春》(子大别五年矣,瀛壖捧袂,枨触昔游,倚此所和)一词两期皆载,属重出之作,因而实际是43首。这些作品以联章词居多,如五卷十一号所载之《临江仙》一调叠至8首,十一卷七号和八号所载之《清平乐》一调敷衍至21首,它们后来大部分被收入了《二云词》和《秀道人修梅清课》两集,对于后人了解民国时期況周颐的行迹以及当时的世风人情,也都不无裨益。
第二代词人多出生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包括冒广生、易孺、张尔田、夏敬观、吴庠、叶玉森、叶恭绰、郭则沄、吕碧城、王蕴章、庞树柏、吴梅、邵瑞彭、汪东等人,以夏敬观和冒广生为代表。夏敬观号为“词坛尊宿”,是民国词坛一代巨擘。他博涉经史,精研诗词和书画,一生著述甚丰,其中相当一部分都以报刊为载体发表,甚至他本人还曾短暂主编过一份综合性刊物《艺文》杂志。就词学论著来看,其《忍古楼词话》载于《词学季刊》一卷二号至三卷四号,《吷庵词话》载于《青鹤》四卷二号至五卷十六号,《词律拾遗补》《况夔笙蕙风词话诠评》《词调索隐》等皆载于《同声月刊》。就创作而言,夏氏是少有的在前面所举四种刊物中都有作品发表的词人,尤以《青鹤》发表数量最多,达44首(7)《青鹤》第一卷第十六期中“近人词钞”收录了夏敬观一副套曲《赠潘兰史桃叶渡题词图·双调》,虽然题为《吷庵词》,但是未计入词作总数。,这些作品大部分收入了民国二十八年(1939)《吷庵词》铅印本之卷四,它们并非一时一地之作,但都反映了夏氏的交游、性情和学养,其中不乏自出手眼的佳构。冒广生与夏敬观年辈相若,在当时词坛也有很高的声望。其《小三吾亭词话》五卷发表在1908年的《国学萃编》,词作则曾多次发表于民国时期的《铁路月刊:津浦线》《文艺周刊》《制言》《国闻周报·采风录》《青鹤》《词学季刊》《同声月刊》等刊物,同样以《青鹤》数量为最多,共41首。冒氏之词,向不为彊村派所拘,如《小说月报》十一卷一号所载之《满江红·京口怀古词十首仿稼轩》组词,《青鹤》一卷二十四期之《水调歌头·题释戡握兰簃裁曲图》、二卷十七期之《水调歌头》(丝竹不如肉)诸作,雄劲霸悍,“才情横溢,时露本色”[10](P424)。由于目前可见之词集《小三吾亭词》仅两卷(8)冒怀辛《冒鹤亭词曲论文集·前言》称《小三吾亭词》有四卷本和未刊稿,惜皆未见馆藏。,都是其早年作品,发表于报刊上的这些词作都可看作集外词,对于我们认识冒氏中年以后之词风颇有价值。
第三代词人多出生于庚子年(1900)前后,包括赵尊岳、谢觐虞、黄孝纾、黄孝绰、龙沐勋等。由于这一代词人一般都生活到了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受“生存人概不阑入,宁贻遗珠之憾,庶避标榜之嫌”[11](P694)的体例所限,再加上百年词史中确实名家辈出,《近百年词坛点将录》对于他们着意较少。考虑到民国词坛的实际情况,这代词人中还可补入夏承焘、唐圭璋、詹安泰、缪钺、张伯驹、顾随等人,而以龙榆生、夏承焘两先生为代表。龙榆生为彊村传砚弟子,词业成就显赫,不仅为现代词学研究开辟了道路,在创作方面也显示出了杰出的艺术才能。龙榆生的词学活动与报刊结缘甚深,他先后主编了《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网罗一代词家,厥功匪浅,无须赘述。在这两大刊物中,其自撰的词学文章和作品都占据了相当的篇幅。以作品而论,《词学季刊》发表了其词29首,其中16首后收入了民国三十七年(1948)铅印《忍寒词》之卷一甲稿《风雨龙吟词》;《同声月刊》发表了其词33首,其中12首后收入了该铅印本之卷二乙稿《哀江南词》。相对于现存龙氏1949年以前全部的173首词(9)此数据统计自《忍寒诗词歌词集》之上编《忍寒庐吟稿》,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而言,报刊上的这些词作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不容忽视。夏承焘被誉为“一代词宗”,且与龙榆生、唐圭璋共被推许为“民国词学三大家”,学养之渊深自不待言,其创作技艺也极为精湛。据《夏承焘词集》[12](前言),民国时期夏氏之词作并未结集出版,至一九七六年方以《瞿髯词》为名油印成册,但其创作活动很早就已持续开展,那些发表在报刊上的作品就是明证。它们散见于《越国春秋》《国闻周报·采风录》《国学论衡》《青鹤》《词学季刊》《同声月刊》《之江中国文学会集刊》《雄风》等多种刊物。以《词学季刊》为例,夏氏在上面共发表了13首词作,分载于一卷二号、二卷二号、三卷一号和三卷二号,特别是二卷二号所载之《浪淘沙·桐庐》一词,曾得朱祖谋、夏敬观等词坛前辈盛赞,堪称夏承焘早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显然,将这些作品刊发出来,在同人圈子中交流传播,对于词人来说也意义非凡。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在文艺专刊上发表作品的词人之中,有些由于年辈稍晚,积稿不丰,算不上主流词人,但在后世却有较大的影响,如万云骏、朱庸斋等先生,似可称之为“潜流”。其实“主流”“潜流”本就是两个具有辩证关系的名词,昭示着一种动态的发展过程。后代之“主流”词人在前代“主流”词人活跃的时期,都可称之为“潜流”;“潜流”们逐渐积蓄学养,大量创作磨炼技艺,慢慢也会变成下一代的“主流”,它们只是用来指代不同时期的词坛精英。我们看到,民国时期无论是老一辈的词坛“主流”,还是年轻一辈的“潜流”,都在当时的文艺期刊上发表作品。究其原因,首先当然是由于报刊媒介本身作为传播工具的便利性。此外,获取稿酬和切磋词艺往往也是重要目的。然而,对于杰出的词家而言,其最深层的心理动因恐怕还在于借助刊物的公共传播功能进行自我情志的剖白,这就有赖于从具体作品中仔细探寻并加以印证了。
三、时代与词心:刊物作品的微观考察
现代报刊的主要读者为普通市民阶层,为了迎合他们的喜好,促进商业消费,许多刊物上刊载的词作内容不外乎风花雪月,应酬无聊之作比比皆是,一般来说,普及性较强的大众刊物多难逃此弊,与主流词坛较为疏离。从前举四种刊物所载文本来看,与泥沙俱下的大众刊物相比,现代文艺专刊不仅集中了民国时期最优秀的词人,其所载作品在思想内涵、情感力度和艺术表现等方面也颇可称道,足以代表当时的创作水平与审美风尚。
首先,刊物反映了新时代背景下传统词人的文化立场。民国肇建,帝制终结;欧风东渐,西学日炽,一派新的气象。但在当时的许多传统文人看来,中国在传统文化和文学方面不弱于任何民族,“文学者,中国所偏胜而数千年所遗之特征也。西国未尝无文学,而历世未若中国之久,修养未若中国之深,好之者未若中国之多且专,此无可逊也”[13](P1),而诗词正是传统文学的代表,是“国粹”之一种。怀着对传统文脉断绝的戒惧,他们自觉延续着诗酒唱酬的生活方式,力图维持风雅之不坠。通观四种刊物,刊载的主要还是那些交游、观览、咏物一类题材的作品,尤以唱和题赠之作为最夥,其最鲜明的表征是刊物中众多围绕同一主题进行集体唱和的同题群咏现象。试举二例:一是“十年说梦图题咏”。《小说月报》十周年纪念时,王蕴章曾请人绘制《十年说梦图》,又撰《十年说梦图自叙》,该文发表在《小说月报》1919年1月25日十卷一号“文苑”栏目。一时间,海内文人纷纷题咏。自十卷二号起至十卷十一号之间,诗且不论,刊发的词则有邵瑞彭、张婴公、寿鑈、潘飞声、陈庆佑、陈匪石、高燮、叶玉森、梁公约、刘鹏年、蔡宝善等词人的11首咏作。词中多用“衰鬓催春”“十年尘迹”“十年一觉”等强调时间转换的字面或典故,表达对王蕴章十载生涯如梦的“同调”之感,而“杜司勋去后,载酒归、江湖念斯人”(婴公《忆旧游》)、“门巷乌衣旧,伫堂前归燕,依恋吟辰”(石工《忆旧游》)云云,也隐含着对王氏多年来办刊时重视诗词,“拟酬和于西昆,风流未歇”[14]之雅意的赞赏。二是“彊村授砚图”题咏。一代词宗朱祖谋以校词双砚授予龙榆生,并于临终前以词稿相托,这是民国时期享誉词坛的一段佳话。据研究者考证,围绕授砚一事产生了大约六幅画作、三篇题记、十二首诗以及十五阕词。[15]单就词作来看,大部分都发表在《词学季刊》上,包括邵章、谭祖任、夏孙桐、张尔田、邵瑞彭、廖恩焘、黄濬、汪兆镛、李宣龚、李宣倜等十人的作品。其中,黄濬、李宣龚、李宣倜三人的作品也见载于《青鹤》。词中常用佛教典故,如“病余禅榻,托意薪传”(谭祖任《烛影摇红》)、“是传人,定应似、衣钵瞿昙,案头早授”(廖恩焘《笛家弄》)、“心肠铁石是皈依”(李宣龚《浣溪沙》)等,寄寓了词人们对龙榆生传承彊村法乳、弘扬词业的殷切期许。以上所举只是规模较大的几种唱和,除此之外,还有《小说月报》所载“香南雅集图”群咏,《青鹤》所载“讱庵填词图”群咏和“遐庵选词图”群咏,《同声月刊》所载“稷园五色鹦鹉”群咏等,二三人之间的小型唱和更是历历在目。尽管这些唱酬活动的主题各不相同,参与唱酬的群体在性情、学养、阅历等方面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但却以较为一致的方式,塑造并强化了彼此共同的文化记忆,展现出了词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深层认同。
其次,刊物反映了乱世中词人们的生存境遇与心灵悸动。与以传统方式刊印的词集相比,现代报刊出版和传播的效率高、速度快,这使其与“当下”的关系更为密切,对社会和时事的参与度更高。民国时期动乱频仍,短短三十八年中,经历了改朝换代、军阀混战、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等种种历史巨变,烽烟处处,百姓艰难求存,强权与刀枪之下,词人的声音不过是一种时代的“弱音”。然而,这股声音韧性十足,从未断绝,始终深情地倾吐着那个时代人们的心曲。先看《词学季刊》。九一八事变之后,面对国土的日益沦丧以及不断的内忧外患,知识分子们受到了极大的刺激,他们继承并发扬了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创作理念,歌哭唱叹,率皆寓于笔端。叶恭绰的《石州慢》作于中秋之夜,适逢月蚀,其上阕云:“夜气沉山,商音换世,愁与天阔。留人岩桂攀余,梦远塞榆都折。琼楼影暗,忍照破碎河山,伤心还话团圆节。涕泪玉川吟,胜枯肠如雪。”词后自注:“是日日本承认满洲国。”本为国人喜闻乐见的团圆佳节,却听闻如此噩耗,就连那天上的月轮也出现暗影,仿佛不忍以清辉相照,匠心中更见悲凉。严既澄的咏史之作《鹧鸪天》云:“乱世英雄貉一丘。更无人解问金瓯。侏儒毕竟轻臣朔,阿斗何曾见武侯。 王霸业,等浮沤。秦淮烟水足悠游。官家大计尊南渡,谁念燕云十六州。”这里显然是以南宋政权比附南京国民党政府,讥讽其不念收复国土而只顾内战的可耻行为,措辞辛辣,酣畅淋漓。类似的还有“太息天胡此醉,任残山剩水,触目惊心”(龙榆生《一萼红》),“大好河山余半壁,煎豆燃箕苦切”(汤国梨《贺新郎·为孙象枢题吴越王画像》),“中原。处处是烽烟。恨苦海难填”(陈配德《木兰花慢·送友人由日本归国》),“病魂弱似药炉烟,犹有洗兵双泪欲经天”(夏承焘《虞美人·病起闻海西战讯》)等,感时哀世之音在在皆是。与战乱相伴的是生命的消逝,故刊物中悼亡之作特多,如陈洵、邵瑞彭、黄孝纾、夏承焘、王易等挽彊村之作,林霜杰悼周梦坡之《齐天乐》,金兆蕃悼秦右衡之《霜叶飞》,廖恩焘悼亡弟之《秋思》等,皆足以动人哀思。再看《同声月刊》。该刊创办于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政治色彩比较复杂。与同时期非沦陷区的《民族诗坛》等刊物相比,在反侵略和鼓舞士气方面自是大有不如,但在表现战争的创痛上并不逊色。张尔田代表当时坚守气节的一类词人,虽滞留沦陷区中,而绝不与倭寇合作。其《满庭芳·丁丑九月客燕京书感》词云:“几点昏鸦噪晚,荒村外、鬼火星稠。”寥寥几笔,已给人鬼气森森之感,而《木兰花令》中的“饥乌琢肉,回首都亭三日哭”,《满江红·丁丑重九感赋》中的“已自摧残人下寄,那堪憔悴兵间活”,《木兰花慢》中的“蚩尤五兵枉铸,浪滔滔、直欲尽生民”,摹写乱世惨象,哀哭唱叹,将情感的烈度推向了顶峰,所谓“诉真宰,泣性灵,声家之杜陵、玉溪也。”[11](P697)廖恩焘名列《汪伪国民政府及其直属各局职官年表》[16](P1033),故有晚年“失节”之嫌,代表了特殊年代的另一类词人。其《八宝妆》一词由吴谚“螺壳道场”引申开来,化入佛家玄理,描绘了一只在螺壳中迷失道路、苦苦挣扎的渺小蚁虫,似有自喻的意味,这种惶惑、恐惧的心境,应是动乱时期的另一面相。
再次,刊物还反映了当时主流词家的美学追求。晚清以来西风东渐,各种新事物、新观念、新思想如潮水般涌入,面对全方位的社会变革,词人们不能不有所回应,并在其作品中有所表现,而与社会生活联系密切的报刊对此是比较敏感的。民国以前的报刊上,就已经能看到在题材、用语、意境上翻新的所谓“新潮词”,如《申报》上“滇南香海词人”发表的以“地火”“电线”“马车”“轮船”为歌咏对象的《洋场咏物词》[17](组词)。至民国时期,这类词集中涌现,如《广益杂志》刊登过《咏国货双妹化妆品词》[18](组词八首),调寄“罗敷媚”,分咏八种现代化妆品;《新医药刊》载有《咏新亚药厂新药词》[19](组词十首),以不同的词调分咏十余种西药,虽语言浅俗,不具词美,但也别具特色。现代文艺专刊上也有部分作品具有这种新变,如《词学季刊》一卷一号上所载吕碧城的两首词,其《玲珑玉·咏瑞士山中雪橇之戏》一阕歌咏域外新事物,《法驾引·英译阿弥陀经既竟感赋此阕》一阕小注夹以英文名词,另外《青鹤》四卷九期上所载张伯驹的《浪淘沙·由广州至汉口飞机上作》一阕,也表现出不同于传统词作的气象。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类词作只是个别现象,遍翻前举四种刊物,不会超过十首,绝大部分作品与前代相比并无明显的变化。二千余首词作中,只有数首例外,占比之小几可忽略不计。这种悬殊的差距,既体现了词体的超稳定性特征,也体现了民国时期主流词家们不盲目趋新,从雅、崇古的美学取向。
综上,现代文艺专刊的作者多为词坛好手,在民国这个大变革、大转型的时代,他们或以敏感的艺术心灵观照生活,或发挥“词史”精神抒写世相,创作了许多不让前贤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经过刊物编者的精心挑选和安排,以一种类似群体词选的方式呈现出来,充分展现了民国时期的创作高度和总体风貌,理应获得更多的关注。
四、余论:词学视域下文艺专刊的价值与地位
现代文艺专刊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词学的现代转型,尤其是《词学季刊》和《同声月刊》这样的专业词学刊物,堪称民国词学研究的中心阵地。与此同时,时常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在于,它们对民国时期旧体词的创作也贡献甚巨。上文我们主要从作者和文本两个维度对其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无论是作者群体的代表性,还是刊物所载作品的高水平,都已经清晰地表明,现代文艺专刊在民国词创作生态与格局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事实上已成为了新的词学创作中心。
与传统的创作中心相比,现代文艺专刊具有如下特点:其一,传统的词学创作中心往往围绕词坛领袖生成,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清代柳州词派、梅里词派、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等大小词派,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莫不如此。文艺专刊则明显不同,它将以往词坛领袖的凝聚力转换成了刊物平台的吸引力,词人们以刊物为依托共同参与创作,彻底打破了时空的天然壁垒,从而构建了一个新型的文化场域。其二,传统的词学创作中心往往以地缘、学缘、亲缘为纽带,文艺专刊则以主编为旗帜,以刊物本身为纽带,更加依赖文化观念和审美趣味的黏合作用。其直接证据就是民国时期众多期刊型文学社团的诞生,如词学季刊社、同声月刊社等,将词人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传承词脉、发扬词学的共同心愿。其三,传统的词学创作中心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形成,现代文艺专刊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朝甫脱稿,夕即排印,十日之内,遍天下矣”[20](P116),传播的范围和效率远超前者,而刊物内部各栏目之间的互动效应,也推动了其影响力的快速成形。
除此之外,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现代文艺专刊至少还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价值:一是保存了珍贵而丰富的词作文献。在刊物上发表作品的词人中,许多都编有词集,但词学名家一般对自己的作品去取较严,单看别集难窥全豹,可据刊物以辑佚或校勘;更多的人迄未结集,然其作品也不无可观之处,吉光片羽,幸赖刊物以存之。二是培养了一批词学后备人才。如果说新式词学教育为他们提供了词学的知识储备,那么现代文艺专刊则为他们搭建了切磋交流和施展才华的舞台,客观上促进了现代词学的传承。三是为以后词学刊物的编纂提供了借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的《词学》杂志,从宗旨、性质到栏目设置,无不打上了《词学季刊》的深刻烙印。要之,现代文艺专刊与民国旧体词的创作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研究民国时期的旧体诗词,如果不对文艺专刊上刊载的作品进行一番系统的整理和爬梳,得出的结论必然是粗疏和不够完整的。这是一片人迹罕至的富矿地带,仍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开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