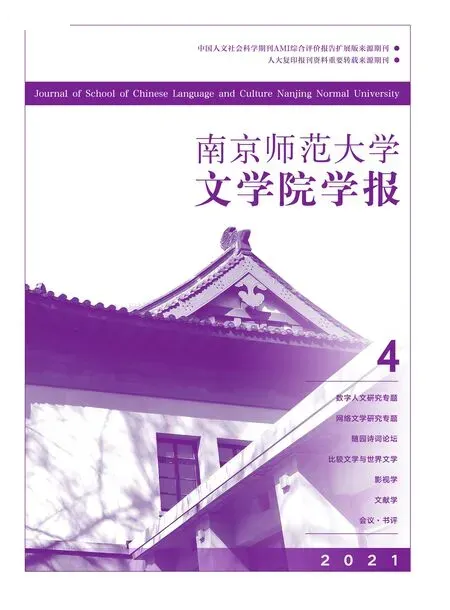论温庭筠词闺阁空间的建构
2021-12-31王淋淋
王淋淋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温庭筠在词中建构了以女性为生活主体的闺阁空间。以往学者多认为此空间“狭深”(1)杨海明先生所说的“狭深”,主要指温词的题材狭窄、抒情细腻深曲;但也可用来形容抒情主人公的活动空间。参见杨海明《唐宋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甚至“意境无多”[1](下册,P868)。词人如果只是对这个“狭深”空间不厌其烦地作精雕细刻,也就不会被推为“花间鼻祖”。正如王兆鹏先生在《唐宋词史论》中指出:“唐末五代词人为突破女性主人公身之所容之境的限制,往往建构一重意之所想的远境、大境来陪衬主人公身之所容的实境、小境,以扩大词的审美空间。”[2](P72)温庭筠在建构空间时,必然采取一定的艺术手法。那么他具体如何建构,又怎样将一个个看似破碎的场景组接成完整、浑融的艺术空间?这种空间的建构方式有怎样的“典范”意义?本文将一一探讨。
一、闺阁空间的类型
温词中的抒情主人公多为女性。由于时代等因素,她们的活动场所大多限制在居室,只能开窗、登楼来观览外界。不过还有一重空间,即明代李日华所提及的“目力虽穷,而情脉不断”的“意所游”之境(2)李日华《竹嬾论画》:“凡画有三次第,一曰身之所容:凡置身处,非邃密,即旷朗,水边林下,景所凑处是也。二曰目之所瞩:或奇胜,或渺迷,泉落云生,帆移鸟去是也。三曰意之所游:目力虽穷,而情脉不断是处也。”参见俞剑华编著《中国古代画论类编》(修订本),人民美术出版社,上卷,第一编,第132页。,也可以作为闺阁空间的一部分。因此,身处、目瞩和意骋之境共同构成了温词的闺阁空间。
(一) 身处之境:闺阁女子活动的主场所
身处之境,就是抒情主人公当下活动的场所。温词中的女子多生活在华丽但封闭、孤寂的闺房中。
华丽的居室空间中,不管是建筑本身、室内陈设,还是主人的服饰,都富艳精工。词中女子都居住于“玉楼”“画楼”“沉香阁”“画堂”等美轮美奂的楼阁中。如“玉楼”,奢华住所的代名词。唐人宗楚客用“玉楼银榜枕严城,翠盖红旗列禁营”[3](第1册,卷四六,P360),形容安乐公主的山庄;“沈香阁”,则是用沉香木所建的贵气楼阁。(3)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杨国忠又用沉香为阁,檀香为栏……禁中沉香之阁,殆不侔此壮丽也。”参见王仁裕等撰、丁如明等校点《开元天宝遗事 外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建筑的局部设备同样描金镂彩。比如词中常提及“雕梁”和“琐窗”,南朝谢朓以“雕梁虹拖,云甍鸟跂”[4](卷1,P130),描绘光华殿屋梁和甍的华丽;李建勋用“云渡琐窗金榜湿,月移珠箔水精寒”[3](第21册,卷七三九,P8433),抒写升元阁窗户的精美。这些建筑意象,共同构筑成华贵绚丽的居室空间。
与建筑本身相应,室内的陈设物也贵气逼人。一为种类繁多。如家具类,有“枕屏”“画屏”“晓屏”“银屏”“锦屏”等屏风;床上用品类,帐子有“锦帐”“罗帐”“凤帐”,被子有“鸳鸯锦”“锦衾”“绣衾”“鸳衾”“鸳被”,枕头有“颇黎枕”“山枕”“鸳枕”“金带枕”;还有“水精帘”“画罗”“翠幙”“重帘”“绣帘”“珠帘”等帘幕;“玉炉”“金鸭”“炉熏”等香炉。二为材质名贵,锦缎织就的“锦屏”“锦帐”“锦衾”;宝石制成的“水精帘”“颇黎枕”;镶金的“金带枕”,嵌银的“银屏”,珍珠串起的“珠帘”。当然这些物件不一定真由黄金、宝石、玉制作,词人选此作修饰词,目的为打造一个金碧辉煌的室内空间,就像李冰若所评:“飞卿惯用金鹧鸪金鸂鶒金凤凰金翡翠诸字以表富丽。”[1](下册,P868)三为工艺精湛,词中提及的陈设品多绣或绘有各种精致的花纹图饰,如绣了鸳鸯、凤凰的衾枕和帐子,绘着山水画的屏风,“晓屏山断续”(《归国遥》),“小山重叠金明灭”(《菩萨蛮》)。富赡的物品、繁多的种类、名贵的材质、精湛的做工,无不彰显室内的豪华气象。
居室主人的服饰,依然华侈靡丽。各种品类,无一不备。如钗,有“玉钗”“翠钗”“钿雀”“金雀钗”“翠凤宝钗”“翠霞金缕”;簪,有“钿筐交胜金粟”“寒玉簪”;还有“小凤战篦”的篦,“翠翘金缕双鸂鶒”中的翠翘等。所用材质,弥足珍贵,首饰都由金、玉、珠宝所制;服装质地精良,像《归国遥》中“越罗春水渌”的“越罗”,是一种产自越地的丝织品。据刘禹锡《酬乐天衫酒见寄》“酒法众传吴米好,舞衣偏尚轻越罗”[3](第11册,卷三六〇,P4070)可知,这是制作舞衣的上好料子。做工更是繁琐精细,以“钿筐交胜金粟”(《归国遥》)为例:先把宝石雕琢成小片花饰,镶嵌到首饰表面;再将细金丝围绕在花饰周围,作为外框;最后在外框上镶嵌粟米大小的金珠。[5](P192-213)这种工艺太过靡费,以至于唐肃宗下诏:“禁珠玉宝钿、平脱、金泥、刺绣。”[6](第1册,卷六,P159)雍容华贵的服饰,象征着主人的身份和地位,也进一步强调闺房的奢华绝伦。
居室空间虽然华丽,却极封闭;当然封闭是闺房的共性。温庭筠用多种方式来强化这一特点。其一,以帘幕等阻隔,凸显空间的狭深。词人一方面选取帘垂、帐帷掩的意象,如“水精帘里颇黎枕”(《菩萨蛮》),“未卷珠帘,梦残惆怅闻晓莺”(《遐方怨》),以及“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更漏子》)等,点出空间层层封闭的特点。本来屏、帘、帐等物件用以分割空间,何况还是低垂密掩的状态。另一方面,借女子放帘、掩屏等动作,像“垂翠幕,结同心,待郎熏绣衾”(《更漏子》)中放下翠幕,“掩银屏,垂翠箔,度春宵”(《酒泉子》)里合上屏风,以及“凭绣槛,解罗帷”(《遐方怨》)的解开罗帷等,将自己主动隔离在更加逼仄的角落,以此增加空间的深邃感,渲染女子的黯然神伤。可并不是躲藏起来,便可逃避。因为窗边、帘外的鸟啼莺语:“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菩萨蛮》),“隔帘莺百转,感君心”(《南歌子》);月影婆娑:“珠帘月上玲珑影”(《菩萨蛮》);草绿花红:“萱草绿,杏花红,隔帘栊”(《定西番》),随时向她们提醒这令人窒息的禁锢感。其二,用卷帘等动作,暗示封闭。如“青麦燕飞落落,卷帘愁对珠阁”(《河椟神》),“罗幕翠帘初卷,镜中花一枝”(《定西番》),惟当卷起帘,才能实现室内外互通。然而,密闭的空间又岂能凭借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以改变。层层封锁,锁住的不仅仅是明媚风光,更有闺中人的青春与欢乐。
闭塞的闺房当然孤寂无比。整个居室弥漫着冷寂的气氛:“洞房空寂寞”(《酒泉子》),“寂寞花琐千门”(《清平乐》),“寂寞香闺掩”(《菩萨蛮》)。这里的主人孤独地生活着:没人说话和陪伴,独自梳妆与失眠;每天重复上演一幕幕独角戏。她们在寂寞里煎熬,时常顾影自怜:“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菩萨蛮》),“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菩萨蛮》);怜惜自己如花容颜空凋零,叹息日复一日无望的守候。随着愁闷积累,安睡都成奢望,她们看着“香烛销成泪”(《菩萨蛮》),“香作穗,蜡成泪”(《更漏子》),百无聊赖;午夜残梦觉来时,“灯在月胧明”(《菩萨蛮》),“画堂照帘残烛”(《归国遥》),无人替灭灯;长夜漫漫,苦忍“夜长衾枕寒”(《更漏子》),“锦衾知晓寒”(《菩萨蛮》)。
温庭筠替笔下的女子建构了富丽堂皇的生活空间,固然为贴合她们的身份,能“在觥筹交错的酒筵席间,营构出一种热烈而惬意的情感氛围”[7](P172);但也“以同样身份的女性的眼光在观察她们、描绘她们,透过她们的举止和妆扮,看到了她们内心的隐秘,处处流露处体贴和同情”[8](P360)。这些上流社会的女子服饰绮丽、妆容精致、姿态柔媚,享受着奢华的物质生活;可独处幽闺,身心拘囿在这狭小封闭的空间里,任岁华空耗、容颜暗损,一腔痴怨无处安放。
长居深闺是温词女子的生活常态,但她们偶尔还是有机会走出绣房,去游春、采莲或送别。因此淡雅、清冷且狭小的户外场景构成了“身处之境”的另一部分。
词人常选淡雅意象入词,比如三首《荷叶杯》(4)分别是《荷叶杯》(一点露珠凝冷)、《荷叶杯》(镜水夜来秋月)、《荷叶杯》(楚女欲归南浦)中,“露珠”“水波”“水面”“月影”“雨”等无色或白色之物象作主景,“绿茎”“红艳”“愁红”等红绿色稍为点缀,描摹一幅朦胧飘渺、清雅疏淡的水乡图景,迥别于绣阁的繁复缛丽。
当然,户外场景也依然冷清。不仅境凄冷,“露珠凝冷”“水风凉”“如雪”“寒浪”“愁红”等词汇,无不构成冷落凄凉的底色;而且心更寂寥,姹紫嫣红带不来赏心悦目,只让她“罗袖画帘肠断”,因为“阮郎春尽,不归家”(《思帝乡》);更莫说离别时,“谢娘惆怅倚兰桡,泪流玉箸千条”(《河渎神》);无处逃逸的寂寞里,“肠向柳丝断”(《河传》),“惆怅,正思惟”(《荷叶杯》)。
闺中女子尽管有时迈出了方寸绮楼,但仍然走不进广袤天地。她们的视野里只有春花秋草、寒塘荷影、湖光涟漪类的幽境,而无阴阳开阖、乾坤日月的大景。当然也受她们身份、生活经验和审美标准所限。这些清新、冷清而又幽深的户外空间,依然是温词“狭深”特点的写照。
(二) 目瞩之境:丰富拓展闺阁空间
人长久地被拘囿在边界鲜明的狭窄格局里,需要寻觅一个突破口,能与无垠的外境获得联系。闺阁女子们,只能“从窗户庭阶”和“帘、屏、栏干、镜”来“吐纳世界景物”[9](P162),观望新的境界。因此,词人借笔下女子开窗观望或登楼远眺,来构建目瞩之境,丰富并拓展空间。
因抒情主人公所站的高度和视野不同,目瞩之境可分近观之场景和远眺之风光。女子近观所得,多为庭院景观,唯美却单调。词人常选春之时节,构筑明媚鲜妍、生机盎然的庭院风光。但花开柳垂、草长燕飞的烂漫春光,激不起闺中人半点喜悦:她们对着“青琐”看“水纹细起春池碧。池上海棠梨,雨晴红满枝”,伤怀“玉关音信稀”(《菩萨蛮》);见“栏外垂丝柳”,怨“音信不归来”(《菩萨蛮》)。窗外绮丽华滋,窗内寂寞如斯。相反的情境,深化闺中人的幽独与惆怅。同时,精致婉约的庭院景象,也是“谢娘心曲”的“外物化”呈现。[10](P123)如池中泛起的细细波纹、圈圈涟漪:“水纹细起春池碧”(《菩萨蛮》),“凭阑干,窥细浪,雨萧萧”(《酒泉子》),实则为女子波动不安的心绪。
当女子登高远望时,视野顿时开阔,所见的便是“千里云影薄”(《酒泉子》)、“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梦江南》)类的广漠浩渺景象。正如王夫之《姜斋诗话》所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即极写大景,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亦必不逾此限。非按舆地图便可云‘平野入青徐’也,抑登楼所得见者耳。”[11](卷二,P56)远眺风光的空旷缥缈,异于近观之境的明媚婉约,增加了空间的张力感;但这重远境并没有拓宽闺中人的胸怀,只让她们更加茫然与寂寞。因为再怎么极目远眺,也望不见远行人的身影。
目瞩之境让闺中女子透过封闭的闺房,窥视到了一重新天地;但这只是暂时的游离,“只是用来强调与外界隔绝的孤独并唤起她对时光流逝的注意”[12](P152),最终目光和心灵都必须“从全部敞开的门窗重新回到家宅里面”[13](P82)。
(三) 意骋之境:突破当下空间的限制
词人还为幽居深闺、日复一日无谓消磨光阴的女子们,另外开辟了一个空间,存放想象、梦幻与回忆,补偿现实中的缺失。这空间便是意骋之境。根据意识活动不同,词中的意骋之境分三类:其一梦中之境。词人描写此重空间时,往往用“梦”或“觉”等字作提示。如《菩萨蛮》中“水精帘里颇黎枕,暖香惹梦鸳鸯锦”[14](第1册,卷一,P17),由“梦”字引出“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之境。还有“闲梦忆金堂”(《菩萨蛮》)“梦长君不知”(《更漏子》)“梦魂迷晚潮”(《河传》)“觉来闻晓莺”(《菩萨蛮》)等。闺中女子每日为相思所困,所梦多与心上人相关。有些是往日场景再现,像“杏花含露团香雪,绿杨陌上多离别”(《菩萨蛮》),清晨杏花含露绽放之时,与心上人在长满绿杨的路上分别。“多”字既说明别离次数之多,也暗示梦见频率之高。往日场景频繁入梦,道出思念之深;有些是心愿的投射,如“江上柳如烟,雁飞残月天”(《菩萨蛮》),那里可能是情郎的所在之处,也可能是女子一直追随心上人的行踪。梦中之境的苍茫寥廓,打破室内空间的幽深狭窄;还有一些是不安心绪的写照,如“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河传》),无论在“若耶溪”“溪水西”还是“柳堤”,都寻不到心上人的身影。镜头迅速切换,既符合梦境无拘束的特点,也象征女子的不安与惶恐。
其二为追忆之境。追忆之境可依“当年”“忆”“昔日”等词判断,不过更需结合全词意脉来领会。与梦境不同,所忆场景都曾真实发生过。它具有情境同向的特点,即乐景写乐情,哀景抒哀情。记忆里与情郎相聚的场景总是充满温馨与快乐,如“蕊黄无限当山额,宿妆隐笑纱窗隔。相见牡丹时,暂来还别离”(《菩萨蛮》),回味着“牡丹时”的欢会,欣喜得忘了理妆;“金雀钗,红粉面,花里暂时相见。知我意,感君怜,此情须问天”(《更漏子》),想起初见时,红粉容颜,彼此心意两知。这幕场景的抒写,有些为加深当下的欢乐,就像《菩萨蛮》中:“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14](第1册,卷一,P27)女子欣喜眼下与情郎心意相通,再想起相处时的愉悦,甜蜜不言而喻。当然更多的时候,反衬当下的苦闷,回忆里“绣衫遮笑靥,烟草粘飞蝶”,现实中“玉关音信稀”(《菩萨蛮》);往昔“知我意,感君怜”,而今“山枕腻,锦衾寒,觉来更漏残”(《更漏子》);曾经“转盼如波眼,娉婷似柳腰。花里暗相招”,此刻“忆君肠欲断,恨春宵”(《南歌子》)。鲜明的对比,让眼下的寂寞更加浓烈。
同理,离别场面总是感伤。如《菩萨蛮》:“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门外草萋萋,送君闻马嘶。”[14](第1册,卷一,P42)杨柳袅娜、春草萋萋的季节送郎君远行,所有的伤怀意绪由“无力”二字道出;风光再美,“楚山如画烟开”,也只让“玉容惆怅妆薄”,肝肠寸断(《河渎神》);离愁别绪被时光酝酿得愈加浓厚,“羌笛一声愁绝”(《定西番》),“卷帘愁对珠阁”(《河渎神》)。
回忆里,无论相聚抑或分别,女子都和情郎一同出现,不似当下孤独的生活状态。因此这幕场景既强化了女子身处之境的孤寂,也交代了她们伤情的缘由。曾经在“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别离,而且别后“画楼音信断”,所以如今只能伤怀“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菩萨蛮》);曾经“秋风凄切伤离”,现在更是“芙蓉凋嫩脸,杨柳堕新眉”(《玉蝴蝶》)。
其三,想象之境。词中的女子因为眼前的声音或物象,触动心绪,虚构出一重因声想象之境或凭物联想之景。前者指女子借听到的风声、雨声、鸟鸣等,构想出的情境;就如王夫之《姜斋诗话》所说:“隔垣听演杂剧,可闻其歌,不见其舞。”[11](卷二,P56)典型如《菩萨蛮》:“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14](第1册,卷一,P65)女子听清明雨下,想着此刻南园的漫天飞絮定经雨打,堆满地面。听“何处杜鹃啼不歇”,想象满山的杜鹃花“艳红开尽如血”(《河渎神》);“暮天愁听思归乐”,念起“早梅香满山郭”(《河渎神》)。
后者为女子由眼中所见而联想的场景。如看到“雨后却斜阳”,想起经雨打日晒的“杏花零落香”(《菩萨蛮》),这也是她细腻、无憀心境的写照;由眼前的“秋风凄切”,想远行人那“塞外草先衰”(《玉蝴蝶》);想象昔年别离的“汉使”那正“千里玉关春雪,雁来人不来。羌笛一声愁绝,月徘徊”(《定西番》)。尽管这些场景无法亲身走进,但都凭思念和牵挂建构。
有了意骋之境,紧缩的室内空间试图向外膨胀,板滞中多了灵动的元素,就如清人恽恪所说:“虚则意灵,灵则无滞……夫笔尽而意无穷,虚之谓也。”[15](第3册,卷末,P256)只是这重境界依然强调了当下情境的凄苦,女子暂时得到宽慰的孤寂心灵,还是要继续迎接生活的下一轮冲击。
二、闺阁空间的建构方式
温庭筠不仅创设了各种境界,而且“截取可以调和的诸印象”[16](P3),或一重,或多重;以恰当的方式,进行排列组合,建构成一个个多姿多彩、意蕴丰富、情感饱满的艺术空间。那么不同层次的空间,以何种方式建构,不致于单调刻板?几幕画面又是如何衔接,使之“蹙金结绣,而无痕迹”[17](下册,P1003)?接下来探讨不同场景的建构方式。
(一)单幕场景的建构
有些词只需一重空间便可构成完整的意境,比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梦江南》(千万恨)、《荷叶杯》(楚女欲归南浦)等。单幕场景以流线式或点面式建构。
流线式指画面随时间流动进行转换,如《菩萨蛮》: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14](第1册,卷一,P3)
抒情女主人公从起床到梳妆的过程,将一个室内空间切割成三幕小场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女子辗转反侧,以致“鬓云欲度香腮雪”的床上空间;随着她“画蛾眉”“弄妆梳洗”“照花前后镜”,画面转到妆台空间;最后切换至试新衣时的房中某处空间。在画面的流变中,女子情绪也发生变化:从慵懒到看“花面交相映”的淡淡喜悦,再是瞥见“双双金鹧鸪”的无限失落。这场生活化的独幕剧每天在上演,女子的孤独与失落、寂寞与哀伤也时刻重复着。
还有《梦江南》:
千万恨,恨极在天涯。山月不知心里事,水风空落眼前花,摇曳碧云斜。[14](第1册,卷二,P212)
画面在时间的渐变中,以类似电影的“淡入”和“淡出”进行切换:当山月升起的场景慢慢淡去后,显现风吹落花的情景,最后缓缓切入清晨水中云影摇曳的情境。这三幕场景的变动,暗示女子在庭院中彻夜枯坐,怨心事不为知,伤花空落,所有情绪积聚成对天涯浪子的“千万恨”;另外与前面《菩萨蛮》场景的间隔时间短暂不同,这三幅画面如慢镜头般进行切换,节奏舒缓。故而两首风格一密丽一疏宕。
流线式建构空间,画面连贯,场景切换符合线性常规和生活逻辑;抒情主人公的愁苦心绪也随时间的延绵不断深化。
与流线式暗含时间不同,点面式则完全关注空间本身。词人从小景物或局部刻画开始,慢慢扩展到对全景的描写或渲染,类似电影中的镜头拉伸。以《荷叶杯》为例:
一点露珠凝冷,波影,满池塘。绿茎红艳两相乱,肠断,水风凉。[14](第1册,卷二,P236)
一颗露珠的特写镜头占据整个画面,清冷、剔透;随着镜头拉远,露珠下的荷叶、叶下水波皆呈现;最后摄取整片荷塘和采莲女。空间扩张也带来感知的变化:由露珠所凝的丝丝冷意到水风吹过的寒意侵人,象征女子的愁苦一点点加深,直到“肠断”。以点面式建构,抒情主人公的情绪在空间的延展中,加深、扩大。
尽管只有一重空间,词人或以时间为主线,或由点及面描摹场景,从不同角度表达抒情主人公情感、思绪的变化,毫无单调感。
(二)双重空间的组合
当单一的场景不能表达更加幽微的情绪时,词人在闺房主空间中,陪衬一重目瞩或意骋之境,增强抒情效果。双重空间的词,主要以嵌入和穿插式组建。
嵌入式,即词人在描写室内空间时,借笔下抒情主人公的耳听或眼观,纳入一重户外场景。典型如《更漏子》:
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 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14](第1册,卷一,P104)
玉炉缭香、红烛淌泪的画堂里,“眉翠薄,鬓云残”的女子辗转难眠,倾听窗外雨打梧桐、滴沥台阶。嵌入的户外声景,催化了“正苦的离情”,也暗示她一夜未眠;其疏淡的风格,冲淡了上片的浓丽(5)唐圭璋:“浓淡相间,上片浓丽,下片疏淡。”(参见唐圭璋《唐宋词简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两重场景构成内外相承、浓疏有致的艺术境界。
再有《南歌子》:
扑蕊添黄子,呵花满翠鬟。鸳枕映屏山,月明三五夜,对芳颜。[14](第1册,卷一,P168)
前三句用类似电影的长镜头展现一场景:闺房中,女子精心妆扮,铺开屏风、摆好鸳枕。后两句,以类似仰角镜头,摄入窗外一轮圆月,映照女子的“芳颜”。内外两重空间一衔接,就如蒙太奇“激发出单独的画面、镜头本身并不一定具有的涵义”[18](P207):做好一切准备去等待的人没有来;月圆人不圆,谁来抚慰孤寂的灵魂?
以嵌入式构建,一方面拓宽了室内空间,增加了空间的层次性和立体感;另一方面,凸显居室环境的冷清与封闭,深化闺中人的寂寞与伤怀。
如果说嵌入式主要在室内主场景中纳入“耳听”或“目瞩”之境,那么穿插式则在“身处之境”中组接一重“意骋之境”,两重场景间有逻辑先后。如《女冠子》:
霞帔云发,钿镜仙容似雪,画愁眉。遮语回轻扇,含羞下绣帷。 玉楼相望久,花洞恨来迟。早晚乘鸾去,莫相遗。[14](第1册,卷一,P187)
起拍三句,身着道服、仙姿灵质的女冠对镜细描愁眉;忆起往昔“回扇遮语、含羞下帏”;于是陷入长长的思念里,希望从此双宿双飞。尽管这首词多解释为女冠和女伴彼此牵挂和祝愿,[14](第1册,卷一,P189)但回忆场景里,女子的娇羞神情分明对着心上人流露;这重“意骋之境”也使当下“久相望”和“恨来迟”的情境和心绪合理化,就如周济评论:“《花间》极有深厚气象,如飞卿神理超越,不复可以迹象求矣。然细绎之,正字字有脉络。”[19](P5)
组建内外结合、远近相辅或虚实相生的双重空间,让眼前空间承载不了的苦闷,由外景或虚景来接纳;看似突兀的情绪,有了逻辑可究。
(三)多重情境的组建
温词中占主流的还是多重情境的作品。词人选用两种或以上的方式,将多重空间进行组合,建构色彩斑斓、变幻多姿的艺术境界,抒写千千情结。
这些多情境的词中,“嵌入+穿插”型最多,有十余首。现以《蕃女怨》为例:
碛南沙上惊雁起,飞雪千里。玉连环,金镞箭,年年征战。画楼离恨锦屏空,杏花红。[14](第1册,卷二,P234)
随着画楼中空对锦屏思妇的遐想,出现了黄沙连天、飞雪千里、惊雁离窜的荒漠边关,征人年年苦征战的场景。因了思绪,绮罗香泽的闺房空间直接延展到苍凉雄阔的塞外,以两个风格迥异的空间在同一首词中邂逅、碰撞产生的张力,抒写思妇深深的离愁和担忧。最后切入窗外的红艳杏花,热烈、美好、平和、富有生机,既映衬室内疏离、冷寂的气氛,也与塞外的苦寒、战场的残酷形成对比。
“叠映+嵌入”也是运用较频繁的建构方式。叠映,即将不同时空的场景重叠在一个画面呈现,两幕场景之间没有间隔和停顿。典型如《酒泉子》:
罗带惹香,犹系别时红豆。泪痕新,金缕旧,断离肠。 一双娇燕语雕梁,还是去年时节。绿杨浓,芳草歇,柳花狂。[14](第1册,卷一,P126)
女子看着罗带所系的红豆,想起离别时情郎相赠;当时的新金缕,如今已陈旧;去年燕语呢喃时节,两人正相守相伴,可当下形只影单。三幕不同时空的场景在一处溶合,道出离别已久、相思无解;而且强烈的对比,更凸显物是人非的伤怀之感。末三句,纳入窗外暮春景象,绿杨渐浓、芳草已歇,柳花乱飞,“光色深暗,画面迷离,映衬出女子意乱情迷的黯淡相思心境”[14](第1册,卷一,P128)。
更有不少词,三四种手法并用,空间组合犹如万花筒般丰富,比如《菩萨蛮》:
玉楼明月长相忆,柳丝袅娜春无力。门外草萋萋,送君闻马嘶。 画罗金翡翠,香烛销成泪。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14](第1册,卷一,P42)
“嵌入+穿插+流线”式并用,勾勒一份隽永的情绪:玉楼中一位女子望月长相忆,不觉又梦见送别的情形:柳枝袅娜、芳草萋萋,游子远行后留下若隐若现的马嘶声;接着画面转回到“画罗金翡翠,香烛销成泪”的室内空间,暗示女子未得安眠,方可见蜡烛燃尽;最后窗外的子规啼鸣,惊破残梦。这些场景的组合和转换,既符合“夜中—深夜—天明”的时间渐变,表明女子彻夜沉溺在思念中;也遵循女子的意识活动,由思入梦,梦醒惆怅,细腻地写出女子难以排遣的相思和惆怅。最后纳入的声景,既使空间转换自然流畅,也点出残春时节,象征女子美好的年华又空空流逝,同时呼应前面的梦境。
这些拥有多重情境的词作,纳户外景于室内,融虚景于实境中,叠加、组合成丰富多变的艺术境界;不着过多情语,凭画面拼接所带来的张力,便展现深闺女子欲说还休的缠绵情愫、难以摆脱的抑郁心绪、无法自主的个人命运,含蓄蕴藉,恰如张惠言的评价:“深美闳约。”[20](P7)
三、闺阁空间建构的范式意义
温庭筠对闺阁空间的建构,为当时及后世的词人们提供了一种创作范式。就如王兆鹏先生所说“五代西蜀花间词人,基本上是遵循温词的范式进行创作”[21](P136),像韦庄词“飞卿之流亚也”[22](上册,P33),牛峤词“大体皆莹艳缛丽,近于飞卿”[1](下册,P875),皇甫松词“凄艳似飞卿”[22](上册,P27)。南唐冯延巳紧追其后,使人“观延巳之词,往往自与唐《花间集》《尊前集》相混”[23](P193)。北宋词人造境亦多承袭温词,比如晏殊和欧阳修,鹿麐在《灵芬馆词话》提及:“风流华美,浑然天成,如美人临妆,却扇一顾,《花间》诸人是也。晏元献、欧阳永叔诸人继之。”[17](下册,P1275)至于后来的“周、秦、苏、辛、姜、史辈,虽姿态百变,亦不能超越其范围。本原所在,不容以行迹胜也。”[22](下册,P1312)
具体来说,当时及后世词人们如是承袭温词的构境模式。首先,他们也建构了一个富丽,但幽闭、冷清的室内主空间。像牛峤笔下的“绿云鬓上飞金雀,愁眉敛翠春烟薄。香阁掩芙蓉,画屏山几重”(《菩萨蛮》),“金雀”“香阁”“画屏”等,共构奢华的居室;但闺房深掩、屏风遮挡,尤见幽深;闺中人居此,愁眉难解,孤独难言。还有“绣衾香冷懒重薰”(韦庄《天仙子》),“玉楼朱阁横金锁”(晏殊《木兰花》),“小院深深门掩亚。寂寞珠帘,画阁重重下”(欧阳修《蝶恋花》)等,这些词句所构筑的闺房场景无不如此。
其次,词人们也建构了一重“目瞩”或“意骋”之境,来拓展闺阁空间。比如韦庄的《应天长》(绿槐阴里黄莺语),以绿槐成阴、黄莺啼语的目瞩之境,凸显闺房幽闭和冷寂的气氛;以“碧天云”般飘渺空阔的梦境,点出女子相思之深,也象征心上人行踪无定;秦观的“困倚危楼,过尽飞鸿字字愁”(《减字木兰花》)句,倚楼的女子看鸿雁飞过,想象传来的书信里,每一个字都写满愁绪。眼观与意想之境叠加,深化这无人问的“天涯旧恨”。
另外,众词家也将不同的场景,以各种方式进行组合,建构完整的情境。以冯延巳的《酒泉子》为例:
深院空帏,廊下风帘惊宿燕。香印灰,兰烛小,觉来时。 月明人自捣寒衣,刚爱无端惆怅。阶前行,阑畔立,欲鸡啼。[24](P14)
廊下的风帘惊起宿燕,也唤醒思妇;于是画面自然过渡到闺房中香灰积落、烛火将近的场景;又嵌入插月下捣衣声景,巧妙地将思妇的“无端惆怅”和“捣衣者”的相思叠加在一起,情感由个体转向普遍,更为深沉;最后镜头转向阶前和阑畔,不同于温词中的美人多时静止于一处,冯词中的女子开始试图主动拓展空间。
在承袭的基础上,这些词人们也丰富并拓展温庭筠的构境式。一方面,词人们对室内空间的描摹,渐改温词中的精雕细刻;多择一二意象,简单勾勒。如晏殊只用“罗幕清寒”“斜光到晓穿朱户”(《鹊踏枝》),“碧纱秋月,梧桐夜雨”(《撼庭秋》)等,将珠光宝气的闺房空间升华为“意余言外的富贵‘气象’”[25](P89)。同样周邦彦的“小帘朱户”(《锁窗寒》),苏轼的“柳丝搭在玉栏杆”“晚晴台榭增明媚”(《虞美人》)等,寥寥数语,构筑居室环境,脱尽繁琐,也使词境无限雅化。
另一方面,他们将笔力多集中在辽阔外景或虚境上。典型如欧阳修的《踏莎行》:
候馆梅残,溪桥柳细。草薰风暖摇征辔。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 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楼高莫近危栏倚。平芜尽处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26](卷一,P57)
主场景不脱闺房,但笔墨甚少;全词以候馆送别的回忆场景切入,再叠映远行人“楼高莫近危栏倚”的嘱咐,又纳平芜尽头的春山,想象行人更在春山外;思念愈加浓烈,而空间也延绵向无尽的远方。淡雅清新、开阔疏朗,“极柔极厚”[27](P64)。晏殊的《鹊踏枝》(槛菊愁烟兰泣露)、辛弃疾的《祝英台令·晚春》(宝钗分)也以类似的方式建构。
此外,词人利用时间的重复,来营造复沓的空间,增强抒情深度。像韦庄的“夜夜绿窗风雨,断肠君信否”(《应天长》),每夜重复的户外声景,暗示女子一直处在没有承诺的等待里,直至绝望,“凄艳入人骨髓”[22](上册,P33)。同样“几回魂梦与君同”(晏几道《鹧鸪天》),“年年陌上生秋草,日日夕阳到楼中”(晏几道《鹧鸪天》),“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辛弃疾《祝英台令·晚春》)等,也都借时间而叠加了无数的空间,相思愈显浓烈、缠绵。
还有词人们营造的“意骋之境”除了温词中常出现的梦中、回忆、想象之境外,增加了幻境和历史场景,进一步拓展空间。比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穿插“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28](P55),将闺房延伸向广阔的历史空间;也为柔婉的惜春、伤春情怀中注入深沉、悲壮的元素。晏几道建构了“碧落秋风吹玉树。翠节红旌,晚过银河路。休笑星机停弄杼。凤帏已在云深处”(《蝶恋花》)这样的天上幻境,为词作增添了浪漫意味。吴文英《思佳客·赋半面女骷髅》中的幽冥之境,愈显凄迷与冷寂。词人们对温庭筠构境方式的沿袭与发展,便也是词的发展。
综上所述,温庭筠为词中的抒情女主人公构建了一个以室内空间为主,部分所见或亲历的户外场景以及所思、所想、所梦的虚境为辅的闺阁空间。词人为突破室内空间的狭隘和封闭,实现审美空间的多样化,采用流线、点面、嵌入、穿插、叠映等方式,对多重空间进行拼接、组合,建构成一幕幕内外结合、远近相辅、虚实相生的艺术境界,既实现了审美空间的张力,又深化情感。这种空间建构方式,为当时及后世的词人们,提供了一种创作“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