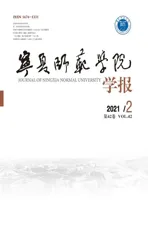地域文化视域中的延安文学经验透视
——评王俊虎《延安文学经验的当代传承——以陕西文学为中心》
2021-12-31王晶
王 晶
(延安大学 文学院,陕西 延安 716000)
延安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最重要的板块之一,它与“五四”文学深刻影响了20世纪前后半叶中国文坛。启蒙主义光辉照耀下的“五四”文学倡导发现、唤醒人,现实主义引导下的“延安”文学贴近人、改造人。自延安文学诞生以来,相关研究不断推进,在各个时代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20世纪80年代以来延安文学研究正式进入学理化阶段,如今已有一大批丰硕的研究成果显现延安文学的独特魅力。与此同时,随着近年来地域文化、民俗研究进入热潮,各地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地域文学研究成果,陕西亦是如此。然而,较少有人系统化、学理化地将陕西文学与延安文学联系起来加以全面地梳理和概括。王俊虎新近出版的学术专著《延安文学经验的当代传承——以陕西文学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对延安文学经验在陕西文学发展中的承传状况进行系统性、创新性地梳理,深入解密陕西文学与延安文学的紧密关系,并将之置于后现代语境中,思索陕西文学当下发展困境和未来突破方向,使研究者们耳目一新又发人深省。
一、视野宏阔
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任何形态的文学都不是一座孤岛,延安文学、陕西文学亦是如此。王俊虎《延安文学经验的当代传承——以陕西文学为中心》一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即是其宏阔的学术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界逐渐转向“纯文学”研究,虽然近年来文化研究热潮对纯文学内部研究带来不小冲击,但文学内转的倾向始终未曾改变。文学研究要么孤芳自赏成为小部分圈内人的专长,要么泛化为社会文化研究失去自身学科特色。可喜的是,在王俊虎的新作中,既保持了文学研究的学理严谨性,又采用了与文学紧密相连的宏观研究视野,他将延安文学与陕西文学研究置于文学、历史、地域、经济、社会、政治等多维视野中考察,增强了文学研究的丰富性和生动性。
延安是陕西的一部分,延安文学产于延安,便不可避免地打上“延安”烙印、染上陕西气味儿。陕西文学源远流长,却随着北方整个文化的没落而在现代失去文坛话语权,是延安文学经验在当代再次激活了陕西文学振兴。王俊虎从地域文化视域对陕西地域古来已久的文化和文学进行了细致梳理,超越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边界,追根溯源陕西古代地域文化文学,发现了古已有之、至今仍在影响陕西文人“将济世理想、道德修养、著书立说有机结合”[1](P32)的文学传统。在历史、地域、文学三重学科烛照之下,王俊虎接着又对20世纪陕西文学做了阶段性、地域性考察。王俊虎指出,陕西文学在20世纪虽然并没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精彩开端,但平常无奇的开端并不注定此后的陕西文学发展平庸。相反,20世纪后半叶陕西文学在延安文学经验的滋养中大放异彩,最终形成令国人瞩目的“陕军东征”的壮阔景象。王俊虎在此还作了生动形象的譬喻,他将20世纪陕西文学比喻为“一部带有浓厚现实主义风格的长篇小说”[1](P25),开端并不哗众取宠,实是传世的鸿篇巨制,既将20世纪陕西文学整个发展特征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又暗示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在20世纪陕西文学发展中的显赫位置,一语双关。作者还聚焦于延安这一地域的历史与现实,对整个陕北古代、近代的政治、军事、文化整合梳理,指出“古代的陕北是铁与血、剑与火所锻铸的高原”文化的史诗性,揭示未经现代化洗礼的边塞小城荒凉、野性、粗俗、质朴的文化底色。简而言之,作者并不以单一的视角局限于某一方面的文学研究,他更多地将延安文学与陕西文学研究置于历史、地域、文化多重视域中考察、分析,学术视野十分宏阔。
二、风格独特
文学一方面具有自身独特的审美属性,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脱离世俗生活。文学的社会属性要求文学研究者在研究文学的过程中决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王俊虎在其新作中始终坚持文学的审美性和社会性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在具体作家研究、文本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生态批评学理论分析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影响下的陕西文学以及延安文学当代经验。
延安文学的生成不是偶然的结果,而是特定时代、特殊环境下的产物。因此,在研究延安文学时,必然不能以当下的文学标准去简单臧否延安文学。应该尽可能地将研究投入到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去体会和感受。历史虽然无法彻底还原,但研究者们拥有重返历史现场的可能性。如“地域文化氤氲中的20世纪陕西文学”一节中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客观性,对延安文学开创、发展、繁荣、进行了历史性论述,援引《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多篇报道从史料角度展示延安当时的文化生态环境,并分别按照不同文学体裁分类展现延安文学基本面貌。延安文学固然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然而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去,在战时艰苦的后方环境映衬下,延安文学无疑成为引导民众前行的一面精神旗帜,亦成为那个年代最真实的时代记录册。延安文学成为历史,延安文学经验却仍烛照当代文学前行。十七年时期延安文学经验指导下的柳青、杜鹏程的小说《创业史》《保卫延安》成为闪耀陕西文坛的双子星座,是对延安文学经验成功运用的有力佐证。作者还对新时期陕军东征这一文学现象进行仔细梳理,充分肯定1985年陕西作家协会在延安、榆林召开的“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的历史意义。王俊虎认为正是这一促进会的召开鼓舞了陕西作家动手创作长篇小说、从而使得陕西摆脱“文学大省无大作”的尴尬处境。陕西至今仍被视作现实主义创作重镇,作者认为这不仅源自陕西文人古已有之的史诗性情结与品格,更源自延安文学现实主义创作经验的积淀。无论是柳青、杜鹏程,还是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乃至叶广芩、杨争光,还有2019年斩获茅盾文学奖的陈彦,无一不受延安文学现实主义经验的影响。延安文学当代经验烛照下的陕西文坛形成了陕西第一、二代文人朴实、厚重的现实主义风格。然而随着新世纪文化生态骤变,王俊虎也指出部分陕西作家缺少将文学视为宗教、事业的热情与虔诚,缺少介入生活的勇气,究其原因还在于作家缺少精神之“钙”。追及当下,想要将文学从时代边缘拉回重要位置,该书多次提到当代作家要有自己的风骨与情怀,汲取延安文学经验之“钙”必不可少。
三、人民立场
文学精神往往通过具体的作家、作品得以传承,王俊虎特意在书中留出专章讨论陕西文学教父柳青在延安文学与陕西文学承接中的重要衔接作用。称柳青为“陕西文学教父”,实至名归。在陕西现代文坛经历难挨的空白尴尬之后,柳青以其强劲、质朴、厚重的写作风格为陕西文坛开立影响其后大半个世纪的现实主义写作风格。作者给予柳青高度评价,认为其不仅“以他的言传身教,影响和启发了陕西当代作家群的文学活动”[1](P121),更遗留给陕西文坛宝贵的延安文学经验。王俊虎对柳青在延安时期的文学活动进行考察,通过研究延安时期柳青的《一个女英雄》《地雷》《在故乡》《喜事》《误会》《种谷记》等作品,总结柳青延安时期形成的以强烈的政教性、浓厚的大众性、多样的开放性、质朴的生动性为主的现实主义创作特征。柳青不仅是延安文学的忠实践行者,他自身就是延安文学建构者之一。柳青将自己融入延安文学运动中,自觉、主动、积极地上山下乡,真正深入田间地头化身为农民,讲方言、写农事、抒民情,成为农民忠实的代言人之一。柳青并没有因为离开延安而放弃延安文学经验的承传,而是在此后始终践行延安文学精神,以身作则扎根皇甫村14年,为文学事业奋斗终生。王俊虎指出,从本质上讲,柳青是一位地道的“乡村知识分子”[1](P137),这一评价抓住了作家柳青最主要的身份特征,无论从实际生活还是文学创作来看,柳青一生扎根土地、书写土地,是土地的代言人,是真正的地之子。文学界有学者对《创业史》中梁生宝身上散发的理想主义激情持怀疑态度,王俊虎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梁生宝身上寄托着柳青对社会主义新式农民的期待和想象,梁生宝形象本身就寄寓着作家对未来社会主义新人的完美想象,因此带着理想化的色彩,但这并不能成为怀疑作者创作激情的理由。柳青离开了这个世界,柳青的文学精神遗产永留世间。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邹志安等作家在他们的创作中继承柳青文学精神,陕西文学之所以农村叙事赓续、现实主义创作不止,与柳青文学精神的发扬光大不无关系。
除了在浩瀚文海中发掘柳青这个耀眼的“贝”以外,王俊虎还对陕西文学评论家也进行了精准点评。王俊虎对陕西四代文学评论家做了纵向梳理和横向比较,分析了四代评论家不同的评论风格,挖掘出他们身上共有的责任感、使命意识、乡土情结和敬业精神。通过横向对比发现四代评论家共同坚守的“人民性”。重拾“文艺人民性”是王俊虎本书论述的又一重点。作者通过对“人民性”一词追根溯源,梳理“人民性”内涵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发展演变,并针对当下陕西文学发展提出理性对待“人民性”复归的问题,进一步提出文学评论家应在现代性视野中坚持人民性的倡议,这是符合当下陕西文学发展实际的肺腑之言。
四、问题意识
学术研究贵在有问题意识,该书多处展现出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思辨气质,给阅读者时时带来思想的启示。在每一章的末尾作者都会立足当下学术研究现实,提出自身对学术发展状况的分析判断,对一些学术不良现象直言不讳,显示出其严谨、刚直、求实的学术品格。
王俊虎首先一针见血地指出陕西文学发展中的“缺钙”问题。时代推动文学前进,文学反映时代风尚。21世纪以来,陕西文学也跟随时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多样化的创作题材、创作手法丰富着陕西文学向来朴实的面孔,却难以再出现陕军东征时的辉煌气势。王俊虎将当代陕西文学发展置于新世纪社会巨变背景下,较为客观地分析陕西文学发展疲软态势之因,指出“新世纪陕西文学亟须补钙,以祛除陕西文坛的萎靡、庸俗、软弱之风,重振陕西文学雄风。”[1](P61)王俊虎不仅提出问题,还根据陕西当下文坛现状提出治病良方,即从延安文学经验中寻找支撑新世纪陕西文学发展的精神支柱。在第二章谈及民族形式的论争时王俊虎提出“假如没有抗日战争,民间文艺能否得到发掘”的思考[1](P89),发人深省。无论古今中外,我们不能否认“纯文学”的耀眼光芒,但同样无法否认文学必须有所倚恃才能持久发展的事实。我们所追求的文学,几乎和爱情一样带有某些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神秘感。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文学家、不同读者对文学都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可要真正描摹出文学的固有面貌,应该说难上加难。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历史是碎片化的,从某些程度上来说文学亦是如此。文学难以与政治、经济相剥离,倘若没有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的有力推行,底层老百姓如吴满有、韩起祥是难有机会进入文学史叙述的。由柳青论及陕西作家群体时王俊虎提到一个重要特点:大多数作家来自农村,都写过农事,都曾以饱满的情感关注底层大众、弱势群体的生存,最终形成深沉厚重的写作风格。陕西作家确乎有一种底层追寻的气质,无论是路遥、贾平凹、高建群,还是陈彦,他们都将目光投注于底层,但他们却又不同于刘庆邦笔下近乎令人绝望的底层描述,陕西作家笔下的底层是温情的、充满希冀的情感世界。对于文学界出现创作与批评的不良现象,王俊虎建议批评家应当在批评实践中时时“三省己身”,坚持原则与社会各界共建和谐、纯洁的文艺批评环境,共同抵制文艺批评中媚俗、庸俗、吹捧等不良现象。
商业化大潮裹挟着社会的每一份子,文学创作者亦不例外。陕西第三代、四代作家在新时代洪流下如何继承传统而又不失特色?如何重振陕西文学未来?路在何方?这不仅是对作家个人的灵魂拷问,更是需要每一个陕西文人寤寐思索的问题。城镇化迅速改变古老中国的面貌,如今的乡村与费孝通《乡土中国》呈现出的乡村面貌已有不同,在城镇化大面积推开的中国今日,陕西作家如何再将一腔乡情成功倾注笔端?每一个硬币都有两面,乡土成就了一大批陕西文人,却也禁锢了一批文人。正如同延安文学经验曾使得陕西文学走向辉煌,也不可避免对作家的视野带来禁锢。延安文学经验在当下的承传与发展离不开“经”与“权”的妥善处理,正如不断发展、完善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延安文学经验亦不是一个封闭的物象。新时代里,“经”与“权”相结合,将延安文学经验灵活应用到陕西文学发展中,陕军或可重征。不止于此,在整个文学被边缘化的今天,向延安文学经验汲取精髓,文学或有重返瞩目地位的可能。
属于一个时代的延安文学远去了,但延安文学经验却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从未结束,永远都是过去完成进行时。真理从不是静止的、绝对的,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只能保持无限接近,在具体的实践中不断加深其认识。每一个文学人都矢志不渝追求文学的理想,正因为如此,文学才更加魅力四射。《延安文学经验的当代承传——以陕西文学为中心》正是陕西文学、延安文学经验研究路途上的一颗烁烁发亮的新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研究问题的角度,刷新读者对延安文学与陕西文学的认知。
《延安文学经验的当代承传——以陕西文学为中心》的优长之处远不止于此,该书堪称一部延安文学经验的当代启示录,作者在书中妙笔生花,新见迭出,发人深省。读者从中不仅能够进一步认识到延安文学与陕西文学的承传关系、陕西人文底蕴、陕西文学生态环境,更能感受到作者宏阔的学术视野、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深厚的学术功底、强烈的问题意识以及缜密的逻辑思维。优秀论著总是说不尽道不完的,一千个读者能从其中获得一千种不同的阅读感受和启示,个中精妙,用心的读者自能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