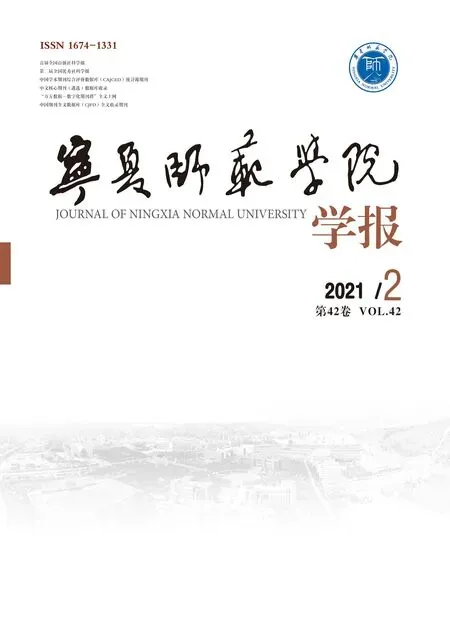《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编纂再议
2021-12-31刘炳辉
刘炳辉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一、《播芳大全》与《四六丛珠》的编者并非同一人
今藏国家图书馆的宋刻本《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卷(以下简称《播芳大全》),由“衢山精舍叶棻子实编,富学堂魏齐贤、仲贤校正”,是一部大部头的宋代文人总集。全书收录表、启、制辞、奏状、奏札、封事等三十三种应用文,堪称公文写作典范。虽然内容冗杂,但是其中保存了许多宋人早已散佚的文章,具有重要的文献和辑佚价值。比如卷一王安石《贺降皇太子表》和卷五十五苏轼《与苏子容四帖》,正是靠此本才得以保全。
《圣宋名贤四六丛珠》(以下简称《四六丛珠》)现存最早为明抄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前有吴奂然序言一篇,目录后有“建安陈彦甫,刻梓于家塾”两行字,从第二卷开始每卷前有“建安叶子实”或“建安叶蕡子实编”一行字。
由于《四六丛珠》与《播芳大全》从书名和编纂者姓名,到编纂体例、刊刻地和刊刻时间,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加之叶蕡其人履历难考,经常有人将两书的编者混为一人。仔细追索文献,我们不难发现蛛丝马迹。宋人吴奂然《四六丛珠序》作于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明人王宠记云:“此书为建安叶子实编,庆元丙辰锦溪吴焕然序。按庆元为宋宁宗年号,然则著者想亦同时之人矣。”[1] (P1278)按照吴奂然作序的时间,王宠推断《四六丛珠》的编者也是同时代人,自是没有问题。之后,《四库全书总目·四六丛珠汇选》云:“前有明嶅序,称宋季叶氏采当代名家汇集成编,名曰《四六丛珠》。”[2](P1165)明嶅即明代王明嶅,《四六丛珠汇选》是《四六丛珠》摘录之本。清人陆心源言《四六丛珠》“一百卷,旧钞本,兼牧堂旧藏,宋建安叶蕡子实编,自来藏书家罕见著录,惟《天一阁书目》《元赏斋书目》有之……叶蕡仕履无考,即与魏齐贤同编《播芳文粹》者”[3] (P618)。陆氏因为“叶蕡仕履无考”,轻而易举就将《四六丛珠》与《播芳大全》的编者混同为一人。随后,清人莫有芝著录云:“《圣宋名贤四六丛珠》一百卷,宋叶棻编。明写本。前庆元丙辰吴奂然序。又有伪王宠跋。”[4](P1528)近人傅增湘亦著录:“《圣宋名贤四六丛珠》一百卷,宋建安叶棻子实编。目后有‘建安陈彦甫刻梓于家塾’二行。首有庆元丙辰九日锦溪吴奂然景仲序,有明王宠手跋”[1](P1278)。莫、傅二人虽然对王宠跋文的真伪看法不一,但是直接将《四六丛珠》的编者定为“叶棻子实”。仝十一妹还认为“蕡、棻字音相近,叶蕡、叶棻无疑指同一人”[5](P8)。于是从陆心源开始,有学者逐渐将《播芳大全》的编者叶棻与《四六丛珠》的编者叶蕡混为一谈。笔者认为文献记载很清楚,《四六丛珠》的编者是“叶蕡”,而《播芳大全》的编者是“叶棻”,并非同一人。其他理由将在下文解释。
二、叶棻与叶蕡
尽管叶棻与叶蕡仕履难考,所存文献资料也严重不足,但是仔细翻检史料,我们依然可以获得一些线索。
(一)叶棻
叶棻其人,史志文献并无详细记载。据《福建通志》记载,福建建安县人叶棻(今福建省建瓯市),于建炎二年(1128)中进士:“建炎二年……建安县叶棻”[6](卷三十四P2)。同书卷二十三:“晋江县知县事……叶棻……绍兴间任”[6] (卷二十三P43)。《八闽通志》卷四十九:“建炎二年……李易榜叶棻”[7](P83),同书卷三十二:“晋江知县……绍兴间任”[7](P91)。《泉州府志》:“晋江知县……绍兴间……叶棻”[8] (P60)。从以上方志记载来看,所记应是同一人,即建炎二年进士叶棻。
另外,《播芳大全》卷首《本朝名贤总目》有“叶棻,字德明”者,虽然由于史料有限,未知是何人,但显然不是本书的编者。宋人杨万里(1127—1206)有诗《赠都下写真叶德明》[9] (P1041),这两个叶德明很可能是同一人。又《福建通志》卷二十三记载:“长泰县……主簿……叶棻……以上俱宝祐间任”[6] (卷二十四P26)。宝祐(1253—1258)是宋理宗的年号,此叶棻显然不是《播芳大全》的编者。
(二)叶蕡
据史料记载,宋代确有叶蕡其人,而且不止一个。《重修扬州府志》:“新化县开元观……淳熙丁未年(1187),知县叶蕡再建”[10](P14)。根据吴奂然为《四六丛珠》作序的时间庆元二年(1196),淳熙年间新化县令叶蕡与《四六丛珠》的编者叶蕡生活的时代相近,有可能是同一人。《处州府志·选举志》:“元祐戊辰(1088)……叶蕡”[11](P28),此叶蕡远早于《四六丛珠》的编定时代,显然不是《四六丛珠》的编者。又,万历刻本《扬州府志·宋秩官纪》:“(宋人)度宗……杨承议、叶蒉,有惠政,俱兴化知县”[12](P41)。宋度宗即赵禥,于1264至1274年在位。虽然“蒉”与“蕡”存在刻工误刻的可能,但是此人肯定也不是《四六丛珠》的编纂者。(明人)凌迪知《万姓统谱》记载:“叶蕡,字仲实,建安人,为赣县尉,……再起为宣城丞,调奉新令,不赴,少尝著《易传》”[13](P700)。《嘉靖建宁府志·选举志》亦载:“元祐六年(1091)……叶蕡,字仲实,《通志》‘蕡’作‘蒉’,《旧志》作建安人”[14](P47),之后的内容与《万姓统谱》一致。而《建宁府志》卷二十作:“元祐六年马涓榜……黄蕡”[15](P16)。《八闽通志》卷四十九作:“元祐六年……黄蒉”[16](P79),同书卷六十五《人物志》作:“黄篑,字仲实,蒲城人,……震曾孙也……蕡少慕之,元祐中登第”[16](P53),以下内容与《嘉靖建宁府志》和《万姓统谱》同。由于“蕡”、“蒉”、“篑”与“篑”非常形近,刻工很容易弄错,因此笔者推断,《万姓统谱》和《嘉靖建宁府志》中的“叶蕡仲实”很可能是“黄蕡仲实”误刻所致。
许开《播芳大全序》云:“予往者守官□阳,于书市经从为款,二君走书言其大概,属予序之。予不得辞。绍熙改元庚戌八月朔”[17](P4)。绍熙元年(1190)是宋光宗赵惇的年号,结合以上材料,符合《播芳大全》编纂条件的似乎只有建炎二年(1128)中过进士,并在绍兴年间(1131—1162)任过晋江县令的叶棻。从时间上来看,建炎二年进士叶棻存在与同时代许开交际往来的可能性,又具备编纂的学识与经济能力。另外,从编纂体例和署名“衢山精舍”来看,叶棻子实应该也是读书人。因此笔者判断,建炎二年进士叶棻很可能就是《播芳大全》的编者叶棻子实。
让我们再回到前文提出的《播芳大全》编者叶棻与《四六丛珠》编者叶蕡并非同一人的问题。宋均有记云:“于苕溪得交王君者香,者香出其舅叶子实先生所编《播芳文粹大全》见示,因言是书初编一百卷,刊行后一时纸贵。……乃复广搜旁辑,成百五十卷,未及梓而卒。……嘉定三年(1210)夏,唐山宋均记。”[18](P73)嘉定三年(1210)是宋宁宗的年号,今存宋刻本《播芳大全》不载宋均此记,幸得在瞿氏铁琴铜剑楼一百五十卷本《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文后保全。此本文后还有清人孙均和姚椿的题跋,清人丁国钧据此有跋抄本。假设两书的编者是同一人,那么叶棻的外甥王者香向宋均介绍《播芳大全》,为什么不言及舅舅生前还曾编刻过另一本书《四六丛珠》,毕竟此时《四六丛珠》早已出版了。而且根据许开为《播芳大全》作序的时间绍熙元年(1190),后出的庆元二年(1196)吴奂然《四六丛珠序》也未提及《播芳大全》。种种问题摆在眼前,不免令人疑窦丛生。真实情况应该是叶棻子实根本就没编纂过《四六丛珠》,因为《播芳大全》刊刻后“一时纸贵”,他正在忙于增补,无暇顾及其他,“成百五十卷,未及梓而卒”。何况就广告效应来说,叶棻也没理由放弃一本畅销书而另起炉灶。
至于《四六丛珠》,陆心源称“其书剽窃割裂,体例纷如,疑当时书坊所刊”[3](P618)。一方面陆氏认为《四六丛珠》的编者也是叶棻,另一方面又怀疑“其书剽窃割裂”,陆氏显然也很矛盾。现在来看,《四六丛珠》的编纂,很可能是叶蕡在畅销书《播芳大全》的基础上,经过抄袭和增删而成,所以仓促之间泥沙俱下,“体例纷如”,漏洞百出。当然,牟利是书商的本性,也不排除书商陈彦甫假托与叶棻之名相仿的“叶蕡”,故意混淆视听。
三、关于《播芳大全》的编纂成书
“乃复广搜旁辑,成百五十卷,未及梓而卒。”宋均记文明确告诉我们,叶棻生前已编定一百五十卷本《播芳大全》,“未及梓而卒”。根据后世各种抄本来看,叶棻去世后,一百五十卷本也曾刊刻过,可惜没有保存下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既然百卷本是由魏齐贤、魏仲贤校订刊刻的,那么同样的工作自然是轻车熟路。或许是因为叶棻去世,无人支付刊刻费用,所以在他们对叶棻编订的一百五十卷本进行校定刊刻后,署名先后顺序也发生了变化。以至于影响了后世《播芳大全》的署名方式,《四库全书总目》著录《播芳大全》即是魏齐贤在前,叶棻在后[2](P1698)。今人祝尚书《宋人总集叙录》、王继宗《永乐大典常州府清抄本校注》等,著录此书也是大同小异。
自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开展熙宁变法之后,北宋重诗赋策论的科举考试格局虽然已经彻底改变,经义也成为科考首选,但是读书人高中进士之后,依然需要撰写各种庞杂的形式不一的公文写作。一些目光敏锐的士人和书商,正好利用这一社会需求,编纂了公文写作体例书,用以实践指导。这类书,往往收集各种名家奏议、表启、书简、祝文等,内容丰富繁杂,应有尽有,极大地满足了官员的日常公文写作。另一方面,自北宋建国后,经济中心不断南移,文化也随之南移,尤其是福建、四川一带,文化特别发达。绍兴八年(1138),福建人贡举考试独占前三。有宋一朝,福建进士约占宋代进士总数十分之一多。正是有着这样的历史背景和读书氛围,《播芳大全》在官员众多的福建之地造成一时洛阳纸贵,自是不足为奇。这也是百卷本《播芳大全》大卖后,叶棻再度增补,使之成百五十卷的原动力。笔者认为,公文写作书大受欢迎,还有一层原因。宋代开科取士太多,造成许多进士无官可做,长期得不到升迁,致使一些士子开始另谋生路。于是,一种名曰师爷的新职业诞生了。这些师爷,无须高中进士,举人或秀才出身,甚至识文断字即可,他们经过专业的公文学习和写作训练之后,更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加之薪资不高,高层次的官员也能负担得起。于是,这类公文写作书,自然为中下层读书人所喜,特别是师爷。
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事业普遍发展的时代,无论官刻还是私刻,都很发达。由于各地的自然和人文条件不同,其繁荣程度也不同。南宋时期,形成了四川、浙江和福建三个各具特色的刻书中心。
福建刻书,尤以建阳最为精美。建阳地处闽北武夷群山中,竹木茂盛,造纸事业发达,为雕版印书提供了有利条件。“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朱元晦《嘉禾县学藏书记》云:‘建阳版本……者,无远不至。而学于县之学者,乃以无书可读为恨。’”[19](P127)据《方舆胜览》记载,建阳刻书主要集中在麻沙镇和崇化坊,闽人“以无书可读为恨”的风气,更是促进了此地刻书业的繁荣。叶德辉《书林清话》也记载,建阳有麻沙书坊、江仲达群玉堂、毕万裔宅富学堂、魏仲举家塾、陈彦甫家塾、魏仲立宅、刘日新宅、刘叔刚宅等十多个书坊和家塾。建阳刻的书被称作“建本”或“麻沙本”,虽然不乏佳本,但是这里盗版书猖獗泛滥,往往会让人降低对建本的信赖。刊刻《四六丛珠》的书商陈彦甫也是建阳人,抄袭《播芳大全》自然不足为奇。
《四库全书总目》云:“棻字子实,自署南阳人。考宋南渡以后,巨鹿南阳皆金地,殆以魏氏本出巨鹿,叶氏本出南阳,偶题郡望,非其真里籍也。”[2](P1698)《百家姓新解》亦云:“叶姓望出南阳郡、下邳郡”[20](P509),可见叶棻自署南阳应是郡望。清人叶德辉《书林清话》有“毕万裔宅富学堂”[21](P84),《善本书室藏书记》卷十四和《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二也有“毕万裔宅刻梓于富学堂”的记载。《巨鹿魏氏宗谱》卷七《书坊下历潘公派下世系》载:“第四世,潘公,成公之子,行流二,(从麻沙)迁居(崇化)书坊下历。娶杨氏,继娶陈氏,生子一:齐贤。”[22](P222)《元和姓纂》云:“周文王第十五子高封于毕,裔孙万仕晋,封于魏……为秦所灭,子孙以国为星”,“曲阳侯、汉巨鹿太守歆,居巨鹿”[23](P1191)。因此,《四库全书总目》“魏氏本出巨鹿”,“偶题郡望”的推断是正确的。“毕万裔”与“巨鹿”一样,应是魏氏以始祖或郡望自称,魏齐贤为建阳人(今福建南平市建阳区)无疑。
另外,既然“富学堂”在建阳,那么,许开序云“余往者守官□阳”,则序言所脱之字应为“建”,原本猜测脱“南”字的想法也就站不住脚了。从个人名字和书名来看,魏齐贤、魏仲贤与刻有《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集》和《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文集》的魏仲举也应该有很大的关系。魏齐贤和魏仲举都是建阳人,与他们大有关系的魏仲贤,极可能也是建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