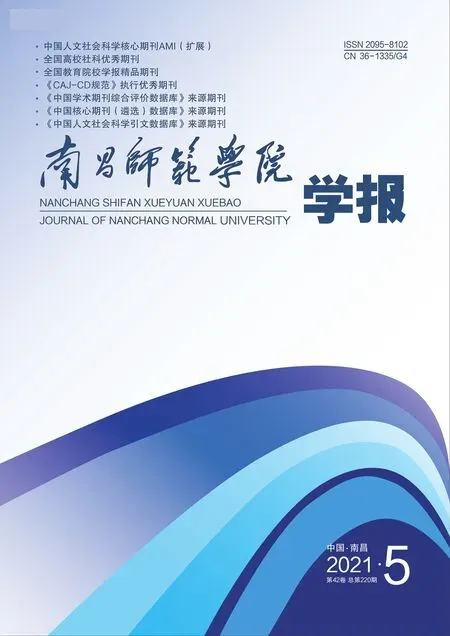托尼·莫里森作品中的历史意识
2021-12-31张纪鸽
张纪鸽
(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陕西延安 716000)
一、引 言
托尼·莫里森是活跃于当代美国文坛的一位巨星。自1970年至今,莫里森共有10部小说问世,由于“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使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充满活力”[1],莫里森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莫里森作品中“极其重要”的方面指的是非裔美国人的生存状况。她将自己作品的背景设定在美国,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是她尤为关注的主题。莫里森作品中的黑人的历史从17世纪初期到20世纪。几个世纪的艰辛奋斗没有改变黑人在美国社会的“他者”地位,黑人的声音始终被埋没在主流的浪潮下,黑人的历史真正成为了“他的历史”(his-story)。他们的历史是由他人构建的历史,是由主流历史学家阐释、美化或者甚至被浪漫主义化了的历史。莫里森笔下的黑人不仅极力掩饰自己的过往,他们同样消极回避自己民族的历史。通过塑造这样缺乏历史意识的黑人形象,莫里森希望能够填补黑人历史空白,还原黑人真实的生存状态,唤醒他们的历史意识,让他们能够审视自己民族的过往。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历史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2],过去与现在是无法割裂的,它包括“人对历史的感性体验和理性认识”[3](P72),它们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融为一体。
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历史意识不仅指作家能以理性的方式看待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更包括作家对人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所遭受苦难和对自身价值观的审视。托尼·莫里森的作品不回避过去,不掩盖创伤,她在文学创作中深入思考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其中既有对历史的反思,又有对未来的展望与探索,体现了她强烈而敏锐的历史意识。莫里森在她的作品中,通过还原历史、直面过去,反思历史等多维视角看待黑人的生存状态,发出了不一样的声音。
二、还原历史,解构话语霸权
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历史始于黑奴贸易。在蓄奴制盛行的时代,黑人经受着身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内战之后,奴隶制名义上被废除,黑人获得了身体上的自由,但种族歧视一直都是美国社会挥之不去的阴影。一直以来,在以白人为主导的美国社会发展中,白人的历史构成了历史主流,而黑人则作为非主流中的一支被边缘化,始终处于历史进程之外。
美国文学史上不乏黑人文学,其中包括写黑人的作品和黑人自己写的作品。前者有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等;在福克纳的很多作品中,黑人也是重要的角色,如《八月之光》《喧哗与骚动》等。《汤姆叔叔的小屋》引发了对黑人生存状态的关注;《八月之光》中的克莉斯莫斯身份令人质疑,他只是传说具有黑人血统,他成年之后因为自己的身世自我边缘化,迷失在“身份”的迷宫之中;迪尔西一家则更像是汤普生家族的守护者,他们是和任何人一样具有情感、理性的人。福克纳作品中这种更为复杂的生存状态发人深思。理查德·赖特是书写黑人历史的作家之一,他意识到了黑人问题在美国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美国问题—黑人》一文中,赖特指出:“在最广意的层面,‘黑人问题’被认为只是一个美国的问题,只是一个要调整和适应和一个血统和皮肤都完全不同的人群一同生活的问题”。[4](P9)赖特显然意识到美国的黑人问题并非如此轻描淡写,也试图塑造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黑人形象,但他作品中“过于戏剧化的冲突和赤裸裸的黑白对抗”[5](P264)却受到黑人作家埃里森和鲍德温的反对。在《看不见的人》中,埃里森表达了主人公之所以不被看见,并不只是白人的原因这样的观点。黑人的历史在进入主流历史的过程中,经历了巨大的挑战。玛丽斯·康德指出,“对于一个黑人来说,历史是个很大的挑战,因为黑人仿佛没有历史……对于离散族裔的黑人来说,发现以前到底怎样确实是个挑战。”[6]
而在莫里森的作品中,她尊重事实,发掘黑人被扭曲、甚至被掩盖的历史,还原他们的生存状态。《宠儿》中,莫里森描述了报纸作为大众传媒重要的手段之一,反映白人的心声,宣传白人优越,贬低黑人的现状。报纸上是基本不会出现关于黑人的报道的,如果报纸上出现了一张黑人的脸,“它必须是件离奇的事情——白人会感兴趣的事情,确实非同凡响,值得他们回味几分钟,起码够倒吸一口凉气的。”[7](P186)基于这样的偏见,对于赛斯杀婴这一事件,白人在报纸上大肆渲染黑人的兽性和残酷无情,而忽略这一事件背后所隐藏的母爱,忽略是因为奴隶制导致塞斯用这样极端的方式表达母爱。
在美国历史中,美国内战后,奴隶制被废黜,黑人重获自由,美国社会实现了民主平等。但事实上,种族问题依旧深深地根植于社会文化之中。“到了1874年,白人依然无法无天,整城整城地清除黑人;仅在肯塔基州,一年就有八十七人被私行处死,四所黑人学校被焚烧”[7](P214)。丹芙去鲍德温兄妹家,被女佣告知“你先要知道该敲那一扇们”,[7](P306)在当时种族隔离的状况下,黑人不可以和白人一样从前门进入他们的府邸,只能走后门。赛斯宁愿在工作的餐厅偷取生活必需品,也不愿和白人一起在商店外排队,因为“直到俄亥俄州的每一个白人都伺候到了,店主才转身对那些从他后门的洞眼上往里窥望的一张张黑脸”。[7](P266)经济上的贫困也是黑人要面对的问题,故事中,年迈的斯坦普为了糊口不得不在码头干苦力,保罗D也只能通过打零工来维持生计。
在1998年的一次访谈中,莫里森指出,“过去已经不存在或被浪漫化处理。这种文化不鼓励思索,更不用说与过去的真相达成协议。”[8](P11)莫里森在创作中强调尊重历史事实,认为艺术家是最真实的历史学家,文学创作记录历史,修正历史。历史具有文学性,文学也具有历史性,但有的时候,文学比艺术更具哲理(亚里士多德),莫里森通过艺术的手法和象征的方式完美重现了黑人历史中不为人知和被扭曲的部分,为人们再认识和重新思考黑人历史提供了新的依据与视角。在她的作品中,黑人不再面临边缘化的命运,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并通过自我言说获得自身的完整性。
三、直面历史,唤起同胞觉醒
在白人写的历史中,黑人的历史或者被遮蔽,或者被扭曲。对于莫里森这样的作家来说,这无疑是令他们痛心的。然而更令他们担忧的是,面对艰涩的过去,连黑人这个群体也自觉地选择遗忘自己以及自己民族那段惨痛的历史。《宠儿》刚出版时,莫里森曾说过,“我本以为这将会是我所有小说中最不为人问津的书,因为这部小说写的事情,小说人物不愿回忆,我不愿回忆,黑人不愿回忆,白人不愿回忆。我是说,这是全民记忆缺失症。”[8](P20)
莫里森笔下的黑人对于自己民族悲怆凄然的历史常常难以启齿。每个黑人个体对于过往的惨痛记忆都唯恐躲之不及,除非迫不得已,没人愿意保存过去的记忆。保罗D是穷苦黑人的典型形象,他多次被贩卖,居无定所,常年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在恶劣的环境中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当他来到蓝石路赛斯的家时,他把自己的过往“一件件,一桩桩深藏在胸口的烟盒里,”[7](P113)他深信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撬开它了。保罗D锁在烟盒里的何止是他对经历的痛苦记忆,他把对生活的向往和热情也同时紧紧地锁进了内心深处。
赛斯早年的经历也令人心痛,她在学校被老师鞭打,背上留下的疤痕宛若樱桃树。多年过去,她以为自己对伤痕已经“没有一点感觉,因为皮肤早已死去。”[7](P18)但是这种肉体上的伤痕早已深深地烙印在她的心里。赛斯想要忘记的不仅仅是伤痕,她想要用麻木的心态对待过去的苦难,但是在她忘记苦难的努力中,她却经受了更多的折磨。赛斯每天都在极力地驱赶过去,在水里洗脚时,她只是专心地让哗哗的水流把脚上的黄春菊叶子一片一片地冲去,什么都不去想,脑袋里一片空白。
莫里森笔下的黑人都在试图清除个人对苦难的记忆,这种个人记忆缺失的后果是不可估量的,它会导致整个民族对过去记忆的空白,即全民历史记忆缺失症(national amnesia)。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是很难有未来的,王守仁认为,“只有健康的社会才能面对历史,正视历史,不管历史曾经多么黑暗,只有真正面对过去,才能拥有未来。”[9]忘记了过去,曾经犯过的错误也许就会重演。以史为鉴方知兴替。莫里森在废奴一百多年之后旧事重提,旨在鼓励黑人民众面对民族历史,抛弃自卑,勇敢地抬起黑色的头颅。
在小说中,宠儿是赛斯死去女儿的化身,她的到来带来的是大家都试图忘掉的过去,是有关奴隶制的悲惨记忆。然而,她的出现终究使得被压抑的记忆再次回归,这样的“压抑的回归”(return of the repressed)[10]也将带领着塞斯和她的族人走向未来。赛斯在她的纠缠下,一点点地讲述过去在“甜蜜之家”农场的经历,逐步梳理勾勒出自己过去十八年的人生轨迹。与宠儿相处的日子,赛丝摆脱了过去的束缚,面对现实,重新获得了母爱的能力,她的伤痛得以治愈。历经风霜的保罗D本以为自己已经心如死灰,不会对任何人或事再有感觉,但事实上,他也未能抵挡住宠儿的诱惑。他重新打开尘封已久的“烟盒”,面对自己内心,面对过去,与赛斯分享自己过去的沉痛记忆,找回了感受爱和爱的能力。保罗D还与赛斯达成共识“我们拥有的昨天比谁都多,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明天。”[7](P317)宠儿无休止的取闹促使丹芙走出孤独,融入黑人社区,所有人都开始了新的生活。宠儿的故事在无限的生机与希望中画上了完美的句号,但真正带来生机的是故事中每个人面对过去的勇气。
四、铭记历史,共同走向未来
《宠儿》是莫里森作品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历史题材小说,通过小说中人物的经历,莫里森表达了面对现实的唯一出路就是直面历史的历史观。然而,黑人不仅要直面自己的历史,还要对历史进行反思,要在一个多元文化融合的时代,保持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特色,才能在未来有立足之地。
《最蓝的眼睛》和《秀拉》虽然没有直接涉及历史题材,却从不同层面表达了铭记黑人历史的重要性。在《最蓝的眼睛》中,小主人公皮克拉想要一双像秀兰·邓波儿那样的蓝眼睛,她被白人歧视、被黑人忽视、被父亲窥视甚至强奸最终发疯;而叙事者克劳蒂亚的家庭虽然也贫穷,但是这个家庭的成员能够坦然面对自己的真实状况。当以白人文化为主流的大众文化吞噬非裔美国人的文化的时候,保持自己的种族特色,铭记自己民族的历史,使其在文化趋同的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才是非裔美国人得以生存的根本。这两个小女孩之间的对比表明放弃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只会加剧来自外界的敌视,加速被摧毁的过程。类似的作品还有《秀拉》中的女主角。秀拉为了寻求自我解放,脱离黑人社区,最终没能得到一直期待的自由,孤独而终。通过秀拉的例子,莫里森意在指明,黑人一定不能把自己与自己民族的历史割裂开来,铭记过去才能走向未来。黑人女作家左拉·尼尔·赫斯顿从现实的角度阐释了热爱自己的文化、肯定自己的身份对于黑人走向未来的意义。在她的散文《有色的我什么感觉?》(“How I Feel to Be Colored Me?”)中,那个年幼的小女孩和通过镇子的白人对话的经历表达出她对自己身份的热爱、对自己民族文化的自豪;长大后,在酒吧的经历反映出了黑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听着源自遥远的故乡的爵士乐,她内心涌起的是蓬勃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渴望,而坐在对面的白人则无动于衷。可见,一个人的历史和文化身份赋予她的力量可以使她坦然面对因为肤色而带来的异样目光。
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有其独特的一面,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在和其他民族的历史相互依存的状态下才能存在的,也正是在相互依存的状态下才凸显出自身的文化价值。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并存是大势所趋,美国非裔文化是多元文化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作为一个整体,莫里森的作品形成了一个关于非裔美国人对历史进行记忆和重构的完整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过去、现在与未来互相交织在一起,不可割裂。莫里森用“记忆重现”(rememory)[11]来描述这种对历史的认识方式,这种反映历史的方式充满想象力、富有创造力。莫里森以此呼吁美国非裔群体铭记自己的历史,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五、结 语
莫里森作品中表现出的历史意识不仅是个人对历史的记忆,它更多地表现为群体对过去的记忆、认识和反思。莫里森深刻地认识到在历史的视域中,过去、现在与未来紧密相关,不可割裂。只有在正视历史中才能反思现实,展望未来。莫里森的小说揭开了非裔黑人被隐藏的历史和遗失的过去,重构黑人的古老价值观。她通过文学创作挑战甚至颠覆了白人主流文化所记载的黑人历史,并赋予作品中每个角色以沉重的历史使命,他们来自往昔,诉说着沉痛的历史,同时又肩负着唤醒本族同胞的责任,寻求最终的解放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