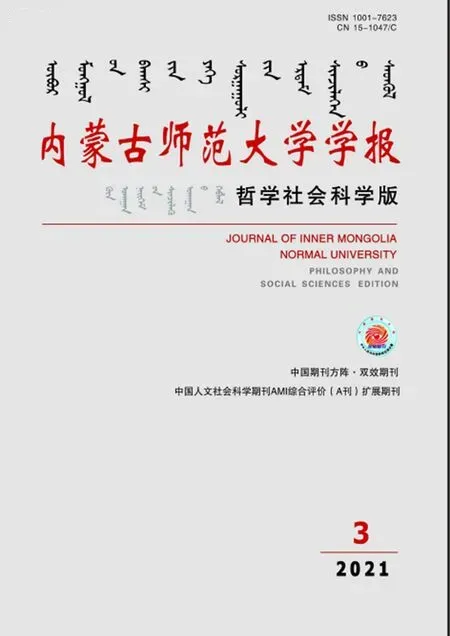运输毒品罪之“运输”研究
——基于云南省2019年245份生效判决书的检视
2021-12-30杨喻博
申 伟, 杨喻博
(兰州大学 法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国家禁毒委员会在《2019年中国毒品形势报告》中指出:“2019年,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8.3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1.3万名,缴获各类毒品65.1吨。”[1]该报告还指出:“我国的毒品大多数都来源于境外,境内制造的毒品数量仅占到缴获的毒品总数量的4.1%。境外毒品通过走私渠道入境后,云南辐射全国仍是主流,云南是‘金三角’毒品主要的渗透入境地和中转集散地,贩毒群体云集。”[1]故云南的毒品犯罪在全国范围内较具有代表性。鉴于此,笔者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收录的云南省2019年以行为人构成运输毒品罪为由作出的245份已生效刑事判决书为素材,观察当前中国刑事司法实践如何认定运输毒品罪之“运输”,并进一步讨论究竟应该如何把握毒品“运输”的规范取向。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①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一个选择罪名。笔者主要研究运输毒品罪之“运输”,故将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检索条件设置为:一级案由为“刑事案件”,三级案由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省份为“云南省”,文书类型为“判决书”,刑事判决书的年份为“2019年”,全文关键词检索条件为“运输毒品罪”,最后一次检索时间为2020年7月23日。笔者共下载刑事一审程序判决书225份和刑事二审程序与刑事审判监督程序判决书24份,最终数量为249份。在筛选的过程中,剔除被定性为其他罪名的共4份刑事判决书,最终确定数量为245份,共涉及334名被告人。
一、 刑事判决书对“运输”行为的认定
(一)刑事判决书中认定“运输”行为的依据
中国《刑法》中没有关于运输毒品罪之“运输”的定义。2016年5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公安部发布的《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中规定:“本条规定的‘运输’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采用携带、寄递、托运、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非法运送毒品的行为。”[2]目前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认定《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中“运输”的规范依据,可能主要是前述《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和其他一些禁毒工作会议纪要②。
会议纪要分别为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4月4日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南宁会议纪要》)、最高人民法院2008年3月26日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大连会议纪要》)及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5月18日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武汉会议纪要》)。这3份会议纪要有很强的时效性,其中《南宁会议纪要》已被后两份代替。
(二)刑事判决书中认定“运输”行为的类型
审读判决书可以发现,云南省各级法院在2019年以“运输毒品罪”作出的245份生效判决书中认定为运输毒品罪之“运输”行为,实质上是以下8种具体的行为类型。
行为类型一:行为人携带毒品进行了空间位移之行为+不论出于何种目的=运输。共有116份刑事判决书对运输毒品罪之“运输”采取了这一理解。在这些判决中,法院认为“查明”了行为人携带毒品且使之发生空间位移即当然构成运输毒品罪,然对“携带”究竟系出于何种特定目的毫不关心。这些判决书中有71份判决于证据部分之被告人供述与辩解显示,行为人是受他人雇佣或在他人指挥安排下,以牟利的主观目的实施携带毒品进行空间转移之行为,然法院在审理查明的事实部分与判决理由部分均未予以确认。有7份判决在证据部分之被告人供述与辩解显示被告人是吸毒者,以自吸为目的携带毒品进行空间位移之行为,法院于判决理由部分对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完全忽略不计。有38份判决书,法院并没有查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以下为法院认定此行为类型的代表性表述:“本院认为,被告人赵明辉伙同彭某伟、熊某荣运输毒品海洛因16471克的行为已触犯我国刑律,构成运输毒品罪。”③“本院认为,被告人张大贵明知毒品而运输的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予以支持。”④“本院认为,被告人张传龙无视国法,主观上明知是毒品,客观上实施了运输毒品的行为,其行为构成运输毒品罪,依法应予惩处。”⑤“被告人刘勇系吸毒人员,驾车携带毒品途经鲁甸县被查获,其实施了具体的运输毒品行为,本案无证据证明刘勇是为了实施贩卖等其他犯罪,查获的毒品数量大,应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⑥此类型判决书中,法院仅考察行为人主观是否明知是毒品,客观上是否携带毒品进行了空间位移,若主客观皆具备即认定符合运输毒品罪之“运输”。判决理由部分亦未考虑行为人事实上以何种目的实施了何种行为,直接陈述行为人实施了“运输毒品”故构成“运输毒品罪”。也就是说,法院的判决实质上是同语反复、循环论证。
行为类型二:行为人走私毒品入境后+以携带毒品进行空间位移+非法牟利目的=运输。有59份刑事判决书采取此种理解。法院认为行为人以非法牟利为目的,携带毒品进行空间位移即构成运输毒品罪。然而笔者通过阅读此判决书获知,行为人于境内携带毒品进行空间位移之前,实施了在境外将毒品走私入境之行为,法院在查明事实与判决理由部分均未予以认定。此事实位于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部分,法院以证据部分证明被告人实施邮寄毒品之行为,也就是说法院认为证据部分均为属实之事实,然而却将走私行为与后续之携带毒品使毒品产生空间位移之行为统一评价为运输毒品罪。法院的代表性表述为:“本院认为,被告人何贵友无视国法,为牟取非法利益,违反国家毒品管理法规,明知是毒品仍进行运输,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运输毒品罪。”⑦
行为类型三:行为人携带毒品使毒品产生了空间位移+非法牟利目的=运输。共有41份刑事判决书对“运输”行为采用此种理解。法院亦认为行为人以非法牟利目的携带毒品,使毒品产生了空间上之位移即构成运输毒品罪。然而有1份判决中,行为人是吸毒者,携带毒品之主观目的为自吸,法院却在判决理由部分认为行为人具有非法牟利之目的。有2份判决中,法院并未查明行为人的目的,同样在判决理由部分认为行为人具有非法牟利的目的。以下为法院认定此行为方式的代表性表述:“本院认为,被告人为牟取非法利益,明知是毒品而予以运输的行为构成运输毒品罪。”⑧“本院认为,被告人违反国家禁毒法律,为获取非法利益,明知是毒品而采用随身携带的方式运输毒品海洛因995.72克的行为已构成运输毒品罪,且运输毒品数量大,依法应予惩处。”⑨“本院认为,被告人违反我国对毒品的特殊管制,明知是毒品,为牟取非法利益,在我国境内运输毒品的行为已触犯国家刑律,构成运输毒品罪,应依法予以惩处。对于被告人辩解查获的毒品系其购买后供自己吸食,并无贩卖的主观意愿的辩解理由,经审查,其在运输毒品的过程中被查获,且运输的毒品数量明显超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2015)129号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规定,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故其辩解不能成立。”⑩
行为类型四:行为人携带毒品进行空间位移+贩卖目的=运输。共有25份刑事判决书对“运输”行为采取这一理解。法院认为行为人具有贩卖毒品之目的,实施了携带毒品进行空间位移的行为,故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以下为法院认定此行为类型的代表性表述:“本院认为,被告人文辉书伙同同案人岳明亮、张萍、袁勇、陶英违反国家对毒品的管制规定,明知是毒品而进行贩卖、运输,其行为已触犯刑律,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本院认为,被告人唐永仁、李就安无视国家禁毒法律,以出售为目的共同出资购买甲基苯丙胺448.59克,并将毒品包装后乘坐旅客列车欲运回湖南永州进行贩卖的行为已触犯国家刑法,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行为类型五:行为人以邮寄方式使毒品产生了空间位移=运输。有1份刑事判决书对“运输”行为采用这一理解。法院认为行为人以邮寄毒品方式,使毒品产生了空间上的位移,其行为即构成运输毒品罪。法院的表述为:“被告人朱江根据他人安排,在普洱市通过顺丰快递欲将藏有甲基苯丙胺片剂2438.2克的行李箱邮寄至湖北武汉,构成运输毒品罪。”
行为类型六:行为人以邮寄方式使毒品产生了空间上的位移+贩卖目的=运输。有1份刑事判决书对“运输”行为采用这一理解。在该判决中,法院认为行为人以贩卖为目的邮寄毒品,使毒品产生了空间上的位移,其行为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法院的表述为:“本院认为,被告人李希平为牟取非法利益,明知是毒品而以邮寄的方式贩卖给他人的行为,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
行为类型七:行为人走私入境后+以邮寄方式使毒品产生了空间位移=运输。有1份刑事判决书对“运输”行为采取这一理解。法院同样认为行为人以邮寄方式使毒品产生空间位移之行为即构成运输毒品罪。然而笔者同样在证据之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部分获知,行为人先行实施“走私”毒品入境之行为,法院亦在判决理由部分将“走私”行为忽略掉,将行为人的两个行为统一评价为运输毒品罪。法院之表述与上述行为类型六一致。
行为类型八:行为人走私毒品入境+携带毒品进行空间位移+贩卖目的=运输。有1份刑事判决书采取这一理解。法院同样认为行为人以贩卖为目的实施携带毒品进行空间位移行为即构成贩卖、运输毒品罪。笔者于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部分获知行为人在境外获得毒品,并首先实施走私毒品入境之行为,法院在判决书的判决理由部分未予确认,而是将两个行为统一评价为贩卖、运输毒品罪。法院之表述与行为类型四一致。
二、 刑事判决书关于“运输”之理解的检讨
(一)偏误之一:认为无论出于何种目的而使毒品发生空间位移皆为“运输”
此偏误之典型表现即法院认为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是毒品且客观上使得毒品进行了空间位移即构成运输毒品罪,然而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根本不查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或者即使查明了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仍在判决理由部分忽略不计。
运输毒品罪之“运输”行为的主观目的实为促进毒品之流通性,使毒品于不同主体间得以流通,故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仅要求行为人明知是毒品,而并不考察或者完全忽略不计行为人之主观目的是不合理的,应实际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促进毒品流通之目的,并于判决理由部分明确说明之。
(二)偏误之二:认为唯有具有非法牟利目的而使毒品发生空间位移才为“运输”
此偏误之典型表现即法院认为仅具有非法牟利目的,使毒品发生空间位移之行为为“运输”毒品行为。换言之,行为人主观上不仅须明知是毒品,还当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指向。
上文述及,“运输”行为之主观目的应为促进毒品流通性,行为人是否获利并非“运输”行为之核心要素。否则,便会造成可罚性漏洞,如行为人不收取任何报酬,不具有牟利之目的,帮助他人将毒品运送至另一主体,《刑法》无法将其评价为运输毒品罪。
(三)偏误之三:认为具有“贩卖”目的使毒品产生空间位移为“贩卖”与“运输”之数罪
此偏误的典型表现系为法院在判决书之判决理由部分将行为人以“贩卖”为目的实施的使毒品进行空间位移之行为同时评价为贩卖、运输毒品罪。这种理解认为行为人以“贩卖”毒品之目的实施使毒品空间位移之行为并不能包含“运输”之行为。
笔者认为,“运输”毒品之行为的主观目的仅为促进毒品流通为目的,而不应当同时具有“贩卖”毒品之目的。行为人以“贩卖”为目的实施流通毒品之行为系为“贩卖”之手段行为,应当包含于贩卖毒品罪之中,否则“贩卖毒品罪”与“运输毒品罪”间即丧失明晰界限,造成重复评价。
(四)偏误之四:认为具有其他毒品犯罪之目的使毒品发生空间位移为“运输”
此偏误的典型表现系法院在判决书中将行为人以“自吸”为目的、“贩卖”为目的,或行为人以“走私”为目的且已将走私行为实施完毕之行为评价为运输毒品罪。此理解意味着“运输”毒品之主观目的包含了“自吸”“贩卖”与“走私”之目的。
笔者认为此理解将会造成运输毒品罪被扩大适用。立法者将运输毒品罪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的同一个条文之中,即是认为“运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其他三种行为相当,并且“运输”毒品之行为也应与其他三种行为有明显之界限,若非如此,立法之规范目的为何?行为人以“自吸”为目的携带毒品进行空间位移之行为显然不具有流通毒品之目的,其社会危害性明显小于以流通为目的携带毒品进行空间位移之行为,故评价为运输毒品罪显属不当。
(五)偏误之五:认为作为其他毒品犯罪之参与行为的运输为运输毒品罪之“运输”
此偏误的典型表现为法院将以下两种情形认定为运输毒品罪:一是行为人明知其他毒品犯罪行为人对该毒品之用途并帮助其促成毒品之流通,但行为人与其他毒品犯罪行为人之间并无共谋;二是行为人帮吸食者代购毒品。在承认片面帮助可罚性的前提下,第一种情形下行为人之“运输”行为应认定为其他毒品犯罪之参与行为而非独立的运输毒品罪;第二种情形下,因本文持吸食者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场,行为人之“运输”行为应认定为非法持有毒品罪之参与行为而非独立的运输毒品罪。概言之,上述两种情形下,行为人之“运输”行为皆为其他毒品犯罪之参与,不应评价为独立的运输毒品罪。如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1月1日审结的案件:“被告人李方华明知赵某1、赵某2以贩卖为目的购买了毒品,帮助两人运输毒品,被告人李方华受赵某1、赵某2安排,驾驶车辆从境外将毒品走私、运输入境交给赵某1、赵某2,李方华的行为构成走私、运输毒品罪。在共同犯罪中,李方华的地位作用相比赵某1、赵某2较小,属从犯,可对其从轻处罚。”这个刑事判决书中,李某明知两人具有“贩卖”之目的,但法院却将被告人李某之行为评价为参与行为之帮助行为,认定为运输毒品罪。
笔者认为,立法者将“运输”毒品行为单独成罪,明确规定在《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之中,则“运输”毒品之行为人应为正犯,即认定仅以流通毒品为目的,实施流通行为之行为人才构成运输毒品罪。如行为人与其他毒品犯罪行为人有共同犯罪的共同故意,或明知其他毒品犯罪行为人之目的而帮助实施流通毒品之行为,应当评价为其他毒品犯罪之共同犯罪。
三、 理解“运输”行为的约束理念
(一)“运输”毒品行为之可罚性
毒品与枪支、弹药、爆炸物一样属于国家禁止流通的物品,这些违禁品会对社会管理秩序造成很严重的威胁,所以立法者将本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一章中,旨在禁止毒品在社会上的流通,维护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
中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所规定的4种行为就是毒品于产生到流通最终到达吸毒者手中的整个过程。立法者订立严厉的刑罚制裁运输毒品之行为的目的即为预防“运输”毒品犯罪,阻断毒品在社会上的流通环节。毒品自产生至最后流通到吸食毒品人员的手中,主要有以下几个环节:首先制造毒品,然后通过制毒人员自己携带运输或者雇佣中间人携带运输,最终流通到吸毒人员手中,这其中有制造、运输、贩卖等环节。走私属于在我国境外运输到我国境内,虽然运输是走私行为的手段,但走私行为同时也侵害了我国边境管理,故立法者将走私单独规定为一个行为。运输行为属于毒品产生、贩卖到吸食者的中间环节,客观上促成了毒品在社会上的流通,侵害了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故运输行为具有可罚性,立法者将运输行为单独成罪,目的是为了对运输毒品行为人起到特殊预防之效果,对于有运输毒品危险性的人起到一般预防的效果,堵截可罚性漏洞。
中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对于运输毒品罪规定了与其他三种犯罪行为同样严厉的刑罚,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看到立法者将毒品之运输行为视为与毒品之走私、贩卖、制造具有相当性之不法行为。在运输毒品罪作为独立一罪的意义上讲,作为该罪客观不法要素之核心的“运输”理当系一类具有“可罚的违法性”[3]24之可罚的不法行为。反过来看则是,唯有当个案中识别出来的“运输”行为被评价为可罚的不法行为时,该“运输”行为才能被评价为运输毒品罪。这应是界定运输毒品罪之“运输”行为的底线要求。明乎此一理解《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之教义立场,面对以“运输毒品罪”名义作出的刑事判决便须反思该案中行为人之运输行为是否果真为可罚的不法运输行为。
(二)“运输”毒品行为之明确性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之一为“罪”之“法定”。此“法定”不仅要求犯罪之构成要素在形式意义上的明文性,更要求犯罪之构成要素在实质意义上的明确性。犯罪构成要素实质意义上的明确性,当然包括犯罪之实行行为的明确性。为贯彻罪刑法定这一基本理念,解释《刑法》规定的任何一个犯罪,以及使用《刑法》任何一个个罪规范作出有罪裁判时,便必须确保对该个罪之理解不可有违“明确性”之要求。具体到本文关注的问题上讲,即是说对运输毒品罪之“运输”的理解,既是内部——什么是“运输”——明确的,也是外部——什么不是“运输”——明确的。内部明确,强调的是“运输”行为的内涵及其类型化表现应该是明确的;外部明确,强调的是“运输”行为的边界清晰。
笔者认为,“运输”行为之内涵在于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即应该明确行为人以流通毒品为目的,这个目的具体表现为认识到是毒品但与其他毒品犯罪行为人无共同故意,没有认识到其他毒品犯罪行为人对毒品用途之情况下,使毒品于不同主体间的流通。这个主观目的是理解“运输”的关键,是运输毒品罪与整个毒品犯罪序列其他以毒品空间位移为表现形式之犯罪行为予以区分的本质特征。
至于行为人是否具有牟利的目的,通过什么行为使得毒品发生空间位移,甚至并没有使毒品发生空间位移,只要具有上述目的,并且使得毒品在不同主体间发生流通则均应认定为本罪。基于此理解,“运输”与其他毒品犯罪的边界即是基本清晰的,如行为人以贩卖为目的流通毒品,此时的“运输”行为是贩卖毒品罪的手段行为,“运输”行为就被包含在“贩卖”行为之中,不单独评价为运输毒品罪。但是“走私”行为与“制造”行为不包含“运输”行为。“走私”毒品的行为固然是以运输为手段的,但是“走私”行为本质上属于在我国边境以外运输至我国边境之内,而“运输”行为只应当在我国境内,故行为人实施了“走私”毒品行为,将毒品运行至我国境内后,再进行之“运输”行为也具有可罚性,构成同种数罪,应当并列适用罪名,以走私、运输毒品罪定罪。“制造”是将毒品原料转化成毒品的行为,该行为不可能是以“运输”为手段行为,故制造出毒品后再实施“运输”毒品行为的,也构成数罪,应当并列适用罪名,以制造、运输毒品罪定罪。
据笔者搜集到的刑事判决书样本中理解的各种“运输”毒品之行为类型,司法实践中对“运输”行为之理解尚不统一,势必造成运输毒品罪之适用混乱,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所要求之明确性。
(三)“运输”毒品行为之正犯性
“根据限制实行人概念,实行人在原则上就被限制在分则的行为构成所描述的举止行为之上了,这样,帮助是刑罚的扩张根据,超出了由实行人所表示的刑事可罚性的核心领域。”[4]9中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明确将“运输毒品罪”规定为独立犯罪,故运输毒品罪之“运输”行为显系该罪之实行行为,亦即该“运输”作为运输毒品罪核心构成要素之一的“正犯”行为,而非任何其他犯罪之参与方式。
否认“运输”行为之正犯性,实质上即是否认了运输毒品罪在中国《刑法》中作为独立一罪的地位。若此,中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明确规定之“运输”将沦为具文。因此,否认“运输”行为之正犯性显然有违《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之文义。更有甚者,否认“运输”行为之正犯性还将导致“运输”行为从《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之可罚行为清单中被移除,由此使得该条所针对者仅余走私、贩卖与制造环节,从而形成促成毒品流通之“运输”环节称为不可罚的环节。因此,否认“运输”行为之正犯性更有违《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之规范目的。
抛开《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之文义与规范目的不论,在中国《刑法》向来在分则个罪条款中仅明确规定正犯行为的立法体例下,若将“运输”解为参与行为,势必表明立法者在第三百四十七条中采取了刻意将参与行为明确化之特殊立法技术。然而,在参与行为不必亦不可能明确化的情况下,立法者于第三百四十七条中采取此特殊立法技术,显然需要额外的充足理由。至少到目前,我们实在看不到立法者意在作此特殊操作,也找不到立法者有采取此等特殊操作之特殊理由。
四、 “运输”毒品行为的规范含义
(一)“运输”行为之定义
“运输”行为的概念尚存争议,司法实践中的理解是:“本条规定之‘运输’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采用携带、寄递、托运、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非法运送毒品的行为。”[2]有学者认为:“运输毒品是指采用携带、邮寄、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在我国领域内转移毒品,只有与走私、贩卖、制造具有关联性的行为,才宜认定为运输,否则会导致罪刑之间不协调。”[5]1144亦有学者认为:“运输毒品是指在一个法域内,行为人以流通毒品为目的,认识到是毒品但不明知毒品的用途,采用各种方式流通毒品,并不根据自己的意志使毒品流通于不同的控制者。”[6]47
司法实践中的观点更侧重于形式上的考察,即行为人是否明知是毒品,是否采用了一些手段使得毒品产生了空间上之位移,至于行为人对毒品进行空间上位移之目的明显没有重点考察,且没有明确区分出本罪与其他毒品犯罪之界限。前一学者的观点则进一步明确了运输行为应当是在我国领域内实施,同时强调运输行为应当与《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的其他行为具有关联性,因本罪与其他行为之社会危害性大致相同。笔者认为最后一种观点具有合理性,即运输毒品行为本质上是为了促进毒品的流通性,使得毒品在贩卖、制造的阶段加速流向吸食者,加大了国家对毒品管控的难度,严重侵害到国家对毒品的管理制度,而不仅仅是毒品在空间上的位移。若将运输毒品行为限制为仅是使得毒品产生空间位移,那么空间位移之距离应当怎么认定?再如甲至乙家里放置毒品,指明丙将前来取走毒品,然乙不知甲与丙对该毒品之用途,且自始至终没有使毒品发生空间位移,丙前来将毒品取走,此时乙之行为又该如何认定?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的四种实行行为中,“运输”实为一种中间行为,即与其他实施走私、贩卖、制造或吸食毒品者无犯罪之共谋,且并不明知该毒品之不法用途。故笔者认为运输毒品罪的定义应该为:行为人仅以流通毒品为目的,在不明知其他毒品犯罪行为人对该毒品之不法用途、与其他毒品犯罪行为人之间无共同犯罪之共同故意的情况下,在我国领土内促成毒品于其他毒品犯罪行为人之间流通之行为。
(二)“运输”之客观要素
“运输”毒品的客观构成要件要素,首先应当考虑的是毒品在空间上的因素,即毒品在空间上的流通性。“运输”毒品的本质是促进毒品的流通,是对毒品向消费终端的靠近做出了实质性的推进[7]4。故毒品之空间位移并不是“运输”行为的核心要素,此处之“运输”应当与词的本义做不同的理解。“运输”的本义是使用一定的手段或工具将货物从一地运往另一地。但运输毒品罪中的“运输”应当是毒品在不同的主体间的流通,即便毒品在空间上的某一地并无发生位移,但是在行为人的作用下,使得毒品从一个主体流动到了另一个主体手中,则应当认定为“运输”行为。前述第一种学者的观点是“运输”行为也应当存在空间位移,且与贩卖、走私、制造行为具有关联性。笔者认为这样的评价会过于限缩运输毒品罪的适用,“运输”行为的核心要素并不在客观行为上,而是在主观目的,即符合“运输”行为之主观目的,无论客观行为是否与其他三种行为具有关联性,也无论毒品是否发生空间位移,均侵害了国家对毒品的管控制度,应当论以运输毒品罪。
其次是“运输”毒品行为的地域因素。“运输”毒品之行为应当限定在我国领土内但不得跨境实施,由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同时规定了走私毒品罪,故跨境的运输毒品行为就不应当认定为运输毒品罪。但此处要注意一个问题:如行为人未跨境,于港澳台地区内部实施“运输”毒品之行为,该如何认定?笔者认为,如行为人于港澳台地区内部并且没有跨境的情况下实施“运输”毒品之行为,最终行为人在大陆地区审判的,也应当认定为运输毒品罪,因为港澳台地区也属于我国领土范围内。
运输毒品罪中的“运输”行为也应当与包庇毒品犯罪分子罪及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中的以“运输”手段“转移”毒品的行为做出明确的区分。运输毒品罪中的“运输”行为与以“运输”手段为表现形式的“转移”毒品的行为,区分的关键点亦为行为人是否具有毒品流通之目的,是否将毒品于不同主体间流通。如仅仅是在原持有人处取得毒品,运送至另外一地后仍然是交给原持有人,则应当认定为转移毒品罪,而不是运输毒品罪。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实现毒品的流通性,此行为之社会危害性明显小于“运输”毒品行为,如论以运输毒品罪则会造成罪刑不相适应的情况。
(三)“运输”之主观要素
行为人实施“运输”行为的主观目的,不能包含其他毒品犯罪之主观目的,只能是以流通毒品为目的,即行为人只要明知其行为使毒品于不同主体间发生流通,即可认定流通之目的。“贩卖”毒品之主观目的可包含“运输”毒品之主观目的,故行为人具有“贩卖”毒品之主观目的则应评价为贩卖毒品罪一罪。“走私”与“制造”之主观目的不能包含“运输”之主观目的,故行为人具有“走私”与“制造”毒品之主观目的,应与“运输”行为同时评价,行为人构成走私、运输毒品罪或制造、运输毒品罪。
行为人仅以流通毒品为目的,与其他毒品犯罪行为人没有共同犯罪的共同故意,并不明知其他毒品犯罪行为人对毒品之用途。行为人与其他毒品犯罪行为人具有共同犯罪之共同故意则构成共同犯罪自不待言。如行为人仅明知其他毒品犯罪行为人对于毒品的用途,此时则构成其他行为人之片面帮助犯,亦应当按照共同犯罪予以评价。
吸毒行为在我国《刑法》上并没有规定为犯罪,但自《武汉会议纪要》始,司法实践中将吸毒者以“自吸”为目的实施使得数量较大的毒品进行空间位移之行为评价为运输毒品罪。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的3份关于禁毒工作“会议纪要”,其中《南宁会议纪要》中对吸毒人员携带毒品行为认定标准为:“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储存毒品过程中被抓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实施了其他毒品犯罪行为的,一般不应定罪处罚,但查获的毒品数量大的,应当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数量最低标准的,不定罪处罚。”[8]85随后的《大连会议纪要》对于该特殊行为的定性基本坚持了《南宁会议纪要》的理解,但是最新的《武汉会议纪要》则推翻了前面两份会议纪要的标准。这份文件的理解是:“吸毒者在购买、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处罚。吸毒者在运输毒品过程中被查获,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毒品等其他犯罪,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以运输毒品罪定罪处罚。”[9]笔者认为,吸毒者以“自吸”为目的,使毒品发生空间位移之行为应评价为非法持有毒品罪更加适合,缘此行为之社会危害性明显轻于以流通为目的之“运输”毒品行为,且非法持有毒品罪最高仅可判处无期徒刑,刑罚的严厉程度也明显轻于运输毒品罪。
其次毒品属于违禁品,故行为人不能在《民法》上取得毒品的所有权。在此假定行为人取得了毒品的所有权,行为人运送其自有的毒品时应当以毒品的用途定罪,此时分三种情况讨论:第一,行为人取得了毒品,但行为人不具有流通毒品之目的,仅仅是将毒品带回家收藏,此时由于不符合“运输”毒品行为之主观上促进流通性的特征,应当论以非法持有毒品罪;第二,行为人取得了毒品,但是以贩卖目的实施了“运输”毒品之行为,论以贩卖毒品罪自不待言;第三,行为人取得了毒品,并且将毒品由甲地运送至乙地,其目的是免费将毒品赠予他人吸食。行为人此时并没有贩卖、走私、制造毒品之目的,故不能论以贩卖、走私、制造毒品罪,此行为亦不符合容留他人吸毒罪之构成要件。然而行为人客观上促进了毒品的流通性,并且主观上也是以促进毒品流通为目的,此时论以运输毒品罪较为适合,并且也符合立法者规定运输行为的堵截性的规范目的。
结 论
综合全文之论述,由于立法对运输毒品罪之“运输”行为的规范含义规定不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本罪适用产生了一定的混乱。本应有一种明确的“运输”毒品行为之规范含义,但法院却在审理具体案件时产生了上述8种行为类型,扩大了“运输毒品罪”之适用范围,违反了《刑法》之明确性要求。为贯彻《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之规范目的,笔者认为,在刑法教义学上应将运输毒品罪定义为行为人仅以流通毒品为目的,在不明知其他毒品犯罪行为人对该毒品之不法用途、与其他毒品犯罪行为人之间无共同犯罪之共同故意的情况下,在我国领土内促成毒品于其他毒品犯罪行为人之间流通之行为。行为人将毒品走私入境后或者制造出来后实施“运输”毒品之行为亦具有可罚性,构成数罪,应当并列适用罪名。
依据笔者对“运输”毒品行为概念与特征之理解,核心要素为仅具有流通毒品之主观目的,在此纠正上述云南省各级法院对“运输”毒品行为之理解。
行为类型一与行为类型五中,72份刑事判决书之行为人虽客观行为不同,以携带或邮寄毒品之行为方式流通毒品,但主观上均仅有流通毒品之目的,应评价为运输毒品罪。7份刑事判决书行为人为吸毒者,携带毒品之目的为自吸,不具有流通毒品之主观目的,故不构成运输毒品罪,应评价为非法持有毒品罪。38份刑事判决书中,法院并没有查明行为人之主观目的,依据罪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此时不宜认定行为人具有流通毒品之目的,应评价为刑罚较轻之非法持有毒品罪。
行为类型二与行为类型七中,共60份刑事判决书之行为人无论其是否具有非法牟利之目的,且无论以何种行为方式实施流通毒品之行为,行为人仅具有流通毒品之目的,评价为运输毒品罪并无不妥。然而行为人实施“运输”行为之前,先行实施了走私毒品进境之行为,“运输”行为无法包含该行为。故将这些行为人评价为走私、运输毒品罪更为妥当。
行为类型三中,38份刑事判决书之行为人虽具有非法牟利之目的,但这些行为人与其他毒品犯罪行为人并无共同犯罪之共同故意,且不明知其他行为人对该毒品之用途,故符合仅具有流通毒品之目的,客观上实施了流通毒品行为,应评价为运输毒品罪。1份刑事判决书之行为人为“自吸”目的,并不可能具有非法牟利目的,遑论流通毒品之目的,故应评价为非法持有毒品罪。2份刑事判决书中,法院并无查明行为人之主观目的,笔者认为无法确认行为人之非法牟利目的,是否具有流通毒品目的更无从考证,故应评价为非法持有毒品罪。
行为类型四与行为类型六中,共26份刑事判决书之行为人虽然使得毒品进行空间位移之行为分别为携带与邮寄,但并不符合“运输”行为之仅具有流通毒品目的,行为人具有“贩卖”之目的,应当评价为贩卖毒品罪更为妥当。
行为类型八中,1份刑事判决书之行为人以“贩卖”之目的,先行实施“走私”毒品入境行为后,于我国境内又实施了运输毒品之行为,但法院同样忽略掉了行为人之“走私”行为。此判决之行为人由于具有了“贩卖”之目的,故不再单独评价其运输毒品之行为,应与先行实施之“走私”行为,评价为走私、贩卖毒品罪,而不应当是贩卖、运输毒品罪。
综上所述,中国刑事司法实践应根据立法者的立法目的,明确“运输”毒品行为之含义,使运输毒品罪与其他毒品犯罪的边界基本清晰,以期符合《刑法》的明确性要求及法条之规范目的。
注 释:
①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三)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四)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五)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的。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第二款、第三款、第四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的,从重处罚。 对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
②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第三条之规定,刑事裁判文书应当引用法律、法律解释或者司法解释。笔者在搜集到的刑事判决书中,一些法院明确列明依据《武汉会议纪要》作为裁判依据,也有些法院虽然没有明确表明以《会议纪要》为裁判依据,但是其判断标准依然与《会议纪要》保持一致。故笔者认为,刑事判决书认定“运输”行为的规范依据就是这些规范性文件。
③ 云南省保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云05刑初229号。
④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云31刑初290号。
⑤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云01刑初503号。
⑥ 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云06刑初141号。
⑦ 云南省临沧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云09刑初216号。
⑧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云31刑初200号。
⑨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云23刑初50号。
⑩ 云南省普洱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9)云08刑初16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