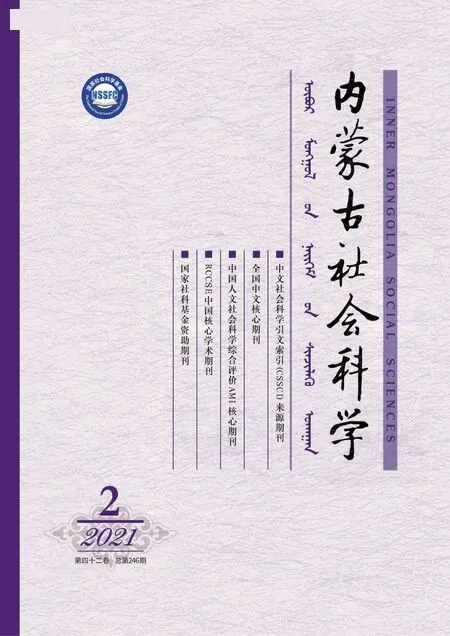元朝帝陵葬地探索的回顾与思考
2021-12-29田广林梁景欣
田广林,梁景欣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有关元朝诸帝陵墓的具体位置,由于今本《元史》失载,遂成不为世人所知的千古之谜。本文旨在从学术史角度入手,对宋元以来有关元朝帝陵的历史学、考古学材料进行系统梳理,以祈有助于这一重要学术课题的研究。
一、清以前相关史籍的记载
据《元史》记载,在元朝14代帝王中,除了宪宗蒙哥和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其余12位帝王死后均葬在起辇谷。(1)《元史》卷1《太祖纪》载,成吉思汗于太祖二十二年(1227)“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葬起辇谷”;卷2《太宗纪》载,窝阔台于太宗十三年(1241)崩于胡兰山行殿,“葬起辇谷”;卷2《定宗纪》载,贵由于定宗三年(1248)“崩于横相乙儿之地……葬起辇谷”;卷17《世祖纪》载,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三十一年“崩于紫檀殿……乙亥,灵驾发引,葬起辇谷,从诸帝陵”;卷21《成宗纪》载,元成宗铁木耳于大德十一年(1307)崩于玉德殿,“葬起辇谷,从诸帝陵”;卷23《武宗纪》载,元武宗海山于至大四年(1311)崩于玉德殿,“灵驾发引,葬起辇谷,从诸帝陵”;卷26《仁宗纪》载,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于延祐七年(1320)“崩于光天宫……癸卯,葬起辇谷,从诸帝陵”;卷28《英宗纪》载,元英宗硕德八剌于至治三年被杀“于行幄……从葬诸帝陵”;卷30《泰定帝纪》载,泰定帝也孙铁木儿于泰定五年(1328)崩,“葬起辇谷”;卷31《明宗纪》载,元明宗和世瓎即位未及一年被杀,“葬起辇谷,从诸陵”;卷36《文宗纪》载,文宗图帖睦尔于至顺三年(1332)八月崩,“癸丑,灵驾发引,葬起辇谷,从诸帝陵”;卷37《宁宗纪》载,宁宗懿璘质班(十三)即位一月即崩,“甲午,葬起辇谷,从诸陵”。
其实,宪宗蒙哥和顺帝妥欢贴睦尔的葬地也在起辇谷。《元史·宪宗纪》只载蒙哥于宪宗九年(1259)“崩于钓鱼山。寿五十有二,在位九年”,没有提到具体葬在什么地方。但《史集·蒙哥合罕纪》记载了蒙哥汗的明确葬地:“把他葬在称为也可·忽鲁黑的不儿罕·合勒敦的成吉思汗和拖雷汗[的陵墓]旁边。”[1](P.271)《史集》是伊利汗国宰相拉施特奉命修撰的官方史书,成书于1300~1310年间,所述14世纪以前的蒙古史事多为直接见闻,具有其他史书不可代替的史料价值。通过这条记录可知,不仅蒙哥汗死后从数千里之遥的四川归葬祖茔起辇谷,其父拖雷虽然未登汗位,但死后也以成吉思汗嫡子身份陪葬在成吉思汗陵墓之侧。
与蒙哥一样,顺帝妥欢贴睦尔也客死于都城之外。《元史·顺宗纪》载,妥欢贴睦尔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退守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境内),一年后复退于应昌府(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南)。至正三十年(1370),“四月丙戌,帝因痢疾,殂于应昌……太尉完者、院使观音奴奉梓宫北葬”。归葬祖茔是北方民族的传统葬俗。元顺帝身后臣属们“奉梓宫北葬”,是遵行归葬祖茔之俗,“北葬”于起辇谷。也就是说,元朝的14代帝王死后都葬在起辇谷。
元朝帝王陵墓所在地在当时属于高度国家机密,因称“大禁地”。《史集·部族志》记载:“在平原上长着一棵很绿的树。他(成吉思汗)十分喜欢这棵树的翠绿清新,[成吉思汗]在树下消磨了一个时辰,他产生了一种内心的喜悦。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众异密和近侍们说道:‘我们的最后归宿应当在这里。’……所以在他逝世后,在那里,在那棵树下,营建了他的宏大禁地。据说,就在那年,这片平原由于大量生长的树木而变成了一座大森林,以致完全不可能辨认出那头一棵树。”[2](PP.259~260)曾经访问过元朝的罗马教皇使者卡尔平尼也说,蒙古贵族的埋葬方式是秘密地选一空旷之所,移开地表上的草木,挖一个深坑,把死者连同生前所用车帐及金银等一并埋入,而后填平墓穴,把草木仍然覆盖在上面,使之恢复原来的样子,以免被人发现。[3](P.14)元末明初叶子奇所著《草木子·杂制篇》曰:“元朝官里,用梡木二片,凿空其中,类人形大小合为棺,置遗体其中,加髹漆毕,则以黄金为圈,三圈定,送至其直北园寝之地深埋之。则用万马蹴平,俟草青方解,则已漫同平坡,无复考志遗迹。”[4](P.60)同为元末人的陶宗仪也在《辍耕录》中有过相类记载。在13世纪中叶成书的《蒙古秘史》中,有关成吉思汗的丧葬仅有“亥年(1227)成吉思合罕升天矣”这样极为简略的记载。今本《元史》虽然记载了元朝诸帝葬于起辇谷,但由于上述原因,有关起辇谷的具体地望,却找不到任何记录。因此,元朝诸帝陵墓的具体位置遂成不为世人所知的千古之谜。
宋元之际,中外文献关于元朝帝陵所在地的记录大体有克鲁伦河、不儿罕合勒敦山、阿尔泰山三种说法。
较早披露元朝帝陵禁地信息的记载见于南宋彭大雅和徐霆所著《黑靼事略》。约在1233~1235年间,彭、徐二人曾先后以南宋使团随员身份出使蒙古,归而分别撰述出使见闻。后来,徐霆将自己所撰书稿与彭大雅书稿互相参照,遂以彭稿为定本,把自己所记不同之处疏于各有关事项之下,因成今本《黑靼事略》。关于成吉思汗墓,彭大雅记载,“其墓无冢,以马践蹂以为平地。若忒没真之墓,则插矢以为垣,阔逾三十里,逻骑以为卫”。徐霆疏曰:“霆见忒没真之墓在泸沟河之侧,山水环绕。相传云:‘忒没真生于此,故死葬此,未知果否。’”[5](P.254)综合二人所记,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其一,成吉思汗陵域位于相传是其出生地的泸沟河即今克鲁伦河之侧,山水环绕;其二,包括元朝帝陵在内的蒙古上层人物墓葬不封不树,“以马践蹂以为平地”,其上没有墙垣、坟垄、享堂、祭殿等地面标识性建筑;其三,成吉思汗的陵域范围“阔逾三十里”,“插矢以为垣”,“逻骑以为卫”。
陈得芝先生据《元史·太宗纪》考证,彭、徐二人出使蒙古期间(1233~1236),太宗窝阔台驻地都在克鲁伦河上游以西至鄂尔浑河上游杭爱山一带,二人都确曾到过窝阔台的大帐;不过,尽管徐霆所疏多用“霆见”云,且所记蒙古墓葬制度与元代的汉文、波斯文、拉丁文史料颇多相合,但从其所记某些内容看,未必都是亲见。说成吉思汗墓葬在“泸沟河之侧”,只记载了大致方位,难以理解为墓地就在克鲁伦河近旁。彭、徐二人都不可能就近观察被定为“大禁地”的成吉思汗墓,所记有关蒙古葬制和成吉思汗墓护卫事项,当得自亲闻,虽然具有很高价值,但不能视为“目击记录”。[6]这样的看法,可谓允当可信。
不过,也应该看到,彭、徐二人出使蒙古之时上距成吉思汗之死不足10年,尽管其所记成吉思汗墓葬位于克鲁伦河之侧得自传闻,但也绝非空穴来风。历史上的克鲁伦河又有泸沟河、庐朐河、胪朐河、怯绿连河等名称,清以后,称为克鲁伦河。此河发源于蒙古国的肯特山东南麓,在中下游的乌兰恩格尔西端进入中国境内,流经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一路蜿蜒东流注入呼伦湖,全长1264千米。成吉思汗所属的蒙古乞颜部以及塔塔儿部、弘吉剌部的原始驻牧地就在克鲁伦河流域,故克鲁伦河又有蒙古人的母亲河之称。徐霆谓传闻成吉思汗“生于此”虽不确切,但其祖上始兴于此却是事实。尽管彭、徐二人所说成吉思汗墓葬在“泸沟河之侧”只是大致方位,不一定就在克鲁伦河近旁,但成吉思汗死后葬于克鲁伦河流域一带,应该大致不误。
无独有偶,约生活于窝阔台到忽必烈时代的伊朗学者志费尼在其所著《世界征服者史》中记载,成吉思汗“在624年剌马赞月4日(1227年8月18日)与世长辞”后一年,各地的诸王贵族“都聚会于怯绿连(克鲁伦)河”的成吉思汗的斡耳朵,举行忽里勒台大会,祭祀成吉思汗,并推举窝阔台继承汗位。[7](PP.214~215)志费尼虽然没有在书中提到成吉思汗的具体葬地,但关于其死后一年蒙古诸部首领都聚集于克鲁伦河畔举行祭祀仪式和忽里勒台大会推举新君,却十分耐人寻味。
《史集》中记载成吉思汗陵墓所在地是名为不儿罕—合勒敦的大山。“蒙古有一座名叫不儿罕—合勒敦的大山……成吉思汗将那里选作自己的坟葬地。他降旨道:‘我和我的兀鲁黑的坟葬地就在这里!’成吉思汗的驻夏和驻冬牧地就在那一带。他出生在斡难河下游的不鲁克—孛勒答黑地方,距不儿罕—合勒敦有六天路程……有一次成吉思汗出去打猎,有个地方长着一棵孤树,他在树下下了马,在那里心情喜悦。他遂说道:‘这个地方做我的墓地倒挺合适,在这里做上个记号吧!’……诸王和异密们遂按照他的命令选中了那个地方。据说,在他下葬的那年,野地上长起了无数树木和青草。如今那里森林茂密,已无法通过。最初那棵树和他的埋葬地已经辨认不出了……这块伟大禁地由兀良合惕部的异密们担任守护。”[8](PP.321~323)
不儿罕—合勒敦山即位于蒙古国北部中央省和肯特省境内的大肯特山的一部分,这条山脉是太平洋水系与北冰洋水系的分水岭,克鲁伦(怯绿连)河、鄂嫩(斡难)河、图勒(土拉)河均发源于此。《蒙古秘史》载不儿罕—合勒敦山地区是蒙古迁居漠北草原后的始兴之地,因此,该山也就成了蒙古人的圣山。据陈得芝先生研究,蒙古部从始居之地额尔古纳河流域迁居到“三河之源”的不儿罕山的时间,约当10世纪之初。[9]
与《史集》大体同时成书的《马可波罗游记》记载:“一切大汗及彼等第一君主之一切后裔,皆应葬于一名阿勒台(Altai)之山中。无论君主死于何地,皆须运葬于其中,虽地远在百日程外,亦须运其遗骸葬于此山……尚有一不可思议之事,须为君等述者。运载遗体归葬之时,运载遗体之人在道见人辄杀,杀时语之云:‘往事汝主于彼世。’盖彼等确信凡被杀者皆往事其主于彼世……蒙哥汗死时,在道杀所见之人二万有余,其事非虚也。”[10](PP.145~147)
到了明清之际,人们已经完全无法弄清元朝诸帝陵墓葬地的具体所在。因此,见于此间的史文记述多为含混闪烁之辞。如约成书于17世纪初叶的《蒙古黄金史纲》记载,成吉思汗死后,被“运往罕山大地,在那里营造了万世的陵寝,作了大宰相们的佑护支柱,成了全体人民的奉祀之神。修筑了永世坚固的八白室……而其真身,有人讲,葬于不儿罕哈里敦;有人说,葬在阿尔泰山之阴、肯特山之阳名为大鄂托克的地方”[11](PP.40~41)。萨囊彻辰所著《蒙古源流》曰:“丁亥年七月二十五日,[主上]在朵儿蔑该城驾崩,享年六十六岁……[众臣]辇舆着主上的遗体起程……一直护送到称为罕·也客·哈札儿地方……由于请不出主上的金体,绝望之中,只好修建了永久的陵墓,在那里建起了普天供奉的‘八白帐’。据说,主上的金体安葬在安台山阴、肯特山山阳的‘也客·斡帖克’地方。”[12](PP.229~232)
针对上述蒙古文史籍含糊其词的说法,亦邻真先生曾经指出,“也客斡特克”可汉译为“大地”,至于“阿尔泰山之阴、肯特山之阳”,这已是一个大而无当的千里空间,等于说葬在漠北高原。[13]
清人对于元朝帝陵地望认识的模糊,还见于康熙朝进士张鹏翮因大青山历史上曾别称祁连山,便望文臆断,认为今天呼和浩特北面的大青山便是元朝帝陵所在的起辇谷。[14]
与清代中国文献相比,同期瑞典人在《多桑蒙古史》中的记载则显得更明确一些。该书载:“(成吉思汗死后)诸将奉柩归蒙古,不欲汗之死讯为人所知。护柩之士卒在此长途中遇人尽杀之。至怯绿连河源成吉思汗之大斡耳朵始发丧……举行丧礼后,葬之于斡难、怯绿连、秃剌三水发源之不儿罕合勒敦诸山之一山中。”[15](P.140)
对于八白室性质的理解,是清代在元朝帝王陵域问题上的又一个认识误区。据学者研究,成吉思汗去世后,岁时祭祀在其生前所居四大宫帐内举行,由于成吉思汗陵墓不封不树,为方便祭祀,遂仿其生前所居庐帐建立八座白色毡帐,号曰“八白室”,以代陵寝;元亡以后,漠北草原的八白室祭祀日渐废弛;明朝中叶以后,漠南蒙古崛起,为确立黄金家族的正统地位,重现成吉思汗时代的声威,达延汗遂移置传统的八白室于鄂尔多斯。[16]清朝政府颁布的《钦定理藩部则例》中称,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境内有成吉思汗陵寝,向设有看守园寝、承办祭祀的达尔扈特五百户。[17](P.92)这样的记述,遂成后人据以误认八白室即成吉思汗陵寝的依据。
二、清亡以来学界的探索
1915年,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张相文在其创办的《地学杂志》上发表《成吉思汗园寝之发现》一文,提出成吉思汗陵寝必置于鄂尔多斯的观点。此论一出,当即遭到著名蒙古史学家屠寄的反对。屠寄针锋相对,也在《地学杂志》上发表了《成吉思汗陵寝商榷书》,认为成吉思汗的葬地不是在内蒙古的鄂尔多斯,而是在蒙古高原肯特山之阳的克鲁伦河侧。张、屠二人于1915~1917年间,就起辇谷所在地问题连续发文,相互辩争。(2)参见张相文《成吉思汗园寝之发现》,载《地学杂志》1915年第3期;张相文《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载《地学杂志》1916年第4、5期;张相文《再答屠敬山成吉思汗陵寝辨证》,载《地学杂志》1916年第8~9期;张相文《成吉思汗陵寝之旁证》,载《地学杂志》1917年第10期;屠寄《成吉思汗陵寝商榷书》,载《地学杂志》1915年第7期;屠寄《答张蔚西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载《地学杂志》1916年第10期;屠寄《答张蔚西成吉思汗陵寝辨证书(续)》,载《地学杂志》1916年第11期。张文认为,成吉思汗葬地在今鄂尔多斯伊金霍洛的主要依据是清《理潘院则例》关于伊克昭盟有成吉思汗园寝、鄂尔多斯七旗设有看护园寝、承办祭祀的达尔扈特五百户的记载及清代中外人士关于成陵的见闻与传闻。这样的立论,证据明显不足。而屠文主张成吉思汗葬于克鲁伦河曲以西、土拉河以东,肯特山之阳的主要依据是《黑靼事略》《史集》等成书较早的文献,同时结合蒙古历史发展的过程,明确提出元朝帝王的葬地与作为祭祀场所的八白室分离的见解,指出元朝帝王的葬地是在四大斡耳朵所在的漠北蒙古高原,而八白室则是可以“自北移南,随地张设”的园寝。现在看来,这样的立论较之张说,明显更具合理性。但是,由于缺乏考古实证材料,屠寄只是重申或强调了《黑靼事略》和《史集》等书的说法而已,并无实质性的创新建树。这场持续两年之久的论争,结果只能是不了了之。
有关元朝帝王陵墓葬地问题,至今仍然是一个持续争辩的话题。
1983年,陈育宁在对有关元朝帝陵的原始文献进行重新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了屠寄的说法,进而分析了由于秘葬缘故导致成吉思汗的葬地与供祭祀之用的陵园相互分离的历史过程。陈育宁指出,成吉思汗时,有四大斡耳朵,负责守卫斡耳朵的人甚多;成吉思汗死后,他们又负责守护和供奉八白室,世代相传,子孙繁衍,逐渐形成一个被称为鄂尔多斯的部。16世纪初,八白室被移奉于河套地区后,传统的祭祀活动被延续下来,并且逐渐形成了更加完整的祭祀仪式和制度。[18]关于成吉思汗陵墓与八白室祭祀传统,赵永铣、那顺巴依尔、奇斯钦等都曾撰文,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较为深入的论证。(3)参见赵永铣《成吉思汗奠祭的由来与流传》,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那顺巴依尔《成吉思汗祭祀的历史演变及境遇》,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奇·斯钦《鄂尔多斯部的由来》,载《内蒙古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奇·斯钦《元朝时期的守宫与今日成吉思汗陵的渊源关系——兼论成吉思汗陵的性质》,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1994年,色音、佟德富、陈喜忠联名撰文,就成吉思汗陵墓位置问题提出新的见解。他们称拉施特所著《史集》关于成吉思汗陵墓的位置有两种说法,其一是在不儿罕合勒敦,其二是在不劣温都儿。关于不儿罕山,拉施特没有明指,因此今日不知此山在何处。而《史集》在叙述巴牙兀惕部落史时,极详细地谈到成吉思汗墓在薛凉格河上游的两个发源地,一曰不劣温都儿,一曰忽儿班·客赫惕,“成吉思汗陵墓位置就在古代的哈剌和林之侧的契辇杰(薛凉格)河两源,南限为翁给河这一三角地带”。[19]显然,这样的意见既无考古实证,也稍嫌缺乏历史文献学角度的实质性创新。
1989年,著名蒙古史学家亦邻真发表《起辇谷和古连勒古》一文,运用历史学、语言学交叉互证的方法,根据“起辇谷”的元代读音,认为起辇谷就是《蒙古秘史》中所载“古连勒古”的雅译,二者为同一地名,其地在今蒙古国肯特省曾克尔满达勒一带,指出起辇谷的地理位置与《史集》上记载的大禁地没有什么差距,《元史》的记载与《史集》也并不矛盾。12世纪80年代,成吉思汗摆脱了对札木合的依附,第一次建立汗斡耳朵的地点正是在古连勒古——起辇谷。亦邻真同时指出,称成吉思汗葬于鄂尔多斯是把祀堂和墓地混为一谈,这样的说法与称伊金霍洛为起辇谷一样,均属讹传。[20]
亦邻真先生关于起辇谷具体方位的考证,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反响。如宝音德力根补充说:“成吉思汗的葬地起辇谷——古连勒古就在不儿罕合勒敦(今肯特山)阳……早在蒙古汗国时期,合不勒汗、忽都剌汗等成吉思汗的先祖的遗骨就被葬在古连勒古……肯特山是由大小肯特山组成的绵延几百里的大山脉;不儿罕合勒敦是指桑古儿河源头西北的属于肯特山主峰的几座山,有时也泛称肯特山为不儿罕合勒敦;古连勒古则是指不儿罕合勒敦之阳的某个山,桑古儿河就发源于此山中,成吉思汗的陵地‘大斡秃克’也应在这里。”[21]陈得芝先生也认为亦邻真关于起辇谷就是《圣武亲征录》所载“曲邻居山”、《元朝秘史》(明初汉译本)作古连勒古的同名异译之说,“其语言学、历史学的论证都十分精到,令人信服”。陈先生指出:“古连勒古是蒙古乞颜氏和成吉思汗的始兴福地,徐霆所谓‘相传忒木真生于此,故死葬于此’,应该是‘兴于此,故死葬于此’……综观《秘史》各节记事,其地应在‘不儿罕山前(南)’,是可以容纳众多牧民居住的水草丰富的原野,曾克尔满达勒一带位于肯特山南麓,原野宽广,符合‘古连勒古’之地的条件……在曾克尔河中上游一带的肯特山南麓坡地寻找元朝诸帝墓葬,方位应该是对的,只是范围大,寻找元朝诸帝墓葬所在,仍需历史—考古者的艰苦努力。”[6]
与元朝帝陵葬地位于漠北蒙古草原这种主流观点相左,近年国内不断有人撰文阐发成吉思汗陵墓葬地就在中国境内的观点。如1993年以来,宁夏的李子杰力主成吉思汗的陵地是在甘肃南部的六盘山。[22][23]持此说者,还有张承志等。[24]2000年,有人撰文称成吉思汗陵墓有可能在新疆北部阿勒泰山中[25]。2002年,内蒙古有学者又称起辇谷就在鄂尔多斯,根据是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境内的阿尔寨石窟(又名百眼窑)发现了成吉思汗丧葬图[26]。近年,类似成吉思汗陵墓所在地就在内蒙古鄂尔多斯的说法时有所见[27](PP.359~374)。
所以出现如此之多的各种说法,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成吉思汗以盛暑之季逝于征伐西夏军中,按照常理,遗体不大可能运往数千里之外的漠北草原。针对这种认识,薄音湖指出,在《元史》记载中,“元朝帝王均葬于漠北起辇谷,其中不乏酷热之时逝于南边而归葬北方起辇谷的记载。如元英宗八月逝于南坡(上都西南二十里处),泰定帝七月逝于上都,元明宗八月逝于旺忽都察之地(今河北张北县北),元文宗八月逝于上都,以上去世时间均为夏秋季,去世地点离起辇谷的距离,只比成吉思汗去世的宁夏距起辇谷稍近一些而已……这些帝王们的遗体如何在暑天加以保护并被运往数千里之遥的起辇谷,详情已不得而知,但的确都归葬于北方”[28]。
在历史学界围绕元朝帝陵葬地问题持续进行讨论的同时,考古界就这一课题也积极地开展了实地考察。早在1925~1926年,苏联著名蒙古史学家符拉基米尔佐夫在对乌兰巴托一带和肯特山地区进行民族学、语言学调查过程中,试图在肯特山一带探寻成吉思汗的葬地,初步发现了元代的祭祀场地遗迹,同时还发现有当时的祭器遗存。[29](PP.1~42)
20世纪60年代,蒙古国考古学者德·普尔赖和联邦德国学者舒伯尔特以《蒙古秘史》为基础资料,在蒙古国肯特省地区进行了多次考古调查,但最终没有获得实质性发现。[30]同时,民主德国的考古学者也与蒙古国有关学者合作,于1961年在肯特省德勒格尔罕县境内,对阿乌拉嘎遗址进行发掘,结果找到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遗憾的是,这项重要发现在当时并未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31](P.120)[32]
1990~1993年间,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和蒙古国相关学者组成的蒙日“三河源”联合考察队,斥资上亿美元,利用卫星遥感技术、航测直升飞机以及当时最先进的勘测仪器对三河源一带进行了拉网式的遥测勘探,企图寻找元朝帝陵,结果发现了大量蒙古汗国之前的遗址遗迹,但于蒙古帝陵却一无所获。
1995~2002年,美国的探险者和考古者也动用卫星遥感、GPS卫星定位和更高清晰度的卫星图像,详细分析蒙古国东部地区,寻找数年,同样也没有实质性收获。[33](PP.96~100)
从1990年起,日本新潟大学的白石典之也在蒙古国展开了对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史迹的考古调查,发现了位于蒙古国中央省额尔德尼县哈老徒河西岸的成吉思汗下葬前曾经停灵的哈老徒行宫遗址。[34]2001~2004年,白石典之与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朝格特巴特尔合作,联合对肯特省德勒格尔罕县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阿乌拉嘎遗迹进行了再次发掘,共发现4层文化堆积。其中,第一层的年代范围约在1155~1270之间,遗迹包括宫帐、街区、房址和作坊,其中宫帐遗迹应该包括成吉思汗的宫帐在内。第四层的年代为13世纪中期至15世纪,主要遗迹为祭祀成吉思汗的灵庙遗址。[35]白石典之认为,成吉思汗灵庙是由成吉思汗的皇宫(大斡耳朵)演变而成的,它是现存于内蒙古的成吉思汗灵庙的原始形态。[36]哈老徒行宫遗址和成吉思汗大斡耳朵宫帐及灵庙遗址的发现,无疑是元朝帝陵考古的重大发现,从而为寻找成吉思汗陵墓葬地增添了重要的新线索。
200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组织蒙古高原考察队,赴蒙古国实地考察青铜时代至明清时期古迹,包括日本学者白石典之调查和发掘过的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曲雕阿兰宫帐遗址和萨里川哈老徒行宫遗址。据考察队的林梅村介绍,曲雕阿兰行宫遗址位于克鲁伦河上游支流阿布拉加(阿乌拉嘎)河口的北岸,遗址的A区为成吉思汗殿帐遗址,遗址内有石头砌垒的“凸”字形台基,遗址的南墙有门,与《黑靼事略》所载“主帐南向,独居前列”相符。在殿帐台基北侧和东侧分布有许多年代为13~15世纪的祭祀坑,坑内出土了大量烧过的牲畜骨头,尤以马骨居多。林梅村引《草木子》中“元朝人死,致祭曰烧饭,其大祭则烧马”的记载,认为成吉思汗殿帐附近发现的祭马坑,即黄金家族为成吉思汗亡灵举行大祭的典礼之处。在白石典之调查的基础上,林梅村进一步明确指出,位于今蒙古国中央省额尔德尼县境克鲁伦河上游西岸的波罗流兀特土城就是成吉思汗下葬前曾经在此停灵的萨里川哈老徒行宫遗址。林梅村还据波罗流兀特土城的考古发现,认为《马可波罗行纪》中所载成吉思汗死后埋葬的阿勒台山即《析津志辑佚·河闸桥梁》中的“金山”,《蒙古秘史》称之为“古连勒古山”,《元史》称之为“起辇谷”,由此认定元朝帝陵就在桑沽河中游西岸哈剌只鲁山和颗颗脑儿附近。[37]这是中外学者有关元朝帝陵所在位置的最新说法。不过,这种说法同样出于推测。元朝帝陵葬地的最终发现,目前仍然任重而道远。
三、几点认识与思考
元朝帝陵的葬地问题是一个举世瞩目的重大课题。数百年来,曾有无数优秀的中外史家和考古家前赴后继,先后加入到探索的队伍当中,尽管用力弥多,但收效并不明显。与此同时,还有数不清的探险家、文化工作者以及政府公务人员也都曾为这一课题付出了不懈的努力。这种现象充分说明,元朝帝陵问题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远远超出历史学、考古学研究范畴的富有挑战意味且具无限魅力的综合性课题。
总括前人在元朝帝王陵墓葬地问题上取得的主要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明确认识。
其一,受到归葬祖茔之俗的影响,元朝历代帝王死后都葬于漠北的起辇谷,而不在漠南的内蒙古或甘肃,更不在新疆和四川。位于今天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园并不是真正的陵墓,而是成吉思汗的灵庙。成吉思汗死后,其生前的宫帐(斡耳朵)由后妃们依次继承,负责掌管陵寝守卫和灵庙祭祀。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后,元廷封宗王甘麻剌及其子孙为晋王,镇守漠北,兼领四大斡耳朵,史称“守宫”。历史上的八白室与今天鄂尔多斯的成吉思汗陵园性质相同,均属成吉思汗灵庙,为元朝守宫祭祀之制的产物。
其二,如果诚如有关学者所说《元史》所载安葬蒙古大汗及元朝诸帝的起辇谷就是《圣武亲征录》中的曲邻居、《蒙古秘史》中的古连勒古的话,此地与《史集》所载的不儿罕合勒敦山也并无多大矛盾,其地望大而言之,都在克鲁伦河上源一带。
其三,既然蒙、日、美等国的考古学家已经对蒙古国境内的三河源地区以及克鲁伦河中上游一带进行了拉网式的调查而未能获得最终突破,这就意味着中国境内的克鲁伦河下游至呼伦湖一带,也属于有希望发现元朝帝陵的重要地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