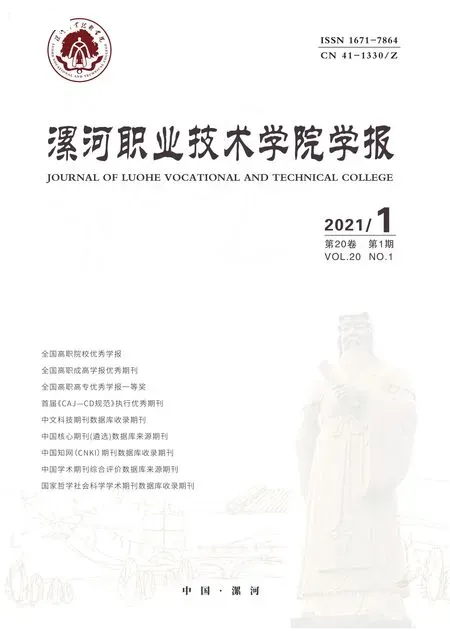诗词格律对绘画色彩教学的启示
2021-12-29赵曦
赵 曦
(郑州大学 美术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魏晋南朝以后诗文越发精美,齐朝永明体发现并开始运用音律,直至唐初沈佺期、宋之问确立“格律诗”。今体诗在字数、韵脚、声调、对仗各方面有许多讲究,词也有严格的声律和种种形式上的特点,如每个词调都是“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这些严格的声律,使词比诗更具有音乐性,每个曲调都表现一定的声韵、达定的情感。如写豪情壮怀,就用《满江红》《令奴娇》《贺新郎》《沁园春》等类慷慨激昂的曲调;如写绵邈深婉之情,则用《满庭芳》《木兰花慢》等类和谐婉约的曲调,如此就能达到声文并茂的艺术效果,增强艺术感染力。刘勰《文心雕龙·声律》曰:“夫音律所始,本于人声者也。声合宫商,肇自血气,先王因之,以制乐歌。故知器写人声,声非学器者也。”[1]人的声音有大小高下之殊,乐器有宫、商、角、徵、羽之异。乐器写的是人声,人声的宫商与乐器的律吕相合。律,代表的是一种风格,中国古代定音之器称为“律管”,固定音律“律吕”,诗词根据音之律吕、声之平仄飞沉形成具有中国古典文学风格的诗词格律。诗词必言及声,作乐必言及音,绘画必言及色。诗词、音乐有调,色彩亦有其色调。我们可以通过对绘画的色彩分析来了解具有中国古典风格特征的诗词格律,也可以通过中国古典诗词格律重新思考绘画色彩的节奏和旋律。
一、飞沉抑扬与传统五色
诗词根据“四声”——平、上、去、入(异音飞沉抑扬)进行和调,古代色有“五色”——黄、白、青、黑、红。王原祁《麓台题画稿》中《仿没色倪黄为刘怀远作》曰:“声音一道,未尝不与画通。音之清浊,犹画之气韵也;音之品节,犹画之间架也;音之出落,犹画之笔墨也。”[2]对于色彩使用的规律,无论东西方皆有一定的“律”。中国传统的五色观对比西方的三原色,虽多出来黑白两色,但是依然是有非常明晰的明度高低的变化。如中国传统称绘画为“丹青”,以及较显著的“黑、白”两色的使用、青绿山水等等。例如先秦的色彩搭配使用,运用率较高的就是黑色和红色,尤其漆器最为典型。马王堆一共出土700多件漆器,大部分都饰有花纹,装饰的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最主要的是彩色漆绘,多用朱砂、石绿、石青、白粉等矿物质颜呈现红、黄、白、金、灰、绿等色彩。红黑两色,对比强烈,显得非常清晰,一般多用黑色为底,以红色和灰绿、赭色作画,赭色与灰绿色同红色配合。当佛教进入中国之后,色彩的使用受到印度佛教色彩的影响,发生了很多变化,较为典型的是唐代山水画色彩,出现金碧辉煌的青绿山水。这些都是运用传统色彩的一些基本认知规律,在变化中不断寻求自身的发展。
较之音乐与诗词的“律”,关于中国画色彩“律”的总结略显松散,大多出现在个人的画论中或师承关系中,较少有极其系统的归纳总结。传统五色的运用如同格律,尽管没有严格的“律”,但是固定的色彩、构图、线条,便是一种节奏、一种“律”,就会产生各不相同的风格。如中国画与日本浮世绘画、西方新古典主义、现代派等相比较,其色彩不同的韵律节奏,如快慢舒缓、明亮阴沉、空旷萧瑟等等,自然产生各自不同的风格特色。绘画、音乐、诗词的“律”若因时而论,也会由于不同的格律而形成不同时期的风格,这在艺术形式上是最容易被发现的,就是因为我们找到了可以为它们定格的有规律的形式特征,例如随着朝代的更迭,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服装与仪容在色彩格律方面会有所变化;不同民族的装饰汇聚在一起,又会形成另外一种风格特征,这就是时期主旋律。
二、诗词和调与色彩旋律
韵与声,极其具体,“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3]飞,即扬,声平清;沉,即阴、抑,声仄浊。如《诗经》的双声叠韵:“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4]“关关”是双声,“窈窕”是叠韵,写生或绘画创作者完全可以将其理解为同类色技法的运用。齐·梁《音律论》谈到“声”“韵”“调”,主要是“韵”“调”,尤其是“调”,因为“韵”比较明显,而“调”比较隐藏。如“辘轳交往”[3]所表达的是比较圆转、柔和的同类色,而“逆鳞相比”[3]对应的则是对比色和补色,这不仅是诗词韵声,也是色彩三要素运用中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声高声低、双声叠韵,色彩的色相、明度、纯度,这些都比较好理解,但对于画面的整体色调而言,如何将这些元素放在画面里,达到和谐的效果,表达出作者的情志,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旋律的高低,来自五音十二律的黄钟大吕、字调的升降飞沉抑扬、五色的明度纯度。若抛开艺术作品,单独讨论色彩的色相、纯度、明度是简单的。也就是说,如果只谈飞沉、抑扬,则不知如何在作品中将其处理或者和成更加恰到好处的“调”。色彩的明暗、冷暖与声音的清浊只是感受,定的“调”是高还是低,所表达的是悲壮、凄凉、空旷悠远还是温婉柔情,基调和节奏所产生的旋律才是最主要的。无论是诗词、音乐还是画面,表达的是一种感情,在写生和创作过程中,如何根据作者的主观情志,使用五音、声韵、五色,做到“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这个过程是比较隐晦的。
在诗词格律赏析教学中,将画面的色调与诗词、音乐的“律”相结合,这样能让美术专业的学生理解中国古典诗词的风格特征,在绘画写生与创作教学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审美意象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在色彩创作教学中,学生可以将所要表现的物象与个人触景感受相结合,通过使用自己常用的几种色彩,对画面色调进行主观的控制,在和谐色调的同时形成自己画面的主色调、主旋律以及独特的风格。这也是宋词对平仄韵脚、字数都有较为固定的格式,以及所形成的固定的词牌名产生不同风格曲调的原因之一。如用中国古典乐器古琴、二胡,演奏现代狂欢乐曲,就无法产生古琴的悠远空旷和二胡的凄凉悲伤。赤橙黄绿青蓝紫,固定的色彩搭配与个人情绪爱好的选择,都会使画面产生截然不同的旋律与风格。弦,还是那几根弦;音,还是那几个音;色,还是那五色(或者说三原色),所不同的是同类色的单一协调,单一与对比的处理,对比色、补色的相互冲击与协调,或通过比例对比,或通过纯度对比,根据作者主观的情感是视觉的柔和还是视觉张力的突显,或减弱冲突,或增强对比,使调的“和”在多变的同时形成各自独特的旋律和风格。绘画是一种视觉语言,画面中的色彩依然如此,色彩的纯度、明度、冷暖就是一种律吕,我们常会说画面的“色调”“基调”“调调”,这就是一种声音、一种符节、一种节奏。色调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在统一的色调基础上,根据主观心声的需要,调整画面色彩的明度(高下)、纯度(浊清)、冷暖(宽窄),使色调与内心的思想情感达到和谐一致。
三、诗词平仄与色彩明度纯度
中国古汉语有四种声调,称为平、上、去、入。平,平声,包括今之阴平、阳平。仄,是不平的意思,即上、去、入三声。除了平声,其余三种声调有高低的变化,故统称为仄声。唐宋以后的诗词是讲究声调的,如在用韵时,平声不和上、去、入声押韵,上、去声也不和入声押韵,律诗、绝句在韵的基础上还要讲究平仄。平仄声调互相交错,就能使诗词的声调多样化,而不至于单调,节奏美感由此而出。没有平仄就没有诗词格律,换言之,色彩没有明度、纯度变化,画面就会失去节奏和韵律。郭绍虞在《蜂腰鹤膝解》中写道:“外听指乐声言,内听则指诗文的声律言。”[5]乐声音高下有定,诗文声律的标准则无定;色彩的明度、纯度有高低,但是画面的整体节奏与色调并无一定的标准。内听之心声是情发肺腑,诗文的声律自然流露;绘画作品的节奏旋律也会自如符节之相合。“响在彼弦,乃得克谐,声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外听易为察,内听难为聪也。故外听之易,弦以手定,内听之难,声与心纷;可以数求,难以辞逐。”[1]外听,琴弦能调,手挥琴弦各发其音;明度和纯度皆可调,如实描写便是。而内听之难,则在于“羚羊挂角,无迹可求”[6]。当然,规律是可循的,于是便可制定一些原则,几个声调共同构成旋律,几种颜色共同构成主旋律色调,或明或暗,或灼或淡。在不影响内容的前提下,色彩的明度和纯度变化是绘画艺术作品给受众最直接的视觉感受。
诗词之韵是就字词的音而言的,音有“音阶”,色有“色阶”。中国旧谱以宫、商、角、徵、羽为谱,即表示音阶大小。西洋为五线谱,皆系“音阶谱”。十二律吕,各律在弦上也是有长度的,音各有高度,各器皆得通用。色阶,是表示图像亮度强弱的指数标准,就是色彩的明暗变化,它与色相没有关系,但却与色彩的纯度密切相关,即明度在提高或降低的同时,色彩的纯度也发生着相应的变化,甚至可以通过色阶调整画面的阴影、中间调和高光的强度级别,从而修改画面的色调范围,打破原有的色彩平衡,创建新的色彩基调与旋律。音阶的大小,声音的高低,与色彩的明度、纯度一样,都是相对而言的,非若律吕各自只有一定高度。声音的高低清浊与色彩的明亮程度与纯度变化一样,影响着画面色彩基调、节奏与旋律。如在色彩明度与纯度的衍生下,会有色彩的同类色对比、冷暖对比、补色对比以及面积比例的对比,甚至可以通过视觉残像的原理调整画面的色彩关系。
四、艺术源于生活的取舍
无论是文学诗词还是绘画音乐,艺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如何取舍,这是每一位艺术家创作中面临的问题。《文心雕龙·声律》曰:“夫吃文为患,生于好诡,逐新趣异,故喉唇纠纷;将欲解结,务在刚断。左碍而寻右,末滞而讨前,则声转于吻,玲玲如振玉;辞靡于耳,累累如贯珠矣。”[3]自然为先,善于刚断,不能让完美的局部色彩影响整张画面的色调。音声迭代,五色相宣。宫商角徵羽、黄白青黑红,声有飞沉四声、弦有五音、色有五色,同类和邻近并无绝对的定律,是通便可易的。音节,神气之迹,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字句,音节之矩,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这实际上是根据作者的主观情绪和艺术作品的内容来处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而画面的神采除了形体结构之外,还有色彩渲染。画面的形式感也是一种基调,基调没有一定的准则,但是可以通过用具体的色彩来体现,色调是否和谐,画面的结构是否流畅,这就要看局部色彩与结构的处理。画面节奏感弱,色彩自然也不会流畅,若过于近其形,情感就极易浮躁,就会牵动画面的主旨、主旋律,致使局部的声韵、色彩改变了初心。
“风力穷于和韵”,作品的风神骨力最终要表现在和韵的问题上,即有取有舍、协调统一的问题。如何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色彩的简化、形体结构的平面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具有统一的韵律与节奏。平仄之和调,谓之和,是声调的升降抑扬相从。句末所用“韵”,谓之同声相应,这是韵脚。“韵”是有规律的,“和”是自然的且没有规律的,画面最终形成的色调并没有一定的规律,在写生和创作教学实践中,可以使用有规律的色彩搭配形式,但不一定最终就能成为你所想象的基调或旋律。也许在创作过程中,细微的色调色彩变化,让画面的调与当初设想的完全不同。因为,五色、五音只是一个工具,一个创作工具,具体运用中则是千变万化的,但无论如何,中国的“韵”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所谓“西技东韵”只是一种创作手段,而最终神气骨力便在这“和”上。和,既是一种取舍也是一种协调。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韵气一定,则馀声易遣;和体抑扬,故遗响难契[3]。羽相变,五色相宣,和而不同,是统一与矛盾的关系。平仄、五色、五声,相间相重,是和。传统用色特色、构图形式,这是一种韵,但实际上韵之易,在于其有迹可循,可是“和”就无影无踪,千变万化了,“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7]这与司空图认为诗歌的极致是“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一脉相承。
《高僧传·经师论》所谓“和”,是运用梵赞转声之法,以论汉土诗歌之音律。《鱼山梵》曲调的主旋律,是汉语声律“转赞七声,升降曲折”的特点和“梵天之响,清雅哀婉”的意蕴所构成,佛教僧徒把“梵呗”看作是具有中和之美的华夏佛音。诗词读起来朗朗上口,这就是口吻易调。求“和”,需注意的是“抑扬”相从。韵易,这是声音的回环、常用色的特点能够把握。难就难在异音相从之和,平仄、五色如何相协调,抑扬、轻重、多少如何把控。“属笔易巧,选和至难”,色彩的写实、精巧容易,如何成调、成为风格就难了。“缀文难精,而作韵甚易。虽纤意曲变,非可缕言,然振其大纲,不出兹论。”[3]为求异而相从,五色的同类色对比等也是和而不同,避同求异。就是在这样的统一与对立中形成画面色彩的韵律与节奏。“和”是技法,求的是异;而“韵”是形式,求的是同。旋律的和谐是主观性的取舍完成的,在诗文和画面中为了不影响内容与情志,律吕韵律、色彩明度纯度等是可以改变的。
区域文化也为诗词与色彩的格律带来了一些地域性特征,诗词尤以方言为典型,因为方言在发音上会出现另外的声韵、节奏与旋律。如《诗经》常被认为是正声雅音,《楚辞》则是“讹韵实繁”“失黄钟之正响也”。但是清代古音学家已经证实了《诗经》《楚辞》用韵完全是相同的,也就是说由于诗词格律的地域性问题,通常受方言发音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调,但是用韵是没有差别的。对于色彩而言,五色完全相同,不同的是色彩的搭配与重新组合,构成为特定区域、环境的视觉代言,这是具有区域自然特征之“律”色彩。无论诗词、音乐还是绘画,情感的表达要高远,而音韵、色调则要习近。
诗词格律作为美术专业的选修课,一直以来都是以欣赏和文学常识与众生共享,然而最早将声音与色彩相提并论的文章是陆机的《文赋》,“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固崎锜而难便。苟达变而识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秩序,故淟涊而不鲜。”[8]世间万物千姿百态,色彩随物而变,音声抑扬交替而成文章,就如同五色清浊高低不同而相间成为锦绣。可见,汉末魏晋时期,不仅是文学的自觉时期,也是艺术审美的自觉时期。沈约的《宋书》中《谢灵运传论》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9]进一步将诗词格律与色彩相提并论,互为解释,认为韵律和谐才能八音协畅,五色相宣才能各适物宜。音在高低变化间产生节奏,绘画则在色彩的明度、纯度相互协同中产生基调和旋律。将诗词格律赏析和色彩教学相结合,深入分析格律与色调、和调与旋律、平仄与色阶以及主观情志与色、音、声的规律,在“律”的取舍及和调中,让美术专业学生深入了解中国古典文学与色彩艺术之间同血脉、同发展的传统美学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