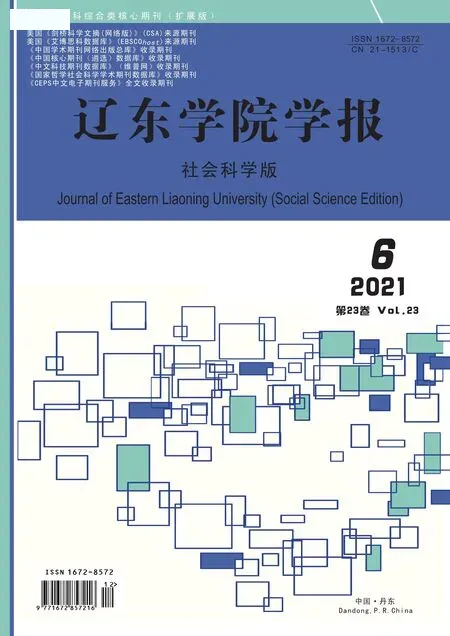西晋不同社会群体的国家认同演变
2021-12-29郑宇虹崔向东
郑宇虹,崔向东
(渤海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目前,“中国古代国家认同”已成为古代史研究的新视角,成果愈加丰硕。西晋统一的五十余年中,各民族思想文化不断交融碰撞,不同社会群体的国家认同值得研究。彭丰文在其专著《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1](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中,探究了两晋时期民族冲突与融合在国家认同形成中发挥的作用;姚大力在《追寻“我们”的根源: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与国家意识》[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一书中,对魏晋民众国家意识变化进行了论述;彭丰文的《从〈华阳国志〉看两晋巴蜀士人的民族观念与国家认同》[3](《中国边疆民族研究》2012年第6辑)一文,从精神文化的角度探析了两晋巴蜀士人对中原王朝政治统治的认同。基于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本文对西晋不同社会群体的国家认同演变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国家认同与国家政治安全的密切关系。
“认同”是人们心理上对某一事物产生的归属感和认可,是一种长期而稳定的心理状态,而“国家认同”则是一种心理的归属和对整个国家制度、文化、族群等各方面的主动接受。一般认为,中国古代国家认同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在改朝换代之际,或者在多个政权长期并立的政治局面下,人们对新旧政权或各个并立政权的辨识与选择;第二个层面是对所选择、所归属政权的热爱与依恋。”[4]显然,这两个层面在认同深度上有着递进关系。古代社会“国家认同”最基本的表现是接受某一政权的统治,即第一个层面的认同,也是政权巩固统治的重要因素。而第二个层面则是在第一层面的基础之上,对国家情感的进一步延伸,其热爱和依恋可表现为忠君、爱国等方面的具体内容。此外,“中国”认同和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可在一定程度上也属于国家认同的范畴,“‘中国’和‘正统’这两个观念本身,就是对超越了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的一个历时性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与政治追求的意识。这应当就是前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的第三个层面”[2]19。这些表现皆是历代统治者希望民众所能达到的对国家认同最理想的状态,其原因在于“国家认同与社会秩序的生成密切相连, 国家认同的水平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5]。笔者正是在这种国家认同观念下,对西晋不同社会群体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进行讨论,不当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一、士人阶层国家认同的逐步深化
士人阶层在战国时开始兴起,至西晋时期已臻成熟,并成为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因素。太康元年(280年)孙皓请降,至此西晋完成了统一南北的大业。疆域的统一有利于促进民族的融合以及文化的整合,以往东吴、蜀汉政权的士人随才擢叙,纳入了西晋的官僚体系之中,他们的国家认同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些士人在西晋的入仕是在东吴、蜀汉政权灭亡后转而对西晋的选择,他们国家认同的观念亦必然经历从对东吴或蜀汉政权的国家认同到对西晋的国家认同的转变。这些士人大多都出自豪门,背后依仗着宗族的力量,他们仕宦西晋,亦等同于整个宗族势力对西晋的依附,因而这些士人国家认同观念的转变也是西晋初期内部政权整合时必经的一个过程,但这样的认同仅是达到了前面所提及的第一层面,即完成了对新政权的选择。
随着西晋政权稳定发展和忠君爱国等儒家文化的渐染,士人阶层的国家认同观念逐步加深,这一点可体现为他们对国家正统性的高度认可。《晋书·礼志下》载平吴之后,西晋的疆域“东渐于海,西被流沙,大漠之阴,日南北户,莫不通属”,其国威远扬,“声教所被,达于四极”[6]655。因而,太康元年九月,卫瓘、山涛、魏舒、刘实、张华等人以天下一统为由,先后五次奏请晋武帝封禅,认为晋武帝之功堪比唐虞三代君主,应封泰山,禅梁父,向天下宣扬其功绩。然而,晋武帝以“所议诚列代之盛事也,然方今未可以尔”[6]657为拒。虽封禅未成,但从群臣屡次提出封禅的态度中可见,西晋士人认同晋受命于魏具有合法性。显然,西晋开国之初群臣欲用封禅这一仪式来宣扬晋武帝功绩,强调君权神授以进一步巩固西晋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些士人对西晋一统天下的自豪和对其政权的高度认同。
此外,士人阶层对西晋的国家认同还体现在“西晋即‘中国’”的认识上。古代“中国”一词,“并非仅仅指称天下中心的洛阳地区,还具有指称地理学意义上的京师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政权,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7]。当“中国”指代“国家”时,“中国”认同便也纳入了国家认同的范畴。《晋书》中多有士人称西晋为“中国”的记载,如袁甫曰:“寿阳已(以)东皆是吴人,……寿阳已(以)西皆是中国”[6]1455。这里就是用“中国”指代西晋,并明确指出了吴与西晋疆域以寿阳划界。又如在《徙戎论》中,江统建议将诸戎徙出塞外,“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6]1532。此处所谓“绝远中国”,具体而言是指边疆少数民族迁出塞外后将远离西晋的疆土,即便有叛离之心,经山河阻隔,亦不会对西晋造成太大的影响。从这些指代中可看出,士人阶层认同西晋能够代表“中国”,因而他们的“中国”认同亦是对西晋的国家认同。
姚大力认为:“忠诚于国家的观念对推动国家认同的发育和强化具有更加关键、更加积极的意义。”[2]80这样的观念反映到古代政权上具体又可表现为对某一皇帝的忠诚或是对某一姓统治的政权的忠诚。士人阶层对于西晋的国家认同,在更深层次的情感倾向中,亦体现在“忠”的意识上,尤其在西晋皇室倾颓之际,西晋士人忠肝义胆的国家认同体现得更为鲜明。西晋末年,晋怀帝于平阳被俘, “刘聪大会,使帝著青衣行酒。侍中庾珉号哭,聪恶之”[6]125。西晋皇帝被辱之际,侍中庾珉不惧刘聪强权,以号哭表达自己的哀恸,这般亡国之际的悲国之情也是对西晋国家认同的表现。此外,西晋末年虽有士人范隆、朱纪等依附刘元海,皆至高位,但更多的西晋士人仍固守着对国家的依恋和忠诚。如崔游年七十时,晋武帝就家拜郎中,“及刘元海僭位,命为御史大夫,固辞不就”[6]2352。永嘉之乱后,刘琨毅然率领部下将士在晋阳镇守九载,并上表陈情,“聪、勒不枭,臣无归志”[6]1684。这般士人的气节及对西晋深厚的国家认同在刘琨等将士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诗妖”所见平民阶层国家认同的消解
“诗妖”是指古代具有祸乱征兆或是含有批判统治阶级之词的里巷歌谣,多以童谣的形式广为流传。如《汉书》言:“君炕阳而暴虐,臣畏刑而柑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8]1377它的出现与当时的政治统治、社会环境皆密切相关,对“诗妖”的解读可成为从底层社会窥探西晋统治者施政得失的一个视角。因而,从这些“诗妖”中亦可透视平民阶层国家认同的消解过程。现将《晋书》所载西晋各时期民间流传的“诗妖”摘录如下,见表1。

表1 西晋各时期的“诗妖”统计表
如上表所示,太康三年(282年),即西晋平吴第三年,江南再三出现预言吴当复国的童谣。史家言,“局缩肉”是预示“元帝懦而少断”,“中国”指代的是西晋;“宫门柱,且当朽”[6]844,寓意西晋政治的腐朽,又言30年之后,吴能轻易推翻西晋的统治。因这些童谣的散播,吴人皆以为孙氏子孙中定当有能复吴者,于是相继为乱。从江南童谣的传播及其在此煽动下产生的动乱来看,吴地虽已统辖于西晋的疆土之中,但在前期江南仍有部分百姓对吴政权有着深厚的眷恋之情,他们对西晋的国家认同,仅是屈服于西晋武力之下而接受的统治和对西晋政权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吴人在与中原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不断加深对西晋的国家认同,后期史书上也再未出现含有“复兴吴国”之意的江南童谣。晋武帝即位后,颁布律法,大封宗室,罢州郡兵,政治逐步趋于稳定。同时又制定“户调式”,发展生产,从而造就了太康盛世,这一期间史书中皆是赞誉之词。然而,晋武帝晚年“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6]80,朝中“三杨”贵盛,又凭借着丰厚的国力,好征伐之事,市井民巷中遂传出《折杨柳》之歌,言兵革苦辛。此外,“杨柳”含有“杨”字,指代的是当权杨氏,“折杨柳”又暗喻着杨氏的没落,其后“三杨”族灭,太后幽死中宫,正应了“折杨柳”之言。从表1对西晋“诗妖”的统计来看,晋武帝时期的讽刺性歌谣仅有两条,分别出现于平吴初期和执政晚期,太康盛世之际,却没有此类歌谣的记载,因而“诗妖”的出匿与政局的稳定与否有密切关联。

以上西晋中后期出现的“诗妖”皆是百姓结合朝政动乱之况,对不同阶段奸佞当权的痛恨和对乱臣贼子进行的控诉。它们的记载将西晋诸多重大政治事件串联在一起,从另一个视角为我们展现了西晋权力斗争的残酷。从“三杨”当权、贾后干政到八王之乱、怀帝即位,西晋政权在权力的争夺中日渐衰微,平民阶层饱受饥寒丧乱之苦,流民四起,人皆相鬻。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所传达的多是百姓对西晋上层贵族争权夺利致使民不聊生的愤懑之情。然而,这一时期仍未出现直接怨怼君王的谣言,甚至在赵王伦篡位后,还盼望“一马化为龙”。元康年间,关西大饥,百姓“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6]3022。永嘉之际,并州流人“十不存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6]1680。由此,在西晋统治阶级的腐败和压迫之下,李特、张昌、王如、杜弢等人先后领导流民起义,响应者“赢粮而景从”,平民阶层对西晋的国家认同逐步崩塌。因而“诗妖”频频出现亦是西晋国家认同危机的体现。在国家动荡、政治腐败之际,平民阶层与统治阶级的对立不断加深,其国家认同意识也随之消解。
三、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演变
自魏以后,晋统一南北,威名四扬。周边少数民族皆前来依附,听命纳贡,响应王德。由此,西晋迎来了第一次边疆少数民族内附、归化的浪潮。史料所见,泰始二年(266年)至永平元年(291年),前来归化和内附的边疆少数民族按照方位划分,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东夷各部族。东夷先后有53个部族遣使归化;内附次数共有9次,多达82个部族。二是北部各少数民族。武帝泰始三年(267年),西北杂虏及鲜卑、匈奴各率种人部落内附。此外,匈奴在晋武帝践祚后,先有塞泥、黑难等二万余落归化,其后又有匈奴都督拔弈虚、余渠都督独雍、胡太阿厚、胡都大博、萎莎胡、大豆得一育鞠等皆率其部落归附。三是南部诸夷。泰始三年,五溪蛮夷率部前来内附;太康参离四千余落内附;永平元年(291年),南夷二十四部并诣校尉内附。这一时期,边疆少数民族内附和归化的频率较高,其间还伴随着边疆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以上内徙部族中便有匈奴十四万余人、部族两万余落及参离部族四千余落。可见,该时段归化或依附西晋的边疆少数民族,不论是部族还是人数都较为可观。显然,边疆少数民族的内附和归化是基于对西晋国力的认同,主动进行的一种重大政治选择,从而纳入西晋统治秩序之下甘为臣属。因而,边疆少数民族的归化和内附不仅是西晋初期国家强盛的反映,亦是他们对西晋产生国家认同的重要体现。
西晋内迁少数民族主要被安置于西北及北部各边郡,如塞泥、黑难率众归化后,居于河西,与晋人杂居,“由是平阳、西河、太原、新兴、上党、乐平诸郡靡不有焉”[6]2549。郭钦上疏时提及应“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6]2549,可见这些地区皆是胡人居住之地,北方少数民族的内徙不断充斥着北部边郡。同时,《徙戎论》中还指出:“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6]1533。这表明西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已进入中原腹地,仅从数量上看,其势力皆不可小觑。在管理边疆少数民族的政策上,西晋采取了双重统治,不仅保留原有的部落组织,以贵者为帅,又选汉人为司马进行监督,边境地区亦设有“校尉”“中郎将”等职。在西晋严格的管控下,内迁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形同编户,“他们要服事供职、承受租调负担。……沦为豪族大地主的佃客,其地位同于奴隶,可以任意买卖”[9]313。如关中羌戎,后汉以来,“其内属者,或倥偬于豪右之手,或屈折于奴仆之勤”[10]2899。匈奴人刘宣也曾言:“晋为无道,奴隶御我。”[6]2648在西晋的高压统治下,内迁少数民族遭受了残酷的剥削,因而不断有少数民族意图脱离西晋的管控。晋武帝泰始七年(271年),刘猛反叛,何桢诱李恪杀猛,此后“匈奴震服,积年不敢复反”[6]2549。咸宁元年(275年),鲜卑反叛,西域戊己校尉马循率军讨伐,斩其渠帅。三年(277年),虏树机能等叛逃,平虏护军文淑率军破之。太康二年(281年),鲜卑攻昌黎,灭夫余,都护贾沉率兵击败慕容廆部众,复国夫余。这一时期,虽有部族接连叛逃,但西晋亦有绝对的实力进行军事镇压。可见,晋武帝时期的综合国力仍可威慑这些少数民族,使之安服于西晋的统治之下。然而,从西晋实施的边疆政策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反抗情况来看,这一阶段边疆少数民族对西晋的国家认同与先前积极内附的归属感大相径庭。前期所形成的国家认同是基于对西晋国力的主动认可,而至西晋中后期,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形成除了汉文化的渐染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西晋在制度、军事等各方面的强力管控。这样的国家认同,正如姚大力所言,“对于国家的单纯的归属感,也可能只是对现状与宿命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承认”[2]80。显然,仅以强权为基础建构的统治秩序存在着巨大的危机,一旦西晋国力衰微,边疆少数民族势必趁乱而起。
惠帝初年,匈奴人郝散与其弟先后叛变,寇略上党诸郡,此后“北狄渐盛,中原乱矣”[6]2550。面对这样的形势,西晋朝堂掀起了激烈的“华夷之辨”。以郭钦、江统为代表的士人认为戎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并上疏徙戎,预警戎狄的猾夏之心,却皆未被统治者采纳。此后八王之乱,西晋在皇权的惨烈争夺中走向衰败,边疆少数民族大肆脱离管控,匈奴刘元海、鲜卑祁弘、羯族石勒、氐族李雄等皆率部反叛,侵略州郡,各自建立独立的政权,造成了西晋无法控制的局面。永嘉五年(311年),刘聪攻入洛阳,晋怀帝被俘。五年后,匈奴破长安,西晋灭亡,边疆少数民族终成为灭亡西晋的一把利刃。综上所述,边疆少数民族对西晋的国家认同从晋武帝即位初期时的心悦诚服和强烈的归属到西晋中后期在民族压迫下逐渐转变为强权压制下的服从和隐忍蛰伏,直至西晋政权衰微,边疆少数民族凭借着不断壮大的势力伺机反叛并建立政权。西晋与内迁少数民族所维系的臣属关系随着战乱分崩离析,西晋政权亦在其冲击下土崩瓦解。
从上文对西晋士人阶层、平民阶层以及边疆少数民族在不同阶段对西晋的国家认同分析来看,士人阶层的命运与西晋的走向紧密相连,在与王权紧密结合的过程中,士人对君主的忠诚和对国家的依恋逐步增强,国家认同意识根深蒂固。平民阶层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则与政权统治下社会秩序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同时,东吴、蜀汉亡国初期,文化的兼容与碰撞亦对两地民众的国家认同观念产生重要影响。对于边疆少数民族而言,他们对西晋的国家认同很大程度上基于对西晋国力的认可,因而在初期主动选择对西晋臣服并内徙北部边郡。显然,这样的国家认同仅是第一层面的选择和辨识,加之在西晋严格的政治管控和残酷的经济剥削下,内迁少数民族并未通过民族融合对西晋政权产生深厚的依恋与热爱。也正因如此,西晋中后期国力衰微之际,边疆少数民族纷纷叛离。西晋晚期平民阶层与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意识的消解,亦揭示了民族矛盾与阶级对立爆发的必然性。但不论是哪一阶层,他们对西晋国家认同的态度终是伴随着西晋政权的兴衰而发生相应的改变,可见国家认同意识的构建与国家政局的稳定程度密切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