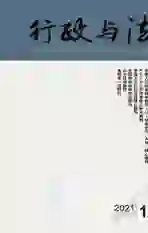重构性别选择堕胎的法律规制模式
2021-12-28翟高远胡雪梅
翟高远 胡雪梅
摘 要:性别选择堕胎人为干预胎儿的自然出生会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为此,应将胎儿性别鉴定行为与性别选择堕胎行为分离,解除胎儿性别鉴定的禁制,建立胎儿性别信息备案制度;将性别选择堕胎犯罪化处理,《刑法》罪名中增设“非法性别选择人工终止妊娠罪”,处罚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医务人员违背法律法规为他人实施性别选择终止妊娠手术的行为。
关 键 词:堕胎;性别偏好;性别选择;“非法性别选择人工终止妊娠罪”
中图分类号:D9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21)12-0081-08
收稿日期:2021-07-22
作者简介:翟高远,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民商法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法与医事卫生法;胡雪梅,上海市“曙光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民法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医事卫生法治研究中心青年项目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YF20-Q11。
一、缘起:生育性别偏好
2015年12月,浙江省温州市永嘉县警方破获了全国范围内最大的“寄血验子”案件①。两年时间内,5万余份孕妇血液样本从全国各地寄往深圳,不法分子将孕妇血液样本非法出关至香港,香港的医疗机构对孕妇血液样本进行化验检测出孕妇腹中胎儿性别,再将胎儿性别鉴定报告寄回关内。[1]胎儿性别的提前知晓对胎儿的生命存续造成了潜在风险,那些不符合父母以及家庭生育性别偏好的胎儿有可能被人工终止妊娠(即堕胎)②。生育性别偏好,即孕妇以及其家庭成员对腹中胎儿性别的偏好,性别偏好本身只是个体的心理偏好,并不具备社会危害性,但其可能引发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选择堕胎①,则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生育性别偏好的根源在于性别不平等。在传统男权制社会的认知中,女孩终归是夫家的人,男孩可以继承父母的家业,名字可以载入族谱,[2]而女孩则不能,由于受性别身份的束缚,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观念更是固化了生育男孩的重要性,进而增进了人们在生育活动中进行性别选择的可能性。“重男轻女”的家庭将生男孩视为生育的终极目的,女性生男孩可以获得一定的荣誉感、满足感,若未能生男孩,容易遭受长辈邻里的负面性评价。近年来,性别选择中的男孩偏好与女孩偏好开始趋弱,从有性别偏好向无性别偏好转变,但总体上对于男孩偏好仍旧高于女孩偏好。[3]
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出台,2021年“三孩政策”推出,生育指标的增加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生育性别偏好的压力。有研究表明,第一个子女为男孩可以有效降低育龄妇女的再生育意愿,[4]相比于第一个孩子是男孩的妇女,第一胎生女孩的育龄妇女选择生育二孩的可能性更高。[5]性别偏好能够提高生育率,[6]生育主体若是通过多生来满足对子女的性别偏好,则大致能够维持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且会提高生育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9年0-4岁年龄段的性别比为113.62,202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2019年我国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跌至1.52,[7]远低于更替水平的2.1,临近“低生育率陷阱”红线1.5,2020年总和生育率则跌至1.3,[8]我国已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生育性别偏好所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仍呈现较高值,而总和生育率却持续走低,二者之间并不成正比关系。可见,满足性别偏好的主要方式已经不是通过多生,而是通过胎儿性别鉴定技术和选择性人工流产手术得以实现。
二、性别选择堕胎之现实危害
(一)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冲击国家对人口与生育的调节秩序
生育权作为一项受限制的自由权,从“独生子女”“单独二孩”“全面二孩”到“三孩”的計划生育政策,均体现了国家对生育权的调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2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为111.3,较2010年下降6.8,[9]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下降反映了人口性别结构有所改善,但仍高于103-107的国际标准水平,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任重而道远。性别选择堕胎介入生育活动,人为干预胎儿自然出生,自然出生规律被人力强行打破,导致国家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冲击国家对人口与生育的调节秩序。女性的性别比率较低,根源是男女的地位不平等。[10]性别比的失衡对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产生了不利影响,“就业性别挤压”愈加严重。同时,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导致男性寻觅适婚女性只能挤压到其他年龄层,极易导致“千万剩男找不到配偶”的社会性难题。
(二)侵害胎儿的生命利益,损害人本身的前期生命形式
生命的存续与保全,是民法上活着的人的最为核心的利益。[11]目前宽松的堕胎政策中,性别选择堕胎往往打着生育自由的幌子,剥夺了健康娩出胎儿出生的机会。胎儿的生命利益与孕妇生育自主决定权之间的博弈一直是堕胎合法与否争论的焦点所在。生育权作为自由权,妇女②可在不违背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自主决定是否生育子女。有学者主张不生育的自由包括避孕的自由和怀孕后堕胎的自由,[12]也有学者主张生育权作为宪法权利,堕胎是生育权实现的手段。[13]笔者认为,主张以堕胎的方式实现生育自由的观点不可取,不生育是生育自主决定权的自由内涵,但是通过堕胎手段实现的合理性有待商榷。胎儿在未娩出之前与母体一体,但胎儿并不因其对母体的依附性而属于母体的附属品,胎儿具有脱离于母体独立的存在价值与生命利益。生命利益先于法律而存在,系人性之表现与自然创造的一部分,[14]如果完全无视胎儿的生命利益,这与国家保护生命的义务是格格不入的。[15]对此,笔者倾向于孕妇生育自由中不生育的实现应当以避孕的方式从性生活开始就阻断生命的形成或者医学上形成胎儿①之前实现,而非通过妊娠后堕胎的残忍手段实现生育自由。这一观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以下简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二十条“育龄夫妻自主选择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措施,预防和减少非意愿妊娠”之规定相契合,即实行计划生育,以避孕为主,预防和减少非意愿妊娠。
“人之所以为人”在民法上的表达即具备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1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三条“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之规定,胎儿不具有权利能力,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胎儿的民事权利除了法律规定的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外,其他民事权利始于出生并个体存活才享有。在母体孕育过程中,胎儿逐渐地向“人”靠拢,直到其娩出母体并存活,方成为法律上的“人”。胎儿虽然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但胎儿是人的生命的原始阶段,[17]是一个活着的生命体,对于胎儿这种逐渐往“人”上长成的生命体,立法应考虑其生命利益。
三、现行性别选择堕胎法律规制模式之逻辑缺陷
(一)现行法律规制模式下非法的性别选择堕胎与不违法的普通堕胎难以区分
199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以下简称《母婴保健法》)已经规定除医学上确有需要之外,严禁采用技术手段对胎儿进行性别鉴定。《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和《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也规定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以及严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胎儿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我国相关地方法规、规章也有类似规定。②从世界范围内的立法来看,关于堕胎的法律规制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即国家放任模式、国家许可模式、有限制的国家放任模式。[18]根据这种分类标准,我国的模式较偏向于国家放任模式,只要孕妇不违背国家明令禁止的性别选择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如意外怀孕、放弃妊娠等原因所致的普通堕胎都是被允许的且不违法。医疗实践中,胎儿性别鉴定行为与性别选择堕胎行为的时间与场所往往是分离的,时空的分离模糊了非法的性别选择堕胎与不违法的普通堕胎的界限,孕妇一方往往使用不违法的堕胎要求掩盖性别选择堕胎的真相,使得医务人员难以真实、有效地识别孕妇一方所要求的究竟是违法的还是不违法的终止妊娠手术。医疗检测技术的发展提高了胎儿性别鉴定的精准度,为胎儿性别的获知提供了极大便利。然而,一旦孕妇通过不正当手段获知胎儿性别,就有可能以普通的不违法的堕胎为名实施违法的性别选择堕胎行为。同时,胎儿性别鉴定行为具有隐蔽性,除非相关知情人员告发,否则外界往往难以取证。
(二)行政规制处罚力度滞后且无法与《刑法》罪名相衔接
2002年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了违反法律规定为他人实施性别选择堕胎行为的处罚方式,主要包括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21年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性别选择堕胎处罚之规定完全承袭旧法,无任何修改。前后两部法律对比可以看出,《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对性别选择堕胎行为的规制条款仍存在不合理之处:一是违法成本较低,处罚力度较小;二是与其他法律衔接不畅。《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新法与旧法相隔近二十年,但是对于性别选择堕胎行为的处罚标准没有改变①,震慑效果欠佳。除此之外,2021年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条规定构成犯罪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但我国《刑法》罪名中尚无与惩治性别选择堕胎行为相衔接的罪名设置,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立法资源的浪费。2016年施行的《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以下简称《两非规定》)较《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从监管、惩治等方面更为系统、全面地对胎儿性别选择堕胎予以规制,其相关规定基本上承袭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内容,也存在与《刑法》罪名衔接不畅的问题。规制性别选择堕胎的各种规范看似规定得当,实则相互推诿,并没有实质且明确的指导性条款。
2012年11月9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印发《关于部分罪名定罪量刑情节及数额标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第九十二条第五项规定“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兒性别3人次以上,并导致引产的”属于非法行医罪的“情节严重”,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19]我国法律规定将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行为认定为行政违法行为,而《意见》第九十二条第五项将其拟制为刑事犯罪行为情节严重之一,此举混淆了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界限,违背了刑法罪刑法定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下简称《立法法》)第一百零四条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外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得作出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而《意见》部分条款超越自身权限,违背《立法法》规定,应属无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将“非医学需要鉴定胎儿性别3人次以上,并导致引产的”情形认定为非法行医罪的做法固然欠妥,但是充分体现了因行政规定与《刑法》规定衔接不畅所致的司法部门办理性别选择堕胎案件时的困惑。
(三)《刑法》对于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医务人员实施性别选择堕胎手术的行为无法以犯罪论处
《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了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为孕妇实施终止妊娠手术的定罪量刑标准,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非法行医罪对犯罪主体的要求是不具备行医资质的人员,但非法为孕妇实施性别选择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的人员并非都是不具备行医资质的人员,也有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医生,医生则明显不属于非法行医罪和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犯罪主体,故这两项罪名不适用医生实施性别选择堕胎的情形。《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关于医疗事故罪的罪名成立要求行为导致侵害就诊人生命权、健康权的不利后果,且系医务人员过失所致。然而,医生为孕妇实施性别选择堕胎并不一定造成侵害孕妇生命权、健康权的不利后果①,不利后果的发生具有一定偶然性,若没有造成法定的不利后果,则无法以医疗事故罪论处。即便发生了侵害就诊人生命权、健康权的不利后果,若该后果不可归责于医生,依旧无法以医疗事故罪论处,不宜以过失致人死亡罪或者过失致人重伤罪论处。由于《刑法》罪名的缺位,导致无法对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医生实施性别选择堕胎手术的行为作犯罪化处理。
四、重构性别选择堕胎法律规制模式之路径选择
(一)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堕胎分离,建立胎儿性别信息备案制度
自然情感是法律存在的基础,这意味着法律必须体现人的正常情感,否则法律就不会发生作用。[20]从自然情感而言,禁止胎儿性别鉴定的规定限制了孕妇对胎儿的性别知情权利,与人的最基本的自然情感相背离,从实际执法效果而言,禁止胎儿性别鉴定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笔者认为,我国立法部门宜将胎儿性别鉴定行为与性别选择堕胎行为分离,只需处罚非法性别选择堕胎行为,而不再处罚胎儿性别鉴定行为。
⒈父母获知胎儿性别符合人的最为基本的自然情感。父母获知胎儿的性别是人最为基本的自然情感的内容,应该得到法律的确认和保护。胎儿乃父母之希望寄托,家族长辈亲朋惦念之至,[21]这一将来意义上“人”的逐渐形成,直接影响到父母及其家庭后续生活的展开,胎儿的性别、健康等特质对于父母及其家庭成员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情感价值。父母及其家庭成员迫切想要知晓胎儿性别是人最为基本自然情感的流露,是符合为人父母心理期待以及社会伦理的,这一最为常识、常理、常情②的要求也符合现代法治要求,法律应当予以尊重和满足,而不是限制人最为基本的自然情感。
⒉胎儿性别识别手段多样化,堵塞不如疏流。医疗实践中,通过熟人委托或者违规交易,医疗检测人员会以极其隐晦的方式暗示胎儿性别,如孕妇产检之际,医疗检测人员告知“给宝宝准备蓝色衣服”还是“红色衣服”,蓝色衣服即代指腹中胎儿是男孩,红色衣服代指女孩;“胎儿长得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像爸爸代指男孩,反之代指女孩;“不要问胎儿性别,反正不是女孩就是男孩”或者“不是男孩就是女孩”,前者结束语“就是男孩”,即暗指胎儿是男孩,而后者结束语“就是女孩”则暗指胎儿是女孩。[22]同时,现代医疗技术为胎儿性别识别提供了便利,以四维彩超为例,无需专业医务人员的告知,孕妇也能凭借清晰的检测画面识别出胎儿的性别,正确率颇高,这为性别选择堕胎行为提供了可能。医疗检测人员与生育主体之間的非法操作打破了禁止非法鉴定胎儿性别的强制性规定,高科技的助益将胎儿性别识别“去专业化”,一味禁止胎儿性别鉴定并非行之有效的选择。
⒊胎儿性别鉴定行为并不直接、必然导致性别选择堕胎的发生。从社会危害性而言,胎儿性别鉴定的危害并不是直接从这一行为中体现出来的,基于胎儿性别鉴定的性别选择堕胎才是社会危害的实现行为。[23]而法律亟待处罚的也是因为胎儿性别鉴定行为引发的性别选择堕胎行为。医疗实践中,鉴定胎儿性别的行为并不直接、必然导致孕妇堕胎,因此,将胎儿性别鉴定行为与性别选择堕胎行为居于同等地位予以禁止的规定有失偏颇。笔者认为,相关部门应当放弃禁止胎儿性别鉴定的做法,仅仅处罚非法性别选择堕胎行为即可。
为了防止胎儿性别鉴定行为合法化后而无法应对有可能发生的性别选择堕胎行为,立法部门应当协同医疗卫生部门共同建立胎儿性别信息数据库,将胎儿性别信息与孕妇个人信息绑定,孕妇一旦获知腹中胎儿性别,非法定情形不得堕胎,以此阻断孕妇以生育自由为名,行性别选择堕胎之实的医疗乱象。为明确各方权责,具体规则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孕妇鉴定腹中胎儿性别之前,医务人员须充分告知其鉴定性质、鉴定后果等相关信息,孕妇自主决定是否鉴定胎儿性别,一旦决定鉴定腹中胎儿性别,胎儿性别鉴定活动须注记、备案,注记与备案的方式宜将胎儿性别信息与孕妇身份证绑定,鉴定之后非法定堕胎情形不能堕胎。胎儿性别信息数据库内数据信息受法律保护,全国正规医院方有权限查阅,且只能由专业医务人员在需要之时查询。第二,在孕妇要求实施人工终止妊娠手术的场合,医务人员可以通过胎儿性别信息数据库查询该孕妇是否已经实施了胎儿性别鉴定措施,获知腹中胎儿的性别信息,若孕妇尚未鉴定胎儿性别,则孕妇可以基于生育自由自主决定堕胎,若显示孕妇已经获知腹中胎儿性别信息,则该孕妇不得实施人工终止妊娠手术。当然,法定的性别选择终止妊娠的情形不在此限制之内。第三,医务人员若违反规定,为已经获知了腹中胎儿性别——本不应堕胎的孕妇实施了终止妊娠手术,则应承担相应责任。
(二)性别选择堕胎犯罪化,增设“非法性别选择人工终止妊娠罪”
医疗实践中,实施性别选择堕胎的主体主要是孕妇和医生。在将性别选择堕胎犯罪化的过程中,将实施性别选择堕胎的医生归为犯罪主体是毫无疑问的,但不宜将选择实施性别选择堕胎的孕妇作为犯罪主体处理。刑法对女性予以特殊保护,如“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等规定均有体现对女性这一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若对实施性别选择堕胎手术之后的女性科以刑罚,恐伤国民之法情感且有致刑罚泛化之虞,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但是,怀孕妇女仅因为胎儿性别不符合自身预期便将其终止妊娠,该做法与国家禁止非医学需要的性别选择堕胎的规定相悖,孕妇虽不宜作犯罪化处理,但不应免除相应的行政处罚。为彰显法之温度,对选择实施性别选择堕胎的孕妇的行政处罚应以财产罚为主,由当地的计划生育部门对其进行罚款,同时施以批评教育。
为弥合2021年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四十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规定之不足,笔者主张在刑法分则罪名中增设“非法性别选择人工终止妊娠罪”,主要处罚情节严重的性别选择堕胎行为,以体现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求,其他未达到定罪标准的行为仍由《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两非规定》等法律法规予以规制。在我国《刑法》罪名结构中,医疗事故罪、非法行医罪、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等医疗条款均规定在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第五节危害公共卫生罪中,性别选择堕胎冲击国家的人口与生育管理秩序,而人口与生育调节秩序属于社会管理秩序,宜将“非法性别选择人工终止妊娠罪”规定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节中。同时,基于节省立法资源的考虑,笔者主张将“非法性别选择人工终止妊娠罪”作为《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的第三款。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非法行医罪”和第二款“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规定了“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人”犯罪的情形,而“非法性别选择人工终止妊娠罪”针对的犯罪主体是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的医务人员。因此,可将“非法”扩大解释为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主体非法和主体合法但行为超越法律规定而致的行为非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的三款罪名在逻辑上便可自洽。考虑到同一条款罪名之间处罚力度的一致性以及性别选择则堕胎的社会危害程度,“非法性别选择人工终止妊娠罪”的处罚标准可以参考《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相关规定,即“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医务人员违背法律法规进行性别选择堕胎行为多是人情使然或者受利益驱动,有必要对涉事医务人员并处罚金,罚金标准参考《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两非规定》等法律法规;情节严重的,以一年之内非法实施2次以上性别选择人工终止妊娠手术为标准。《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条罪名增设之后,罪名全称为非法行医罪;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非法性别选择人工终止妊娠罪。第三款具体规定为医务人员违反法律规定,为他人进行性别选择人工终止妊娠手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参考文献】
[1]谢树华.永嘉警方破获最大“寄血验子”案[EB/OL].温州网,http://www.wzrb.com.cn/article733136show.html.
[2]See Stephen Mosher.A Population Study of China and Legal Solutions to Gender-Selective Abortion,Regent Journal of Law & Public Policy 6,no.1(Winter2013),p60.
[3]侯佳伟,顾宝昌,张银锋.子女偏好与出生性别比的动态关系:1979-2017[J].中国社会科学,2018,(10):89.
[4]穆滢潭,原新.“生”与“不生”的矛盾——家庭资源、文化价值还是子女性别?[J].人口研究,2018,(1):100.
[5]靳永爱,宋健,陈卫.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中国城市女性的生育偏好与生育计划[J].人口研究,2016,(6):30.
[6]郭志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08,(4):6.
[7]任泽平,熊柴,周哲.中国生育报告(2020)[EB/OL].澎湃新闻网,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9539003.
[8]李岩.总和生育率1.3意味着什么?[N].北京青年报,2021-05-12(A05).
[9]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EB/OL].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76.html.
[10]See Tulsi Patel.Sex-selective abortion in India:gender,society and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Sage Publications (2007)p.203.
[11]Vgl.Christian v.Bar,O.a.a.,S.62.转引自朱晓峰.民法典编纂视野下胎儿利益的民法规范——兼评五部民法典建议稿胎儿利益保护条款[J].法学评论,2016,(1):182.
[12]梁洪霞.我国多省市“限制妇女堕胎”规定的合宪性探究——兼议生育权的宪法保护[J].北方法学,2018,(1):40.
[13]姜玉梅.中国生育权制度研究[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235.
[14]王澤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83.
[15][18]王贵松.价值体系中的堕胎规制——生命权与自我决定权、国家利益的宪法考虑[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7,(1):143-144,150.
[16]李永军.我国《民法总则》第16条关于胎儿利益保护的质疑——基于规范的实证分析与理论研究[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9,(2):99.
[17]李锡鹤.胎儿不应有法律上利益——《民法总则草案》第16条质疑[J].东方法学,2017,(1):3.
[19]陆杰华.应尽快出台严格禁止“两非”的司法解释[N].人民法院报,2015-04-11(05).
[20]胡玉鸿.“自然人”的社会与“自然人”的法律[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6,(4):10.
[21]张红.民法典之名誉权立法论[J].东方法学,2020,(1):69.
[22]薄荷.这些B超医生暗示胎儿性别的话,你竟然没懂[EB/OL].妈妈育儿网,https://www.mmyuer.com/huaiyun/snsn/11251a152017_2.html.
[23]范跃.注重裁判理由的可接受性——“寄血验子”案的法律解释分析[J].法律方法,2019,(3):234.
Reconstructing the Legal Regulation Model of Sex Selective Abortion
Zhai Gaoyuan,Hu Xuemei
Abstract:Sex selective abortion artificially interferes with the natural birth of fetus,resulting in the imbalance of sex ratio at birth. Therefore,we should separate fetal sex identification from sex selective abortion,lift the prohibition of fetal sex identification,and establish a fetal sex information filing system;Criminalize sex selective abortion,add“crime of illegal sex selective artificial termination of pregnancy” in the crime of criminal law,and punish medical personnel who have obtained the qualification of doctor to perform sex selective termination of pregnancy for others in viola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Key words:abortion;gender preference;gender selection;“crime of illegal sex selection and artificial termination of pregnan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