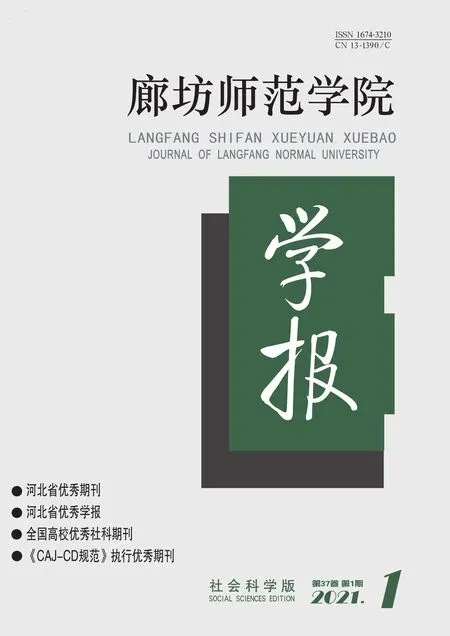义疏的黄昏:《五经正义》第三次修订与唐代经学路径转折
2021-12-28高亮
高 亮
(复旦大学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孔颖达主持的《五经正义》(以下简称《正义》)在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以前编成①《正义》编成时间不详。《资治通鉴》将其系于贞观十四年(640)二月下:“二月,丁丑,上幸国子监,观释奠,命祭酒孔颖达讲《孝经》,赐祭酒以下至诸生高第帛有差。是时上大徵天下名儒为学官,使之讲论……上以师说多门,章句繁杂,命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疏,谓之‘正义’,令学者习之。”(见司马光等编,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152—6153页)《通鉴》体例,凡言“是时”者,多为补充事件背景,未必与所系事件同时。故不能以此为《正义》编成之年。张宝三先生据《正义》各篇序文提及初次修订时间“至十六年,又奉敕与前修疏人及……”之语,认为《正义》编成之年必在十六年以前,比较妥当,今从其说。(见张宝三:《五经正义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页)。、贞观十六年至十七年(643)初次修订②据《旧唐书》孔颖达本传,初次修订“功竟未就”(见刘昫:《旧唐书》卷七十三《孔颖达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03页)。按:贞观十七年(643),孔颖达以年老致仕。同年,太子李承乾谋反被废,负责《正义》修订复核工作的太子右庶子赵弘智被除名。两位关键人物同年离职,则初次修订工作应即停滞,故云“功竟未就”。、高宗永徽二年(651)至四年(653)第二次修订并颁定天下的历程已是学史常识,而永徽四年(653)末至六年(655)的第三次修订却罕有提及③仅见潘伟忠:《〈五经正义〉成书考》(《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简称潘文)、白长虹:《〈五经正义〉及其研究综述》(《鞍山师范学院》2007年第1期,简称白文)略言于此。潘文将此次修订与第二次修订混同(参见潘文第41页),且未作考证;白文则简述而已,亦未作考证(参见白文第52页)。。此次修订牵涉永徽后期高宗与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集团的中枢权力斗争,且事关唐代经学路径转折的发生,故试为发覆。
一、第三次修订始末
《五经正义》第三次修订由御史大夫崔义玄负责。据《旧唐书》本传,崔义玄出自清河崔氏,武德初入唐,随秦王征王世充,颇有功绩。高宗永徽初,为婺州刺史,因平定永徽四年十月睦州女子陈硕真之乱,升任御史大夫④(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七十七《崔义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88—2689页。。第三次修订《正义》即在此后。本传略叙其事:
义玄少爱章句之学,五经大义,先儒所疑及音韵不明者,兼采众家,皆为解释,傍引证据,各有条疏。至是,高宗令义玄讨论《五经正义》,与诸博士等详定是非,事竟不就。①(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七十七《崔义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89页。
此段叙事时间不明。崔氏升任御史大夫当在永徽四年末至五年(654)初,奉令讨论《正义》不早于此时。至于下限,据下文推测,应在永徽六年十月皇后废立前后,至迟不晚于显庆元年(656):
高宗之立皇后武氏,义玄协赞其谋,及长孙无忌等得罪,皆义玄承中旨绳之。显庆元年,出为蒲州刺史。寻卒,年七十一。②(后晋)刘昫:《旧唐书》卷七十七《崔义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89页。
永徽六年崔氏忙于谋划皇后废立及构陷长孙无忌集团成员,修订工作不可能不受影响。至迟在其显庆元年卒于蒲州任上,修订停止。
《正义》第三次修订不早于永徽四年末,不晚于显庆元年,最有可能集中在永徽五年春至六年秋之间。
二、第三次修订与永徽后期中枢权力的博弈
此次修订的起因,上引本传亦未明言,只谓崔氏本人精通经学。此说甚勉强,且不论其人学识如何。但永徽第二次修订本《正义》参与者多为当时名儒,尤其是谷那律、王德韶、贾公彦、范义、随德素、赵君赞六人参与过贞观时期的编纂与初修工作,谙熟经义,经验丰富。即便挂名者,亦学殖深厚,像长孙无忌、褚遂良等,更是元老重臣,执掌中枢,权倾朝野。即使第三次修订,自可仿照初修时马嘉运之旧例③作为初次修订的实际发起人,太学博士马嘉运曾参与《周易正义》编纂,后又参与《周易》《左传》二疏的初次修订,但编纂与初次修订的主持者仍为孔颖达。(见刘昫:《旧唐书》卷七十三《孔颖达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01页;刘昫:《旧唐书》卷七十三《马嘉运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03页;王弼、韩康伯注,孔颖达等疏:《周易正义》,影印清南昌府学《十三经注疏》(第1册),第14—15页;杜预注,孔颖达等疏:《左传正义》,影印清南昌府学《十三经注疏》(第4册),第3692—3693页。),令崔氏与事即可,不必主持。在有第二次修订的元老重臣与名儒经师的前提下④除谷那律已卒外,其余与事者当时仍见在。(见《旧唐书·谷那律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952页。),第三次修订时却改用崔氏主持,不仅不合情理,亦有损重臣之体面。且崔氏时任御史大夫,掌百官纠劾,以其人主持第三次修订,与事诸人(尤其是诸博士官)不免投鼠忌器,未必敢尽心论学,不利于修订的正常开展。凡此种种,皆提醒我们,第三次修订一事恐非单纯出于经疏修订目的,而应有更深层的动机。
从时间上看,第三次修订所处的永徽四年末至六年十月间,正是唐高宗在向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重臣集团(以下简称长孙无忌集团)争权的过程中⑤长孙无忌集团主要包括时任宰相的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韩瑗、柳奭,以及柳奭之甥王皇后,而以长孙、褚二人为中坚。这一集团形成不晚于永徽三年(652)七月,以高宗庶长子李忠立为太子为标志。《旧唐书》卷八十六《燕王忠传》:“王皇后无子,其舅中书令柳奭说后谋立忠为皇太子,以忠母贱,冀其亲己,后然之。奭与尙书右仆射褚遂良、侍中韩瑗讽太尉长孙无忌、左仆射于志宁等,固请立忠为储后,高宗许之。”(见刘昫:《旧唐书》卷八十六《燕王忠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824页。)黄永年先生认为,高宗本欲以于、韩、柳三人牵制长孙、褚,但以册立太子一事为纽带,三人与长孙、褚结成同一利益集团。见黄永年:《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载《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2册)《国史探赜》(下),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2页。,由相对温和的渐进阶段,逐渐加速转变为公开对立的激进阶段。细言之,在永徽四年末之前,高宗亦有争权举动,但主要通过调整宰辅以分割中枢权力⑥主要通过增补宰辅人数、改动其职位的方式促进分权。对长孙无忌集团成员则偶有抑退,但不会持久。如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己巳太宗去世时,宰相只有长孙无忌、褚遂良二人。至次日庚午,即以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为相。六月癸巳,李勣拜相。永徽二年(651)正月乙巳,宇文节、王皇后之舅柳奭拜相。其间永徽元年(650)十一月己未,左迁中书令褚遂良为同州刺史,但三年(652)正月己巳,又召褚遂良入相。四年(653)九月张行成死,以褚氏为尚书右仆射。(见《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6—72页。),只有永徽元年(650)十一月至三年(652)正月左迁中书令褚遂良为同州刺史一事,算是对长孙无忌集团一次提醒,不过还谈不上实质性打击①黄永年先生认为此事系高宗对元老重臣的首次公开进攻(见黄永年:《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黄永年文史论文集》(第2册),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31页)。按:褚遂良出任外职只约一年,且在近畿之同州,绝非远谪,对长孙无忌集团影响很有限,不足以称为“进攻”。。总体上看,永徽四年之前,高宗与长孙无忌集团虽有内部矛盾,但仍然保持着核心政治利益的一致性,这种矛盾,尚非主要矛盾。直至四年二月,房遗爱勾结荆王李元景谋反失败,构陷吴王李恪②《通鉴》详述其事:“恪有文武才,太宗常以为类己,欲立为太子,无忌固争而止,由是与无忌相恶。恪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无忌深忌之,欲因事诛恪以绝众望。遗爱知之,因言与恪同谋,冀如纥干承基得免死。”(见司马光等编,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80页。),长孙无忌将计就计,导致李元景、李恪等被赐死,其党羽亦被剪除③房遗爱谋反案处理结果如下:“(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等并伏诛;元景、恪、巴陵、高阳公主并赐死。左骁卫大将军、安国公执失思力配流巂州,侍中兼太子詹事、平昌县公宇文节配流桂州……特进、太常卿、江夏王道宗配流桂州,恪母弟蜀王愔废为庶人。”(见刘昫:《旧唐书》卷四《高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1页。此案牵涉较广,沉重打击了宗室重臣势力。)。经此一事,威胁高宗皇位与长孙无忌集团核心利益的外部隐患基本肃清,太宗贞观十七年易储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也得到了解决,高宗与长孙无忌集团的内部矛盾逐渐成为权力斗争的焦点,并趋于公开化、激进化。
将《正义》第三次修订置于上述背景下,其背后政治动机一目了然。第三次修订主持者崔义玄作为三朝老臣,在长孙无忌等人执政时期,一直未得重用。永徽四年末以戡乱之功拜为御史大夫,才得要职。不过这项任命,恰有奥妙。《资治通鉴·永徽四年》“义玄以功拜御史大夫”条下胡三省注云:“御史大夫,天子耳目官也,非以赏功。厥后崔义玄承中宫旨绳长孙无忌等,岂不忝厥官哉!”④《资治通鉴》卷一九九,胡注“承中宫旨”(见司马光等编,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 年版,第6283页)。《旧唐书》崔氏本传作“承中旨”(见刘昫:《旧唐书》卷七十七《崔义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689页);《新唐书》本传作“以后旨”(见宋祁、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一百九《崔义玄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96页)。表面上看,武后是促成长孙无忌集团垮台的幕后推手,但实际上铲除长孙无忌势力是高宗之意,只因高宗碍于舅甥亲情与翼戴之功,不便直接出面,武后不过代表高宗积极运作而已。一语道破其中玄机。御史大夫纠察百官,宰相亦不例外,长孙无忌集团不会希望对其不利者充任。崔氏为御史大夫,应出自高宗之意。以崔义玄这样长期受长孙无忌等人排挤、心怀不满而又经验丰富的老臣为之,深挖长孙无忌集团的漏洞,自有效果。从这一任命也能看出,永徽四年以来,高宗在摆脱长孙无忌等人的钳制方面,已经从调整宰辅以分割中枢权力,逐步转向提拔长期受长孙无忌集团抑制而又颇有政治手段的官员,积蓄力量,并制造彻底铲除长孙无忌势力的机会。高宗不顾长孙无忌等主持《正义》第二次修订者的颜面,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即改用御史大夫崔义玄主持《正义》第三次修订,其本质应是一项政治任务,即对长孙无忌集团发出公开警告,表达对长孙无忌等人过度专擅的不满。当永徽六年因皇后废立引发的中枢权力冲突达到高潮,《正义》的修订已彻底失去政治价值,其政治使命随之终结。即便崔义玄仍有主持修订的精力,亦无修订之必要。此次修订最终不了了之,也在情理之中。
三、第三次修订的经学史影响
虽然《正义》第三次修订是永徽后期中枢权力斗争的一部分,但其本身仍属小事件,然而其在经学史上的影响却相当深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其一,标志着皇权不顾经典本身之权威性,开始强行干涉经典诠释。自西汉以来,经典诠释乃至经学争论以学术性为主,政治性为辅。在这一时期,虽然经学与政治紧密结合,但仍保有相当的学术独立,皇帝尚不能以政治权威强行干涉经学。以汉宣帝时的石渠会议为例,可以看出当时皇权试图调整经学时的谨慎态度。《汉书·儒林传》叙其始末如下:
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穀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徵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复死,乃徵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谊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庆、姓皆为博士。姓至中山太傅,授楚申章昌曼君,
为博士,至长沙太傅,徒众尤盛。①班固等撰,颜师古注:《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18页。
汉宣帝欲兴《穀梁》,做了如下准备:以精通《穀梁》的蔡千秋教授郎官十人;征《穀梁》经师瑕丘江公之孙为博士,以刘向助之;征周庆、丁姓继续教授上述十位郎官;自元康中至甘露元年(前53 年),历经十余年,确保诸郎官精通《穀梁》学之后,方才召开石渠会议。会议期间,又经过激烈论战,方使《穀梁》居上。宣帝不过希望在保持《公羊》博士的同时,增立《穀梁》博士,以兴《穀梁》之学而已,尚须处心积虑,大费周折,前后准备十数年,待万无一失,方能施行。如此耐心、谨慎,无非欲使朝野学者心服。由此可见,在这一时期,皇权还不能直接强行干涉学术,学术尚有一定独立性。
然而,延至初唐,作为中枢权力斗争一部分的《正义》第三次修订工作打破了上述局面,政治性反客为主,学术性被政治性覆盖,为后世帝王凌驾于经典之上,直接干涉经典诠释,乃至擅改经典,提供了一种可行先例②唐人改动儒家经典,始于魏徵删改《礼记》而成《类礼》(见刘昫:《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59页;王溥:《唐会要》卷三十六《修撰》,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51页),不过《类礼》进呈之后即遭雪藏,在当时没有产生学术影响,不可与《五经正义》同日而语。。唐高宗永徽之后,擅改经典的现象常见诸史册。唐玄宗颇好改动经典。终其一朝,增改《月令》经文,命李林甫等依之作注,成《御刊定礼记月令》(以下简称《御定月令》)③玄宗天宝元年以后行用《御定月令》(见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五《贡举上·明经》,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374页)。《御定月令》经文保存于唐开成石经本《礼记》中,注文亡佚,仅有英藏S.621号敦煌写本残卷保存十行注文。;变动《礼记》篇次,以《御定月令》为首④见《新唐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新唐志》),“《御刊定礼记月令》一卷”条小注:“(《月令》)自第五易为第一”(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434页。,又改名《时令》⑤改《月令》为《时令》在天宝五载。(见刘昫:《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19页。);改换《尚书》文字,以“陂”易“颇”,又改隶古定《古文尚书》为楷书⑥《新唐志》“《今文尚书》十三卷”条小注:“开元十四年,玄宗以《洪范》‘无偏无颇’声不协,诏改为‘无偏无陂’。天宝三载,又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第1428页。;改《道德经》“载”字为“哉”⑦(宋)王溥:《唐会要》卷七十七《贡举下·论经义》,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1411页。等等。明太祖“并令儒臣修孟子节文。先是,上览孟子,至‘土芥寇雠’之说,大不然之,谓‘非臣子所宜言’,议欲去其配飨。诏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刑部尚书钱唐抗疏入谏,舆榇自随,袒胸受箭,曰:‘臣得为孟轲死,死有余荣。’上见其诚恳,命太医院疗其箭疮,而孟子配享得不废。至是,乃命修《孟子节文》,凡不以尊君为主,如‘谏不听则易位’及‘君为轻’之类,皆删去。”因厌恶孟子君臣“土芥寇仇”之说,令儒臣删节《孟子》经文,成《孟子节文》①(明)陈建:《皇明通纪·洪武二十三年》,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74—275页。引用时标点略有调整。《明史·钱唐传》同此。《明实录》、明代《国史》皆讳言其事。《孟子》删节的主持者为刘三吾,万斯同《明史·艺文志》“孟子节文二卷”条小注:“洪武间,翰林学士刘三吾上言《孟子》一书中语气抑扬太过,请节去八十五条,课试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余存一百七十余条,颁之学宫,命曰《节文》”(《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4页),将此事责任全推给刘三吾。,则是皇权野蛮干涉经典的最极端案例。
其二,《正义》第三次修订的政治导向及其对学术性的覆盖,使得《正义》错过了一次宝贵的修订机会。一旦颁定天下,长期行用,在官方经学的权威下,《正义》中存在的诠释缺陷就会逐渐被默许,以此为天下士子传习与考试依据,难免造成将错就错、应付差事之趋向,儒典义疏由此走上死板僵化之路,思想活力大为退化②乔秀岩先生认为,初唐义疏“止于表面操作,加工旧说,竟无创立新学说、新学术之力”,可谓一语中的。(见乔秀岩:《义疏学衰亡史论》,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70页。),迫使有识之士不得不另辟蹊径,寻求经义创新之路。作为宋学先驱的中唐韩李、啖赵之学,随之兴起③唐高宗时期义疏僵化与理学兴起的内在联系。(参见高亮:《两晋南北朝隋唐义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20年,第324—325页。)。从此意义上讲,《正义》第三次修订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经学由义疏之学向义理之学的转化,间接开启了唐代经学转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