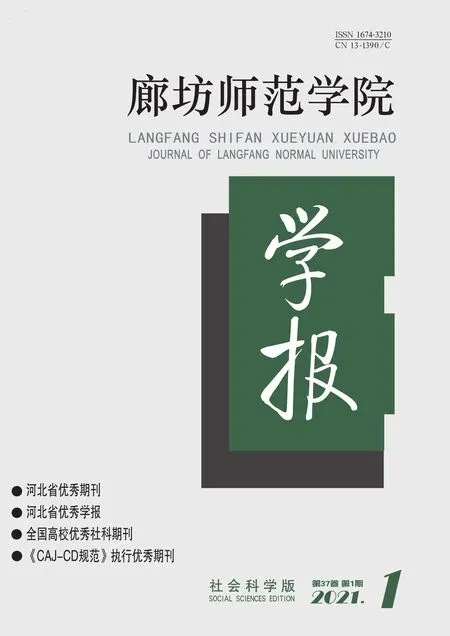何干之对20 世纪30 年代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研究
2021-12-28康桂英
康桂英
(安徽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淮南232001)
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发生是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在思想界的直接反映。此时的中国,再次面临革命要怎样进行的问题。思想革命作为社会革命的先导,率先开始了探讨。众多学者围绕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问题各抒己见,集学术见解和政治观点于一体,热闹异常。其中,社会史问题论战着重探究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是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的一次重要实践,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何干之(1906—1969),中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既是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亲历者,又是学术界第一个对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进行总结评述及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1937 年,当社会史问题论战接近尾声时,何干之撰写了《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和《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两书,对社会史问题论战进行了总结评述和研究,成为学界了解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必备参考书。当前,关于何干之对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研究已有不少著述问世,但基于社会史问题论战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何干之史学价值的可挖掘性,使得这一问题仍有较大的研究空间。本文试以何干之对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研究为视角,立足于20世纪3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步发展阶段,就何干之对社会史问题论战研究的价值与不足提出粗浅认识,就教于方家。
一、关于社会史问题论战
学界一般认为,社会史问题论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史问题论战包括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而狭义的社会史问题论战则指的是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不过,广义狭义往往难以精确区分,人们通常将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放在一起论述。”①陈峰:《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4页。总体而言,这几场论战依次发生,且争论的焦点也不太相同,但其本质却是一样的,即探讨中国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正如何干之所言,这几场论战“可说是关于一个问题的多方面的探讨”②刘炼编,何干之著:《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86页。,为了认识现在的社会,那么从逻辑上必然会追溯对过去社会的认识。从时间上看,当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在“新思潮派”和“动力派”之间激烈开展的同时,一场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过程的争论也悄然兴起,这是思想界试图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积极尝试。1930 年,郭沫若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在书中,郭沫若以大量的出土文物和文献资料为依据,将中国历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五种社会形态说”相印证,第一次把1840 年前的中国历史描述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几种社会形态,确认了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遍性,从而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和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特征提供了历史依据。郭沫若的观点一提出,反对声、质疑声便接踵而来。其中,“新生命派”和“托派”对郭沫若的围攻最为猛烈,他们纷纷著书立说,与郭沫若相辩驳。而其他派别也围绕这些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见解。社会史问题论战就这样开始了。
鉴于社会史问题在思想界的热议,1931年,王礼锡任《读书杂志》的主编时,专门开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并于当年的8 月1日出版了“社会史论战”专号第一辑。在短短的两年时间里,《读书杂志》一共出版了四辑《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汇集了思想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的奴隶制问题和封建制问题等各种有代表性的论作,一度形成了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热潮。其间,陶希圣、李季、王礼锡、胡秋原等人纷纷撰稿,立足于批判,发表见解。他们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认识在一篇篇的著述中呈现出来,而中国社会问题也在诸位学者唇枪舌剑式的争论中日渐成为思想界的焦点。遗憾的是,1933 年,《读书杂志》由于政治原因被迫停刊,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因失去了这个平台而逐渐降温,留下了许多非常有争议的议题,之后进入到了农村社会性质论战时期。
纵观社会史问题论战,争辩的主要内容是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奴隶社会问题和中国的封建社会问题。社会史问题论战之初,以陶希圣为首的“新生命派”发表了《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中国到底是个什么社会》等著述,率先发起了论战。陶希圣认为,中国不存在奴隶社会,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衰落,但封建势力依然存在,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一个先资本主义的社会,其特征是“官僚士大夫与外国资本相结合、大封建系统崩坏而小军事封建系统林立、宗法制度崩溃而宗法势力仍然存在的杂乱景象”③乔治忠:《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问题探实》,《天津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而以李季为首的“托派”分子则以生产方法为标准,把中国社会划分为原始共产主义、亚细亚、封建、前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五种形态,并认为亚细亚社会在中国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时期,中国不存在奴隶社会阶段,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属于前资本主义时期。显然,无论是陶希圣的“先资本主义”说,还是李季的“前资本主义”说,都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五种社会形态说”不符,其实是混淆了封建的生产方法与“封建制度以前的各种生产方法的残余”④刘炼编,何干之著:《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357页。的区别。就“新生命派”和“托派”的错误观点,吕振羽也曾发文进行批评,并正式提出了殷代奴隶社会说。虽然这和郭沫若的西周奴隶社会说认识不同,但都是在肯定中国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五种社会形态说”的前提下进行的学术争鸣。吕振羽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有力地声援了郭沫若。
轰轰烈烈的社会史问题论战给思想界带来了飓风,“参与论战的各方都借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阐释和马克思主义阐明的关于人类社会演进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的历史与社会”①温乐群、黄冬娅:《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形成和初步发展。但由于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参与者在占有史料和方法论的把握方面良莠不齐,甚至出现了“一致以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辞句为渊博,主要的在辩护其个人的偏见,而忘记了现实的历史,忘记了马克思对历史发展之整个的见解,因而变成了经院式的诡辩,而不是史的唯物论之应用”②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4页。,致使社会史问题论战留下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尚未达成学术层面的共识”③陈峰:《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7页。。需要指出的是,“解放以来史学界讨论的古史分期和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这一次论战的延长和深化”④刘炼编,何干之著:《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64页。,这是社会史问题论战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二、何干之对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研究
作为社会史问题论战的亲历者和学术界第一个对社会史问题论战进行总结评述及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何干之关于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研究,不仅勾勒出了这一重要的历史问题的概况,而且表明了以他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立场,展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发展时期的情况和成长历程,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第一,较为全面地呈现了社会史问题论战的概貌。
社会史问题论战参与的派别众多,观点各异,对其进行梳理着实不易。在《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和《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两书中,何干之本着忠实于社会史问题论战本来面貌的原则,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此次论战发生的原因、论辩的内容、发展过程以及产生的意义及影响都进行了精辟独到的分析,较为全面地呈现了社会史问题论战的概貌。而其援引的论者著述也为我们保留了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第一手资料,后来的学者在谈及社会史问题论战时,何干之的研究都成了他们必备的参考资料。
何干之认为,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发生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运动受挫的表现,思想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法问题、中国奴隶社会问题、中国封建社会问题的争论对于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性质以及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绝对不是心血来潮之举。这就精准地指出了社会史问题论战的背景和实质,即表面上是各学派的学术观点之争,实则是关于中国革命的政治道路之争。
何干之还着重分析了苏联和日本学界关于中国历史问题的认识对中国学界的影响,重点介绍了苏联的马扎儿学派、歌德斯、日本的森谷克己、秋泽修二、早川二郎等学者的观点,并分析了他们对参与社会史问题论战的陶希圣、李季、丁迪豪、胡秋原等学者的影响,既指出了这场论战的跨国界特征,又保留了大量苏联和日本学界对于中国社会历史认识的资料。
在指出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实质和跨国界特征的同时,何干之又认真梳理了参与论战各方的主要观点,将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内容归纳为亚细亚的生产方法是什么、中国有没有奴隶社会、中国封建社会有什么特性三个方面,并就这三个论辩内容对各派观点及其意图进行了评述,尽可能地呈现了参与各方的主要观点,使纷繁复杂的社会史问题论战主题鲜明,易于理解。此外,他还着重探究了亚细亚生产方法是什么、中国是否经历过这样的时期、中国有无奴隶社会、与希腊和罗马奴隶社会有何区别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性和长期停滞的根源等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对于社会史问题论战的重要影响,何干之认为,通过此次论战,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历史所作的研究和论证,使得中国社会历史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结论深入人心,这“对于中国现代社会,对于现代中国的解放运动”①刘炼编,何干之著:《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大有意义,并与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收获的重要结论——中国是“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②刘炼编,何干之著:《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一道积极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实践证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明确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领导力量、同盟者、步骤等元素,确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最终将中国革命引向成功。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理论也“在理论学术源流上,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学理基础”③郭若平:《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学理探源——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有益成果的吸收》,《中共党史研究》2003年第4期。,证实了何干之所言的,社会史问题论战是中国思想界的一件大事,所争论的主题“有助于救亡”④刘炼编,何干之著:《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有助于未来中国革命的发展。
第二,深入揭示了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实质。
社会史问题论战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重要事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对中国革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何干之说,“对于这一次有历史价值的论争,一定感觉到有深刻了解的必要。可惜这一次思想界的盛事,至今也还没有人肯作结算的工夫”⑤刘炼编,何干之著:《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表达了他“为大论战作总结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出于对这场论战的长期关注和深刻洞察”⑥耿化敏:《何干之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正是这种对社会史问题论战的长期关注和深刻洞察,使得何干之能够在广泛搜集资料、对参与社会史问题论战各派学者的观点进行系统梳理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精准地抓住这场论战的精神实质——浓厚的政治性。
何干之说,“无论哪一种思想文化运动,都不是无头无脑的运动,必与当时的社会生产状态,有不可分的关系”⑦刘炼编,何干之著:《何干之文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而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发生就是对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失败后的思想回应,参与论战的各派都试图从中国过去的历史中找寻支持他们对现在社会性质判定的证据,这些观点从不同层面折射出了其背后的政治动机。就社会史论战问题中争执的亚细亚生产方法、中国奴隶社会问题和封建社会问题而言,何干之认为这些都事关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如果坚持亚细亚生产方法是一个独立的社会构成,那么就会否认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历史,否认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自然就会否认中国革命的反封建性,进而否认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普遍适用性。故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同的政治观是由不同的社会观而来的”,“各党各派要决定本党的政纲,打击敌党敌派的政纲,就不得不发掘中国社会结构的内层,确认中国社会的性质,以决定中国社会改造的动力和方向。在抗争再出发之前,迫着各阶层各党派的学者,为着确定或辩护他们未来的政治生活”,“在公开或半公开的或不公开的刊物上,各人都展开了自己的认识,以刀枪相见”。⑧刘炼编,何干之著:《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10页。
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翦伯赞和吕振羽也曾对社会史问题论战进行过总结评述,他们对社会史问题论战的解读与何干之的认识有许多相似之处。翦伯赞在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中指出:“研究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史的问题,决不是一种经院式的无病呻吟;反之,而是一个最迫切的政治任务。”⑨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5页。吕振羽于1940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也认为,社会史问题论战是中国各阶级、阶层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反思,“在论战中,表现出中国社会诸阶级、阶层之交错复杂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正面的反面的和中间道路的不同道路的斗争”①吕振羽:《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页。。这说明何干之对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研究与同时代的学者有着大致相同的认知。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社会史问题论战日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而何干之从政治立场对社会史问题论战所做的总结研究,已广为学界接受,“成为中国革命史视角下的经典解释”②耿化敏:《何干之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周子东、杨雪萍等编著的《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在谈及社会史问题论战的性质时,认为它是“在历史问题中包含着现实的斗争”③周子东、杨雪萍等:《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49页。;温乐群、黄冬娅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论战》一书中,将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发生描述为“直接起因是当时的政治形势急切地需要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做出科学的判断”④温乐群、黄冬娅:《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0页。,并认为社会史问题论战“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始终是不变的关怀”⑤温乐群、黄冬娅:《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陈峰在其著述《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中认为,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发生,从现实根源上看,“当是社会政治变动的产物”⑥陈峰:《民国史学的转折——中国社会史论战研究(1927—1937)》,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8页。。以上著述都借鉴了何干之对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研究立场,在肯定这场论战学术性的同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其浓厚的政治性。
第三,积极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由李大钊的介绍传播到中国,逐渐为追求进步的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问题,经由社会史问题论战,积极促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何干之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圭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参与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各派观点进行了评述和研究,积极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何干之认为,“辩证法不承认一般和特殊有冲突。一般是特殊的一般,特殊是一般的特殊,彼此是相依为命地联系着”,“看不见一般和特殊的相互关系,或者把一般和特殊割裂开来,在方法论上一定是陷于机械观的泥坑中,在实际上一定是抹煞当时当地的客观事实”。⑦刘炼编,何干之著:《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20页。他主张研究中国社会历史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相结合。同时,他也主张,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名词和术语,需要充分考虑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要充分认识到亚细亚生产方法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尤其不能割裂亚细亚生产方法和中国的奴隶制、封建社会的联系,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奥秘。
以此为基础,何干之指出,苏联和日本学界以及参与社会史问题论战的陶希圣、李季、丁迪豪、胡秋原等人大都忽略了“特殊的社会现象,总离不开历史的普遍法则”⑧刘炼编,何干之著:《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页。和“具体的历史,不一定这样呆滞,也许要夹杂了许多特殊的现象”⑨刘炼编,何干之著:《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90页。等这些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只是单纯从公式主义出发来认识中国社会历史,把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些现象当作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本质,提出了中国社会是“前资本主义”“先资本主义”“专制主义”等错误观点。
在社会史问题论战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都分外关注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并据此阐发了中国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何干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认为中国历史符合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各国历史的演进,虽不是千篇一律,但一般历史的法则,万不能加以抹煞,开口闭口说‘国情不同’,是民族的偏见,并没有丝毫真实性的”①刘炼编,何干之著:《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但同时,他又认为中国历史也有自身的特点,“东西奴隶社会实际上有着浓淡、深浅、成熟不成熟的不同”②刘炼编,何干之著:《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314页。,封建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并且是一种经济构成”③刘炼编,何干之著:《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336页。。这种见识可从他对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的认识中体现出来。
何干之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阐明中国社会“没有脱离历史发展的普世法则”④耿化敏:《何干之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59页。,“打破了一两千年官学对中国古代史的‘湮没’、‘改造’和‘曲解’”⑤刘炼编,何干之著:《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313页。,对于研究中国社会问题具有拓荒作用。同时,何干之也指出,此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草创阶段,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尚处于尝试阶段,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将东西方奴隶社会完全等同起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没有真正做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相结合,故其对中国历史的一些认识仍有待商榷。有鉴于此,何干之在《中国社会问题论战》一书中大声疾呼,马克思主义理论完全适用中国,“我们东洋人的祖先,也走着西洋人的祖先所走过的路,我们的国情原来没有什么不同”⑥刘炼编,何干之著:《何干之文集》(第1卷),北京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这样,何干之既充分肯定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中国历史的大致判断,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那个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分外关注的“在确认了运用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来解释中国历史的范式以后,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一般性”得到确认以后,考虑中国历史和社会的‘特殊性’问题”⑦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
今天,将规律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已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而何干之的历史见识,使得他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得出了很多正确的认识,既积极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
三、对何干之关于社会史问题论战研究的反思
社会史问题论战过去快要一个世纪了。今天,何干之对社会史问题论战的总结评述与研究已成为我们了解和分析此次论战的重要参考。值得肯定的是,他对社会史问题论战产生原因的分析、对参与此次论战各派观点的分析以及对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地位和历史价值的分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和思想价值。但是,在20 世纪30 年代特定的时代革命背景下,以何干之为代表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分析问题时,由于自身背负着重要的政治使命,故在迫切的政治任务面前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学术与意识形态缠绕在一起,从而过分强调学术为现实服务的政治使命。同时,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也不够深入。这使得何干之对社会史问题论战的总结评述与研究也存在一些缺憾。
从总体上看,何干之在对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研究中,对参与论战的各派观点所作的分析,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斗争,对他们之间论辩的学术价值或学术意义关注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学术性。事实是,社会史问题论战集政治性与学术性为一身,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思想论争,虽然它在发生的时候就已承载着时代重任,政治色彩浓厚,但众多学者参与论战并发表见解,又使得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学术性特征也异常明显。李泽厚分析说,在社会史问题论战中,陶希圣主张的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不符合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但他强调了商业资本在中国社会的长久的活跃传统,强调了士大夫阶级在中国地主社会中的极为重要的统治地位和统治功能,却显然是值得重视,需要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而不能一笔抹杀的”①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74页。。而事实确实如此,社会史问题论战固然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但参与论战的各派学者也都是在搜求大量论据材料的基础上,通过严密的逻辑来推理自己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和描述了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而马克思主义学者正是与他们一道,在观点的针锋相对中加深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正确认知,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可见社会史问题论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奠定了重要基础,其学术价值不容忽视。
虽然社会史问题论战促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但当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受时代所限,以何干之为代表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中国社会历史问题进行分析时,难免有套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和概念之嫌。翦伯赞在其《历史哲学教程》中就指出,何干之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一书既对社会史问题论战中的“这些‘旧的问题’予以‘新的看法’”②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页。,又试图指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方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何干之在研究社会史论战上“没有尽量地运用具体的历史资料,仍然偏于方法论方面的讨论”③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这说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需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自身中国化的问题,需要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不断成长。
社会史问题论战又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奋斗的方向。何干之对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研究,有助于学界了解这一久远的问题出现的起源和背景,了解以何干之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立场和见解。通过何干之对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研究,我们见证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初期的发展状态。而正是这种初期的发展状态,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后来的不断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何干之对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研究对后来的学界影响较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对这场论战在学术史特别是史学史上的意义进行再考察,没有突破何干之的解释框架”④耿化敏:《何干之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60页。。近年来,虽然学界对社会史问题论战的认识又有了新的诠释,但何干之对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研究仍是重要的参考著述。时代在发展,学界对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研究也将会不断深化。我们可以深信不疑的是,何干之对社会史问题论战的研究,代表了那个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成长的阶段,其厚重的学术价值应该得到后人的普遍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