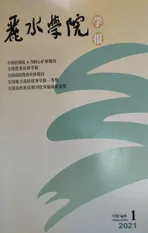《文选》五臣音注研究综述
2021-12-28陈小珍
陈小珍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00)
梁朝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问世之后即为世人所重,先后有萧该、曹憲、许淹、李善、公孙罗、五臣等学者为之作注,其中尤以李善注和五臣注最受欢迎,两者以其各自独特的风格并行于世,且此消彼长地引领着唐以后文选学的发展方向。李善和五臣不但给《文选》释义,而且也注音。其中学界之于李善音注的研究较多,五臣音注的研究则在过去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无人关注,直至20 世纪末,才有学者涉足。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20 世纪以来国内五臣音注的研究现状。
一、关于五臣能否为音的讨论
五臣注《文选》问世之后,曾经风靡士林,但从晚唐开始备受批评。李匡乂、丘光庭、洪迈、姚宽、王懋、苏轼等相继指摘五臣注的粗浅谫陋。选学大家、“章黄学派”代表之一的黄侃先生不仅批评五臣注的释义,甚至质疑五臣的音注能力,认为“五臣注既谫陋,亦必不能为音”,“纵命出于五臣亦必因仍前作”[1]。骆鸿凯在《文选学》中引用了黄侃先生的观点,认为五臣不能音注,“斯则所云‘并具字音’,皆由钞袭矣”[2]。因此五臣音注研究,首先要面对的是五臣能否为音这一问题。
徐之明《〈文选〉五臣音钩稽》[3]首先通过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所言“并具字音”的内证,肯定五臣注确有注音;其次从音注与义注的位置,以及五家音与传世本五臣注、六臣注的音注的比较指出《文选集注》所辑录之“五家音”就是五臣音。又,因《文选集注》残卷第九三卷、王褒的《圣主得臣颂》“及至巧治铸干之璞……”一段的注文部分里,在《音决》的注音之后五臣注之前,有“五家刘治音也”6 个字,徐文认为五臣之一的刘良参与了注音,但因《文选集注》笼而统之称为“五家音”而非“刘家音”,推测恐怕非刘良一人所为,应该是几个人所作,但不管是几人所为,都可以视为“一家之音”。
董宏钰、刘贞玉《五臣“能为音”说》[4]同样注意到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中“并具字音”的内证,除此之外通过五臣音注与李善音注在音注数量、音注形式、音注内容等的差异论证五臣“能为音”,认为五臣音注是对前人及李善音注的继承、发展、超越,是对时音的一种保存。
上述两位研究者都认为五臣注《文选》中的音注为五臣所作,可作为“一家之音”整理音系,学界尚未见与此不同的声音。黄侃先生认为五臣不能为音,即使五臣注《文选》中的音注真为五臣所作,肯定也是抄自前人,所以我们认为关于五臣能否为音这一问题,还可以从“抄自前人”这个角度出发,不仅与李善音注作比较,也可与《音决》音注、《博雅音》等作比较,看“抄自前人”是否属实。
二、五臣音注体例、音注形式变化、不同版本音注差异的探讨
孔令刚《〈文选〉五臣注从单注本到合注本演变过程中出现的问题》[5]《〈文选〉五臣音注从单刻本到合刻本形式之变化》[6]《〈昭明文选〉六家音注从单刻本到合刻本的演变规律——以奎章阁本第二卷〈西京赋〉为例》[7]《奎章阁本〈文选〉增五臣音注研究》[8]等系列文章及博士论文《奎章阁本〈文选〉研究》[9]第四章“奎章阁本《文选》音注研究”对五臣单注本音注体例、五臣音注形式变化及演变规律、五臣音注增添与删除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孔文指出单注本五臣音注的基本体例是:采用句中夹注的形式,即直音法作“某”,反切法作“某某”,四声法作“平”;如果音注恰与句后正文注相连,直音法则作“音某”,反切法则作“某某反”,四声法则作“平声”。奎章阁本《文选》五臣音注形式之变化一共有以下3 种情况:为避讳改“反”为“切”;当音注后增添校语或正文注时增“音、切、声”字;当音注后正文注被移走时删“音、切、声”。奎章阁本处理五臣音注和李善音注的4 条规律是:当音注五臣有李善无时,保持五臣原貌;当五臣无李善有时,或保持李善原貌,或将其变为五臣夹注的形式;当两者皆有且相同时,保留五臣注删除李善注;当两者皆有但不同时,两者皆保留。根据孔令刚统计,与正德本五臣音注相比,奎章阁本《文选》增添205 个音注,其中有180 个见于李善单注本且大多音注完全相同,据此认为奎章阁本正文所增这180 个音注来自李善注;全书共删除五臣音注29 处,可分为5 种情况:因善注有而删、疑秀州本误脱、疑奎章阁本误脱、误作正文字体、被改为李善音注。
根据傅刚《〈文选〉版本研究》[10],秀州本(奎章阁本的底本)所录李善注的底本是天圣年间国子监本,应是目前所知李善注本中最好的版本,孔令刚对于奎章阁本《文选》增添五臣音注的结论非常重要,提醒我们奎章阁本所辑录之李善注中的音注是有所删节的,使用时应格外注意。
邹德文、董宏钰《陈八郎本〈昭明文选〉五臣音注与胡刻本李善音注对比分析》[11]对李善音注与五臣音注的内容、体式进行对比分析后概括李善音注与五臣音注的共同点有二:一是两家音注都以反切为主,直音为辅,并标有平、上、去、入四声;二是李善与五臣随文注音均具有教授《文选》、顺读选文之意,且在随文注音中都有重复注音的现象,音注用字多以常见常用的简便字为主。李善音注与五臣音注的不同点有四:一是五臣音注的数量比李善音注多,这可以在音注方面证明五臣没有抄袭李善。二是李善音注既征引其所引用典籍的音注,也有自己的音注,且音注都在注文中,不方便辨认其音注是前人音注还是李善音注;五臣音注出现在正文中,但却不标明是五臣中何人所作的音注,这与其释义体式不同。三是“某某反”与“某某切”形式是胡刻本《文选》音注与陈八郎本《文选》音注在形式上的最大不同之处。四是陈八郎本《文选》其正文、注释、音注多出现简体字、俗体字、异体字,胡刻本《文选》正文、注释、音注极少出现这些简体字、俗体字、异体字。
董宏钰、崔秀兰《陈八郎本〈昭明文选〉音注特点及其版本价值》[12]以陈八郎本《文选》五臣注为工作底本,并参考朝鲜正德本、明州本与奎章阁本中的五臣音注及唐写本《文选》残卷中的五家音,概括了陈八郎本《文选》五臣音注的4 个特点:一是以反切为主,直音为其补充,并标出平、上、去、入四调;二是五臣音注标出“某、音某、某某”,却不说明是五臣中何人所注音,这与其释义体例不同;三是五臣音注直接出现在正文被注音字的下方,这样的注音方式比较直观,符合读者阅读习惯,便于阅读文本、掌握字音,为人们阅读《文选》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四是五臣注在正文及音注切语中有颇多简体俗体字,因这些简体俗体字在正德本、明州本、赣州本、尤刻本中非常少见,反而在《唐钞文选集注汇存》中有大量类似的简体俗体字,因此认为陈八郎本《文选》五臣音注保存了唐写本五臣注的原貌。总体而言,这篇文章的观点与邹德文、董宏钰《陈八郎本〈昭明文选〉五臣音注与胡刻本李善音注对比分析》中关于五臣音注的论述大致相同。
李华斌《五臣音注的形态与传播》[13]认为五臣音注最初出现在五臣注文中,且标注了作音者,附在义后,它的音注数量和李善的差不多,后在传播的过程中发生了位置的变化,由注文中变为正文中,这才作为一个整体,不再区分吕延济或李周翰等,音注越增越多。李文的观点比较新颖,但论据及论证过程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关于五臣音注体例、音注形式变化,上面几位研究者基本已经概括清楚,但不同版本间的音注差异的探讨我们觉得还有进一步深究的必要,比如五臣注刻本与钞本相异的音注,刻本与刻本相异的音注,它们谁是原貌,非原貌的音注来自何处,这些问题的追溯对于各个版本所保留的音注的性质讨论意义重大。
三、关于五臣音注音系整理
(一)音系整理的版本选择
现存五臣注《文选》有若干版本,大致可分为单行本和合刊本两种。其中单行本包括天理图书馆藏本(简称“天理本”或“九条本”)、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锺家刻本(简称“杭州本”)、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陈八郎刻本(简称“陈八郎本”)、朝鲜正德四年(1509)朝鲜刻本(简称“正德本”)4 种。合刊本有《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简称“集注本”)、明州本、奎章阁本等。合刊本之五臣音注或有删减,或阑入李善音注,并非五臣音注音系研究的善本。单行本之中,天理本仅存第二十卷,杭州本仅存第二十九、三十两卷,都非完本,也不适合作为音系整理的工作底本。因此五臣音注的音系整理一般是以陈八郎本或者正德本为首要选择。
1.认为陈八郎本更适合音系整理
徐之明《〈文选〉五臣音声类考》[14]认为陈八郎本与毋昭裔刻本相距仅百年,其保存五臣注原貌的可信度较高,故以之为工作底本整理考订《文选》五臣音的声类系统及其特点。
董宏钰《陈八郎本〈昭明文选〉五臣音注研究》认为正德本五臣音注“是以宋韵正之”[15]23,“故其音注多与《集韵》、《类编》同,反映的是宋代的语言系统”[15]24,而陈八郎本刊刻早于正德本,反映的至少应该是宋朝以前的语言系统,因此以陈八郎本为底本整理了五臣音注的声、韵、调系统,之后与王延东合写的《陈八郎本〈昭明文选〉五臣音注韵类考》[16]亦采用陈八郎本。
2.认为正德本更适合音系整理
赵蕾《朝鲜正德四年本五臣注〈文选〉研究》认为“陈八郎本虽号称全帙,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来自五臣注本”[17]2。“与奎章阁本、秀州本相比,正德本是最能反映孟氏本音注状况的本子。与陈八郎本相比,正德本在更大程度上保留了唐钞本五臣音注的旧貌。故而,若要研究五臣音注,正德本是最为可靠的本子。”[17]127
韩丹《陈八郎本〈文选〉五臣音注探源》[18]将陈八郎本与正德本、奎章阁本正文中的音注进行比较,认为陈八郎本与正德本不同的音注,透露出陈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钞本时期的面貌,五臣音注的音系系联等研究,正德本与奎章阁本一致的音注更为可靠,而陈八郎本音注则对五臣版本演变及中古时期单个音注的研究有独特价值。
此外,高博《正德本〈昭明文选〉音注研究》认为陈八郎本与正德本的音注与诸韵书的差异程度在伯仲之间,两版本音注不存在孰优孰劣,哪个更接近“五臣注原貌”的问题,“无论是正德本还是陈八郎本中的音注都无法代表五臣音注的原貌,两者之中都含有部分后人(尤其是宋人)根据当时韵书等著作修改的音注”[19]21。
(二)音系整理
徐之明《〈文选〉五臣音声类考》[14]采用系联法,辅之以比较归纳法,整理考订出《文选》五臣音的声类为40 个。其声类系统的特点如下:唇音的轻重唇已基本分化完毕;舌音的舌头、舌上亦分化完毕;从邪分明,但船禅已混。最后徐文推测五臣音反映的大概是8 世纪较为通行的实际读书音。
董宏钰《陈八郎本〈昭明文选〉五臣音注研究》亦采用系联法、比较法,但整理考订出五臣音注的声类为35 个,与徐文不同的是,董文认为五臣音注轻重唇尚未分化、泥娘相混。此外董文考订五臣音注韵部29 个、声调4 个。其中韵类系统特点如下:江、微、鱼、齐、废、肴、豪、麻、侵等九韵独用,与《广韵》独用韵部一致;支脂之、虞模、佳皆、寒桓、删山、萧宵、阳唐、蒸登、尤侯幽、覃谈、咸衔等11 组,与《广韵》同用韵部一致;东冬钟、灰咍泰、真谆臻欣、文魂痕、元先仙、庚耕青清、盐添严凡等韵合并;歌、戈两韵独用,不同于《广韵》同用、独用例;董宏钰、王延东《陈八郎本〈昭明文选〉五臣音注韵类考》结论类此。声调系统特点如下:上声调型兼有平、去两声特点;“全浊上声变去”的音变情形,在《文选》五臣音注中并未开始出现。关于五臣音注的性质,董文亦认为《文选》五臣音注音系反映唐代读书音,既有对古反切的继承,又有作者的时音特点。
高博《正德本〈昭明文选〉音注研究》[19]在校勘的基础上归纳了正德本音注的体例,使用反切系联法、音注类比法、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对正德本音注的声、韵、调系统进行了全面研究,研究结果为正德本音注共有50 个声类、245 个韵类、4 个声调。
由上文可知,五臣音系的整理目前还存在版本选择、结论不一的问题,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四、关于五臣音注与《文选》解读
徐之明《〈文选〉五臣音特殊音切与〈文选〉解读》[20]首先界定了“特殊音切”的两条依据:一是与五臣音声韵系统不相吻合的音切,二是与《广韵》声韵系统不相吻合的音切。以此为标准,文中对5 个汉字的音注进行了解读,认为“嵚”五臣音读作“晓”母是为了与后面的“巇”字构成双声,借此与前面3 个联绵词相对应,以体现《文选》辞赋的声律美。“五臣音“呼觉”义“狶声”与韵书的音“莫江”义“草名”相距甚远,是因为五臣注中的与韵书的“乃同形异词,并且指出《文选全译》(máng 芒):猪叫声”的注释采用韵书音五臣义,显得“不伦不类”,按照唐代的反切折合今音“应读作“xuè”。“岬”五臣音“峡”义“两山之间”,是指出“岬”通“峡”,相对于《文选全译》“岬,山谷”,徐文认为“‘岬’在这里当读为‘峡’,指两山之间”的注释较为贴切。“瀼”读作“书”母也是为了与后面的“湿”构成双声联绵词,并指出《汉语大词典》收录“瀼瀼”词条并引《海赋》书证是“望文生训”,五臣注《文选·海赋》中的“瀼(音伤)瀼”只是音素,韵书中的“瀼(汝阳切)瀼”才能独立成词。“剹”五臣音“渠幽”韵书音“力竹”,二者声韵相去甚远,既可能与联绵字的改易其读有关,也不排除被切字字体嬗变而带来的问题;针对《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的注音“jiū”以及《文选全译》的注音“qiú”,徐文通过考证,认为读作“qiú”方为贴切。
从上面徐文主要内容和观点的概述,我们能看到五臣音注(尤其是特殊音注)对于《文选》解读的重要性。今人读《文选》实在难懂,借助今人的注释、翻译是初学者的首选,因此准确的注释和翻译就显得尤为重要,而要准确地注释和翻译,除了参照古人的释义外,古人的音注也起到很大的作用,音义两者紧密结合,缺一不可。徐文释读了五臣音注中的5 条特殊音注,借此抛砖引玉,但类似这样的特殊音注远不止5 条,把类似的非纯粹注音的特殊音注遴选出来并进行解读,不仅对五臣音系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有益,而且有助于《文选》的注释、翻译。这项工作虽然很难,但不可回避。
五、结语
综上,先行研究涉及五臣音注研究的面很广,对后人的研究颇有助益,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先行研究还有可以深化、改进之处。
第一,研究者不多。例如五臣音系整理及音注与《文选》解读的关系应该是五臣注《文选》音注研究的重中之重,但前者只有一篇文章及两篇硕士论文涉及,后者只有一篇文章,且只研究了5 个词语。
第二,结论有异。徐之明与董宏钰同样以陈八郎本为工作底本,同样采用系联法、比较法,但一个得出声类40 个,一个得出声类35 个。董宏钰和高博分别以陈八郎本和正德本为工作底本,他们整理出来的声类、韵类差距更大。
第三,研究的论证过程值得商榷。例如关于帮非混切的证明,董宏钰举了“镳(甫娇)彼娇①斜杠前的括号为《广韵》反切,斜杠后为五臣反切,下同。、镳(甫娇)彼苗、镳(甫娇)悲苗”3 个例子,然而这3个例子恰恰证明《广韵》还存在的“类隔”切,五臣音已经“音和”,是五臣音注帮非分化的铁证。董文不仅帮非分化,反切上字也有明显唐代特征:“镳”字是重纽三等,切上字也是重纽三等。重纽三等绝无变轻唇的,因此《广韵》用轻唇音作切上字,是《广韵》轻重唇不分,五臣改用重唇且用上字管介音的切上字,证明五臣轻重唇已经完成分化,不能再互作切上字。
对于韵部归类的举例同样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冬钟混切的例证:豵(即容) 宗(作冬)、脓(奴冬)女恭②原文为“脓 女恭(奴冬)”,应是录入之误。。其中,“豵”在《广韵》有即容、子红二切,释义皆为“豕生三子”,若采用“子红”之切,与五臣音注音韵地位相同。“脓”《广韵》仅“奴冬”一切,释义“上同”,即“肿血也”,与五臣“肥也”之义相差甚远,五臣中的“脓”本字应为“醲”;“醲”《广韵》反切“女容”,与五臣音注音韵地位相同。因此,这两例都不适合作为冬钟混切之例。
第四,细节方面有待深究。例如先行研究大多提到陈八郎本与正德本之间存在互为有无、音注差异等问题,虽然各研究者的数据有所出入,但概而言之,陈八郎本有正德本没有的音注大概有200个,正德本有陈八郎本有的音注550 多个,两书相异的音注450 个上下,这些数量并不少,只在一个版本存在的音注来自何处,两书相异音注又来自何处,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五臣音注研究及音系定性至关重要。除了这两个单行完本相异音注的溯源外,单行完本与残卷特别是钞本的音注差异的溯源也是非常重要,不仅要指出彼此的不同,还应深究不同的出处。又,先行研究提及正德本音注经宋韵而改,《文选》六家注本之奎章阁本书末所录《五臣本后序》亦言“字有讹错不协今用者皆考五经宋韵以正之”,那么这里的“五经宋韵”指的是什么呢?有宋以来的五臣注刊本与宋代韵书的关系到底有多亲密呢?这些问题值得深究。
第五,综合研究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先行研究对五臣音注研究各个方面都有涉及,但基本都是只持一端,这很容易造成结论的片面或不准确。不同版本的音注整理、甄别、筛选是五臣音系整理的基础,反之,五臣音系的整理对于五臣注不同版本的音注整理同样有帮助;五臣音注随文而注,音义紧密相连,以音求义,因义辨音亦是相辅相成。
此外,高博《正德本〈昭明文选〉音注研究》也提到了先行研究的几点不足:一是对五臣音注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某些领域还是空白状态;二是研究方法的使用有误,如系联法;三是对一些音韵学方面的基本概念混淆不清,常将声类与声母、韵类与韵母混为一谈;四是对音系特征、性质的判定使用模糊用语或一些易混淆的概念,如读书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