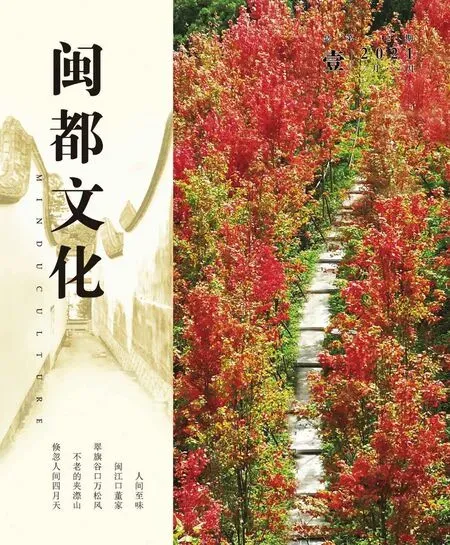南方有佳人
2021-12-28赖华
赖 华
邮寄地址:福州南门外禄家乡。
如此模糊的地址,却能精准投递。几位七八十岁的林姓老人,看我惊讶地张着嘴,无比开心,笑得满脸都是褶子,再次七嘴八舌地确认,没错,信封地址不用这样写:福州市闽侯县祥谦镇禄家村,因为这里曾被喻为“小香港”。

龙祥岛
谁能想到,乌龙江中的一片小沙洲上,曾经有粮店、布店、酒楼,甚至还有人在此贩卖私盐,开地下工厂制造假银圆?村前的两个码头停满南来北往的摇橹双桅船,日日人声鼎沸。炎炎夏日,我漫步在环岛堤岸上,走过古码头,身边闽水汤汤,江中汽笛声声,岛内却是一片静谧,唯有盛夏的蝉鸣不停不休。是什么成就了乌龙江中一片小沙洲的繁华?是什么让南来北往的客商就此停下脚步?解放战争时期,是什么让小沙洲谱出一曲英雄赞歌?又是什么令沸腾过的小沙洲重归寂静?我在江边徘徊,追寻历史曾在此造就的繁华时光,寻觅佳人远去的足迹。
传说远古时候,七星坠地,落入乌龙江,形成七块礁石。随着时间的推移,礁石阻水沉积而成七个礁洲。后来,一渔妇生产,将污秽产裤晾晒在礁石上,这个礁洲因此沉没,只余六礁。六礁连成片后形成岛屿,即龙祥岛。岛上有两个行政村,禄家村和江中村。福州乡语“六礁”与“禄家”谐音。“禄”有福气、福运之释义。“禄家村”,用七星坠地之天地灵气来命名村庄,寄托着岛上先民的殷殷期盼。
龙祥岛未通桥之前,四面环水,与世隔绝。清咸丰八年(1858),尚干镇淘江边龙屿村的林姓先祖登鲤尾山扫墓,遥见淼淼江水中一岛屿若隐若现,水草丰美,鸥鹭点点,为之心动。回村后即与族人商议,决定前去垦荒。他们先是从山上砍伐大量的细竹竿,用船运到岛上,插入沙地,以阻挡急流,令泥沙沉积。数年之后,岛上沙洲果然长高,泥层增厚。林姓先祖策公和略公率先带领7户人家40多人,驾船登岛,搭棚建舍。他们从此过着最原始的刀耕火种、与天地相抗争的垦荒生活。
我望着眼前不大的村子。小洋楼林立;家家户户门前荔枝树、龙眼树郁郁葱葱;江风掠过大片大片的甘蔗田,绿波微漾;小四轮机动车满载着从田里连根拔起的毛豆,茎秆上挂满成熟的豆荚。岛上一派生机,岁月安然,林姓先祖策公和略公在九泉之下,该捻须含笑了吧。
顺着乌龙江逆流而上,可达永泰、南平、闽清、三明等地;顺流直下,于三江口汇入闽江,而后向东,流入台湾海峡。龙祥岛位于福州市南台岛南侧的乌龙江中,是古时福州城南大门的水上交通咽喉。禄家村位于龙祥岛西面,从航拍的角度观龙祥岛,整个岛屿像一只逆流而上的大鲶鱼,而面积1.5平方公里的禄家村则像是“鲶鱼”的大嘴巴。俗话说嘴大吃四方,从上下游而来的船只皆在此歇脚,然后转向福州城或闽江沿岸县市。因为闽江中上游是山区性河流,两岸多高山峡谷,滩多流急,往中上游而去的船只,更需要在此添加补给。
在后门渡古码头,我面南而站。抬望眼,村子南面对岸是五虎山,头虎气势昂扬地紧伴在村旁,俨然忠实守卫;码头北面与盖山隔江相望,曾经有渡船每日往返其间。村支书林晓明说,本村有两个码头,另一个在七星洲,叫前门渡码头,渡船往返于本村与鲤尾村之间。鲤尾村东去尚干,西往南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陆上交通不便,人们多选择水路出行。禄家村成了闽江上下游的中转站和补给站之后,许多外来人到此落脚做生意。渐渐地,村里商铺林立,分布粮店、布店、酒楼等;因福建山区缺盐,贩卖私盐利润高,胆大的村民即买船前往海边,贩回私盐,卖往山区;因为商品在禄家村成交量巨大,有人盯上用以交易的货币——银圆,在此开地下工厂制造假银圆。

龙祥岛上远眺五虎山
我闭上眼睛,江风扑面,似乎感受到古码头上曾经的熙熙攘攘。似乎听到各色商贩招揽生意的吆喝声,穿戴齐整、来去匆匆的客商招呼“鸭撇仔”声,靠搬运做苦力的脚夫小心翼翼的问询声,从上游放木排到福州城的排工上岸歇脚、呼朋唤友声——禄家村下辖的文山洲水域,停泊着一大片木排。我恍惚还听到有艘摇橹双桅船上传来永泰嵩口古镇的乡音,当年往返福州—永泰的商船被称为“南港船”,此处是必经之地。或许我的先祖也曾踏上这片沙洲。无端地,我有些激动。福州城里城外,谁人不知禄家村?我看到一张照片:一封发黄的竖式信封,封面左侧是印刷繁体字“福建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右侧是收件地址“福州南门外禄家乡”,中间是收件人“林其塘先生”。民国的两张半分邮票贴在左上角。两个民国邮戳将时光定格在信封上,为一块小沙洲的繁华做证。
翻开历史书卷,浓墨重彩从来只留给大都市,一块小沙洲曾经一世繁华,却变成村里老人口口相传的传说。唯有穿梭在茫茫光阴里的英雄的身影,不曾被历史遗忘。
村支书林晓明谈起先祖、族人时,满怀敬意。他说先祖是从尚干淘江边迁来的,因此,岛上的林姓皆称“淘江林”。祖辈林森公是所有“淘江林”族人中最令人骄傲的人物,赫赫有名的辛亥革命元勋,民国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府主席。1943年,林公逝世时中共中央致唁电:“国府主席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读过历史的人,谁不知林公?!他也是我们福建的骄傲。林公出生于福建闽县尚干凤港村,是“淘江林”三十二世。我问晓明支书是“淘江林”几世,他答“三十七世”。时光还未走远,伸手可触。打开历史之门,找寻的不只是一段记忆,更是一份爱国爱家的传承。
历史也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而是一代又一代人打拼下来的生命印迹。
在村委里,和几个林姓老人闲聊禄家村的前世今生,他们谈及村里地下武工队“青鸭帮”的一段历史,让我触摸到有着铮铮铁骨质感的旧时光。
老人家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有国民党保安团官兵驻守在禄家村西南面的南通镇上。龙祥岛是闽江下游的咽喉要地,镇上的保安团官兵常派船在乌龙江沿岸巡弋,或是将押运的粮船停泊在文山洲岸边。为了福州城顺利解放,共产党地下党派林培琛回禄家村发展地下武装力量,这支力量就是地下武工队——“青鸭帮”,队员大部分姓林。老人接着解释,“青鸭帮”的“青”是指男子的土布黑短褂。福州方言“青鸭”和“青蛙”同音,乌龙江边的男子哪个不似青蛙般善游善泅?遇到保安团官兵追捕,“扑通”一声,跳进江中,谁能奈何?“青鸭帮”确实令保安团官兵头疼不已。原来只知白洋淀上神出鬼没的“雁翎队”,没想到禄家村也有“青鸭帮”,不禁肃然起敬。“青鸭帮”在村里执行着上级地下党布置的任务,为解放福州城而全力以赴地与保安团官兵周旋,确保福州城的“咽喉”要地不被占领。说到兴奋之时,老人们随口而出“青鸭帮”成员的姓名:带头人叫林木枝,成员有林依万、林依阔、林明和、林玉灼、林金光等十余人,皆是青壮年。
林依港(林木枝的儿子)、林国藩两位老人带着我,参观地下武工队“青鸭帮”秘密开会地点,一座黑黝黝的单层老木屋,也是林木枝、林依港父子俩的家。把秘密聚会点设在自己家里,相当于把一家子的身家性命都搭上,何等坚定的革命意志。难怪当我要求林依港老人讲讲他父亲的故事时,旁边的老人立即笑着说,他不懂,那时才几岁呢,保安团官兵一上岛,除了他爸,全家人都逃到鲤尾山上躲了起来。也是,提着脑袋干革命,容不得丝毫的差错,哪能把执行过的任务当作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两位老人还把我带到村子中央的日益超市旁,指着一个屋檐下的一块地方说,烈士陈定波于1949年8月17日上午在此就义,而福州城就在当天下午解放。我的心为之一震,久久无法言语。岁月静好,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吾辈当珍惜!
看着村里挤挤挨挨的小洋楼,可以想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禄家村的“小香港”地位。那份繁华曾给小村庄带来红利。村民除了种植农作物外,主要收入靠什么?靠运输,几个老人异口同声。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禄家村家家户户有船只,运输业做得风生水起。
随着运输走四方,“兴学育才为重”的念头在见多识广的村民心里逐渐生根。1917年秋,村里第一所学塾在林祥清祖厝里成立。林公在世时,十分注重教育,且将这支“淘江林氏”聚居地视为第二故乡,曾对禄家小学慷慨解囊捐建校舍,并亲自题写对联:“树立农村基础,养育民族健儿。”横批:“培育英才。”历年来,禄家小学先后培养出数以百计的党政军领导干部及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南尾星,只坠坠,划船仔,去开会……”走在环岛堤岸上,望着堤坝外湿地上芦苇摇曳,荟草青青,我的脑海里不由得蹦出禄家村的这一句童谣。仿佛看见一群放学后的孩子,冲出校门,爬上自家的小船——鸭撇仔,唱着童谣,在这个南方的水乡泽国里摸蚬子、捞流蜞、掏鸟蛋、钓蟛蜞……
2013年,福州市螺洲大桥正式通车并经过龙祥岛。与世隔绝的岛屿从此变通途。随着全省交通日益发达,禄家村作为福州城南门外水上交通的咽喉要地的地位逐渐地成为历史,水上运输日渐式微,村里的青壮年携家带口转到其他地方讨生活。村庄沉静了下来。看着作为福州城呼吸吐纳的“肺”——乌龙江中的湿地,呼吸着纯净的微润江风,《诗经•蒹葭》里的诗句蓦然涌上心头,挥之不去:“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南方有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