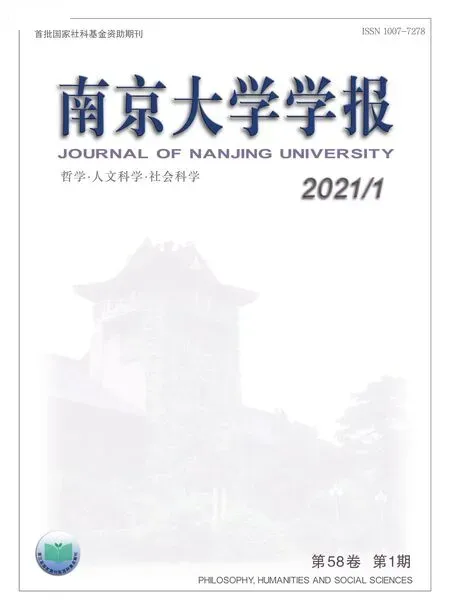国有企业法律属性的困境与出路
——基于行政组织私法化的新视角
2021-12-27何源
何 源
(上海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 上海 210000)
一、引 言
与国有企业改革在实践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国有企业法学理论研究明显不足,其突出表现为:国有企业的法律属性尚未达成共识。在长期处于经济学思维主导下的“产权进路”改革背景下,法学界将研究重点置于国有企业的私法属性上。它背后的核心逻辑为:国有企业属于公司法人,对内应当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对外应当做到政企分开,从而实现国有企业的自主经营。然而,上述逻辑既无法充分关照现实需求,又与现行法律制度相悖。
其一,现有学说不能契合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要求。经济转型时期,改革目标在于推动产生于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国有企业向市场经济转向。与此相应,学说注重国有企业的私法属性有助于实现企业的自主经营。2013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指出,国有企业已基本与市场经济融合。(1)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3年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因此,在国有企业迈入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改革目标也已转型为使国有企业成为实现国家重大战略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此时,过分强调国有企业的私法属性,反而容易导致企业的公益性被营利至上的论调扭曲与异化,无助于改革目标的实现。
其二,现有学说无法有效解释其与现行法律制度之间的龃龉。过分突出国有企业的私法属性并不符合其在法律制度中的定位。现行法律规定对于国有企业的调控存在诸多与私营企业不同之处。比如,公司制改革后的国有企业原则上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调控,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以下简称《企业国有资产法》)中又增加了不少审批性条款。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及能源领域的单行法对公用企业进行特殊规定,一定程度上允许其享有垄断地位。上述种种附加义务或是特殊待遇,若仅仅简单地归因于政策诉求或是历史遗留,则不啻为一种逃避,也丧失了从法释义学角度直面国有企业不同于私营企业的法律属性这一问题的可能性。
归根结底,现有学说无法有效对国有企业公益性自圆其说,这包括国有企业公益性的正当性基础以及公益性与营利性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目前展现出的对于国有企业公益性的理论关怀,仍立足于私法属性的基石之上,仅将公益性加以特殊处理。这使得其对于公益性的内涵及其来源思考不足。对此,本文的立场是:国有企业是一种“私法化的行政组织”,它在功能上的公共属性与组织上的私法属性相互分离,二者间的冲突需要通过公私交融的制度设计才能得以消弭。
二、国有企业法律属性的理论困境
现行法律规定并未明确国有企业的法律属性,这导致该问题在理论上存在争议。改革初期,“单一性”理论占据主导地位,其强调将国有企业作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来看待。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企业的公益性逐渐受到关注,“双重性”理论亦应运而生。然而,无论是“单一性”理论,还是“双重性”理论,都存在内在矛盾,不足以准确定位国有企业的法律属性。
(一)单一性理论
1.理论背景与内涵
“单一性”是指突出国有企业的商事公司性,将其看作以营利性为主的市场主体。典型代表为“商事公司说”,该说主张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的根本动机是把企业塑造成真正的市场主体,因此应当将国有企业视为一般性商事公司。(2)参见王保树:《国有企业走向公司的难点及其法理思考》,《法学研究》1995年第1期。“商事公司说”的提出契合于彼时国有企业改革的现实背景。经济转轨的大时代下,诞生于计划经济并与之相匹配的庞大国营工业体系迅速向市场经济“转身”,力求尽快消除计划经济的烙印,“国有企业”迫切地向“国有公司”转变。1984年7月,我国第一家由全民所有制企业改建而来的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国有企业改革战略的落实与飞速发展的实践共同对学界提出亟待解决的议题:如何推动国有企业向公司法人的转变。“商事公司说”就此诞生。诚如王保树教授所言,改革初期,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商事公司仍与旧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残留痕迹有所冲撞。且商事公司已远离中国经济生活几十年,相关传统于中国并不存在,相关认知更是匮乏。(3)参见王保树:《国有企业走向公司的难点及其法理思考》,《法学研究》1995年第1期。因此,强调国有企业的商事公司特性符合彼时公司制改革的实践需求,对促进企业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随着改革的深化,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日趋完善,营利能力与竞争力均大幅提升。目前,国有企业总体上已经同市场经济融合,国有企业改革自此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单一性理论已不足以应对新的矛盾,更无法有效指导改革实践。
2.理论困境
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阶段,主要矛盾已经从国有企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身”发展为其商业性与公益性之间的矛盾。长期“产权进路”改革模式所追捧的经济学思维虽然提高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但也过度放大了企业的商业性功能。在效率至上的价值引导下,盈利水平成为实践中评价企业好坏的主要甚至是唯一标准。比如国资委明确将企业利润总额与经济增加值作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的基本指标(4)参见《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办法》(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40号),2019年3月1日发布。,过度重视商业效率的弊端已见端倪。有学者指出,国有企业商业化的深层原因,是国有企业不恰当地承担了应由一般企业完成的“商业功能”,这使得国有企业在现实中“完全沦为私法意义上的商事工具,其公共性越来越被掩盖或扭曲”(5)蒋大兴:《国企为何需要行政化的治理——一种被忽略的效率性解释》,《现代法学》2014年第5期。。更有甚者,营利至上与国有企业私有化等论调,使得国有企业的公益性愈发模糊。无怪乎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感叹“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我,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6)参见中国广播网:《国资委主任李荣融:为什么国企好坏我都挨骂》,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09/12/id/385822.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9月17日。其内在症结便在于,国有企业并未真正做到为公共福祉服务,人民未能分享到国有企业改革的红利。
单一性理论无法解释国有企业双重属性之间的矛盾。以该理论所遵循的逻辑来看,既然国有企业是商事公司,是真正的市场主体,那么营利性本就是公司法人的天然追求和核心目标,所以注重企业的商事效率似乎也无可厚非。于是,国有企业公益性法律保障的缺失导致一系列严重问题,比如,改制过程中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有学者指出,这一大规模、深层次、关系数万亿国有产权变动和流转、牵涉上亿职工命运的改制,却是由不少彼此矛盾与冲突的低阶的行政规定指导的。(7)参见郑万青:《国企改制的法律缺位及其原因探究——对郎咸平现象的法理学思考》,《法学家》2005年第1期。再如,国资委的法律定位模糊不清。按照《公司法》的设计,国资委应像私营企业股东一样行使职权,但实践中国资委又不可能“放手”到如此地步。于是,国资委一直在“老板”和“婆婆”的双重角色之间游离。上述种种问题已非简单地将国有企业打造成一个“纯商事公司”便可以解决,法学理论需要进一步的突破。
(二)双重性理论
1.理论背景与内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2015年8月24日发布,以下简称《深改意见》)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国有企业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这一政治话语背后隐含着若干法律上的难题需要回应。如何保障国有企业的战略意义与特殊地位真正实现?政府是否需要对国有企业重新进行干预?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究竟是否具有同样的法律属性与功能?对此,单一性理论的局限促使学界对国有企业除商事公司之外的另一重特性开始进行挖掘,即所谓“双重性”。关于国有企业的“双重性”,现有学说主要包括“特殊公司法人说”“特殊法人说”与“公共企业说”三种。
第一,“特殊公司法人说”认为国有企业同时具有“公司性”与“行政性”。该说主张,国有企业兼具“公司法人属性”与“行政色彩”,是一种“特殊公司法人”。(8)参见顾功耘等:《国有经济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71页。这种双重性的来源是基于国有企业“经济人”与“准政治人”的双重身份,其使得政府追求的社会政治稳定与企业经济效益等“双重目标”也自然延伸至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的双重性也可被理解为“企业性”与“公益性”。(9)参见顾功耘、胡改蓉:《国企改革的政府定位及制度重构》,《现代法学》2014年第3期。
第二,“特殊法人说”将公有企业范畴中的国有企业认定为一种兼具公法人和私法人特征的“特殊法人”。私法人特征,是指国有企业同私营企业一样以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身份注册,具有经营自主性。公法人特征,则是国有企业需要受国家控制、要体现国家政策、目标具有社会公共性,等等。该说所得出的结论是:无法将公有企业范畴内的国有企业简单地纳入公法人或私法人范畴,应将其视为“政府规制与意思自治”之间的“特殊法人”。(10)参见胡改蓉:《论公共企业的法律属性》,《中国法学》2017年第3期。
第三,“公共企业说”强调国有企业的公益性本质。该说认为,当下改革举措促使国有企业向营利性强的商人主体转变,这极易导致国有企业“在现实政策中完全沦为私法意义上的商事工具”(11)蒋大兴:《国企为何需要行政化的治理——一种被忽略的效率性解释》,《现代法学》2014年第5期。。国有企业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其能否盈利”,而在于“作为人民的企业形式,能否满足普通民众福利的提升”以及“利润有多少贡献给了公众福利”。(12)参见蒋大兴:《废除国资委?——一种理想主义者的“空想”》,《清华法学》2016年第6期。国家或政府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私人不愿追求或无法实现的公益任务应由政府或国有资本来承担。(13)参见史际春:《国企公益性之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4月9日。
2.理论困境
上述学说虽论证思路不尽相同,但具有共同的出发点与核心目标,即均以私法性视角出发,将国有企业视为一种公司法人,并试图找到国有企业与其他公司法人之间的区别。就现状而言,此种努力似乎陷入了以下困境:各学说均无法提供一个适当的理论框架来论证国有企业公益性的正当性基础,以及双重属性间的关系。
第一,“特殊公司法人说”认为国有企业是一种兼具公司与行政色彩的特殊公司法人。该说毋宁是国有企业的现实状况在法律上的表达,但对其特殊性的来源与表现之理论关怀则显得不足。若将特殊性归咎于国有企业的“准政治人”身份,那么“准政治人”与公司的意思自治原则是否相互违背?同时,该说认为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国有企业的公益性。那么,公益性与资本的天然逐利性又是如何相互融合的?简言之,该说并未能充分说明国有企业特殊性的来源及其与公司性之间的关系。
第二,“特殊法人说”更加具有突破性,它试图在公法人与私法人之间创设出一种“特殊法人”。然而,该说的困境在于与现行法律制度的冲撞。一方面,2020年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96条规定,“特别法人”是指机关法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城镇农村的合作经济组织法人与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这与该说中的“特殊法人”含义大相径庭,不足以作为法律依据。另一方面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依《民法典》第76条之规定,应当属于营利法人,即私法人范畴。可见,在公私法人二元分立格局尚未形成的我国,构建一套突破公私法人区分的“特殊法人”,只能加剧理论及现实间的龃龉与摩擦。
第三,“公共企业说”与“特殊公司法人说”相似,本质上是将国有企业视为一种“特殊的公司形态”。这种新型公司应当被置于一部“公共企业法”中,从含义、目标、设立到公司治理、财务制度、信息披露、解散以及法律责任全部单独规范。 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公共企业说”其实为“特殊公司法人说”提供了一种更加具体的方案。但二者亦面临同样的困境,即国有企业作为公共企业,其公共性的正当性基础究竟在哪里。
三、行政组织私法化:一个新的理论框架
自公司制改革以来,国有企业便一直被置于公司法人范畴讨论。但是,若将时间节点向前拉伸,便会发现国有企业诞生之初乃是作为行政组织而存在的。因此,本部分将不同于传统的私法性视角,而是从公法性视角出发,对“行政组织私法化”理论框架及其与我国改革实践的契合性予以研究。
(一)行政组织私法化与私法化的行政组织
行政组织私法化中的“私法化”译自英文中的“Privatization”一词,其泛指原由公共行政承担执行责任的行政任务移转至私法人的变更过程。
根据私法化程度不同又可区分为组织私法化、功能私法化与任务私法化。(14)参见Martin Burgi, Isensee/Kirchhof (Hrsg.),Handbuch des Staatsrechts,Band IV, 3. Aufl., Heidelberg: C.F. Müller, 2006, S.210.组织私法化位于私法化光谱最弱一端,意指行政部门仅于组织形式上利用私法工具,在一般行政组织体系之外,另行设立、承继或将原公法组织改制为私法形式组织。
“行政组织私法化”这一过程所导致的结果是“私法化的行政组织”。“私法化的行政组织” 以公司法人为主,其最大特点在于组织形式与功能性质的分离,即实质上的行政任务与行政部门对任务所负有的责任维持不变,但任务履行者已由传统的行政组织转变为私法组织。这会导致以下问题:第一,法律属性判断较为困难,“私法化的行政组织”究竟是私法人,还是公法人。第二,如何进行法律调控,究竟以私法为主,还是以公法为主。
关于法律属性问题,学界所达成的基本共识为:私法化的行政组织本质属性乃国家而非私人。对此,可将其区分为两类进行讨论:公设私法人与公私合营公司。所谓公设私法人,是指由国家百分之百控股的政府独资公司,在我国习惯称国有独资公司。学界普遍认为其仅是国家换上“私法袍服”而已,本质上仍属于行政权的行使。(15)参见Dirk Ehlers, Hans-Uwe Erichen /Dirk Ehlers (Hrsg.),Allgemeines Verwaltungsrecht,14.Aufl., Berlin: de Gruyter, 2010, S.5.其次,公私合营公司是否具有国家本质要视其实际控制人而定。私人股份的加入使得公司的法律属性判定更加困难。对此,通说认为应当以公司背后的“人”作为判定标准。(16)参见Willy Spannowsky,“Der Einflub ffentlich-rechtlicher Zielsetzungen auf das Statutprivatrechtlicher Eigengesellschaften in öffentlicher Hand: öffentlich-rechtliche Vorgaben, insbesondere zur Ingerenzpflicht,”ZGR1996, S.409 f.公司背后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家,则公司本质属性为国家;实际控制人为私人,则公司本质属性为私人。进一步而言,关于如何判断公司背后的实际控制人则采清晰易行的持股比例标准,即国家股东与私人股东哪一方的持股比例超过50%便被认定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比如,在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案”中,经营法兰克福机场的F公司,其52%股份由黑森州与法兰克福市共同持有,另外48%股份由私人持有。据此,可认定政府对公司具有控制力。(17)参见BVerfG NJW 2011,1201(1202 ff.).当然,如果国家持股不足50%,但其被证明通过其他途径得以实际控制公司的经营活动,例如相对控股、协议控制等,也可认定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关于法律调控问题,学界达成的基本共识为:私法化的行政组织应在公法与私法中寻求平衡。私法化后的行政组织在形式上属于私法人,应当在私法框架内活动。唯有如此,私法组织具有的灵活性、决策效率高、融资渠道广等优点才能够充分发挥。但是,私法化的行政组织担负着公共任务,又需要受到公法的调控,以保障公共任务不被私法人的逐利性所吞噬。受到哪些公法的调控?公法与私法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这无疑是行政组织私法化对法律调控最大的挑战。对此,颇具代表性的处理方法为德国法上的“行政公司法”理论。依照该理论,国家负有影响或介入政府公司的义务,以保障其公益性的实现。但公司法属于联邦法,根据“州法不破邦法”的原则,市镇自治章程中关于国家影响义务的规定很难完全在公司法框架下得以实现。因此,市镇自治章程等公法规范有权对公司法进行补充与调整。
“行政公司法”自形成之初便一直饱受质疑。在反对者眼中,“行政公司法”最大程度的作用,也只是提醒市镇不要忽略通过在公司章程中规定监事派遣权等内容的方式来保障国有公司公共目标之实现而已。(18)参见Dirk Ehlers,“Interkommunale Zusammenarbeit in Gesellschaftsform,” DVBI 1997, S.137 ff.基于此,又产生了若干其他理论,最具代表性者为“特别公司法”与“新公司形式”理论。“特别公司法”主张以例外性规定或新设性规定来保障影响义务在公司法框架内实现的可能性。比如可以在德国《股份有限公司法》第四章第一节“区域社团法人参股公司的特别规定”中设置若干“例外性规定”。新设性规定则是指通过特别法的形式创设一种新的公司形态,比如1994年颁布的德国《邮政法》与1933年颁布的德国《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法》。“新公司形式”理论则主张将国有公司解读为公法框架下的一种全新组织形态。其中,“公共经济公司”(Gesellschaft für öffentliche Wirtschaft)是呼声最高的形式,甚至还产生过专门的《公共经济公司法(草案)》。
从上述理论的激烈争议中,可以发现,一方面各种理论均致力于解决同一个问题,即政府公司同时受到的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之间的关系。对于私法化的行政组织而言,兼顾公法规范保护的公益价值与私法规范保护的自由价值是不可动摇的命题。另一方面,实现两种价值协调与平衡的具体机制与制度设计可以有多种选择。民营化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现象,它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亦有着不同的解读和实现形式。同样的,行政组织私法化中的价值平衡亦需要结合各国的具体实践与法律体系而展开。
(二)理论框架与本土实践的耦合
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质上是一种行政组织私法化的过程。所以,可以用行政组织私法化框架来分析中国国有企业的法律属性。为此,需要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早期国有企业是一种“行政组织”么?第二,如果改革启动之前的国有企业属于行政组织,那么它的“私法化”又是如何实现的?
1. 作为行政组织的国有企业
行政组织私法化的前提在于,必须存在所谓的“行政组织”。诞生之初的国有企业,虽名称中带有“企业”二字,但它与现代商事公司完全不同,毋宁说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体制紧密契合的“行政机构附属物”与“被动执行上级计划指令的执行者”。(19)参见邵宁主编:《国有企业改革实录(1998~2008)》,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6页。它在组织形式与功能性质上均具有明显的行政属性。
(1)组织形式上的行政属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央政府效仿苏联模式将没收的官僚资本企业组建为工业企业,彼时称为“国营企业”。与现代商事公司不同,国营企业的设置、结构、编制、人员管理、职权等重要的组织问题都不能由企业自行决定,只能按照国家指令行事。这更加接近行政机关所遵循的依法组织原则。
首先,国营企业在人财物上无任何自主权,仅是完成上级机关下达生产计划与指令的工具。企业与政府机关一样,有固定的人员编制,引进职工需要向劳动主管部门申请,由国家进行分配,他们的工资也由国家发放。企业对干部的选用仅有建议权,任命权掌握在主管部门手中。企业运营所需的物资与资金,需逐级向主管部门申请,中央主管部门编制预算报国务院批准后,再逐级分配至企业。(20)参见朱锦清:《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律调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页。
其次,企业在生产与销售环节也不享有自主权。生产计划的制定为“两上一下”模式。(21)参见朱锦清:《国有企业改革的法律调整》,第11-12页。国务院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建议制定生产额度与指标,层层下达至企业。之后,企业根据自身能力提出建议草案,逐级上报至国务院。国务院汇总草案,在全国范围内做出平衡后,制定最终方案并报全国人大批准。最后由国务院将最终方案下达至各企业,并责令其严格执行。产品销售实行“统购统销”制度。相关部门统一收购,再通过批发站销售至各商店。企业不允许自行销售,否则将受到警告,甚至处罚。此类生产经营与其说是一种商业活动,毋宁说是下级机关对于上级机关行政指令的执行活动。
(2)功能性质上的行政属性
行政组织的功能是承担特定的行政任务,这与现代商事公司以追逐利润为主要目标的功能性质完全不同。就国营企业而言,其也承担着特定的行政任务,即生产任务与社会保障。计划经济体制下,国营企业建立的目标并非自身盈利,而是完成国家的生产任务,从而促进独立、完整工业体系之形成,为国民经济发展奠定物质基础。从事实来看,国营企业也确实完成了这一任务,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生产能力得到大幅增长。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国营企业还需要为企业职工提供社会保障,职工的福利、养老、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管理职能均由企业承担。中国石油化工企业曾宣称:“一个人从生到死所涉及的社会职能,中石化全有,从医院、幼儿园、学校、就业到火葬场。”(22)参见邵宁主编:《国有企业改革实录(1998~2008)》,第259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有企业对于政府社会保障职能的分担无疑起到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某种程度上企业已成为“国家基层政权组织”,承担着基层政府的相应职能。
2. 作为私法组织的国有企业
在市场经济逐步建立的过程中,国有企业承担起“公司重建”的任务,肩负着本应由私营公司承担的商业功能。这也正是上文中“商事公司说”提出时的社会背景与现实基础。然而,回望40余年的国企改革,却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国有企业的战略地位与实际功能使其从未成为过真正的“纯商事公司”。一方面,相关政策赋予国有企业有别于私营企业的特殊地位。上述《深改意见》开宗明义地指出,国有企业是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实践中国有企业除商业功能之外也往往承担着实现国家战略的重要使命。比如,在上海,国有企业已成为建设科技创新中心的主力军。(23)参见金琳:《上海市国资委积极鼓励国企创新》,《上海国资》2016年第6期。因此,国有企业不同于一般性商事公司,它具有独特的法律属性。具体而言,此种独特性可从组织私法化与功能性维持两个层面来解读。
(1)组织私法化
组织私法化,是指国有企业从组织形式上逐渐转化为公司法人。就立法层面而言,这一转化的重要节点是中国首部《公司法》的颁布。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目标,1994年《公司法》正式实施,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两类公司形式。同年,国家经贸委确定了100家国有大型企业作为公司改革的试点。2017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中央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7〕69号),要求到2017年底,央企(不含中央金融、文化企业)应全部改制为公司形式。至此,中国国有企业在组织形式上已基本实现向私法人,即公司法人的转变。
组织形式的变化自然带来行为模式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下,根本不存在市场,也就不存在真正的市场经济活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尽管仍然存在政府干预定价(例如成品油定价机制)与一定程度的国有企业垄断(例如电信、电力、石油领域),国有企业的行为市场化特征已普遍形成。私法性的组织形式及市场化的行为模式使得国有企业在人事、管理、财务上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与灵活性,具有更高的经济活动效率。1998年到2010年10余年间,国有企业资产总量从14.87万亿元增加到68.62万亿元,实现利润总额从213.7亿元提高到2.21万亿元。(24)参见邵宁主编:《国有企业改革实录(1998~2008)》,第495页。
(2)功能性维持
除采用公司法人的组织形式之外,改革呈现出的另一特点为国有企业的功能性维持。尽管企业在组织形式上已经转变为公司法人,但其仍然承担着公共性任务。只是与早期的生产任务与社会保障相比,国有企业现在承担的任务内涵发生了较大改变。
随着政企分开进程的加快,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分任务逐渐转移至私人和社会资本上去。比如,社会保障任务已通过“减轻国有企业办社会负担”的改革举措转移至政府部门。(25)参见《国家经贸委(已变更)、国家教委(已更名)、劳动部(已撤销)、财政部、卫生部(已撤销)关于若干城市分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分流富余人员的意见的通知》(国经贸企〔1995〕184号),1995年5月2日发布。同时,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行的“放小”与“退出”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使得国有企业更多地集中于自然垄断与公共服务领域,大批中小型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上述领域中原本由国有企业承担的国家任务也释出至私人与社会资本,交由私营企业承担,如日用品、食品、纺织品,等等。
部分任务被保留下来,与此同时被赋予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内涵,如公共服务功能。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在公用事业领域提供满足人民基本生存需求的产品与服务,包括供气、供水、供电、供热、能源、交通、电信领域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7条明确规定,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实践对于这一功能的重视往往存系于政治话语中,如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指出“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26)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3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总而言之,通过40年的改革历程,中国国有企业已明显具有私法化的行政组织所具有的组织与功能二元分离特征。国有企业的组织形式已经完成私法化转变,但它承担国家任务的功能性质并未改变,只是被时代赋予新的内涵,由生产与社会保障任务发展为公共服务与经济调控。当下国有企业既不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组织的一部分,也很难讲已经成为完全的市场主体。正因如此,国有企业的法律属性及其对应的调控模式亟待进一步探讨。
四、新双重性理论的提出及其制度构建
新双重性理论延续了当下学说认为国有企业具有双重属性的思路,但将双重属性重构为功能属性与组织属性。其中,功能上的公共性为核心属性,即“第一性”。组织上的私法人属性则为辅助属性或称工具属性,即“第二性”。两种属性背后的法规范体系是相互矛盾的,因而又需要“双轨制”设计来寻找平衡以缓解甚至消弭冲突。
(一)新双重性理论
1.作为第一性的功能属性
行政组织私法化理论框架中形成的第一组共识是,私法化的行政组织本质上属于国家。这一论断从国有企业定义中的“国家控制力”标准可以得证。我国通说认为国有企业包括国家或政府可以根据资本联系,对其实施控制或控制性影响的企业(27)参见史际春:《国有企业法论》,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7年,第13页。,此种“国家控制力”标准甚至可称为一种世界现象。欧盟发布的《成员国、公营企业与特定企业间财务关系透明性指令》第2条规定,“公营企业”(öffentliches Unternehmen)是指任何行政部门基于所有权、财政参与、章程或其他规范组织活动的规定对其直接或间接行使支配性影响的企业。(28)参见Transparenzrichtlinie, RL 2006/111/EG.德国在其《联邦预算法》第65条中规定,联邦政府可以新设或参与已存在的私法组织形式的企业,但必须对该企业拥有适当的影响力,尤其在监督委员会或其他监督机关中,且需在章程中载明。美国商务部亦将处于政府控制之下的企业认定为国有企业,属于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第1.1(a)(1)条下的“公共机构”。(29)参见WTO Panel Report,United States-Definitive Anti-Dumping and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Certain Products from China,WT/DS379/R, adopted 22 October 2010, pp.40-41.
国家的核心目标从来不是营利,而是完成公共任务并实现公共利益。国家的公共性或称公益性在传统上主要由行政活动来实现。传统行政活动中,公法性行政组织承担公共任务,二者的属性相同,而行政组织私法化打破了这一局面。行政组织私法化以及公共任务维持使得组织属性与功能属性的分割成为现实,私法组织也能够且必须承担公共任务。根据我国《宪法》第7条之规定,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发挥其对于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国有企业无疑是国家完成此项任务的重要组织工具。然而,“主导力量”属于不确定性法律概念,它所具有的高度抽象性与概括性使得其在实践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与内容。
具体而言,不同类型的国企所承担的公共任务有所不同。我国现有国企包含“国有公共企业”与“国有商事企业”两类。“国有公共企业”是指承担公共任务的企业。现有政策分类下,它主要包含公益类国企与部分商业类国企。(30)参见《国资委、财政部与发展改革委关于国有企业功能界定与分类的指导意见》,2015年12月7日发布。前者的公共企业属性不存在争议,甚至有学者认为它是实质意义上的“行政机关”。(31)参见朱芒:《公共企事业单位应如何信息公开》,《中国法学》2013年第2期。后者则是指处于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且主要承担重大专项任务,以及自然垄断行业的商业类国企,其在政策上被划归为商业类国企,但本质上仍在履行公共任务。
“国有商事企业”是指与私营企业相同的一般性商事公司,以营利性为主,并不承担公共任务。现有政策文件中,“以国有资产增值保值”为主要目标的商业类国企是否属于国有商事企业需要进一步讨论。此种商业类国企又可区分为“非纯营利性国企”与“纯营利性国企”。对于非纯营利性国企而言,其仍承担着其他发挥国有经济主导力量的任务。比如,中粮集团与中汽集团便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振兴汽车产业的重要任务。由于《宪法》第7条中的国家任务内涵较为宽泛,此种商业类国企大部分都属于上述情形,即仍然承担公共任务。
“纯营利性国企”则是指单纯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国企。经过1995年至2006年的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大批中小国有企业退出市场,“纯营利性国企”已经十分少见,目前多见于房地产行业,也包括少量食品百货类企业。对于此类国企,需要考虑的问题是:追求利润本身是否也属于公共任务?如果不是,那么纯营利性国企的存在有无正当性基础?关于第一个问题,目前学界所达成的普遍共识是:仅仅追求利润本身不属于公共任务,除非所取得的利润用于公共任务的完成,且必须保证每位公民都有可能因此任务的完成而获益。(32)参见Wolfram Cremer, “Gewinnstreben als öffentliche Unternehmen legitierender Zweck: Die Antwort des Grundgesetzes,”DÖV 2003, S.929 f.在现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下,仅五类中央企业需要上缴利润,所占总利润比例仅为0-25%,且上缴利润的绝大部分又“自体循环”后用于国企的自身发展。(33)参见《财政部关于进一步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的通知》(财企[2014]59号),2014年4月17日发布。这便涉及第二个问题,不承担公共任务的国企是否具有存在的正当性基础。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诚如前文所述,公共任务的履行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既然国企的本质属于国家,这一准则同样适用于国企。 所以,“纯营利性国企”并不具备正当性基础,国家应当从中逐渐退出而让位于市场力量。
2.作为第二性的组织属性
国有企业本身是国家完成公共任务的一种私法组织工具,这一认知背后蕴含着行政组织法研究视角之变迁。传统观念中,人们习惯将行政组织视为国家行政权力存在与实施的表现形式。此即行政组织法的制度性视角,将行政组织视为国家权力的制度表现。此种视角之下,国有企业几乎不可能会被视作行政组织范畴内的研究对象。反而基于剥离行政权对企业的过度干预,即所谓政企分开之考虑,国有企业被认为应当尽可能摆脱行政组织属性,而充分突显企业的自主性。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行政组织被认为还应当从工具性的角度予以研究,即行政组织仅为国家履行公共任务与实现公共福祉之组织工具。如此一来,无论是公法组织还是私法组织,只要利于国家公共任务之履行,便可作为组织工具来使用。
当国家利用国有企业这一私法组织工具完成公共任务时,它所采取的是亲自参与经济生活的方式,此种打破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传统角色的新方式被称为“柔性干预”。诚如德国学者君特·平特(Günter Püttner)指出的那样,国有企业是一种“天才的发明”,它将国家任务的履行与企业的经营行为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国家可以有效地对经济活动进行柔性干预。(34)参见Stefan Storr, Der Staat als Unternehmer,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1, S.57.“柔性干预”包括身份的柔性化与手段的柔性化。身份的柔性化是指,国家不再趾高气扬地运用高权方式来干预经济活动,而是屈尊穿上“私法的袍服”,以竞争者的身份出现在市场中。它首先体现为具体组织样态的变化,譬如公司法人形式相较于科层制的政府组织而言,更能够发挥高效、灵活、融资渠道广等优势,以适应瞬息万变的经济生活之需求。其次,国家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国家不再仅仅扮演监管者角色,而是“亲自下场”参与市场竞争。这一过程中,作为企业的国家与竞争者、消费者均处于平等地位。手段的柔性化则是指,国家不再直接决定结果,而是通过影响决定的过程干预经济生活。具体而言,作为企业的国家不再像在计划经济下那样直接决定生产种类与数量、交易价格等,也不再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行政手段直接进行干预,而是通过亲自参加经营活动间接性地影响市场供需。在这种模式下,调控对象往往作为竞争者、合作方或是消费者身份而出现,整个过程通常以交易方式完成。
(二)政府与市场维度下的双轨制
行政组织私法化框架所形成的第二组共识是,私法化的行政组织应当在公法与私法中寻求平衡。具体到国有企业而言,现有法律调控机制实际上已经呈现出公私交融的特征,其可被提炼为“双轨制”。但是,现行“双轨制”尚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1. 政府维度下的双轨制
目前涉及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的法律调控在形式上包含以下两组:第一组以《公司法》为中心,主要遵循公司自治原则。第二组则以《企业国有资产法》为龙头,《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为基础,以国务院国资委制定公布的21个行政规章和115个规范性文件为主要内容,包括各省市国资委起草制定的1 800多件地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35)参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有关问题的通知》(国资发法规〔2008〕194号),2008年11月12日发布。该体系并非以公司自治为核心,而是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保护国有资产安全为主要目标。
上述两组法规范中实质蕴含着两条调控轨道。轨道一不仅适用于国企,也适用于私营企业,因而可称之为“一般性私法框架”。在这一轨道中,国企原则上应当与私营企业一样,以保障公司自治为核心,注重对利润的追求。但是,仅仅依赖轨道一可能会导致对国有企业公益性关照不足,这是因为资合公司从来就不是为国有企业量身定制的形式,它很有可能会导致公司与国家间的关系疏远,从而使得公益性最终被资本逐利性所侵蚀。在一定程度上,轨道二是对轨道一进行功能性弥补的公法性轨道,其侧重于保障国有企业的公共任务之实现。譬如《企业国有资产法》第36条规定,国家出资企业投资应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并按照国家规定进行可行性研究。由于轨道二排除了私营企业而适用于国有企业,因此也可被称为“特殊性公法规范”。
当下政府被认为对国企干预过多,很大程度上是缘于轨道二中的行政手段运用过多所致。为了防止国企的公益性被营利性所侵蚀,轨道二中设计了许多直接运用行政权干预企业经营的条款。首先,国资委下发的各种文件中,不乏直接干预国企具体治理内容者。比如,直接干预企业的高管薪酬、职工福利、培训安排、财务信息化等内容的例子并不鲜见。(36)参见邓峰:《国资委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http://ah.ifeng.com/news/wangluo/detail_2015_09/24/4385056_0.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12月11日。其次,轨道二中包含不少行政审批性条款。比如《企业国有资产法》第29条、第34条与第35条。再如国有产权转让领域繁多的行政规章与规范性文件之规定。如此一来,国企难免被行政权牢牢捆住手脚。
要突破上述困境便必须认识到,保障国有企业公益性并非仅能通过行政手段得以实现。轨道二中大量使用行政权的目的无非在于确保国家对国企的控制力,即国家之于国企的“影响义务”。(37)参见Günter Püttner, “Die Einwirkungspflicht-Zur Problematik öffentlicher Einrichtung in Privatrechtsform,”DVBI 1975, S.353 ff.但影响义务并非只能通过行政手段实现,而以过度干预国企经营自主性为代价保障其公益性之实现则更不可取。反观当下中国现实,国有企业刚刚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身,计划经济的烙印尚未完全祛除。因此,行政手段的运用应当尽量缩减与避免,以真正发挥公司法人形式所具有的高效、灵活、融资能力强、盈利性强等优势。2017年《国务院国资委以管资本为主推进职能转变方案》中一口气精简了43项国资监管事项,正是体现改革实践弱化行政干预的趋势。
可能的出路在于:最大限度地借助于轨道一实现国家对国企的影响义务。具体实现途径主要包括人事管理与章程参与。首先,人事管理是指国资委通过派往国有企业的人员贯彻自身意志,保证国有企业公益性不被营利性侵蚀。基于董事会独立原则,人事管理的可能性集中于被委派的股东和监事上。在股东层面上,《企业国有资产法》第13条规定,被委派股东应当按照委派机构的指示提出提案、发表意见、行使表决权,并将其履职状况及时报告委派机构。在监事层面上,《企业国有资产法》第19条规定了监事会的监督义务。《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第9、10条进一步规定,监事会每次对企业进行检查结束后,应当及时做出检查报告,并将报告报送政府有关部门。其次,应当充分利用公司章程的形成空间。在我国,公司章程多为《公司法》相关规定的简单重复,其价值尚未充分发挥。以上海国有企业为例,为更好地贯彻建设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的国家战略,上海国资委引导国有企业将增强创新写入公司章程中,从而实现国家战略与公司战略的统一。(38)参见金琳:《上海市国资委积极鼓励国企创新》,《上海国资》2016年第6期。
总而言之,国资委的“红头文件”式管理应尽量避免与审批制管理会导致影响义务与公司自治间的失衡,尽量在私法框架内寻求国有企业双重性的平衡方为解决之道。当仅借助私法框架确实无法达成国有企业的公共任务时,国家应当更换完成此项任务的组织形式,而非不惜诉诸更具强度的行政手段予以简单粗暴性处理。
2. 市场维度下的双轨制
以市场维度观之,国有企业与其他竞争者之间的关系也处于双轨制法律调控体系之下,一为竞争法,另一为产业法。竞争法轨道是指,国企与私营企业同样受到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及其配套性文件的调控,主要以保障竞争者的平等地位、推进竞争自由为核心原则。产业法轨道由公用事业领域的各单行法与行政规定构成。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以下简称《电力法》)对电力供应、定价等内容做出特殊规定,《石油价格管理办法》限制我国成品油的最高指导价。在经济转型阶段,受计划经济时期的影响,我国产业法以“行政主导”为根本特征。(39)参见叶卫平:《产业结构调整的反垄断法思考》,《法商研究》2010年第6期。如此一来,产业法不但未能促进竞争,为了实现特定公益目标甚至会促成国有企业垄断局面的形成。
竞争法与产业法分别维护的核心价值“竞争”与“垄断”无疑截然相反。那么国有企业是否能够在二者之间寻求平衡呢?换言之,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究竟是否可以享有垄断地位。既然私营企业需遵循自由竞争原则,国有企业得以例外的正当性基础又是为何?为此,首先应当厘清的是,国有企业参与竞争的本质仍属于国家对于私人竞争领域的干预。竞争活动一直以来被认为属于私人领域,新古典自由主义学说的代表人物哈耶克早就将竞争定义为一种“自我发现的过程”,并不信任国家干预。(40)参见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哈耶克文选》,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61-164页。国家以企业形式参与到市场竞争中,仍然是对于私人领域的干预,它不同于私人之间的竞争,因而需要具备一定的正当性基础。此种正当性基础是,国家竞争行为应以完成公共任务为目标。这是因为,权限与自由是国家与社会区分之表现。权限意味着受限,国家只能从事与完成国家任务、促进公益相关的活动。同时,按照比例原则的要求,国家活动还需对公共任务的完成具有适合性与必要性。(41)参见陈征:《国家从事经济活动的宪法界限——以私营企业家的基本权利为视角》,《中国法学》2011年第1期。
无论是垄断性国企还是竞争性国企,都必须符合上述前提。换言之,垄断与竞争都只是国有企业的行为所遵循的价值,其均应服务于企业的公益性功能。就垄断性国企而言,根据《反垄断法》第7条之规定,国企垄断主要集中于公用事业领域。这一领域对管线网络之依赖使其具有投资额巨大、周期长、沉没成本高等特点,国有企业的进入有利于抑制市场失灵,保持价格稳定与产能充足,满足人民生活与生产的基本需要。但是,当国企的垄断地位不再对于其公共任务的完成具有适合性与必要性时,其垄断地位便失去了正当性基础。譬如,在电信行业中,由于互联网与通信技术的颠覆性发展,对网络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大大减弱。国有垄断模式带来的优势已不再明显。正因如此,相关行业内的国家垄断也呈现出因市场竞争滑动的趋势。放开虚拟运营商牌照、引入民资、全面实行市场调节价等改革举措均体现了上述趋势。
即便是竞争性国企,公共任务的完成仍然是其首要目标。与垄断性国企通过国有垄断实现其公益性不同,竞争性国企主要是利用市场竞争机制完成公共任务。就行为机制而言,竞争性国企应当与私营企业在竞争中居于平等地位。诚如国际上普遍推行的“竞争中立”政策便要求,政府的商业活动不得因其公共部门所有权地位而享受私营部门竞争者所不能享有的竞争优势。实践中,国有企业享有的税收减免、融资优惠、交叉补贴等诸多优势无疑违反了平等竞争原则,应当逐渐予以革除。就功能归属而言,竞争性国企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根本目标仍在于公共任务之完成。正因如此,忧虑“竞争中立”政策可能会促使国有企业成为完全“商主体”,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并导致国有经济控制力的逐渐丧失大可不必。(42)参见胡改蓉:《竞争中立对我国国有企业的影响及法制应对》,《法律科学》2014年第6期。竞争机制有助于激发国有企业活力,提高自身经营能力,国企自身实力的壮大也利于其公共任务之完成。若在某一特定领域,社会资本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那么也就意味着国家并无太大必要进入该领域,相关任务完全可以由私营企业完成。因此,竞争机制的引入不仅有利于国有经济的优化布局与结构调整,也是为国家参与竞争活动设定了界限。
五、结 语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实践倒逼下的行政组织私法化进程。诞生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有企业徒有“企业”之名,实为几无自主性的行政机关附属物。基于经济体制转轨历史背景下向市场经济“转身”之实践需求,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使其在组织形式上彻底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私法人。又因其所具有的战略功能与重要地位之特殊性,中国国有企业不可能等同于一般性商事公司。国有企业在功能上需承担的公共任务,与其组织上的私法人属性产生了分离,这正是导致国有企业双重属性困境的根源之所在。
迥异于私法性视角下诞生的传统学理,立基于公法性视角的行政组织私法化框架为国有企业组织属性与功能性质之分离提供了理论基础。国有企业是“穿上私法袍服”的国家,是国家“亲自下场”从事经济活动的私法组织工具。所以,国有企业既在功能意义上具有国家属性,又在组织意义上具有私法人属性。两种属性之分离可能会导致国有企业的法律调控产生冲突。一方面,国有企业在组织形式上属于私法人,其行为规范应在私法框架内进行。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代表国家承担公共任务,因而必须受到公法调控,以保证公共任务顺利实现。此种冲突只能藉由具体法律制度中公私法交融的“双轨制”设计予以消弭,这与一般性商事公司所处的单一私法性轨道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国有企业固然可称为一种“天才的发明”,如何在充分发挥私法人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基础上,避免国有企业的公益性被私法人所天然具有的逐利性腐蚀,从而妥当处理二者的关系,是这场对中国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改革能否取得理想成效的关键。为此,国有企业战略功能的顺利实现不仅需要决策者的勇气与决心,更加需要公有制基础上运行市场经济的精密法律设计与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