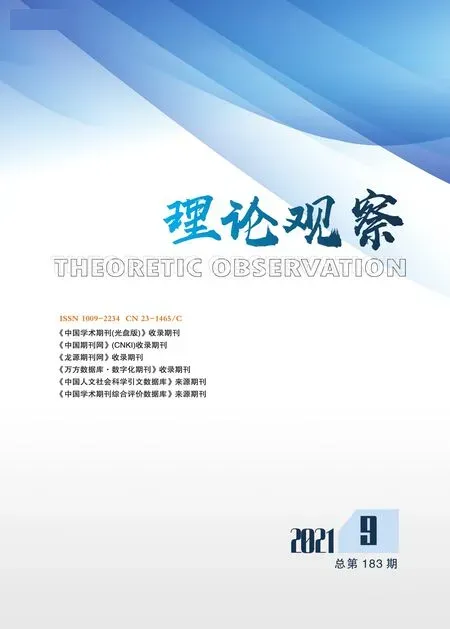继承与发展:治国理政具体方针下的文化底蕴探析
2021-12-27宋魏旻
赵 壮,宋魏旻
(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通 22600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1〕优秀传统文化作用于新时代的实践空间主要集中在国家一系列的大政方针中。通过发掘国家大政方针中的优秀传统因子,不仅可以明确优秀传统文化自身所蕴含的深厚价值,更可以为进一步深化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优秀传统文化实践价值的发掘证明了中华民族自身的博大精深,优秀传统文化实践价值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应用则为新时代国家的日益富强繁荣提供了强大助力。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原始实践价值以及在新时代的伟大实践中所产生的现实效能,最终都将为文化自信的生成助力。因此,将从以下三方面展开优秀传统文化实践价值的探析。
一、“德法兼用”传统对“以德、以法治国”方针的影响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将“依法治国”“以德治国”作为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方针,坚持发挥“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的治理效能。作为中国重大决策方针,“以法治国”“以德治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上至殷商先秦、下至近代,都可以在传统思想和实践活动中发现“法治”“德治”的传统。
(一)“引礼入法”传统“德法兼用”的重要模式
“引礼入法”作为中国“德法兼用”传统治理模式的一个重要板块,重在提倡“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广泛效能。有关“法”的解释,以韩非子为优,其言:“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韩非子·定法》)以韩非子的看法,“法”是由官府用文字公布出来的,以尚善罚恶为基本原则的律令,是官员驾驭百姓的基本依据。有关“法”的准确解释以法家学派为主,但是“法”的应用应该可以追溯到上古圣王。《左传·昭公六年》记:“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国语·鲁语上》载:“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史记·五帝本纪》则谓:黄帝命皋陶制刑法。由此可见,“法”在中华文化有着较为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法”治传统。将“法”与“礼”结合并谈则是韩非子的老师:荀子,“隆礼重法”便是其所推崇的国家宰制方略。在荀子的理论视野下,“礼”是从区分与调节不同人的利欲关系中产生的,并有双重的含义。当“礼”与“义”同行时,“礼”更多地是指涉道德,有着深厚的“德”治色彩;当“礼”与“法”并称时,更多地是指制度,通过制定一系列的条文和规范,约束人的行为和调节人的欲望。〔2〕荀子所表述的“礼”在一定程度上与“德”相和,“德”意义上倾向于抽象的概念,“礼”则是“德”抽象概念的具体展开。“礼”与“德”相和,“隆礼重法、则国有常”中的“法”自然也带有一种“德”的色彩。代表了荀子的思想倾向,期望“法”可以引进一定的道德伦理,从而完善自身。秦朝作为严苛峻法的代表性政府,其自身因为过于提倡刑法,使得百姓人人畏法、厌法,更不堪法律所带来的身体上的折磨。所以,秦灭以后汉朝主要管理阶层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在国家层面选择将“法”放置于隐性状态,转而大力提倡“儒家”,进而形成“儒表法里”的管理态势。儒家所提倡的“德”“礼”,相比与单纯的“法”比较温和,易使百姓接受。但是,在表面施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方针下,整体国家的各级行政人员多是以“酷吏”“循吏”为主,有着深厚“法治”倾向。因为,秦时留下的管理学习传统,多数的官员对国家法律条文都有过系统的学习。在这样一种“儒法并用”的治理模式下,汉朝逐渐走向兴盛,并且为后世王朝稳定社会、加强管理,提供了极佳的借鉴。
在新时代主张“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政策方针下,传统“引礼入法”的治理模式有很多地方值得借鉴。一方面,加强法律条文治理效力的实现。传统“引礼入法”的治理模式局限于用人方式的简单化,为能充分有效发挥人在治理中的关键作用。因此,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国家从制定、执行、监察等多方面,系统组织人员,发挥各群体主体力量,形成制定、执行、监察的完备体系。即使人成为了法律条文具体效能的受益人,也使人成为法律条文具体效能的维护者。一方面,以道德伦理溶解法律条文治理效力的单一性。传统“引礼入法”在一定程度上,便是将道德伦理引入法律体系中,以补充法律条文的单一化、固定化的缺陷。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不仅再次提出了“德治”,更是将“以德治国”作为与“依法治国”互为补充的基本国策之一。在“以德治国”的引领下,新时代国家治理将“润人心”作为重要工作目标,力争培养广大人民的自觉意识,使得广大人民养成内有觉解、外有实行的深层次自觉。
(二)“德主刑辅”传统“德法兼用”的重要变相
“德主刑辅”是中国传统“德法兼用”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强调“德”在国家治理中的显著作用。在有关国家治理的古代文献中,“德”较早出现于《尚书》,“克明德慎罚”“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此时“德”是在“天”“鬼神”的文化氛围中被提出的,大意主要是指:上天公正无私、绝对公平,唯有对那些德性高尚、品智端正的人才会欣赏。表述中虽未明确提及以“德”作为治理部落或邦国的方法,但是身处“天”的色彩较为浓厚的殷周时代,将“德”与“天”相连接,必然可以在现实中引导民众养成“尚德”的观念,从而发挥“德”的现实效能。先秦时代,儒家创始人孔子将“德”与“政”结合,明确了“德主刑辅”的治理观。孔子言:“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民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表述中,孔子提倡“德政”“德治”,认为施行“德政”可以实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的国家治理状态,并且在这样的治理中民众可以做到德化于内,达到“有耻且格”的认知水平和执行程度。孔子强调“德”政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漠视“刑”的作用。由此可见,“德主刑辅”的理念在孔子的思想中是有一定体现的。发展至汉朝,德治传统的确立有赖于儒学大师董仲舒,在其著作《春秋公羊学》中明确提出了“三纲五常”之说,将“德”治传统以“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以及仁、义、礼、智、信的方式具体展现出来,作为约束百姓行为的规范。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汉朝各级管理系统有着“刑副”、甚至“刑主”的治理倾向。“西汉中期以前特别是在西汉前期,秦代尚法而治的社会风气仍给当时的社会以较大的影响,而且此时儒家的思想学说虽逐渐得到上层统治者的青睐,但在实际政治中儒家学派没有能够、也没有能力马上占据国家立法和司法的阵地,因此在社会中‘尚刑名法术之学’的‘文吏’仍在实际上操纵着司法统治大权。”〔3〕汉朝的一系列举措,为后世国家发展奠定了一条“德主刑辅”的治理路径。唐代将“德礼为政教之主,刑罚为政教之用”作为治国方略,便是对汉代“德主刑辅”之治理模式的进一步发展。“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是“德法兼用”的一种变相,重在突出“德治”在历朝历代的国家治理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德治”作为一种优秀传统理政方式,也可以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焕发新的生机。
“以德治国”是对“依法治国”方针的补充,“德治”下的各种举措有助于完成社会群众由外而内的自身转变。传统“德主刑辅”的德治理念对新时代治国方针的制定提供丰厚的理念借鉴。首先,治理社会应借助“法治”的力量。传统以“德治”为主的治理体系中,“德治”始终占据着主流,并且发挥了极大的治理作用。但是,后来随着社会形态的演进、社会要素的改变,“德治”难以维系,必须求助于“法治”。通过借助“法治”“德治”有了明确的、书面化、强制性力量的参与。单一的“德治”力量太过单薄,倾向于依靠个人力量的自我约束以及群体力量的非强制性制约。自我约束以及非强制性制约并不能在人口众多、生产资料极度丰富的社会中发挥普遍效应,或者说难以得到民众的广泛性遵循。所以只能将约束与制约诉诸“法治”,从而通过一种强制力使得民众日常行为得到积极管理。另一方面,“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4〕法律与道德应该双向联动,形成一种互相渗透的发展态势。只有如此,“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治理模式才能逐渐落实和发展。“法治”与“德治”是对社会治理、公民管理的多维途径,二者相互联合,会形成一股全方位的治理合力。既可以从内心出发,使得广大群众在耳濡目染和行为实践中,建设自身内在约束观念,也可以从外在出发,通过法律条文强制力的规制与约束,帮助群众建立底线思维,避免违法行为的出现。总之,“德治”与“法治”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在古代社会发挥重要作用,也可以在现代社会焕发生机。“德治”与“法治”在现代社会通过“依德治国”“依法治国”的新形式展现出来,不仅意味着本身所具有巨大价值,同时代表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紧跟社会的发展走向。
二、“选贤与能”传统对“全方位选拔人才”政策的影响
“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5〕人才的多寡贤良与否,更影响着国家整体治理效能的具体展开。强调人才的重要性不仅是新时代的重要课题,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才也始终被历代思想家、政治家所关注。因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中,中国形成了一系列选人、育人、用人的科学理念和系统制度。而新时代作为中华历史发展的最新阶段,不仅因历史惯性承接自身历史文化的滋养,同时也会根据自身需要主动借鉴传统中有益于当下的理念和制度。
(一)“选贤与能”理念的出场与发展
“选贤与能”理念的出场与发展。“选贤与能”的思想萌芽起源较早,可追述至上古先王的“禅让制”。“选贤与能”理念的正式出场则是在《礼记·礼运》中,书中写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此文中所表述,是将“选贤与能”的人才选拔方式放置于“天下为公”“此为大同”的社会理想之中,尚未进入维护君主的窠臼。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君主权威的加强,先秦诸子在理论制定上多数将君主接纳、国家安定作为自身的首要考虑对象。值得关注的是,先秦诸子有关“选贤与能”的许多看法是颇具进步性的。首先,破除世袭垄断。《墨子·尚贤上》中表述道:“故古者先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墨子的表述意在打破旧的选官、用官原则,消除亲属贵贱的世袭之风,强调选官、用官应该以品性与能力为主。并且墨子还把“选贤与能”的范围扩展到了“农与工肆之间”,从而破除了阶级与血缘的界限。墨子之外,孟子强调人才选拔应该不拘一格,其言:“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孟子·告子下》)其次,选官、用官方式的优化。孟子言:“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又见贤,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又见不可,然后去之;”(《孟子·梁惠王下》)社会化的选官方式将“贤”与“能”的选举放到群体性的社会中,由社会中的多数人或者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人民,来作为“用”还是“去”的判断标椎。此时“贤”与“能”的判断是靠他们自身所能产生的社会效应决定的。用官方式的优化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要 “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孟子·公孙丑上》)使他们皆可在一定的位置上实现自身的价值;二是要善于向臣下学习。作为国家的最高管理者,始终与臣下联动,交互学习,让臣下在受尊重的环境下开展工作。“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同上)最后,考核意识的增强。考核决定着官员的去用以及录用后的升降问题,应该定期开展。《管子》有言:“岁一言者,君也;时省者,相也;月查者,官也。”针对职位不同,制定相应的省察时间。荀子则建议分别开展小考与大考,其言:“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然后中和察断以辅之,政之隆也;然后进退诛赏之,政之终也。故一年与之始,三年与之终。”(《荀子·致士》)
新时代的人才观念继承了传统重贤、重能的基本用人取向,并结合民情、国情、世情所需,相应作出了有效改进。首先,新时代对贤能的关注更加细化。传统社会中,对贤能进行认定时,多是关注人本身是否具有贤德和才能,很少论及贤德与才能的具体所指。在新时代,对贤德的认定倾向于从私德与大德两方面,私德是指个人德性的健全与否,大德则是指是否爱党、爱国、爱人民。私德是个人道德提升的本来拥有物,大德则是选拔干部、调整职位的重要依据。才能的认定则在注重传统才能观的同时,将创新型人才与科技型人才作为重要人才认定标准。习近平总书记说:“更好地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努力建设一支能够站在世界科技前沿、勇于开拓创新的高素质人才队伍。”〔6〕其次,在传统选才、用才的基础上,增添了育才的新主张。新时代各个领域积极发展、争创一流,急需一批高素质人才与之相联动。因此,在选才、用才基础上,应加大育人力度、明确育人方向,“营造良好创新环境,加快形成有利于人才成长的培养机制,”〔7〕从而为时代发展提供丰富的人才资源。最后,人才考核的精准化、制度化、人民化。人才考核精准化是针对不同领域人才的合理性设定,通过精准化考核可以有效激发人才工作的积极性和工作方式的创新性,为人才升降提供更准确的具体依据。人才考核的制度化保障了人才评价机制、人才激励机制、人才升降机制的长效性,使得顶层管理系统与基层考核组织有机联动,为对人才的溯源性考察提供现实可能。“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根本宗旨,人才考核的人民化符合我党一贯的价值倾向。因此,2020年10月,中组部下发《关于改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的通知》,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判领导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绩的重要指标。
(二)“选贤与能”制度的出现与发展
“选贤与能”制度的出现与发展。从原始社会的禅让制,到商周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到两汉时期的察举与征辟制度,再到后来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中国古代社会虽是封建王权专制,但对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却非常重视。上古先王的禅让制有着朴素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部落首领的选举基本是以个人贤能以及部落成员对其的评价作为是否选用的依据。随着“家天下”时代的到来,传统具有朴素民主倾向的禅让制被世卿世禄制所取代。世卿世禄制下的人才选拔,多局限于贵族世家,多数的技艺也被上层阶级垄断,使得广大民众难以冲破自身阶级局限。即便部分民众可以得到一官半职,施展自身的抱负,但也是以依附于贵族为代价,缺乏自身独立性。诸子时代打破贵族的技艺垄断,使得一系列的知识、技艺,在广大民众中得到了一定的普及。随着技艺与知识的平民化,人才的发展出现了繁荣态势,战国时代的九流十家便是鲜明例证。打破技艺垄断的历史性行为具有极大的进步性。不仅使传统人才形成方式出现了巨大转变,由单一的官学发展为多途径的官私并办,也为后世人才资源的快速发展提供可能性。因此,两汉时期的察举与征辟得以兴起。察举制是自下而上的人才荐举制度,通过地方官长发掘治下有才之士,然后上报朝廷。人才推举后,如能通过最高管理系统的认定,推荐者有功;若推举不当,推荐者也难辞其责。在两汉时期,察举制的主要考核准有“孝廉、茂才、察廉、光禄”四科,另外还预设了“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至孝、有道、敦厚、尤异、制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等特殊类科目。〔8〕征辟制是自上而下的选拔方式,汉武帝曾下诏通过“德行高妙、志节清白”“学通行修、经中博士”“明达法令、足以决疑”“刚毅多略、遭事不惑”等科目开展贤士征辟。两汉时期对人才的认定标准得到了极大的扩充,从宏观到具体、从普通到特殊,涵盖了各领域人才。但是,制度的优化依然无法超越其本身所在的具体历史,察举与征辟最终还是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徇私枉法的工具。发展至魏晋,曹操设立“九品中正制度”,专门设立名为“中正”的官员,让其在各郡县专门从事人才选拔、品评的工作。与此相应,根据人才的贤能程度分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尽管,曹魏政权使人专司此事,并详细划分人才品级,可终究还是未能摆脱“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封建王朝之弊病。隋唐时期门阀士族走向衰落,“大批中下层士子,由科举入仕途,参与和掌握各级政权,从而在现实秩序中突破了门阀世胄的垄断。”〔9〕相比之前的人才选拔制度,“隋所创之科举制,至少具有其他选才制度难以企及的三大优点,即客观性强、公平性好、效率性高。具体而言,“一切以程文高下定去留”,使人才选拔标准具有较强的客观性;程式化、制度化的操作流程,极大地确保了人才选拔的公平性;以纸笔为测验媒介与载体的考核方式,则赋予了科举选才极高的效率性。”〔10〕如果说隋唐科举制之前的选拔制度是依据荐举者的考评表述,隋唐后的选拔制度,则更倾向于以本人所呈考卷为判断依据,前后的转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称之为主观判断向着客观判断的转型。
上述的选拔制度各有利弊,但总的来说,随着历史的发展,主观判断或者客观判断所带来的弊端正在逐渐消解。发展至新时代,各类选拔制度的弊端被溶解剔除,成为了新时代“人才全面选拔方式”的生成基础。首先,选拔方式的多样结合。国家公务员选拔方式是不同领域选拔方式的一个缩影,不仅继承传统选拔方式的优势,并且使选拔方式更加多样化。“以考试录用和选调为主的“入门”性选拔方式,以调任和“借调”为主的交流性选拔方式,以竞争上岗、公开遴选、公开选拔为主的竞争性选拔方式。”〔11〕其次,人才分类更加精细化。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兴起,许多新兴领域相继涌现。传统简单以贤能以及特殊科目为分类标准的人才认证体系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因此,新时代下的人才选拔一方面仍然坚持以贤能为基本用人导向,一方面结合社会要素变化、细化人才分类,在以贤能为基础的前提下,发掘了更多时代新兴人才,如人力资源规划师、网络媒体高级编辑、职业规划师、动漫设计工程师等等。最后,人才选拔更加数据化、信息化。数据化、信息化的人才选拔方式是对传统人才选拔方式的历史性超越,使得人才选拔在以为人基础的同时,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实现了被选举者与选举者的多维度互动。
三、“协和万邦”传统对“新型”外交方式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发展方式的推进,各国之间交流合作日益频繁,国家外交方式的重要性也更加显著。审视中国外交方式的价值取向与具体措施,中国外交方式对“协和万邦”传统是有一定继承和发展的。不仅继承了“协和万邦”传统的价值取向和具体举措,也在古代外交传统基础上形成了许多具有时代性、世界性的新成果。
(一)“协和万邦”传统的具体所指
“协和万邦”传统的具体所指。《尚书·尧典》载:“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大意是指,举荐德才兼备之人为官,使得广大人民亲密团结起来,并表彰百官中治理有效者。百官尽责,诸侯国之间关系协调、和谐,天下自然也和谐、和睦、安定。上述表述中,“协和万邦”是建立在“百姓”“九族”“万邦”之上的一种状态,代表着对安定、团结、和谐、和睦的社会氛围的渴望。从天下层面,“和”呈现出了强烈的包容性和有序性。晏子则另辟蹊径,对“和”状态的具体所指做了生动的叙述。《左转·昭公·二十年》记载:“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晏子以日常烹饪为喻,将“和”清楚的阐述出来。在晏子看来,“和”是指具备多样性,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东西,但同时又应该“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使各种事物以一种相对和谐、协调的状态容纳在一起。“和”本身指一种和谐稳定的状态,但是和谐稳定状态的生成是建立于多样事物的共存。唯有多样事物共存才有可能实现这样一种状态,单一事物存在于某个环境中,只能称曰:“同”。因此,不论是以万国为基础的“协和万邦”,还是以诸多食材佐料为基础的烹饪之道,二者都共同将“和”内涵建立在了多样性上。多样性是“和”状态实现的前提,真正地实现还需百官善治、宰夫善烹。若仅存在“多样性”,将极有可能造成“诸侯相征伐”的乱局。
相比中国传统中对“和”的简单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新时代应运而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保持了传统中对“和”状态的追求,同时又结合全球化发展背景的需要,在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新型预设。首先,对“和”理念坚定追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议中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12〕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表述中,“和睦”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联系后,所应该达成的状态。除了坚持强调“和睦”外,“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基础还在于“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与“协和万邦”传统有着天然的相似点,都将达成“和”的状态着眼于多样化事物的共同存在。但是,相较于传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着眼点更加具体、更加可感。因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建立是在打破时间、空间壁垒的基础上,各个民族、国家也都在壁垒消失后展现出自身存在。其次,在关系“和睦”基础上,将“万邦”的协和发展推向纵深。万邦共存的世界不仅要和睦、和谐,还应“建设一个远离恐惧、普遍安全的世界”,“建设一个远离贫困、共同繁荣的世界”,“建设一个远离封闭、开放包容的世界”,“建设一个山清水秀、清洁美丽的世界”。〔13〕在万邦共存的世界中,形成“和谐”的平稳状态只是初步发展,为了满足人类的普遍需要,“安全”“繁荣”“包容”“美丽”应该成为“和谐”之后的新追求。对新型状态的追求是一种超越,代表了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二)“协和万邦”传统的具体举措
“协和万邦”传统的具体举措。首先应“克明俊德”。在“协和万邦”的原文表述中,“克明俊德”是最终形成“协和万邦”状态的第一步,希望通过选举德才兼备之人,加强国家治理,进而使得天下和睦、和谐。中国传统思想中,“天下”与“德”关系向来非常紧密,“德”更是在传统社会中被视为与外邦交流的原则。孔子有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中庸》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发展逻辑。“修文德”的表述是从国家层面展开,欲通过国家的整体转变实现与其他国家的良好关系。“修身”的表述则是从个人层面出发,但是其最终关怀确实指向“平天下”。两者共同将目标放置于自身,都一直认为加强自身建设是实现与他国良好关系的基础。同时,“修文德”“修身”的主题是围绕“仁”“礼”“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观念展开。修仁意味着“泛爱众”,是展开邦交的基础;修礼意味着规则,是有效进行邦交活动的前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作为指导自身行为的原则和化解国与国、民族与民族、宗教与宗教、文明与文明间冲突对抗的原则;“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原则则可以帮助不发达、落后地区和国家,以求共立共达。〔14〕其次,“先义后利”的价值取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是对个人价值追求的描述,以“君子”与“小人”为例,体现了对“义”的推崇,对“利”的贬斥。在个人修身基础上,孟子又将之扩而广之,延伸至一国。《孟子·梁惠王上》载:“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已。”在义利关系中,孟子将“义”放在了首位,认为求“仁义”治理国家的重要方法。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孟子还是对“利”予以肯定,认为应该“制民之产”,满足民众的普遍生活需要。最后,强调多样共存。在《国语·郑语》里记载了史伯 关于“和”“同”的一段论述,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水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聪耳,正七体以役心,平八索以成人,建九纪以立纯德,合十数以训百体……夫如是,和之至也。”由史伯的论述展开探析,可以发现“和”的状态的达成必然需要多样事物的参与。不同事物相互碰撞,有助于单个事物的发展,“能丰长而物生之”。
传统外交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在习近平外交思想和实践中,得到了继承和升华。首先,周边外交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15〕“亲、诚、惠、容”的外交方式强调对周边国家的关注,“亲”指对周边国家亲近、友善,“诚”指诚心诚意对周边国家,“惠”指与周边国家展开互利互惠的合作,“容”强调要具有包容天下的胸襟。上述的周边外交方针,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传统“仁”观念的具体展开。因为,“仁”强调“泛爱众”,“泛爱众”自然意味着要与周围相处的对象亲近、友善;“仁”是人“修身”所欲达到的理想状态,但是“修身”先需“正心”“诚意”。此外,“惠、容”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有相似之处,都是在表明一种双向共促发展的方式。其次,“新型义利观”的建立。传统义利观在一定程度过分加强“义”在义利关系中的比重,但是,习近平总书记话语体系下的“义利”实现了新的蜕变,在某种程度平衡了二者的关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一方面坚持“义”在义利关系中的第一性,认为要“有原则、讲情义、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16〕另一方面,又强调“只有义利兼顾才能义利兼得,只有义利平衡才能义利共嬴。”〔17〕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义利”关系做出调整,是出于对当下世界发展的现实态势的考量。因为,现实社会高速发展,经济在各个国家乃至全世界发展比重中都占据重要地位,不考虑经济利益的影响,自然也都难以展开。此外,新时代大国外交的展现方式,尚有许多值得广大学人探析研究的地方。新时代大国外交作为中华五千年文化涵养的时代成果,其内在也必然与优秀传统文化有着更深层、更复杂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