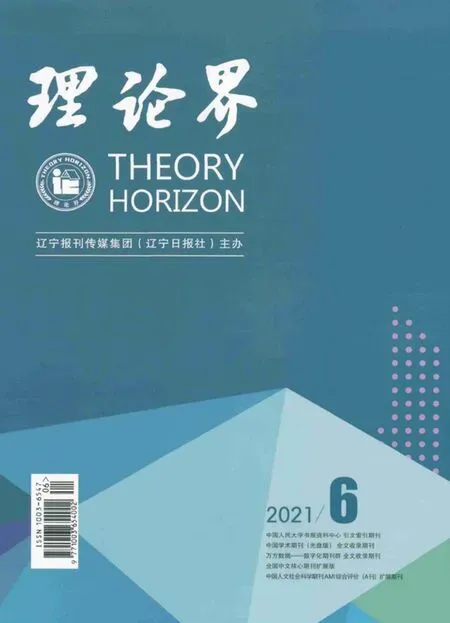葛兰西实践性意识形态思想的地位与影响
2021-12-26孙璐杨伍志燕
孙璐杨 伍志燕
葛兰西的思想不仅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为欧洲的文化思想研究打开了新的突破口。非洲民族独立的伟大战士、第三世界政治思想家弗朗茨·发农(Frantz Fanon)和巴西的人民教育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在领导被压迫民众奋起反抗的时候,他们的思想中总能找到葛兰西实践性意识形态思想的基因。英国的文化研究者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斯图亚特·霍尔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中汲取营养,承认人的能动性的重要性,认为民众可以通过文化(叙事、图像、音乐、对象)的创造,建构民众自己的阶级,建构一种新的民族与人民的话语权。拉克劳和墨菲在后现代语境中通过对葛兰西的领导权的分析,将其改造成为一种话语实践的理论,而且以此作为激进民主的战略基础。葛兰西对以上思想家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过丰富的探讨。但是,葛兰西实践性意识形态思想对阿尔都塞、齐泽克以及马尔库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却鲜有学者研究。
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实践的物质保障
阿尔都塞在肯定葛兰西实践性意识形态思想的基础上,继承并发展了该思想中的“市民社会”理论以及“主体性”理论,将以上两个要素成功地吸收到自己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思想当中。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必须是实践的,更是一种物质的现实性的存在。他评价马克思是阶级意识形态斗争的先驱,正是在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践中,“迫使马克思非常早地——从他青年时期的著作开始”,〔1〕就承认意识形态实践在意识形态斗争以及政治斗争中的重要角色。同时,他高度肯定了葛兰西对现实与实践问题的观照。阿尔都塞认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思想是“向人们发出的投入‘实践’、投入政治活动、投入‘世界改造’的直接呼吁”。〔2〕在马克思与列宁之后,真正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努力捍卫马克思主义事业的人,“据我所知只有葛兰西”。〔3〕
1.“市民社会”的另类诠释
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已经明确地将国家构想为一种“镇压性机器”。阿尔都塞认为,将国家看成资产阶级和他的同盟针对无产阶级的斗争的镇压性的干预,这触及了“国家”的本质,也定义了国家的基本“功能”,但这种对“国家性质的表达也仍然是描述性的”。〔1〕阿尔都塞将“国家政权”与“国家机器”进行了对比,认为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夺取“国家政权”,并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国家机器”。阿尔都塞在对镇压性“国家机器”与“国家政权”进行区分的探讨中,发现资产阶级在对无产阶级进行压制的过程中,有一个“现实”的东西犹如幽灵一样无处不在,并且对无产阶级民众有着极强的迷惑与统治功能。这个幽灵不同于“国家机器”包含的内容,政府、行政部门、军队、警察、法院、监狱这些机器使用的是肉体的暴力,他们并不能完全解释资本主义存在与运行的原因,而真正能解释这个原因的是“我们将冒着理论风险把这种现实叫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但是,发现这个奥秘的第一人是葛兰西,答案应该到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中去寻找。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一个由各种确定的机构、组织和相应的实践所组成的系统”,〔1〕在这个系统的各种机构、组织和实践中得以实现,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这些机构与组织包括:教育机器、家庭机器、宗教机器、政治机器、工会机器、传播机器、出版发行机器以及文化机器等。很明显,被阿尔都塞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这些机构和葛兰西市民社会思想中的丰富要素有多处重合,也正如阿尔都塞所说:“这就是我——追随葛兰西——称之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制度的东西,它指的是一套意识形态的、宗教的、道德的、家庭的、法律的、政治的、审美的以及诸如此类的机构。”〔4〕阿尔都塞认为,资本主义正是通过对这些机构的运用,维护了自身统治的稳固。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生产服从的同时,也生产了劳动力,即“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再生产”与“服从”两者之间又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不断巩固着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工人进行“管理”,帮助工人“学会了一些技能,同时还学到了不少别的东西,包括‘科学文化’或‘文学’方面的一些要素”,〔1〕也正是在机构中习得的这些本领,帮助他们成为一个合格的工人。同时,又潜移默化地让工人学习良好的举止规范,说到底“就是由阶级统治建立起来的秩序的规范”。〔1〕从此,工人就成了资本家的奴仆,并以积极的心态臣服于统治他的阶级。
2.意识形态实践的实质:摒弃“伪主体”
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主体意识以及革命斗争意识,已经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浸染中近乎消失,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意识形态实践斗争,建构自己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才能重新唤回自己的主体性。葛兰西意识形态主体性建构功能的思想影响了阿尔都塞。阿尔都塞认为,无产阶级之所以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蒙蔽,是因为资产阶级给无产阶级制造了一个“主体”的幻觉,让无产者以为自己就是社会的主体,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事实上此处的“主体”是“伪主体”,是资产阶级奴役无产阶级的工具,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丑陋本质的展现。当无产阶级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主体性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便得到了成功的实践。阿尔都塞认为,这种“主体性”是非主体性,只有对这种主体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进行批判,无产阶级才能展现“真我”,建构真正的主体地位。
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的存在就是为了主体地位的建构,并且意识形态的存在又必须依靠主体。资本主义凭借对人的主体地位的建构,战胜了封建专制,也浇筑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堡垒。在主体与意识形态双重构成的运作中,“存在着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的发挥”。〔1〕阿尔都塞认为,“个人——甚至在出生前——总是——已经是主体”,〔1〕人生来是主体这是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但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蒙蔽的人们“对此一无所知,却在勤勉为之”。〔5〕阿尔都塞认为,孩子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家庭便争取为他创造更好的环境,为他设定好的发展规划。此时此刻,孩子是占据家庭主体地位的家庭成员。可是,细究便发现孩子是“被主体”,因为从最初的那一刻起他并不拥有主动性。同时,与主体相伴而生的便是意识形态的建构。这个孩子被寄予的期望,其实也就是这个家庭的意识形态,这个家庭的意识形态追根溯源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正是如此,“通过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的实践仪式发挥功能”,〔1〕一边制造虚假的主体,一边巩固自己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通过对资产阶级构造的主体性的批判,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启示无产阶级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被虚假的主体与虚幻的意识形态所迷惑。无产阶级只有摧毁这个迷局,才能发现真的自我。
二、“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实践性意识形态的黑格尔式嫁接
布哈林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高度,认为上层建筑是物质世界的反映,上层建筑不能脱离劳动者的劳动而存在,因此,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也是一种物质化的存在,它“凝结为物,并且也在完全是物质的客体中积累起来”。〔6〕布哈林认为,这种物质化的存在以劳动为前提,劳动分为物质劳动与上层建筑的各种劳动,意识形态劳动与物质劳动并行不悖,都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并以一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前提。尽管布哈林触及了意识形态物质性的范畴,但是意识形态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依然附庸于经济基础,即“这些意识形态的‘生产部门’的分工,归根到底,决定于社会经济结构”。〔6〕真正明确提出意识形态物质性范畴的是葛兰西。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中的印刷工业,它不仅是一种物质工具也是一种上层建筑。印刷行业承载着某个阶级的政治、宗教、道德、科学与文学,通过宣传达到意识形态实践的效果。除此之外,学校、教堂、研究机构这种市民社会中的物质性要素,也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无产阶级在革命实践中只有掌握这些意识形态的物质性要素,才能把握革命实践的主动权。阿尔都塞认为,承载着资产阶级宗教、道德、法律以及政治、审美、文化、教育的这些机构,都属于意识形态机器,而意识形态就“存在于这种机器的某种实践或多种实践当中,这种存在就是物质的存在”。〔1〕无产阶级的生产性行为由资产阶级的物质性意识形态机器规定,无产阶级的实践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实践。齐泽克对葛兰西所阐明又经阿尔都塞发展的意识形态物质性思想进行了创造。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文明不容或缺的一种实践性的物质性力量。
1.物质性意识形态:痴迷于实践的幽灵
葛兰西将市民社会中众多的要素看作意识形态的物质性体现,认为资本主义市民社会运转的过程就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实践的过程,无产阶级要对这些物质性要素进行攻克与转换,占有这些物质性要素从而重获并巩固自己的主体地位。阿尔都塞认为,无产阶级之所以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蒙蔽,是因为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构造了一个虚伪的主体。因此,无产阶级要获取真正的主体性,首先应该批判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构造的虚假主体。葛兰西、阿尔都塞之后,齐泽克再次扛起以对主体性的探究为切口的深入剖析意识形态物质性范畴的旗帜。齐泽克认为,意识形态本就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它在任何角落都自在自为地实践着。无产阶级要想获得身份的反转,境况不容乐观。
齐泽克认为,“狗智主义”已经发展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传统的意识形态批判程序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作用已经丧失。布衣百姓不管怎样用陈词滥调反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揭露资产阶级鲜艳皮囊下的自利、血腥与暴力,都不能真正动摇狗智主义意识形态。狗智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帮办,这些帮办用狗智智慧(CynicalWisdom)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梳妆打扮。狗智主义“把正直、诚实视为最高形式的欺诈,把品行端正视为最高形式的放荡不羁,把真理视为最有效的谎言形式”。〔7〕他们的任务就是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做最变态的肯定。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不仅是谎言,而且是被视为真理的谎言”,〔7〕它在社会结构层面已经成为社会现实的物质性存在。齐泽克将这种现实称作“意识形态幻象”。意识形态幻象即无意识幻象,齐泽克把意识形态置入无意识领域。幻觉之所以可以成立,是由于人们已经忽视了幻觉,“幻觉正在结构我们与现实之间的真实、有效的联系”。〔7〕幻觉让无产阶级肯定自身的价值属性和行为举止,肯定自身正处于现实实践之中,但是无产阶级忽略了他们正受到幻觉的引导。幻觉真正的由来是主体的欲望,主体借助幻觉弥补自身的缺失。于是,意识形态便成为主体弥补自身在真实世界中欲望缺失的麻醉剂。意识形态已经不是一种遮蔽人们意识的虚假观念,而是主体构造自身现实的社会物质性存在。欲望的主体,通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与自在存在。“意识形态因素成了结构化的意义网络(Structured Network of Meaning)的一部分”,〔7〕成为一种物质性力量,治愈无产阶级在社会现实实践中存在的创伤,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正常运行的有力保证。意识形态帮助劳动者抚平现实的缺口与原始冲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已经成为无产阶级自证其存在的“良药”,离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无产阶级的欲望将无法“弥补”,创伤将无法“缝合”。
2.自发实践的意识形态
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影响了齐泽克的哲学思想与哲学研究方法,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矛盾分析法。拉康的精神分析思想为齐泽克提供了分析问题的术语和概念框架。马克思的作品为齐泽克提供了著作背后的动机或原因,齐泽克意识形态思想旨在探究商品拜物教背后的奥妙所在。宗教的构成在黑格尔那里主要包含三种要素,即教义、仪式和信仰。齐泽克按照黑格尔对宗教要素的概括,将意识形态分成三个形式:作为观念复合体的意识形态、客观形式的意识形态与自发的意识形态。这三种意识形态并不是前后继承的关系,而是共时的关系。齐泽克认为这三个形式的意识形态,符合黑格尔式的自在、自为、自在自为的三个组合。在此基础上,齐泽克进一步对葛兰西以来的意识形态物质性思想进行拓展与创造,丰富了意识形态实践的内涵。
作为观念复合体的意识形态,主要通过以下形式实践,即概念、理论、信仰与论证过程等。作为观念复合体的意识形态存在的目的是为统治阶级的权力服务,让被统治阶级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作为自己行动的真理。这种意识形态掩藏了统治阶级的自利、暴力与丑陋,歌颂的是官方意识形态的自由、正义与平等。这种意识形态缺乏实践活动的自主性,它自身被规定之后很难再产生新的内容,是一种自在的意识形态。“自为的”意识形态如同宗教里面的仪式一样,是客观的物质存在,即“意识形态的物质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8〕自为的意识形态具有较大的能动性,可以改变自己的状态并外化为一定的形式,进行自我实践。自为的意识形态有规定性,可以外化为一种机构,一种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但“这种规定性不再是有限的规定性,有如某物与别物有区别那样的规定性,而是包含区别并扬弃区别的无限的规定性”。〔9〕齐泽克认为,自为的意识形态就是葛兰西市民社会思想中的诸要素,以及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SA)概念所概括的契机”。〔8〕教会作为宗教信仰的载体,是一种物质性机构,它运转的基础并不是信仰本身,而是它背后的体制机制。下跪、祈祷、忏悔作为客观存在的意识形态实践过程中的仪式,颠覆了信仰的本质。信仰的本质规定是由于信仰才下跪,但是在自为的意识形态中“跪下,那么你就会相信你是因为自己的信仰”。〔8〕正是因为人们要肯定自己对宗教的信仰,他们才接受自为的意识形态中“跪下”这一仪式。民众自愿接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因为他们要弥补自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足。自在自为的意识形态即自发的意识形态,它不同于被规定的刻板的信条与理论,也不同于物质性的意识形态客观存在,它如同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一样,可以自足地形成一个意识形态实践的网络。齐泽克认为,这种意识形态事实上是一种幻觉,它支撑起主体的整个现实,并结构主体的社会活动。换言之,齐泽克所谓的意识形态幻象是一种社会活动的抽象假定,它决定了主体感知现实的形式,进而支撑着包含“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内的社会物质活动本身。
三、达到“爱欲”的解放:意识形态实践的最高诉求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商品和劳动者物化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物化意识思想。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物化意识已经占据了无产者的头脑,无产阶级已经完全失去了阶级意识与革命意识。无产阶级进行斗争,首先要消除物化与异化。生产结构转型时期的意大利,资本家越来越富裕,劳动者却变得一贫如洗,葛兰西认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劳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认为,工业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理性,而用它的非理性控制着人。面对异化的工业,只要消费者使用了它,那么它就会将消费者图画式。文化工业已经同统治阶级的意志完美结合,并转化成一种意识形态统治着无产阶级,欺骗着人民大众。如果不遵从,将“意味着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软弱无力,意味着‘受雇于自己’”。〔10〕马尔库塞作为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同时代人,发现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得到了提升,但是政治与文化思想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他发现科学技术和政治沆瀣一气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11〕科学技术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取得了统治的合理性。马尔库塞认为,爱欲是人最本质的特征,科学技术正是通过利用与压制人的爱欲,使人沉沦在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之下,因此,要解放人的爱欲。由于技术合理性的介入,人类原始作为“快乐原则”的心理机制转换成“现实原则”。在“现实原则”中被压抑的人将最后的避难场寄托给艺术,但“艺术异化跟其他否定方式一道屈从于技术合理性的进程”。〔11〕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异化是当代工业社会异化过程中最高水平的一种异化。艺术不再发挥自身的批判功能,而变得更加和谐,服从统治阶级拟定的一种秩序。因此,要实现“爱欲”的解放,必须为艺术松绑,而“爱欲”的解放是人类最终的解放,是人自由的实现。
1.意识形态实践的“爱欲”解放途径
在无产阶级通过“运动战”直接去与资产阶级政权作斗争又屡屡失败的情况下,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应该转变斗争战略。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之所以获得如此稳定的统治,是因为拥有“市民社会”这一坚固堡垒。无产阶级应该以实践哲学为武器,进行意识形态实践斗争,建立总体性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以及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重要思想来源。道格拉斯·凯尔纳在《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未能达成的接合》一文中提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诞生为西方文化研究转向提供了契机,这场文化研究的转向是一种“葛兰西转向”。马尔库塞继承了葛兰西实践性意识形态思想中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将文化和艺术的解放作为无产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的钥匙。
20世纪中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变得较为充裕,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到了资本的“红利”,科学与技术的产物也相应进入寻常无产阶级家庭。表面上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相安无事,但马尔库塞提醒我们,资产阶级时刻都压迫着无产阶级的精神与生活。马尔库塞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中,无产阶级“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反对权的基本的批判功能就会逐渐被剥夺”。〔11〕科学与技术充当着资产阶级的爪牙,在高精度的生产仪器面前,生产者已经成为了它的附庸。无产阶级不仅失去了劳动的意识,也失去了独立思考与提出问题的能力。技术已经渐渐丧失了解放的功能,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融为一体,并取得了意识形态合理性。在这种技术理性支配下,人类本能的“快乐原则”服从社会的“现实原则”,技术的压抑使得劳动者力比多不能实现自我超越,爱欲也得不到释放。可爱欲是人类生命的本质,是人类发展最高的境界。因此,无产阶级要将自己从被压抑中解放出来。
马尔库塞认为,技术理性意识形态不仅渗透进政治、经济领域,而且渗透进人类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技术理性意识形态的作用下,高级文化已经被驳倒,因为文化工业需要建构文化的一致性,“通过把它们全盘并入既定秩序,在大众规模上再生和展现它们”。〔11〕在技术合理性的支配下,个性思想与独立思维遭到扼杀,批判性观念被同化,劳动者变成一个“单向度”的人。当无产阶级开口说话的时候,他们表达应用的语言是“他们主人、恩人、广告商的语言”。〔11〕马尔库塞认为,当无产阶级已经不具备批判思想与革命思维的时候,便需要开展对他们的思想启蒙。艺术革命是思想启蒙的第一步,因为艺术的解放能激起无产者力比多在最大限度的释放,同样也是他们爱欲在最大程度上的解放。马尔库塞认为,艺术具有革命功能,艺术的革命功能与美学结合在一起,美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超越现实,通过幻想打破现实的蒙蔽,去构想一种自由,对现实进行公诉。无产阶级可以借助艺术表达自己的理想,使自己的压抑得到最大限度的释放,从而获得一种鼓舞人心的效果,进一步团结大众去斗争。艺术不用服务现实,它的意义在于否定现实,“不断提出将人从存在的悲惨境地中解放出来的要求”。〔12〕
2.“爱欲”解放的归宿:人的自由解放
葛兰西欲通过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获得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反领导权,使无产阶级重新获得自己的主体地位。进一步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从而将人类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束缚中解放出来。马尔库塞将葛兰西实践性意识形态思想中的文化内涵挖掘出来,坚持同技术理性意识形态作斗争。把文化与艺术看作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的核心,通过艺术唤醒人类最初的欲望,激发民众的力比多并踊跃同资产阶级作斗争,从而解放自己,解放全人类。
马尔库塞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质就是将民众从“剩余压抑”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意识革命,一种追求自由的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旨在创造一种非压抑的文明,社会主义运动就是为爱欲而战、为生命而战,将人的本质从资产阶级技术理性的意识形态中释放出来。关于人的本质,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3〕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六条中指出,人的本质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4〕将以上两种论述加以概括,人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关系总和中可以自由自觉地从事社会生产劳动。葛兰西认为,人时刻处在一系列能动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不是机械的,而是“能动的和有意识的”。〔15〕马尔库塞直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众的劳动是被动的劳动,是受压抑的劳动。它属于一种“额外压抑”,这种压抑是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强加于民众的。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民众不具有自我意识。劳动本来应该是民众的一种自在、有目的、自由的爱欲活动,但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在技术理性的支配下,人的本质已经丧失,人成了“单面人”。为消除这种理性的控制,马尔库塞决定建立一种新理性,即批判理性,而这个批判理性的依托就是艺术。艺术具有极强的批判功能,它表达着人们的向往与价值追求。真正的艺术是人把握世界的一种特定的方式,也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并且它集中地表现了人的本质,即爱欲。艺术代表着一种新的价值,这种新的价值推动技术、科学与社会重新结合,“从而实现人和自然的双重解放,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