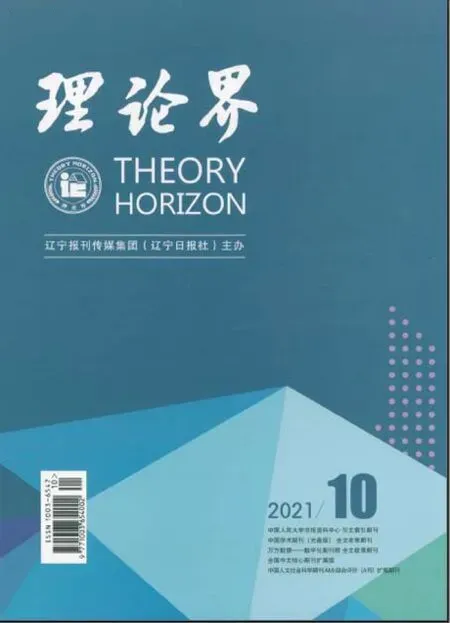华兹华斯诗歌中的家园与共同体书写
2021-12-26宋晓涵代显梅
宋晓涵 代显梅
引言
“家园”,泛指家庭或家乡,各种解释大同小异;相比之下,“共同体”这一概念较为抽象,各家阐述侧重不一。德国学者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认识到不同时期对同一个概念可能存在的理解偏差,于是引入“社会”这一观照物,以期对“共同体”给出较为客观全面的界定。他提出以下两种群体共同生活的模式:共同体生活与社会生活。前者“意味着真正的、持久的共同生活”,而社会则是“短暂的、表面的”。〔1〕“社会/共同体”这一对基本概念的提出是具有独创性的,它警示我们当下的社会运行模式与人际交往方式已然偏离理想的共同体状态,共同体成员之间应该维持一种情感维度上直接自愿的、和睦共处的平等互助纽带,这与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主张和诉求高度契合。在《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序言中,华氏赞扬“诗人是人性的维护者与保存者,他走到哪里,就把关系与爱带到哪里……诗人用深情和知识把人类社会这个辽阔的王国联结在一起,让整个地球和所有时间都用这个纽带联结在一起”。“关系与爱”意旨个体与万物丝丝入扣休戚相关的联系,不仅“与生理上的感觉、伦理上的情操以及激起这些东西的事物相联系,也与风暴、阳光……感德和希望、恐惧和悲痛相联系”。为了发掘爱,诗人需要“一定数量的直接知识,以一定的信念、直觉、推断”来激发同情心和愉悦感,因为知识“只有由快乐建立起来、单凭借快乐而存在于我们的心中”。〔2〕简言之,华兹华斯笔下的共同体是包罗万象的,成员拥有一致的思想方式、更高的精神层次与集体使命,人与自然、人与人、生者与死者之间均存在无法割舍的爱的纽带。华兹华斯依靠“深情和知识”(Passion and Knowledge),在诗歌创作时敏锐捕捉并刻画这种“关系与爱”(Relationship and Love),用炼金术般的技艺勾勒出家园与共同体的温暖蓝图。
一、人与自然的良性共生
1770年,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出生于英国的坎布里亚湖区(Cumbria Lake District),此地风光壮美,草原湖泊密布。得天独厚的成长环境使华兹华斯从小便与大自然结下不解之缘,自然之魅始终在其审美中占据不可磨灭的神圣地位。
华兹华斯的乡村抒情诗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一种自然共同体观念:他倡导人们从大自然汲取养料、灵感和启迪,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家园。《水仙花》(The Daffodil)就是诗人在平和心境下与大自然中随风飞舞的一大簇金黄烂漫水仙的邂逅。此诗语言看似朴实无华,缺少华美乐感,然而这正是华兹华斯在《序言》中所竭力主张的:“一切好诗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3〕诗人本似流云一般独自游荡,却被刹那间不期而遇的美景牢牢吸引。面对盈盈波光映照下一大簇依湖而生的水仙,单是闭目冥思就足以令人陶醉,更何况置身其中的直观体验。自然带给人的愉悦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身临其境,享受自然独一无二之美,人们便不会再促狭于尘世中的功名利禄,不会因虚无而焦躁,不会因纷繁杂事而烦恼。自然之美是有力量的,因此,诗人乐于亲近自然,在自然中放松自我,找到自我;自然之美是纯粹的,它使人们敞开心灵,享受大自然赋予的无限美好。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在一成不变的刻板中,现代人陷入焦虑迷失的困境,离自然越发疏远,万丈高楼越发遮蔽人的眼睛,闭合人的心灵。大自然的意义就在于为疲于奔命的人们提供灵魂的栖息地,使之放慢脚步,对所处的生存困境拥有清醒的认知,从而意识到自己被泯灭的、被压抑的和要追求的究竟是什么。所以,城市人应常常回归自然,以清风明月、芳草鲜花为伴,饮一杯山泉,洗涤为世俗纷争而困扰的心灵,将整个自我纾解于自然之中,一如华兹华斯,去偶遇打动自己的那束水仙。
此外,《丁登寺》(Lines Composed a 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把“古老与当下、自然与文化、自然景观与古代遗迹交织在一起”,〔4〕再现了与自然之美交融的青年记忆。在华兹华斯辗转于拥挤城市期间,是丁登寺旁的山谷溪水、村舍田地、果园树木这些“美丽形式”一直在给予他慰藉。诗人在“焦躁的时刻”回想起往日经历,继而脑海“恢复平静”,感觉负担减轻,变成“活的灵魂”。因为“大自然从来不曾背弃任何爱她的心,她有特殊的力量能够把我们的岁月从欢乐引向欢乐”,让心灵远离“流言蜚语、急性的判断、自私者的冷嘲”,从而灌输一个“愉快的信仰”,〔5〕即世界时时刻刻都充满关系与爱。这些诗句表明大自然能强烈影响我们的灵魂,给内心带来舒畅,潜移默化地促进行善和施爱。自然是人类物质需求的馈赠者,是人类心灵港湾的净化者,亦是人类终极追求的归依处。换言之,华兹华斯回归自然家园与故乡与其说是“身”的重返,不如说是“心”的返璞归真。作为一个居住在自然乡村的游历者,他书写自然,通过想象的力量打造出一个人与自然良性共生的生态共同体,不仅重新审视了自然的力量,而且对现代人提出新的要求与责任,强调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举足轻重。
二、自我与他者的移情顿悟
工业化冲击下,传统的家园与共同体形态分崩离析,建立一个新世界、新体系势在必行。但是,那个“不忠不义的时代”竟有一批“愚蠢先生与虚伪先生……将本不口渴的羊拼命赶往它们一向回避的水池”,〔6〕诗人深感忧虑,针对这种唯理性主义和科学至上的风气进行了尖锐批判与挑战。他多次提到“我们那好事的理智,扭曲了事物美丽的形式——我们解剖一切,却谋杀了生命”,〔7〕并且反思自己曾“动用逻辑推论,片刻间摧毁生命中的奥秘。然而,恰恰是这些奥秘,曾经——并且将会永远——使四海一家,结为兄弟”。〔8〕这显然展现了一种自我与他者休戚相关的共同体情怀。由此,就共同体中的人际交往而言,首先要摒弃物质至上的干扰,用不计功利、不求回报之心对待每个个体。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意味着“真正的、持久的共同生活,而社会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表面的东西。因此,共同体本身必须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9〕这与华兹华斯的共同体情怀十分契合,他反对社会利益网架构下短暂的虚假情意,批判功利主义及其支配下的阶级意识,呼吁个体包括陌生人之间长期的感同身受与移情共鸣,并且努力靠“深情与知识”完成顿悟,建设人与人相互关爱的共同体。在其诗歌中,读者可以体验对他人的共情,得以同欢乐的牧童同乐,与孤寂的老人共苦。这种人际交往模式强调互通有无后的治愈弥合,颠覆了他人即地狱般的异化疏离。比如,在《两个小偷》(The Two Thieves)中,老人和孙子经常在乡村街道行小偷小摸之事,但诗人并未谴责二人,一老一小两个无害的小偷甚至是纯真的、可爱的。同样,《决心与自立》(Resolution and Independence)中对老人由鄙夷到尊重的态度转变,也表现华兹华斯对底层群体高贵人性和强大生命力的赞赏。诗歌塑造了一位年老体衰却因维持生计而疲于奔命的捞水蛭人,“说不尽千辛万苦,长年累月,走遍一口口池塘,一片片荒野;住处靠上帝恩典,找到或碰上;就这样,老实本分,挣得一份报偿”。〔10〕老人言谈举止中的淡定和乐观映射出品性的坚韧与自信,自带一番庄严气派。悲苦人生境遇中的老人贫困却不贫乏,其自立自足散发着伟大的人性光辉,给叙述人抚慰。这是一个合作的过程,一方面,捞水蛭人具有洗涤人心的力量;另一方面,叙述人则富有敏锐的感知力与吸纳力,二者依靠“关系与爱”实现了移情顿悟,完成了心灵的升华。对各个阶层的怜悯与同情,使华兹华斯始终保持宽容与谦逊的态度,从兄弟情谊的大视角把全人类置于同一宇宙家园的屋檐下,打造出具有持久温度与安全感的人类共同体。
需要指出的是,华兹华斯虽倡导感同身受,但也提醒读者提防过犹不及的消极悲伤。正如在《废毁的茅舍》(The Ruined Cottage)中,一位年老的旅人讲述了玛格丽特默默等待、接连受苦的故事。老人的言语里不乏Happy、Joy等表示快乐欢欣的措辞,然而,年轻的转述者却因为玛格丽特的遭遇而极其悲伤。于是,年老旅人告诫他莫要陷入过度伤感,“我们的目的是获得智慧;聪慧些,快活些,别再用廉价的目光去解读事物的形态”。〔11〕在此,华兹华斯实现了对18世纪感伤主义滥情的超越,从而赋予移情顿悟以现实意义和价值。诗人是善于辩证思考并具有长远眼光的,他们将参透世事的智慧与关怀世人的深情二者巧妙结合,可谓张弛有度,游刃有余。
华兹华斯在《序言》中指出,诗人“有一种气质,比别人更容易被不在眼前的事物所感动,仿佛这些事物都在他面前似的;他有一种能力,能从自己心中唤起热情”。〔12〕这种善良的气质、细腻的情感和对人类本性的把握,铸就了华兹华斯关注人间冷暖的心。自我与他者之间相互宽容理解,靠关心、责任、尊重、认识来化解矛盾,无疑是建设幸福共同体的不二法门。
三、现世对往世的延续传承
华兹华斯强调人类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传承观与生命力,呼吁构建由记忆与继承为纽带的共同体。这种现世对往世的延续,一方面意指对家庭内部成员的眷恋、思念,另一方面也包含对那些素未谋面的大师的致敬、缅怀。
首先,书写家园叙事的小诗《我们是七个》(We are Seven)着眼于一位沧桑成年男子和单纯小女孩之间关于死亡的问答。对于男子“兄弟姐妹共有几个?他们都在哪里?”的发问,小女孩答道:“我们是七个,两个当水手,在海上航行,两个在康威住着。还有两个躺进了坟地。”〔13〕思维定式下的男子试图纠正小女孩的说法,坚持认为只有五个。小姑娘随后介绍自己在墓园织袜子、缝手帕、吃晚饭,言语之中不掺杂丝毫伤感与悲痛。成人之所以会为亲人的离世痛哭流涕,部分原因是他们已偏离自然的思维方式,随着年龄增长与自然的轨迹渐行渐远,摆脱了所谓的幼稚却走向了无谓的痛苦。因此,相较于世故的成人想法,天真的儿童信念更能使人幸福和宽慰。诗歌以“我们是七个”收尾,再次印证了诗人的家园与共同体理念:童真与爱可以超越生死的限制,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亲情是任何事物都无法分割的永恒传承。类似的,《迈克尔》(Michael)中的老牧羊人经常对路克谆谆教导,“把咱俩拴在一块的,没别的,只有爱”。〔14〕这正是对华兹华斯《序言》中“关系与爱”的生动例证。事实上,现世的每个人都是一面镜子,映照并传承其家族的优良品质,只要对于已故亲人心怀感恩、时刻不忘发扬其高风峻节,他们便永远与我们同在。哈布瓦赫曾强调:家庭记忆“总是能够成功地激发起成员之间的互爱,即使彼此分离,即使远隔千山万水”。〔15〕这种家庭记忆的黏合剂便是一种历时较久的纽带:一种对逝去亲人的虔敬与怀念,一种对优良家风的继承与发展。
此外,《伦敦1802》(London 1802)则是华兹华斯对于历史长河中智性巨匠的追思。首句“弥尔顿!今天,你应该活在世上:英国需要你!”〔16〕诗人一改婉转语气,直抒胸臆呼唤大师的到来,表达了对智性共同体的渴望。19世纪中期以后的英国宛如一头饱餐过后昏昏欲睡的雄狮,资本主义、功利主义宰制下的种种丑恶导致人类本性的堕落与思维的腐朽。古老英国的风尚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物欲横流中的急功近利。随着对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社会现实进一步失望,华兹华斯呼唤弥尔顿式的战士来力挽狂澜,维护共同体的正常运行与生机勃勃。
诗歌先是用一般现在时呼唤弥尔顿:“哦!回来吧,快把我们扶持,给我们良心、美德、自由、力量。”接着用一般过去时颂扬弥尔顿:其灵魂就像“孤光自照的星辰”,其声音宛若“壮阔雄浑的大海”。〔17〕华兹华斯通过现在与过去两种时态的交替使用,灵活传达出一种横亘古今的呼应与链接。即使先哲已逝,其光辉品行仍熠熠生辉,对后世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
由此,历史的发展前进轨迹离不开每一位个体的无私付出与真诚努力,“无论以什么方式,无论见解多么不同,只要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发展与幸福,都是殊途同归的合作”。〔18〕
结论
诗人亦人师。在华兹华斯的共同体蓝图中,个体与他者、传统与现代、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都是和谐共处的。他强调了人与自然、人与人、生者与死者之间丝丝入扣的爱的纽带,传达出厚重的家园与共同体意识。反观当下,功利主义与浮躁之风盛行,科技进步带来表面便捷的同时,也瓦解了稳定的生活方式,销蚀了家园共同体的熟悉感,因此,回归文学、追溯经典,重构人性的维度与人文的关怀迫在眉睫。一致的艺术追求,真诚的感同身受,共同的文化之根,宽容的和谐相处,在自由思想与道德审美中获得生命的踏实愉悦感,这不正是家园与共同体的最好诠释吗?华兹华斯的这种意识与书写因为超越了地域、宗教、种族等的限制,表达了全人类对精神家园的共同渴求,为实现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与配合提供了一张良方,所以在今天的我们读来也一样具有极大的启迪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