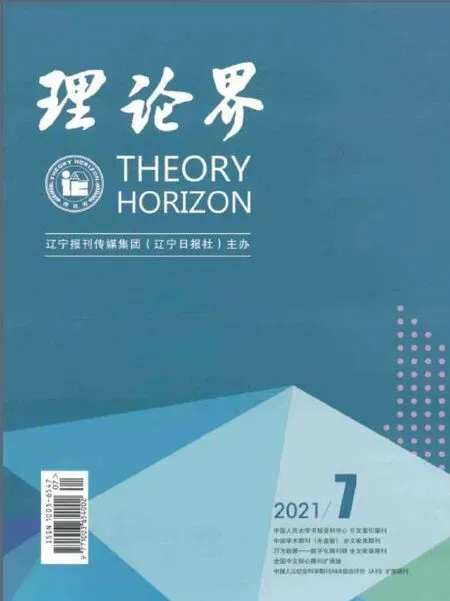索恩-雷特尔的居有实践理论及其启示——兼论康德先验论难题的破解
2021-12-26付高生
付高生
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1〕就此而言,一切看似神秘的深邃理论都存在一个实践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挖掘理论难题背后的实践就是其重要的理论使命。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以下简称“雷特尔”)正是秉持这种使命,用他的一生力求破解康德的先验论难题。他提出的居有实践理论就是破解这道难题的锁钥。
一、破解康德的先验论难题:雷特尔提出居有实践的理论初衷
哲学始于惊诧,这种惊诧有时源于实践,有时源于理论。对于雷特尔而言,他的惊诧源于后者即康德的先验观念论难题。我们所熟知的康德理论可分为前批判时期与批判时期,其中1781年出版的《纯粹理性批判》(以下简称《纯批》)是界分这两个时期的标志。康德的先验统觉论即出于此书。
在《纯批》一书中,康德认为:知识必须是客观的与普遍的,而人的先天综合判断就是实现这种知识的前提。先天综合判断发生于人的经验界即现象界,它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外界对象刺激主体之后,在先验感性即空间与时间的纯粹直观下形成了感性表象的杂多;第二个阶段就是这种杂多的直观表象在先验观念中经历的一个以先天的综合统一性为基础的综合过程。其中第二个阶段中的“先天的综合统一性”,在康德看来,就是“我意识到这些表象的一个先天必然的综合,它叫做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一切被给予我的表象都必须从属于它”。〔2〕只有在这种统觉的综合统一下,知识才能形成并达致客观性与必然性。但问题是,康德对这种统觉自身的起源没做进一步的说明。他认为,关于这种统觉的特性“很难说出进一步的理由,正如我们为什么恰好拥有这些而不是任何别的判断机能,或者为什么惟有时间和空间是我们的可能直观的形式,也不能说出进一步理由一样”。〔3〕既然康德在这里同时提到了先验统觉与先验感性的来源问题,就需要提及康德在1770年为竞选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席位而作的论文《论可感世界与理知世界的形式及其原则》(以下简称《形式及其原则》),因为该文曾提到先验感性的来源问题。
如前所述,康德理论可区分为前批判时期与批判时期,如果说《纯批》(1781年)是界分这两个时期的标志,那么《形式及其原则》(1770年)则是康德从前批判时期向批判时期转变的奠基性作品。在《形式及其原则》一文中,康德曾这样反问:时间与空间是“天赋的还是获得的”?康德认为,它们“毫无疑问是获得的”,但不是“从对象的感官感知得出来的”,而是“从精神的活动自身得出的”。〔4〕易言之,康德认为先验感性不是天赋的而是人自身生成的,但这种生成却不是源于经验或感性的反思而是源于人的精神活动。进而言之,我们有理由推测,对康德而言,《纯批》中的所有先验要素部分如感性直观、范畴、统觉等都是源于人的精神活动。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能否进一步追问人的精神活动源自何处呢?
从西方哲学史看,近代西方哲学发轫于笛卡尔的主体性哲学,而后者具备一个重要特征,即知识源于“思维着的我”这种思维主体。但“这个主体性并未就其存在得到询问,自笛卡尔以来,它就是禁地”。〔5〕从这个意义上看,康德批判哲学显然延续了笛卡尔的主体性哲学传统。在雷特尔看来,康德将先验统觉的原则归基于主体的“先验自发性”,从而拒绝了时空意义上的发生学解释。〔6〕易言之,康德沿用了主体性的禁忌,而这种禁忌的特征就是遮蔽主体性的起源问题,从而导致他规避了先验要素(包括直观、范畴、统觉等)的自身起源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看,“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7〕由此,康德的哲学必然存有自己的物质生产基础。因而,康德之所以规避统觉的起源问题,缘由在于他遗忘了他所做的批判与他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而寻找这种统觉与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就是雷特尔所指称的先验论难题。破解该难题即雷特尔提出居有实践的理论初衷。
二、居有实践的内涵及其特征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在三种意义上言说了实践。其一,他们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即在劳动的意义上言说实践。这种实践即生产性实践,它主要指向物质财富(其中也包括特殊的物质即商品)的生产。其二,他们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也言说过实践,指向的是社会改造。社会形态的更替、生产关系的嬗变、阶级之间的斗争等都从属于这种人际关系意义上的实践。其三,他们还在精神维度上言说过实践,指向的是文化的生成或文化的再造,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生产活动。由此可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实践既能表达人与自然之间的生产性关系,又能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生产,以及精神维度上的生产。质言之,实践是一种开放性的概念,能够包容多种样态。这种概念的开放性允许研究者拓宽实践的形态,从而有利于他们构建立基于新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那么,雷特尔提出的居有实践是在什么意义上言说的呢?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8〕在雷特尔看来,到目前为止,这种物质生活生产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其中全民共同生产并且共同分配物质生活资料;第二个阶段则为剥削社会,其中只有一部分人从事这种物质生活生产,而另一部分人则居有前一部分人生产的产品。在第一个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立基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生产关系,前一种关系依赖后一种关系;而在第二个阶段,“人与自然之间的生产关系变成了一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对象,并将服从于后者的秩序与法则,因此,它相对于‘原始’状态而言乃是‘去自然化’的”。〔9〕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把从奴隶制社会直到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历程称为阶级社会,而雷特尔则称之为剥削社会。这种称谓上的差异绝非止于语言层面,深层次看,这种差异涉及特定社会形态下的实践指认。如上所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阶级社会中的实践具有三种形态:物质层面的生产性实践、社会层面的革命实践以及精神层面的精神生产。而在雷特尔所指称的剥削社会中,他实际上提出了一种基于社会关系层面的新的实践形态即居有实践。
在雷特尔看来,剥削社会中的一部分人从事物质生活的生产,可称之为生产性实践;而另一部分人则居有前一部分人生产的产品。这种居有行为虽然不是直接的生产,但它却“是一种直接的实践的事实情况”,〔10〕即:它发生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表现为一部分人居有另一部分人生产的产品,从而使这些人脱离了与自然之间的生产关系。在雷特尔看来,这种居有他人产品的行为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中的居有实践”。〔11〕在这里,雷特尔区分了马克思文本中表达生产关系的三个重要概念,即Eigentum(所有、财产或产权)、Besitz(占有)、Aneignung(居有),〔12〕并且把生产关系意义上的“居有”升级为实践层面上的“居有实践”。
雷特尔认为,居有实践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由于集体共同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人们拥有了一定量的盈余产品,而这些盈余产品的出现导致了无须回礼的礼物交换(或礼物赠送)。此后,随着氏族之间的冲突,原始社会开始爆发抢夺剩余产品的战争,即“一个民族战胜另一民族,为的是以占有后者的剩余产品为生”。〔13〕雷特尔认为,无论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内的单向礼物赠送,还是战争导致的暴力掠夺,二者本质上都属于单方面的居有产品行为。这种行为即最初的单向居有实践。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解体之后,人类社会开始步入剥削社会,此时的人类之间虽然也存在单向的居有实践,但同时逐渐发展出商品交换行为。这种商品交换行为即双向的居有实践。雷特尔认为,居有实践从单向的居有转变为双向的居有,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且,雷特尔重点讨论了作为商品交换的双向居有实践,缘由在于这种双向居有实践是导致康德先验统觉的现实基础。
在雷特尔那里,作为商品交换的居有实践具有如下重要特征。首先,居有实践只存在于剥削社会之中,因而它是一种特定社会形态下的阶段性实践或历史性实践。其次,生产性实践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生产性关系,但雷特尔的居有实践则“否认‘同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人的物质生活’的实践,因此首先否认‘生产劳动’”。〔14〕就此而言,居有实践“不是生产实践,而是生产实践的对立面”,〔15〕是一种非生产性实践。再次,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商品交换本身不创造价值,而是对生产者抽象劳动的剥夺,是一种非正义的行为。故此,这种居有实践具有非正当性,即一种异化了的非正义实践。最后,在商品交换行为中,“交换者的行为与意识、行动与思维都分散开来,并且分道扬镳”,〔16〕这种行为与意识相分离的特性使得交换行为成为一种现实抽象。所谓行为与意识相分离,是指个体层面的有意识行为与社会行为层面的集体无意识二者之间的分离。具体而言,在具体的商品交换行为中,就个体而言,交换者诚然是有意识的;但就社会整体而言,由于商品交换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化成商品与商品之间的关系,因而它导致了有意识的个体在交换行为集体层面上的无意识,即不能认识交换行为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雷特尔看来,这种个体层面有意识而社会层面集体无意识的商品交换即为一种现实抽象,故此,居有实践具有现实抽象的特征。
三、居有实践与先验统觉的奠基性关联
雷特尔认为,康德哲学形成于商品交换已经成为社会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时期,此时,“资产阶级获得了其经济上的自主,它便也成功实现了外在的、政治的解放,康德哲学便是为这种解放提供意识形态基础的”。〔17〕在此,雷特尔不是把商品生产而是把商品交换作为解释康德哲学的实践基础。从逻辑上看,雷特尔把商品交换定位为特殊形态的居有实践,而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特定实践形态导致相应理论观念的主张,他的这一做法显然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尽管哲学与宗教等意识形态与物质基础之间存在联系,但它们“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18〕因此,对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揭示实践与理论之间的关联是一种巨大的理论挑战。在雷特尔那里,虽然他已确定商品交换是破解康德先验论难题的关键,但是如何揭示商品交换与先验统觉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难题。一方面,仅仅依靠宣称前者决定后者而不展示这种“决定”的具体过程,显然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另一方面,直接展示这种“决定”又是困难重重,在理论上难以操作。因而雷特尔必须寻找第三条路来破解康德的先验论难题。就居有实践与先验统觉之间的关系而言,雷特尔认为它们之间是一种奠基性关联,这就是他寻找到的第三条路。遗憾的是,雷特尔并未清楚地解释何谓奠基性关联。但从雷特尔的论证过程来看,笔者认为所谓奠基性关联,是指:如果人们难以揭示特定现实是如何导致特定观念的,但他们若能揭示该现实与该观念共有某种特征,那么他们就可以宣称前者是后者的奠基性关联。这种奠基性关联意味着哲学家形成其特定观念时往往受到时代现实的影响,但有时他们并未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正如马克思所言,“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19〕
依据这种奠基性关联,雷特尔试图找出现实社会中的“综合”,从而以此呼应康德哲学中源于精神本源的先验统觉。事实上,雷特尔认为这种“综合”的确存在于居有实践(商品交换)之中。在居有实践中,“商品——其使用价值是不可通约的——在它的交换行为中获得了作为价值的可通约性,在其中,它们按照形式而被设定为同一的,仅仅是在量上被区别开。因而,这正是康德意义上的‘综合’”。〔20〕在这里,所谓商品的“综合”,从句意上看是指商品之间的等价性或可通约性;但深层次看,它却是指居有实践创造的社会—综合功能。而所谓社会—综合功能,亦可称为功能社会化,特指剥削社会中居有实践产生的一个整合分裂社会的人为功能。雷特尔认为,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由于人们共同从事生产性实践,因而他们同时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由此导致了公社内部生产与消费的天然统一以及公社成员之间交往的天然统一。而进入剥削社会之后,人与人之间出现阶级分化,社会开始出现生产者群体与消费者群体的分裂。由于不从事生产的消费者的生存离不开对生活资料的消费,因而他们必然要寻找一种妥当的方式来获取生产者的物质生活资料。在雷特尔看来,这种妥当的方式就是商品交换即双向的居有实践。这种双向居有实践由此取代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生产性实践以及单向的居有实践,重新连接了分裂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的关联”。〔21〕而在雷特尔看来,商品交换中商品体现的社会—综合功能,即对生产与消费的整合以及对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整合,非常类似于康德先验统觉对知性表象的综合功能。由此,雷特尔认为居有实践的综合功能与先验统觉的综合功能是相似的,居有实践与先验统觉构成了一种奠基性关联。
四、余论
由上所述,我们看到雷特尔在区分生产社会与剥削社会的基础上,把剥削社会中的商品交换行为定性为居有实践,进而根据马克思的实践观,进一步探求康德先验统觉的现实起源。就破解康德的先验论难题而言,我们看到雷特尔首先揭示了居有实践中商品展露的社会—综合功能,其次他把这种社会—综合功能看作康德先验统觉的现实性对应,最后才把居有实践确定为先验统觉的奠基性关联。可以说,雷特尔的这种论证思路颇为新颖,并且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但与此同时,他的论证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即这种社会—综合功能何以进入人的意识之中,并且何以导致康德的先验统觉,雷特尔并未给出清晰的证明。虽然存有这种缺陷,但瑕不掩瑜。
笔者认为,雷特尔坚持从实践出发分析观念的起源性问题,这启发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要立基于中国的实践。应该说,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概有三种研究路径。第一种是以苏联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路径,第二种是以德国、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第三种是以中国共产党人为主体所推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路径。这三种研究路径的背后都立基于实践,但第一种研究路径所立基的实践是苏联的实践,第二种研究路径所立基的实践是国外的实践,只有第三种研究路径所立基的实践是中国的本土实践。就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现状而言,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以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主的现象,折射出对当代中国实践研究的欠缺,使得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现实问题意识不浓的特征,进而导致“三失”问题,即学科中的失语现象、教材中的失踪现象以及讲坛上的失声现象。就此而言,雷特尔对康德先验统觉起源难题的解答启发我们,不仅要善于依靠实践解疑答难,更要善于从中国的实践中发现中国的问题、解答中国的问题,在发现中国问题、解答中国问题的过程中建构中国的话语、建立中国的理论。
雷特尔把商品交换定性为居有实践,这启示我们应该注重拓宽对实践形态的研究范围。例如,就城市化而言,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年代,资本主义的城市建设开始兴起,但尚未达到规模化的程度,这使得他们对城市生产的思考尚未完全凸显。20世纪以后,西方城市化开始规模化,这使得列斐伏尔开始注意城市化这一现实行为,并将之提升到“实践”的高度,从而开辟出社会空间的转向,形成了以“社会空间”“空间生产”“空间正义”为核心范畴的社会空间理论,推动了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发展。近些年来,随着国内城镇化的发展,国内部分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反思国内城市建设;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些研究者主要是通过译介国外社会空间理论的方式推动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反思,而没有很好地立足中国城镇化建设展开相应的反思。这种以西方社会空间理论为中介反思中国城镇化建设的研究路径明显地忽视了中国城镇化建设与西方城镇化建设的异质性。在此,就城镇化议题而言,本土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与其借用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如结合中国的城市化理论研究成果,以中国的城市研究史料为基础着手梳理与反思中国的城市化现状,提炼中国的城镇化建设特征。总之,雷特尔的启示可以归结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应该结合本国国情,本着拓宽实践样态的研究原则,提炼符合中国国情的实践形态,从而切中中国的现实,最终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