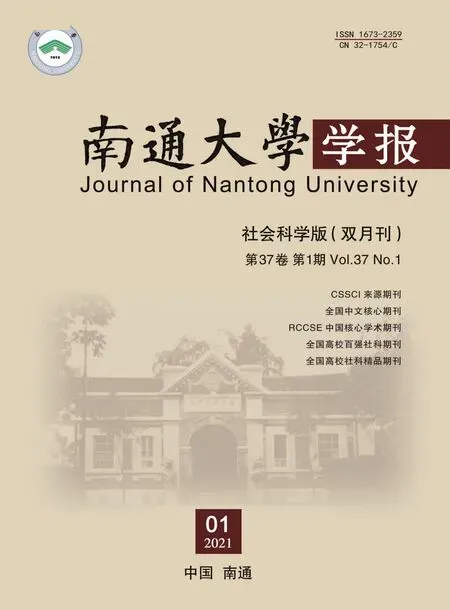从人格到人设:数字化时代人格面临的新挑战
2021-12-25徐强,胡婵
徐 强,胡 婵
(1.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2.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20013)
人格的核心要义是“格”,即格调,它是人之为人的表征。人设是指人物设定,它是一种被虚拟化的人物形象。人设可以视为人格的变种,但又不同于人格,它是一种虚拟化的个人,是借助网络平台以社会方式完成的对个体的结构性建构。在数字化时代的商业利益和资本的共推下,人设如同个体炫目的名片,吸引着人们的眼球,通过赚取流量,实现着商业利益的攫取。在今天,人设问题已是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也是哲学需要直面的问题,对其进行反思实属必要。
一、人格:人之为人的规定
自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创立以来,人们对于人格开始有了逐渐清晰的认知,同时也为多视域的人格探讨提供了可能。这里我们着重是从哲学的意义上来看待人格问题。
在黑格尔看来,人格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单一意志。这种自我意识具有双重规定:一是关于“我”这个特殊性的认识,一是关于“人”的普遍性的认识。自我意识就是普遍性中的特殊性认识。人在本质上是自由意志,当人只认识到“我”的存在时,这是一种被规定的、非自由的存在,它体现的仅仅是一种“自然的”自我意识,只有将“我”这种自然的自我意识提升为简单无限性的自我意识(即无规定性的、“自由的”自我意识),从“小我”即独立个体的认识达到“大我”即人的认识时,人格才可能确立。相反,如果一个人只是意识到“我”的存在,而意识不到“我作为人”的存在,则这种自我意识越强烈,就越可能成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人,而并不意味着具有独立人格。对于“我”而言,重要的不是确认“我”的存在,而是在于确认“我作为人”的存在。
在黑格尔的理念中,“我”不只是一个自然生命体的自然存在,更是一个自由意志的自由存在,后者才是更为重要的、人之为人的存在。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黑格尔才说“人间最高贵的事就是成为人”[1]46,人格就是个体达于人的规定。所以,对于个体而言,不仅要确立作为存在论意义上的、形而下的存在,而且更要确立抽象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存在,人格是“抽象的‘自我’本身的自由”。一个人不只是要成为“我”,而且要成为“人”。当一个人还没有达到对“自由的存在”的认知时,便没有拥有独立人格。我们在评说一个人的人格及其高下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黑格尔认为,不能把人简单地当成主体,人是意识到自己主体性的主体。他说:“人实质上不同于主体,因为主体只是人格的可能性,所有的生物一般来说都是主体。”[1]46从政治法律的平等权意义上来说,个人拥有天生的人格权;但从哲学的意义上来说,个人只有“成为人”或者说成为具有自由意志的主体性存在才真正具有了人格。因此,个人仅仅获得社会承认的人的身份还不够,还需要通过自由意志的获得真正成为人。只有借助自由意志,个人才能超越有限、摆脱被规定性,趋向无限、非规定性,从特殊达于普遍。从社会层面来说,人之为人具有平等的自由权利,这一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它高于其他一切权利,是权利的权利,因而它是一种抽象的母权利,用黑格尔的术语来说,就是一种“法权”。法权属于最高权利,但它又必须通过具体的法律——人格权来予以确认。从社会层面来说,法律规定和保护个人的基本人权,是社会对“你是人”的承认;从个人层面来说,个人还需要学会做人,亦即“成为人”,维护人的“格”。这是个人对自己是“人”的证明。当社会承认个人是人时,个人的行为也必须与人的身份相匹配。个人需要以自身的尊严来维护自己作为“高贵者”的存在,人不仅是其所是,而且要努力成为其所是。说到底,一个人既要认识到“我是我”,又要认识到“我是人”,并且努力以自己的行为确证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只有在此时,人格才可以确立。“个人和民族如果没有达到这种对自己的纯思维和纯认识,就未具有人格。”[1]45-46在这里,黑格尔以纯思辨的方式完成了他对人格本质的规定。对于个人来说,我们很难用一个绝对化的标尺来衡量一个人“是人”重要还是“成为人”重要。实际上,前者关乎社会对个人作为人的确认以及个人作为人的生存权、人格权的维护,后者则关乎个人自身如何通过言行来表征自我,确证自己作为人的存在。对于人格而言,不管我们如何理解,其根本性内涵在于确证这样一个事实,即“我是我”,是作为人的我的存在。
黑格尔虽承认了“我在我的存在中依赖别人”“我是一个由于一个别人才是自为的存在”,也就是说,他承认了另一个同样是自我意识的他人的共在,个人主体的存在只是由于被对方承认。但是,黑格尔同时认为当自我意识处于自在阶段时,我与他人的关系却是对立的。“自我意识有另一个自我意识和它对立;它走到它自身之外。这有双重意义:第一,它丧失了它自身,因为它发现它自身是另外一个东西;第二,它因而扬弃了那另外的东西,因为它也看见对方没有真实的存在,反而在对方中看到了自己本身。”“因为它们最初是等同的,并且是正相反对的,而它们朝着统一的返回又还没有达到,所以它们就会以两个正相反对的意识的形态而存在。其一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它的本质是自为存在,另一为依赖的意识,它的本质是为对方而生活或为对方而存在。前者是主人,后者是奴隶。”[2]123,127在这种关系里,奴隶才成为奴隶,主人才成为主人,这就是黑格尔著名的主奴辩证法。这里黑格尔以一种抽象思辨的方式表达了对人格的基本立场,揭示了人格的本质特征即在于对人之为人的确认。
从总体来看,黑格尔对自我意识的确认是肯定意义上的表述,他不是把他人当成自我意识从否定意义上理解的他者,而是相互的认同和肯定(当然这是在自为存在的意义上说的)。这与下面我们将要讲到的拉康的他者论不同。在拉康那里,他者与自我是完全异质的,而非彼此的认同。正是这种异质的他者存在,改变了主客关系,使人丧失了自我的主体地位。
二、人设:人物的设定
近代哲学对“我”的澄明是始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法国著名思想家拉康则从镜像展开。在拉康看来,镜像是“可见世界的门槛”,它以虚拟的意象映照着机体与现实的关系、“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如果镜像是“我”的话,那么,“我”本身就成了客体的投射,镜像反而成了主体。因此,人不过是一个伪主体。在拉康眼里,人的欲望是大他者的欲望,是对于大他者的欲望,是来自大他者的欲望,是作为大他者的欲望。我们总是欲望着别人的欲望,这在无形中确证着人的否定性存在。拉康的观点虽然显得过于尖锐甚至尖刻,但的确又是对现实人的一种真实观照。
拉康哲学是一种主体批判理论,他通过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批判性玄思,指认了主体从来就是一种自欺。如果说尼采宣布“上帝死了”,那么拉康则宣布了作为主体的“我死了”。从婴儿期把镜像作为“可见世界的门槛”开始,经过命名和现实异化,拉康不仅说明了镜像之我走向社会之我、个人主体被构成的虚假性,同时也证明了作为真实存在的“真我”已被放逐为一个无名的他者。拉康赞同人经历了一个被建构的过程,但这种建构过程不是肯定意义上的,而是否定意义上的。拉康的批判理论直指真我(无限流动的欲望能指)与主体(凝滞定格的符号所指)的对立。人身处世界,面临着真我与支配我的幻影(想象界)、人的符号(象征界)以及实体性物化世界(现实界)的一体化或结构性协调,因此,在“集中营式的社会关系”中,社会之我已经不是真我,人彻底沦为被言说的对象,主体也“不是在说话而是被说”。“在这里自然个人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事实上面对死亡中加于他的绝对主人,人的主体是无足轻重的。只有通过别人的欲望和劳动的中介人的欲望才能得到满足。”[3]118
在拉康那里,“‘我’是在逻辑时间的功能中通过使与他人的竞争的主观化而定义的,论定的主体所确证出来的‘我’乃是以与他人的互为主体作为参照的,‘我’被当作是‘他人的他人’,‘我’只是在‘理解的时刻’才能获得这一主体的形式,如拉康所说‘每个人都是通过他人而抵达真实的’”[4]116。拉康指认了主体自我确证时的“集体逻辑”,也正因为如此,这是一种非主体性的主体,即伪主体。因为“我”是伪主体,所以,不是“我思故我在”,而是“我在我不思之处”[5]449。
拉康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对20 世纪60 年代以后欧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它是后现代思潮消解主体哲学、反对人本主义的理论缘起。受拉康的影响,阿尔都塞提出了著名的个人主体质询理论。在《意识形态与国家意识形态机器》一文中,他用“质询”(interpellation,也译作“唤问”“询唤”)来描述语言和主体的建构性在场的关系。他说:“通过我们称之为质询的那种非常明确的活动,在个人中间招募主体(它招募所有的个人)或把个人‘改造’成主体(它改造所有的个人)。”[6]488在这里有权质询的主体是上帝以及种种大写的类本质(绝对观念、存在、人、总体、主义等),现实中存在的个体不过是这种主体的镜像复制。阿尔都塞由此得出如下结论:“一切意识形态的结构(以一种独一无二和绝对的大写的主体之名把个人建构成主体,是反射,亦即是一种镜像结构)和双重的反射:这种镜像的复制构成了意识形态,并保证了它的作用。”[7]197随着个体意识形态的被复制,“个体被询唤为(自由的)主体,以后他将(自由地)屈从主体的诫命,也就是说,他将(自由地)接受他的臣服地位,即他将‘完全自动’(allbyhimself)做俯首贴耳的仪态和行为”[7]199。自然,个体在这样的状态中也就不成其为主体,与之相应的则是外在于他的大写的主体。阿尔都塞与拉康的不同在于,前者用大写的主体取代了后者大写的他者,这就在确认个体对象化的同时指证了对象主体的存在。阿尔都塞的这一改写,使得在拉康那里发生在个人早期主体建构中的镜像作用,变成了意识形态通过内部运作机制对个人主体的直接复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尔都塞更鲜明地揭示了社会对成人的建构过程。
福柯的权力理论则论证了对个体话语压迫(discourse oppression)的普遍存在。福柯区分了两种权力:一是“古典式的权力”,它处在意识形态的中心领域,呈现出的基本特性是“禁令的循环”,即否定的压制性;一是“现代式的权力”,它是变动的、生产的、复数的、可再生的、无处不在的权力,福柯将它称之为“一种积极的权力观”。在现代社会,身体是权力生产出来的,生命受到权力的积极干预。非人格化的权力使得身体取代了主体,成为无意识的、受权力操纵的肉体存在。个体失去了自我意识,完全成了权力的附庸。在他看来,主体的位置也同样是由它相对于对象的各种不同范围或群体有可能占据的处境所确定的:从某种明显或不明显的提问界限来看,它是提问的主体;从某种信息的程序来看,它是听的主体;而从典型特征的一览表来看,它则是看的主体;从描述典型来看,它是记录的主体。福柯的理论对当时欧陆思想界形成极大冲击,但他对古典式权力和现代式权力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的理解,则受到了后现代理论的猛烈批评。例如德勒兹、巴塔利等人就不赞同福柯对待权力的看法,相对于福科对权力持有的一种相对否定的态度,他们则把权力视为具有某种生产性,在某种意义上它可以和欲望结合起来并进行有效再生产。
德勒兹等人也从欲望出发,但是他们所讲的欲望不同于弗洛伊德式的由匮乏而引发的欲望,而是生产性欲望。在他们那里,“欲望”与“社会生产”实际上是一回事,因为欲望本身不属于自我,而是社会性的。个体主体是在社会和自然机器中发挥作用的不同部分的集合,因此重要的是要揭示各个身体部分及其之间的社会联系。
以上是对主体认知的历史线索的简单梳理,实际上是为了明晰从前现代到现代再到后现代的主体向主体性的转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主体慢慢丧失了主体地位,而沦落为被他人凝视的镜像中的人。个体在社会的构境中,充其量只是带有一定的主体性,而不再具有主体地位。我们对人设的理解放置在这一理论背景中才能被更好地理解和把握。
人设本来是动画中的专有名词,它包括人物的基本设定:姓名、年龄、身高等,还有背景设定:出生、学习情况、生活场景等。简单来说,人设就是创造一个完整的人物,供编剧或者业内人士讨论时使用,但今天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日常。所谓人设,是人物设定的简称。人设的基本特征是一种设置,有人把它比喻成商品的贴牌过程,即对一切试图出卖自己的个体的一种再认和定位。
人设是现代向后现代、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理性时代向后理性时代、权威时代向媒介时代转接的产物。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新的历史场域中,人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都发生着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言说方式和行为方式也在发生巨大转变。社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共振力诱使人们向它屈服和献媚,同时也裹挟着人们在名利场中以一种讨好的方式立足和寻求接纳。在数字化时代,网络的迅疾、强辐射及其有的巨大推动力似乎为人设的出场提供了一切可能。人设的产生就是一场有预谋的对人的重写或改写,它是对人的自我夸张和虚饰,目的是为了赢得他人的好感,并利用这种好感为自己谋利。
我们这里所探讨的人设,主要是指个人为了获得商业利益而进行的人物设定。虽然它是对个人的设定但却未必由个人完成,通常是在个人背后由一个强有力的商业运作团队推出和维系,个人只要配合表演即可。人设是网络时代媒介特有的东西,它通过他人在个体身上的情感投射,借助网络平台,迅速实现了对社会的全覆盖。人设通过平台制造了种种奇迹,如同变戏法一样完成着对个体的复制和粘贴。人设体现了想象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关系,是虚拟与现实的相互渗透。它通过想象构筑起一个童话世界,成为一个虚幻意象,却又回到现实,成为获利的工具和资本。
人设诉诸被结构化的想象,在虚幻中完成自我建构。主体本身以为这就是自我,实际上这只是被虚构出来的自我。当他成为被凝视的对象时,他既在接受他人的凝视,又在接受自己的回望;既与他人遭遇,又与自己遭遇。尤其是当他在遭受质疑时,更是无法规避对自我的批判性反思,显露人设空无的本相。人设如同海市蜃楼,人们自以为看到的是实景,实际上却是幻影。可见,在人设中,个体既是被凝视的对象,同时也是被质询的对象;是主体的非主体化,同时也是客体的主体化。主体面对他者的凝视由主转客,他者则在凝视中反客为主。在他者的凝视中,个体的人设会遭遇身份质询。原本人设是被包装、建构的自我,它可能不是无中生有,但却未必名实相副。它通过想象逻辑,完成了对个体的社会结构化,个体被重新建构,成了标签化的存在,因而也是利益化的存在。人设不是主体的彰显,而是主体的屈从。在人设构建的虚拟化主客体关系中,由于确立了一个被他者接受和认可的伪主体,真实的个体是以隐匿的方式躲避着他者。然而,一旦人设崩塌,个体就难逃他者的质询。所谓人设崩塌,实际上就是伪主体的去伪过程。由于个体自身的不小心或不检点,让他者发现其真相,从而还原成真实的个体自身。此时,个体却没有重回自我的喜悦,反而有被看穿真相的沮丧。
人设表明:当一个社会以它的方式要求于人,而不是以人的方式要求于社会的时候,个人其实是无抵抗的。从表面上看,它是个人对社会的主动因应,实际上它是个人另一种缴械投降的方式。它用出卖自己来满足他人的欲望,以千人一面的方式勾勒出固定脸谱戴在不同人的脸上。当一个人维护着自己的某种人设时,便同时接受着大他者的规训和他人的凝视:一方面在规训面前意识到自身的渺小,另一方面又在他人的凝视中洋洋自得。人设不是成为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个体,而是终于成为人们心目中期望他成为的样子。你是清纯的抑或是成熟的,是严肃的抑或是搞笑的,都取决于人们对你的角色定位。在一定的人设下,你不再是你,而是人们心目中的“他”;你也不再是主体,而是供人消费或消遣的客体。在人设中,对自我的主宰已让渡给大他者和他人,自我不过是在完成着一场人生的游戏,并且以非自我的方式游戏着人生。
面对我的人设,我自身也成为他者。我关注的不是我的样子,而是我在别人眼里的样子。从表面上看是我被他人凝视,实际上是我有意制造凝视。当人设把一切当成同谋时,自身便无所逃避。人设以其最鲜明的赤裸裸的方式表征着消费社会对人的社会化建构,是落在人身上的醒目的烙印(尽管个体本身并非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它反映的是景观社会中人的生产机制在它的控制下人的一切都成为一种利益的共谋和疯狂的表演。人被镶嵌于社会中,既可能被社会和盘托起,同时又可能被肆意踩踏。社会在追捧和叫好声中完成着对人的复制和粘贴:一个人的人设崩了,另一个人又会继起。社会从来不担心个体的沉浮,它担心的只是能否从中得利。人设的目的不是要使个体成为最好的自己,而是如何更好地成为别人眼中的你。人完全被虚化了:真实的自我隐而不见,膨胀的非自我却招摇过市。在人设建构中,公众意识以其独有方式渗透进个体意识,一方面它使个体自以为仍是主体,另一方面它又剥夺了个体的主体地位,以至于在社会生活中彼此都互认主体,却又谁都不是主体。这种公众意识在阿尔都塞那里称为“意识形态”,而在笔者看来它更是一种社会舆论——一个时代中暗流涌动的精神偏好。
人设是人的符号化表征。它是一张网也是一个陷阱,它将人锚定在一个固定的场域中,使人成为一个行走的符号。符号是文化内生的、固定化的,它反映了资本对于社会、生活,乃至于生命的复活与占有,凸显的是主体的对照关系而非显现关系。也就是说,人设并不是对个体主体地位的彰显,而是对主体与他者对照关系的悬设。人设归根结底遵循的是一种幻觉逻辑,在他者的凝视下个体成为客体,成为他者凝视的对象。个体通过镜像化的模仿和复制,在大他者(社会无意识话语)的注视下完成着浮夸式的表演。在拉康那里,自我等于小写他者的镜像投射,而主体则是自我在象征化中虚化为大写他者谋杀后的残迹。而在阿尔都塞那里,则直接成了大写他者(意识形态)对个人主体的强行复制,从而使拉康的大写他者转化为大写主体。但不论如何表述,都表明在当代社会,个体已经失去了它的自明性而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个体不仅成为社会建构的组成部分,而且在技术加速的时代不断强化着这一趋势。人设以个体被裹挟或屈从的方式,实现着向社会有意的、精致的镶嵌。人设如同历史跟人开的玩笑,个人以为那就是自己,他人以为那就是你,结果却全都不是。它是一种大家都以为的自以为是,是时代造就的迷雾和魅影,是个人与他人共同制造出来的另一个他者。借助这一虚幻他者,个人获得英雄般的满足,他人实现了自己的情感投射。此时,你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满足不同需求的符号。人设就像众人共酿的美酒,它的无形魔力既让众人迷醉,也吸引着众人为它痴狂。在人设世界里,他者完成着对另一个他者从身体到灵魂的探询和观照,同时也是对他们自身欲望的探询和观照。不仅如此,他者一旦沉迷其中,还会在共同制造的神奇里维护着神奇,在虚假中维护着虚假,从而使人设得到双重维护。
人设是数字时代制造出的虚假镜像。人设的维护离不开平台,而平台既是名利场,也是助推器。人设是借助数字化平台实现的人的镜像化的表演。如果说在拉康那里,大他者只是由语言和言说话语构成的象征性他者,而人类主体不过是被大他者暴力侵凌的伪主体,人不过是从小就开始走向的伪自我的镜像之舞,那么,在齐泽克那里则将它还原成了社会现实,人也同时摆脱了镜像,成为更实在的存在主体,尽管这一主体仍然不能摆脱伪主体的特性。他说:“简言之,这个‘大写他者’是对社会实体的称谓,是对所有下列事物的概括——由于它们的存在,主体从来无法完成支配自己行动的结果,也就是说,由于它们的存在,主体行为的最终结果总是它试图获得或预期获得的事物之外的某物。”[8]253
人设是资本进入个体生命的一种投射方式。在现代社会,任何人都无法摆脱他人的注视,成为众人之看。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就曾将女人称作被凝视的性别。当我被他人注视时,我就成为他人注视的对象,他人就成为我对象化的条件。于是我在他人的注视中就成为他人眼中的我,而不再是本真的存在。我自以为仍然是为我的存在,却实际上已成为为他的存在。正如萨特所言:“我既不知道我是什么人,也不知道我在世界上的位置是什么。”[9]355虽然我与他人共在,但我却消逝不见了。在资本统摄的世界,资本主宰着一切,当个体感觉无力或无心与资本抗衡时,便与资本同谋。人设便是个体与资本合谋的产物。我们今天在网络媒体上到处可见的各种直播网红,维持着不同的人设,满足着人们不同的猎奇心理以及不同顾客(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因此,从资本逻辑来看,它不过是人的价值的一种精心布展,目的是为了提升人的交换价值,获得更多的商业利益。
人设通过镜像化构建了一个理想型自我,并且完成了小他者向大他者的屈从和被结构化的塑造。一旦形成虚拟化的人设,人就成了实在的镜像。它既被自己凝视,也被他人凝视。任何人设都不是一时的头脑发热,而是精心的预谋。人设背后的创新创造都是被结构化的。因而,一种新人设代替旧人设就成为必然。它要不断迎合不同他者的口味,并且密切注意他者的兴趣动向。人设总是不断以不同的方式博取他人的眼球,赢得他人的关注。在流量经济时代,流量便是财富。为了获得更多的流量和财富,人设背后的资本总是无孔不入,敏锐地捕捉着人们的目光,从而形成新的聚焦点。
人设所制造的种种迷幻,表面上光怪陆离,但实则资本才是最终的谜底。一切都因资本而起,由资本推动,也因资本而灭。被符号制造出来的消费社会的资本逻辑成为人们的日常法则。在人设世界中,个体越来越成为景观社会中的景观,而不是真正的活生生的人。人们必须直面景观社会的生产机制以及它对人的控制。当个体一旦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取得成功时,似乎一切就开始反转:“我”成了一个被制造出来的、能够吸引流量的标签,一旦这一标签获得公众认可和接受,即便是生活的日常,“我”也会成为资本暗流涌动的无形生产线上的有形符号。即使个体不愿被裹挟进资本的洪流,面对它的汹涌恣肆,每个人都很难独善其身、置身事外。
三、人格与人设的遭遇:自我的奥秘
从上可知,人设不是单纯的个体随意行为,而是具有社会结构性。如果说人设是一场游戏和表演的话,那么,它就是一场有预谋的、利益化的游戏和表演。它是利益个体与利益群体的共谋,也是个体的我与社会、资本的合谋。人设是个人对社会在想象中完成的结构性反应,而这种想象在经过包装和渲染之后又跳出了想象落入世俗的尘埃,并且公然为利益站台。通过人设,一个个影视明星、歌星或网红等等构建起各不相同且相对固定的公众形象,并且通过维持这个形象使不同利益者从中得利。为了能够获得公众的认可和追捧,人设总是以一种浮夸乖离的方式表现着个体,致使个体虚假的一面被无限放大甚至扭曲。我们很难对人设进行纯道德性的评判,但可以确定的是,人设往往带有极强的目的性,即它的逐利性。人设通过形象的设计和维护,以夸张的手法不断吸引着公众的眼球,引起公众注意,并通过这种注意来获得流量,进而获利。所以,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无论是公司还是艺人都拼命维护着人设,不使个人的声誉受损、群体的利益受损。人设的商业特性使得它总是试图以正面形象示人,这既带有一定的欺骗性和隐蔽性,同时也留下了人设崩塌的隐患,这意味着人设的维护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在公众面前,艺人要注意自己的形象以及言谈举止,要小心翼翼地遵循着商业运作模式行事,一旦出格就会受到公众的惩罚。人设如同一个“善意的谎言”,只要这个谎言不被戳穿,它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创造商业价值,带来商业利润。因此,不论人设的表现形式如何,是“清纯”人设还是“成熟”人设,是“硬汉”人设还是“柔情”人设,其本质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为了获得稳定的商业利益,实现其商业价值。
诚然,从人格的原意上来说,它也具有面具的意思,但是,人设与人格相比显然更具有面具的意味,而人格则是跟人的存在规定性相关。人格是在任何情况下,个体努力维护的一份做人的尊严,人设则是竭力使个体成为别人消费和娱乐的对象。作为回报,个体赢得了关注,获得了利益,这恰恰是与人格精神相违背的。所以,人设至多只能被看作一种人格的变种,它设立的目的就是供出卖的,是为了帮助人“卖笑”。人设从来代替不了人格,尽管它有时似乎充当了人格的角色。人设是虚构出来的、对人的某一特质的无限放大,而他人则配合着他去完成这一角色定位。我们看到的人设越多,人格也就越少。人设遵循的是幻觉逻辑,越是虚幻越是真实;而人格则是真实的,是人身上具有的人之为人的规定。
人设的主要特征是:它是对个体的美化和凸显,从而使个体显得与众不同。它通过异乎寻常的方式和耐心维护着一个虚幻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体自身的范围,而具有了社会结构性。它是社会群体在资本和利益推动下合谋的产物。
人设的悖论在于:它似乎在维护着什么却又在失去着什么,只要个体维持着自己的人设不致崩塌,他就会被人尊崇,更重要的是从中获利。然而,个体所拼命维护的东西却未必是真正属于他的东西,那是因利益的共谋加诸其上的,而不就是他自身。人从此不再是实在生命的真实存在,而是具有了象征意味,成了无主体的符号链条上的一环和象征性存在。在它的背后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欲望的涌动,无论是群体还是个体,欲望占有了人类并肆虐着人类。人设不同于人格,但一旦人设崩塌,却会牵涉到对人格的评判。
撩开人设加诸人身上的层层面纱,我们是否还能找寻到真实的自我?在被别人娱乐和消费时,我们是否还能保全自我,赢得尊重?能够回答这一问题的,或许不是个人,而是社会,是制造人设同时又推动人设的看不见的无形之手和无形之力。当我们为社会量身定做自己时,我们成为的不可能是自己的样子,而是社会要求和期望的样子;当我们自己按照自己的心意创造更好的自己时,我们不需要人设的加持和包装。如果说在疫情时代健康码是对个体身体的俘获,人设则是对个体精神的俘获。无论是生命政治还是文化建构,它们都把人召唤为客体,实现着角色预定。因此,身在一个人设化的社会,个体想要实现非客体化,就必须主动质询自己身份的真实性,是否是自己所具有的。人身在世俗中而不世俗终究要靠人自己对人自身生而为人的持有,这份持有便是人格。而倘若失去人格,人设崩塌便是迟早的事。但愿有一天,当我们无意中回望镜像,我们发现原来我还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