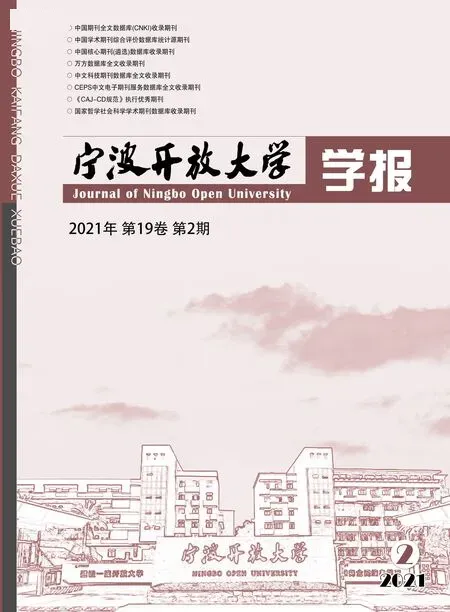青少年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的关系问题研究
2021-12-24任娟娟
任娟娟
(西北政法大学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陕西 西安 730000)
所谓网络欺凌,是指蓄意、恶意并重复采用信息通讯技术(ICT)来中伤、羞辱以及(或者)操纵以及(或者)排斥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1]75。总体来看,虽然青少年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的本质相同,且两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共发性或连贯性,但由于发生场域殊异,网络欺凌又具有一些与传统欺凌明显不同的新特征。因此,在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厘清青少年传统欺凌与网络欺凌的联系与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把握网络欺凌的本质与特征,是对其进行有效规制的前提。基于此,在青少年网络欺凌研究领域,有关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的关系问题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基础议题。在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虽然网络社会学界一直存在着“创新说”与“延伸说”之分,但更多的学者仍倾向于认为网络社会源于现实社会,但又异于现实社会,前者是后者在网络空间的延伸与变异[2]。本文尝试从网络社会学有关虚实关系问题的基础共识出发,对青少年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
一、网络欺凌是传统欺凌在网络空间的延伸
当面欺凌和网络欺凌涉及许多相同的人,二者拥有更多的相同点而不是不同点[3]。网络欺凌至少在欺凌要素、根本诱因、欺凌角色的复合性及被欺凌者应对方式等几个重要方面实现了对传统欺凌的移植,其边界延伸至虚拟的网络空间之中。
(一)欺凌要素的共同性
无论发生在何地,以何种面貌出现,欺凌就是欺凌,其本质相同。所以,尽管不同的研究者对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的界定并不完全一致,但大多数研究者在欺凌行为的构成要素上已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上达成广泛一致:第一,欺凌双方存在强弱失衡,即:欺凌者往往在力量、心理、关系或网络技术驾驭等方面强于受欺凌者,欺凌过程呈现明显的恃强凌弱、以大欺小、以众欺寡的特征;第二,欺凌行为的蓄意性或恶意性,即:欺凌行为并非偶然发生,而是欺凌者故意谋划的结果;第三,欺凌行为的攻击性,即:欺凌过程伴随着推搡、击打、嘲弄、侮辱、诽谤、恐吓、隐私信息曝光、孤立、排斥、骚扰、财物破坏、抢劫、敲诈勒索等形式的敌对或攻击行为;第四,欺凌行为的重复性,即:欺凌行为并非仅发生一次,而是在某个时间段内反复发生;第五,欺凌行为的伤害性,即:欺凌行为对欺凌的相关主体——欺凌者、被欺凌者和旁观者——均产生不同程度的伤害或威胁。构成欺凌的上述要素决定了无论是何种形式的欺凌,也无论是何种程度的欺凌,其本质都是侮辱性的残忍行为[4],需要被作为反社会行为来认真关注、思考和处理。
(二)欺凌诱因的共同性
对传统校园欺凌的诸多案例进行分析可见,青少年之间的口角、玩笑、碰撞、经济纠葛等偶发事件或微不足道的琐事是绝大部分校园欺凌事件发生的直接诱因。此外,网络成瘾引发的敲诈勒索、网络暴力游戏引发的行为模仿,恋爱引发的情感纠纷以及社会团伙的教唆等因素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校园欺凌事件的发生。总体来看,青少年网络欺凌的诱因呈现模糊化、游戏化和琐事化[5]。对比可见,虽然网络欺凌因发生情境的特殊性而在诱因方面有所不同,如网络的去抑制性可能强化网络欺凌[6],网络的便捷性可能触发网络欺凌等。但总体而言,青少年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产生的诱因具有更多同质性,而非异质性。首先,欺凌的直接诱因。正如贾斯汀W.帕钦(Justin W.Patchin)在其研究中指出的,无论欺凌发生在哪里,其原因都是相似的,欺凌事件的主要导火索仍然来源于学校[7]30。针对网络欺凌的研究亦指出,凡受到网络欺负的人,都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过校园欺负,而且大部分的网络攻击的理由都来源于日常生活[8]。因此可以说,青少年因为日常学习、生活中的龃龉、矛盾和冲突而选择通过欺凌他人释放压力、宣泄情绪、表现自我或打击报复等是导致该群体欺凌行为频发的主要的直接诱因。其次,欺凌的根本诱因。发生时空的殊异仅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扩大或抑制欺凌行为的作用,但两类欺凌背后的行为主体的同一性决定了根本诱因的一致性。詹姆斯E.狄龙(James E.Dillon)在分析欺凌行为时指出,隐藏角色——成熟过程中的青少年的大脑——对欺凌行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一角色解释了为何学生们不能很好地分辨是非、对他人的感受如此淡漠;解释了学生对世界的看法为何有别于成人,以及为何要把他们视为“半成品”,要比成年人得到更多的关注[9]。处于人生风暴期的青少年,其在生理、心理、道德发展、人格发展及社会交往等方面的不成熟、不稳定,往往导致其无法以恰当的方式处理与同辈、异性,甚至是陌生网友等人群的关系。同时,在其所嵌入的外部社会环境,包括家庭、学校、社区、社会等相关主体未能提供及时、有效的教育、引导和监督的情况下,部分青少年便容易因为认同青少年帮派亚文化或犯罪亚文化、屈从于群体压力、内化外部群体为其贴上的负面标签、在与不良或严重不良行为青少年进行接触的过程中进行模仿和学习、基于对被欺凌者的性别、性取向、种族、信仰、残疾、体重、相貌、身体能力、心智水平或社会地位等所形成的歧视或偏见,以及希望通过欺凌他人赢得同辈群体的认同与尊重而出现不同程度的欺凌或暴力行为。
(三)欺凌角色的复合性
青少年群体中存在一定比例的“复合欺凌”现象,也即:传统欺凌与网络欺凌在某些青少年身上同时发生,从而导致两类欺凌中的主客体角色交叠或复合的情况。首先,传统欺凌的施害者与受害者很可能转换为网络欺凌的施害者与受害者。针对陕西省青少年网络欺凌问题的问卷调查也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中,有13.9%的受访者曾同时遭受过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有2.5%的受访者曾同时实施过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同时,对网络欺凌的受害者与施害者所进行的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发现,有30.1%的受害者表示同时遭受过来自欺凌者的网络欺凌和传统欺凌,有45.5%的施害者表示同时实施过针对被欺凌者的网络欺凌和传统欺凌。此外,黎亚军对青少年网络受欺负与传统受欺负的共发性的实证研究也显示,两者之间具有较强的共发性,69.4%的网络受欺负者同时是传统受欺负者[10]。其次,传统欺凌的欺凌者亦会转换为网络欺凌的欺凌者或受欺凌者,而传统欺凌的受欺凌者亦可能转换为网络欺凌的受欺凌者或欺凌者。例如,贾斯汀·帕钦等人指出,当面欺凌别人的青少年在网络上遭受或实施欺凌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两倍多,当面遭受欺凌的孩子受到网络欺凌的可能性几乎是其他人的三倍[11]7。此外,另一项调查显示,传统欺凌中,有超过33.0%的被欺凌者和27.3%的欺凌者遭受过网络欺凌,有16.7%的被欺凌者和30%的欺凌者同时也是网络欺凌者[12]。欺凌角色的复合性表明,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确实涉及更多相同的人,即:两类欺凌的主客体基本相同。
(四)被欺凌者应对方式的共同性
大多数传统欺凌和网络欺凌的受害者在面对欺凌伤害时选择隐忍,即使选择向外求助,大部分受害者也会优先选择向同学、朋友甚至是网友求助,而选择向家人、老师等成年人保持沉默。阿代尔等人以新西兰为基础的研究指出,仅有21.0%的欺凌被报告给教师以及(或者)其他成年人[13]52-53。刘晓梅对天津17所学校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近七成受到校园欺凌的学生并没有将自己所遭遇的暴力告诉老师、家长,也没有向警方报告,而是选择了忍耐和沉默[14];网络欺凌方面,针对陕西省青少年网络欺凌问题的问卷调查显示,有60.8%的被调查者在遭受网络欺凌后出现了求助行为,同学、朋友和网友被求助的次数占总选择次数的76.0%,家人和老师仅占32.4%。江文等在其研究中报告的此类数据分别为63.2%和34.5%[15]。杨巧、陈祉诺所开展的质性研究也有类似发现,网络欺凌的受害者会碍于情面、对父母限制自己上网的担忧,以及对学校和老师在处理网络欺凌事件上的策略的无效性的认识等方面的原因,而选择对其保持沉默[16]。遭受欺凌的青少年对欺凌行为的默然应对,在强化欺凌行为的隐蔽性的同时,弱化了欺凌问题的严重性;而家长、老师等重要成年人在青少年欺凌行为应对过程中的普遍缺位,则在显著地弱化被欺凌者的社会支持系统的同时,强化了欺凌问题规制的困难性。
二、网络欺凌是传统欺凌在网络空间的变异
作为发生在虚拟、流动、匿名、去中心的网络空间中的欺凌行为,网络欺凌因其发生场域的殊异而在发生时空、力量对比原则、主客体的熟识程度、角色转换的可能性、旁观者施加影响的可能性、欺凌的形式、欺凌的危害程度以及规制的困难性等几个不同侧面实现了对传统欺凌的挑战,使其成功地具有了一些新面貌。
(一)发生的时空不同
青少年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发生的时空殊异。已有研究表明,传统校园欺凌主要发生在课间、就寝时间、午饭时间、上学前后、乘坐校车期间等有限的时间节点,并主要发生在操场、教室、走廊、食堂、洗手间、宿舍、学校门口及校园周边等家长、老师和其他学校管理人员无法实施有效监管的相对隐蔽的现实物理空间。与之不同的是,网络欺凌具有明显的网络或电子属性,其主要利用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以及其他新型的电子交流工具实施,并发生在不受上述具体时间和物理空间限制,只要能够顺利利用网络便可随时进入的虚拟的网络空间之中。
(二)力量对比的原则不同
青少年传统欺凌与网络欺凌均存在欺凌双方的强弱失衡现象,即:欺凌者与被欺凌者在力量或影响力方面的不平衡现象。但不同点在于,两者在强弱失衡的基本维度——力量对比的基本原则——上存在明显不同。传统欺凌的强弱失衡往往指的是欺凌双方在身体素质、语言能力、社会地位等方面存在明显的不均衡。由于其发生时空迥异,传统的力量原则在虚拟的网络环境中面临挑战。在网络欺凌中,基于网络技术驾驭能力的高低、网络社交圈子的大小,以及网络互动程度的深浅等方面的差异而导致新的失衡,并赋予力量原则新的含义。
(三)主客体的熟识程度不同
传统欺凌是一种当面欺凌,因此,欺凌者清楚地知道自己对谁实施了欺凌,被欺凌者亦明白无误地知道是谁实施了针对自己的欺凌。然而,由于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上述在传统欺凌中不言自明的信息在网络欺凌中却变得的模糊不清、难以把握。网络欺凌的受害者并不一定清楚是谁在欺负自己,而网络欺凌的施害者亦有可能并不清楚自己对谁实施了欺凌。针对陕西省青少年网络欺凌问题所进行的实证调查便显示,有41.8%的被欺凌者不认识欺凌者或不清楚自己认识不认识欺凌者,同时,也有66.5%的欺凌者表示不认识欺凌者或不清楚自己认识不认识被欺凌者。由此可见,与传统欺凌相比,网络欺凌中的主客体的熟识程度明显较低。
(四)角色转换的可能性不同
在传统欺凌中,由于欺凌者与被欺凌者之间在生理、心理、社会关系等方面力量对比悬殊,因此要实现角色转换绝非易事。但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这种力量或演化为不受限制的数字技术,或来自于网络上的声望和影响力,或来自于网络上的先发制人,或仅仅来自于网络本身的匿名性[17],从而使得欺凌者与被欺凌者之间的角色转换变得相对容易。有研究指出,以往不同年龄段可能表现为不同的欺凌行为,但在网络上,欺凌行为的持续传播会跨越年龄的限制,被不同的人群复制和模仿,从而可能会循环出现。网络欺凌的循环往复让欺凌者和被欺凌者可能快速转换。有研究证明,实施网络欺凌者成为被欺凌者的风险是其他人的20倍[18]。
(五)旁观者施加影响的可能性不同
旁观者是指欺负事件的知情者、目睹者及干预者(包括帮助受害者,也包括帮助施暴者),根据其行为类型可以分为四类:协同欺负者、煽风点火者、置身事外者和保护制止者[19]。旁观者的行为选择在欺凌行为的扩大或抑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针对陕西省青少年网络欺凌问题所进行的实证调查显示,当目睹网络欺凌时,有42.5%的受访者选择既不参与也不干预、有50.1%的受访者选择帮助被欺凌者,有2.1%的受访者选择协助欺凌者。而当目睹传统校园欺凌时,受访者在上述三类选项上所作的选择则分别占到了总选择次数的37.4%、59.2%和2.2%。对数据进行对比可见,两类欺凌的旁观者中均有略超过半数的人表示曾对受害者施以援手,但相比较而言,网络欺凌的旁观者采取积极的施助行为的可能性要低于传统欺凌,采取消极的旁观态度的可能性则要大于传统欺凌。凯利 狄龙(Kelly Dillon)和布拉德 布什曼(Brad Bushman)对人们在在线聊天室中看到网络欺凌时是否愿意进行直接干预的研究也显示,仅有10%注意到欺凌行为的参与者进行了直接干预(通过发送信息给攻击者,或通过联系群主的方式[20]。究其原因:第一,网络欺凌所导致的伤害的不可见性或难于察觉性,可能大大降低了网络欺凌的旁观者对被欺凌者因遭受欺凌而承受的痛苦、伤害或不幸的感知水平;第二,网络欺凌数量众多的旁观者的存在可能导致更为明显的责任旁寄与责任解构[21]现象的出现;第三,网络空间的流动性、异质性,尤其是网络交往中普遍存在的陌生人关系,可能导致网络欺凌的旁观者在能力感、控制感、安全感、关系感和支持感的明显弱化,从而可能促使其采取更为消极、冷漠的方式对待被欺凌者。
(六)欺凌的主要形式不同
传统欺凌的形式多样,既有生理欺凌(也称直接欺凌或攻击),也有心理欺凌(也称间接欺凌或攻击),前者致力于给目标人物造成身体伤害或财物损害,后者则重点对其进行内部攻击[22]14-16,针对陕西省青少年网络欺凌问题所进行的实证调查显示,无论是遭受、实施,还是目睹过校园欺凌的受访者,均表示“挖苦嘲弄、侮辱责骂、疏远孤立及散布流言蜚语”等心理欺凌形式是青少年最为频繁使用的校园欺凌形式。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之中,由于行动者身体的不在场或曰缺场,导致基于生理的直接欺凌难以出现,从而使得心理欺凌成为青少年网络欺凌的绝对形式。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样,网络是人性的实验室,从本质上来看网络欺负是一种心理虐待[23]。由此可见,无论是在传统欺凌还是网络欺凌中,心理欺凌均为欺凌的主要形式。但区别在于:第一,与传统的心理欺凌形式相比,网络欺凌依托虚拟的网络空间,萌生了包括网络辱骂、网络骚扰、网络追踪、在线孤立、网络论战、网络威胁、网络敲诈、披露隐私、网络诋毁、网络伪装等在内的更为复杂、多元的心理欺凌形式;第二,在传统欺凌事件中,生理欺凌与心理欺凌常常以不同程度地组合发生,往往伴随直接的生理伤害,且“殴打”在遭受、实施和目睹校园欺凌的受访者的选择中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但在网络欺凌事件中,生理欺凌与心理欺凌组合发生的情况并不常见,生理伤害通常可能只是心理欺凌产生的间接后果。然而,在两类形式的欺凌组合发生的事件中,被欺凌者往往遭受了严重或相当严重的身体攻击,这类行为往往已溢出欺凌的界限,成为犯罪行为。
(七)欺凌的危害程度不同
青少年网络欺凌与传统欺凌均后果消极、影响负面,其不仅给受害者带来身体伤害和心理创伤,而且给旁观者带来不良示范和心理压力,同时亦增加了欺凌者因自身的欺凌行为而遭受报复、谴责、惩处,以及未来出现更为暴力的反社会行为的风险。但正如坎贝尔(Campbell)、斯皮尔斯(Spears)等所指出的那样:虽然那些被当面欺凌过的学生说,欺凌对他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比那些受到网络欺凌的人受到的影响更加残酷和难以忍受,但从他们的心理健康水平来看,网络欺凌的受害者比当面欺凌的受害者具有更多的社会问题,也更加焦虑和沮丧[24]。可能的原因在于:(1)网络欺凌的实施不受时间、地点限制,欺凌者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受害者实施网络欺凌。由于被欺凌者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都可能收到恶意的短信、邮件、视频等,这种持续不断又无法躲避的欺负行为,会给受欺负者带来更严重的心理折磨[25];(2)网络表达的随意性,网络言论的难于消除性、以及网络伤害的不易察觉性,使得欺凌者可能采取更为残酷的方式对待被欺凌者,并必然因此使被欺凌者遭受比传统欺凌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3)在流动的网络空间之中,可能会有无限多的受众在极短的时间内即通过简单的鼠标点击了解、甚至是参与网络欺凌事件,其所暗含的被疯狂传播、人尽皆知以及叠加欺凌的风险,使得网络欺凌的危害无限膨胀,并因此急遽加剧了受害者的心理痛苦。
(八)规制的困难程度不同
传统欺凌与网络欺凌均难以进行有效规制,但网络欺凌规制的难度更大,原因在于:首先,网络欺凌的高隐蔽性导致规制难度增加。与传统欺凌相比,网络欺凌更难识别。一方面,基于“担心父母可能因此限制自己上网”“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被欺凌这件事”及“自己能够应对解决”等方面的考虑,网络欺凌的受害者在面对欺凌或攻击行为时往往不愿将可能、正在或已经发生的网络欺凌事件告诉成年人;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欺凌行为所具有的显而易见的偏差性和越轨性,欺凌者往往以匿名或身份伪装方式实施欺凌,因此,即便网络欺凌的受害者及时告知了网络欺凌事件,相关机构或主体也很难及时,甚至根本无法找到欺凌者。当网络欺凌事件发生时,网络欺凌的主客体双方的双向隐匿必然在增加网络欺凌的识别难度的同时增加规制的难度。其次,重要成年人在帮助青少年应对网络欺凌过程中的缺位导致规制难度增加。由于对网络欺凌存在的可能的认识偏差、时间精力不足,以及网络技术有限等原因,家人、老师等重要成年人在帮助青少年应对网络欺凌方面作用相对有限。再次,现有的规制策略的效力有限。我国当前针对青少年欺凌问题的规制策略仍主要集中在传统校园欺凌领域,尚未能在虑及网络欺凌的普遍性、特殊性的基础上制定系统且具有针对性的规制策略。因而,即便对少量被知晓的网络欺凌事件进行处理时,也往往因为规制策略缺乏针对性而无法对欺凌事件的实施者、受害者等相关主体采取应有的惩戒或及时有效的救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