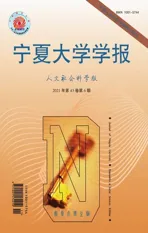《元刊杂剧三十种》研究述评
2021-12-24宋百惠杨宝春
宋百惠,杨宝春
(青岛大学 文学院,山东 青岛 266071)
《元刊杂剧三十种》原书无名,清代藏书家黄丕烈定其名为《元刻古今杂剧》。1914 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请著名的湖北刻书人陶子麟加以复刻,以《覆元椠古今杂剧三十种》之名刊印出版,并附(日)狩野直喜序文。1924 年上海中国书店据日本复刻本照相石印以《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为名出版,石印时经由王国维对剧目作者进行了考定,重新排列次序,并撰《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一文,该书逐渐为中国学者所关注。1958 年,《古本戏曲丛刊》第四集将元刊本影印收入,题名为当今沿用之名《元刊杂剧三十种》,该书现存于国家图书馆。《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研究主要涉及校勘、版本、文学、舞台四个层面。
一 《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校勘研究
《元刊杂剧三十种》出自坊刊,仇校不精,讹误实多,加上翻印、仿刻和年代久远等种种因素,增加了阅读困难,因而对《元刊杂剧三十种》进行校勘整理,是元刊杂剧研究的最初一步。
1935 年,中国杂志公司陆续出版了由卢冀野编选的8 册《元人杂剧全集》,该书收录了《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11 种杂剧,卢氏对其进行了简单的校正。1958 年中华书局出版隋树森《元曲选外编》,收录了《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14 个孤本。1958 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吴晓铃等编校的《关汉卿戏曲集》、1976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关汉卿戏剧集》,这两部戏曲集对《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关汉卿的3 种孤本杂剧进行了校订。1958 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编《关汉卿戏曲选》、王玉章编《元人杂剧选》以及邵曾祺编《元人杂剧》对入选的元杂剧在校订时也参考了元刊本。以上是对《元刊杂剧三十种》进行整理校订的初步成果,它们都不是全面的校勘,仅涉及其中的部分剧目。
对《元刊杂剧三十种》进行全面校勘整理的是郑骞、徐沁君、宁希元三人,校勘成果分别是1962年世界书局出版的郑骞著《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1980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徐沁君著《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1988 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宁希元著《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郑骞先生的《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是该书的第一个全面校勘本,该校本以日本京都大学的覆元椠本为底本,郑氏本在书前载有《校订凡例》二十条,在每剧后附载《校勘记》,该书校勘细致,依照明代版本校订格律、增补曲文,并将元刊杂剧的体制面貌进行规范化整理。在校订这三十种杂剧时,郑骞根据《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中《王粲登楼》一剧上的校记,整理出一本在元末流传的《王粲登楼》剧的节略本,附录在书后,这对今天的元杂剧原貌研究可谓意义重大,然该书最大的缺憾是以复刻本为底本。徐沁君的《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晚出,因人事阻隔,在校勘中并未参考郑本。徐本书前有《校订说明》和《入校版本》,对该书体例和入校版本予以详细说明。每剧之前有剧情说明和剧中人物表,以备阅读参考,每折之后附有《校记》。徐本是徐沁君在不知台湾地区郑本已出的情况下,大陆方面出版的第一个全面校勘本,因而徐本和郑本一样都具有历史开创意义。宁希元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新校》出版颇有曲折,该书于1980 年完稿并交付出版社,但当时正值中华书局即将出版徐沁君的《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一书,于是出版事宜暂时被搁置,直至1988 年才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宁本的书前有王季思序、吴小如序和自序,每剧之后附有校勘记,其中包括剧情简介和剧情来源等。除“三十种”之外,参考郑骞之意,将《王粲登楼》一剧重加校订,附于全书之后。宁希元在校勘中极为重视审音正读和书写符号的辨认工作。在长期校勘中,他概括出字音通假和字形简化的通例,运用这些通例解决了大量的校勘问题。同时由于郑本、徐本的刊出,使他能够有所比较选择,从而博收广取,后来居上。
经过郑、徐、宁三家的全书校勘,此书的阅读障碍得以基本扫清,为后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三家都只注意校勘,没有注释和疏义。此外,三家校本从本质来说,与臧懋循修订《元曲选》并无二致,都带有鲜明的文人雅化色彩,然而,这种文人的雅化一定程度上是与元本的通俗属性相背离的。
在《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多种校勘本出版前后,学界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它们对《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校勘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1980 年,王季思《怎样校订、评价〈单刀会〉和〈双赴梦〉:与刘靖之先生商榷》一文,对刘靖之《关汉卿三国故事杂剧研究》中的《单刀会》曲文的校勘提出了四点可商榷处,对《双赴梦》提出了十四点可商榷之处;1981 年,隋树森《读〈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和张增元《〈新校元刊三十种〉补》对徐沁君《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疏失之处进行了详细说明;1982 年宁希元《〈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文字待勘符号的辨正》和1983 年徐沁君《〈元刊杂剧三十种〉校勘举例》分别为自己的校勘本做了校勘说明;1987 年,李崇兴将《古本戏曲丛刊》四集影印的《元刊杂剧三十种》和郑本、徐本核对,发现徐本仍有一些可商榷之处,作《〈新校元刊杂剧三十种〉商榷》一文。21 世纪以来,仍有一些零散的校勘辨正,如许巧云《〈元刊杂剧三十种〉校勘释例三则》(《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年第6 期)、许巧云《〈元刊杂剧三十种〉及其校勘释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 年第3 期)、许并生《元刊杂剧〈诈妮子调风月〉会校疏证及元杂剧原貌考论》(《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4期)、孙改霞《〈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圈符意义探微》(《文化遗产》,2014 年第5 期)、张莹莹《〈元刊杂剧三十种〉校读札记五则》(《古籍研究》,2019 年第2 期)等。校书如扫落叶亦如扫尘,将《元刊杂剧三十种》这样一本十分粗糙之书校勘得无一处疏漏,确实是件很难的事,上述论文将《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校勘进一步细化,使《元刊杂剧三十种》呈现出更清晰的面目。
日本的《元刊杂剧三十种》校勘整理与研究成果斐然,已经有约四十年的历史。目前共校出15种,分别为《拜月亭》《任风子》《赵氏孤儿》《看钱奴》《薛仁贵》《汗衫记》《老生儿》《调风月》《三夺槊》《气英布》《西蜀梦》《单刀会》《贬夜郎》《介子推》《范张鸡黍》。日本学者所作的校订、整理工作较为规范细致,其研究团队结构合理,具有优秀的传承传统,以田中谦二为始,高桥繁树、井上泰山、金文京等参与校勘,渗透着三代学者的心血。传统小说知识的欠缺是日本学者的不足之处,由此造成了一些误校、误注,但日本方面的元刊杂剧校本仍然称得上是优秀的校本。由于种种原因,日本方面的校勘成果,目前在中国并不多见,相关情况可参照焦浩《日本的〈元刊杂剧三十种〉研究》(《艺术百家》2019 年第2 期)一文。
二 《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版本研究
学者们在研究《元刊杂剧三十种》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即: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该书为何被刊刻发行,为谁刊刻?关于元刊本杂剧的版本性质,学界观点繁多。然而,由于刻本本身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这方面的戏曲史料也很匮乏,因此难成定论。此外,部分学者对《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版本谜团存而不论,将关注点放在不同版本的差异比较上,形成了版本比较研究的热潮。
(一)《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版本性质
最早对《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版本进行定性的是王国维,他在《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中提出“民间坊本说”。关于刊刻时间,在考订《大都新编关张双赴西蜀梦》时云:“此剧刊板出于元季”[1]。关于刊刻地,文章结尾称,三十种杂剧,虽剧本题写的刊刻地不同、字形大小不一,“然其纸墨与版式大小,大略相同,知仍是元季一处汇刊。其署大都新刊或古杭新刊者,乃仍旧本标题耳”[2]。总而言之,王国维认为《元刊杂剧三十种》是元代的民间坊刻本,刊刻地应为一地,但有意标榜大都或古杭新刊。王国维对自己的观点并未作出适当解释,因而自此之后,元刊杂剧的版本性质问题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和讨论。
首先,元刊杂剧刊刻于元代,得到了学界大多数学者的肯定,但也有少数质疑的声音。最先对此提出异议的是小松谦、金文京等日本学者,其《试论〈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版本性质》(《文化遗产》2008 年第2 期)指出,《陈抟高卧》剧中有作者马致远之后才出现的元末大儒吴澄的谥号,认为这部分应系元末改写的,并且通过复刻、补刻的痕迹推断,“元刊三十种”大约是在元明间印行的。这一说法得到一些学者的响应,张倩倩的《〈元刊杂剧三十种〉并非刻于元代说》(《文艺评论》,2015 年第12 期)即沿着小松谦的思路,通过词句互证(例如《公孙汗衫记》正末唱词以“凤城”称南京,而南京在元代并未称都,建都乃明朝之事)、文献互校(版式接近于明初刊本)进一步得出其非元刻的结论。
其次,民间坊本说代表了学界对于元刊杂剧性质的传统观点,长期被人认可,但很多学者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有三个:台湾地区学者汪诗珮在博士论文《从元刊本重探元杂剧——以版本、体制、剧场三个面向为范畴》中将“坊本说”具体为“建本说”;杜海军《〈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刻本性质及戏曲史意义》(《艺术百家》,2010 年第1 期)提出“剧团自刻本”说;方彦寿在《〈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刻本性质与刊刻地点另议》(《艺术百家》,2011 年第3 期)一文以杜海军和汪诗珮的观点为基础,作了一个相对圆通的解释:“从刻本性质来说,《元刊杂剧三十种》是元代民间私家刻本;从生产单位来说,《元刊杂剧三十种》又是元代民间私家(剧团)委托建阳书坊刊行的特殊的‘建本’”[3]。
再次,三十种杂剧究竟是同一时地、同一书坊刊刻,还是分别刻于不同书坊,后由人结集成册,也是有争议的。王国维认为《元刊杂剧三十种》是汇刊本,但他对此亦不十分确定,其后郑骞认为这部书是“书坊杂凑而成的本子”[4]。目前多数学者认同此观点,并试图根据不同的版式和总体特征将三十种杂剧进行分组,每一组为一个书坊刊刻,最后得出四个书坊、九个书坊、十四书坊等结论。但由于辅助证据不足,加之每组分类特征并不具备完全的排他性,因此所得结论仅为缺少说服力的一家之说,但这种分类仍可视为一种有价值的尝试。
最后,关于元刊杂剧为何会刊印及其功用,学者们进行了大胆猜测,主要有以下观点:第一,元刊杂剧的受众是观众,它的主要作用是帮助观众听清唱词,理解剧情。狩野直喜在京都帝国大学复刻本《覆元椠古今杂剧三十种》的序中, 将其定性为观众观剧时阅读用的小册子;中国学者如李大珂《元刊杂剧的价值》(《戏曲研究》第2 辑,1980年)、甄炜旎《〈元刊杂剧三十种〉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年)等也持此观点。第二,元刊杂剧的面向群体是演员,它或是演员舞台演出的提示本,可参见孔杰斌《元杂剧的明代改编本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年);或是艺人用于学唱的掌记本,可参见徐扶明《元代杂剧是怎样演出的》(《文史知识》,1985 年第3 期);或是师傅给正角教戏时所用的本子,可参见洛地《关目为本、曲为本、掌记为本、正为本——元刊本中的“咱”“了”及其所谓“本”》(《中华戏曲》,1988 年第1 辑)。第三,元刊杂剧不是作家写作的稿本,而是演员们舞台演出的记录本、台本。王季思的《辨析元明间失名剧本的初步设想》(《戏剧艺术》,1987 年第2 期)、赵天为的《从选本看元杂剧之流变》(《求索》,2010 年第12 期)等文章都持这种观点,宋常立在《元杂剧的编创方式: 作家与伶人协同创作》(《河北学刊》,2013 年第6 期)一文中更是认为,作为一种舞台表演艺术,元杂剧的每一次演出都不会是完全一样的,因而作为演出记录本的《元刊杂剧三十种》,实际上是不知经过伶人多少次改进过的“台本”。第四,元刊杂剧是文学读物。许并生在《元刊杂剧〈诈妮子调风月〉会校疏证及元杂剧原貌考论》(《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4 期)一文中持此观点,他认为元刊本只录曲文,有可能是文人按照当时的演剧来谱写乐府,形成文学产品,还可能是由于书坊有意为之,为了卖于文人。此外,张倩倩在《元杂剧版本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8 年)一文中提出了较为中庸的观点,将《元刊杂剧三十种》定性为第一批由剧团掌记抄本向案头阅读转变的杂剧文学读物,它既保存了较多的舞台表演特征,又适应了普通大众阅读的需要。
目前学界较为普遍的看法是,元刊本不是案头剧,而是直接来源于舞台的戏剧文本,它可能是为演员学唱所用,也可能是为了便于观众听清唱词。但对于这种结论的由来,没有学者做过细致且令人信服的考证。对于《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性质界定,目前学界众说纷纭,由于缺乏更多的文献资料,没有哪一种观点具有完全的说服力,它们都是在猜测之上的自圆其说。
(二)元刊杂剧元明版本的比较研究
《元刊杂剧三十种》自1924 年由上海的中国书店出版而被广大中国学者所关注,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元杂剧研究依赖明刊本的局面。《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有14 种是孤本,其余16 种在其他杂剧选本中都可见到,其中与《元曲选》重复的有13 种:《楚昭王》《看钱奴》《陈抟高卧》《任风子》《老生儿》《气英布》《赵氏孤儿》《合汗衫》《薛仁贵》《魔合罗》《铁拐李》《范张鸡黍》《竹叶舟》。与《元曲选》重复的这13 种,每种都与《元曲选》有相当差别,或是结构不同,或是文字不同,或是曲牌次序不同,或是曲牌多寡不同,青木正儿在《元人杂剧序说》第三章中有详细说明。此外,《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有9 种留存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有6 种留存于《古今名剧合选》。基于此种情况,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同一剧本元明刊本的差异。
从历史上看,对元杂剧元明版本的比较,自臧懋循的《元曲选》刊行以来就开始了。对《元曲选》持肯定态度的人,认为它大有留存元杂剧之功;持批评态度的人,则将《元曲选》与元刊杂剧作比较,责难臧懋循行事孟浪,擅自篡改元人剧作,致使其失去了本来之面目。如王骥德在《曲律》中说《元曲选》“句字多所窜易,稍失本来,即音调亦间有末叶,不无遗憾”[5];清人叶堂的言辞最为激烈,他在《纳书楹曲谱》按语中称:“‘百种’系臧晋叔所编,观其删改‘四梦’,直是一孟浪汉,文律曲律,皆非所知,不知埋没元人许多佳曲,惜载!”[6]
至近代,元杂剧的各种异本相继被发现,于是这一问题被重新提出来。孙楷第、严敦易、吴梅、邵曾祺等人都曾贬低臧懋循《元曲选》而对元刊杂剧给予较高评价,如孙楷第在《也是园古今杂剧考》中指责臧氏“师心自用,改订太多”[7];吴梅在《元剧研究》第二章责备臧懋循把元杂剧原本“盲删瞎改,弄得一塌糊涂”[8]。为臧氏辩护的则有王国维、吉川幸次郎、隋树森、徐朔方等人。事实上,某些对《元曲选》的批评,失之过严,严敦易在《论元杂剧》一文中以《元曲选》的来源是御戏监本,从而否定这部书的价值,更是不恰当的;某些对臧氏的辩护也有偏护的嫌疑,失之过宽。时至今日,经过历史的沉淀,学者们对《元刊杂剧三十种》和《元曲选》已经少有偏激的观点。徐扶明的《臧懋循与〈元曲选〉》(收录于《元明清戏曲探索》)、郑骞《臧懋循改订元杂剧评议》(收录于《从诗到曲》)、蒋星煜《元人杂剧的选集与全集》(《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3 期)等都对元明刊本的价值争议问题进行过详细梳理,最终得出应客观对待二者的结论。
如上文所提,《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有14 种是孤本,其余16 种在其他杂剧选本中都可见到,于是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同一剧本元明刊本的差异。由于《元曲选》是杂剧选本中最精良的一个版本,且留存的元刊杂剧最多,所以在比较研究中选择明代版本时,选取《元曲选》本是最普遍的。
在单篇论文中,目前所见的同剧元明刊本的比较共有14 种,包括了可见于他本的元杂剧的绝大部分,目前未见比较研究的2 种是《张鼎智勘摩合罗》和《诸葛亮博望烧屯》。将宾白、唱词等杂剧元素进行比较,试图探究其成因,是这类比较研究最常见的思路,如王珏《浅析〈薛仁贵〉杂剧元本和明本的不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4 年第3 期)一文,从人物设置、曲文、宾白三个方面比较了元明刊本的差异,并分析差异产生的原因。
学者们还试图通过同一剧本的比较,推断杂剧在元明两朝的发展演变,进而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认为臧懋循的改编使元杂剧更加适于舞台表演;另一派则认为杂剧由元到明有从舞台走向案头的趋势。前一派如薛梅《〈楚昭王疏者下船〉两种刊本比较——兼谈臧懋循“当行”理论在杂剧剧本改编中的体现》(《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4 期)、孔杰斌,陈建森《从〈吕洞宾度铁拐李岳〉看明人对元刊本杂剧的改写》(《戏剧艺术》,2012 年第1 期)都认为明刊本对元刊本增改和润色的目的是适应舞台演出的需要。另一派的代表如朱存红《从〈陈抟高卧〉一剧看杂剧刊本从元到明的变化》(《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 期)一文,考察了《陈抟高卧》一剧的元明版本在曲词、科白两方面的变化,进而推广到整个元明杂剧发展变化的过程,认为从元到明各刊本的演变过程是一个在文人手中不断雅化的过程,杂剧由元到明有从舞台走向案头的趋势。
实际上,元杂剧由元至明究竟是走向了案头化,还是更适宜舞台表演,这两派的论争在元明版本的比较研究中是始终存在的,并不仅限于同剧的版本比较之中。荷兰学者伊维德在《我们读到的是“元”杂剧吗——杂剧在明代宫廷的嬗变》(《文艺研究》,2001 年第3 期)中指出,《元曲选》的编者将来源于宫廷的演出本改编为江南文人书斋中阅读的案头剧本,元杂剧由此成为固定的供阅读和阐释的文本。中国学者杜海军有完全相反的观点,他的《从元剧之元明版本比较看戏曲意识的发展》(《艺术百家》,2015 年第3 期)一文认为,明代戏曲通过删去案头化的曲辞、增删典故、文字口语化、增加科诨这四个方法,使戏曲的剧本更加通俗化,戏曲的场上意识增强。伊维德与杜海军的观点看似相悖,但实际上都反映出其观点的片面之处。元杂剧剧本的舞台表演性和文学性无法截然分开,从剧本出发,研究元杂剧究竟是走向案头化,还是更适宜舞台表演,都只是偏取一面而已,其结论尚需借助其他更有力的文物或文献证据考证。
在专著方面,同剧的元明版本比较研究,要推郑骞《元杂剧异本比较》和严敦易《元剧斟疑》。郑骞将《元曲选》中有异本的85 种进行逐一比较,其中包括与元刊杂剧重复的13 种,研究成果是以题目为《元杂剧异本比较》的5 篇系列长文刊印于《台湾编译馆馆刊》(1973 年第2 卷第2 期、1973 年第2 卷第3 期、1974 年第3 卷第2 期、1976 年第5卷第1 期、1976 年第5 卷第2 期),目前中国无法看到该书全部面目,但郑骞论文集《从诗到曲》收录了《关汉卿窦娥冤杂剧异本比较》一文,其研究体例大致为,先列举《窦娥冤》现存的几个版本并从整体上给予评价,接着将每折的关目、宾白、套式、曲文进行详细比较。郑骞的比较研究细致而扎实,但不时流露出对元刊杂剧的推崇和对臧氏删减的不满,带有较为明显的个人情感倾向。严敦易的《元剧斟疑》涉及4 种元刊杂剧,其中《冤家债主》和《疏者下船》有明代版本,严敦易将异本从情节、曲牌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对比,但该书并不止于比较研究,而是着重探索元杂剧的真伪和作品的隶属问题,较系统地提出了收录于此书的86 种元杂剧的有关疑问。作者视野广博,态度严谨,对于学界尚存疑的问题也只在一定的证据之上作理性推断,因而作者的不少观点对后人颇具启发意义。
同剧的异本比较也受到了戏曲目录学家的关注,其中以傅惜华、庄一拂、邵曾祺三家为代表。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作家出版社,1957 年)著录了737 种元代杂剧作品,其中包括30 种元刊杂剧。全书以杂剧作者为纲,前有作家小传,后著录杂剧作品,该书对每种剧目的版本比较,集中于总题、题目、正名、简名、别名、存轶情况,其对版本的搜罗极为广泛全面,但内容稍显简略。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卷四至卷八汇集了元明清三代杂剧存目共1830 余种,全书同样以作者为纲,每种曲目均略述内容梗概,考订其本事,但详略未能一致。其中对各剧版本的比较更为简略,仅集中于题目正名。但因所收曲目丰富,编排合理,易于检索,该书成为研究戏曲史之必备工具书。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收于赵景深主编《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丛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年),收录以元代和明初的杂剧作家、作品为主,分5 部分著录。该书依曹寅本《录鬼簿》及《录鬼簿续编》排列作家次序,并撰写作者小传,作品按存本、残曲、佚本继次列出。每一剧名条目下皆 列“简 明”“著 录”“剧本”“题 目正 名”“剧情”“考释”。“考释”部分对剧情内容进行了多角度考论,多综合元曲实例进行比较研究,真知灼见尤多。与傅惜华、庄一拂两书相较,邵曾祺《元明北杂剧总目考略》可谓后出转精,对元代杂剧作家及其作品目录的介绍和考释更为丰富,体例也更为明晰。
同剧的异本比较往往从细处着手,对宾白、唱词,乃至关目等的不同进行比较,这种研究细致扎实,属于基础性研究,但这类比较研究往往偏重“是什么”,少有对“为什么”等更深层次问题的思考。
三 《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文学研究
对元杂剧进行文学性解读是元杂剧研究的主流方向,这种倾向自1925 年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就已确立。《宋元戏曲史》第十一章《元剧之结构》、十二章《元剧之文章》等便是关于元杂剧文学性研究的显著表现,其中对元剧文章妙处的论述,即“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更成为后人不断引述的经典论断。纵观现今的各种戏剧史专著可以发现,学者们构建的戏剧史大多以作家作品为纲,把作家考证和作品的文学性解读作为主要内容。就元杂剧文本而言,在同时具备元明两种版本的情况下,学者们基本都以明代版本的元杂剧为研究对象,仅有极少量专以元刊本为对象的研究。
(一)作家与作品研究
在元杂剧发展后期,出现了对戏曲作家作品的评论,钟嗣成的《录鬼簿》是记载和评论元代戏曲作家的最早一部著作。现今元杂剧的作家与作品研究中,最具热度的当数关汉卿及其杂剧。《元刊杂剧三十种》中有关汉卿杂剧四种,分别为《西蜀梦》《拜月亭》《单刀会》《诈妮子调风月》。现将专以元刊本为底本的研究梳理如下。
伏彦冰,李占鹏《〈西蜀梦〉:一部悱哀怨、凄厉沉痛的抒情悲剧》(《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5 期)以元刊本为研究对象,作者认为,《西蜀梦》的底本不可考,元以前文献中也并无赴梦传说,关汉卿迎合人们的心理愿望对史实进行了生发与点染;该剧的悲剧性体现在人物性格、全剧气氛、主旨等方面,是一部动人心弦的悲剧作品。《拜月亭》有杂剧元刊本和南戏两个版本,对该剧的研究多体现在比较之中。(韩)吴秀卿《〈拜月亭〉在杂剧、南戏中的演变》(《河北学刊》,1995 年第4 期)从关目排场、人物形象、语言表现三个方面对二者进行了比较;亢一帆《元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与南戏〈拜月亭记〉的比较》(《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0 年第2 期)从题材内容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进行对比。《诈妮子调风月》只有元刊本,宾白不全,剧情难以理解,赵景深《谈〈诈妮子调风月〉》(《戏剧论丛》,1957 年第2 辑)、王季思《〈诈妮子调风月〉写定本说明》(《戏剧论丛》,1958 年第2辑)、宋光祖《〈诈妮子调风月〉臆解》(《戏剧艺术》,1993 年第3 期)等,都对剧情做了一定的推断尝试。蔡红英《论元杂剧〈诈妮子调风月〉喜剧性结局的合理性》(《四川戏剧》,2009 年第2 期)则从人物情感逻辑、故事事理逻辑、社会风俗与创作意图等方面,断定《诈妮子》是喜剧。以上研究在具体观点及研究方法上,尚有可推敲之处,但以元刊本为研究底本,凸显出研究者的版本意识。
20 世纪元杂剧的研究基本涉及大多数作家和作品,尽管对其他作家作品的研究远未达到对关汉卿作品研究的热度,但这类研究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傅惜华《元代剧作家传略》,邵曾祺《元杂剧前后期作家传略》,孙楷第《元曲家传略》《元曲家考略续编》、谭正壁的《元曲六大家略转》等,厘清了一批剧作家的生平状况,为元杂剧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些剧作家的作品研究中,专门以元刊本为研究底本的极少。高培华《〈张千替杀妻〉结局考略》(《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 年第4 期)一文从元杂剧概况、该剧本事两个方面考证《张千替杀妻》的结局,认为张千的最终结局是遇赦,该剧不是悲剧而是正剧。
今试以姚婷婷《论元杂剧中的屠夫形象》(《四川戏剧》,2015 年第10 期)一文看当今元杂剧研究中的底本选择问题。该文选取了以屠夫为主角的三本杂剧,分别是《马丹阳三度任风子》《张千替杀妻》《小张屠焚儿救母》,这三本杂剧皆收录于《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其中《任风子》《焚儿救母》有元明两种版本,《替杀妻》只有元刊本。使人困惑的是,作者在行文中,《任风子》《焚儿救母》两篇以明刊本为研究底本,《替杀妻》则以元刊本为底本。作者明知元刊本的存在却选择避而不谈,只在没有明本可用的情况下才选用元刊本,这种情况在元杂剧研究中似乎是常态。
戏剧史的撰写虽多以作家作品为纲,但对元刊杂剧的文学研究寥寥可数。作者们虽然会提及元刊杂剧,但仅限用于版本交代,在论述剧情时仍会遵循明代版本;仅在只有元刊本的情况下,使用元刊本。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吴梅《中国戏曲概论》等均无出其右。
(二)元刊杂剧体制研究
过去人们对于元杂剧体制特点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整饬的《元曲选》为参照的,《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杂剧、宾白与科范极其简略,元明版本的种种不同促使学者们对元杂剧的体制结构重新进行思考。
《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杂剧基本无宾白,这引发了宾白是谁作的问题。明代王骥德、臧懋循均认为宾白是伶人作,现今的研究者也多有认同,如唐文标(《中国古代戏剧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5 年版)、傅谨(《中国戏剧艺术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 年版)、解玉峰《元曲杂剧“题目正名”考》(《民俗曲艺》,2003 年第6 期)等;与此相反,王国维认为剧作家应该兼作宾白;宋常立在《元杂剧的编创方式:作家与伶人协同创作》(《河北学刊》,2013 年第6 期)一文中提出了较为折中的观点,他认为元杂剧的编创是剧作家和伶人合作的结果,元杂剧最终是在表演中完成的。
脚色制是中国古典戏曲结构体制的根本所在,对脚色进行的研究也蔚为大观,现择取与《元刊杂剧三十种》直接相关的研究梳理如下。一类是对具体脚色进行考源辨正的研究,其中涉及《元刊杂剧三十种》中的作品。刘晓明在《旦脚起源于声妓说》(《艺术百家》,2006 第2 期)一文中梳理了旦角渊源的学术史,共有13 种观点,对诸说进行评议之后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作为戏曲角色的“旦”起源于声伎。但刘晓明也承认对其中某些观点无法彻底反驳,只能暂存其说,因而“声妓说”也只是在文献基础之上的某种合理推测。解玉峰的《北杂剧“外”辨释》(《文献》,2000 年第1 期)、谭美玲《净脚小考》(《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2 期)、姚小鸥,麻永玲《宋元戏剧脚色体系中的“孤色”》(《戏剧艺术》,2013 年第6 期)等论文均是此类研究,这对杂剧的脚色来源不明、划分不清等情况有一定的辨明作用。另一类是从戏曲史的角度研究脚色。从解玉峰开始的一批学者将脚色的发展与古典戏剧的发展相联系,解玉峰《“脚色制”作为中国戏剧结构体制的根本性意义》(《文艺研究》,2006 年第5 期)一文将中国戏剧的根本特征归之于脚色制,提出中国戏剧发展演变的历史也是脚色制渐趋规范和稳定的历史。元鹏飞《中国戏曲脚色的演化及意义》(《文艺研究》,2011 年第11期)一文从脚色与戏剧形态的演变规律入手,指出古典戏曲脚色的演化有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对应着戏剧发展的不同形态。元鹏飞的研究打破了传统脚色研究追根溯源,罗列排比的局限,将脚色与戏剧演出相联系,是一种极具价值的新视角。许强《“戏”与“曲”的演替——脚色制视阈下中国戏曲表演形态的技艺化进程》(《文艺研究》,2020 年第4 期)一文全面继承了此种视角,并使之更加细致深化。另外,对元杂剧的脚色进行元明时代文本的比较研究,也是较为常见的。解玉峰《论臧懋循〈元曲选〉于元剧脚色之编改》(《文学遗产》,2007 年第3 期)认为,臧懋循的《元曲选》在编辑元剧时曾对元剧角色做过很多案头化改编,这些改编改变了元杂剧以曲为本的色彩,使戏剧性得以彰显。范德怡《元杂剧的版本差异与脚色研究》(《文化遗产》,2017 年第1 期)一文梳理了角色研究史中元刊杂剧价值的逐渐显现,作者认为,从不同版本的继承关系来看,元杂剧的脚色体制在《元刊杂剧三十种》中就已经形成,明代改编本均未从根本上撼动这种体制。该论文虽是在版本对比之中研究脚色,但并不是求异,而是求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比较研究中单一的求异现象。
至于元杂剧的折、楔子、题目正名、一人主唱等,均有不少研究成果面世,其中某些直接以元刊杂剧为研究对象,如汪诗珮《元杂剧“题目正名”新探——以元刊杂剧为切入点的考察》(《中华戏曲》,2005 年第2 期)一文专门对元刊杂剧进行观察,辅以与时代相近的文献资料。都刘平《元杂剧“折数”辨析》(《文化遗产》,2018 第1 期)以《元刊杂剧三十种》来检视明代曲论家构建的“一本四折”理论,得出“一本四折”是明代曲学家的理想化构建、与元杂剧实际情况不符的结论。
对元刊杂剧艺术体制作整体性研究当以杜海军为代表,杜海军《从元刊杂剧重新审视元杂剧体制之原貌》(《求是学刊》,2009 年第4 期)一文以元刊杂剧文本审视元杂剧体式的特点,作者认为元刊杂剧作品在分折、题目正名等多方面存在不规范现象,与今日所云元杂剧的体制规范相去甚远,因而要认识元杂剧体制与内容的真实面貌,必须对《元刊杂剧三十种》予以重视。杜海军的另一篇论文《从元刊杂剧看元杂剧艺术未被揭橥的特点》(《艺术百家》,2011 年第3 期)从元刊杂剧文本审视元杂剧的内在艺术特点,认为元杂剧具有重语言轻形象,重说唱轻表演的阶段性特点。
从元刊本重新探讨元杂剧的艺术体制,此类研究在2000 年之后陆续出现,它们是在文献文本层面的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之后的更深一层研究。由于元杂剧体制自身的复杂性,这类研究目前呈现出较为零散的状态,相左的观点多,有较大的研究空间。
(三)元刊杂剧编剧研究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有结构的,从广义上讲,戏剧的艺术结构就是剧本的全部组织和结构,即今日所云编剧。剧作家如何进行艺术构思,设计人物关系,组织戏剧情节,矛盾如何展开,如何开场,如何结局等,都要精心安排。中国历代曲论家都很重视结构,(元)周德清《中原音韵》附录有“作词十法”,(元)乔吉《南村辍耕录》有“凤头猪肚豹尾”说,但这些在当时并不是用来论述戏曲的,至王骥德、李渔等人,戏曲编剧理论才发展得较为成熟。中国的戏曲编剧虽然事实上早已存在,但编剧学自立门户不过几十年,尤其从编剧的角度探讨古典戏曲的艺术规律,这一领域的研究目前较为薄弱。
在元杂剧作家中,关汉卿既是编剧又是导演、演员,其剧作缜密精巧,矛盾冲突环环相扣,非常适宜场上演出。在单篇论文中,编剧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关汉卿与其剧作。对于关汉卿编剧的特点,台湾地区彭镜禧《计将安出?———浅说关汉卿编剧的一项特色》(《河北学刊》,1994 年第1 期)一文抓住“计谋”这一突出特点在关氏剧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注重探讨它与戏剧编写的关系。关汉卿剧作用计频繁、用计铺谋,它们在点染剧中人物性格、推动故事情节发展、强化戏剧结构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该文以小窥大,且在涉及具体剧作时具有非常明晰的版本意识,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对关汉卿剧作结构的研究集中于《单刀会》。该剧结构独特,众评纷纭,李健吾《关汉卿〈单刀会〉的前二折》(收录于《李健吾戏剧评论选》,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 年),作者认为该剧是主要人物出场较迟的一出颂剧,前两折在结构上虽有种种缺点,但它又具有服务观众、为关羽出场作铺垫等几大好处,该文具有为《单刀会》的结构正名的意味。郭明志《铺垫蓄势 抒情写意——谈谈关汉卿〈单刀会〉的谋篇布局》(《文史知识》,1993 年第2 期)一文认为,《单刀会》的独特结构正充分显示了关汉卿的美学追求和艺术匠心。《单刀会》前三折起铺垫和蓄势的作用,第四折只写关汉卿的引吭高歌,这样的安排最能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和精神风貌,使后面直接冲突的高潮到来显得水到渠成。许灏《元杂剧〈单刀会〉结构简论》(《学术交流》,1996 年第2 期)则对《单刀会》一剧的结构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该剧里的“起”占去了整本戏的大半,这是作品结构的失衡,导致事件在前三折一直在原地打转,许久不能入戏。
四 《元刊杂剧三十种》的舞台研究
元代是中国戏剧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同时也是中国戏剧学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可以说,元人对戏剧的表演、创作已经有了自觉的审美意识,某些专著在元明清三代六百多年中是绝无仅有的。刘晓明在《杂剧形成史》中提出,近年来中国古典戏剧研究存在着“表演转向”,即从表演技艺的角度考察戏曲发生与发展的内在理路。学者们在反思与展望元杂剧研究时,普遍指出单一的文学角度研究导致元杂剧研究范围变狭窄的问题,呼吁将剧本文学与舞台演出作统一的考察。从实际的研究成果来看,学界对元杂剧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其综合艺术特点。对《元刊杂剧三十种》舞台演出的重视与探索,是与戏曲研究的“表演转向”相契合的,其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文本进行直观的表演提示研究。王之涵《元刊杂剧三十种表演提示研究》(《滁州学院学报》,2007 年第2 期)、许巧云《〈元刊杂剧三十种〉的表演提示及角色词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11期)对表演提示用语进行分类研究,使人一目了然,但其缺憾是缺少更深层次的研究。
二是演出形态研究。黄天骥、康保成《中国古代戏剧形态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 年)一书第十二章《元剧的“杂”及其审美特征》、十三章《元杂剧中人物上下场和冲场的表演形态》都探讨了元杂剧的演出形态。黄天骥感于元杂剧演员演唱任务的繁重,从而认为折与折之间必然有补空的表演;元杂剧之所以称为“杂”是因为在表演中混有多种技艺;元刊本中的“开”指演出中人物上场时作介绍的开场白,“开呵”类似于今日的“节目主持人”。作者的不少学术观点具有很强的创新性,但有值得商榷之处。王万岭的《元杂剧的“开”与“节目主持人”无关——与黄天骥先生商榷》一文就对黄天骥的观点有所质疑。麻国钧《元明杂剧中的队舞与队戏》(《中华戏曲》,2010 年第1 期)详细论述了元明杂剧中的队舞插演,其中的某些舞蹈“队子”在其他文献,乃至地方戏中仍有留存。黎国韬《元杂剧“坐演”形式渊源考——唐乐与元曲关系之一例》(《戏剧艺术》,2013 年第1 期)一文,作者认为元刊杂剧中的“坐演”这一特殊表演形式,可以溯源于唐代燕乐“坐部伎”的堂上坐奏。演出形态的演变也是这类研究的重要层面,江南大学王阳的硕士学位论文《元杂剧演出形态演变研究——以元明刊本比较为中心》(2013 年)一文,从版本学的角度将元明版本中的“唱”与“念”作细致对比,由此得出其舞台演出形式的演变规律。元杂剧元明版本的研究层出不穷,该文从舞台演出的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三是演出程式研究。中国古典戏曲的程式化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程式化体现在古典戏曲的方方面面,有形式层面的,也有内容层面的,在此不赘述。专对元杂剧进行演出程式研究的成果也有很多,如顾肇仓《元代杂剧》(作家出版社,1962年)等,但这些研究的普遍缺憾是以明刊本为研究底本,偶涉元刊本。曾永义《元人杂剧的扮演》(收录于《说俗文学》,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年)一文从戏剧要素和扮演过程两个方面进行元杂剧扮演的探索,前者说明元杂剧的背景,后者叙述元杂剧扮演的情形。该文旁征博引,论述有据,且在行文中,有意区别元刊杂剧和明刊元杂剧,版本意识明晰。
四是舞台美术研究。舞台美术包含化妆、穿关、砌末等,最能表现出元杂剧的场上演出属性,它是杂剧搬演至舞台的直观呈现。目前没有对《元刊杂剧三十种》舞台美术的专门研究,这类研究多附属于元杂剧或古典戏曲的舞台美术研究之中。龚和德《舞台美术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87 年)一书汇集作者近几年的著述16篇,内容包括对舞台美术的基本原理,以及戏曲人物造型和景物造型历史沿革的研究,对1949年后30 多年间舞台美术创作基本经验的探索,并附图60 余幅。其中《元明杂剧的舞台美术》一节从化妆、服装、舞台装置与道具三个方面详细论述了杂剧的舞台美术,每部分在举例时都略微涉及元刊杂剧。该书既涉及古典戏曲的舞台美术,又有现代思考,对舞台美术工作者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五 结语
《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发现是中国古典戏曲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具有非常重要的文献意义和学术价值,但遗憾的是,《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研究始终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自1924 年上海中国书店以《元刻古今杂剧三十种》为名出版该书,直至今日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元杂剧研究却并没有因《元刊杂剧三十种》而发生太大变化。
王国维是《元刊杂剧三十种》整理研究的开山祖师,自他之后,元刊杂剧的校勘整理一度形成高潮,至郑、徐、宁三家校本出版后,校勘整理的工作基本结束。到20 世纪90 年代,对它的研究更趋于沉寂,没有出现一篇专门以《元刊杂剧三十种》为对象的论文。据笔者检索,除零散的单篇论文之外,学界对《元刊杂剧三十种》的专门研究成果只有两篇博士论文,分别是汪诗佩《从元刊本重探元杂剧——以版本、体制、剧场三个面向为范畴》(台湾“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年)和甄炜旎《〈元刊杂剧三十种〉研究——以元、明版本比较为中心》(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 年)。此外,文学史和戏剧史也多会涉及《元刊杂剧三十种》,但多是一般介绍,缺乏学术的考辨和源流探究。有些戏剧史甚至直接回避元刊杂剧,以明代编辑的元杂剧为依据,这就使读者对元杂剧的认知还停留在明本元杂剧之中,实为极大的缺憾。
事实上,《元刊杂剧三十种》还有很多问题亟待研究。《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元刊属性仍受到学者质疑,其流传过程也不甚不楚,即使整理方面也只注意校勘,而没有注释笺证,不能说是尽善尽美。总之,《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校勘和版本等文献文本层面的研究较多,其他更深层次的研究为数不多。《元刊杂剧三十种》遭受冷遇,一方面是因为《元刊杂剧三十种》是一门绝学,研究难度较大;另一方面,因为当今“避难就易”的学术风气,一个学者很难几十年如一日地坐冷板凳。
研究《元刊杂剧三十种》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对刊刻年代的确定。如果连《元刊杂剧三十种》的属性都不能确定,那么在此基础之上的任何研究都是很难立住脚的。假使《元刊杂剧三十种》并不是元代刻本,而是明代某个民间剧团的演出本,那么整个《元刊杂剧三十种》的研究将会是另一番面目。也就是说,《元刊杂剧三十种》的产生与流传过程是亟待专家、学者廓清的,但鉴于目前相关文献资料的匮乏,这也必将是《元刊杂剧三十种》研究的一大难题。
除此之外,抛却年代问题,《元刊杂剧三十种》的文本与明版本相比具有显著的独特性,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它特有的属性,这也是《元刊杂剧三十种》研究较为薄弱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