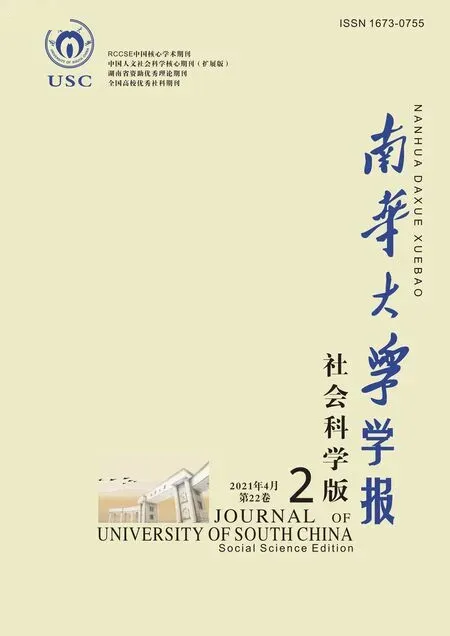律法焦虑与政体健康:体液理论中的莎士比亚问题剧《一报还一报》
2021-12-23陶久胜郭梦娜
陶久胜,郭梦娜
(宁波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外研社英文主编乔纳森·贝特在给《一报还一报》撰写导言时指出,这部莎士比亚的问题剧被记载的首次演出是1604年12月26日,英国新君詹姆士的圣诞庆典之上,“尽管剧中的公爵并非喻指詹姆士”,但其中关于神学和道德争论,对权力隐秘源泉的探寻都映射了当时英王詹姆士在国会和教会关于律法问题探讨的论辩中的态度[1]4-5。一直以来学界都十分关注剧中的法律与道德的问题,一些批评家从公爵文森修的角色扮演角度阐释一个社会体系中恢复司法的重要性[2],也有学者从法律与宗教的关系出发,研究詹姆士一世对待清教主义的立法提议所采取的政策[3],乔纳森·戈森则研究了其中的政治神学,探讨基督教思想是如何与当时的法律相互渗透结合以达到服务于社会治理之功效[4],但实际上古典医学的动态体液平衡理论与政体和人体的大小宇宙类比关系已经成为早期现代英国社会暗指和理解国家法律和政体健康的有效途径[5]。因此,本文拟从古典医学体液理论角度出发解读剧中的维也纳城邦的性欲糜烂所导致的社会秩序失衡和法律名存实亡的现象。首先,根据体液理论阐述剧中维也纳市民和“暴政”的执法者安吉鲁“体液过剩”的状况。其次,分析法律在剧中的政体健康隐喻、执法者对法纪的阳奉阴违和公爵文森修利用“政治方面的种种机宜”[6]262拨乱反正最终恢复国家政体健康。最后,解析莎士比亚在剧中表达的对英国法律现状的忧虑和对英王詹姆士能否激发法律的“克制”作用,恢复英国政体健康的焦虑,并解读法律在其中作为“不过我们的刀刃虽然锐利,/用起来却要小心,/不可大砍大杀,/要人性命。”(彭译,II.i.5-7)①之中所隐含的道德层面的因素。
一 古典体液理论与疾病化的维也纳
文艺复兴时期医生数量非常少,人们需要自我医治,因此当时的戏剧中总是以医学术语来呈现人物,所以当时的医学话语已经不是一个专业术语而是作为一个通用语言存在[7],而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报还一报》中就涉及了一系列明说暗指的医学话语,如医学上常用于治疗梅毒的“发汗”之法与双关语“法国丝绒”(法国病暗指梅毒[1]14)和“骨头都空了”(骨头脆是梅毒晚期的症状[1]15)等词对性病侵染后果的暗喻,这些医学话语的使用一方面说明了市民荒淫纵欲以致患病的状态,另一方面映射了维也纳国度的健康隐患。
在剧中,公爵文森修指出,由于他“放纵人民”(彭译,I.iii.38),整个城邦充斥着“年轻人如火的热情”(彭译,I.iii.5),维也纳的“礼仪法纪都荡然无存”(彭译,I.iii.32),但是“若因为他们干出我默许的行为,/势已难改,/再去骚扰打击他们,/我就成了暴君。”(彭译,I.iii.39-41)当时的维也纳公民因为色情商业的高度发展和律法多年束之高阁,早已无法自制,导致整个国家法纪陷入一种“瘫痪”状态。公爵将维也纳法纪和秩序崩坏的现状与城内年轻人体内的“情热”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暗指由于“体液过剩”引发的过旺情欲而导致个人身体健康受到影响,进而影响整个社会法纪的健康且危及国家政体健康。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将自己视为一种包含着各种液体和蒸汽的海绵式的容器,人体内部的不平衡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造就了他们的情绪和性格,且两者处于永恒的流动之中,而这个思想又是建立在古典体液理论之上的[6]。因此,当这种纵欲心态由个人身体的体液不平衡中产生、扩散并与外在环境进行交换时,必将危害政体健康最终使整个国家陷入疾病状态。
由古希腊著名医生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of Cos)提出的“体液学说”对早期现代医学的影响巨大,而由伽林医生提出的“体液平衡学说”是其重要的医学理论之一[8]62。尽管后来证明了有其他体液的存在,但在16世纪时,只有四种体液的观念已经成为真理般的存在[9]136。莎士比亚的戏剧特别是复仇剧就经常涉及体液与医学相关的术语,喜剧与问题剧中也不少。而根据希波克拉底的“体液学说”,人体内有四种体液:胆液质、血液质、粘液质和黑胆质,它们之间的平衡是相对的。而当其中一种体液占据主体地位时,身体和心理倾向就会受到影响,从而使身体产生病态:异常胆液质、异常血液质、异常粘液质和异常黑胆质[9]38。维也纳城中泛滥的性欲和善热就是由于胆液质占据体液主导地位引起的,而这种体液不平衡就会外化为个人的一种病态。第一幕中,路西奥和两位绅士的对话中就提及疾病与性欲的相关话语。路西奥是城中的纨绔子弟,与女主人公的弟弟私交甚笃,“他就把凯特·吉普东小姐弄大了肚子,/答应要娶她。/到今年五月一日,/那孩子就该有一岁零三个月了”(彭译,III.i.428-430),并且反过来到处说帮助他养孩子的老鸨欧弗东太太的坏话,如果说莎士比亚将整个维也纳视作一个自然身体,那么路西奥的存在就是导致国家内的疾病传染的“病毒”即过剩的体液。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可是芒刺,/粘住就不放”(彭译,IIII.iii.164-165),而芒刺除了有“草木茎叶、果壳上的小刺”之义,还可以引申为“隐患”的含义,此外,舌生芒刺也和纵欲一样,在中医看来这是热毒内伏,心肺火盛所致。由此可见,如路西奥这般患有“体液过剩”之病的市民就是危害维也纳政体健康的“芒刺”,是国家疾病的内热来源。
四种体液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而乔瑟琳也曾将自己的尿液形容成含有“过多的白色的粘液”以此说明自己体内充满了“冰冷的水质的体液”。根据伽林医学理论,粘液质包含冰和水的特质:寒冷和潮湿[9]136。这就与路西奥对摄政王安吉鲁的指控相互映证。路西奥借用体液修辞来说明摄政王安吉鲁行事严苛不讲情面的性格,他宣称安吉鲁“撒尿的时候,/尿出来的都是冰。”(彭译,III.i.354-355)连德高望重的大臣爱斯卡勒斯也认为安吉鲁是一个“一丝不苟”“严谨”的人。他能结冰的尿和冰冷的血液足以说明此人的性格沉稳,不近人情,根据体液理论,当粘液质在体内占据主导地位时,自然身体与思想便受其影响,进而表现出性子沉静,身体湿寒的状态,显然他体内的血液质都已经受其影响失去了原本的活力。但这违反了伽林的体液平衡学说,显然摄政王安吉鲁体内的另一种体液过剩,才使安吉鲁呈现一种“严谨”的状态,但是“严谨”一词原本就是与伪善的清教徒连接起来的[1]2。由此可见,代理执政者安吉鲁本身就是国家另一类疾病的存在。而当安吉鲁见到伊莎贝拉之后,他也感染了城市中的热病,萌生了玷污这个即将成为修女的求情者的想法并在之后付诸行动。“实际上,古典医学的体液理论是一套涉及人体、政体和天体的病理理论和修辞话语......和谐与完美为至高状态。然而,当这种秩序被打破时,紊乱和疾病就占主导。”[10]当这种热病传染到摄政王的身上时,必然感染到他所代表的法律的健康即政体健康,从而使维也纳陷入疾病状态,而剧中的公爵从一开始就通过各种政治和宗教手段想方设法使维也纳恢复到法治状态之下,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二 法律的政体健康隐喻和公爵的“净化”之法
柯尔律治曾经给予了《一报还一报》极高的评价,将它视作“莎翁剧作之大成”,因其所包含的话语之广、内容之复杂和诠释的多义性。正因如此,我们才得以在古典医学理论的框架下阐述,而维也纳的社会弊端既然已经显现出来,那么统治者公爵文森修便用道德责任去遏制这种风气的滋长,作为剧中的“操刀”者,必须给社会“放血”以达到恢复城邦体液平衡的目的。
早期现代医学还有一种观点,疾病的起因不仅仅是由身体内部的体液不平衡造成的,外部污染也会导致身体内部健康的体液受到污染,使体液呈现病态或者直接感染健康的体液[9]38-39;136-137。英格拉西也指出,“传染病蔓延的真正原因”是健康人和被感染者的混合体[11]291。剧中纨绔公子路西奥曾称自己在老鸨欧弗东太太家“买了不少病”(彭译,I.ii.41),也说过“以后我总要挑头向你敬酒,/以免落在你后边,/染上脏病。”(彭译,I.ii.26)与体液话语相映衬,此处的敬酒行为映射了外部污染源梅毒的传染性,为了防止梅毒从他人身体传染给自己,因此要先给对方敬酒避免患病。和路西奥一样,剧中因犯通奸罪而要被处死的克劳迪奥也曾形容自己为“马刺”(彭译,I.iii.139),认为安吉鲁将“城邦大权当做胯下之马”(彭译,I.ii.137),又在后面提及严刑峻法就是摄政王所谓的“城邦大权”。可以从上述言论中看出,身为“马刺”的他和路西奥危害的是法律健康,而内部“体液过剩”也正是相当于他们身体健康的“芒刺”,最终致使他们和城邦都感染热病。此外,路西奥与另外两位绅士言谈之间便随意地抹去了“十诫”中的一诫“汝勿偷盗”(彭译,I.ii.10),这也就说明了以他为中心的这一群人对于国家法律的不尊重。他们所产生的罪恶最终都影响到了个人和社会的健康,但普通法能够让每一件事各归其位,找到其最适宜的位置[12]。如果将法律做身体化处理,那么它在剧中隐喻的就是一个国家政治身体的健康。
戈森指出,17世纪的新教神学强调将神圣性从教会教庭转移到国家身上,因此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是否道德高尚就显得十分重要[4]。剧中的两个拥有执法权的人都被不同的人指控“残暴”“暴政”“发疯”或“疯头疯脑”,原本“严刑峻法”的严格执行者安吉鲁因受魔鬼的诱惑而坠下了“城邦大权”之马,自恃德高望重的公爵也被自己的臣子当做“疯了”,由此可见,他们在公民的眼中也是疾病化的,一定程度上德行有亏。而即使部分言论是来自他人的恶意诋毁,剧中各处无不在暗示着国家司法体系中存在安全隐患。考克斯也指出,尽管公爵取得了部分成功,但是无法净化整座城市的精神污染[13]。但公爵利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权谋先是以安吉鲁的严法维护了国家政体健康,又以国教“公开忏悔”的形式根除国家的痼疾,使律法恢复健康状态,这一举措也暗含了詹姆士一世对通奸罪所采取的政策[3]。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关于政治统治强调:“人只有在强制下才会向善;如果人能为所欲为,秩序必将荡然无存。”[12]剧中公爵文森修也发表过相同的观点,“淫乱之刑太过泛滥,/必须严厉纠正。”(彭译,III.i.346)也就是说,城中的法纪崩坏,道德风尚受损必须让国家重新恢复到法治状态之下,才能够让政体恢复健康,修复荡然无存的秩序。早期医学的治疗方法基于对抗疗法的基础之上,即热病当配以寒性药物[9]38。借由爱斯卡勒斯对公爵的形容,市民们无法像他一般“淡泊克制”(temperance)导致维也纳城中人“患上一种急于做好事的热病,/非得把好事变坏,/这种病才能治好。”(彭译,III.i.449)体液理论针对此类疾病的排解之法包括:放血、排便、发汗、呕吐等[9]140。戏剧伊始,公爵便开始了对维也纳的“净化”。一方面他将国内实权暂时移交给安吉鲁,启动城中的法律以整顿风纪。但单论道德问题,安吉鲁就不适合执法。其实公爵早已知道安吉鲁抛弃过玛利安娜,而这一点从公爵毫无犹疑地向伊莎贝拉提出“床上计”就可以看出,且他离开距事发不过一日,根本没有时间去打听这方面的事情,而且无论是论资历还是论道德品格,德高望重的大臣爱斯卡勒斯都是更加合适的人选,那么“明知一个人是恶棍还要擢升他,其意自然不在于‘考验’他了”[14]。公爵此时就是将他当成一个如刽子手一般的操刀者,关于这方面爱斯卡勒斯也曾提示过安吉鲁操刀需谨慎行事,刀锋足够锐利,但不需致人性命,只需适当“放血”,实际上刽子手这个职业在早期现代英国算不得什么光彩的工作,无人愿意接手,一般都由囚犯“代理”[15]。而安吉鲁在得到权力后立即在城中实行了严刑,使其居民“发汗的发汗,/有的上绞架”(彭译,I.ii.72-73),并且判定克劳迪奥死罪。但是他本人却也知法犯法,贪图肉欲,面对大臣的劝诫时,他却声称“你不能因为我有类似的毛病,/就减轻他的罪过。”(彭译,II.i.27-28)但他却以权谋私,认定即使伊莎贝拉说出事实真相也不会有人相信,置法律于腐败之地。据此看来,公爵不过知晓安吉鲁的冰冷性格与当时社会盛行的性欲正是对立面,利用了古典医疗中的对抗疗法来让安吉鲁在城中实行了“发汗”之法,意在使维也纳重归法治健康状态。另一方面,他暗地里伪装成修士,聆听罪人们的忏悔,使他们重获健康。忏悔也是剧中的关键词之一,具有宗教和法律的双重含义。忏悔既是一种宗教仪式也是作为一种法律补充形式存在。伊丽莎白·福勒指出,早在13世纪,忏悔就正式地被当做是教会法庭司法权的一种外部补充之法,用以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的一种可选之途[16]21。忏悔是通过教会法庭,使人的灵魂获得拯救,被视为一种个人再生之法[13]。类似于“发汗”的疗效,犯罪的克劳迪奥和玛利安娜还有安吉鲁通过对“神父”公爵的公开忏悔获得了新生,洗清了身上的罪恶恢复健康,并且在“神父”的主持之下,几对新人双双成婚,使其原本不合法的关系重新走回了合法轨道。公爵既通过安吉鲁震慑了市民,整肃了社会上的道德问题,又亲自推翻了所谓的“暴政”,使用“忏悔”和“发汗”使维也纳最后恢复到法治轨道之中。
三 对英王詹姆士一世的暗指和莎士比亚对新王统治的焦虑
剧中安吉鲁曾下令“维也纳郊区的窑子一律拆除”(彭译,I.ii.78),以整治城中糜烂的风气。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是不合法的,但是由于过剩的体液驱使,家庭框架之内的性已经无法满足泛滥的爱欲,而妓院作为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梅毒等性疾病是司空见惯又具有传染性的,如剧中就曾提到妓院常备的零食“梅子”就是用来治疗梅毒的,这足以看出梅毒在妓院的盛行状况。通过性交行为,男女双方发生接触互相感染了病毒,又由各自的家庭向外扩散,最终致使整个城中道德问题横生,社会陷入了无序状态。塞缪尔和约翰指出,1575—1578年的瘟疫在造成社会混乱、暴动和法律失衡方面有着自己的“得天独厚”的影响并且当初多个地区如佛罗伦萨、米兰等都针对瘟疫的流行和如何处理流浪汉等制定了相关法律[11]265;286。而实际上在1603—1604年这段时间内,英国又爆发了一次黑死病,超过25000伦敦人死亡,伦敦剧院也因此于1603年3月18日关闭,直至1604年8月8日才重开[13]。该剧于1604年12月26日在宫中上演,与剧中的梅毒盛行话语相互映衬。希尔多也曾在他的小册子中指出,这种肮脏的妓女与嫖客之间相互感染的疾病不仅可以通过躺在一起感染,而且可以通过呼吸和接触感染[13]。且剧院与妓院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人群聚集之地,是容易受到外界污染并由此滋生更多疾病的媒介场所,且剧院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国家安全,是反叛与犯法行径频发的场所。虽然剧中的场景设置在维也纳,也容易让当时英国民众联想到意大利。《一报还一报》就是折射出詹姆士新政黑暗面的镜子[13]。但从剧中的梅毒话语出发,观众不难联想到早期现代英国瘟疫频发的现状并不自觉地将剧中的维也纳想象为伦敦,而剧中所传达的法律道德思想也不免化为大英帝国的道德理想。
在伊丽莎白后期,关于君王的政治统治等问题便不允许在剧院中再现,而莎士比亚的剧团在女王去世几周后便被重新命名为“国王剧团”,从《一报还一报》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关于英国和英王詹姆士的影射。剧中公爵所采用的宗教遏制政策与詹姆士对清教采取的政策一致,均是为了稳定国家大局[3]。而新教神学就是“寻找那些神圣的存在或可能被重建的地方”,它将神圣性从教会、其官员和它的圣礼转移到国家,从而将后者的管辖权扩展到精神和个人领域[4]。无论这个神圣的领域是在统治者或者更广泛的国家之中,统治者的道德责任意识就至关重要。而这一信仰鼓励像詹姆士一世这样的基督教保皇党人,让他的法院系统尝试用教会的悔罪和恢复性方法来取代国家传统的刑罚和惩罚性刑事司法,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是为了拯救个别罪犯的精神[4]。因此剧中公爵所采用的“公开忏悔”的惩治形式正符合莎士比亚时代英国的世俗法律,通奸等性道德问题通常是由英国教会也就是国教“交纳罚金或者公开赎罪”来进行惩罚,这也符合詹姆士一世的政治理念[16]6。并且剧中公爵所采用的马基雅维利式的君王政策和探索权力源泉的态度与现实中詹姆士一世所阐述的统治思想一致,公爵提出“我爱老百姓,/但不愿受万众瞩目,/展现自己”(彭译,I.i.72-73),詹姆士一世也不喜欢像伊丽莎白女王那样“通过盛装游行展示君主权威”[1]4。英国历史学家劳伦斯·斯通发现,十六、十七世纪时期的英国并不稳定,那时候的人们由于缺少“管制”导致“脾性暴躁不安”,且人们总是随身携带武器,在此期间英国法庭的诉讼大幅增长[17]。而当时在英国王庭之中,贪污腐败现象也甚嚣尘上,屡禁不止。玛丽莲·威廉姆森注意到,早在1603年,詹姆士的宫廷就已经道德败坏,地方当局也肆意挥霍,他们经常对亚文化的非法活动视而不见,并参与其中[18]。此外,詹姆斯国王1603年9月17日的《斯图亚特王朝宣言》中声称“流氓、流浪者和闲置放荡的人”都是治安法官和其他官员的“过失”[19]。由此可见,早期现代英国也正是缺乏律法的约束导致社会风气败坏,道德紊乱,国家不安定,这正与剧中法律不严导致的秩序失调现象相呼应,表达了莎士比亚对当时瘟疫横行,律法不严所带来的社会混乱以及对新王詹姆士是否能够处理好现存问题,把握道德与法律的尺度以还英国社会安定的焦虑。并且,莎士比亚希望詹姆士一世发现自己与文森修公爵的相似之处,并且受这个“道德”公爵考验和教化臣民的激励[13],并以此参与到政治讨论之中,希望詹姆士一世可以像剧中公爵合理处理国家所面临的道德困境,遏制国家司法体系腐败现象并维持英格兰的政体健康。
17世纪初,新王詹姆士继位,各种社会道德问题逐渐显现出来,英国国教徒与清教徒关于如何惩治通奸者的争端也愈演愈烈,而身为执法者则必须对司法的严谨性负起相应的道德责任。从古典医学的体液理论视角出发研究《一报还一报》,可以发现剧中文森修公爵的一系列维护城市安定之举措取得了整顿社会乱象,恢复国家政体健康的效果。通过维也纳的疾病化,莎士比亚意在刻画社会乱序现状并参与政治讨论,向詹姆士一世传达他的政治理念与道德理想。
注释:
①参见莎士比亚《一报还一报》,辜正坤主编,彭发胜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版。本文中该剧引用此版本译文时随文注出彭泽,Ⅱ.i.5-7分别表示泽者、原文的幕次、场次及行数(下同)。本文所用的全集版本为S.GREENBLATT etal. eds,The Norton Shakespeare (New York:W.W.Norton, 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