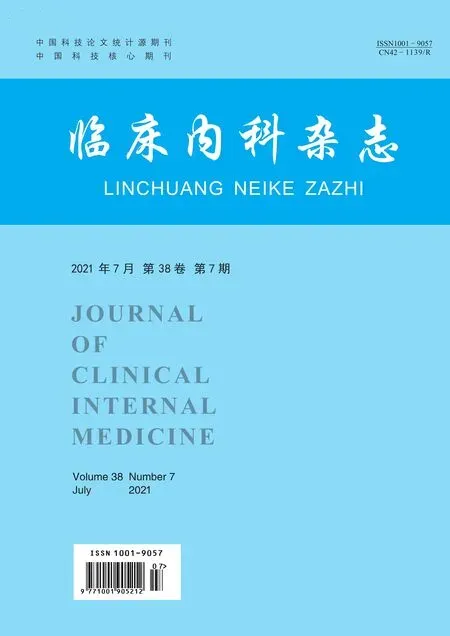间变性淋巴瘤激酶阳性大B细胞淋巴瘤的研究进展
2021-12-23夏玉雪方峻崔国惠
夏玉雪 方峻 崔国惠
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阳性的大B细胞淋巴瘤(ALK+LBCL)最早于1997年由Delsol等[1]报道,因其具有独特的形态学、免疫学和细胞遗传学特征,在WHO(2008)造血和淋巴组织疾病分类中被归为一种独立的成熟B细胞肿瘤。国内外报道该病患者不足200例,国内报道了约32例,其中ALK阳性的弥漫性大B细胞淋巴瘤(DLBCL)占DLBCL的比例<1%[2]。ALK+LBCL发生年龄为9~85岁,中位年龄35岁,男女比例为3.5∶1[2-3]。ALK+LBCL具有高度侵袭性,对常规治疗反应差,预后不良。由于ALK抑制剂如克唑替尼单药治疗某些ALK阳性肿瘤具有显著的临床疗效,以ALK基因异常作为肿瘤生长驱动因素的一类肿瘤统被称为“ALKoma”[4]。本文将对此类淋巴瘤的临床特征、病理特征、免疫表型、细胞遗传学及治疗进展进行综述。
一、临床特征
约50%的ALK+LBCL患者以无痛性淋巴结肿大为主要症状,可伴发热、肝脾肿大。ALK+LBCL临床过程具有高侵袭性,白细胞分化抗原20(CD20)阴性的患者临床过程更具侵袭性。50%的ALK+LBCL患者伴随B症状(发热>38 ℃、盗汗、半年内体重降低>10%),44.4%的患者乳酸脱氢酶升高,57%的患者在初诊时已处于进展期,30%的患者累及骨髓。ALK+LBCL患者对CHOP样化疗方案反应差,5年总生存(OS)率为34%,中位OS期为1.83年[3]。进展期ALK+LBCL患者的5年OS率仅为8%[2]。研究发现,年龄、ANN Arbor分期、国际预后指数(IPI)评分均是影响ALK+LBCL患者预后的重要因素,局限期患者预后相对较好,禽髓细胞瘤病病毒原癌基因(myc)易位与预后较差相关[5-6]。
二、病理及免疫表型特征
ALK+LBCL的病理学特征为淋巴结结构消失,肿瘤细胞呈弥漫性浸润或窦内浸润,淋巴瘤细胞为单形性、大的免疫母细胞样或浆母细胞样[7]。肿瘤细胞体积大,胞质丰富,呈嗜酸性、嗜碱性或嗜双色性。细胞核大,居中或偏位,核仁明显,核分裂像易见,部分患者可见单核或多核的巨型肿瘤细胞或R-S样细胞[8-9]。ALK+LBCL通常具有特殊免疫表型。淋巴瘤细胞ALK呈强表达,多局限在细胞质中、呈颗粒样分布,少数患者也可在细胞核、核仁中检测到ALK强表达[10]。淋巴瘤细胞还强表达上皮膜抗原(EMA)和浆细胞标志物如CD138、VS38C、CD38,并表达多发性骨髓瘤癌基因1(MUM-1)和IgA,几乎不表达B细胞标记,如CD20、CD79a、PAX5,但大多表达BOB1和OCT2两种B细胞转录因子[3,5]。因此有学者推测ALK+LBCL可能起源于发生类别转换和浆细胞分化的生发中心后B细胞[10]。肿瘤细胞中CD30阴性,但偶有病例报道可见局限性弱表达。肿瘤细胞中T细胞标志常呈阴性,但CD4、CD57、CD43和穿孔素可能呈阳性[5]。ALK+LBCL通常发生在免疫功能正常患者,与EB病毒(EBV)或人类疱疹病毒8型(HHV8)感染无关[7]。然而,有1例HIV感染者患ALK+LBCL的案例报道[11],也有罹患溃疡性结肠炎近20年的患者服用巯唑嘌呤后继发ALK+LBCL的报道[12],尚未见EBER原位杂交检测阳性的病例报道。
三、细胞遗传学
在ALK+LBCL中,ALK基因表达的上调超过75%由t(2;17)(p23;q23)、产生CLTC基因与ALK基因融合所致;仅17%类似于ALK+ALCL,与t(2;5)(p23;q35)、产生NPM-ALK融合蛋白有关。此外,作为融合基因伴侣,SQSTM1、SEC31A、RANBP2和IGL也有报道[3]。85%的患者IgH基因存在克隆性重排。有研究报道,ALK+LBCL患者高表达磷酸化STAT3,STAT3下游的转录激活使MYC在没有MYC易位或扩增的情况下表达,ALK蛋白的致癌机制可能也涉及STAT3通路的激活[13]。由于融合基因不同,ALK融合蛋白的亚细胞定位目前分为粒状细胞质染色(GCS)和非粒状细胞质染色(non-GCS)两类,non-GCS的OS期较低,进一步证实了ALK+LBCL的预后取决于ALK融合伴侣。此外,ALK融合伴侣影响对ALK抑制剂的敏感性,在体外研究中表达NPM-ALK的细胞较表达SEC31 A-ALK的细胞对ALK抑制剂更敏感[2,14]。
四、治疗进展
1.联合化疗及放疗:目前ALK+LBCL患者的临床治疗以联合化疗为主,因ALK+LBCL患者通常CD20表达阴性,利妥昔单抗疗效受限,临床上多选择以CHOP方案为基础的化疗方案,可联合放疗;挽救治疗方案主要为基于铂类的DLBCL二线治疗方案和(或)造血干细胞移植(HSCT),即便如此,现有研究结果显示疗效仍然不佳。我们检索了中外文献报道ALK+LBCL的案例,其中治疗方案以化疗及放疗为主(不包含HSCT和ALK抑制剂)且资料详细的患者59例,汇总结果显示局限期患者预后尚佳,进展期患者预后差。采用CHOP样方案患者共45例[2-3,15-22],Ⅰ/Ⅱ期患者共19例,客观缓解率(ORR)为94.4%,中位无进展生存(PFS)期为25个月,死亡患者1例,为22岁男性Ⅲ期患者在6个CHOP方案治疗后因疗效不佳最终死亡,OS期为10个月;Ⅲ/Ⅳ期患者共26例,ORR为26.9%,中位PFS期为9个月,26例患者中16例死亡。初治时采用CHOP样方案作为一线治疗,疾病进展(PD)后改用大剂量化疗方案(HyperCVAD、DHAP和ACVBP等)共9例,均为Ⅲ/Ⅳ期患者,ORR为10%,PFS期为23个月,其中5例患者死亡[3,23]。首选方案为基于儿童淋巴瘤化疗或大剂量化疗方案5例,其中4例为青少年患者,均采用儿童淋巴瘤化疗方案,3例10~13岁Ⅱ/Ⅲ期患者一线治疗采用儿童淋巴瘤化疗方案,均达到完全缓解(CR),ORR为100%,中位PFS期为62个月[3,13];1例多部位骨和淋巴结累及的Ⅳ期16岁男性患者在LMB89方案结束4个月后复发,最终死亡,OS期为24个月;1例为伴胸部包块的ⅢA期32岁成年男性患者,采用大剂量Hyper CVAD方案获得CR,随访时间为14个月[3]。
2.造血干细胞移植:我们汇总了既往文献中共20例接受HSCT的ALK+LBCL患者[3,11,24-26],Ⅰ/Ⅱ期7例,Ⅲ/Ⅳ期13例,其中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autoHSCT)者14例,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alloHSCT)者1例,移植类型不明者5例;OS期为3~56个月;死亡12例,存活8例。接受autoHSCT的14例患者中,局限期4例,进展期10例,报道时存活6例,死亡8例,存活患者随访时间为24~56个月,死亡患者随访时间为17~26个月;3例患者在移植前为CR,随访时间为24~44个月;4例局限期患者中死亡2例;10例进展期患者10例中死亡6例,存活4例,移植前4例达到临床缓解,2例复发进展,4例移植前评估不明,移植后3例达到临床缓解,4例复发进展,3例移植前评估不明,其中1例移植前达到CR的11岁男童移植45天后死于重症肺炎伴发呼吸衰竭[25]。接受alloHSCT治疗的是1例化疗后复发患者,移植后14天获得CR,但移植后7个月时死于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26]。这些临床研究报道显示,即使接受HSCT,ALK+LBCL患者的预后仍然不佳,alloHSCT可能改善预后,但报道病例数量甚少,尚需进一步研究。
3.ALK抑制剂:克唑替尼是一种口服小分子腺嘌呤核苷三磷酸(ATP)竞争性的酪氨酸激酶受体抑制剂(TKI),可抑制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c-Met)激酶,阻断其信号转导通路,进而抑制ALK融合基因表达,从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2011年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了第一代ALK抑制剂克唑替尼用于ALK阳性的晚期、复发难治的非小细胞肺癌(NSCLC)。2021年1月,FDA也批准了克唑替尼用于复发或难治性系统性ALK+ALCL的≥1岁儿童和年轻成人患者。我们总结了中外文献中克唑替尼用于治疗ALK+LBCL的7例患者情况,克唑替尼均在疾病进展后使用,3例用于autoHSCT后复发的患者;6例采用克唑替尼单药治疗,1例与吉西他滨+奥沙利铂(GEMOX)和地塞米松联合应用;4例患者因疾病恶化死亡,3例患者为移植后复发、报道时仍存活,其中1例采用克唑替尼单药治疗获得并维持CR,至截止随访时已达16个月[3,11-12,27-28]。克唑替尼在复发、进展的ALK+LBCL中具有潜在疗效。
克唑替尼在复发或难治性系统性ALK+ALCL成人患者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尚未明确,使用过程中需警惕耐药。据报道,ALK+NSCLC获益明显患者常在1~2年内出现对克唑替尼耐药[29]。研究发现,ALK+NSCLC患者对克唑替尼耐药的机制主要包括以下4项:(1)原发性耐药:主要机制与罕见的ALK融合伴侣、BIM缺失多态性、PTEN/mTOR突变、ALK G3709A突变及KIT突变等相关;(2)继发性耐药:主要为ALK通路占优势的耐药,包括ALK激酶区突变和ALK基因拷贝数的扩增;(3)驱动基因的转换:肿瘤细胞可激活其他致癌驱动程序及信号通路来代替ALK通路;(4)表观遗传途径:包括miRNA的增强子重塑和表达的改变;(5)肿瘤的异质性[30-31]。目前克服ALK TKI耐药的治疗策略主要包括以下4点:(1)靶向ALK依赖的信号通路,如下游的STAT3信号通路;(2)靶向替代ALK的信号通路,如C-MET、C-KIT、PDGFR、IGFR、EGFR和KRAS等;(3)免疫疗法,ALK融合蛋白通过转录因子STAT3上调PD-L1的表达,临床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对晚期和转移癌有效;(4)应用ALK衍生肽触发ALK胞浆内近膜区域的凋亡信号[32]。此外,第二代ALK TKI对ALK融合突变及多种ALK激酶区耐药突变均具有活性,alectinib对中枢神经系统转移的ALK+NSCLC患者有较好的疗效,但多数患者在1~2年内仍可耐药。2018年11月,FDA批准了第三代ALK TKI劳拉替尼(Lorlatinib)用于治疗接受第一、二代ALK抑制剂治疗之后病情仍进展的转移性ALK+NSCLC患者,目前尚无第二、三代ALK抑制剂应用于ALK+LBCL的病例报道。
ALK+ALCL的体外研究发现,克唑替尼介导ALK失活导致Bcl-2水平升高,从而抑制克唑替尼在淋巴瘤细胞中的细胞不良反应,而在使用克唑替尼的同时下调Bcl-2表达,可通过增加自噬通量和细胞死亡来抑制淋巴瘤细胞增殖,提示联用克唑替尼和Bcl-2抑制剂可能有助于治疗ALK+ALCL[33]。
4.免疫疗法:(1)ALK嵌合抗原受体T(CAR-T)细胞:Walker等[34]构建的ALK CAR-T细胞在体外研究中通过裂解ALK+LAN-5细胞,并在抗原刺激下产生干扰素-γ来发挥抗肿瘤作用,CAR-T细胞的抗肿瘤应答功效受CAR表面密度和靶抗原密度调节,细胞因子的产生高度依赖于ALK靶标密度,但神经母细胞瘤细胞系中ALK的靶标密度不足以最大程度地激活CAR-T细胞,致使其在ALK+神经母细胞瘤中的抗肿瘤作用有限。(2)ALK单克隆抗体:在ALK阳性神经母细胞瘤细胞系的体外研究中发现,ALK抗体具有抗体依赖的细胞毒作用,可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研究显示,克唑替尼可诱导肿瘤表面ALK蛋白积聚,促进ALK抗体与抗原结合;克唑替尼可增强ALK抗体抑制肿瘤增殖的作用,ALK抗体也可提高肿瘤细胞对克唑替尼的敏感性;联用ALK单克隆抗体和克唑替尼较单用ALK单克隆抗体处理肿瘤细胞发现,处于sub-G0期的细胞比例更高,提示这种联合ALK靶向策略的抗肿瘤机制主要为诱导凋亡[35],为ALK靶向治疗提供了新方向。
五、小结
ALK+LBCL的诊断及鉴别诊断主要依据其独特的分子生物学及形态学特征,易误诊。ALK融合基因伴侣及ALK融合蛋白的亚细胞定位等均能影响预后,现有的国际预后评分系统无法准确预测预后。以CHOP为基础的一线方案疗效不佳,即使接受HSCT,复发难治患者的预后改善也非常有限,而首选基于儿童淋巴瘤化疗或大剂量化疗的方案疗效尚可;ALK抑制剂克唑替尼可能具有潜在疗效,但需要进一步研究。ALK CAR-T细胞和ALK抗体等新兴免疫治疗及Bcl-2抑制剂应用的探索可能为改善此类淋巴瘤患者预后提供新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