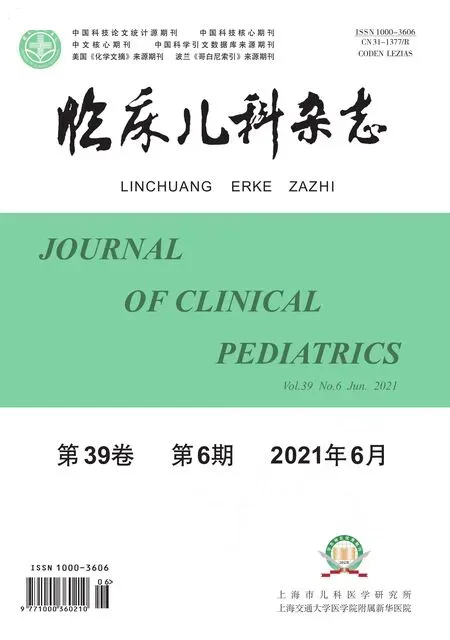短链脂肪酸与食物过敏的肠道黏膜免疫
2021-12-22李心悦综述李在玲审校
李心悦综述 李在玲审校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儿科(北京 100191)
食物过敏(food allergy,FA)定义为暴露于某种食物后可重复发生的,由特异性免疫反应引起的组织结构和功能的紊乱[1]。据不完全统计,受食物过敏影响的人群高达10%[2]。而世界范围内儿童食物过敏的患病率就高达4%~6%[3]。美国的调查显示18岁以下儿童食物过敏的患病率为8.0%[4]。我国南方12月龄以下婴儿牛奶蛋白过敏的患病率为2.69%[5]。成都市24月龄以下婴幼儿食物过敏的患病率为8.8%[6]。因此,食物过敏为世界性的健康问题,不仅可以发生在各个年龄阶段,严重的食物过敏还会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产生影响[7]。
食物过敏可以由IgE或非IgE介导,以及IgE和非IgE 共同介导。临床上以IgE 介导的速发型过敏反应多见,对人体产生多系统损害,皮肤和消化系统最常被累及,严重过敏反应可累及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甚至危及生命[1]。总的来说,导致各种食物过敏的共同机制是人体正常的免疫耐受机制不能建立,即肠道黏膜免疫系统对食物抗原的沉默反应发生偏移,转为攻击反应。发生这种偏移的原因尚不明确,除了与个体遗传因素密切相关以外,还可能与肠道物理、化学屏障损伤,抗原暴露,肠道微生态失衡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有关[8]。肠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谢产物作用十分广泛,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其对肠道甚至全身免疫功能及稳态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9]。本文对肠道微生物代谢产物——短链脂肪酸(short chain fatty acids,SCFAs)与食物过敏的联系,及其在食物过敏时肠道黏膜免疫反应中的作用及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食物过敏的肠道黏膜免疫机制
食物过敏是免疫耐受的偏移。食物免疫耐受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抗原递呈细胞参与,在肠道中主要是CD103+树突细胞(dendritic cells,DCs)[10]。抗原递呈细胞将食物抗原呈递给肠系膜和区域性淋巴结后,促使有活性的食物抗原特异性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T cells,Treg)产生,从而诱导人体建立起对食物抗原的免疫耐受反应。在免疫耐受建立过程中起作用的DCs 可称为致耐受性DCs。然而,发生食物过敏时,DCs 的表型改变转而诱导T 辅助细胞2(T helper cells,Th2)的产生,而Th2型免疫反应是IgE介导食物过敏的关键。Th 2 细胞可以直接分泌IL-4,还可促使肥大细胞或嗜碱性粒细胞分泌IL-4,IL-4 能够促进B 细胞发生IgE 的类别转换[11]。IgE 被分泌入肠道或通过淋巴系统进入循环,在局部甚至全身致敏肥大细胞和嗜碱性粒细胞,当机体再次接触食物抗原后,被致敏的肥大细胞及嗜碱性粒细胞便会释放一系列炎性物质,导致组织特异性食物过敏反应。下文中出现的食物过敏若无特殊说明均代表IgE介导的食物过敏。
食物过敏发生时,肠道上皮屏障渗透性增加,肠上皮细胞会分泌一系列细胞因子,如胸腺基质淋巴细胞生成素(thymicstromal lymphopoietin,TSLP)、IL-33、IL-25等,这些细胞因子提高DCs表面OX40配体水平,该配体与表达于活化T 细胞表面的OX 40 结合后起作用,刺激T 细胞增殖和分化为Th 2。食物过敏的动物模型显示,小鼠肠道上皮细胞表达IL-33,该免疫因子诱导OX 40 配体在肠道CD 103+DCs 的表达[12]。类似的研究表明,对受损的小鼠皮肤进行抗原刺激可诱导胶质细胞表达IL-33、IL-25和TSLP,活化真皮CD 11 b+DCs 的OX 40 配体[10]。此外,IL-33 还可通过直接对肥大细胞起作用增强IgE介导的免疫反应[13]。除了促进Th 2 转化,这些细胞因子还能抑制Treg产生。研究表明,IL-33可促进肠道第2组固有淋巴样细胞(innate lymphoid cells,ILCs)的增殖和活化,产生大量IL-4,从而抑制皮肤、肺和小肠Treg细胞的产生[13-14]。
2 短链脂肪酸
SCFAs是包含1~6个碳原子的有机羧酸,主要包括乙酸、丙酸、异丁酸、丁酸、异戊酸、戊酸,是由小肠内不被消化和吸收的碳水化合物,在结肠内经过肠道微生物的糖酵解产生。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乙酸、丙酸和丁酸。研究表明,高纤维饮食可促进肠道菌群向产SCFAs的优势菌转化以及增加SCFAs的生成[15]。除饮食结构外,其他改变肠道微生物组成和多样性的因素,如抗生素的使用、感染等,都会影响SCFAs 的产生[16]。
2.1 SCFAs受体
SCFAs 主要通过激活G 蛋白偶联受体家族(G protein-coupled receptors,GPCR)发挥作用[17-18]。SCFAs 抗炎和免疫调节作用涉及的受体主要包括G蛋白偶联受体41(GPR41,也称为FFAR3)、G蛋白偶联受体43(GPR 43,也称为FFAR 2)、G 蛋白偶联受体109 A(GPR 109 A,也称为HCA 2)及嗅觉受体78(olfactory receptor 78,OLFR78)。这些受体可在不同的细胞类型中表达,包括免疫细胞,如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还有肠道上皮细胞、肾内皮细胞等[19]。而相关受体被激活后可导致进一步信号级联反应,包括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MAPK)、磷脂酶C(phospholipases C,PLC)、核因子-κB(nuclear factor kappa-B,NF-κB)等途径。此外,SCFAs 还可通过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istone deacetylases,HDACs)来影响细胞内组蛋白的乙酰化和脱乙酰化,从而改变多种功能基因表达[20]。所以,SCFAs的作用十分广泛。
2.2 SCFAs与食物过敏的联系
SCFAs可以减轻食物过敏。在食物过敏小鼠模型中发现,高纤维饮食和外源性SCFAs可以促进小肠固有层中IgA 的产生,并提高派氏结中Tfh 的数量;在口服SCFAs 的食物过敏小鼠中可观察到过敏临床评分减低和血清总IgE 水平减低,并进一步发现SFCAs受体敲除小鼠表现出更严重的过敏反应以及血清总IgE 水平的增高[21]。同时,在牛奶蛋白过敏小鼠中发现SCFAs 能够增强口服免疫耐受治疗的疗效[22]。虽然暂时缺乏相关临床试验的报道,但动物实验均表明SCFAs确实影响着食物过敏,可能通过诱导免疫耐受来实现,具体可能机制在下文探讨。
反之,食物过敏似乎也影响着肠道中SCFAs的含量。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相比,食物过敏患儿粪便中产生SCFAs的菌群减少,而经过临床治疗并且症状得到缓解的患儿粪便中产SCFAs 菌群增多[23]。在食物过敏小鼠模型中也观察到肠道SCFAs 含量的显著改变[24]。然而,SCFAs的改变与食物过敏发生发展之间的时间关系、因果关系尚未明确。研究发现,SCFAs水平高的儿童在6 岁之前发生食物过敏的可能性更低[25]。这似乎表明SCFAs的变化早于食物过敏的发生。
非IgE介导的食物过敏对SCFAs的影响尚存在争议。曾有报道17名1~2岁非IgE介导牛奶蛋白过敏患儿的粪便SCFAs与健康对照者相比无统计学差异[26]。同年,也有报道46 例1~26 月龄之间的非IgE 介导的牛奶蛋白过敏患儿的肠道菌群及代谢产物与健康对照者相比,粪便中丁酸盐含量显著降低,而经过深度水解酪蛋白奶粉以及鼠李乳糖杆菌口服治疗并获得免疫耐受后,患儿粪便中丁酸盐水平较前增加[27]。
食物过敏调节SCFAs的作用机制尚不明确,并且肠道SCFAs 水平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如是否母乳喂养、添加辅食种类、抗生素及益生菌应用等,因此生命早期肠道菌群及其代谢产物处于波动中。所以在对SCFAs影响因素的合理控制下,未来需要样本量更多的纵向队列研究揭示SCFAs 的动态变化与食物过敏之间的联系。
2.3 SCFAs对食物过敏的肠道黏膜免疫调节作用
SCFAs 具有复杂的免疫调节能力,其对食物过敏的肠道黏膜免疫影响可能是通过诱导免疫耐受的建立实现的,如影响消化道的上皮屏障和防御功能;作用于固有免疫细胞(如树突状细胞等),调节固有免疫;调节由T细胞和B细胞介导的抗原特异性适应性免疫。
SCFAs可以增强肠道黏膜屏障。首先,SCFAs能促进上皮细胞产生特定细胞因子来增强黏膜屏障,如IL-18和抗菌肽。研究发现,盲肠灌注丙酸可上调猪肠道中IL-18 的表达[28]。IL-18 可来源于肠道神经系统神经元,并作用于肠道上皮细胞中的杯状细胞,促进抗菌蛋白的表达,参与维持肠道黏膜屏障的稳态[29]。虽然,SCFAs对上皮细胞来源的IL-18具有促进作用,但其与肠道神经系统来源的IL-18之间的联系尚未见报道。此外,在动物模型中发现,丁酸可能通过作用于肠道上皮细胞的GPR 43,在mTOR 和STAT 3 介导下促进抗菌肽表达[30]。这些研究均表明SCFAs 在加固肠道化学黏膜屏障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SCFAs还可通过抑制HDAC 和激活AMP-依赖的蛋白激酶(adenosine 5’-monophosphate-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促进上皮屏障紧密连接和黏蛋白表达,从而增强肠道物理黏膜屏障。特别是丁酸能够影响紧密连接蛋白的功能,包括促进occludin及 Zonulin-1从胞质向紧密连接的转移,抑制促通透性的Claudin-2表达,增加体外跨上皮电阻[31-32]。细胞实验表明,SCFAs可以通过调节MUC2启动子处组蛋白的乙酰化/甲基化诱导MUC2 mRNA启动子的激活,从而促进人肠道杯状细胞分泌特异性黏蛋白MUC2[33]。近来的研究发现,在结肠炎的小鼠模型中,SCFA 可以通过调节肠上皮的氧耗稳定HIF的表达,从而促进肠道屏障保护性基因表达,降低肠道通透性和减少细菌移位,但具体作用机制仍待进一步探究[34]。
SCFAs 在固有免疫方面的作用主要为通过调节DCs及相关细胞因子诱导Treg产生。研究发现,高纤维饮食喂养的小鼠TSLP和IL-33基因表达明显低于低纤维饮食喂养小鼠,并且将两种饮食结构的小鼠DCs 与幼稚T 细胞共培养后发现,高纤维饮食喂养小鼠的DCs 具有更强的诱导幼稚T 细胞向Treg 转化的能力[21]。在体内外实验探究其中可能的作用机制中发现,SCFA 可通过诱导肠上皮细胞中的视黄醛脱氢酶(retinaldehyde dehydrogenase,RALDH)的表达促进视黄酸(Retinoic Acid,RA)的产生,又进一步在细胞实验中验证SCFAs对RA的代谢调节作用是通过抑制HDAC 活性实现的,而RA 可促进致耐受性DCs 的产生,并与DCs共同诱导Treg的分化[35]。
SCFAs 除了上文提到的SCFAs 可通过影响固有免疫来间接促进Treg数量和功能,还可以通过直接促进Treg 的生成作用于适应性免疫。在动物和细胞实验中均观察到丁酸能够提高Treg的数量,并且发现丁酸可能通过抑制HDAC 活性增加细胞内Foxp 3基因位点的乙酰化,诱导Foxp 3基因的表达,而该基因的表达则是Treg 细胞发育和分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步骤[36-37]。在体液免疫方面,SCFAs可促进B细胞类别转换并且分泌IgA。研究发现,高纤维饮食喂养的小鼠肠道中分泌IgA的浆细胞数量增多,并且在体外实验中证实SCFAs 能够上调浆细胞分化相关的基因表达,包括Aicda、Xbp 1、Irf 4、Prdm 1和Sdc 1基因[38]。SCFAs 对基因表达的调控很可能是通过抑制HDAC活性实现。在小鼠以及细胞实验中均发现SCFAs 处理后的B 细胞的总体HDAC 活性降低。另一方面,SCFAs 能够为B 细胞分化提供能量,在细胞实验中观察到SCFAs能够降低B细胞的AMP水平和AMPK活性,增加乙酰辅酶A 和ATP 的水平,从而维持B 细胞分化的高代谢需求。同时,与对照B 细胞相比,用SCFAs培养的B细胞通常体积大于对照B细胞,并且具有较高的Ki-67表达。为了探究SCFAs是否增强机体对病原体的抗体反应,研究者用鼠源性啮齿杆菌感染小鼠后发现低纤维喂养的小鼠更易被感染,而高纤维喂养小鼠的肠道及脾脏中IgA +B 细胞数量增多,对抗病原体的黏膜抗体反应增强[38]。而另一方面,SCFAs 能够通过调节其他免疫细胞来间接调控B 细胞,在体内及体外实验中,SCFAs 能够促使滤泡辅助性T细胞(T follicular helper cells,Tfh)生成增多,而Tfh 则促进B 细胞活化并且分化为产生IgA 的浆细胞[39]。由此可见,SCFAs不仅可调节T细胞,还能够影响B细胞表型,具有十分广泛的免疫调节作用。
2.4 SCFAs的应用前景
SCFAs 相关制剂已应用于临床治疗。研究发现,丁酸钠灌肠可减少因炎症性肠病、大肠癌或憩室炎行肠造口术后患者的肠黏膜萎缩[40]。还有研究发现,丁酸钠口服能够减少憩室炎发作,提示丁酸可能具有预防憩室炎的潜力[41]。这些研究均表明SCFAs 对于改善肠道炎症具有一定疗效,但是具体给药方式以及剂量仍需大量的研究工作。截至目前,尚无SCFAs治疗食物过敏相关的临床试验,但相关的动物实验均提示SCFAs在改善食物过敏,诱导免疫耐受方面具有一定疗效。因此,在更充分理解SCFAs作用机制的基础上,SCFAs 很可能成为治疗食物过敏极具有潜力的方法之一。
综上,食物过敏的发病率正在逐年增高,影响着越来越多人的健康。食物过敏主要与人体免疫耐受的偏移被打破相关,已有大量证据表明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产物SCFAs在其中起着正向调节作用,然而作用机制尚未明确,非IgE 介导的食物过敏发病机制仍有待探究。这些研究将有助于规范临床对食物过敏的诊断标准,发现可能的治疗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