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变局形势下的世界历史研究
2021-12-20刘德斌
刘 德 斌
2020 年以来,中国学界围绕“百年未有之变局”的讨论不断深入,尽管参加者多为国际关系学界中人,但历史学界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参加进来了。讨论不断深入的一个突出标志是焦点不再仅仅集中于百年变局的界定和表现,而是深入到新形势下相关学科所要探讨的新问题和新领域中来了。这对历史学科是一个重大挑战,因为历史学家往往喜欢与现实保持一段距离,不愿意让变动中的现实影响自己的历史思考,倾向于等待尘埃落定之后再去追溯事件的来龙去脉。但今天人们遭遇的现实不同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接连不断,大变局正在我们眼前发生,正在一个已经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世界上发生,置身其中的人们已经难以对当今世界的重大变故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特别是当其他领域的学者都已经“涌进”历史领域,探索大变局的源起和趋向的时候,历史学家就更难作壁上观了。
关于大变局形势下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见仁见智,我认为有这样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坦陈如下,供学界同仁批评。
一、回应西方学界“历史的回归”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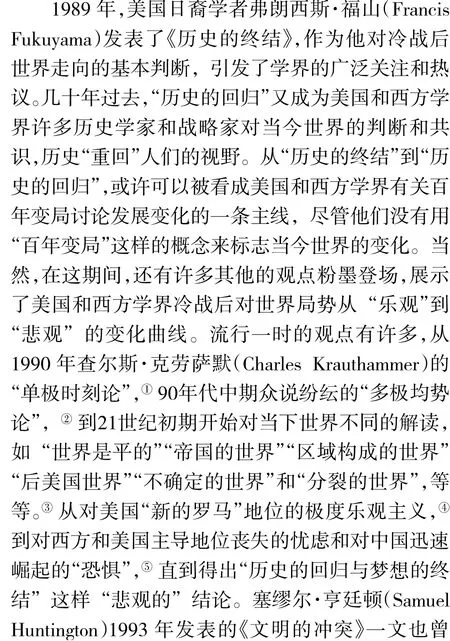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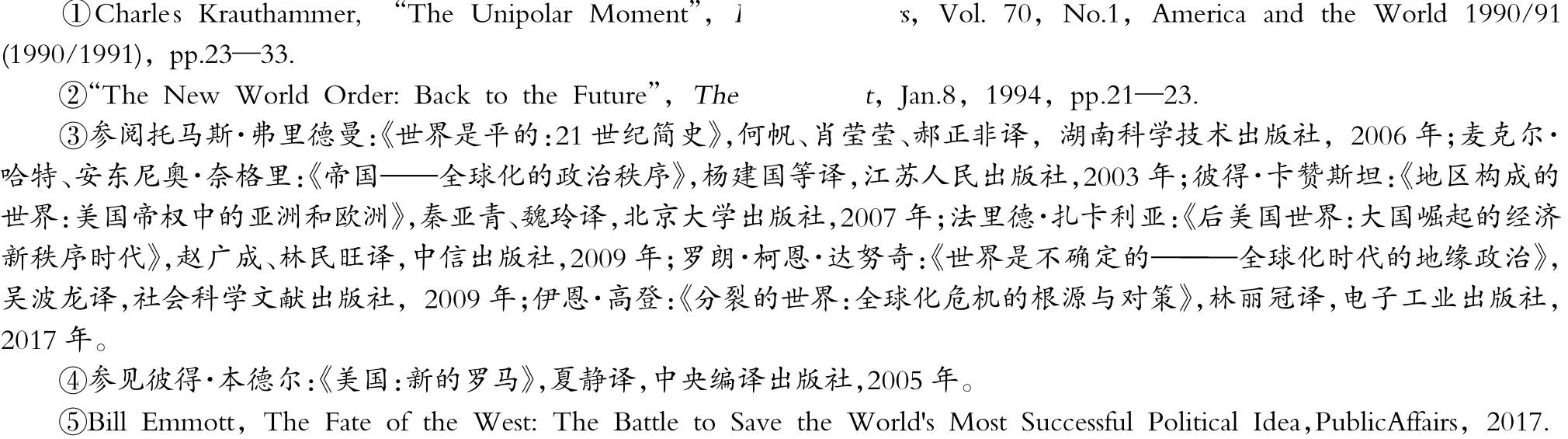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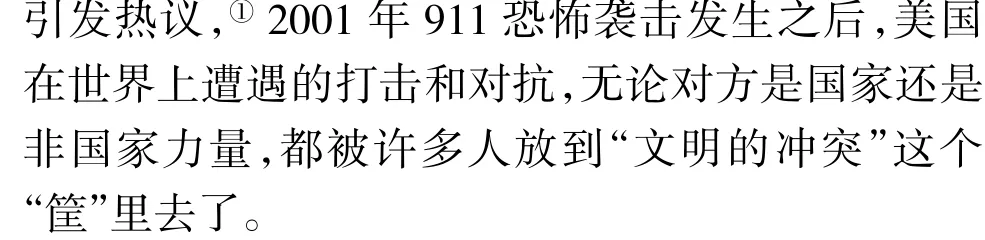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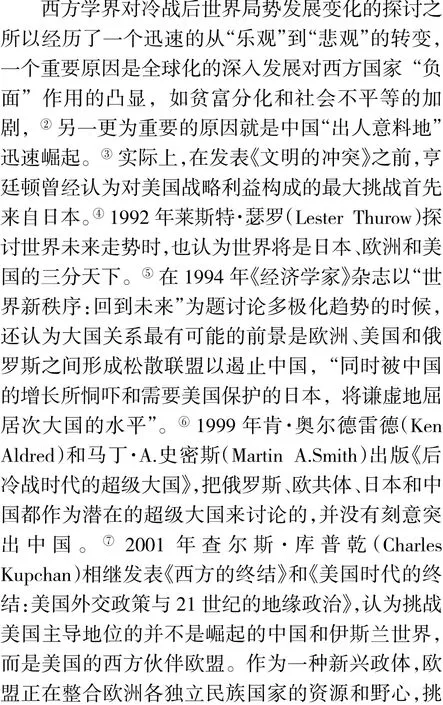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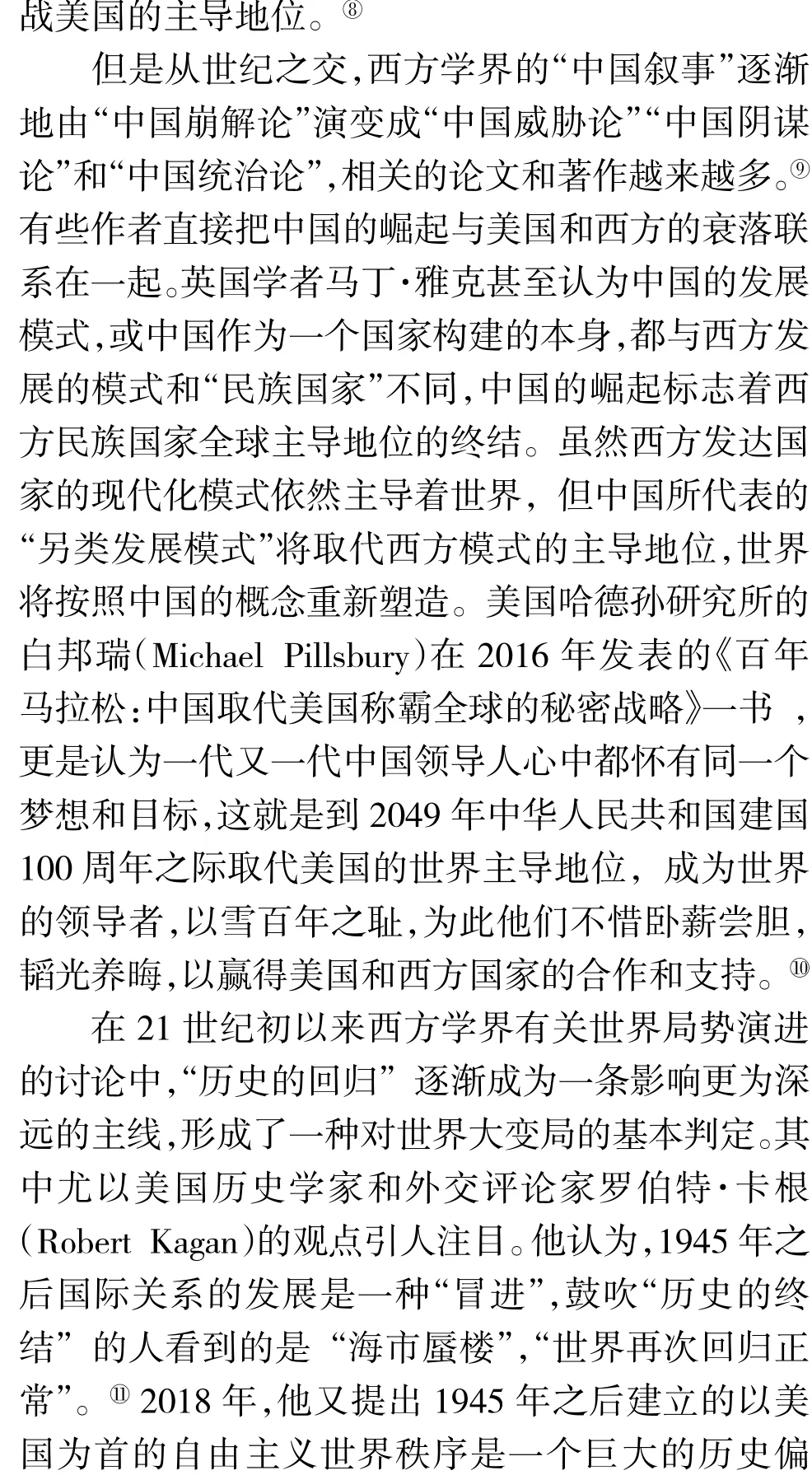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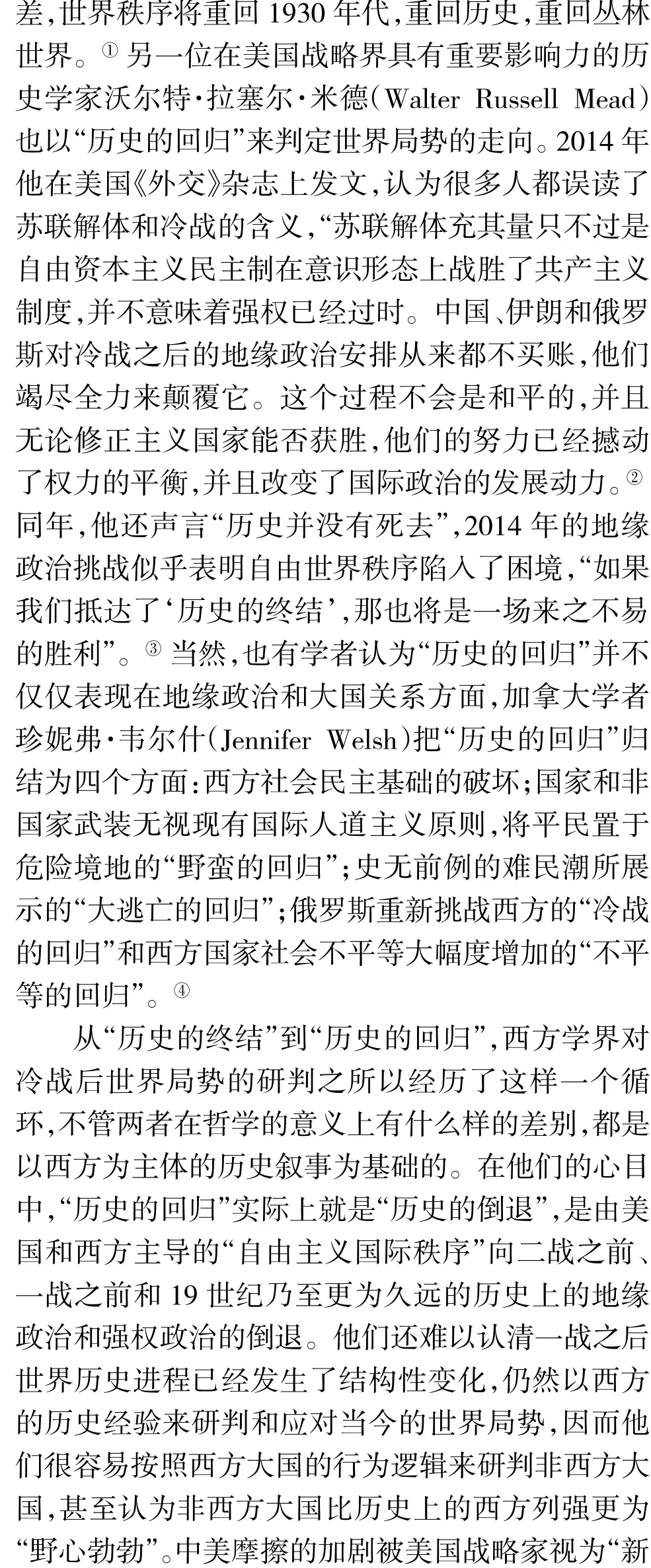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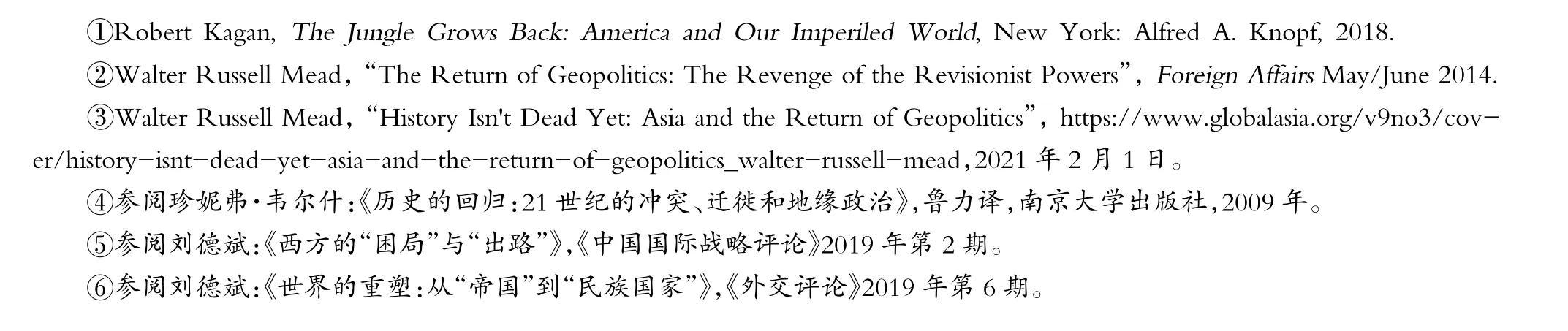
二、大变局的历史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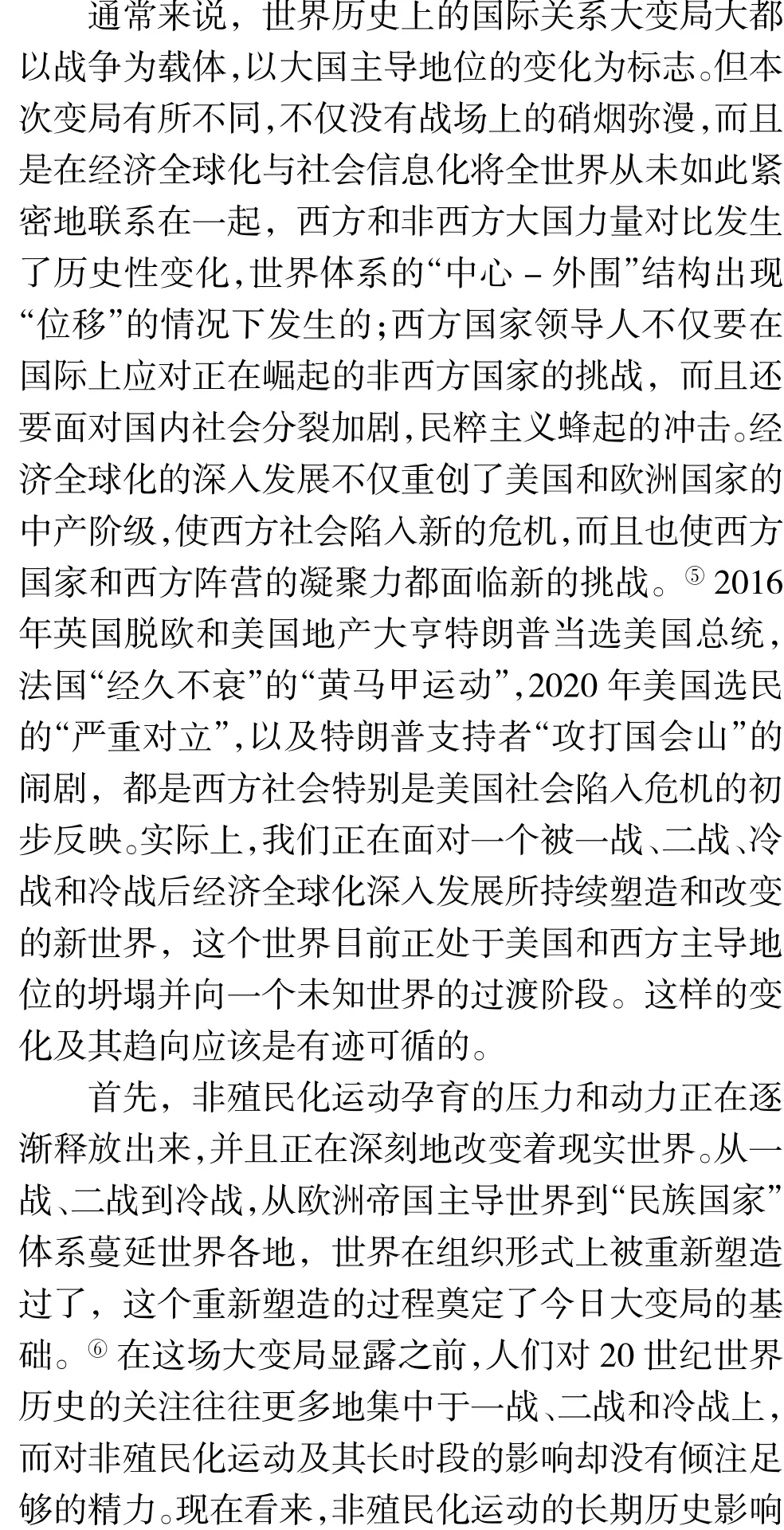
可能会超越一战、二战和冷战,成为历史学家和战略家编撰新的世界历史教程和判定世界局势的重要考量。首先,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都是在非殖民化运动中“构建”或“再构建”起来的,新兴国家不仅构成了冷战中的“第三世界”,也构成了冷战后世界在数量上的“基本盘”。随着东西方冷战的终结和西方主导世界地位的坍塌,大国干预新兴国家内部事务的动力、能力和意志都在减弱,一批新兴国家在经历了种种“主义”的实验和磨难之后,纷纷走上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成为当今世界大大小小的所谓的“新兴经济体”,有的甚至已经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概言之,“第三世界”国家的精神面貌已经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和分化。第二,新兴国家中的新兴大国在冷战后表现更为“抢眼”。新兴大国不仅构成了冷战期间“第三世界”的中坚力量,而且还能够在冷战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乘势而起,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实现跨越式增长,成为西方大国不敢小觑的力量,甚至成为西方主要大国的竞争对手。第三,尽管还有新兴国家在国家构建的道路上挫折不断,甚至沦为“失败国家”或“脆弱国家”,但随着新兴国家医疗水平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提高,随着人口出生率的提升和死亡率的下降,新兴国家大规模的人口增长正在逐步成为当今世界大变局持续发展的“有生力量”。他们或者已经成为新的劳动力大军,使所在国家和地区在卷入全球化的过程中得享“人口红利”;或以移民和难民的身份流亡欧美,不仅弥补了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步入老龄社会之后劳动力的不足,而且还改变了那里的人口比例,甚至重塑了部分大城市的地方文化。据统计,二战之后世界人口持续增长的大部分来自新兴国家,特别是非洲大陆,而且到2050 年,世界新增人口的50%将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总之,非殖民化运动所释放出来的压力和能力正在逐步增长,并且正在改变西方所主导的世界历史进程,而且这个改变的过程可能刚刚开始。
第二,经济全球化的多重效应。随着冷战之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历史进程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全球贸易总额和全球财富的大幅度增长,并使亿万新兴国家的贫困人口从贫困状态中摆脱出来,而且还呈现出这样几个“出人意料”的结果:首先是非西方世界的崛起,特别是非西方大国的崛起,改变了近代以来西方与非西方力量对比,其中尤以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影响巨大,被认为重新塑造了欧亚大陆的战略格局。其次,新一轮全球化在缩小西方与非西方国家经济差距的同时,加剧了西方社会的贫富分化,削减了中产阶级规模,促使社会不平等再次成为触发西方国家社会矛盾的主要问题。实际上,这一过程在冷战结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但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的深入进一步加剧了西方社会分化和分裂。面对非西方国家的强势崛起,美国和欧洲国家陷入一种新的社会危机,很多政客把这场危机归咎于资本、技术和就业机会的外流,归咎于经济全球化和新兴国家的贸易政策,全然不顾新兴国家在这一轮新“优化资源配置”的分工体系中所提供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不顾新兴国家和人民在融入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所付出的资源、环境和社会的代价,并对新兴国家的产业升级持排斥和打压的态度。这是世界历史进程中一种新的结构性矛盾,中美摩擦就是这种新的结构性矛盾的突出例证。第三,随着这种新的结构性矛盾的生成和发展,世界体系“中心-外围”的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中心”国家增多,规模扩大,一批新兴国家逐步进入到“中心”中来,而一批原来意义上的“中心”国家和一些“中心”国家的落后地区则面临着沦为“外围”国家和地区的压力,甚至已经成为新的发展中国家或发达国家中的“第三世界”。尤为重要的是,在这个历史进程中,非西方国家之间形成日益密切的新的协作关系,进入了更为独立自主的发展时期,西方学界甚至出现了“一个没有西方的世界”(A World Without the West)的说法,[1]Naazneen Barma,Giacomo Chiozza,Ely Ratner and Steven Weber,“A World Without the West? Empirical Patterns and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Vol.2,2009.以美国和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秩序的物质基础正在解体。
第三,新的技术革命正在为大国兴衰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塑造新的历史条件。我们正在迎来一场新的技术革命,这场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生活、工作以及彼此之间的相处方式。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利用水和蒸汽的力量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第二次工业革命利用电力实现了大规模生产,第三次工业革命采用电子和信息技术实现了生产的自动化,那么我们正在经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则是在第三次革命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数字革命。这场革命的速度、范围和对各种体系的冲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与此前的工业革命相比,第四次工业革命不是以线性速度前进,而是呈几何级增长,正在迅速地改变着人类社会所有行业的发展模式。[1]克劳斯·施瓦布、尼古拉斯·戴维斯:《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魏薇等译,中信出版社,2016 年。这场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正在改变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为新兴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加剧了大国之间在新技术制高点上的竞争,同时也在改变人类社会的组织形态,拉近了不同族群、宗教和社会之间的距离,让世界不同地区的国家和民族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前三次的工业革命助推了西方的崛起及其世界主导地位的确立,并把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推广到全世界,促使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地区都按照“民族国家”形式组织起来,同时也把全世界分割成“中心”和“外围”、“西方”和“非西方”两大部分,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则与新一轮的全球化相向而行、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把不同国家、地区和族群更为紧密地聚合在一起,为人类社会组织形式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历史条件。
三、世界历史研究的新课题
大变局为中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开辟了新天地,亟需研究的新课题和有待开辟的新领域有许多,学界对此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尤为重要的是构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史阐释体系,将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更多地纳入到国际关系史的阐释体系中来;其次是拓展共同体研究领域,汲取不同人类共同体之间相互交流的经验,重新阐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与世界关系。
随着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世界历史正在迎来一个百年未有之变局。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已被打破,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正在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国际体系正在经历近代以来最重大的变化,这为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近代以来的世界历史进程及其对当下的影响,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一条主线就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欧洲走向世界,以西欧国家为蓝本的“民族国家”取代了部落、城邦、王国和帝国等“前现代”国际行为体,成为人类最普遍的组织形式,“民族国家”也因此构成了国际关系理论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但是,在“民族国家”的表象下面,不同地区国际行为体演进的方式差别巨大。在欧洲,出现了欧盟这种新的超国家主权的共同体组织形式。但是在非洲和中东,部落组织依然存在,并在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在预测现实的时候屡屡失败,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把非西方的历史经验纳入到国际关系理论的构建之中。
国际行为体的历史演进也就是人类历史上不同形式的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为解决当今世界问题指出了一条新的思路。这个思路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敢于在民族国家相互竞争的世界上,提出了超越国家之间固有矛盾,在不断扩大和拓展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案。重新梳理历史上不同共同体发展和演变的线索和规律,总结和阐释它们相处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无疑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阐发和传播,同时也为世界历史理论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提供新的理论思考。
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而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有待进一步的讨论和阐释。在这其中,对“何为中国”的反思或许是重构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关系的起点。在“欧洲中心论的”影响下,中国在世界历史的阐释中长期作为一个多面的“他者”而存在,既是一个《躁动不安的帝国》(文安立),[2]Odd Arne Westad,,Basic Books,2012.又是一个《停滞的帝国》(佩雷菲特),[3]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年。现在到了中国历史学家厘清中国的真实身份及其与世界历史关系的时候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多种共同体的凝聚和整合,是多种共同体的共同体。中国在消除国家纷争,推进共同利益,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方面,应该比欧洲国家富有更多的经验和智慧,承接世界更多的期许。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依然在调整和磨合之中,重新构建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但追问“中国是什么”、梳理中国经验并将其纳入新的世界历史叙事体系是最为重要的基础和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