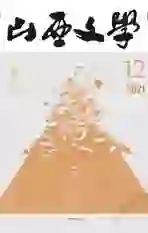一棵诗意行走的树
2021-12-18郭剑卿
还是阳春三月的时候,海平兄寄赠他的第四部散文集《太阳很红,小草很青》,一个平实拙朴的书名,坐落在简洁明快的封面上方,红日绿草飞鸟的画面,天地人居中,万物生长各得其所。一个步履矫健的身影,正从太阳红小草青的地方出发,开启他行者无疆的旅程。这个构图写意非常切合生活中的作者形象,迈开大长腿,身背长枪短炮,捕捉人间风景乐此不疲。是怎样的驱动力让他成为一个行吟诗人?高海平自己发明过一个词汇:“绿色欲望”。“故乡山野的绿色欲望,其存在不仅仅是一种标本,坚强旺盛的绿色基因已经植入那片沃土。”(《那抹绿》)把这段话拿来作他的夫子自道,也未尝不可。
我们是大学同学,同窗四年无多交往,甚至连说话交流都少之又少。原因无他,都是青涩羞涩的年纪,都从县城中学考入高等学府又加性格内向,还没有具备男女同学大方交往的“素质”。那时候全班十个女生都在前排就坐,男生居后,印象中高海平因为长得瘦高屈居教室末座,每天进教室必得从前到后全程穿越,总是大步流星翩然而过。及至大学毕业之际,在毕业纪念册上给每一位同学留言成了我们最隆重最认真的一个仪式。高海平给我的留言十分“惊愕”:“刺破青天锷未残,剑卿堪称好汉!”龙飞凤舞两行字,虽让我一头雾水至今不解,反倒给我留下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好汉”印象。果然,一向低调寡言的他,大学毕业到了声名显赫风头正健的语文报社,一鸣惊人成为我们羡慕的“高记者”。没过几年,处女作《带女儿回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出笼,洋洋洒洒几十万字,谈天说地评头论足涉猎广泛,摇身一变成了我们班第一位“高作家”。接下来是“高社长”“高书法家”“高师傅”——因为他的摄影技术了得,我尊称他为“师傅”,一半是戏称,一半是佩服。海平端的好汉也!眼花缭乱的多重身份中,我最看好的自然是记者作家高海平,有沉甸甸的作品为证:《一抹烟绿染春柳——高海平散文中学生读本》(北京日报出版社2016)《我的高原 我的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2017)《太阳很红,小草很青》(北方文艺出版社2021),200多万字的散文创作,一种高原红日气象喷薄而出,不由感佩他满目青山的绿色襟怀,“映出心底的绿野仙踪”,却又透着金秋沃野的成熟饱满。人常说“五十而知天命”,读山水、识形胜、窥探世事,怎样调和出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欣然坦然自然?我从中读出一种渐入佳境的人生况味,也捕捉到一个被作者忽略了的好题目、一个绝妙意象:一棵诗意行走的树——地之子和行吟诗人的完美结合。
学者赵园先生认为,“‘地之子’应属于五四新文学作者创造的表达式。中国现代史上的知识分子,往往自觉其有承继自‘土地’的精神血脉。”(赵园《地之子·自序》)这土地就是他们的“故乡”。故乡,是中国现代作家心中挥之不去爱恨交加的一片厚土。在鲁迅以横眉冷对为主打的表情包中,虚构的《故乡》或非虚构的《朝花夕拾》,这些篇什无疑是他最动情的文字。“乡土文学”派作家群的出现,几乎是现代中国作家故土书写的集大成者。蹇先艾叙述贵州的《朝雾》是 “借以纪念从此阔别的可爱的童年”,许钦文给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取名为《故乡》,在鲁迅看来,都是“被故乡所放逐,生活驱逐他到异地去了,他只好回忆‘父亲的花园’”。(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如果说这是早期现代中国作家被迫挤出的“乡愁”痛苦,在高海平这一代作家,背离故土是一种主动选择,也是人生奋斗的理想。《一道坎,迈了三次》堪称全家合力为他实现奔异乡走异途而“奋斗”的三部曲,也是当代农家子弟百看不厌的“金榜题名”正剧。令人吊诡的是,一旦离开故土在都市安居乐业,乡土记忆就变得异常鲜活,故乡宿命般成了创作的母体,也是游子眼中“这边独好”的风景。从处女作《带女儿回家》不难看出,他的文学起步于“回家”,领着城市长大的女儿,告诉她《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如数家珍般讲《乡间故事》《乡间乐事》。写给中学生的散文读本《一抹烟绿染春柳》,充溢着一个《语文报》资深报人的殷殷情怀,他希望能传递给孩子们已然淡漠的故乡情愫,懂得从山水行走中收获敬畏哲思和温情,从阅读中收获文字晕染的“一抹烟绿”,找到心灵的家园和精神的故乡。如果说前两部作品寄托一个地之子的温情,《我的高原我的山》则凸显一份豪情。开篇依然心系“故乡情思”,但此时的故乡已然内化为作家的精神高地,异乡观澜、枕边听雨、河畔回眸,不妨视他乡作故乡,百川归海无不流向地之子心中那块高地,艺术化为“我的高原我的山”,这份一览众山小的霸气是需要底气支撑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故乡已经烘托成为一种境界。走到这步田地,前面竟是《太阳很红,小草很青》!出乎意料之外,却在情理之中。我被他这个代入感极强的命题所吸引,跟随“师傅”看“遍地风流”,听“荒腔乱弹”,不亦快哉。
顺理成章地,所谓遍地风流,在他的景区里,首先绕不开的永远是故乡。只要踏上通往故乡的《那条路》,就会“看”到《那把镢头》,地之子生命深处潜在的农耕文化基因就会被激活,“直接深入土地寻找泥土的芳香,探索生命的奥秘”。关于这一点,作者也曾夫子自道,称之为感情的“重新回归”。在评价同乡一位乡土诗人王晓鹏时,感叹他们脱离不了的“宿命”:“当年都有逃离故土的记忆,为了求生存,逃离故土像逃离瘟疫一样,那种心情足以让故乡哭泣,让故土悲痛欲绝。如今,又在感情上回归,即使肉体不能重返故土,感情的回归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乡村出来的诗人或者作家经历的心路历程。”在我看来,所谓感情“回归”,何尝不是作者的一场自我寻根自我指认。走遍千山万水,抑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终将认同一种“宿命”,故鄉是地之子 “爱”的源泉与归宿。重拾每一个故乡记忆,体味每一个令人萦怀的细节,于高海平而言,是握住记忆的根脉,也是品味活着的感受,为自己找到不绝的生命之源。一条瓜蔓一个萝卜不无故事,家族内外人情世故都有来历。他信手打捞的农家农事农具故事,分明是在认知和体恤自己的生养之地,沿途亲历的人和事都成为自我确认的历史证言——除了真实的“乡土相”,也画出心灵的真相。虽然有时感叹失去了远方故乡“春光灿烂的窑洞”,在他的意识深处,不曾有知识分子的文化优越感,也不曾居高临下去悲悯,他会带着儿时的鲜活记忆津津乐道爷爷《那把镢头》,对“闹庄稼”的人拥有一把称手的农具爱不释手。在乡村泥土经验里长大的少年眼里,“我家的镢头有好几把,唯有爷爷的那把好用。刃口闪着白光,镢把光滑颀长,抡起来像一道闪电”,“爷爷手里的几件家具都是这样让人眼馋”。哪怕是如今成为记者作家,仍然不改对爷爷传授的乡村哲学的深深认同:工具是有灵性的,常使用勤打磨懂爱护,工具就会善待你。地之子无疑是一个诗意的旁观者,带着浓情敬意挖掘祖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乡村经验,收藏到自己的记忆深处,这样的诗情和哲理,无疑会滋养强壮一个以“地之子”为宿命的文人的肉体和精神,让他诗意的行走更加踏实坚定。
当年诗人舒婷曾这样解读顾城的诗:“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是的,每个文人总有一双自己的眼睛,有选择风景的“特异功能”,也有汲取养分的智慧。作者不以诗人自居,但并不妨碍他活成“一棵诗意行走的树,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受到什么样的风霜雨雪洗礼,双脚在大地上是踏实的,把生命的根牢牢扎在大地之中,是幸福的”——读这样的文字,你会发现他对“诗意”有着如土地般朴实的理解。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经历过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诗意”就是放学回家母亲笑盈盈端出香喷喷的饭菜,“你深深地呼吸了一下,恨不得把飘溢的香味全吸进自己的肚子里,那种满足感就是诗意”。这种从一瓢饮一箪食一呼吸当中滋生的“诗意”,恰是最形象生动可感的阐释。这也使得作者具备了一个地之子可贵的潜质与禀赋:置身喧嚣浮躁的都市,偏喜发现、捕捉那些熟悉的鸟虫传出的清音;熙来攘往争先恐后的红尘中,总能保持不急不缓的步履,省略过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朝着太阳红小草绿的地方出发。哪怕在高楼看城市上空,目光似乎依然习惯性飞越到乡村:夏日窗外 《那些熟悉的鸟虫》发出不同的鸣声,思绪会宿命般沿着根性蔓延到乡村,作者念念不忘的是,这些进城的鸟儿在乡村还有巢吗?《盛大的叶子》里看秋风起舞,“风像赶羊群的牧羊人,打着口哨,扯着羊鞭,追赶叶子們回地面就像赶羊归圈”;冬天倏忽而至的《那场雪》,吸引眼球、触动思绪的是雪中的腊梅、麻雀、喜鹊、白鸽,它们无不延宕出作者骨子里的绿色之思自然之趣。
打动我的还有他对万物有灵亦有命的切肤体认。在晋北考察草木稀少的长城古堡,一眼认出故乡晋南田野上常见的刺蓟,牵引出儿时削刺蓟的传神描写:“镰刀触动刺蓟的神经,刺蓟会下意识地跳动,跳动时能看见刺蓟的欢悦。这种感觉在仅仅维持一秒钟之后就会化为极度的痛苦,痛苦之后就是无声无息,刺蓟的生命消逝了。”一株野草,激起写作的灵感,乃是源于万物平等的常识性真理,由此,那蓟疙瘩被作者赋予了独立存在的意义:“它默默地长在某个角落,接受阳光的检阅,接受自然的熏陶。蝉在山野鸣唱时,它是无语的;蛇在洞中先把尾巴伸进去,慢慢把整个身子缩进去,刺蓟也看见了,并不稀奇;我在刺蓟前,用相机对其‘咔咔’地拍照,刺蓟的形象精准地摄入了镜头,定格成永恒,刺蓟也没觉得多么不可思议。”《瓜蔓儿》写故乡的地垄爬满了“贱命”的南瓜,“像一个外子,借了别人的地盘扎根”,“出色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南瓜的命运就是如此,“生性卑贱,其实很好吃,也有营养”。然而让他动心动容的不是“金贵和娇气” 的西瓜和甜瓜,而是在城镇化的今天,当南瓜们离开土壤,被摆进城里的菜市场后,那根维系生命的蔓儿还在吗?这种看似“矫情”的追问,其实透出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隐忧和寄意。鲁迅说过,“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高海平则说,“心中有爱,诗意才有所附丽。”不无道理。
高海平写农家农人农事农具,带着生命的味道,挟着土地的诗意,不乏地之子磊落坦荡的“根性”。这使他自动跳脱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拂去“乡土文学”派的伤感乡愁,有“遍地风流”的自在自足,却是脚踩土地贴近生活的。在评价刘亮程的散文写作时他认为“作家采取了‘向下’的方式,把自己深深地扎在土地之中”,“同时又把故乡置于崇高之上,仰望着村庄,仰望着故乡,仰望着土地”。不妨把这段话看作高海平的写作追求。在他笔下,故乡既不是时时“蛊惑”“哄骗”游子回头的“诱饵”,也不是供“逆子”们批判破败愚昧甚至劣根性的代名词,贾平凹式的视故乡为“血地”也不免沉重。故乡于高海平而言,就是他呼吸其间的空气,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日子,是植入坚强旺盛的绿色基因的那片沃土。我突发此想,假如没有这样的体认感悟附着其上,这些文字也许不过是“碎片”化的流水账。特别要指出,假如没有经过个人化的修辞表达,有关故乡记忆就是平淡无奇的铺陈。我特别喜欢他的“那”系列——《遍地风流》首先收入的是十多篇“那”字打头的短章:《那条路》《那抹绿》《那场雪》《那把镢头》《那本书》《那个血色黄昏》《那束光芒》《那一抹灰色》《那些人》《那些熟悉的鸟虫》。我相信这不是单调的重复而是一种有意为之的感情修辞。它是作者轻音乐般的抒情音符。往事与故人有了一份审美的距离,一份谈天说地的优裕,几许端详几许遥望,少了执着与拘泥,平添从容与超拔。每个作家写作背后都有一束光,映照出自我与历史的面容,从而有了属于他自己的别一种味道。作者让我们记住故乡的同时记住了那些有着生活智慧、灵魂散发泥土味道的人物——爷爷父亲母亲,老师邻居朋友,同窗同事乃至哥们儿。散漫的人与事,因围拢在作者笔下而升腾出生活的况味。
作者向我们描画着他用心灵的眼睛所看到的“遍地风流”,“乱弹”着心灵深处的“荒腔”,有些是借了通往故乡的记忆之桥,有些是借着客居城市、人在旅途的见闻,叩问历史也好,解读文学也罢,他既不“矫情”,
也不“卖弄”,只如熟人相对,娓娓而谈,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使我们在这喧嚣浮躁的时代,感到一种生活的本真色相:“太阳很红,小草很青”。大道至简,大欲有色——这欲望却是一派绿色!身居闹市,窗外那些鸟们——麻雀、喜鹊抑或罕见的珠颈斑鸠,不过是一抹灰色飞过,却牵动观者最敏感纤细的神经,幻化出令人惊喜的一抹亮丽。让你又一次感受其内心“绿色基因”的强大惯性。(《那一抹灰色》)高海平看世界,目光是专注的,内心是敞开的,语调是明快的,姿态是谦和的。惟其如此,他才能这么平静地娓娓而谈。读山水、识形胜、窥探世事,经由他笔下形成一条有“阅历”有温情的珠链。文人雅客寻访名胜古迹,每常“约定俗成”预设为游山玩水之余的诗兴大发,一不小心就陷入附庸风雅的窠臼俗套。在高海平笔下,遍地风流的发现,凭的是脚踏实地的丈量、叩问与确认。《寻访古堡》《代州行》都是这样的篇什。炎炎夏日匆匆路过薛富成故居,无知的偶遇变成肃然起敬的邂逅,作者放慢了谦卑的脚步,却坚定了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决心。(《访薛富成故居》)农妇怀抱羊羔进古城门洞的动作、乡人淳朴友善的表情,都能触动他的温情想象。(《寻访古堡》)你能感受到他对周围《那些人》的注目与动情:“我依偎着周围那些像萤火虫一样的人,他们所发出的光,温暖和烛照着我。”书房摩挲凝视《那本书》,品味“合住是静静的物质,打开便是纷纭的世界。能在字里行间探秘,还有与书为伍的亲密感和新鲜感”。在《那个血色黄昏》听朋友讲亲人的早逝,听出了一种“无事的悲哀”的人生况味;《绿宝石花开》则在友人善待花草动物的故事中获得心绪的温润,氤氲出灵魂的香气。驻足或举步,在作者都是一种汲取,向外,在路上摄取故乡抑或异乡的营养;向内,则在阅读中丰富自己的魂灵,“要发见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世界,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鲁迅语)经由这样的书写,作者在遍地风流的寻觅和荒腔乱弹的吟唱中,何尝不是追求生命和精神的双重滋养。“就像庄稼的生长需要充足的养分,一个人的人生——无论其身份地位民族种族——不仅需要阅历和远行,也需要根植大地的底气与安然。” (李小江语)一番自我寻根与确认,让高海平的文学生命平添一份丰沛健硕。这样的创作状态对一个作家而言是可遇不可求的幸运。正如秋八月的《萝卜红了》,故乡发明的上等绝配羊肉红萝卜饺子,“好吃到让人欲罢不能,飘飘欲仙”。更有意味的是,“一个美妙的时间段,默默无闻的红萝卜、白萝卜被我推举为八月乡村最美的风景,浸染故乡的山野、田苗。”
创作真是一件难以十全十美的事情。写得“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广”,“所感觉的范围却颇为狭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写得高而广,又不免流于虚浮宽泛。“既有思想的光芒,也有生活的色彩,”是高海平给自己设定的一个标尺,他用自己三十多年的耕耘,孜孜不倦一步一个脚印地靠近那个地标。文学是有年龄的,读罢掩卷,不知不觉,那棵诗意行走的树立于秋天的沃野,我的耳畔想起《垄上行》的旋律,眼前浮现米勒《拾穗者》的画面,敞亮的灵魂有一束光,也有一种笃定的力量。
【作者简介】郭剑卿,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