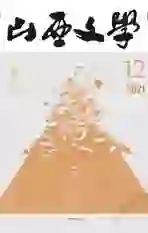“泥塑”之道兼及聂尔散文断想
2021-12-18王朝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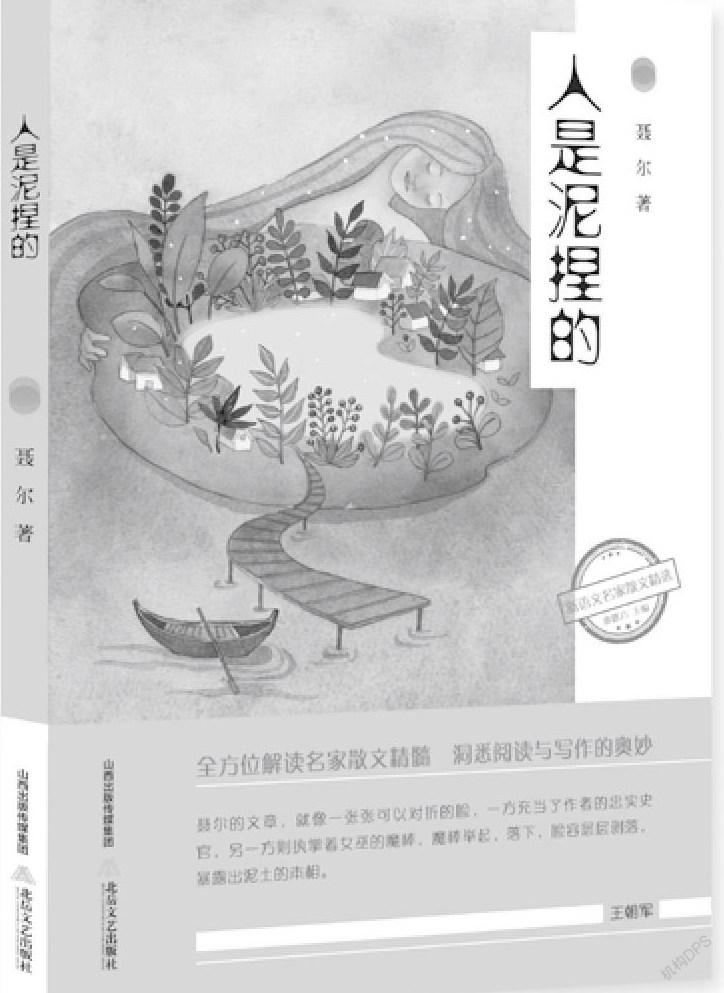
无趣的人不希望别人也无趣,这是普遍心理。所以我在面对评论对象(这里指文学散文)时总期待他或他的作品是有趣的。唯有趣,才能补偿我的无趣。但即便是如此卑微的小确幸,也很难实现,常常是:失望从起点一路忍耐到终点。然后,我的脑袋里塞满虚无。
我惧怕虚无,就像我惧怕一篇文章的始作俑者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他的前身、他的先驱、他的祖先……总之,就是那个站在前写作期,拽住他思想衣角的既定程序。文章写完了,里面却没有他,他始终在复制粘贴别人的声音。这岂止是无趣,简直是无聊。但我们又怎能苛责众多的散文家呢?他们生活在被深度符号化的世界,当他们开始写作时,他们早已习惯了真理在握的感觉,而那个“真理”是绝对的、封闭的、不可置疑的,他们要做的事,就是把真理重重包裹起来,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抖落之。为了凸显真理的重要性,他们不惜笔墨给真理拖上一条长长的尾巴。尾巴很漂亮,很光滑,给人一种心理的过渡,不过它也仅仅是过渡,注定会消失。就像猴子的尾巴在人身上消失一样,连带真理本身都失踪了。
是的,在现代汉语散文领域,有趣者甚少,如聂尔般的有趣就更是稀缺了。稀缺才稀罕,才有见到宝贝便想占为己有的冲动。于是我效法《西游记》中的老和尚将聂尔的散文“借来一观”,以期长长久久披上这缀满珠玉的袈裟,度化那个无趣的自己。结果呢,我愈看得清楚就愈自卑,“不是真僧不敢穿”哪,还是把它留在原处,老老实实地摩挲一番为上策。
然后我就摩挲出一种目光,它属于孩童,或者说它被预设为来自孩童。它正奋力穿过小主人的双眼,辨认这陌生而广大的天地。这是一种直视事物的眼光,在它的路径上没有人类经验的背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藤蔓,只有新鲜的、透明的感官,它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世界的图景诚实地映现在它背后那面心灵的镜子上。因此,它在《王莽岭看雪》中看到的就不再是李白杜甫的雪、老舍的雪、普希金帕慕克的雪,也不再是“独钓寒江雪”或雪落人群的喧闹,而是它独自认领的雪。“我看见了光在每一处的变化,风在雪地留下的痕迹,林中细弱的草如何与雪纠缠。”还看见“野鸡脚印。它那清晰的三根指头印下的脚迹,形成一条直线,仿佛一行自然的密码,静谧地指向路边深沟”。很难说这些发现都是拜孩童眼光所赐,但它们会造成一种时间上的错觉,让人以为这就是人类最初看到的事物的模样,最“简单”、最直接、也最真实。所以当我们跟随作者发现光之于雪的秘密时,同样为之惊喜。因为我们信了。而这信,并非源自已知,而是源自未知,或者说是将已知转换为未知。此时,作者已悄然将我们的目光滑动到历史开始的位置,他要带领读者重新勘探和编纂这个自以为无比熟稔的世界。
这多有趣啊,因为我们的好奇心有了满足的可能。谁都知道,未知的世界里遍布“奇遇”,既然王莽岭的高处有,生活的低处也应不遑多让。这不,《短暂的猫咪》和《我家里的空气》便将“奇遇”落实到了匍匐在地面之上的人间。
猫咪是带着庄严的使命来到作者家的,这使命很实用,因此也很短暂,就是抓老鼠,除此之外,在作者眼里猫并无他用。可猫咪并没有沿着人类规划的蓝图行事,非但抓没抓着老鼠成为一个谜,还留下了斑斑“劣迹”。
窗台以及其外别样浓重的夜色,茶几下搁板上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隐秘通道,地板上的每一条砖缝直至其每一寸光洁的空无之处,还有我那久已无人光顾的大写字台荒凉的表面,以及我家所有可能的角落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
当然,省略号里还藏匿着一条猫咪极不得体的罪状,那就是在妻子的被窝里睡了一整天。这是猫咪诸多“劣迹”的延伸,也是它最终被决定赶出家门的直接诱因。在此之前,猫咪就像一个傲慢的女王,在它的领地上巡游,尽管该领地狭小而局促,但它总能在复杂的局面里寻找到一条鲜为人知的通道。对,就是“鲜为人知”,当作者和他的同类还在汲汲于生活的功用时,猫咪却以它短暂而偏僻的行程揭开了这个世界的内在奥秘。事物由此脱离了“合法”的认识轨道,重新在我们生活的平面上耸动、拱起,直至“呈现出如同山峰一般的高度”。
一切都变得有趣起来,猫依托行动与人争辩的同时,居然真的把人“说服”了:“它总是显出一副悠闲而毫无负疚之心的样子,它难道知晓人心总是不欲深究罪恶,甚至是迷恋于犯罪的?”这等于是在说,人同猫心,心同猫理,只不过人类忘记了自己还有野性,还有不驯,还有粗糙但蓬勃的生命活力。在人的被窝里睡觉又怎样?那不是恰好证实了人生活在规矩里却看不到自己的事实吗?——这当然不是怂恿我们“犯罪”,而是向我们表明猫咪的“无用之用”,即它已经“捕捉”到一个蹿出人类经验(抓老鼠)之外的生命法则:我们在,就必须出具一份在的证明。
在《我家的空气》里,聂尔就出具了一份强有力的证明。他以普鲁斯特式的耐心和敏感,精心搜集了各种身份的空气,并为空气钻探出味道。商人家是“交换”,官员家是“凝固”,艺人家是“膨胀”,农家是“童年”,穷人家是“凛冽”。如果将这份味道料理手册依次罗列下去,可能需要穷尽聂尔的一生,况且即便如此,他也很可能会感叹“人生太短”。因为类似的事,普鲁斯特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干过,他动员了周身所有的官能,也仅仅将清晨的市声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拖拖拉拉了三十多页。聂尔知道这事儿唠起来没完,所以他明智地选择适可而止,味道学研究的方向也迅速转向了自身,转向了“我家”。
“我家的空气”是怎样的呢?在妻子眼里,是“万千飘荡的尘埃”;在女兒劈波斩浪的身姿下,是摄于威严的“动荡”;到了作者的鼻端,则是一寸一寸的书的味道。我就知道作者会将空气最终收拢到书里。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宿命,不谈书,你难道让他谈股票不成?
但我关注的不是这些,我关注的是语言本身的幽默和躲闪在幽默之间的智慧。何以幽默?在聂尔,则是汪洋恣肆的想象,还有对自身经验的高度执着。你看,诸种空气在他心灵感官的扫描之下,显映出一帧帧风景的奇观。而在这些奇观中,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以及人的所有感觉,都经由联想和想象的加工、转换、淬炼,释放出精神的“味道”。这些精神味道长久地潜伏在时间深处,等待想象的密钥将其激活。聂尔直觉地找到了密钥,也就唤醒和穿越了他的“普鲁斯特时刻”——通过嗅觉瞬间开启记忆中某个时刻的特定感受。
举证并不困难,例如“戳指可破”的如绸缎裹着一具华丽胴体的《追忆似水年华》,例如“阴暗潮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例如可以把人变作幸福的蚯蚓的浑身“土味”的卡夫卡。就算离开了书和书的作者,聂尔也能在事物之间建立惊险的、偏远的联系。
写农家空气的味道就是一例。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时常走入的,或者就是我们从那里走来的、农家的空气。农家的空气里洋溢着童年的味道,这是很容易闻见的,因为它以慢过时间许多倍的速度,在一个深底缓缓地流淌着,当我们离开几十年之后回来,那弥留的味道仍然还在。如果不加避讳,可以说那里的味儿稍显污浊,但这浅浅的污浊正是慢的表征,正仿佛数百年的气味积聚在这厚墙之内,造成了不同于空气的又一种物质,以保证可以从中提取出豆腐渣似的乡愁。
嗅觉上的“稍显污浊”,浅浅的,淡淡的,给人以心理时间的“慢”,甚至这慢还要“慢过时间许多倍”,在视觉上则体现为“在一个深底缓缓地流淌着”。继而通过“积聚”委身于现实的厚墙。现实是什么?现实自然是浓郁的乡愁。但因了感官的有效接通,这乡愁就不再是一种形而上的观念,而是味觉接收到视觉信号后的创造性成像:豆腐渣。“豆腐渣”和乡愁,这两种分别处于物质与精神两端的事物,围绕“童年”记忆达成了一致。
——我断言,幽默就在这“豆腐渣”的体内。如果你有足够的乡村生活经验,乃至你的童年也在乡村度过,你定会对此会心一笑。豆腐渣是乡村生活的常见物;论资历,完全承当得起“数百年”的时间长度;它身上散发出的味道也的确给人以浅浅的污浊之感;而它细碎如蚁的颗粒状,不正像童年记忆的残片吗?至于豆腐渣这种并“不体面”的乡村食材还给作者留下过什么其他印象,我们不得而知。但当你隔开岁月的距离,重新把目光投向农家时,“豆腐渣似的乡愁”很可能让你的鼻腔里涌动着放纵与怜悯、嘲谑和忧伤的复杂感情。
这便是乡愁,它无限小,又无限大。这也是散文的基本伦理,它不一定要做“大事”,讲“大道”,但它要体验并肯定“自由”,在意义世界的海洋里享受探险的乐趣。
这一点聂尔比谁都清醒,所以他在文章的末端行使了彻底的“自由”:“沉默”或“沉默之味”。他解释说:“我要我家的空气只充溢着从未有人描述过的空无之味。”既是空无,本无色无味无形无声,但聂尔还是忍不住在想象中构筑了它的形体(默之丘山)、声音(音乐的声响)和气味(天堂禁果一般的异香)。当然还有色彩,那是吞噬整个世界的纯然的黑。在此,空间的几何学和时间的心理学赋予了“沉默之味”以终极的形象和品质。聂尔也得以雄辩地确认了自己的在。没错,他在,他才能做出选择和行动,他才能在“书写”的行动中“啃啮”出一片智慧的天地。
哈罗德·布鲁姆说:“真理之有趣并不亚于真理之严肃。”由是观,然也。
其实我读聂尔的散文,更想读到故事。于是我根据标题,极尽猜度、推测之能事,挑选了几篇自以为可以偷窥其“私人细节”的文章,依次是《我的女儿》《我的写作故事》《我的恋爱》《父女之间》《审讯》 《我的儿子》。我想象,这些名字上一定叠印着丰盛的故事,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少女山鲁佐德,她在国王身旁的每一个夜晚都是故事的容器,因为白昼一旦降临,故事即刻终止。
不过,我窥人“故事”的私欲很快就被故事本身阻挠、改造,变得严正起来。我知道我的内心起了某种化学反应,造成这种反应的核心介质则是“真心”——基于文章里那个“自我”的严肃的赤诚的真心真情。也就是说,聂尔拒绝向我提供一个纯粹的自洽的“他者”的故事。想听故事,你可以去读小说呀!他时不时从故事中“跳出来”,提醒我的正是这一点。他还提醒我:对于文学散文,没有人情是会短命的。——这句话的原型出自电视剧《潜伏》:“没有人情的政治是短命的。”人情是什么?人情就是人的真心本心素心赤子之心,就是推己及人、破除执念,就是谦卑审慎、虔敬万物。而有了真心,才会看到真相。
这不是玄学的演绎,而是关于散文写作至关重要的认识论立场。人首先得对自己的认知限度保持应有的警觉,知道自己的“无知”,知道世间万事万物除了自身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想到的之外,还有更多更难以意料的可能。甚至有时,这些可能性会否定我们的“过去”,杀死我们的“已知”。我们犹疑、困惑、跌跌撞撞,不断在自我质疑和辩驳中更新对事物的认识,体认生命和世界的广阔真相,也同时确认我们自己。说到底,正是因为“无知”和“有知”的相伴相生,那个“我”才得以成立。
所以好的散文就是民主精神的集散地,它会生成一个开放的对话空间,而“我”则小心翼翼地发出聲音,接纳来自各个方向的责难、非议,从中求证“我的”信与不信,并由此出发,赶赴新的未知疆域。
现在,聂尔为我们贡献了这一过程,也一步步敞开了围绕自我的多个心灵侧影。
“我的女儿”在她成长的各个时间刻度上给予“我”的连续性惊讶和不解,让“我”我逐渐意识到:生活原本就是自由意志的最佳试验场。
“我的写作故事”并无多少奇崛之处,但它的每一次变奏,都是“我”学习在写作中盛放自己肉身和灵魂的转换器。小学五年级时,作文被老师改写后的那一段,“成为永远的缺憾,成了我的心灵鸡汤里的一粒老鼠屎”;升入高中,在病床上翻成语词典,“一个个成语故事成为我的病中童话,它们教会我过去的人们如何在古代汉语里进行人生得失的计算”;上大学时尝试写小说而失败,这才理解“实际上我们的自我认识很多时候是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安慰和欺骗均来自别人,我们只是不自觉而已,我们把它看作是坚强和耐心”;大学毕业后,因在评论征文竞赛中获一等奖,被调入专门机构做理论编辑,而“我”却对这个称号痛恨有加,“这个称号给了我双倍的压力:一方面我必须为此名称往自己的脸上涂上一层理论的假面,这使我颇不自在;另一方面,我暗地里进行的小说练习成为一种僭越、一个阴谋,使我越加不能放开手脚”……
“我的恋爱”起初近乎于“自我牺牲”,但当“我”好不容易迁就现实,即将摘得爱情果实时,爱情的成本效益学卷土重来,再次将“我”灭失在同一条河流。“他们绝不会向人的情感让步。他们面对自己的情感,也是这样的态度。这是因为,情感是没有任何社会价值的,因而它是一种应该被普遍加以克服的东西。人们不应该有情感,只应该有特定情况下的需求。人怎么会对情感有需求呢?这就是他们的信条。”无疑,这也是生活对作者的“奖赏”:它直截了当地拆除了幻觉,显露出坚硬的内质。
好了,还是不要跟进下去了吧,《父女之间》那个惊慌失措的父亲,《审讯》里那个被推迟的判决,《我的儿子》中那个活在“我”想象之途的儿子,乃至聂尔的其他文章,就像一张张可以对折的脸,一方充当了作者的忠实史官,另一方则执掌着女巫的魔棒,魔棒举起、落下,脸容层层剥落,暴露出泥土的本相。
嗯嗯,“人是泥捏的”。聂尔恰好有一篇以此为题。但我认为,这个标题本身,就是需要人的一生才能写就的散文。
(此评论系为聂尔最新散文集《人是泥捏的》所写。《人是泥捏的》将由北岳文艺出版社于2021年内出版发行。)
【作者简介】王朝军,笔名忆然。文学评论家,鲁迅文学院第36期高研班学员。山西省作协首届签约评论家,大益文学院签约作家。获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文学评论奖。曾任《名作欣赏》副主编,现供职于北岳文艺出版社。发表文学评论、思想随笔若干。出版有评论专著《又一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