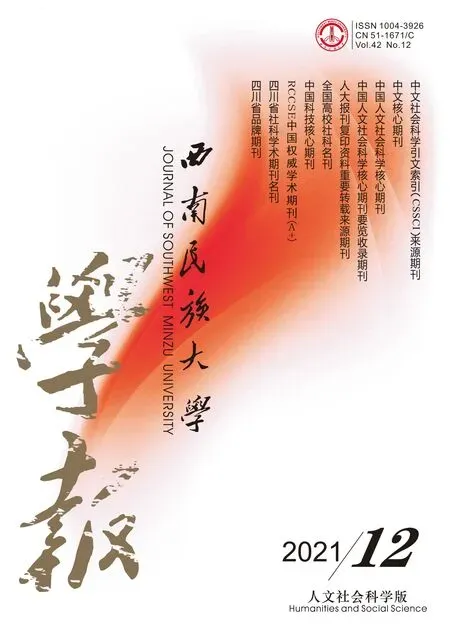金铜之辨:藏传佛教的“疑伪经”之争
——松巴堪布与土观呼图克图有关“佛典”问题之争论
2021-12-15落桑东知
落桑东知
[提要]公元1782年,松巴堪布针对藏传佛教中有关“佛典”问题,撰写了一部颇具“文本批判方法”的辩论文。同年,作为其高徒的土观呼图克图,对上师之观点作了“纠谬之事”。本文通过分析诤论文中两者对藏译佛典之形成、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的性质及掘藏文献的真实性等问题的不同理解,展现他们对“佛典”概念的不同诠释。继而,又将两者诤论之意义,置入到藏传佛教史脉络谱系中,以期凸显其思想史意义。
在亚洲腹地各国、各民族吸收佛教的过程中,佛典之译介是最重要的工作。然而,随着译典数量的不断扩大,精英阶层在辨认佛典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随之产生了“疑伪经”的概念。关于“疑伪经”的准确定义,目前学界还有争论。本文遵从佛教传统,以佛亲口所说或佛认可者为 “经”,不符合这个标准而妄称为“经”的,则是伪经;真伪难辨者,则为 “疑经”。汉藏佛教界都存在疑伪经的辨别传统。18世纪在清朝宫廷尊享皇家礼遇的两位著名藏族学者——松巴·益西班觉与土观洛桑却吉尼玛师徒对此问题的不同诠释,既与佛教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意识有涉,也反映了藏传佛教学者独特的视域。
Matthew Kapstien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末,最早对这场诤论作了拓荒性的研究,为学界介绍了诤论背景,并对“佛典”这一概念作了富有启发性的分析①。2019年才让教授对《陀罗尼集》中的文本作了细致的对勘,为进一步研究疑伪经相关文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笔者在两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试图以较为微观的方法,展现诤论中对“佛典”的不同诠释,其中第二、三、四部分与双方诤论之焦点有关,第五、六两个部分阐发其思想史意义。
一、辩驳文写作及其缘由
松巴堪布·益西班觉(sum pa mkhan po ye shes dpal 'byor 1704-1787,以下简称“松巴堪布”)晚年针对藏传佛教中有关“佛典(gsung rab)”问题,撰写了一部颇具“文本批判方法”的专著《清净佛典·净化水垢之澄水宝珠》(gsung rab rnam dag chu'i dri ma sel byed nor bu ke ta ka)②。根据后记及其自传,这是松巴堪布在79岁高龄时,即公元1782年,在佑宁寺撰述③。关于为何写作此书,松巴堪布引用萨迦班智达(sa pan kun dga' rgyal mtshan 1182-1251)《三律仪论》中的经典说法以作依据。萨班在其著作中坦言,若经典的要义被篡改(gnad bcos can),那么经典就会整体性地失去其意义[2](P.102)。其次,松巴堪布着眼于宗教救赎之功效,认为若“教法(lung gi chos)”被曲解,那么善男信女就会蹉跎暇满人生,最终也不会得到解脱。如此,辨认“佛典”对他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工作。
土观·洛桑却吉尼玛(thu'u bkwan blo bzang chos kyi nyi ma 1737-1802,以下简称“土观呼图克图”)作为其弟子,在松巴堪布付梓刊印其书下半年,就撰《回驳文·澄水宝珠之擦拭》(dgag lan nor bu ke ta ka'i byi dor),对上师之观点作了“纠谬之事”④。土观呼图克图也引了萨班《三律仪论》中的说法,但此处显然是另作他用,从自身视域对“佛典”作不同的诠释,认为经典的词句是次要的,其所诠之义才是首要的。他写作此文的另一个目的,就是劝导缺乏是非判断之人,停止再造“毁法之业(chos spong gi las)”而堕入恶趣,从而也否定了松巴堪布作品的形而上意义。
二、藏译佛典之形成问题
松巴堪布对藏译佛典形成之看法,集中体现在其对《陀罗尼集》中“疑伪经”的辨认方面。他认为《陀罗尼集》中有52部“疑伪经”,并逐一进行了文本分析,最后以七个论点总结了他的理由:(1)首题梵藏名称不一致(thog ma'i rgya bod skad kyi ming byang mi 'dra ba);(2)首题尾题不一致(mgo mjug gi ming yang mi mthun pa);(3)存有显密经论中未曾出现的大量新措辞(mdo rgyud dang rgya bod mkhas pa'i gsung dang 'dra min gtam gsar mang ba);(4)存有布顿大师校勘的《密咒集》中未收入之诸咒(sngags na bu ston rin po ches zhus dag mdzad pa'i sngags 'bum du med pa sna tshogs);(5)混杂经续语与自造词(mdo rgyud kyi tshig dang rang bzo'i gtam 'dres pa);(6)密咒中掺有苯教、密咒师之粗语(sngags la'ang bon dang bod sngags kyi khyim pa'i blun tshig sogs 'khyal gtam gyis bslad pa);(7)行文和密咒中似有汉语、突厥语,另有既非梵语亦非蒙藏文之混杂语(tshig dang sngags nang rgya nag dang yu gur skad 'dra dang gzhan rgya hor bod gang gi'ang min pa'i 'dres skad)。从松巴堪布的理由看,佛典中夹杂有本土文化因素的西藏语,是他关于藏文佛典疑伪经形成问题上采用的最主要的分析工具⑤。
土观呼图克图针对松巴堪布因经文掺杂有“西藏本土语”而将其剔出佛典之做法,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理路。归纳起来,土观呼图克图在三个方面展开了他的反驳。第一,土观呼图克图对语言表述与语义表达间的关系作了不对等的处理。从佛法的观点着眼,若其宗旨违逆四法印,那么无论其语言如何优美、文笔无论如何高雅,也不能将其归入佛典之列。与此相反,若符合四法印的宗旨,间有掺杂本土语,其作为佛典之属性即无法消解。第二,密咒中掺杂西藏本土语,并不是判定伪造佛典的充分条件。土观呼图克图分别列举了噶当派、格鲁派和萨迦派所认同的数部续典中的相关案例以作论证。第三,佛以无量众生之言讲法,结集者亦以诸种方言结集。土观呼图克图在此虽有宗教神秘主义之旧染,但更多的是否定以梵语作为佛典唯一之原语的主张。
两位对判定正统佛典之标准的不同诠释,根本上也是印度佛教一直关注的议题。印度佛教关于“何为佛典”的问题意识,从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大乘佛教,最后到金刚乘佛教,一直都按照各自的历史和教理语境,提炼出不同的标准,形成各具特色的解释类型⑥。在佛教世界中,“佛典”是一个流动的概念,每个佛教宗派传统上都有属于自己的佛典文献群,此宗派的某部佛典,可能被彼宗派视为疑伪经。譬如,“大乘非佛说”即是某些小乘派别的说法。此即是,说所谓佛典,不是“一元谓词(one term predicate)”,即不能说“某某是佛典(being canonical)”,而是“二元谓词(two term predicate)”,即“某某对某某来说是佛典(being canonical for)”[3](P.121-122)。在特定的语境下,某部佛典只对某种类型的佛教宗派,有其佛典属性的有效性,而不能笼统地覆盖所有的佛教宗派。对佛典概念建构一个统一标准,并付诸每个经典文本,其复杂程度可想而知,也难达其目的。
在佛教传播亚洲各国的过程中,存在卷帙浩繁的译典,这使得印度佛教所讨论的佛典问题,导入到更加错综复杂的场域。面对源源不断的译介,本土佛教徒逐渐意识到了辨认佛典的难度,开始编订各种形式的经录,以期区分佛典与疑伪经。在藏地,密教续典的真伪历来是大师们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续典乃印度佛教最晚出的文献群,藏传佛教各派对其佛典之地位是公认的,然而对某些续典之印度来源是存疑的。这种对续典“来源”问题的深切关注,其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将旧译派的大部分续典视作有问题、有缺陷的,进而未收录至《大藏经》,而由宁玛派人另编为《宁玛十万续》。
近来学界提出的“灰色文本(Gray Text)”概念,使得传统基于“来源”而辨认真伪的认识有了新的思考空间。此说认为印度佛教自始至终都有“经典创作的文化(Culture of Scripture Composition)”,这在密教续典生成中更加明显。大成就者们(Siddhas)的短小精悍的诀窍或修习引导书,后来经过修订扩充而成为续典。在密教盛行的7至11世纪,这种对其经典的体系化(Institutionalized)改造广为流行,造就了在短短四个世纪之内密教典籍的大量涌现。当这种经典创作的文化在西藏流行之时,却遭到了质疑和批判,首当其冲的就是对旧译派续典的否定,其理由是这些续典之“来源”有疑——出自藏人之手而不是来自域外。然而,新译派中存在的,在藏地由印度班智达和藏族译师合作而形成的“灰色文本”,既不是完全由藏人炮制,亦非在印度佛教界业已完成,从传统基于“来源”考察真伪的视角,本应是“非法”的,却成了“合法”的⑦。譬如,有些印度班智达在进藏途中,打听藏族人的喜好,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经典创作,随后又与译师一道将其翻译为藏文[4](P.212)。这类“灰色文本”的存在,为我们呈现了真伪之别更为复杂的面向,同时也需要纠正传统上依据“来源”而作出的判定。
三、藏文《大藏经·甘珠尔》性质问题
经过藏传佛教前后弘期数个世纪的翻译实践,译典数量可谓数不胜数。对于如此庞大的文献群,如何辨别其作为佛典的真实性?松巴堪布认为,是否收入历史上相继编纂的各种《甘珠尔》刻写本及其目录,是审定之依据。在此我们先梳理,他认为哪些《甘珠尔》及其目录是合法的。首先是吐蕃时期的藏文佛经三大目录,之后依次是钦·姜贝央(mchims 'jam dpal dbyangs13世纪中叶)从元廷寄送笔墨等物资,在纳塘寺首次刊行的《甘珠尔》纳塘古写本及目录(1312-1320年),蔡巴·贡嘎多杰(tshal pa kun dga' rdo rje 1309-1364)编纂的《甘珠尔》蔡巴写本及目录(1347-1351年),江孜法王·热丹更桑帕(rgyal rtse chos rgyal rab brtan kun bzang 'phags 1389-1442)编纂的《甘珠尔》廷邦玛写本及目录(完成于1431或1432年),噶玛红帽系·京俄却扎(zhwa dmar spyan snga chos grags 1453-1524)与郭译师·循努贝('gos lo gzhon nu dpal 1392-1481)编纂的《甘珠尔》钦瓦达孜宫写本及目录(具体时间不详),丽江土司木增请噶玛红帽系·却吉旺秀(zhwa dmar chos kyi dbang phyug 1584-1630)校订的《甘珠尔》丽江—理塘刻本及目录(完成于1615年),明永乐时期《甘珠尔》永乐刻本(目录未知,完成于1411年),卓尼土司捐资刻成的《甘珠尔》卓尼刻本及目录(完成于1731年),康熙时期官修《甘珠尔》龙藏写本(目录未知,完成于1669年),颇罗鼐·索南道杰(pho lha bsod nams stobs rgyas 1689-1747)勘刻的《甘珠尔》纳塘新刻本及目录(完成于1732年),德格土司出资刻印的《甘珠尔》德格刻本及目录(完成于1733年)⑧。
松巴堪布将是否载于这些《甘珠尔》版本及其目录,作为判断佛典真实性的标准,这就意味着《甘珠尔》是佛典结集的最终形态,其结集也处于闭合的状态⑨。佛典结集的这种闭合状态,在解释上就无法避免两种困境:(1)它是否覆盖史上所有的藏译佛典,是否存在未收入《甘珠尔》的藏译佛典?藏译佛典历史之长、参与译师之多,使得编纂者无法搜集所有的译本,并将其整理入编,这是不争的事实。另外,由于编纂者个人的主观判断,致使无法收编也是有可能的。(2)佛典数量浩如烟海,是否有未藏译之佛典?若有新译的佛典出现,其闭合状态是否要为之敞开?
土观呼图克图对佛典之结集问题,与松巴堪布持相反的立场,他更加倾向于经典结集始终处于开放的状态,有一个动态持续的入编过程。他最为重要的一个理论依据,就是汉译佛典对《甘珠尔》的补阙功能:“汉译佛典中尚有未藏译之多部佛典,谓《勇行经》者,遍知章嘉已藏译。”三世章嘉呼图克图(lcang skya rol ba'i rdo rje 1717-1786)主译的这部佛经,确有单行本存世,其全名为《御制证得如来秘密成就义之因显明诸菩萨万行佛顶勇行之大乘经(十卷)》。此经是汉传佛教影响极大的一部大乘经典,全名为《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简称《楞严经》,据传是唐朝时期的汉译佛典[5]。此单行本还附有译经题记,据此我们可知此经藏译之始末。乾隆时期(1752-1763年)敕修满、蒙、汉、藏四体合璧《首楞严经》,并撰《御制楞严经序》。御制序中写道,“今所译之汉经,藏地无不有,而独无《楞严》”,这是《楞严经》藏译之原因。然而,《楞严经》藏译古本在西藏并非完全不存在,“藏地中叶,有所谓狼达儿吗汗者,毁灭佛教,焚瘗经典时已散失不全”。此处所说“散失不全”确有其根据,早期佛经目录中确实提及了两个藏译古残本。在吐蕃时期编纂的《丹噶尔目录》第259号录有《圣大佛顶之显魔品》('phags pa gtsug tor chen po las bdud kyi le'u bstan pa),600颂,2卷[6](P.140)。纳塘寺堪布·觉丹热饶(bcom ldan rig pa'i ral gri 1227-1305)在其所撰佛经目录《教法兴盛·庄严之光》第11章“译自汉地、于阗(rgya dang li las bsgyur ba'i le'u)”中录有《大佛顶之魔品》(gtsug tor chen po bdud kyi le'u gnyis bam po gnyis),2卷[7](P.53-156)。《布顿佛教史》中除了前述第一个译自汉地之古译本外,又提及了另外的一个译本,即《大佛顶经》(bcom ldan 'das kyi gtsug tor chen po'i mdo)。之后,《首楞严经》的这两个藏译残本在不同的目录中出现,也在相关大藏经刻写本中刊印。
土观呼图克图以汉译佛典《勇行经》为个案,指出藏汉文大藏经互通有无之必要,以此为径路阐发了《甘珠尔》之结集是无限敞开的观点,因此也不能将其收录与否作为判定佛典真实性的标准。松巴堪布除了将《甘珠尔》各版本及目录,在广义上视为佛典唯一真实性来源之外,在具体操作上更将《布顿佛教史》和自宗克珠杰·格勒贝桑(mkhas grub rje dge legs dpal bzang 1385-1438)《续典总目》(rgyud sde spyi rnam)视为最终的依据,如此他对佛典结集的认识又进一步窄化了。
四、伏藏文献的真实性问题
松巴堪布对宁玛派所传的伏藏文献,虽言需作慎重文本批判而加以甄别,但从其行文逻辑看,对其持质疑、否定的态度亦是明显的。松巴堪布总分两大部分,即“辨认佛典”(gsung rab yang dag)与“辨认混杂、伪造和存疑文本”(bsres bslad can dang ltar snang dang the tshom can),他对伏藏文献的讨论集中在第二部分,这就表明他的分析倾向于否定。
他对伏藏文献真实性的定夺,见于论著中的两处讨论。其一,藏人对古本进行篡改,假说为“伏藏文献”。松巴堪布此观点可能蕴含两种可能,一是完全否定伏藏行为,二是部分性地认可伏藏文献。关于第二种可能性,我们需要关注文本生成中的两个阶段,即他确认无误的伏藏源头和伏藏时期或之后篡改而形成的混杂部分。松巴堪布对伏藏文献所作的文本构成之解剖,从根本上说是对传统叙述所说“伏藏-掘藏机制”的一种颠覆。伏藏传统辩护者通常将伏藏作为这种机制的最重要的部分,伏藏作为结果只是各种愿力所催生的必然结果而已,从这种配置看伏藏比掘藏更为重要。这种机制中的伏藏阶段,最为重要的特点是认为所要伏藏的文献,不管以高度符号化的编码形式还是以另外的形式出现,内容都完整、自我结构都合理,业已成型,后世掘藏者需要做的无非是解码而已。然而或由于时机尚未成熟,或为后世之人的福祉,或为逃避法难事件等诸多因素,暂时封存于历史的深处,并祈愿在特定时间、地点由掘藏师发掘。伏藏传统辩护者的这种叙述,用意是将当下的伏藏文献置于遥远的过去,通过过去来保障现在,这种合法化策略的旨意无非是将文本生成定格在过去的伏藏阶段。松巴堪布质疑:当下与过去并非如他们所说是完全匹配的。简言之,当下的托古行为污化了过去,因为当下不是过去的直接重现。如此一来,所谓伏藏文献的神圣性就被消解了,传统伏藏-掘藏机制也就断裂了。其二,是对掘藏行为的完全否定。此观点遭到了土观呼图克图的驳斥。
针对松巴堪布对伏藏文献的断然否定,土观呼图克图采用了两个策略予以反驳:一是将其渊源置于印度佛教语境,二是将其视为藏传佛教各派所共有的现象。土观呼图克图的第一个策略,与掘藏合法化者惯用之路径是一致的,即征用佛典中的相关记录。譬如他引用《大方广菩萨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jam dpal rtsa ba'i rgyud)、《圣集一切福德三昧经》('phags pa bsod nams thams cad bsdus pa'i ting nge 'dzin)和《贤愚经》(mdzangs blun zhes bya ba'i mdo)等经中的相关章句和典故,来论证伏藏非藏地特有之宗教现象,这种经典生成方式在印度就有其先例。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掘藏并非仅仅是将文献埋入地下等处,之后再进行发掘这么简单。掘藏作为一种宗教现象,有其繁琐的神话和仪式嵌入、特定社会文化烙印等意涵。简言之,它是作为一种机制在运作,有着较为广博的文化意义空间。以宗教类伏藏文献为例,在其合法性叙述中往往将其归为佛说,然后由莲花生大师等中间人,以神秘的方式从空行宝藏和尸林等处获得,并将其密意传授给后代以转世形式出世的掘藏者,再将其以诸种缘由进行伏藏,并让空行护法等进行护持。掘藏者在后世行将掘其伏藏时,往往面临着灵性考验等,通过佛菩萨的加持和修习上的不断精进,才最终成为称职的掘藏者,并向世人公布其所掘之经典,这绝非凡夫所能达成的。通过这样的神话和仪式的塑造,保证了伏藏文献的神圣地位。掘藏形式也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会出现不同形式的伏藏品,如晚近出现的意伏藏(dgong gter);早期伏藏文献所聚焦的内容与赞普有关,莲花生大师的影响局限于非常小的范围,然而在后期文献中这种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易位,这种转变或与宗派意识形态的不断强化有关[8](P.212-213)。由此而言,伏藏这种宗教现象是作为一种机制在运作,倘若只将其视为印度佛教的某种复制,一种简易的文本发掘过程,显然是无法涵盖伏藏庞杂的文化系统的。印度背景对伏藏现象形成的功效是微乎其微的[9](P.154)。新近关于伏藏现象多元起源性的探讨,对传统伏藏合法化辩护者的印度单一说有了新的理论发微空间[10](P.119-184)。
土观呼图克图的第二个策略,即强调伏藏并非某派某宗所独有,是藏传佛教界普遍、共有的现象。土观呼图克图如此阐述,彰显出围绕伏藏而存在的某种张力。伏藏批判者认为这是宁玛派所特有的而不予认可,进而将宁玛派在文化形塑和政治权势双重意义上进行边缘化。若伏藏现象超越宗派的藩篱,在各派都可觅见其行迹,那么这种指责就是武断的。他在叙述了其他宗派中的相关案例之后,又列举了他们师徒二人自宗格鲁派的三则掘藏情况。其一,纳塘寺第18任法台持律师·巴登桑布('dul nag pa dpal ldan bzang po 1402-1473),依止第一世达赖喇嘛根敦珠巴(rgyal dbang dge 'dun grub pa 1391-1474)和第一世班禅喇嘛克珠杰·格勒贝桑等上师学法,将阎罗修法仪轨(gshin rgyas las tshogs)进行伏藏,后由扎什伦布寺第4任法台班钦·益西孜毛(pan chen ye shes rtse mo 1433-1510)的弟子局钦·桑杰嘉措(rgyud chen sangs rgyas rgya mtsho 生卒不详)掘藏;其二,在安多地区赫赫有名的拉卜楞寺第一任法台嘉木样·协白多杰('jam dbyangs bzhad pa ngag dbang brtson 'grus 1648-1721/1722),发掘觉域派玛久拉仲(ma gcig lab sgron,11-12世纪)的相关伏藏;其三,甘丹寺第54任金座阿旺却丹(khri chen ngag dbang mchog ldan 1677-1751),在其梦境中得到宗喀巴大师授记:去菩提寺(byang chub dgon,此寺似在甘肃省临夏州康乐县境内,但未能证实)佛塔中掘藏。他未能返回安多,此事不了了之。土观呼图克图这些叙事不管是否有历史依据,但掘藏这种现象确实在非宁玛派宗派中也曾出现。然而,同样需要我们思考的是,相较于宁玛派上百部卷帙的伏藏文献,其他教派伏藏文献的数量可说是相形见绌的。因此通过举证其他教派的个案,将宁玛派伏藏传统合法化,其效果似乎也并非如他所想。
伏藏文献作为宁玛派两大文献来源之一,在为此派修习者提供新的仪轨从而产生新的传承系统(譬如“无垢友心滴”),提供叙事素材从而构建新的历史编纂方式(譬如莲花生传记的大规模产生)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宁玛派学者甚至认为,其比传世文献(bka’ ma)更有神圣性。传世文献因为其“远传(ring brgyud)”之属性——在漫长的线性时间之流中相沿传承,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篡改、误解等主客观损害;掘藏文献作为“近传(nye brgyud)”体系,在时间上是一种点对点的传承,从吐蕃时期伏藏直到掘藏,其间未有任何词句之改动。此外,其内容亦有“空行母符号(mkha' 'gro gsang ba'i brda)”编码,只有大成就者才能解码并公布于众,从而保护了它原封不动的最初形式。宁玛派掘藏师自11世纪崭露头角,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大量的文献,这些文献少部分被收录至《宁玛十万续》中,直到19世纪才首次较为完整地进行了汇编。由工珠·洛珠塔耶(kong sprul blo gros mtha' yas 1813-1899)汇编并冠名为《大宝藏》(rin chen gter mdzod),虽然也有缺漏,但已收录有100多卷。对于宁玛派如此重要的文化遗产,藏传佛教史上相继出现了的各种微词,这关乎宁玛派存续之根本。从这个意义而言,师徒二人对其真实性之辩论,牵涉到了更为重要且复杂的问题。
五、藏传佛教思想史的另一层书写
18世纪的这场师徒争论,与11世纪初见端倪的以“驳斥谬咒(sngags log sun ‘byin gyi skor)”为名的文类所阐发的观念具有同质性、连贯性,对“疑伪经”的讨论是其核心内容。这种文类所存设之论辩双方,对正统性之意欲和对自造之排斥所形成之张力,形塑着藏传佛教史书类著作的写作范式。历史编纂学家们受其影响,在建构其宗教史叙事之际,对孰轻孰重都有涉及。譬如作为典范史书之《贤者喜宴》和《青史》,在涉及宁玛派相关历史和教义之际,借用了大篇幅阐述这种论辩。
这种论辩散发的力量从藏传佛教后弘期之始至18世纪的这场师徒诤论,一直在发酵之中,甚至在20世纪宁玛派著名学者杜钧·益西多吉(bdud 'joms 'jigs bral ye shes rdo rje 1904-1987)所撰之《旧译宁玛派教法源流史》(rnga bo che'i sgra dbyangs)中亦有余响。对藏传佛教史各阶段的以“疑伪经”为核心内容而展开的诤论进行思想史梳理,无疑会填补藏传佛教史书写中的另一层空白。反过来,这又为理解藏传佛教史提供了一扇重要的窗口。我们在此不妨对这种论辩发端之历史语境稍作探讨,以凸显其对藏传佛教史研究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崩溃到10世纪末古格王朝兴起的百余年间,佛教在藏地经历了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学界称为“黑暗时期”。这一时期,相继出现了诸多互不统属的佛教团体,形成了分散的局面,直到拉喇嘛·益西沃(lha bla ma ye shes 'od 947-1024)时期才发生转变。作为吐蕃赞普之后裔,益西沃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其中最为著名的当是实施某种“政教二轨制”。益西沃规定“先前有父王未殁王子不继王位之法,于此,创立尊父王为大喇嘛,其子即可为王之俗”。在此所说“先前”,指吐蕃王朝时期。现在益西沃对陈法作了修正,即先王隐退为宗教掌管者(bla chen)之后,其子在先王仍在世的情况下,可成为世俗掌权者(mnga’ bdag)。虽然古格王朝只是西藏西部的一个小邦,但这种“政治结构(Political Structure)”对藏地此后的行政设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他还在宗教领域采取了一种新的修辞策略,认为只有回归显宗、构建经院佛学体系,才能拯救佛教。他在公共领域制造新的知识框架,用意在否定“黑暗时期”密教传播的贡献,认为此时出现了自造之伪典和错误的修习方法。将益西沃的这些措施置入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会发现他是对某些“邪法(chos log)”之杂学歧出深感不安,并尝试对其进行剖析和审视,譬如迎请印度高僧、派遣藏族青年留学印度以期明察秋毫。这也与其新的政治话语的生成有着脉脉相通的关联。这就是说他对宗教理解图景的重置,也较为明显地呈现了其政治性特征,这也是其进行社会变革的一种源动力。益西沃的这种宗教诠释策略,对其后的思想史的塑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益西沃侄子降曲沃时期迎请至藏地的著名印度论师阿底峡尊者,在其名著《菩提道灯论》中更是确立了“先显后密”的修道次第。这种修道次第的显著特点是,否定了修行人直接修习密教的可行性和合理性,甚至认为这样的方法是误导性的,在宗教救赎层面亦是无意义的。果真如此?当然是仁者见仁的事情了。也有不少宗教诠释者倾向于认为,因密教是所有教法中最为殊胜的,在这暇满短暂的此生直涉密教修习,可最大化地获得无上的功德;相反,显宗修习因其时段长、义理复杂难解,在快速成就上可能稍逊一筹。阿底峡这种“先显后密”的修道次第框架达到极致,当是在宗喀巴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等论著中。从这个思想史演进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益西沃强调的显宗优先的修习策略,无疑在后期噶当派—格鲁派一系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影响力。
益西沃的宗教措施在公共领域产生的效果,是通过他相继颁布具有法令性质的系列“文告”而达成的。其中一则公元990年左右颁发的,署名为“普兰之王拉喇嘛(pu hrangs kyi rgyal po lha bla ma)”的文告,后世学者将其称作《驳斥谬咒之书》。自益西沃发端的批判滥修密法的洪流,他之后的大译师·仁钦桑布(lo chen rin chen bzang po 958-1055)、颇章·喜瓦卫(pho brang zhi ba 'od十一世纪)、萨班·贡嘎坚赞、恰译师·切杰贝(chag lo chos rje dpal 1197-1264)、布顿·仁钦珠、直贡贝增·尼玛桑布('bri gung dpal 'dzin nyi ma bzang po 14世纪)和班钦·释迦却旦(pan chen shAkya mchog ldan 1428-1507)等一批著名学者投身其中。逐渐地,关于“疑伪经”等内容的讨论脱离了益西沃时期具体的历史语境,被引入到宗派意识形态的诤论中。宁玛派学人甚至也暗示其锋芒所指为自派。这种讨论,历史之长、参与者之多、诤论之激烈,无疑是学界在建构藏传佛教史之际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议题。
六、宗派间教义-仪式的互渗性意义
松巴、土观两人对“疑伪经”问题的聚焦,与他们对“宗派边界”的不同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宗派意识形态较为浓烈的氛围下,对“佛典”的讨论带有一定的宗派之见,如上所述松巴堪布将自宗《续典总目》之入载与否视为佛典真实性的准绳。对“宗派边界”的迥异认知,突出地表现在不同宗派由于各自教义和仪式的习染而致的结果上。
松巴堪布认为自宗之“极密忿怒马头明王之仪轨(rta mgrin yang gsang khros pa'i cho ga)”是可疑的,其锋芒所向为宁玛派对自宗之渗透。莲花语部马头明王类修法,在藏传佛教各派都有不同的传承,但极忿怒马头明王是宁玛派大瑜伽(rnal 'byor chen po)实修部(sgrub sde)八大本尊之一,其仪轨是宁玛派不共之本尊修法。其修习所依之续典《莲花具力极密忿怒续》(padma dbang chen yang gsang khros pa'i rgyud),据其题记所载是莲花生大师传授给赤松德赞,由毗卢遮那翻译为藏文的。根据宁玛派《极忿怒马头明王传承史》叙述,12世纪的达恰巴·仁钦桑布('dar 'phyar rin chen bzang po)为这一传承的中枢人物。他不仅融摄了三位掘藏师的传承,而且在净相中得到莲花生大师的传授,因此他亦被视为“两传合受者(brgyud pa gnyis ldan)”。此后,源自莲花生大师的这种红马头明王修习,被历代宁玛派学人传承至今。或由于此仪轨的宁玛派渊源这一不争事实,松巴堪布意图将其排除在自宗以外,并用恰译师·切杰贝的相关说辞作为自己的证据。
土观呼图克图对这一教派间修法的相互吸收,显然是持包容、开放的态度。他罗列了自宗高僧将极忿怒马头明王视为本尊进行修习并造仪轨本之情况。我们进行了文献学之梳理考证,发现土观呼图克图的这些叙述源自五世达赖喇嘛(rgyal ba ngag dbang blo bzang rgya mtsho 1617-1682),其后江龙班智达·阿旺洛桑丹白坚赞(lcang lung ngag dbang blo bzang bstan pa'i rgyal mtshan 1770-1845)和喀尔喀·旦奏多杰(khal kha dam tshig rdo rje 1781-1855)等人亦作了相同的论述。根据他们所提供的信息,我们发现格鲁派著名高僧如二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rgyal ba dge 'dun rgya mtsho 1476-1542)、四世班禅喇嘛洛桑却吉坚赞(pan chen blo bzang chos rgyan 1570-1662)、色拉寺首任堪布洛追仁青僧格(blo gros rin chen seng ge 15世纪)等皆为其传承者。另外,土观呼图克图还指出极忿怒马头明王为色拉寺主供的本尊的事实。从这些既定的事实而言,土观呼图克图更愿意接受而非排斥。
从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而言,宗派之间由于借鉴、展演等而相互习染是不可避免的,寻求一种“纯正的宗派”,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臆想。松巴师徒二人对此问题的不同回应,其实与格鲁派内部对“宗派边界”的两种态度交织在一起。譬如,五世达赖喇嘛在格鲁派内部是开明派的代表,宁玛派在17世纪中叶再次兴盛,公认为是得益于他对敏珠林寺(smin grol gling)、多杰扎寺(rdo rje brag)、佐钦寺(rdzogs chen dgon)等著名寺院的扶持。然而,他的这种宗派观,也招致了其他人的不满。如其同父同母兄弟扎龚·彭措嘉措(brag sgo phun tshogs rgya mtsho)公然反对他的做法[11](P.492)。不同宗派观的张力,无疑在宗教史产生了许多困境,对同一宗派内部而言,这可能会成为宗派分化的诱因;对其他宗派而言,即是宗派纷争的前兆。
宗派间在教义和仪式上互渗而形成的既定事实,为我们对宗派关系的认识提供了新的思考向度。各宗派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单元,相反在教义和仪式上的相互流动是显性的,因此作孰是孰非之判断,甚或优劣高低之划分,无非是一厢情愿之私欲。作为社会整合和宗教和睦的重要因素,唯有宗教宽容理念,才是需要积极维护和强调的。
余论
虽然两位学者诤论之文的篇幅较小,但已充分体现了他们对相关问题的诠释,这在他们影响深远的佛教史著述中亦有佐证。在疑伪经问题带有较强烈的宗派意识的背景下,土观呼图克图为了现实宗派间的和睦友好,或为了杜绝宗派纷争之后患,始终抱着一种文化多元主义之胸怀。这种视野是难能可贵的,尤其在唯我独大的宗教政治氛围中。然而,这也限制了他对问题的深刻把握,即对疑伪经问题的根本性和紧迫性没有足够的认识,对松巴堪布的反驳也只是流于表面,只是其文化策略的一种表达而已。相反,松巴堪布在依据藏地学者辨认佛典的学术光谱,以及在翻阅《甘珠尔》所获个人经验等基础上,试图提炼一种“文本批判方法”,用于疑伪经的辨认。然而,由于其比较狭隘的宗派观,致使其方法之缺陷处处可见,最终也未能形成适用于所有宗派的佛典标准及其理论体系,离天下之公器之路亦甚远。对此,Matthew Kapstein教授说道,西藏始终也没有出现,如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产生的那种精密而普适的“文本批判方法(Text Critical Scholarship)”[12](P.134-135)。这种方法的产生还有待于现代藏文文献学的建构,任重而道远。
注释:
①Matthew Kapstein,The Purificatory Gem and Its Cleansing: A Late Tibetan Polemical Discussion of Apocryphal Texts,in History of Religion,Vol. 28,No.3.(1989),pp. 217-244.其修订本参见Matthew T. Kapstein,The Purificatory Gem and Its Cleansing: A Late Polemical Discussion of Apocryphal Texts,in The Tibetan Assimilation of Buddhism: Conversion,Contestation and Memory,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121-137.
②载于松巴·益西班觉著,青海省共和县藏语委编,《松巴·益西班觉文集(第4卷)》(藏文),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16年。
③辩论文后记中虽作80岁,或可能为抄写员笔误,根据松巴堪布自传中出现的具体年份推断,是其79岁时写作此文。参见松巴·益西班觉著,青海省共和县藏语委编,《松巴·益西班觉自传·文集(第4卷)》(藏文),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16年。
④洛珠江泽:《答关于前弘期密乘的争论》(藏文),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341-396页。此著述虽未收录在其文集中,但其作者为土观呼图克图是确凿无疑的,因为在松巴堪布传记中对弟子行为斥责有加。参见松巴·益西班觉著,青海省共和县藏语委编,《松巴·益西班觉自传·文集(第4卷)》(藏文),西宁:青海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605页。
⑤关于松巴堪布上述52部疑伪经中掺杂的西藏本土语情况之分析,参见才让:《〈陀罗尼集〉中的疑伪经:松巴堪布的质疑与批判》,《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1期,第119-130页。
⑥Ronald Davidson教授对印度佛教史佛典标准问题作了比较详尽的阐述,涉及原始佛教时期的语言观、部派时期结集、大乘和金刚乘佛教时期的神话化等议题。从中我们可以窥见早期佛教徒对“佛说/佛典”所持某种僵硬的“历史真实原则”,即由释迦牟尼佛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宣说之法才被称为“佛说/佛典”,然而随着佛教思想的进一步深入,这种历史原则的缺陷不断被证实。大乘尤其是密乘佛教的兴起,佛说内涵不断扩大,佛不仅仅是释迦牟尼而有无量的佛,其弘法利民之事业也不拘泥于某特定的时空,早期历史原则逐渐被某种“逻辑推演原则”所替代和摈弃。Davidson观点在Kapstein文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参见Ronald M. Davidson,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andards of Scriptural Authenticity in India Buddhism,in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edited by Robert E. Buswell JR,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0),pp.291-325.

⑧这些《甘珠尔》版本刊行的时间等历史信息,依据东噶·洛桑赤列、辛嶋静志、Paul Harrison 和Kurtis Schaeffer等教授的论著,依次为:东噶·洛桑赤列:《东噶·洛桑赤列文集·目录学卷》(藏文),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4年,第10-27页;辛嶋静志著,裘云青、吴蔚琳译,《论〈甘珠尔〉的系统及对藏译佛经文献学研究的重要性》,《佛典语言及传承》,上海:中华书局,2016年,第373-384页;Paul Harrison,A Brief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ka' 'gyur,in Tibetan Literature: Studies in Genre,edited by José Ignacio Cabzón and Roger R.Jackson,New York: Snow Lion Publications(1996),pp.70-94; Kurtis R. Schaeffer,the Culture of the Book in Tibet,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9),pp.90-119.
⑨松巴堪布将广义“佛典”与狭义“藏译佛典”概念相混而谈,土观呼图克图的理解是依前者而阐发的,笔者在此也根据土观呼图克图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