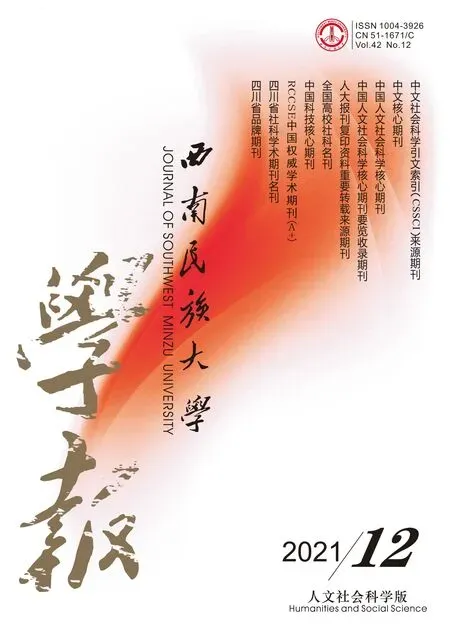场域·视语·认同:竹枝词的西南少数民族图像空间
2021-12-15罗杰
罗 杰
[提要]民族的图像空间呈现是竹枝词特有的一种空间叙事方式,其以视觉语言为文化符码来展演可视的西南少数民族。竹枝词的民族图像空间以“可视的语言”为视觉形象的媒介形式,对西南族群的盘瓠神话、跳月对歌、节日庆典、婚丧礼仪等仪式场域进行展现。在“同化”视野下对西南族群进行服饰、发式、秉性、形貌等种族特征的视语建构,呈现为以视觉语言解码破译与编码转译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符码。与跨界想象、族群边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及社会结构互动中演进形成认同的根源,建构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义上的“西南少数民族形象”。
通观历代竹枝词对西南地域百余族群的视觉表述,发现其有明显的民族图像空间呈现,西南少数民族在与文化持有者知识边界的碰撞中动态地“可视化”,而“可视”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建构认同。书写者如何向接受者传递他们在西南地域看到的多元族群?“我们建构一种‘可视语言’,把视觉和声音、图像和言语结合起来。”[1](P.101)竹枝词的西南少数民族图像空间体现了“文学是符号系统,那它们必须是编码的,或以形象形式编码,或以词义的形式编码。”[2](P.125-127)竹枝词集中地展现了“语言文本”中形象形式编码的民族图像空间,依此可探索文学中西南少数民族形象的生成、承继、推进、演化,这符合作为注视者一方的书写者认同“他者”并将之转译后,以图像空间的形式呈现。竹枝词的西南少数民族图像空间折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文学化路径,即书写者是在一个相异性的地域文化空间中关注和想象他者。这时书写者的视觉思维与审美意识必然起到决定作用,书写者尝试掩蔽自我原生的文化身份,以“在场”身份来完成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解码破译、编码塑象、建构认同,最终在竹枝词中生成民族图像的“完形”①机制。本文借鉴中国空间叙事理论来思考竹枝词的西南少数民族图像空间,考察其叙事动力何以生成认同的根源,以期对西南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的互动影响中作深层的思索。
一、图像之域:族群记忆的仪式传递
书写者在竹枝词中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视觉建构时,将他们彼此之间复杂的族际文化分属归类,集中呈现为地域空间、族源传说、婚丧礼仪、迎神接祖、对歌跳月等族群记忆图景的仪式场域。仪式场域是书写者体验后的浸染着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气息的地域空间,透过地域空间,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异彩纷呈,形成了书写者与接受者之间可以共享和互通的情感空间。“进而言之,仪式不仅属于一种历史形貌的展现形式,也是人们参与和认知的内容。”[3](P.17)仪式场域是书写者参与和认知西南地域文化的表征,生活节庆习俗是对西南少数民族真实生活的关注,节日庆典是书写者共性表述的文化隐喻,婚丧礼仪是对族群风俗民情的差异性考察,族源神话突显书写者获得的认同感,共同建构为包容西南少数民族多元文化的文学地域空间。
(一)地域空间呈现
仪式场域是竹枝词的地域空间呈现,相当于书写者作为仪式表述者的参与身份,是将自我身份设定为“在场的他者”来呈现特定的时空观。在历代竹枝词序跋中多以此来说明书写西南少数民族的缘由,强调所述内容中西南地域文化和审美空间的体验,具有鲜明的“在场”仪式感。“这种特征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就是文学的地域性。是具体可感的审美空间。”[4](P.140-143)唐宋到明清,竹枝词承袭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仪式场域,虽然朝代更替,但仍延续着西南少数民族仪式歌的地域空间。通过对历代竹枝词序跋的勾稽可知书写者是如何通过仪式场域来展现族群记忆的。如唐人刘禹锡《竹枝词》序言:“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5](P.852)宋代苏轼《竹枝词(忠州作)》序云:“竹枝歌本楚声,幽怨恻怛,若有所深悲者。”[6](P.646)明人林奕隆《竹枝歌》序言:“蜀万州风俗:士女于峨嵋碛击小鼓,唱竹枝歌。”[6](P.658)清人舒位《黔苗竹枝词》自序:“黔于汉属西南夷,唐宋以来曰蛮曰獠。苗既居处言语不与华同。其风俗、饮食、衣服各诡骇不可殚论。余从车骑之后,辄以见闻所及,杂撰为《竹枝》体诗,且为之注。”[7](P.2242)由此可见,“西南夷”仪式场域成为嵌入竹枝词的内在文化情境。在竹枝词序跋中交代书写的文学地域,这源于书写者参与了西南少数民族竹枝歌舞仪式的文化记忆,且在书写者的认同意识与族群文化交互体验中营造出特异的地域空间。地域空间的想象成为书写者和接受者关注西南少数民族的根源,“人之所以对地域空间感兴趣,其根源在于存在。”[8](P.1)竹枝词中西南地域文化的仪式场域,书写者的文学书写将之融入西南少数民族的“视觉化”,可视之为自我身份的确立和强化族群边界的重要方式。
(二)族源共同之仪式:盘瓠信仰
盘瓠神话在西南族群间流传,竹枝词中有大量书写与西南少数民族族源相关的盘瓠神话。在清人舒位《黔苗竹枝词》的篇首为“西南夷”:“嫁得盘瓠不自由,岑山孖水远来游。”词下注云:“‘盘瓠’,高辛氏之畜狗也,衔犬戎吴将军头献阙下。帝酬其功而妻以少女。盘瓠遂负女走入南山石室。三年生六男六女,自相夫妇。衣服制裁皆有尾形,号曰‘蛮夷’。”[7](P.1454)张澎《西垣黔苗竹枝词》:“盘瓠鼻祖想余威,结束栏干独立衣。”[9](P.66)可见“盘瓠神话传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传甚广。除黔地苗族崇拜外,与之有地缘关系的巴蜀、湘桂地区的百越族群都有“盘瓠崇拜”,即“五溪之蛮,皆盘种也。聚落区分,名亦随异。”[10](P.357)书写者在表述西南少数民族时,以盘瓠神话来追溯他们共同的族源,故族源神话是竹枝词中西南少数民族视觉表述的重要内容。盘瓠传说中的跳月、斗牛等仪式内容至今仍延续在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中,信仰盘瓠是百越各族的文化认同资源,溯源族源的表述中潜藏着书写者的认同意识。
(三)生活习俗之仪式:节日庆典
西南少数民族节日庆典是竹枝词中的生活仪式场域,多涉及三月三、绕三灵、星回节、拜年插禾、清明重阳、中秋除夕等。在此以竹枝词中滇地民族“星回节”为例来说明生活习俗仪式场域,如清代李中简的《大理民家曲》:“星回节近天火然,家家占岁照园田”[9](P.100)。史梦兰的《滇竹枝》:“剁生饮酒俗相沿,节到星回岁序迁。”词下有注解:“滇俗以六月二十四是为星回节,街燃松炬,村落以炬插田间。此户剁生饮酒,夷汉同之。方言‘松炬’为‘松明’。”[9](P.142)吕及园《滇南竹枝词》:“剁生生食血腥和,节重星回火炬多。糁入松香起烟焰,乱红烧遍万山河。”[9](P.147)吴应枚《滇南杂咏》:“剁生盘冷佐椒馨,佳节星回味荐腥。”[9](P.150)赵筠《临沧竹枝词》:“六月星回节更奇,通红火把列高低。”[9](P.133)许印芳在《星回节考》中考释:“滇中士大夫谓六月二十四日为星回节取星回于天之义,考之民俗,是日但称火把节。”[11](P.217)历代书写者在滇地的不同时空里以竹枝词书写了星回节的仪式场域,不同身份背景的书写者择取星回节仪式来表述西南相邻族群关联文化。在竹枝词中“星回”与“剁生”“松明”“饮酒”等语词和意象建构了节日的仪式场域,其内在的文化体验包含在视觉表述中。在特定场域情境下生活习俗与民族渊源、火的崇拜传递了滇地的生活仪式信息和浓厚的生活气息,以星回节为文化符码动态表述仪式场域。
(四)婚恋礼仪之仪式:对歌跳月
竹枝词的婚恋仪式场域中,西南少数民族多与跳月、对歌、民族生活场景等意象联系在一起。清人竹枝词中多以滇黔地区苗族形象来表述,此类形象与跳月歌舞仪式场域为共构关系。如张澎《西垣黔苗竹枝词》:“花苗:蜡绘花衣锦裙裳,振铃跳月斗新妆。”[9](P.66)田榕《黔苗竹枝词》:“芦笙吹彻响铃摧,花簇球场趁月开。花树跳花花一簇,月场踏月月三更。”[9](P.58)黔地孔昭虔《跳月词》序言详述跳月仪式:“苗俗,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择平址为月场,及期,更服饰妆,男截芦管编笙吹之。女振铃继于后,联袂比肩回翔宛转,和歌相洽。”[11](P.43)西南少数民族的跳月活动是成人仪式,在跳月活动中进行择月场、男吹笙、女摇铃、对歌跳舞等仪式表演活动,“芦笙”“跳月”“对歌”等仪式场域中的文化符码成为竹枝词中西南少数民族婚恋文化活动的隐喻,“对歌跳月”是场域中的重要仪式主题。竹枝词中对跳月对歌仪式活动的互文性表述提升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可视化,表征了西南族群共享的文化生活,也是西南族群共有的文化习俗资源。
(五)竹王崇拜之仪式:赛神赛歌
竹枝词中的仪式场域中多出现“竹王祠”“赛竹王”等文化形象,如李中简《黔中竹枝词》:“铜鼓山头雨半晴,竹王祠畔沸春声。”[9](P.47)蒋攸铦《黔阳竹枝词》:“黑衣竞逐乌鸦队,铜鼓声里赛竹王。”[9](P.53)孔昭虔《乌蛮竹枝词》:“渝舞蛮歌诸葛鼓,村村争赛竹三郎。”[9](P.5)余上泗《蛮侗竹枝词》:“闻道前村花鼓闹,背儿赛看竹三郎。”[9](P.38)滇地《竹枝词》:“织就斑丝不赠人,调来铜鼓赛山神。”巴蜀地区王培笱《嘉州竹枝词》云:“报赛迎神唱竹枝,竹公溪畔竹王祠。”[6](P.530)舒位《黔苗竹枝词》中还有详实书写:“流水淙淙匝夜郎,浣纱人见竹三王”。词下自注:“初有女子浣于遯水,见三节大竹流入足间,闻哭声,剖竹得一男。妇养之,长而自立为竹郎侯,以竹为姓。汉武帝杀之,后封其三子,民为立竹王三郎神祠。”[9](P.60)从此可见“西南各族群丰富的竹王神话和仪式,述说着先民集体记忆中的远古史话,折射反映出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12]书写者将“铜鼓”“歌舞”“服饰”等视觉表述为守护家园和维系族群的文化形象。仪式展演意在呈现“竹生人”的族群记忆,以此来延续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殖崇拜与生命信仰。竹王祭祀是与先祖灵魂交汇提供的仪式表演程式,使西南少数民族与竹王崇拜仪式凝聚为有整合功能的族群记忆。
仪式场域是竹枝词民族图像空间呈现的基本表现形式,具有族源“黏合”特性的地域空间呈现了西南少数民族共同的仪式图景,展演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空间的原貌。“书写者与异域文化、民族形象之间是互识、互证、互补的关系,具体而言,在异质文化互动影响的过程中两者之间建构起书写者与异域文化、民族形象复杂的共生关系。”[13](P.15)书写者的地域文化体验与异文化间文学体验的互动是辅之以与仪式展演相关的真实生活场景,仪式场域是西南少数民族共享文化和创造共同信仰的共生过程,正是多类型仪式场域中的共生关系生成了相对固化的西南少数民族的视觉表述机制。
二、图像之语:可视的语言
可视的语言是编码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符码的重要依据,“文化的可视性是通过可视的视觉语言编码来展示的”[14](P.86),如何将在西南地域空间看到的族群真实呈现,运用视觉语言表述西南少数民族成为竹枝词图像空间的重要方式。竹枝词的空间叙事是“由抒情诗歌语言文本所唤起或转换的,具有具象意义的图像空间”[15],即书写者借助视觉语言来解码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继而将破译后的族群文化以视觉符码形式在竹枝词中塑形为图像空间,呈现为可视的民族形象。接受者通过想象以视觉语言编码来转译文本内容,视觉形象能让阅读者更好地在大脑中形成具象,以此来完成对文学文本内容的接受,书写者和接受者同处构型与接受的想象轴两端,需凭借想象完成图像构型,即图像空间是视觉语言的产物。竹枝词中西南少数民族是通过视觉语言解码与编码形式的图像空间呈现,具体表现为:首先,采用微观视角摄取视觉语言元素作为文化符码来破译西南少数民族文化。正因为竹枝词适应了地域文化体验而衍生出对族群种族特征的图像空间呈现方式,通过视觉语言编译文化符码可以说明认同性及其身份认同的关系。其次,视觉表述并不是偶然性的生活再现,而是透过蕴含丰富心理色彩的视觉语言来解码与编码文化。西南少数民族已被转译为图像空间,复杂多元的西南少数民族文化被视觉化分属和具象化归类,反映出书写者力求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视觉真实”呈现,彰显民族的形象化是叙事认同的内在张力。最后,书写者透析西南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视觉真实已转译为文学真实。书写者力图借助原生的知识话语把西南少数民族的仪式场域等视觉元素都纳入族群边界,依据富含心理色彩的视觉语言来分类认知、归类编码和民族识别。又从主流话语中提炼出色彩、造型、形貌、性情等视觉语言对之进行编码,经文化破译将细化后的族源、形貌、服饰、头饰、发式、体质、语言、信仰、习俗、饮食、礼仪、生计、居所、秉性等媒介编码为可视的文化符码。与此同时,对图像空间进行具象化调整,并将之内化为文学文本中的西南少数民族形象体系,形成了明确专为表述西南少数民族的审美话语系统,构建为具体“可视”的图像空间。且与仪式场域并置,生成竹枝词空间叙事的内在动力,“可视的语言”具有统摄族群文化的整合功能,是可供人们彼此交流的“视觉形象”。因此,书写者关注西南少数民族时,运用直观可视的视觉语言来对其文化进行破译,将与之文化情境相应的地域空间、仪式场域编码后建构为西南少数民族图像,形成了竹枝词空间叙事的分类认知和视语同化功能。视觉表述的编码功能是具象化和“视觉化”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性,增强“西南少数民族”的审美性,是“文化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符号过程。”[16](P.12)在此过程中长期被隐蔽的西南少数民族显现为活态可视的图像,并经视觉语言编码转译为可供文化持有者认知的文化符号。
在竹枝词中形成的“蛮女”“蛮娥”“僰女”“苗女”“巴女”“夷女”等相对固定的女性形象视觉表述模式,呈现为一系列形态鲜活的女性群像图景。

表一 竹枝词中的西南少数民族女性图景
表中所列,为书写者所看到的西南少数民族女性图景,当书写者来到陌生的西南地域空间时,其视角聚焦在女性的服饰、形貌、体态、生产、劳作、歌舞等生活图景,集中可视性强的语词编码为形象形式的文化符码,多角度呈现西南少数民族女性的视觉表述策略提升了形象的可视化效果。对西南地域生活场景中女性的服饰、发饰、发式、配饰、银器、仪态、秉性、形貌、色彩等与身体仪式细节的整体展演,通过可视的语言将生活原型解码后重新编码为立体的视觉形象,反映出书写者的视域空间和认同视野发生了变化,其目的在于确立了西南少数民族女性形象的身份认同,为女性形象提供可视化的空间,建构女性形象话语的文化符码。故而她们在竹枝词中被建构为身着色彩绚丽服饰和发饰殊异的女性形象,着重对服饰、发式等细节特性的描述是以区分和凸显不同族群特征的边界,而这些与身体延伸相关的视觉语言是文化符号意义得以生成的关键,为分类认知西南少数民族提供了视觉形象,也是身份认同的重要依据。
竹枝词中西南少数民族女性之所以呈现多维图像视角,须结合明清时期方志中增设《种人》类目和涌现《职贡图》《百苗图》《滇夷图》等多类民族图册,对普通民族百姓认知的拓展以及国家治理政策调整演进来思考。如,明代天启《滇志·羁縻志》设立《种人》子目,包括了滇地民族的外貌服饰、婚丧习俗、民生劳计、语言文字等。方志和图册对普通民族百姓生活状况书写图说体例的变化,说明对少数民族群体有了一个相对全面的认知。书写者获得了依赖自我所属的文化体系和民族知识框架创造可共享交流的文化符码的合法渠道。竹枝词强调注视者将视角转变到对西南少数民族女性视觉元素特性的摄取,即采用自注视者的语词来表述作为被注视者的西南少数民族,破译解码后编码转译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竹枝词书写者关注西南族群中的少数民族女性,将其可视的元素符号化,体现了“社会领域的国族、社群、性别、种族、个体等的身份认同均须通过语言媒介(文化符码)来加以建构”[17]。竹枝词中西南少数民族女性是以文化符码呈现的图像,以视觉思维凝聚族群→视语符码→文学塑形为视觉形象,其意义在于书写者在社会空间中建构了她们身份认同的过程。书写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女性进行视觉语言编码时,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文化、语言的间隔被消解。视觉表述的文化内涵成为仪式符号体系中的一部分,在书写者的表述中糅合为可视的文化符号,体现出书写者在族群间跨文化交流时达成了“民族是可视的”的表述机制。视觉表述实际上将相邻族群边界间视觉文化元素建构为形象符码的文学活动,竹枝词的图像空间生动地整体展现了她们的整体视觉形象,即解码破译后编码转译为具有镌刻脑海效果的图像。
书写者除了从知识结构中的视觉语言来建构外,还择取西南少数民族文化中的词汇来进行表述,将其纳入主流话语体系。如,在尤侗、舒位、田榕、张澎、余上泗、伍颂圻等人的竹枝词中,对“黔苗”的视觉表述出现互文性现象,形成了多个相对独立又可联成体系的苗族图像空间。

表二 竹枝词中“黔苗”形象的互文性
如表所示,多首《黔苗竹枝词》中以“椎牛白号”来表述共同的事象,“白号”仪式场域中的童男童女、彩带歌舞、椎牛庆典等已被书写者破译编码为“黔苗”的文化符码。十月收获后,名曰祭白号。祭白号又称祭白虎,即“岁十月收获后,名曰祭白号”,是苗族丰收祭祀仪式及劳作生产重要的文化象征,与之相关的丰收祭祀庆典内容构成清晰可视的图景。在竹枝词中可看到黔地苗族经书写者可视的语言构成一系列的图像空间,形成表述“黔苗”的互文性现象。此外,地方兴起的文学竞技、以诗证史与文人间的唱和激发出竹枝词体例完整且复杂的视觉表述体系,如尤侗、舒位、田榕、张澎、毛贵铭、易梧冈等人各写有同题名的《黔苗竹枝词》,均采用分族支系的方式视觉表述了近86个类别的“黔苗”形象。透过七言四句抒情体例“可视的语言”,生成了较强的叙事动力,可以呈现出多个图像空间,能快速地凝聚苗族视觉形象。显然这是竹枝词在与社会结构互动演进关系中调适出的一种可交流共享的视觉文化符码体系,在对新奇事物和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驱使下,力求通过文学书写与审美建构苗族形象,将破译后的黔地族群多层面、鲜活地呈现,以地域空间邻近关系方式展现族群定义、分类与认同。“黔苗”在视觉语言编码中转译为可视的文化符码,其图像空间动态呈现为白号、椎牛、吹笙、赛神、彩带、丰收、对歌、跳月、生计等融为一体的立体画面,经由书写者在竹枝词中视觉解码为文化符码后,形成了一套“共生”的文化符码体系。“黔苗”经可视的语言编码后在图像空间中呈现出有丰富意义的文化符码,转译为身份认同的符号。书写者以视觉语言解码后编码来创造和展现族群的文化特征,形成共同认知的族群文化符码,凸显了竹枝词作为媒介传递文化符码的空间叙事动力。“在解码又重新编码中文学起到了描述创新和结构化过程的作用。因为文学化的过程中隐喻、书写、叙事成为影响文化现象被表述的方式,从观察到形构的过程中终获文化符码。”[18](P.31-32)因书写者对“黔苗”视觉建构方式的创新,“黔苗”从生活原型经编码转译后嬗变为相对固定的文化符码,在文学形象化过程中合成了“民族性”,展现了西南少数民族经文学书写及认同后进入主流话语的过程。
竹枝词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化视觉表述的具象化策略,正是经由历代文化持有者的文化破译与转译,这些视觉思维活动唤醒书写者开拓知识疆域的动力,展现了西南少数民族经文学书写及认同后进入主流话语的过程。
三、图像何为:认同的根源
竹枝词中西南少数民族形象为何以图像空间方式呈现?因视觉真实是一种建构认同的文化事实,可视之为“地域文化体验”的文学书写路径,体现了建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可能。从空间叙事的角度来探讨竹枝词的西南少数民族图像空间呈现,并探究认同的根源何在,即书写者如何通过竹枝词的图像空间叙事动力将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符码转译为视觉形象,如何运用可视的语言表述看到“与汉同”的西南少数民族。正如建构认同论学者霍尔所言:“认同问题实际上是在其形成过程中(而非存在过程中)有关历史、语言、文化等资源的使用问题,认同是在再现之内而非之外构建而成的”[19](P.6)。因可视的语言凝聚了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同汉人”的认同根源,在此过程中西南族群间的联系与区分因视觉表述的比照而显现,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符码体系成为构建民族认同过程中的媒介,书写者在视觉表述西南少数民族的同时,也认同了他们的文化。书写者之所以关注西南少数民族,源于知识边界的拓展和异文化交流的心理诉求,“文化认同性基本上是指民族性的。”[20](P.11)在视觉表述西南少数民族形象过程中认识真实的自我,在视觉真实建构的认同中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审视,历经竹枝词视觉表述、文化符码和内生结构的演进,超越了所属社会群体的刻板印象,跨越了想象间距④后的民族形象就越“民族化”。在力图开拓新的文学疆域的心理诉求驱使下,吸收西南民歌的精髓,保留了竹枝词仪式场域展演特征,具象化主流话语对西南少数民族的想象,西南少数民族被建构为具有认同功能的图像空间,此间生成的叙事动力成为认同的根源。视觉语言创造了可视的西南少数民族形象,具象化的图像空间促成叙事动力在西南地域文化体验与文学体验互动中实现“同化”的多种可能性。其间是以社会结构、族群边界、跨界想象、心理诉求等具体内容的互动来实现的,构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多民族文化的融合。

表三 竹枝词中的“汉化”叙事
上表所示,“与汉同”“同汉人”“学汉人”“俨汉人”“同汉俗”“通汉语”“学汉装”“汉家音”等互文性,在对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族源、服饰、语言、婚丧等视觉表述的过程中,“归化”出对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相近礼俗的表述,“汉化”“汉风”“华风”在竹枝词中业已形成系统化和结构化的叙事主题,这种系统化和结构化是一种对话与认同表征,旨在强化仪式场域中的族源记忆,而且“这些词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一种特定的文化中可多少直接地传播他者形象。”[21](P.130)书写者的文学体验体现了在异文化间的碰撞、交融后“认同”被注视者文化的心理诉求,书写者深入体验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后,他们依据原生知识体系作出认知判断,以文化体验建构西南族群边界,以可视的语言为传播媒介编码文化符码并建构西南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意味着西南少数民族被认同为内涵丰富的社会总体想象物。“它还意味着一个明确的社会空间——一块边界相对清晰的,为其成员所认可并为他们带来归属感的领土。”[22](P.15)一个新的知识话语体系的生成,不能脱离原生所属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知识结构,在异文化互动中西南少数民族的知识边界开始清晰和被“同化”“归类”。书写者在竹枝词图像空间中呈现“与汉相类”的西南少数民族,实现了认同的审美转变,从而调整视觉建构方式,使之适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审美体验。文学建构的调整“既能识别文化差异,又不会强化刻板印象,既能保护文化少数群体不受刻板印象威胁的负面影响,又能为文化少数民族赋予权力。”[23](P.299)西南少数民族文化因“与汉同”而被纳入主流话语体系,被形塑为可视的“西南少数民族形象”,竹枝词的叙事动力突破了异文化之间习俗等隔阂因素,既在视觉表述西南少数民族“同汉人”的过程中识别了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又为“礼失求诸野”的视觉建构西南族群提供了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合法性。书写者通过仪式场域与“可视的语言”在竹枝词中生成让接受者更容易形成民族图像,显得更具体生动和更易区分识别。继而书写者对新奇、陌生的西南少数民族的探索欲望和书写技巧展现,更深层次化的是“中华认同”的心理诉求,力图通过视觉表述建构西南少数民族“与汉相类”的审美形象,以此来突破异文化交流中的既定印象。因其处于中心与边缘动态的弹性关系中,书写者需冲破和超越历史书写中的刻板印象。视觉建构模式是一种内在认同的同一结构,通过竹枝词的空间叙事将内在的心理图像结构以民族图像形式呈现,其深层的叙事动力是自觉的自我身份、民族、文化、审美、国家的认同合力作用,排除了一些妨碍互相理解的观念,最终呈现为“原本于汉”的叙事认同,内在的文化记忆为群体间更好地交融提供了条件,也为身份建构提供了认同的合法化。
竹枝词还原了书写者所看到的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原图,西南少数民族形象是书写者的情感共同话语建构出来的民族认同,“我们要加以分析的艺术作品不仅具有象征性,而且其生产的根源不在诗人的个人无意识,而在无意识的神话领域之中。”[24](P.99)这意味着通过分析竹枝词的图像空间呈现方式,寻绎出西南少数民族形象为书写者所属社会群体的总体想象物。书写者身负地域文化体验与文学体验两重身份,展现了在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空间中“在场的书写者”与心灵跨界“缺席的西南民族”的对话关系。书写者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视觉表述消解了异文化碰撞中的族群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既有的知识边界,在编译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符码过程中,逐渐明晰“自我与他者”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在中国西南这个特定的区域内,……拥有悠久的历史和足以让人惊叹的文化,他们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各种形式的交往,形成种种联系,体现出极其生动的民族关系画卷,丰富着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史内容。”[25](P.6)竹枝词中极其生动的西南少数民族图像空间,源于“每种文化都会形成一种‘凝聚性结构’,凝聚性结构可以构成被再次辨认的模式,从而被当作共同的‘文化’元素得到认同”[26](P.6-7)。正因为书写者借由主流话语的竹枝词来书写西南族群,从关注西南少数民族到对之文化的“同化”破译,继而分类识别到视觉表述使之图像化后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文化符码,再而是在词下加详注的体例重建知识体系,最终深化成认同建构的文化符码。文学体验的视觉真实不同于历史书写的刻板印象,它是以具体文化情境中的视觉语言来呈现西南少数民族,而拓展知识边界和文学探寻是一种文化记忆与自我身份认同的“共情”糅合,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凝聚性结构即竹枝词中形成的图像空间叙事具有建构认同的总体功能,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勾连。
余论
竹枝词的图像空间呈现跨媒介叙事特性的西南少数民族视觉形象,形成了完整的视语符号体系,为认同提供了深层次文化基础。竹枝词的仪式场域与视觉语言深化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同源性,化解了在西南少数民族生活原型与文学形象之间间距产生的语象转化问题。至此,可拓展出更深入的思考:一是西南少数民族形象作为图像媒介具有了解码文化记忆的象征作用。从竹枝词中西南少数民族图像空间的可视化程度来看,完整的文化符码系统体现了主流话语对西南少数民族的认同过程。视觉表述的内容从地域空间、仪式场域、形貌服饰、生活细节拓展至民族心理等全知视域的演进,将文化体验的视觉真实解码并编码转译为文学体验的语言真实,这是一个双向共生互识建构认同的过程。“可视的语言”建构了凝聚力更强的西南少数民族形象,竹枝词的西南少数民族图像空间体现了形象能够实现主体性交流的媒介作用,与“西南夷”的知识边界合力建构了多元文化并存、包容族群差异的西南少数民族形象,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路径的聚合式演进。二是竹枝词的西南少数民族图像空间展现了叙事动力是认同的根源。书写者创造性地在竹枝词中建构了对西南少数民族视觉表述的多种形式,这不仅是站位国家行为层面的宏观认知,也是拓展文学疆域获取新知的自我身份认同诉求。一整套视觉语言编码建构的西南少数民族形象系统随着文化符码的完善而完整,通过空间叙事与文化空间、社会结构的互动将西南少数民族形象纳入主流话语的知识体系中,其续发性表现为具象了民族群体间可对话的认同根源。认同的根源促成民族群体传递情感、思想、心态且强化了具有共同族源的集体记忆,也吸引身份共同的族群融入包容性强的文化空间,这符合中华多民族文学文化共同体关系的研究,即带有“认同”“同化”被注视者文化的倾向。破除了影响族群之间交流的某些固定思维,增进多民族间的互识与对话。
注释:
①完形心理学术语,格式塔心理学派认为审美主体的心理结构具有通过视觉思维将外在对象塑形为完整形象的功能。
②表1“滇地”“黔地”引文出处参看丘良任编《中华竹枝词全编》第7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161,140,162,105,151,48,68,39,10页。“巴蜀”引文出处参看丘良任编《中华竹枝词全编》第6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547,531,577页。
③表2引文出处参看丘良任编《中华竹枝词全编》第7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62,67,73,40,22页。
④法国学者保罗·利科在《从文本到行动》中讨论了想象理论,总结出在注视者与被注视者之间的交流存在一定间距。
⑤表3引文出处参看丘良任编《中华竹枝词全编》第7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129页,第73页,第104页,第10页,第20页,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