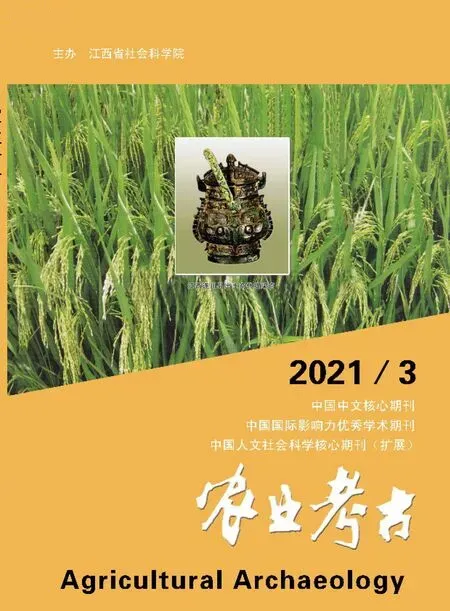试论明代畿辅水利营田的首次实践*
——以丰润、玉田县南兵营田为中心的考察
2021-12-14张汉青肖立军
张汉青 肖立军
万历十二年至十四年间,明廷首次在京畿地区开展水利营田活动。其中丰润、玉田县的南兵营田开发最早,规模最大,且取得了一定的实绩。其军队营田的经营方式为此后的水利营田活动所继承,并留下了一定的教训。目前学界有关明代畿辅水利营田的研究成果颇丰①,但尚未关注到丰润、玉田县的南兵营田,本文拟对相关问题略加考察。
一、明代畿辅水利营田的兴起
北京东部地区河网密布,地势平坦,具备开发水田的自然条件。隆庆年间,一些地区已开始种植水稻,如丰润县天宫寺附近“有水田数十顷,收稻倍利,宛然南方景界”[1](卷十二《古迹》,P494)。万历初年,给事中徐贞明考察畿辅州县,倡议开发水田,但未能施行[2](卷四四,P994-995)。
直至万历十余年间,明代官方才开始大规模开发畿辅水田。据《明史·河渠志》记载,徐贞明提出开发畿辅水田之议后,蓟州道兵备副使顾养谦、顺天巡抚张国彦最先在丰润、玉田二县开垦水田,但未载明起始时间[3](卷八八《志第六十四·河渠六》,P2170)。据万历十三年十一月蓟辽总督王一鹗所上《议复遵化辎重营疏》称,“今丰、玉二县,兵一千六百名,把耒耕锄,已历一岁”[4](卷一《议复遵化辎重营疏》),可见丰、玉两县的水利营田应开始于万历十二年十一月左右。
营田兴起之初,顾养谦、张国彦等人考虑到多方面因素,并未采取民屯或明代正规卫所军屯的经营方式:
第以创始之时,因北人不曾习水利,势不得不召南人以导之。欲南人尽力也,势不得不悬重饷以待之。及南人之云集,而虞其无统也,又不得不勒之以兵,而制为千、把、百总以约束之。军饷既无正额也,又不得不借支官银,而计一岁之所入以偿之[4](卷一《议复遵化辎重营疏》)。
结合相关材料可知:其一,水田中的生产者属于募兵,主要来自浙江金华府东阳、义乌等地的“田家子”[4](卷一《议复遵化辎重营疏》),不属隶于军籍的卫所屯军。其二,领导南兵的军官为千总、把总、百总等省镇营兵系统的基层军官,而非卫所系统的指挥、千、百户等武官。其三,治田南兵皆支军饷,而其军饷系官方临时挪借。其四,水利营田的收获全部缴纳入官以抵补军饷。综言之,丰玉营田的经营方式更类似于明中后期九边军镇兴起的镇戍部队营田②。
鉴于试点工作颇有成效,明廷任命徐贞明为尚宝司司丞,令其“遍历郊关,与抚按司道讲求疏浚潴蓄之法”[2](卷一五九,P2924-2925)。同年九月,徐贞明升任监察御史“领垦田使”,所上水利营田七策皆被采纳[2](卷一六五,P3000),整个京畿地区开始组织水利营田活动。
丰润、玉田县开展营田期间并非一帆风顺,起初开垦水田之令下达给南兵后,军士“大噪”,险些出现哗变。其原因在于军饷标准的降低:“南人之应募而耕者,原有慕台兵之重饷而来也,台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田兵月饷一两二钱”[4](卷一《议复遵化辎重营疏》),守台兵饷多,营田兵饷少,南兵自然不愿开种水田。之后蓟镇南兵营参将朱先稳定士卒,营田才得以顺利开展[5](P663)。另外,营田之初所借支的银两不够一年军饷支用。而“司农惜小费而忽大计,致田卒之纷纷”[6](卷四《答张弘轩巡抚》,P147),说明户部也未再拨发新的款项。至年底统计时,已欠发南兵八月至十二月共六个月(包括闰九月)的军饷[4](卷一《议复遵化辎重营疏》)。
万历十三年年底,“丰润、玉田二县原招募官兵一千六百三十五员名,共垦成水田三万二千亩,内种过熟田二万六千四十余亩”。在“亢旱失种、淫潦被淹、冰雹致损”的情况下,仍收获稻米26605石、稻草133025束,且指导当地百姓开发的水田中也收获了稻米23450石[4](卷一《议复遵化辎重营疏》)。营田收获全部归官方所有,本应用作抵还借支库银,但 “因各兵月饷久缺”,只能将其中稻米10261.57石用于发放闰九月、十月兵饷,余16343.43石留作下年种粮,稻草则“给各兵喂牛并盖营房之用”[4](卷一《议复遵化辎重营疏》)。虽然营田收不抵支,但对于当地水田的开发仍具有开创意义,所谓“自来开荒田者必不惜费于初年,而后可以遗厚利于久远”[4](卷一《议复遵化辎重营疏》)。
二、丰润、玉田县南兵营田经营方式的调整
丰润、玉田县的治田南兵为新增募兵,不在正规部队序列之内,无固定的军饷来源。为解决军饷问题,部分大臣提议复设此前裁撤的蓟镇遵化辎重营,将南兵附入该营,令其继续垦种丰、玉二县水田。围绕这一观点,朝廷中出现争论。
支持者以大学士申时行、总督王一鹗等人为代表。其认为:首先,田兵“苦于饷无所出”,若附入遵化辎重营,则属蓟镇镇戍部队序列,兵饷由该镇提供,不必再各处挪借,所谓“兵有所归,饷有所出”[7](卷三九三《答张弘轩抚台》,P4246)。其次,开垦田地中还有余田3840亩,“若留待新军至日领种,则工夫间断,必致荒芜”[4](卷一《议复遵化辎重营疏》),而遵化辎重营尚有未遣散的余兵1123名,可直接调拨余兵进行耕种。
反对者以大学士王家屏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首先,招募南兵的本意是为指导北方人开垦水田,而南兵附入正规部队后,需担负军事任务,“彼已为兵,谁复训农?”其次,仅令千余名辎重营官兵耕种水田,“垦田有限,则收获亦有限,公帑何时可偿也?”[7](卷三九三《答张弘轩抚台》,P4246)。
万历十三年十二月,神宗最终同意了王一鹗等人的意见,“复蓟镇遵化辎重营及其将领等官”[2](卷一六九,P3055)。至万历十四年四月,“将丰润、玉田二县田兵与遵化余兵复设辎重,并为一营”[2](卷一七 三,P3180-3181)。
据总督王一鹗《议复遵化辎重营疏》,田兵附入辎重营后,丰润、玉田县水利营田的经营方式可归纳如下:
其一,丰、玉二县水田中的生产者为附入遵化辎重营的南兵,其所担负任务:“平时听自相耕种,有警之际,或派守信地,或推挽刍粮,临时听本镇从宜调遣,耕战两兼。”[4](卷一《议复遵化辎重营疏》)其二,辎重营官兵的军饷与冬衣布花等项仍官方提供。但南兵月饷一两二钱,辎重营月饷平均五钱七分,为抵补差额,将开垦土地拨给南兵,每人20亩“永为己业”,亩征稻米1石,余归军士所有[4](卷一《议复遵化辎重营疏》)。其三,增设主管将官,属蓟镇省镇营兵系统。合营之后,遵化辎重营的营将为游击一员,设中军一员掌传宣号令,其下千总二员分统南兵与余兵,每员千总之下各设把总四员管理军士,南兵把总统兵704名左右,余兵把总统兵561名左右。
南兵附入辎重营后,每人领种定额分地、缴纳定额子粒的经营方式类似于卫所屯田。但其规定亩征子粒1石,上一年水田的亩产量才1.02石,所谓的租额与全部征收区别并不大。同时遵化辎重营为镇戍部队,也需肩负作战任务,故其经营方式与上一年相比,更趋近于镇戍部队营田。
三、畿辅水利营田的裁撤
万历十四年三月,京畿水利营田“续所报开垦成熟田数则已三万九千余亩”[2](卷一七二,P3133)。据前引,丰玉营田中熟田26040余亩,占总数近67%,可见所开垦水田主要分布在丰润、玉田二县。然畿辅水利营田的开展招致许多非议,因营田杂处民间,反对者“不曰南兵侵民舍,则曰南兵夺民田,不曰此兵当亟散,则曰此田当属民”[4](卷一《议复遵化辎重营疏》)。所谓占民田、侵民舍等只是北方缙绅的借口,因内地民田多为豪强所占,若连片开垦水田,必然会侵及地方豪强的利益,这一点前辈学者已经指出③。不久后,监察御史王之栋上疏提出畿辅水利营田有十二不可,神宗听信其言,下令停罢畿辅水利营田[2](卷一七二,P3132-3133)。
丰玉营田停罢后要面临如何安置南兵的问题。但南兵本为重饷而来,一时遣散难免招致非议甚至引起哗变,申时行提醒当地官员遣散南兵时要做到“可渐而不可骤,隐有散之之实而无示以散之之名”[6](卷四《答蹇理菴巡抚》,P161)。万历十四年八月,总督王一鹗上《条陈蓟镇未尽事宜疏》,对遣散治田南兵进行规划:
首先,治田南兵分别安排:“其年力精强者编发边台;其孱弱思归者资送回南;其愿留耕种者悉归丰润、玉田二县入籍,责成该县俱与土民一例给田,止令纳租,不与月饷,盖不复为兵矣”;其次,遵化辎重营保留,以各省直清勾解到新军等补充缺额,南兵遗下水田由余兵一体耕种[4](卷五《条陈蓟镇未尽事宜疏》)。
之后神宗同意其请,下令遣散治田南兵[2](卷一七七,P3290)。然而还是引发了南兵哗变,参将朱先“单车行田,造图册,开诚训告,壮者兵,老弱给道里费,耕者籍农,哗止”[5](P662)。万历十四年十月,明廷下令“开垦水田借过丰润、玉田、遵化三县库银一万五千两,又蓟镇积贮银一万五千两,准与开豁,免其补还”[2](卷一七九,P3345),水田的开发成本终未能以收入抵补。
虽然万历十四年间,明廷已中止畿辅水田的开发。不过丰润、玉田两县的水田并未全部荒废,十余年后仍称“至今耕种,尚可按籍而考”[8](卷九一,第60册P3403),但水田多为豪强占种,当地平民并不能得利,如万历二十九年十月神宗的诏令所称:“近京涿州、房山、良乡、天津、玉田、丰润及山东、山西处渐开水田往往既垦成熟,被势豪及经管地主混占告夺”[2](卷三六四,第P6814)。
四、结语
综合上文,总结如下:
第一,丰润、玉田县南兵营田为明代首次畿辅水利营田活动的试点,其规模最大,取得了开垦熟田26040余亩,收获稻米26605石、稻草133025束的成效。南兵还帮助百姓开垦了部分水田,对于该地区引种水稻,开发水田具有开创意义。而徐贞明所组织开发的其他地区水田则“未匝岁,竟无绩可叙”[9](卷十二,P254)。
丰、玉二县开垦水田借鉴了九边军镇作战部队营田的经营方式,取得了一定的实效。但仍存在一定问题:“一则给饷太厚,二则杂处民间”[6](卷四《答贾春宇兵侍》,P160)。意即招募饷额极高的南兵开垦水田,成本太高,以致收不抵支。另外,水田位于内地,会侵及地方豪强的利益。明代再次开发畿辅水田时多能吸取这些经验教训,如后来汪应蛟、董应举等人主持的天津水利营田活动中,均采用了镇戍部队营田的经营方式,但所用兵力为天津海防左、右营(春、秋班军营)、海防营等当地驻军,未再新募南兵,降低了成本;所开垦土地,在天津葛沽等人烟稀少之处,与地方豪强利益甚少瓜葛。后几次畿辅水利营田活动的持续时间更长,所取得成果更显著,与此当不无关系。
第二,营田初兴时,南兵因军饷标准降低,违抗军令。营田裁撤时,又因安置不妥,南兵聚众哗变。这并非个案,万历年间蓟镇南兵群体中多次出现类似事件,如十三年,南兵擅自殴辱克扣军饷的军官叶伯明[6](卷四《答王舂陵总督》,P145-146);十五年八月,“南兵守台者以减粮致变”,副总兵朱先“擒首恶吴公泰等四人,闻于朝,斩之”[10](卷一八二,P797);二十三年,因欠饷“南兵鼓噪”,总兵王保大肆屠杀南兵[2](卷二九一,P5392)。从这一系列事件中不难发现,南兵哗变多与军饷相关。蓟镇南兵哗变的事件屡屡出现,既有继任者不得其人、军纪败坏等原因,更多的还在于朝廷难以一直供应南兵的厚饷,或降低军饷标准,或欠饷不发,引起南兵不满。总督王一鹗即指出,“有功蓟镇者,固南营之台兵,而有蠹于蓟镇之饷者,亦南营冗役也”[2](卷一八二,P3403)。
注释:
①参见郑克晟《关于明代天津的水田》,载《南开史学》1980年第1期;蒋超 《明清时期天津的水利营田》,载《农业考古》1991年第3期;李成燕《清代雍正时期的京畿水利营田》,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8-73页;张磊《天津农业研究(1368-1840)》,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李鹏飞《汪应蛟天津兵屯研究》,载《农业考古》2014年第6期;李鹏飞《董应举天津兵屯研究》,载《农业考古》2015年第3期。其他有关明代畿辅水利营田的研究成果,恕不一一胪列。
②明中后期,九边军镇为补救卫所军屯废弛曾开展营田,其主要特点:第一,劳动者为作战部队,屯守不分。第二,营田者以集体受田。第三,营田收获全部入官。第四,营田军士的身份属于‘兵’,而非‘军’,其生产工具及军饷等均由官方提供。第五,营田收获专备修边支给。参见王毓铨《明代的军屯》,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4-9页。
③参见郑克晟《关于明代天津的水田》,载《南开史学》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