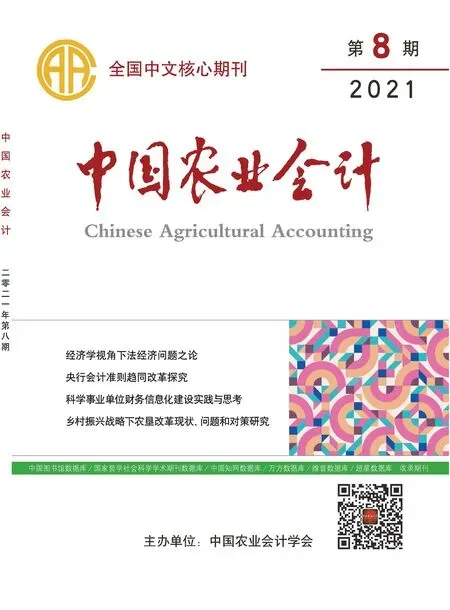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市民化灰色预期及化解
2021-12-12刘歆立
刘歆立 靳 戈 陈 娱
城镇化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载体与基本趋向。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发达国家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70%以上,美国早在2000年农村人口比重就已减至5.3%。在我国,2018年底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9.58%,全国人户分离人口(即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籍地半年以上的人口)2.86亿人,其中流动人口2.41亿人。不过考虑到城镇化达到一定阈值后,由于各种自然的社会因素叠加而必然放缓速度、停顿甚至出现逆向负增长,我国城镇化要达到2021年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5%的目标仍然任重而道远。其中农民工对市民化的灰色预期,是一个重要而又容易被忽略的影响城镇化发展的变量。本文拟探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灰色预期的影响因素及其化解。
一、加剧农民工市民化灰色预期的影响因素
党的十九大明确做出了我国经济新常态的科学预期,并概括出其基本特征是经济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变。近两年来,整个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际交往受限,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这些不利方面投射到我国,则是经济恢复基础尚不牢固,投资增长后劲不足,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困难较多,稳就业压力较大。以上影响因素对城市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能力造成直接冲击,使得具有市民化意愿的农民对进城后生活质量、社会融入、社会保障和社会适应等愿景产生了灰色预期。
(一)习得性无助心理效应强化了农民工市民化灰色预期
心理学实验表明,经过训练的狗能够学会跨越屏障或躲闪实验者加于它的定时电击。但是,当遭受不可预期且不可控制的多次电击之后,它即使有机会逃离电击,也无所适从与坐以待毙,随之会出现沮丧、压抑、缺少主动性等消极心理状态。这种由于无力预期来自外部伤害而产生的无助感被称为习得性无助效应。类似地,人如果获致这种习得性无助后也会陷入绝望、悲哀等负面情绪的阴影中,对未来发展前景因预期灰色而采取消极无为的行动策略。不期而至的外在经济波动(例如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就业机会减少、生活成本陡升等经济伤害,也会在抗经济打击能力偏弱的农民工身上产生习得性无助效应,本来有着市民化意愿的农民甚至会迟延或取消这些打算。
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研究,二代农业流动人口市民化水平总体偏低,拖家带口在外打工几十年最后仍选择返乡生活而非“市民化”的农民家庭不在少数,这同“流动家庭”在外漂泊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而产生灰色预期直接相关。而我们近期的相关调查也表明,大约有26%的农民工家庭因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黑天鹅事件”影响,取消了进城购房到城市生活的发展计划。
(二) 当前城市化阶段性特点加剧了农民工市民化的灰色预期
研究表明,2013年起我国城市发展出现了“三个反超”和“一个分化”的阶段性特点:大城市对中小城市的反超,消费型城市对投资型城市的反超,服务型城市对工业型城市的反超。房地产价格波动出现了由大中小城市“同涨同跌”变成了“大城市大涨,中城市小涨,小城市基本涨”的分化格局。这“三个反超”表明,当前城市由以投资和工业为基本特征的中小城市向以服务和消费为基本特征的大城市转变,农民城市化路径由以原初的从农村走向以工厂为主的工业化中小城市,变为当前的从农村直接跨越到以服务和消费为主的大城市。相对于之前较低的制造业就业门槛与中小城市市民化流向,当前农民市民化的门槛、成本付出、进城风险无形地被提高了,例如购房这一刚性需求就让进城农民望而生畏,使他们对市民化难以产生积极的心理预期。
另外,2019年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的比值是1.4,世界平均是2.0,发达国家是3.4,这种“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特征,直接导致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民工进城后生活成本增加与生活满意度降低,最终导致城市吸引力对之减弱。例如还处于工业化阶段的城市,空气质量差、接送孩子上学麻烦和居住交通拥挤等城市问题,使许多习惯了乡村生活方式的农民产生恐惧、厌恶未来的城市生活环境与生活方式等不良心理预期。
(三)社会融合困难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着明显不利影响
现在的农民工市民化不是过去“农转非”式户籍登记方式的简单改变,而是要使他们具备对城市深度认同而萌生永久居住意愿的社会经济条件,能够对平等享有城市公共服务、就业发展前景、家庭稳定收入等生活愿景有合理预期,减少对可能受到社会排斥、权利受侵和社会冲突等市民化风险的灰色预期。研究表明,相对稀薄的社会网络、城市的陌生感和社会歧视目光,阻碍了农民从心理上文化上转向市民化的积极性,周工作时间、风俗习惯、卫生习惯等,也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存在一些负向影响。
在当前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大背景下,农民家庭市民化决策选择通常会参照所熟悉与信任的同群者的行为决策。这是因为我国社会至今仍保留着“熟人社会”的大量痕迹,在外来海量信息真假难辨与不可靠的情形下,农民家庭出于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决策潜在风险而倾向于认可熟人传递的相关信息,使自身决策与邻近相似个体呈现趋同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同群者”可能出于怕落埋怨等自我保护心理而过于言词谨慎,可能夸大城市融入困难带来的生活麻烦与隐患。因而,这种“同伴效应”也会直接影响农民在新冠肺炎疫情尚未缓解下的市民化灰色预期。
二、减弱农民市民化灰色预期的化解措施
一是立足新发展格局优化市民化发展环境,使农民形成积极的市民化预期。面对前所未有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世界经济深度衰退等多重冲击,2020年我国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城镇新增就业1 186万人,1亿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目标顺利实现,全国城乡区域发展格局不断优化,等等。同时,中央又提出了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有效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使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70%等目标。要广泛宣传教育这些发展成就与国家“十四五”规划,使之成为提振农民市民化信心与形成积极预期的强心剂,使农民市民化成为当前畅通国内大循环、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高水平动态平衡的有力引擎。
需要强调的是,单靠改变宣传教育和“农转非”的户籍登记方式,不能完全消除农民市民化灰色预期,地方政府还要采取切实措施优化农民市民化发展环境。例如,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大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不良风气治理”,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正值结婚年龄高峰期,进城买房是农村待婚青年(农村“剩男”居多)成家立业的前提条件,坊间流传的“农村丈母娘踹动城市房地产”的说法在许多地方越来越成为现实。然而,为婚购房如果完全由农民承担其家庭负担会很重。可见,农村婚姻市场挤压,并不能转化为农民市民化的有效动力。所以,地方政府宜探索合理的农民市民化成本分摊机制,对于那些有强烈购房刚需的农民家庭,进行必要的政策帮扶、资金补贴等。
二是加快体现共享理念的户籍制度深层改革,缩小城市内部不同群体间的福利差异。通过分析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发现农业转移人口的人力资本、职业层级、经济收入、公共服务、融入情况和居留意愿与流入城市的发展规模与行政级别成正比,收入低、就业难、房价高和子女教育问题是农民市民化灰色预期的重要成因,地级及以上市的农民市民化难度大而发展后劲不足。县城及中心城镇必然成为当前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农民就近市民化的目标靶向地,因而国家要积极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机制,以有力反制“三个反超”和“一个分化”的阶段性特点带来的负面作用:合理安排中小城市产业布局,增加行政资源供给,优化就业环境等;地方政府要同步跟进落实国家提出的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规划,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等,采取切实措施有效提高农民市民化后预期收益。同时,还要将农民市民化工作重心由落户转向基本公共服务的无差别覆盖,从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新市民”城市生活质量入手,把他们寻求稳定工作的成本降下来,提升农民流动家庭城市生活满意度。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已构成市民化的主体,家庭市民化成为市民化的关键,因而,要想实现2021年城市化65%的目标,必须解除土地、户籍、社会保障、收入、房价等影响因素对农民市民化的实际影响,进一步通过政府赋权、市场赋利与社会赋能的协同联动提高新市民家庭应对城镇化风险的能力,从而有效对冲市场的非均衡性、地方政策的不连贯及大环境的不确定性等带来的农民市民化灰色预期。
三是营造开放包容的市民化发展氛围,增进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积极预期。农业转移人口主观社会融合受迁移模式、社会网络、生计资本、年龄特征和外出经历等因素综合影响。研究表明,宏观上,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能显著地增强融入、削弱隔离,淡化户籍制度造成的融入障碍;中观上,迁入城市加强社会交往和积极参加组织活动、改善住房和提高收入,能够有效提高融入程度;微观上,近距离、长时段和家庭化迁移的流动人口主观融入程度较高,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有助于流动人口削弱主观隔离,更好地融入流入地。为此,地方政府应促进市民化人口客观融合并使其与主观融合相匹配,改变以农民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的单向思维,真正地缩小城市内部不同群体间的福利差异,有效减弱农业转移人口或“新市民”同老市民的距离感,增加他们对城市的深度融入感与永久居住的意愿,切不可使农业转移人口处于身子进入城市新家,而脑子依然留在农村老家的“半城市化”或“伪城市化”状态,真正实现农民从主观“愿意”市民化到客观“能够”市民化的社会融合。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我国农民市民化大量出现了“一家两户”现象:部分青年农民夫妻一方带着子女入户城镇,另一方户口仍保留在农村;新一代青年农民工安家入户城镇生活,老一代父母留守农村守护着其农村户籍拥有的各项权益。之所以出现这种另类的“半城市化”现象实际上不难理解,一方面,农村既有利益、职业周期风险、故土情结与风险规避等促成了保留农村户口,反映了安全第一的社会理性和家庭利益优化的经济理性的中国式城市化逻辑。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城乡关系已从城市中心主义向城乡一体化转变,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农村开始拥有日益彰显的比较优势。因而,对这种“一家两户”的二重化户籍登记现象,宜采取包容发展的方式。